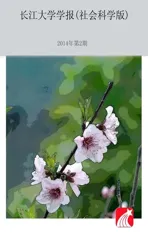《红高粱》叙事情境及其效果探析
2014-03-26梁晓安
梁晓安
(江苏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镇江212013)
小说《红高粱》是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的第一部。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成名作品,《红高粱》描写了抗日战争期间“我”的祖先在高密东北乡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人生故事。《红高粱》曾被译成近二十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另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获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
《红高粱》小说的叙述视角极具特色,出彩的叙述使“我”的高密祖先身上敢爱敢恨的血性展现得淋漓尽致。本文应用叙事情境相关理论,从叙事方式、叙事人物及叙事聚焦三个角度对小说的叙事及其效果进行分析。
一、《红高粱》的叙事方式
作为叙事情境的构成要素之一,叙事方式是指叙述故事的角度即“谁在叙述”。 叙事情境相关理论认为,作品中的叙事方式有两类:“讲述”和“展示”。“讲述”是叙述者置身事外地独立叙述,“展示”是叙述者隐藏在故事中人物和事件的背后,使读者几乎无法感知他的存在[1](P146)。莫言的《红高粱》中,“我”对祖先们传奇人生的评述和情感抒发属于典型的“讲述”;小说中以“我父亲”儿时的口吻讲述的故事和“我奶奶”对当年故事的追述属于“展示”。作者并不试图将自己的感受和思考传递给读者,而是由读者通过阅读去感悟。
“有人说这个放羊的男孩就是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2](P2)小说中这一段采用的是典型的“讲述”方式。表达对“我”是不是那个放羊的男孩以及“我”对高密的复杂感情。作者丝毫没有隐藏叙事者对这段文字走向的影响,甚至可以说作者有意通过“讲述”对读者进行暗示和引导,使读者强烈地感受到叙事者的意向,同时在阅读时自然而然地将叙事者的情感和小说的主旨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死吗?我就要死了吗?再也见不到这天,这地,这高粱,这儿子,这正在带兵打仗的情人?枪声响的那么遥远,一切都隔着一层厚重的烟雾。豆官!豆官!我的儿,你来帮娘一把,你拉住娘,娘不想死,天哪!天……[2](P77)”这段文字描写的是“奶奶”死前的心中所想。和上段不同,我们只能发现一个充当“反映者”的人物——“奶奶”。此段运用限知视角,写出“奶奶”死前对人生的感受。作者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和评论透过文字传递给读者,但“奶奶”的切身感受都能够使读者直接感受“反映者”的意思。通过“反映者”的展示拉近了读者和主人公的距离,使读者透过生动的叙述深深感受到“奶奶”对生命的眷恋,对儿子、情人以及这片红色高粱地的深深眷恋与不舍。
由此可见,《红高粱》并不只运用一种叙事方式,小说中“叙述者”方式和“反映者”方式交叉出现。莫言使“我父亲”感性的视角和“我”理性的视角相结合,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相互交错,从而打破了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时间阻隔,叙述效果更好。
二、《红高粱》的叙事人称
叙事人称是叙事情境的第二个构成要素。《叙事学导论》将叙事人称大致分为了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第一人称叙述者就生活在这个艺术世界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第三人称叙述者尽管也可以自称我,但却是置身于艺术世界之外的。[1](P169)这样的分类所获得的文体效果和“展示”、“讲述”的叙事方式有些相似。《红高粱》中叙述人称的分类并不同于前面的分类,一开头就是“我奶奶”、“我爷爷”,是第一人称,置身于虚构的世界之外;“父亲”、“罗汉大爷”等第三人称叙事则置身于虚构的世界之内。
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奶奶披着夹袄,送他们到村头。余司令说:‘立住吧。’奶奶就立住了。奶奶对我父亲说:‘豆官,听你干爹的话。’父亲没吱声,他看着奶奶高大的身躯,嗅着奶奶的夹袄里散出的热烘烘的香味,突然感到凉气逼人,他打了一个战。肚子咕噜噜响一阵。[2](P1)
此段是小说的开头。作者使用了第一人称“我父亲”,开门见山,有效地交待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故事情境等等。这样的叙述体现不了任何第一人称所具有的“性格化”意义,却有了一般第三人称叙述的特色:居高临下,俯览全局。
“父亲被迷雾扰乱的心头亮起了一盏四块玻璃插成的罩子灯,洋油烟子从罩子灯上盖的铁皮、钻眼的铁皮上钻出来……父亲和罗汉大爷披着大蓑衣,坐在罩子灯旁,听着河水的低沉呜咽——非常低沉的呜咽。[2](P6)”这段文字描写了“我父亲”回忆和“罗汉大爷”一同捉螃蟹的往事。父亲作为第三人称叙述却身处作者虚构的世界之内。“父亲”的回忆可以说是自我体验的总结。当叙事人称在“我”、“我父亲”和“我奶奶”等之间变换时,不同叙事人的内心世界表达得更为直接,这样比简单的第一人称视角要丰富和开阔得多,充分体现了创新。
三、《红高粱》的叙事聚焦
叙事聚焦是叙事情境的第三个构成要素。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奈特提出的叙事聚焦这个概念基本涵盖了传统的叙事视角、叙事视点的内涵。
《红高粱》小说以“我”说、“父亲”看为主,文中穿插了 “罗汉大爷”、“奶奶”等人物视角。尽管“看”的人不尽相同,作为后代的“我”在对历史的讲述过程多采取了全知视角,因而小说绝大部分内容采取了外在式聚焦。
“天赐我情人,天赐我儿子,天赐我财富,天赐我三十年红高粱般充实的生活。天,你既然给了我,就不要再收回,你宽恕了我吧,你放了我吧!天,你认为我有罪吗?你认为我跟一个麻风病人同枕交颈,生出一窝癞皮烂肉的魔鬼,使这个美丽的世界污秽不堪是对还是错?[2](P77~78)”这段心理描写是“奶奶”死前对自己人生的回顾。和《叙事学导论》分析的一样,并非所有的心理描写都属于内在式聚焦,这段就属于全知外部聚焦。这里的关键在于区分聚焦者和聚焦对象。这段内心独白尽管多次提及“我”,但聚焦者仍然是故事之外的全知“我”,“奶奶”的心里描写仅仅是聚焦对象。因而,这段心里独白显然已经经过整理和归纳,而不是原生的心理状态。这段文字把“奶奶”对三十年富足的高粱地生活,对自己心中的美、浪漫和幸福的追求表达得很充分。同时,作者借“奶奶”的口,通过强有力的质问表达了对敢爱敢恨人生的追求和对人性真实的渴求这个小说的主旨。
总之,《红高粱》采用“作者叙事情境”——“编辑者全知类型”叙事情境,对小说中叙事方式、叙事人称及叙事聚焦这三个叙事情境基本要素进行了灵活多样和独具匠心的运用和恰到好处的转换,使人物形象得以真实丰满,小说主旨得以突显升华,体现了莫言独特的文体风格。
参考文献:
[1]罗钢.《叙事学导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2]莫言.《红高粱》[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