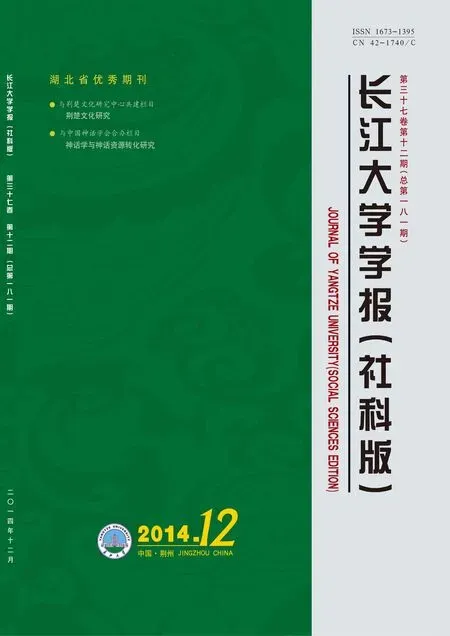教育学话语范式刍议
2014-03-25桑运福徐竟芳
桑运福 徐竟芳
(华侨大学 校长办公室,福建 泉州 362021)
受科学主义的影响,教育学在我国一直以学科范式存在,呈现出一种静态化的倾向,制定出一系列规则以实现对教育研究的控制,不利于教育学的发展。缘此,本文用话语范式取代学科范式,将教育学作为一种话语体系来考察,以期拓展教育学的时空,从而为教育问题的解决提供启发。
一、教育学话语范式的特点
教育学作为教育研究的理论形态与学科样式,是由一套专门概念(术语)、命题、范畴而构建起来的话语方式和体系。作为一套规范的话语体系,教育学包括话语范式内容、话语范式方式、话语范式价值取向等三个部分。其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的特点。
(一)教育学话语范式内容的特点
首先,话语范式内容的无人化。教育是把培养人作为主要内容。然而这种培养主要着眼点并非人的自主性和全面性,而是按照现代社会的需要,通过片面的传承社会文化、传递生产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增进人的知识和技能。它并不考虑这种知识和技能是否是人本身所必需的,也不考虑人的情感和需求。此外,以吴宗璜为首的“主客体关系学”研究课题组还将教育视为一种主客体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受教育者被视为有待影响和塑造的客体。这种教育学所强调的必然是对人的设计、加工和改造,统一化而非个性化。这种教育学是制器的教育学而非育才的教育学。
其次,话语范式内容的非生成性。教育学话语范式内容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个体由于内在的体验和感悟而产生的言说,这种话语范式内容是生成性的;另一个是受外在条件的影响而产生的言说,这种话语内容是非生成性的。因受外在条件的控制较多,我国教育学话语范式内容主要是一种非生成性的话语内容。这种话语范式内容并非来自教育和话语主体的需要,是一种非生成性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意识形态是教育学话语范式内容的风向标。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培养阶级斗争的意识和能力是教育学话语范式的内容;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为市场经济服务、教育产业化则成了教育学话语范式的内容。第二,西方教育理念的移植成为了我国教育学话语范式内容的源头活水。从本质主义到存在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每一次西方教育理念的移植都会在教育学中衍生出新的话语范式内容。然而,这种话语范式内容只是西方文化的产物,未必符合我国的教育现状。第三,逻辑性成为了教育学的唯一合法话语范式。教育学的话语范式主体在逻辑话语的影响下,理所当然的认为教育是一种科学的活动,教育具有自己的本质和规律。因此关于教育本质的各种逻辑推断顺理成章的作为一种合法的教育学话语范式内容得到传播。而一些关于教育的真实言说则往往因为其非逻辑性而成为非法的话语而被摒弃。
(二)教育学话语方式的特点
科学化。“教育是什么”是一种科学化的话语范式方式,说明话语主体已经将“教育“视为一种客观的、待认识的对象,并假定其存在永恒的本质和规律,这样就把教育学静态化了。然而教育是一种实践性和体验性极强的个体活动。由于个体的独特性,其在不同的境遇中体验必定不同,由此而产生的言说也应该是多样的、变化的。既有理性的逻辑推断也有感性的情感表达,更有信仰的狂热追求。惟其如此,才能丰富教育,丰富人的生命。
同质化。“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映射出了我国教育学话语方式的同质化。在当前的教育学话语范式方式中本质、规律、目的、意义等词汇成为衡量教育学话语水平高低的唯一指标。受这一指标的约束,教育学话语范式已经由个体关于教育的体验和感悟异化为空洞的整齐划一的口号。另一方面,主客体论和因素论作为一种话语方式时刻规训着教育学的言说,所有的学者都在教师、学生、教材及环境等孰客孰主的言说框架内争执不休。所有的话语主体都在为某个因素是否属于教育而高谈阔论。然而“没有声音区别的思想喧哗只是无意义的噪音,它无助于教育思想的繁荣,更无助于教育本身的发展。”[2]这种表面的无意义的争论恰恰证明了教育学话语范式方式的同质化。
(三)教育学话语范式价值取向的特点
教育学作为一种独特的话语体系不仅是对教育现实的表达,更是话语主体对教育的感受和要求的言说。在教育学话语范式中隐含着话语主体对教育的价值追求,这种内隐的价值追求就是教育学话语范式的价值取向。其具有以下特点:
工具化价值取向。无论是作为培养人的社会活动还是作为传递和保存人类经验、技术和文化的手段,“教育”在当前的教育学话语中都无法摆脱其工具的角色,教育被视为满足人类目的的条件。教育学更多关注的是教育要达到的目的而非教育本身。教育帮助人类实现其目的的能力成为衡量其合法性的主要指标。教育学话语主体对“教育”的这种界定使当前的教育学呈现出浓厚的工具化价值取向。
科学化价值取向。在上述关于“教育”的界定中潘懋元提到“本质属性”、王道俊提到“质的规定性”或“本质”、吴宗璜提到“根本特性”和“本质”。在这些话语主体的言说中教育学呈现出明显的科学化价值取向,他们将教育视为一个可认知的客体,努力探求其本质和规律,以求更好的控制和利用教育。
媚俗化价值取向。话语主体往往将教育学局限于当下的生活,而关于人的生活的批判、反思和超越被大部分话语主体忽视了。这种教育学以当下世俗的需求为目的,努力满足于世俗,教育学话语范式成为现实世俗的传声筒和风向标。这种教育学话语范式忽视了整个生命的需求,表现出媚俗化的病象,其所指导的教育必然是复制的而非超越的。
通过对教育学话语的内容、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当前的教育学是静态的、僵化的、近视的。它只局限于当下狭小的时空。然而,“教育乃是永恒的事业,教育需要指向所有的时间,即不仅仅指向现在和未来,还需要指向过去。当下必须指向未来,却总是植根于过去”。[3]
二、现代性对教育学话语范式的制约
当前的教育学是在现代化的境遇中诞生的,现代性中蕴藏着教育学问题产生的原因,同时也因其世俗主义、国家主义以及科学主义的三种价值观对教育学话语范式特质产生制约。这三种价值观衍生出各种异化的教育学话语范式,从而将教育学局限于狭窄而短暂的时空,进而设计出异化的教育制度和理念,生产出以现代性为主导的教育。
世俗主义的制约。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主义从人文主义与宗教主义的冲突中诞生,并日益成为一种独立的价值体系。它一边用理性主义对宗教主义进行除魅,一边用功利主义为人文主义呐喊。就这样,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一起催生了以功利主义为核心的世俗主义。它使人类放弃了对永恒的信仰和追求,转而在当下的世俗生活中寻求人生的意义。人逐渐沉迷于世俗的享乐,而忽视了对完整生命的追求,以至于日渐“委身于常人、沉陷于职能、淹没于物欲。”[4]受世俗主义的影响,教育学日益局限于现实生活,强调通过教育实现人的社会化,增强人类征服自然和追求感官物欲的能力。将当前的生活作为教育学的存在时空,而忽视生命的要求,无疑导致了教育学时空的萎缩。
国家主义的制约。我国学者朱新卓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指出:“现代教育被国家化以后,很快就被拴在经济的车轮上,成为富国强兵的国家战略中的一个‘棋子’。教育逐渐抛弃原始教育的神秘性和古代教育的神圣性而强调世俗性的需要,以实用性,即满足国家和个人生存的实际需要去换取自身存在的合法性。”[4]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国家主义使教育学沉湎于暂时的功利追求而忽视永恒的灵魂守望。在世俗的教育学话语范式中,教育只是富国强兵的工具,而非寻求人类生命意义、守望人类灵魂的途径。这种教育学固执于服务当下的价值追求而忽视了坚守传统和超越未来的时间向度。
科学主义的制约。科学主义向来强调合理性和必然性,本质和规律是其认识的逻辑。受科学主义的影响,教育学日益追求“体系化”和“结构化”。我国学者刘旭东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认为:教育学的“体系化”、“结构化”取向使教育学静态化、符号化,无以对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和生活做出令人满意的解读,更不要说去“指导”教育实践。此时它只倾心于如何使教育更“科学”,更能够符合某种“人工的逻辑”而不是教育本身的自然法则。[5]这种强调必然性的教育学强烈排斥信仰以及可能的意义,它摒弃了对教育可能性的信仰和追求,而是努力为教育设定严密的行动程序。这样的教育学仅仅是一套理论逻辑,而非对教育现实的鲜活表达。
三、科学构建教育学话语范式的对策
教育学由于局限于窄化而短暂的时空而使教育出现了种种问题。因此,拓展教育学的时空对当前教育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学者金生鈜认为:“天下是思考教育的最大的空间结构,还有尺度就是时间的尺度。站在公共福祉的角度思考教育的时间尺度是永恒。”[6]教育学作为教育的话语言说应与教育处于同一时空。此外,教育学也应在生活和生命中思考教育和人的独特关系。基于上述因素,本文将教育学的时空重新拓展界定为永恒时空。
生活与教育学话语范式。生活与教育学具有密切的联系。在时间上生活是教育学的源头,“教育学话语不是脱离教育生活与‘生活世界’的,它们与生活世界具有内在的同构性。没有教育生活与生活世界作为背景的教育学话语是无源之水,是没有鲜活生命力的话语。”[7]在空间上生活是教育学存在并不断更新的场所。教育学不应是一个固定的形而上的权力话语框架,而是一个生成性概念。它不断在生活的境遇中进行着对教育的反思,从而使教育更好的促进个体生活的幸福。在这种反思中教育学也完成了自身的更新。
生命与教育学话语范式。人的一生都在追求着更美好的生命存在、更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追求着自身生命存在的意义。这种追求,不是对确定的目标的实现,而是一种动力学的力量、策略性行为,是一种不断生成、不断发现、不断转化为现实、并且不断生成着新的希望、新的追求的过程。[8]这种无止境的追求使处于生活中的教育学总是难以安于现状,它不断的追问生活的可能性。而正是这种追问使教育可以帮助个体实现从现实的生活向可能的生命的转化,从而丰富和提升个体的生命。
构建教育学话语范式的永恒时空。从生活到生命并非一个短暂的时空,而是一个永恒的无限螺旋上升的存在。生命是生活的一种美好而又完整的可能。达到这种可能需要教育学不断批判和超越现实的生活。而这种可能性一旦实现,生命便转化为当下的生活。然而“人不是现成性而是生成性的存在者,人的本质内涵在于:他是些什么向来有待于他自己去是。”[4]人类这种永恒的生成性会促使当下的生活向可能的生命过渡。就这样生活和生命在个体的存在意境中构成了一个永恒时空,这既是人存在的时空也是教育学话语范式的时空。只有在这一时空中教育学才能扎根现实的生活,时刻获得话语源泉,并且时刻获得批判和超越教育的动力,从而不断的引导个体和教育向着更加美好和完整的生命前进。
参考文献:
[1]刘剑红,赵则玲.大众化语境下教育学话语的变革与话语范式转换[J].教育科学,2006(2).
[2]栗玉香.实现教育学话语根本性转换的途径[J].教育评论,2003(4).
[3]刘铁芳.从苏格拉底到杜威:教育的生活转向与现代教育的完成[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2).
[4]朱新卓.本真生存与教育[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6.
[5]刘旭东.教育学的困境与生机[J].教育研究,2005(11).
[6]金生鈜.无立场的教育学思维——关怀人间、人事、人心[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3).
[7]林美香.范式转换必须创新教育学话语[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1).
[8]李家成.关怀生命[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