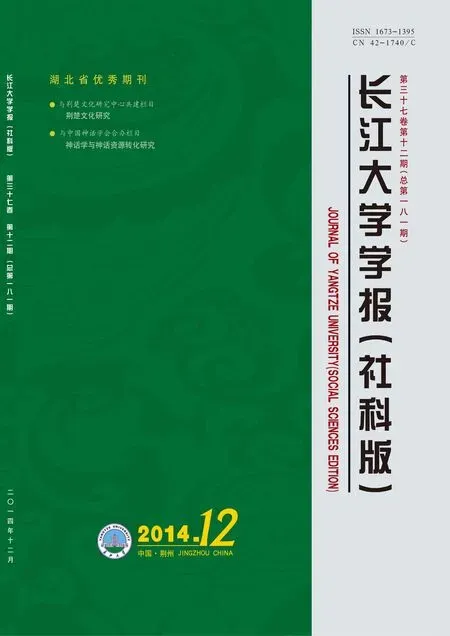招贴设计中的迹象论
2014-03-25陈璐
陈璐
(中南民族大学 美术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迹”是以工具作用于材料留下的踪痕,用来指绘画作品、绘画过程中产生的肌理、质感等因素,也指艺术家手工或半手工的操作痕迹;“象”是艺术作品的色彩和形象,指自然形象、艺术形象及其方式、形态。“迹与象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在可视的物象中,没有无迹的象,也没有无象的迹。在自然物象中,象是物的形状和体量;迹是物的质地和纹理。从理论上说,一切物象都不例外。”[1]从19世纪下半叶期开始,招贴就以独特的美的形式在众多宣传媒体中脱颖而出,吸引了愈来愈多极具才华的艺术家和设计家纷纷参与招贴设计。由于招贴兼有绘画和设计的特点,这些艺术家把绘画理论中的“迹象论”等多种表现形式和技法综合运用到招贴设计中,在作者创意的统帅之下,使招贴呈现出风格迥异、精彩纷呈的多元化发展格局。
一
迹之象就是形成“迹”的“象”的因素。中国艺术史的迹之象,首推具有中国特色的书法和绘画。中国书法讲究下笔的形状、形态、力道,每一笔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绘画更是如此,无论是线条粗细、下笔轻重、还是色彩浓淡都是以“迹”成“象”的。中国绘画史上有“误墨成蝇”和“败墙张素”的故事。“误墨成蝇”讲的是大画家曹不兴的一幅画作上的一只苍蝇被当时吴国君主孙权误认为是真的苍蝇,想赶走却发现是画出来的,孙权对此大加赞赏。原来曹不兴在作画时不小心将墨滴在了画上,他便根据墨点的形状改画成了一只苍蝇。“败墙张素”出自北宋沈括《梦溪笔谈》,现在已成为中国画术语,指壁痕如画,能让人根据墙壁上的裂痕创作成画。这两个典故形象说明了由“迹”成“象”的原理。中国的玉石雕刻艺术更是以“迹”成“象”的典范,很多玉器的造型是根据玉石本身的纹理分布而创作出来的。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翠玉白菜》就是以“迹”成“象”的典范。它是一整块半白半绿的翠玉,运用玉料自然的色彩分布雕刻而成:菜叶是极品翡翠独有的翠绿色,在绿色最浓之处还有两只虫,一只蝗虫和一只螽斯虫,而洁白的菜身更是与菜叶相映成趣。雕刻家运用天然玉石的迹设计了玉器的象,可谓技艺精湛。
日本平面设计大师新村则人在他设计里常用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素材作为设计的主体。在他保护渔业的环保海报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鱼的形态,再仔细观察会发现,鱼的身子是用树叶代替的,树叶已经枯萎,叶脉失去养分后茎脉分明突出,叶子的一角已经被虫吃掉了一部分,远远看来很像鱼的骨头。这幅招贴就是用树叶枯萎后本身的纹理和鱼的尾巴作迹,形成迹之象。另一幅招贴远看起来很象一朵美丽的蒲公英,认真观察后会发现其实是一根细细的鱼线上悬挂着无数个鱼钩,明显已经负荷过重。作者用了真实的鱼线和鱼钩作为这幅招贴的迹。这两幅招贴首先用视觉上的冲击吸引人们的注意,背景干净、明了,很容易将注意力直接放在了主体上,然后引导观赏者仔细观察图形,深刻地体会现在渔业面临的严峻问题,即过度捕捞导致物种灭绝、生态失衡。这样,用物体自身带有的“迹”巧妙构图设计,让主体充分突出,使得“象”达到了完美效果。
法国大师卡桑德拉将绘画和招贴设计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用绘画所产生的迹,形成招贴设计中的象。他用蜡纸和油漆喷雾器作为迹创作了极具个人风格特征的快速行驶火车的图像,所有的线条成放射状,蜡纸本身的特性和喷雾器等工具所能形成的迹让画面看起来金属感强烈,形成一种看起来真实的象。[2]招贴设计在表现的手法上和内容上都不仅仅局限在绘画上,拼贴、摄影、插画、文字甚至是空白等也可以,或者混合几种方法来表现。因此,招贴设计的迹象比单纯绘画中的迹象更为丰富,生活中或者大自然中的任何材料都可用作招贴的设计素材。
二
所谓象之迹,简单来说就是组成象的迹的因素。我们见到的图像都是有质地和纹理的。在今天看来很简单的一个过程在早期的手工绘制招贴中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例如,在古老的拜占庭艺术中,艺术家们在建筑装饰中使用了镶嵌画,《狄奥多拉皇后》就是著名的镶嵌画作品。制作这样一副镶嵌画,要备齐一些形状不规则的小石头作为“嵌片”。它们是大理石的,玻璃料的,陶土烧制的。把它们排放在一起,组成人物或者画面,并由砂浆固定住。一张有若干块嵌片大小的金箔被用来作背景,一些螺钿成分用于突出皇帝夫妇项链上的闪光。各种各样的嵌片方法使壁面程度不同地捕捉和反射着光线,这就赋予镶嵌油画表面以镜面般的感觉,并且使色彩效果比起油画来要强烈得多。我们知道人物的形象是固定的,需要的就是在这个象里面使用合适的迹,这样类似马赛克的、小块的、不同肌理的镶嵌方法就是组成象的迹。在一组名为sonora的招贴设计也用到了类似的马赛克似的拼接。从远处观看这组招贴时,我们能够清晰的辨别出招贴中的象:有咆哮的女人、靠在墙上男人、捋头发的青年和伸着舌头的嘴巴。为了突出主体,背景简单,只用纯色修饰。但走近一看,画面瞬间模糊起来,这时就能够发现每一个图形都是由大小均等、不同颜色的小方块构成的,这些小方块所构成的类似马赛克的特殊纹理正是一种肌理的迹,是适用于这个招贴的迹。当这些迹填充在具体的象里面时,由于远清楚近模糊的特殊效果,使得观赏的人能够在远近不同的角度中体验到招贴的乐趣,在乐趣中感受迹象的奇妙。[2]
德国招贴大师冈特·兰堡的土豆系列招贴中,[2]每个画面都是以土豆的原始形态为主体,作者直接利用土豆表皮本身的肌理而且没有进行修饰,再对土豆进行不同形态的处理:土豆皮的缠绕、切割成块后的堆砌、四等分的处理和平均的分割。但是总体看来仍然是土豆的形状,又对每一个切面进行不同颜色上的处理,把土豆的轮廓与色彩结合起来,让人有着耳目一新的感受。图中的土豆因为表皮的完整而成为一个整体,又因为人为的分割和色彩的渲染形成新的形象。土豆就是一个完整的象,土豆表皮的迹、切割后形成的迹和色彩的迹共同构成了招贴的主体,迹与象相互融合贯通,让观赏者探究更深层次的含义。
一个好的设计需要迹与象的完美结合。一幅优秀的招贴,其迹与象不是随心所欲、杂乱无章的拼凑,而是由作者的创意来统帅。所谓创意就是“观念、境界、情感、美,以及一切你想(或者别人以为你想)表达的内涵”。[1]在招贴设计中,我们可以说创意是整个设计的灵魂所在。一幅招贴的好坏,创意是关键,然后是作迹造象,或者因象造迹。我国优秀的设计师靳埭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将中国独有的书法艺术和水墨画这种迹运用到招贴设计中,创造出独特的象,加上他独有的创意,使其设计作品广受好评。他不仅接受西方的前卫艺术,也对东方的本土文化有独到领悟。他的作品中时刻透露出蕴含儒家、道家、释家文化的大智大慧,使得他的作品既古典又现代,既有东方的独特韵味,也有西方的审美品位。例如,他的作品《自在》环保花纹纸,是为日本纸坊创作的一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纸张。画面主体由水墨书写的“坐”、“行”、“吃”、“睡”构成,再用石凳、鞋履、虫吃叶、睡莲这些实物作为字的背景,手造纸的毛边、宣纸竹纹的肌理,以自然变化构成山水自然的意象,表现中国人追求无忧无虑、悠然自得的生活态度。从这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佛家“大自在”的哲学思想。这就是迹与象的完美结合构造出的作品意境。好的创意使迹象完美结合,成就了优秀的招贴设计。
参考文献:
[1]钟孺乾.绘画迹象论[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
[2](法)雅克·德比奇,等.西方艺术史[M].徐庆平,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