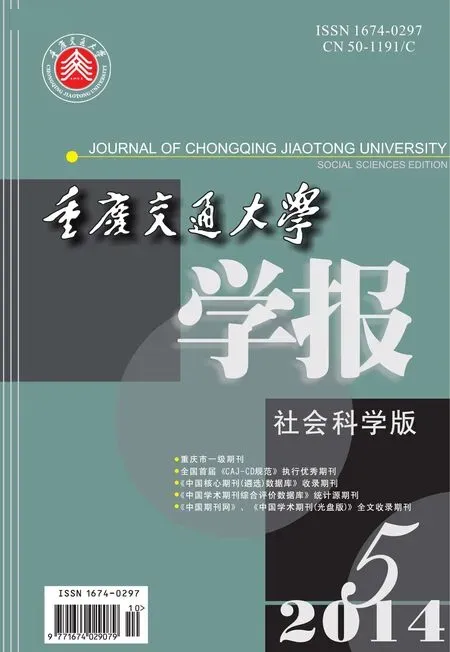儒学的超道德境界探析
2014-03-25郭德君
郭德君
(重庆医科大学,重庆 400016)
一、以伦理为本位使儒学的发展保持了超越性连续
儒学的产生有特定的文化背景,由此形成了和西方哲学迥然不同的风格。先秦儒学具有强烈的入世情结和无神论色彩,正如孔子所言:“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高度注重人生和现世的特征与孕育儒学的文化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发源于内陆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属于典型的内陆农耕文明,儒学因而形成了以重视家庭血缘关系、宗族伦理秩序和强调对祖先的绝对崇拜为显著特征的思想文化体系。儒学中的“孝”“悌”之义就是此特征的具体反映:“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孟子亦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孝”“悌”便成了博爱的道德基础,“仁”则是涵盖这些哲学思想的总体文化外现,因此,先秦儒学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非常关注人伦理秩序的和谐,这是先秦儒学倡导“修齐治平”人生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社会基础和历史文化背景。从高度注重“逻各斯”精神的西方哲学视角来看,先秦儒学具有更多的伦理学特征,其重要经典之一《论语》更像一部伦理道德手册。受儒学的重要影响,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许多大一统朝代,统治阶级纷纷选择儒学作为官方哲学,他们不仅推崇“仁”的治国理念,而且把“三纲五常”等道德原则固定化,这些价值原则一直是维系封建社会稳定的重要思想价值体系。
在中国罕见的大分裂和大黑暗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连绵不断的战争和频繁的政权更迭使这一时期中华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的影响,其突出表现是玄学的兴起、佛教的快速发展、道教的勃兴等诸多新的文化因素互相影响、交相渗透,因而这一时期孔子的形象和历史地位以及传统儒学的发展等问题也趋于复杂化。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大分裂以后,中国知识分子身上一贯具有的深沉历史责任感促使他们肩负起了重构儒学的伟大使命,宋明理学就是在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中国儒学出现了和西方哲学或伦理学完全不同的发展路线,它并不是在形而上的层面对道德法则的依据进行廓清,而是先建立了较为完整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其后才被赋予了形而上的终极含义。以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等为代表的儒学大师,成功地回应了佛、道等思想带来的巨大挑战,在吸收这些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以“理”为核心的完整的思想体系,从而成功复兴了儒学。发展到南宋,朱熹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理学提出“理”先于天地而存在,其为学主张“即物而穷理”。但是,理学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构建一种单纯充满思辨性的理论体系,而是当时有抱负的知识分子力求解决汉末以来中国社会极为严重的信仰和道德危机发动的一场积极的文化攻势。不仅如此,从自身的理论演进、具体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因素等宏观视角来看,心学与理学在许多方面也保持了一种超越性的连续。理学中的“理”是一个位于超验世界的目标,但是仅仅靠格物致知的认知方式无法有效实现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统一,为了克服主客的二元对立,心学将“理”放在了人的心中,格物由此变成了格心。从道德实践的角度来看,由格物向格心的重大转变更加凸显了个人的主观精神和意志。道德行为的出现不单单是因为遵循道德规范的结果,更是发自个人内心的本然要求,是人天然本性自然显现的过程。因此,社会道德的内容并不是人可以创造出来的生硬的教条规范,而是源自具有伦理本性的个体之心,这样认识论与修养论便在以心为本体的心学体系中达到了有机的统一。
因此,以伦理为本位,以普世主义的价值作为最高原则并使其与社会的发展模式保持高度整合,是儒学内在结构呈现连续性演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先秦儒学到宋明理学,在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儒学的理论形态愈来愈复杂,但其核心的价值并没有弱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其价值功能反而有进一步增强的趋势,儒家思想内在的演绎过程和整体发展脉络由此得以呈现,这也是了解儒学核心思想和价值原则的关键所在。
二、儒学关注的根本是超道德的境界
由上所述,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使儒学的核心价值追求一直保持了一种内在的连续性,注重人自身和生活世界的基本原则使儒学有了浓厚的入世情结,宋明理学对终极境域的关注事实上是建立在维护儒学基本伦理道德法则的需要之上的。但是,由此就认为儒学仅仅是一种道德哲学是一种片面的、不客观的观点。因为儒学追求的人生境界不仅仅限于道德境域,而是包括了道德境域的更为宏阔的境界①。冯友兰先生曾说:“中国哲学有一个主要的传统,有一个思想的主流。这个传统就是求一种高的境界。”[1]因此,追求理想的人生境界便成了儒学家毕生努力去实现的最高理想。理想人生境界实现的一个基础就在于人自身首先要达到至高的修养,在此基础上实现有效的社会价值才能成为可能。儒学内圣外王的追求决定了人不单单需要“格物致知”等认知方式,更重要的是需要“正心诚意”“主敬涵养”等深刻的生命体验,在此基础上方可做到知行合一。
在提高个人修养的过程中,儒家世界中更深刻的体验逐步得以显现,人一旦达到这样崇高的境界,就会超越物质欲求。“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贫贱当然没有什么好乐的,但为什么一般人都不能忍受的贫困忧患不能改变颜回的快乐呢?程颐曾和他的门人讨论过这件事:“鲜于侁问伊川曰:‘颜子何以能不改其乐?’正叔曰:‘颜子所乐者何事?’侁对曰:‘乐道而已。’伊川曰:‘使颜子而乐道,不为颜子矣。’”(《程氏外书·卷七》)在程颐的视角中,颜子所乐显然超越了道的范畴,他认为如果颜子真是乐道而已,那他就不是颜子了。颜子所乐的是什么呢?道既然不是乐的对象,这里的乐就是一种神秘的类似李翱所讲的“寂然不动”的深刻体验。如果勉强要用语言来表达,也许说的就是人与道为一的境界。事实上,在儒学家的内心深处,他们有着更为深沉的生命体验,这种体验实际上超越了比道德境界更为本源的领域。在这个境界中,圣人与天地星辰融为一体,表现出一种极高的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与其说是崇高的宇宙领会,不如说是完美的生活体验。在超道德的境界中,人了解社会万象,洞悉宇宙的真谛。达到这一修养境界的人拥有一个更为广博的胸怀和更为高尚的品质,真正可以与天地比寿,与日月齐光,是真正的天之骄子[2]。因此,颜子之乐是一个既不脱离世俗生活,情志又超乎物外的至高的超道德境界。在此境界中,人与万物相融,精神极度自由,道德原则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得以实现。
超道德的宏阔视阈使得中国的哲人对生命和生活本质有着更为深沉的思考,并给予了深刻的、渗透着相当浓厚生活气息的哲学解答。孔子和弟子曾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这段精彩而深刻的对话在阐释了孔子基本政治理想的同时,映衬出孔子追求一种能充分显现自己个性的理想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模式中,孔子孜孜以求的自由、畅适的精神生活,即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能最大程度地得以实现。因此,咏而归的超脱精神境界是人内在气象的自然展现,这种境界已经超越了道德本位、社会关怀、文化忧患等较为狭隘的层面,达到了一种悠然自得、与天地万物上下相融的状态,从而进入到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这种具有自己独立心性见解和自由人生态度的生存方式远远超出了常人的境界,也被称为圣人境界。但是,悠然自适的精神状态并不是指人应自然顺势、消极无为,而是在对世事有深刻的洞悉之后所达到的一种极度自由的精神状态。因此,自信、乐观的生活态度和自强不息的人生追求在孔子的精神世界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人来到世上,必须要展现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且必须要以坚韧不拔的超人毅力去践行自己的生活目标和人生理想。当然,成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冥冥之中的“命”:“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当人尽了己力之所及后把事情的成败归结于“命”,这并不是一种消极的宿命论的思想,而是将执着的坚持和勇敢的放弃并行不悖地统一起来,执着的坚持是一种智慧;适时的放弃是一种更高的智慧,展现出经历了世事沧桑后一种非凡的生活睿智和达观主义的人生态度。
三、儒学超道德境界出现的深层原因分析
由上所述,以伦理为本位、注重人伦关系是儒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儒学发展的一个持久动力。但是,儒学关注的对象不仅仅局限于道德领域,而是追求一种更高的、精神极端自由的境界。儒学对生活和生命本质深刻体悟的目的不单单是伦理性质,而是在于提炼高度的智慧,以达到一种至高的人生境界。
儒学中超道德境界出现的一个重要基础在于中国哲学中独特的“天人合一”思维②。虽然“天人合一”的概念是张载明确提出的:“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正蒙·乾称》),但是中国远古的先民很早就形成了从宏观整体去把握事物的方法论和形象思维,在儒学的早期经典《易经》中就以阴阳五行、取象比类以及形象化方法去认识对待周围世界,从而凸显出中国传统哲学主客不分的独特思考方式。在这种思维模式中,天、地、人并没有看作是完全对立的两极,而是在阴阳流转中自然地统一起来。《周易》中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中庸》亦阐述了至诚尽性的“天人合一”思想:“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孟子认为“万物皆备于我矣”,“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因此,早期儒学中“天人合一”的思维对人生存状态和宇宙生成模式进行了整体性的阐述。之后的宋明理学大师更是从异常宏阔的视阈中来审视人和天地万物的构成关系,不仅人与天地诸物息息相通,而且人的存在价值也是在天地万物的整体关系中显现出来的,道德责任因而也是人必须要勇敢承担的义务③。这种精神境界集于张载所著的《西铭》中:“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唯肖者也。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颍封人之赐类。不弛劳而厎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张载突破了狭隘的世俗之爱的界限,而是将其推及到了宇宙万物之间,这种绽放宇宙大爱的价值理念和精神诉求不仅是对宋儒哲学内核的高度概括,也彰显出中华文化最伟大的品质和永恒的魅力。程颢也曾不无自豪地说过,虽然其学说受到别人思想的影响,但“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因此“理”是理解二程以及朱熹理学思想最为重要的哲学范畴。在程朱理学中,万物通过“理”彼此联系起来,天人一理,这事实上是“天人合一”思维在具体哲学思想体系中的另一种形式表达。
“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方式更多需要的是生命体验,在这种思维方式中,主体与客体完整地统一起来,天、地、人被纳入到一种多维度的整体关系之网,主体自然而然地融入到这种整体的大系统中。这种认识从本质上来说并不完全是一种反映与被反映的简单过程,而是需要更多内心深刻的精神体验,这是中国哲学一个独特的认识域构成。通过深刻的生命体验,形而上和形而下的领域才可相互贯通,宇宙论和价值论才能密切结合,因此,深刻的内心体验使儒学中的认知主体具有了先验性的倾向,不仅在认识宇宙的最高本体的时候,就是在提高个人道德修养的过程中亦是如此。儒家经典《大学》中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是一条修身的路径。《孟子》中亦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程朱理学则进一步转向内心,强化了人的内省直觉。程颐曰:“世之人务穷天地万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脏六腑,毛发筋骨之所存,鲜或知之。善学者取诸身而已,自一身以观天地。”(《程氏外书·卷十一》)朱熹曰:“心之全体湛然虚明,万理具足,无一毫私欲之间;其流行该遍,贯乎动静,而妙用又无不在焉。故以其未发而全体者言之,则性也;以其已发而妙用者言之,则情也。”(《朱子语类·卷五》)由此可看出,和先秦儒学保持一致,程朱理学将成就理想人格的基点建立在了自我身心的基础上,由内而外的自省自察的认知路径和自我价值实现方式导致儒学更多赋予了理想人生境界以精神层面的含义。陆王心学更是将心的本体作用发挥到极致,王阳明格竹七日以致劳思致疾后,“方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传习录下》),以心为本体可以说是整个心学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因此,从先秦儒学到程朱理学再到陆王心学,都非常注重而且逐步强化了人的内心体验,在此基础上再创建使人心有皈依的价值体系,这就是极富魅力的中国儒学的一个独特的认知视角。
深刻的内心体验之所以能发生,与儒学对“天”“道”“理”等哲学范畴独特的释义有密切关系。有的学者认为,在传统西方哲学中,人们把自然仅仅看作是认识和改造的对象,由此逻辑的和知识化的哲学得到了自身发展的对象;而在中国哲学中,对“天”等概念的独特理解使人们获得了伦理价值和感情的依托,由此可以建立依靠外在力量的价值体系和理想人格范型。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上的差异,与西方传统哲学中“天”等概念被单纯地赋予了自然方面的含义不同,在中国哲学中,“天”等概念包含了多重性,不仅指自然现象,也有宇宙的本源、至高无上的权威等不同含义,但更多包含了伦理道德方面的内涵或使其具有了人格化的特征。《论语》中多次谈到了“天”“道”以及与之相关的概念:“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巍巍乎,惟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五十而知天命。”(《论语·学而》)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论语·公冶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论语·公冶长》)“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耻也。’”(《论语·宪问》)“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在宋明理学中,“理”等形而上的哲学范畴所具有的伦理特质更大于本体论方面的含义。它们并不只具有形而上的终极含义,因为儒学大师们主要不是从本体论的角度来构建这些范畴的,而是从价值论的层面使理想道德境界的实现有可靠元伦理学的依托而阐释这些概念的。这样,人进入无限自由的精神境界才有了可能,至少有了逻辑上的可能。由上面的分析可看出,儒学思想体系中独特的“天人合一”认知方式以及对人生存状态和宇宙生成模式的整体性解释,高度注重人的内心体验,对“天”“道”“理”等概念给予了多重性的释义等诸多因素结合起来,才使得儒学所追求的超道德境界的出现有了可能。
注释:
①境界一般指主体的精神感受,境域一般指客体存在的范围,二者有密切的依存关系,因为主体的心灵感受、精神状态一般以对客体的感知为基础,人生境界并不能脱离生活境域而独立存在,故在此将道德看成了客观存在现象的一部分而用了道德境域一词。
②“天人合一”不仅是一种独特的认知方式,也是一种至高的人生境界,即和本文中论述的超道德境界是等同的,但是本文探讨的是这种超道德境界何以出现的深层原因,因此此处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理解“天人合一”的。
③对比来看,西方哲学在古希腊时期就存在着主客不分的思维,将人与自然看成是息息相关的整体。但是,详尽阐释这一构成模式却是在20世纪的存在主义等哲学思想中,海德格尔就认为,此在的基本建构为“在世界之中的存在”,虽然如此,海德格尔依然是从本体论的角度来阐释此在的基本建构的,此在并没有伦理学方面的深层含义。因此,通过这一对比更能显现出理学大师思维的超越性。
[1]冯友兰.三松堂全集[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573.
[2]王晓兴,李晓春.宋明理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3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