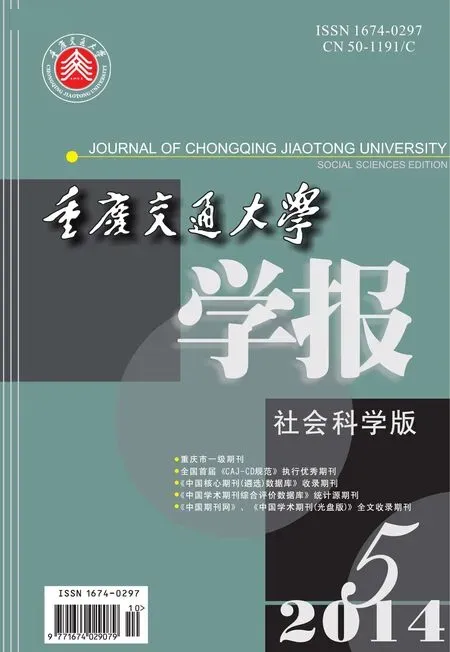《奥兰多》中的次要人物与性别身份
2014-03-25李蕾
李 蕾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外国语学院,广东珠海 519087)
弗吉尼亚·伍尔夫不仅是一位天才的小说家,现代主义文学的领军人物,更是一位始终关注着性别问题的女作家。其出版于1928年的小说《奥兰多》以贵族女文人、伍尔夫的情人维塔·萨克维尔-维斯特为原型,为主人公奥兰多描绘了一幅奇幻瑰丽的人生画卷。小说开头的奥兰多是一位生活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贵族少年。30岁时他在异乡土耳其出任大使时突然神秘地由男转女,回到英国后还嫁人生子。而在小说结尾的1928年,经历了4个世纪的奥兰多也不过才36岁。
《奥兰多》一出版就畅销不衰,算得上是伍尔夫难得的商业上的成功之作,且明显地改善了她的经济状况。据统计,《奥兰多》出版后半年内卖出8104本,伍尔夫公认的代表作《到灯塔去》在出版第一年也不过卖了3873本[1]。尽管如此,伍尔夫本人似乎并不将其视作自己的重要作品,从一开始就在日记中强调它是“玩笑”。伍尔夫的这种“不重视”也得到了后来很多文学评论家的肯定,甚至南希·贝茨(Nancy Bazin)在她专门探讨伍尔夫的性别观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与双性同体幻象》(Virginia Woolf and Androgynous Vision)一书中也忽略了这部作品,尽管事实上《奥兰多》对于政治、性别和创造力的关注度甚至超过了《到灯塔去》《海浪》和《岁月》[2]。萨克维尔-维斯特的儿子奈杰尔·尼克尔森(Nigel Nicholson)对于该书的那句广为人知的评语——“文学史上最长最动人的情书”[3]——也许可算作促销口号中的高明案例,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印证了对于该书作为严肃文学的质疑。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部小说被女性主义批评家纳入视野。与《奥兰多》同一年出版的《一间自己的房间》被广泛视作伍尔夫的双性同体宣言,国内外的研究者多用双性同体的视角来分析这部小说中变性/易装情节和复杂多变的欲望,也有研究关注于小说中暗藏的女同性恋情结或其对传统传记叙事的颠覆,分析的焦点自然集中在主人公奥兰多身上。
奥兰多的性别身份和性别意识的进化是分阶段逐步实现的,其在不同阶段结识的小说中的次要人物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仅如此,这些次要人物本身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程度上挑战了性别规范,共同构成了伍尔夫笔下这个异彩纷呈的性别万花筒。在此,笔者尝试按照出场顺序对这几位次要人物进行解读。
一、萨沙:来去不定的火
少年时代的奥兰多对莫斯科大公国的公主萨沙一见倾心。这位公主滑着冰第一次出场时,“身着宽松的俄罗斯式束腰衣裤,让人辨不出男女”[4]15,此时奥兰多就已经对这位不辨性别的神秘人物着迷了。只见这位滑冰人“中等身材,苗条纤细,一身牡蛎色的天鹅绒,用罕见的绿色皮毛镶边。然而在那全身散发出的特殊魅力映照下,所有这些细节都淡化了”[4]15。最初奥兰多认为,滑冰者的“双腿、双手和姿态都像男孩”[4]16。但是很快他又改变了看法,因为“没有一个男孩会有那样的双唇;没有一个男孩会有那样的胸脯;没有一个男孩会有那样晶莹剔透的碧眼”[4]16。最后,当滑冰的萨沙停下来,距奥兰多只有咫尺之遥时,奥兰多才做出了最终的判断,“是女子”[4]16。
然而这个判断是否如奥兰多本人那样笃定呢?毕竟他刚刚还坚定地认为“一定是个男孩,女子绝不可能如此敏捷、矫健”[4]16。事实上,这里的所谓“敏捷、矫健”正是美国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公认的酷儿理论的开创者之一朱迪斯·巴特勒在其成名作《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体的颠覆》中指出的所谓“不和谐的形容词”,或者说是被“实在的性别范畴(substantative identity)”[5]34事先排除了的可能性。巴特勒指出,正是人们对作为本质的性别属性的期待赋予了性别建制以权威性。换言之,并非是有什么样的性别主体就有什么样的性别表达,恰恰相反,是性别表达通过操演(performativity)构建了性别主体。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取向之间的所谓一致性并非是天然的,而是通过风格化的行为重复实现的一种文化构建。也就是说,性别实质上是操演性的,这些持续的风格化的身体行为建立了一种本质主义的性别“内核”的表象。萨沙的存在实际上就是对性别身份的一种追加界定,从而拓展了实在的性别范畴,甚至对这种实在的本质提出了质疑。
在奥兰多看来,萨沙的迷人之处正是在于她的这种不确定性,仿佛“绿色的火焰似乎隐藏在翡翠之中,丽日总被山岚遮蔽。只有外表清晰可见,内里却是一团变幻无常、来去不定的火,从没有英国女子放射出的那种平稳的光束”[4]22。英国女子放射出的那种平稳的光束是指什么?奥兰多在遇见萨沙之前曾爱过的英国女子们也许会给我们一些提示。她们之中既有对他宠幸有加的伊丽莎白女王,也有他在露天啤酒馆邂逅的大胆随意的平民姑娘们,当然更有许多名门闺秀,书中列举了其中三位:见不得血动辄昏倒的克罗琳达小姐、世故残忍的斐薇拉小姐和注重保养的奥兰多的未婚妻欧佛洛绪涅。这些人在萨沙面前都相形见绌,“恍若锯末和炭渣”,成了奥兰多眼中“一位骨瘦如柴的老妇,不计其数的红脸蛋儿妓女,一位成天哀诉的修女,一位刚愎自用、言语刻薄的女冒险家,一位毫无主见、沉浸于花边与礼仪的女人”[4]17。放射出平稳光束的英国女子自然还包括奥兰多的母亲。当他的父辈驰骋在战场上建功立业的时候,他的母亲却只能由侍女尾随着在园中喂孔雀。这些女子虽然身份悬殊、性格各异,却都摆脱不了淑女或悍妇的传统女性形象。她们身上所谓“平稳的光束”则是在异性恋霸权的框架内建构出来的虚假的性别归属感。
热恋中的奥兰多常常感觉萨沙的魅力难以用言语描绘,搜肠刮肚也寻觅不到适当的辞藻。“白雪、奶油、大理石、樱桃、雪花石膏、金丝线”这些传统意象都无法让奥兰多满意,因为它们“如同那些曾经给过他灵感的女人,一点儿没有新意”[4]21。其实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这些传统意象指涉的都是女性的阴柔气质。奥兰多“渴望另有一番风景,另有一种语言。因为用来描绘萨莎,英语太直白,太甜蜜”[4]21。也许问题并不在于英语的直白甜蜜,而是男权统治下的、逻各斯中心的语言中的性别对立二分的法则。巴特勒解读伊里格瑞和福柯的语言观,提出性别在霸权语言里表现为一种始终如一的假象,因此文法永远无法真实地反映出性别关系[5]25。语言将阳刚之气和阴柔之美与男女两性强制性地板上钉钉地各自对应起来,因此对“越界”的萨沙,她的“变幻无常、来去不定”的魅力无能为力。
萨沙是奥兰多第一次投入激情的爱恋,也是出生以来就顺风顺水的奥兰多第一次遇到了求而不得的挫折。更重要的是,她是奥兰多视野内出现的第一个挑战性别规范的人物。萨沙的离去对奥兰多的打击是巨大的,她陷入了第一次神秘的长时间昏睡中。
二、大公:穿女装的传统骑士
大公是一个特殊的角色,他的跨界是靠易装进行的。他曾因迷上身为男儿的奥兰多,男扮女装来追求他,基于虽不被承认却确定无疑的同性爱慕。正如巴特勒所强调的,“扮装和颠覆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6]女装的大公绝非挑战性别规范的斗士,倒十足像个滑稽角色。在奥兰多眼中,他的模样活像一只足有六英尺高的跳兔,脸有一码长,眼神呆滞,穿着可笑。因为不堪他执拗的纠缠,奥兰多避走君士坦丁堡任大使。
在大公身上,最引人注意的不是他的易装,而是他的缺乏魅力。也许有读者会问,如果说萨沙是因为她的“跨界”而吸引了奥兰多,大公不更应该如此么?何况恢复男性身份的大公是如此的尊重女性——他单腿下跪来请求奥兰多原谅自己曾在性别上欺瞒,双膝下跪热烈地求婚甚至留下眼泪,继而为自己的失控流泪而道歉,他直言自己“崇拜”奥兰多。为何奥兰多要如此厌烦他呢?
大公在奥兰多有意作弊激怒他后作出的反应或许可以说明问题。虽然奥兰多在牌戏中作弊令他彻底崩溃,但他仍然准备以“她毕竟只是个女子”[4]104为由,发扬他的骑士风度来宽恕她。这恰恰是身为女子的奥兰多所不能接受的。正如凯特·米利特在其经典的女性主义著作《性政治》中所指出的,相较于传统的“大男子气概”而言,“骑士行为代表的是一种妥协,是一种公正的补偿,给顺从的女性某种保全脸面的方式。骑士制度是对不公正的妇女社会地位的妥协,同时,也是掩饰这种不公的手段……是统治集团将其臣民提高到险要地位而玩的一种游戏”[7]45。米利特分析其原因在于中上层阶级的男性不同于社会下层的男性,后者更多地是单凭自己的性别优势来宣称自己的权威,而前者的地位确保其在任何情况下都拥有更大的权力。她引用历史学家们的研究指出,实际上骑士制度并没有丝毫地改善妇女的经济地位,对其社会地位的影响也微乎其微[7]45。不仅如此,骑士制度还把所谓的“女性美德”强加到妇女身上,要求女性充当男性的良心,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她们的行动[7]46。
一旦女性决定摒弃这些“美德”自由行事,做出在游戏中作弊或者往衣服里塞癞蛤蟆这些“不可饶恕的恶行”,温情脉脉的面纱就会立刻被撕下,痴情的大公立刻翻脸诅咒,继而摔门而去。由此可见,大公彬彬有礼甚至有时貌似卑躬屈膝的骑士风度,不过是一种屈尊俯就的姿态,丝毫不会改变他内心深处视女性为低劣人群的看法,而奥兰多也不过“只是个女子”,表面的跨界改变不了他刻板的男性思维,使得他缺乏魅力。
大公和奥兰多之间最戏剧性的一幕当属变为女性的奥兰多回国后二人初次见面时。奥兰多第一眼看到的大公仍做女性装扮。迫于礼节她很勉强地邀请大公进来。在她转身去拿酒杯时,还因为反感大公的纠缠而暗自诅咒着女人(此时奥兰多完全忘了自己新的性别身份),再回身时看到的,已是除去女装后绅士打扮的大公了。奥兰多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性别,继而意识到大公的性别,于是恰如其分地做出了此种情况下女性被要求做出的反应:
“啊呀!”她喊道,手捂住肋骨,“你简直吓死我了!”
“可爱的人儿,”大公高声说,一条腿跪下来,同时把一种烈性甜酒贴在奥兰多的唇上。“原谅我曾经欺骗你。”
奥兰多啜着那美酒,大公跪在她面前,吻她的手[4]101-102。
对此叙述者评价道,“有那么十分钟的时间,他们两人热烈地扮演了男人和女人的角色,然后才进入自然的交谈。”[4]102
虽然大公的本来身份是男性,此时的奥兰多也是毫无疑问的女性,然而他们对应于各自性别的表现却有着“表演”的性质。正如巴特勒所言,不仅同性恋的性别文化在重复异性恋建构的同时有可能对性别范畴去自然化和进行调动,异性恋的性别文化亦有可能。同性恋并非对异性恋的模仿,因为异性恋作为“真品(original)”的地位完全是建构的[5]44。
尽管大公并非一个有魅力的追求者,但身为女子的奥兰多后来“用衬裙的性感来换马裤的诚实,轮番享受两性的爱”[4]127,不能不说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他的启发。
三、奈尔:谁在为谁表演?
当奥兰多对文人蒲伯先生之流感到失望时,她换上男装出门,在广场邂逅了性工作者奈尔。奈尔初看“仿佛是典雅、纯朴与忧伤的化身”,因为把奥兰多认成了男性,她以“杂了恳求、企盼、战栗和惊恐”的目光看着他,“轻轻地、但有点乞求意味地依偎在”[4]125奥兰多的身边。这种姿态和举动的效果斐然,奥兰多感觉自己心里唤起了男人的所有感情,一时间她的模样、感觉和谈吐都像男人了。然而正如奥兰多所怀疑的那样,她的“羞怯、回答问题时的吞吞吐吐、在门口和斗篷的皱褶里摸索钥匙、手腕的无力,都是为了感谢她的男子气而装出来的”[4]125。一旦奥兰多坦白了自己的女性身份,她立刻放下伪装,放弃了自己“那些感伤、恳求的作态”[4]126,笑声大到马路对面都能听到,谈吐也立刻变得粗俗。然而对奥兰多来说,这样的女性才是活色生香,哪怕是“他妈的”这样的言辞,相较于虚伪文人的言谈,也是像美酒一样醉人。奥兰多听奈尔和像她一样身份的女人们凑到一起,“讲故事,发议论,精彩纷呈”[4]127,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愉悦。
奈尔本身是为传统的性别伦理所不容的局外人,即便如此,她仍然要扮演温顺体贴、楚楚可怜的形象,因为她知道这样的形象最吸引她的顾客。连女儿身的奥兰多面对奈尔都不由得产生了男子气,更不用说通常的男性了。这种男子气概何尝不是为了感谢奈尔伪装的女性气质而装出来的呢?因此,巴特勒把性别视作一种协同表演,认为“一个人总是与别人一起或者是为了别人而‘制造’性别的,即使这样一个‘别人’只是想象出来的”[8]。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男性在这种情况下或许不会有奥兰多的敏锐,他们被激起保护欲,自然而然地认为局势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实际上,用米利特的观点来看,奈尔伪装出的女性气质表面上看起来是要为传统的男子气概服务,“实际上却在兴高采烈地挖苦和背叛它”[7]483——也许奈尔才是那个真正控制局势的人。
四、谢尔默丁:古怪敏感如女子的船长
奥兰多是非常幸运的,当阴沉的维多利亚时代来临,时代精神使得单身的她感到巨大的压力甚至无法写作时,她遇见了谢尔默丁,一位气质“浪漫、侠义、热情、忧郁但坚定不移”[4]145的士绅。他与奥兰多之间有着惊人的默契,“尽管相识的时间很短,但最多只有两秒钟,他们就已勘破对方的本相,就像恋人间一向发生的情形。现在只剩下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需要填充”[4]146。
对于谢尔默丁的外貌和衣着,小说中几乎没有提及,唯一一处仅是奥兰多第一眼看到的“一个高大的黑影”。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奥兰多的判断,即此人并不为任何性别藩篱所束缚,身为男子却可“古怪、敏感如女子”,正如奥兰多自己也“宽容、坦率如男子”[4]150一样。因为两人性格中都兼有传统上并不属于自己性别的优秀特质,两人才能如此有默契,以至于在相识之初产生“可怕的疑虑”:奥兰多突然对谢尔默丁喊道“你是女人,谢尔!”与此同时他也对她喊道“你是男人,奥兰多!”[4]146
作为一个复杂的个体,谢尔默丁明显有其阳刚的一面。当管家通报说两位警察来呈送女王的令状时,谢尔默丁完全是一副男主人的姿态。他干脆地命令带警察上来,同时采取了一种背剪双手的姿态立在壁炉前,“仿佛是在自己的甲板上”[4]148。他是一位冒险家,以顶风航行为毕生追求,却又脸红着不肯轻易对奥兰多承认。他对自己事业的辩白是“现如今男人大概也只剩这一件事可做了”,但同时却是“怯怯地”说出这番话的。对于自己表现出的传统男性气质,或者用巴特勒的话来说,对于自己对性别规范的“引用”,他似乎并不像大多数的男子那样引以为荣,而是少了一点理直气壮。
谢尔默丁是婚姻制度下的完美丈夫,他的及时出现挽救了因为单身而承受压力甚至感到绝望的奥兰多。更重要的是,他和奥兰多之间有着“倾盖如故”的默契,也和奥兰多一样是游离于传统的两性标准之外的人。在他和奥兰多的慌乱而喧嚣的婚礼上,仅仅出现了片刻的沉静,从而“清晰地凸现出来”“至死不渝”这个词[4]152。因为一声霹雳响起,“谁也未听到‘服从’这个词”,而且“谁也未看到交换戒指”[4]153。这象征性的一幕充分说明了在他们的理想婚姻中,什么是至关重要的,什么是无足轻重的。
五、结语
从推动情节的角度看,萨沙是奥兰多在性别觉醒道路上的启蒙者,大公启发了奥兰多易装的乐趣,谢尔默丁更是挽救奥兰多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完美丈夫。即便是萍水相逢着墨不多的奈尔,也以她活色生香的魅力把奥兰多从烦闷中拯救出来。然而这些次要人物的意义远不止如此。他们多角度深层次地展示了伍尔夫对性别的思考和超前认识,丰富了我们对性别的可能性的想象。
[1]段艳丽.弗吉尼亚·伍尔夫自己的房间[J].文学教育,2007(12):104-107.
[2]Lisa Rado.Would the real virginia woolf please stand up?Feminist Criticism,the Androgyny Debates,and Orlando[J].Women's Studies,1997(26):147 - 169.
[3]Nicolson Nigel.Portrait of a Marriage:Vita Sackville West and Harold Nicolson[M].Chicago:U of Chicago Press,1973:202.
[4](英)弗吉尼亚·伍尔夫.奥兰多[M].林燕,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5](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宋素凤,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6](美)朱迪斯·巴特勒.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M].李钧鹏,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113.
[7](美)凯特·米利特.性政治[M].宋文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8](美)朱迪斯·巴特勒.消解性别[M].郭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