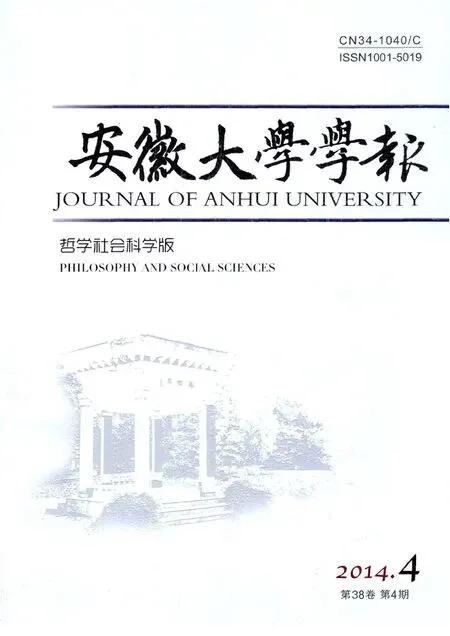清代图甲与保甲关系新论:基于徽州赋役合同文书的考察
2014-03-20黄忠鑫
黄忠鑫
一、学术史述评
关于清中叶及其以后图甲(里甲)的走向,学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主流观点认为里甲制被保甲制取代是历史发展大势,只是在交替的轨迹上学者们存在一些不同的意见。如,唐文基认为明后期是保甲和里甲双轨并存时期,彻底取消里甲是在清代乾嘉时期①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345页。。赵秀玲则认为明清两代都经历了里甲到保甲的演进过程②赵秀玲:《中国乡里制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0~50页。不过,余清良对赵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认为明代乡里制度的实际操作和演变还需要具体深入的论证,不能只停留在制度的表象上。余清良:《中国乡里制度研究的路径——读〈中国乡里制度〉》,《史学月刊》2002年第8期。。孙海泉勾勒了清代里甲制向保甲制演变的过程,指出其标志是保甲开始行使钱粮催科、编查人户等职责③孙海泉:《论清代从里甲到保甲的演变》,《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
尽管保甲取代里甲的观点为多数人所接受,但是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萧公权将里甲、保甲、社仓和乡约并列为清代乡村控制的主要因素,认为它们各具功能④Kung- Chuan Hsiao,Rural China: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Washingt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0.。刘志伟则认为按里编甲的做法不但没有停止,而且由于一条鞭法的推行,更加偏重以土地作为纳税对象,加上当时均粮均役运动的需要,这一做法更为普遍。“事实上,在包括广东在内的许多地方,里甲制(清代文献多称为图甲制)不但保留下来,而且还是一种比保甲制更为重要的地方制度。”⑤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地方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6页、190页。相比而言,刘志伟的说法是基于一个具体区域的论证,而不是从全国角度泛泛而谈。这一说法也得到一些区域研究者的证实。如隗瀛涛从清代巴县档案中发现,尽管建立了保甲制度,但是里甲制度并没有被废除,只是其功能集中在征收赋税方面。巴县档案中在涉及事件发生地和百姓住处时仍称里甲,可见里甲作为行政区划是比较稳定持久的①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567页。。
杨国安的观点较为调和,其论断是基于两湖地区的地方特点得出的。他以为明中后期的保甲制主要是作为一种治安手段在局部地区推行,直至清初方可称为“双轨并行”。从里甲到保甲的转换,过程是逐步而缓慢的,而且其内涵也相当丰富。他还进一步指出,“在历史传承极为浓厚的传统乡村,或在里甲体系之内编排保甲,或在保甲组织内融入里甲是地方较常见的做法”②杨国安:《明清两湖地区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3~55页、67页。。这是具有相当启发意义的观点,说明里甲和保甲的关系可以从区域差异的角度进行考察。类似地,杜正贞认为,山西泽州的保甲也是在里甲的框架或者在里甲的名义下执行的③杜正贞:《村社传统与明清绅士——山西泽州乡土社会的制度变迁》,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249页。。常建华梳理清初各类文献后发现,“甲长虽然肩负着督察邻右的保甲职责,但是其来源也有可能是建立在原有的里甲之上的,是里甲的甲长发挥保甲甲长的作用”。由此,他认为这一现象体现了里甲制向保甲制转变④常建华:《清顺康时期保甲制的推行》,《明清论丛》第12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2年,第324页。。
在边陲台湾,其基层组织中的里、保并行的情况,则具有南北差异。南部“里”的编制,始于郑氏统治时代,清代继续沿袭。清中叶以后逐步开发的中北部地带,由于当时保甲制的施行,使得“保”成为当地的基层组织⑤戴炎辉:《清代台湾之乡治》,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第5~6页。。这一发现也为基层组织和区划的地区差异性提供了鲜活案例。
在徽州研究领域,不少学者亦持有里甲必然为保甲取代的看法。周绍泉以都图文书《休宁县都图里役备览》为例,认为此类文书在当时还是有用的,里甲编审仍在进行。同时他还认为明初以来一直存在的里长、排年,至迟到清中叶尚未消亡⑥周绍泉:《徽州文书所见明末清初的粮长、里长和老人》,《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但这一论点并没有深入展开。栾成显基本沿用了这些论点⑦栾成显:《明代黄册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45页。。权仁溶从徽州里甲编制增减的侧面进行观察,认为明清之际通过增减里的方式,缓解里甲内部变化的压力。他由此认为直至清前期徽州的里甲制仍旧存在⑧[韩]权仁溶:《明代徽州里的编制与增减》,《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清初徽州的里编制和增图》,《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正因为深受里甲必然为保甲取代论点的影响,上述学者都没有对里甲究竟何时、如何为保甲取代展开具体讨论。
刘道胜发现徽州基层保甲的管理范围在很多情况下与特定聚居宗族相重叠的情况。同时,他还发现徽州保甲设置往往于一图之中,由大姓各自设立一保,其仆人或细民小姓则归辖大姓保甲之下⑨刘道胜:《明清时期徽州的都保与保甲——以文书资料为中心》,《历史地理》第23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洪性鸠虽然承认保甲是在里甲、宗族基础上设置的,但又认为随着徽州既具有顺庄法意义,又以保甲为基础的滚单催征的施行,保甲取代了里甲⑩[韩]洪性鸠:《清代徽州的保甲与里甲及宗族》,[日]中国史学会编:《中国史学》第13卷,京都:朋友书店,2003年。。显然,他们都发现了清代保甲的设置基础,却受制于主流观点而没有继续深入挖掘。
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汪庆元依据鱼鳞图册、保甲烟户册等第一手资料,强调了里甲与保甲内涵的差异。“里甲主于役,是把农民编制起来承担赋役,并限制其流动;而保甲不论原管都图册籍,是在承认社会人员流动前提下的治安组织。清代由保甲编户取代里甲编审,只是户籍制度的转变,都图的地籍管理仍然存在。”这便是接受了里甲、保甲并存观点而提出的新看法。另外,他也发现了清初徽州保长由里长佥派的现象,论证了“图”直至清末仍是赋税催征单位的事实⑪汪庆元:《清初徽州的“均图”鱼鳞册研究》,《清史研究》2009年第2期。。陈瑞的研究又将该认识推进了一步。他通过对休宁县二十八都多份赋役合同的解读,认为徽州宗族社区中保甲之役的承充是在里甲制的框架内进行运转的①陈瑞:《明清时期徽州的宗族与保甲推行》,《中国农史》2012年第1期。。这一看法,与前述杨国安、杜正贞等人的意见一致。可见,保甲与里甲间的关系颇为复杂,不能简单地用替代论进行概括。
前人的讨论,主要从功能与形制两个维度展开。基于区域史的研究,能够将里甲、保甲关系梳理得更为细致,也更有说服力。乾隆时期,户口编审统一归于保甲,事实上取消了里甲编审人口的功能。但在实际上,这是里甲与保甲互补功能的内在因素,且户口编审与赋税征收未必同属于一个系统,在户籍登记上存在烟户和花户的差别②单丽、曹树基:《从石仓土地执照看花户内涵的衍变与本质》,《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更何况,基层组织在形制上因地而异。因此,笔者认为简单地提出里甲向保甲转化的结论,过于草率。
徽州相当数量的民间文书,尤其是赋役合同的留存,能够为这一话题的深入探索提供支撑。徽州赋役合同的数量至少有二百份以上,其中,一部分实物以散件形式混入大量契约文书之中,又有相当一部分存在于谱牒、誊契簿、讼诉案卷等簿册文书中。从赋役制度与基层组织角度看,赋役合同可以分为土地清丈、里役承充、户名更替、保甲乡约等几类。这类文书的主要价值体现在:它们包含的赋役信息较为丰富,体现了民间社会应对赋役制度的种种策略,以及民间社会内部的复杂关系,尤其能够反映宗族、村落中的各种社会关系。笔者初步归纳,保甲合同等民间文书语境中的保甲与里甲关系,至少包括职役佥点、组织形式与实际功能三个方面。
二、职役:保长的佥点
保长作为基层赋役体系的一种职役,主要是由图甲佥点。不少保甲合同就记载了订立缘由,从中可以看出保甲制在施行之初的实态。如雍正五年(1727)的一份合同明确无误地指出当时保长就是在图甲基础上添加的一个职役,与相关合同结合,可为我们认识保长佥点方式提供重要的线索。
立议合同汪兴、吴宗睦、戴宗远、金华宗、王宗章、朱淳义、叶涌等,缘因雍正五年奉旨,各都图添设保正,续奉县主票唤本里众报,是以合里公议,分作四阄,对神拈定,轮流承充,不得推诿。所有工食银十二两,每年在于本里二十九甲户内公派,议为承充之人料理公务等用。其承充之人一应公务,尽在承值,不得误事。所有分阄条款另列于后。今恐无凭,立此合同一样四张,每阄各执一张存照。
一阄丁未年四月起,金华宗、王宗章、朱淳义、叶涌。
二阄戊申年四月起,吴宗睦。
三阄己酉年四月起,戴宗远。
四阄庚戌年四月起,汪兴。
一议,承充之人在于各阄自行议举。
一议,唤认使费银三两,四阄每阄派银七钱五分,在于四阄名目付出与承充之人应用。倘下年另唤报,亦照此例公派。
一议,倘有飞差,照都内概例,四阄公议。
其十甲倪尚义住居三十都地方,路途遥远,难以照管,不在议内。倘有累及,四阄理论。
公议在官名目系“王仁德”,轮流顶名充当,倘遇换报,听从本阄名姓具报。(下略)③周向华编:《安徽师范大学馆藏徽州文书》,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6页。
合同开头明确指出,保正一职,是在各都图甲基础上添设,由各图呈报。这是官方规定的一般程序。其规定可以追溯至明代,如,“地方设立保长,司一图公务,其责甚重”④《新安歙西沙溪汪氏族谱》卷12《崇祯三年众议保长逐门轮流承管》,道光五年(1825)刻本,南京图书馆藏。。这里,保长的管辖范围就是一图,换句话说,保长就是基于图甲框架而设立的。然而,实际情形则较为复杂。
其一,该合同内容虽为图内民众决定保正承当人选和分工,但保长人选的佥点却往往被图差所垄断。由于保长职役负担沉重,图差任意佥点忠厚懦弱之家充任,“懦弱之辈不谙事理,何能充当,多有误公”①《歙县九姓轮充保长文约》,安徽省博物馆编:《明清徽州社会经济史资料丛编》第一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574页。该文书又以“清代道光二十九年七月祁门谢德和等共议保长轮流充当合文”为名,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就地域坐落而言,合同出现的“三四都”名称,当为祁门县所独有,而不是歙县。。这就导致相当一部分保甲合同的订立,要求摆脱图差任意佥点的束缚,由图众或族众自行约定人选,抑或组成共同协作组织,如以下所引光绪五年(1879)祁门县三四都的合同:
立议三四都四保越国汪公圣会合文经手人等,议论该阖地保甲,向奉(迁)[佥]点。不料,近年本图差役,此虎狼心之辈,近年调换各处安厚农民,不存良心,贪金爱利,恐有误了公事,地方所害,以致阖地心伤。各姓自愿出身,嘀议助出资本,建立越国汪公圣会以好(引者注:此处疑为衍文)。近年向奉(迁)[佥]点,四保会内懦弱之人当年保甲,会内派人充当,公议贴补保甲以办工食之资。簿据再明,以免日后所遭图差之害,点换农民,贪利肥己。倘有官差公务正事,我等会内之人公同出身料理,不得累及充当之人,保甲亦不得推挨一处。自今立合文之后,遵文为据,会内之人无得生端,反悔异说。如有等情,听凭鸣公理论。恐后无凭,立此四保越国汪公圣会合文一样十七纸,各收一纸,永远遵守存照。
再批:日后会[内]丰肥,人心不一,自愿出会,先前助出资本不得退回,又照。
又批:合同一样十七纸,匣存一纸,挨次轮流,各收一纸,又照。(下略)②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四辑第三册《祁门三四都汪家坦黄氏文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9页。
当地六姓以越国汪公圣会的名义进行互助。尽管图差佥点不能取消,但无论点到何人,会内皆派人充当,便能在相当程度上减少受侵害的程度。不过,更早的合同显示,当地是由乡约佥点保长。
立议仝心充当保长李子学、汪君旺、黄仲和,今因乡约谢朋万举报身等三人充当该地三四都一图小洲地方保长。因身等三人俱系务农生理,恐有不暇误公,是以立此仝心合墨,倘官内有事票唤,不拘唤何一名,总是三人相帮管办,凡地方内编查烟火巡查等事,亦议三人附近照理管办,不得推卸。凡有需用杂费,亦是三人均派,毋得异论。今欲有凭,立此仝心充当议墨存照。
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下略)③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四辑第一册《祁门三四都汪家坦黄氏文书》,第379页。常建华同样发现,晚明山西保甲是在乡约的名义之下执行的,使得里甲、乡约兼顾治安职责,当地保甲并不显著。参见氏著《明清山西碑刻里的乡约》,《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
无论是图差、乡约佥点,还是由图众、族众共同推举或轮充,保长这一职役的设置往往以图甲为基础。
其二,由于图甲已经超出一定的地域界限,图内各户未必居住在邻近地区,如前引雍正合同中附带说明的十甲倪尚义户,“住居三十都地方,路途遥远,难以照管,不在议内”,即该户被排除在这个“保甲共同体”之外,而以地域相邻的图众联合应付保正职役。因此,该合同虽由民间订立,实际上确立了保甲编排的地域和社会范围。这样的情形主要存在于异姓所订立的合同之中,但同时又强调“本图地方保甲长”的轮充标准是“置有产业及图内居住”④刘道胜:《明清徽州宗族文书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4页。。这既是保甲制“以近附近”原则的体现,也是保甲在推行时兼顾图甲地缘性的表现。即,保甲原则上的管辖范围是一“图”,而“图”内已迁居他地的人员则不纳入保甲体系。虽然保甲的管辖范围与图甲有所差别,但又源于图甲。
其三,在前引雍正合同中,该保甲作为一个共同体,由七个族姓、二十九个甲户联合组成,只以“王仁德”一名向官府备案,内部则分为四阄,轮流承顶该名,承当保正相关任务。无独有偶,顺治十年(1653),祁门县三四都汪家坦地方设立保甲长,“其甲长的名,系‘王茂安’名目,递年即应此名为卒,周而复始,以遵永行,不致误公,以闹地方”①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四辑第一册《祁门三四都汪家坦黄氏文书》,第118页。。康熙四十六年(1707),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亦是如此,“本图乡约公报总名‘王道明’,轮流随保充任”,乡约与保甲总名合二为一②《休宁藤溪王氏文约契誊录簿·本图保长议墨附约议》,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藏。转引自陈瑞《明清时期徽州的宗族与保甲推行》,《中国农史》2012年第1期。。这一现象,如同图甲中的拟制户名,仅仅是为应对某项职役而专门设立。民间针对某些临时性的差役,亦会设立类似的姓名,呈报官府。如休宁七都张氏的一份顺治四年“当图正墨”提及,为了应对土地清丈任务,张氏族人推举张时旸等四人具体负责,“立墨串名‘义朋’,具认承役在官”③《槐溪张氏茂荆堂田契册》,1册,清抄本,上海图书馆藏。。无论是图正还是保正、甲长,其呈报官府名目通常是拟制姓名,而背后则是复杂的社会群体。我们固然看到保甲册、烟户册所登记的实在姓名,但作为一种职役,保长姓名的呈报却仍旧按照先前图甲的形式。
综上,保长的佥点、管辖范围和报名,都存在沿用、依托图甲运作模式的情况。不仅如此,保甲的形制也存在不少依托图甲的现象。
三、形制:保甲推行依托图甲结构
(一)形制的合一
保甲往往依托图甲内部结构进行编制,即图甲之甲,也是保甲之甲。如《雍正六年休宁李陈茂户丁李四宝等立里保应役合同》④原件藏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前引陈瑞《明清时期徽州的宗族与保甲推行》一文录有合同全文,并对该户相关合同进行了归户考证。,以宗族为单位,陈、李两姓共同承管里长、保长职役。合同记录了两姓分管里役、保役的月份,也有分管甲分,“陈姓管二甲、三甲、四甲、六甲、九甲”,“李姓管一甲、五甲、八甲、十甲”。从甲的构成来看,仍具有图甲结构特征,即一图(里)十甲。且这些甲并没有明确标明是图甲之甲还是保甲之甲,或可认为是图甲与保甲组织合一的产物。从当地相关合同的订立来看,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末。
此类情形可以追溯至明中后期。如婺源十都四图,为万历十九年(1591)新增图甲(即所谓的“升图”)。“既升四图,即立四图乡约。因烟村涣散,分立两乡约,一清源,一晓起,各五排为一约,以人烟均,统属易也。一甲洪芳生、二甲洪胡、三甲洪遇春、六甲曹启先、九甲吴汪詹,五排联合为清源约。四甲孙国用、五甲孙义兴、七甲江永兴、八甲叶洪鼎、十甲胡先,五排联属为晓起约。历今百有余岁,世守无异。”⑤《入清源约出晓起约叙记》,1册,清康熙抄本,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此处的“排”是里甲排年的衍变,是图甲体制下一图十甲(排)结构的基本单位。虽然这是乡约依托图甲编制的案例,却足以证明在基层社会推行保甲和乡约之时,并没有完全摆脱里甲(图甲)体制的影响。
歙县张氏的几份合同也能充分反映图甲和保甲在形制上的合一。乾隆五十七年(1792)张氏与程氏共同订立了一份保甲合同:
立合仝十排人张、程等,向来本图九甲保长系张方馨承当,因人力寡弱,难以支撑,曾于上年浼十排人等,愿将伊甲膳年保长便换族叔祖张兆圣等承管,□祖茔处,永远存照。今保长轮值四图张雍和等,窃以保长事,自古迄今,□系张姓、程姓承管,当□□无敢擅入,自恐十排人众,人心不齐,为此会仝公议,自当恪守前规,无违古制,倘有异姓私谋,致存擅入之心,各排之人得其迹者,即行传单通知,以便协力仝心,呈公理论,无得推诿。自议之后,如有反悔不遵者,言定罚白米二十担,以存公用,无得异说。今欲有凭,立此合仝一样十纸,每排一纸,永远存照。
清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 日立合仝十排人一甲张元明(押)、二甲张承善(押)、三甲张敦伦(押)、四甲张雍和(押)、五甲张程朋(押)、六甲张元德(押)、七甲张允忠(押)、八甲张祖应(押)、九甲张仲友(押)、十甲程明高(押),册立[里]程觐斑(押),凭中张且初(押)、张日明(押)、张引中(押),代笔张书田(押)①《清代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歙县张元明等更换保长合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藏。为节省篇幅,署名格式略有调整,以下所引合同皆同。
合同中,强调保长职役为程、张两姓所垄断,异姓不得担任。可见,保甲职役并非只是苦差,也是地方社会的身份象征,包含有相当的权益。这一点和图甲里长户名之于地方社会的意义完全一致。
合同虽然声称订立者身份为“十排”,即保甲体制下的“排”,但是署名则为图甲体制中的“十甲”。与该地的图甲合同比较可以发现,每甲之后的姓名即为户名。再以张元明户内部关于共同贴费的合同进行观察。
立议约合同人张元明等,今有承祖排年一役,向系七房轮流承值充当无异,近因各家输纳延迟,以致拖累经管排年之人,比较受奔驰之苦,粮差费酒席之需,为此俟同各家公议,承祖所有各处租利,付次年充当排年之人收取,以作支应粮差催征算总之费,众人毋得私收,入己私用。其钱粮各家务宜急公上纳,四月如出圈户,其使用照粮派出,已纳者不管。八月出批,其粮差使用亦照未完钱粮数目派出,已完纳者不管。如钱粮至十月不完清者,系欠粮之人支应比较,不得累及充当排年之人。其里长、保长会粮、贺礼、使费,俱照排年轮流充当承值,毋得推诿。倘有飞来大差,会众公议,不在此议之内。此系会众自愿公议,务宜遵依,设有反悔推托者,其罚白米十石入众公用,仍依议约合同行事。恐后无凭,立此议约合同,永远为照。
又议:其钱粮营米八月不完者,听凭管年之人秉公毋悔,再批。
雍正十八年八月 日立议约合同张元明、张亮先、张公盛、张永茂、张有恒、张惟吉、张继科、张继禅,代书张圣言。四房收执②《清代雍正十年八月歙县张元明等议约支应粮差催征算总之费合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藏。
署名中,张元明之后列有七个张氏姓名,则代表张氏七房,轮流承当总户头“张元明”的种种任务。另外,合同还提及里长、保长费用亦是七房轮流负担。可见,“张元明”既是图甲户头,又是保甲户头。从整个图的范围来看,其余九个户头亦属于同样的情形。乾隆三十六年和嘉庆十六年(1811),十甲排年两次订立了关于南米(即南方各省漕粮)催征的合同。这一任务为里长轮流完成。其十甲署名与前述保甲合同几乎完全相同③《清代乾隆三十六年二月歙县张元明等承充里长督催合同》以及《清代嘉庆十六年三月歙县张元明等遵合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藏。。可见,至少在歙县这一“图”中,图甲与保甲合为一体。在不同的语境之下,或使用“排”,或使用“甲”。这或可认为是地方社会对于保甲制的认知。由此推知,保甲的实际编制状态,即为在图甲制基础上添加的一个新职役。
(二)乾隆五年后的变化
作为两种不同的职役,图甲和保甲的结构差别日趋显现,甲以下的单位差别更为明显。一般而言,图甲之下为数量不等的户丁(子户)、寄户,而在康熙四十七年以后,确立了保甲“保长—甲长—牌头”的结构④巫仁恕梳理了清代保甲从“总甲—甲长”到“保长—甲长—牌头”衍变的轮廓。参见氏著《官与民之间——清代的基层社会与国家控制》,黄宽重主编:《中国史新论》(基层社会分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9年,第432~433页。,“牌”成为保甲的基础组织形态。乾隆五年正式废除里甲编审之后,“牌”在保甲文献中更多地出现,这是否意味着保甲取代里甲(图甲)呢?祁门十三都康氏就有一份增牌的保甲合同,可以解答这一疑问。
立合同文约石溪康大周同弟、侄、庄仆人等,为奉县主吴老爷尊奉各宪,票唤加增保甲事。原本都只有保长一名,现年举报甲户,本都只有八排,本族一排。今本族加增三排,共有四排,各排人名均以眼同拈阄某月为定,轮流挨次经管。凡遇排内有事,共排之人管理,毋得退缩,不得拖累别排之人。仍有数十余灶无名承充甲长,凡遇排内有事,其费用与共屋共排一体出办。又奉县主佥点保长一名,族内康大梁,今官中票唤各事,俱系大梁承充经(官)[管],是以族内眼同公议,日后递年编点,其保长换别名,官中票唤各事,亦要承充经理,再恐有命盗之案及无头公事,今众议其费用俱系照灶出办朋贴,不得独累有名出身之人。倘族内有事票唤保甲长,是某股之事,亦系本股自承在官保长的名,早为调理,不得混扯别股;或本户公事,另议一人出身,择能言者入官答应。自立合同文约之后,各宜凛遵奉行,如违,执约鸣官理治,仍遵此文为准。今欲有凭,立此合同文约一样二纸,各收一纸存照。
乾隆六年八月初四日立合同文约康大周(押),同弟康大梁(押),同侄康士俊(押)、康杨(押)、康肇佐(押)、康世英(押)、康惟栢(押)①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二辑第一册《祁门十三都康氏宗族文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64页。
这份合同恰好是乾隆五年之后订立的,所反映的保甲编制与组织方式,与图甲几乎完全相同。合同中声称的“有名”与“无名”,当为康氏宗族及其与佃仆的差别。呈报官府的保甲长名为康氏,而由于佃仆依附其中,则为“无名”。而图甲结构中,也是地方大姓垄断图甲户名,小姓人等或为附户,或朋充里长户,其户名为各姓组合。前述的保长姓名呈报,也是如此。稍有不同的是,官府票唤康氏担任保长,是以实在人名进行登记。
与前文讨论的保长拟制户名相同,尽管康大梁被官府佥点为保长,但这并不是一个人的负担,而是全族按照股份(即费用“照灶出办朋贴”)承充。这既是保长户名趋于拟制化、固定化的端倪,又是一个大型宗族内部的举措。而晚清祁门县三四都六保订立的保甲合同,则是谢永和堂、谢崇德堂、方聚义堂、方桂茂堂、黄明德堂、陈敦义堂、江敦仁堂、胡义和堂和叶敦本堂等九个宗族“挨换轮流充当”②前引《清代道光二十九年七月祁门谢德和等共议保长轮流充当合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藏。合同自称为“九姓人等”,但其署名所示为九个宗族、七个姓氏。收录在《明清徽州社会经济史资料丛编》第一辑的《歙县九姓轮充保长文约》则将署名略去,使得读者不能认识到实际订立合同的是宗族,而不是个人。。这两种情形,与图甲制度下总户之下的子户(户丁)或甲户、附户按股轮充里役的方式极其类似。可见,图甲和保甲的运作都主要长期依赖于宗族组织。以宗族为纽带,图甲和保甲的形制差别和运作在清中后期仍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差异。
综上,仅从结构构成与运作这一角度观察,我们可以认为保甲制度的推行与变化,不过是都图里甲体系为主体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之进一步的功能细化分工,其基本构成并没有太多创新之处,而是继续沿用或模仿图甲结构。
四、功能:图(里)、保并存与相互渗透
保甲制度推行之后,长期存在图(里)、保并存的格局,它们之间功能或有重合、互相渗透的情况,却没有发生更替。
(一)功能的互相渗透
一般认为,里甲(图甲)主要承当赋役钱粮征收,而保甲则重在治安。但是,图甲制越来越难以对人口进行统计和控制,保甲的烟户登记则可以做到这一点。这往往被认为是保甲取代里甲的最重要标志。马丁·海德拉就认为,由于“地方的里甲登记长期以来未经修正,不能真正体现一个地方的居民或他们户的结构的实际情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地方保甲制的发展是对里甲制度的地域和人口统计的修正”③[美]马丁·海德拉:《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第九章《明代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468页。。这是基于户口登记功能而提出的,若从基层赋役体制角度观察,情况可能有所不同。
清代徽州民间“里保两役”的说法颇为常见。所谓“忆里保两役,祖宗所遗,户户所不能免者”④《新安休宁青山张氏世谱》下卷《文翰·永济里保急公会序》,康熙二十三年(1684)刻本,上海图书馆藏。表明,图甲和保甲在徽州民间社会属于两种并列的职役。在一些赋役合同中就有包揽人同时承包这两个职役的记载。如,乾隆四十二年,程楚珍包揽程棣华堂十年一次的“一甲册籍经管”,除了完纳钱粮和编造册籍之外,还需要承管“该轮里保二役”①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卷2,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4页。。
或许正是因为个人或团体(如宗族)同时承当两份职役,使得图甲和保甲功能出现互相渗透、重合的情况。例如,早在明万历八年,洪、李两姓订立的里甲合同条款中,除了催征钱粮等基本职能外,还有“缉捕盗贼”等治安功能②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宋元明编》卷3,第62页。。但是,这样的条款在里甲图甲合同中似乎并不常见。至于乾隆朝以后,“催粮”作为保甲的一项新增任务,屡屡出现在徽州文献之中。如休宁古林黄氏十六条祠规中的“饬保甲”:
荆公新法之设,概不能无弊,识者讥之。惟保甲、雇役二条,自元明以至于本朝,相沿勿替,盖以弭贼盗,缉奸宄,责甚重也。近更加以催粮,尤非轻任。③《休宁古林黄氏重修族谱》卷首下《宗祠》,清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无论如何,这些都是图甲、保甲功能互相渗透和添加功能的表现,而不能证明两者发生了更替。
(二)功能的区分
在不少地区,钱粮催征方面仍由图甲里长负责,而治安等方面则由保甲承当。图甲与保甲功能确有相互渗透的实例,却也有将这两者进行有效区分的例子。《新安婺源上溪源程氏乡局记》的一份合同可谓极佳的注脚:
立合同乡约程远、保长程钟秀等,向奉上司明文,以近附近,编立乡约、保甲。本村里甲丁粮有远辖别约地方者,有与二图同里甲者,本村各遵上司行乡约,点保甲,设团长、灶丁,及中平镇一应差役,官有确据保甲之籍册,私有历立充约之合同,论约不论图,历世无异。今因中平派造营房,二图里长借端妄扯程公立、程永芳越纳津贴。窃思上纳钱粮,自应照图催征;约、保差派,自应照约供应。各自完公,何得混扯?且造营房,亦只是以附近地方,故九都亦不派到,况国志、公立等历来轮充乡约,若任妄扯,照图本乡丁粮减去一半,丁粮辖在别都、别约者,岂肯远贴?本约三图乡内单寡,乡约、团长、灶丁何人承充?衣甲、器械、工食等费何处措办?难容借偶然之营房,翻历来之定例。端不可开,局不可破,为此约内共立合同,全约保局,倘致兴讼,照依丁粮敷斗,毋得推诿执拗,以坏乡局。今恐无凭,立此合同六张,各执一张存照。
约程汝振、程尔炽、程汝同
约程文耀、程志昌、程煌
约程时泰、程万兴
约程公立、程志椿、程集义
约程宜一、程永芳、程中兴
约程廷、程鸣阳、程文保
康熙十四年闰五月十八日立④《新安婺源上溪源程氏乡局记·与下村争曹村上屋充当差派合同》,清抄本,安徽省图书馆藏。转引自王振忠《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社会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6页。转引时,标点略有修正。
在这份合同中,17个立约人姓名可与都图文书抄本《婺源都图九口十三田》“十都”下二图三甲程公立、四甲程显(宜)一、六甲程永芳,三图一甲程煌春、二甲程汝同、三甲程汝振、四甲程文曜(耀)、五甲程廷、六甲程志昌、七甲程尔炽、八甲程时泰、九甲程万兴、十甲程鸣阳大体对应⑤《婺源都图九口十三田》,1册,清抄本,复旦大学王振忠先生惠赐复印件。。其中,程志椿、程中兴、程文保未能与都图文书的户名记录对应,程集义户则见于九都九图四甲。笔者认为,这4个姓名皆列于牵涉纠纷的二图总户名之后,或为这些总户之下的子户,又或为所谓的“丁粮辖在别都、别约者”。无论如何,与前文引用的多种合同类似,该合同应是以图甲户名签约,每一户名都代表了一个利益群体。根据合同内容,二图三甲程公立、六甲程永芳与三图各户皆居住在上溪源,后因中平镇需要建造营房,二图里长企图将程公立与程永芳两户扯入其中,甚至将九都的图甲户也一并混入,遭到上溪源程氏宗族的强烈反对,故而立下这份合同。
可见,这是一份聚族而居的村落宗族订立的合同。17个立约的图甲户名分为6组,或对应了宗族内部不同的房派。至于合同开头所谓的立约人“乡约程远、保长程钟秀”,应该是隶属于这些图甲户名之下的实在人名。之所以出现立约人的差异,是由于这一事件牵涉到整个宗族的利益,而图甲、保甲和乡约与宗族无法完整对应,故而在保甲、乡约方面出现的纷争,应以保长、约长牵头立约。不应纳入保甲、乡约的部分宗族群体,又是以图甲划分的,故而具有决定意义的结尾立约人,是以宗族内部的各个房派进行签署。它们以图甲户名出现,表明了不同利益单位的差别。
早在明代后期,保甲就与里甲、乡约相提并论。如选择乡兵之时,保长需要“会同乡约、里排,将保内各户壮丁堪充乡兵者开报”①(明)傅岩:《歙纪》卷8《纪条示·严保甲》,陈春秀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07年,第87页。。而在上述合同中,“官有确据保甲之籍册,私有历立充约之合同,论约不论图,历世无异”,“各自完公,何得混扯”明确说明,在徽州府婺源县的乡民观念中,保甲、乡约分别属于官、私两个系统,民间立下合同应付相应差役。保甲、乡约皆按照地域邻近原则(“以近附近”)编排,而图甲编排并非如此,从而出现“本村里甲丁粮有远辖别约地方者,有与二图同里甲者”的状况。特定任务的征派,根据当地“论约不论图”原则,即依据一定地域空间而不是图甲编排。同时,“上纳钱粮,自应照图催征;约、保差派,自应照约供应”则说明此时图甲制只是纯粹的纳税组织,保甲、乡约承当起治安及特定劳役等职能,基层组织出现了功能分工。民间社会对此分辨清晰。
可见,从组织编排到功能分异,保甲与图甲各自为政,不可混淆。当然,此处的“混扯”与前文所称的职能混杂并不矛盾,而是依靠相关规则的约定。在“里保两役”的承包中,同一人或同一群体承担了基层组织的多种功能,造成职能重叠;“混扯”破坏了特定差役“论约不论图”的地方规则,从而需要明确和强调不同组织的职能。
五、结 论
一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徽州地区保甲制才完全取代图甲制。以祁门三四都留存的民间文书为例,在1930年,“三四都一图十甲王大用户”仍旧出现在上下限执照的记录中②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四辑第三册《祁门三四都老屋杨王氏文书》,第443页。。到了1946年,当地的买卖契约上才以“环谷乡上谢保某甲”作为产业、税粮的推收单位③刘伯山主编:《徽州文书》第四辑第三册《祁门三四都汪家坦黄氏文书》,第214~216页。。显然,民国后期的保甲制度才完全具备县以下行政组织与区划的功能。就明清时代的徽州而言,与其说是里甲(图甲)为保甲所取代,倒不如说是两种职役的并存和功能混杂,甚至是保甲长期模仿图甲的运作方式。
从更长的时段来看,职役间的功能混杂并不始于明清时代。如元代“都”一级主首的职能应在于辅佐里正和“禁察非违”,与里正统辖“乡”级事务、社长专门负责劝课农桑相区别。而实际上,主首还负有多种乡村社会管理事务。同时,元代典章法令的记录中,既禁止主首插手地方治安以外事务,又禁止官员将其他社会事务强加在这些专门职役人员身上④刁培俊、苏显华:《元代主首的乡村管理职能及其演变》,《文史》2012年第1辑,第153~168页。。这两类禁令很明确地反映出地方职役混杂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主首和官员的私人意愿,也适用于明清时代。
不过,这种混杂情况属于较为极端的情形,是由于基层社会制度重合到难以被官府控制的程度。而本文所揭示的则是保甲与图甲并行、重合的一般情况。就官府而言,保甲是以里甲(图甲)为框架进行设置的新职役。职役分工的细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辅助县级行政的运行。就基层社会而言,增加新的职役意味着负担的加重,从而催生了大量赋役合同的订立,以共同轮流承当或推举一名代理人承管的方式进行应对。这就使得不同职役往往由一人或一个群体承当,保甲和里甲之间的界限从而也变得模糊。只有在发生上述“混扯”之类纠纷之后,才予以辨明。
图甲、保甲之间存在功能重叠的状况,还可解释为地方官的不作为:“就应官府的差役而言,或许里甲与保甲组织本就无甚差别,因为他们所应的差早已包罗万象,里甲与保甲规条分别设定的催督粮务与缉盗安良只是他们众多差役的一环。地方官只要能得到他们所需索的服务,至于提供服务的叫什么并不重要。”①刘铮云:《乡地保甲与州县科派——清代基层社会治理》,黄宽重主编:《中国史新论》(基层社会分册),第390页。清代平湖知县王凤生的《保甲事宜》称:“里、甲长名目已古,本系尊称,第近人每谓地保为保长,遂以此名为卑贱。今本县酌改‘长’字为‘耆’字。”(徐栋辑、张霞云点校:《保甲书》卷2《成规上》,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6页)改变名称只是将职役名目进行包装,并未改变实质。该县保甲在地方上的实际领导人是里耆和甲耆,也是打着里甲之名、行保甲之实的典型代表。在民间文书的情境中,还可以认为保甲是在图甲基础上添设的新职役,使得图甲与保甲在组织结构上具有极高的雷同性。地方社会也往往将里保两役交由同一人或同一群体承当、包揽,以节省开支,减轻负担。这些现象,都无法得出保甲取代图甲的结论,而是反映了民间社会为应对各种基本职役形成的具有足够弹性的调适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