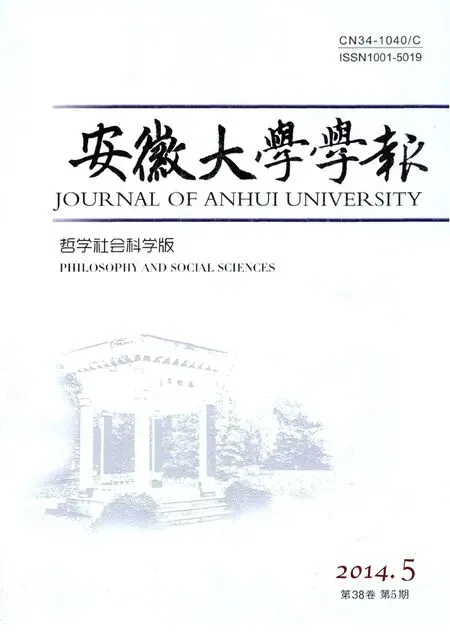龙头企业领办合作社的异化行为及其规制
2014-03-20孟飞
孟 飞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在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中,一个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分散化的小农如何以组织化的方式参与农业大市场的竞争。2007年7月1日实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为农民以联合互助方式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加入合作社成为农户的优先选择。相比较没有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合作社社员的收入普遍比非社员同业农户高出20%①乌云其木格:《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五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农民合作社》2012年第7期。。从发起人的类型来看,我国合作社主要是以种植、养殖等生产专业大户、营销大户领办兼业小农为主要形式,占全部合作社的69.2%,完全由小农自发联合组建的合作社数量很少,而由龙头企业领办的合作社占5.4%②王曙光:《论新型农民合作组织与农村经济转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我国合作社立法也是认可和确立龙头企业组建合作社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14条就确定了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加入合作社成为社员的法律资格。这里的企业实际上就是以龙头企业等为典型形态的营利法人,而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则是非营利法人。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是,龙头企业与普通农户的谈判力是不对等的,龙头企业借助于资本、管理技能、市场影响力等资源禀赋实际控制着合作社,成为核心社员,而普通农户则被边缘化,社员共同治理的民主机制无法得以实现。龙头企业在尽可能地控制农产品来源的同时,攫取政府部门提供的优惠政策。那么,如何理性地对待龙头企业领办合作社这一中国现实选择,不仅直接关系合作社发展的可持续性,而且直接关系到政府公共政策的有效性。从中国合作社发展的阶段来看,龙头企业领办合作社既有其现实社会基础和政策环境,有助于解决农民自组织能力不足的问题,但同时龙头企业也存在着不同于普通农户的利益诉求,扭曲了合作社的民主治理原则。因此,如何对龙头企业领办合作社的异化行为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是提高合作社发展质量的关键。
二、龙头企业领办合作社的政策基础和利益诉求
合作社是一种实行社员民主自治的组织形态,只要社会中存在着弱势群体,就必然存在着对合作互助的需求。但是,农民朴素的合作意识并不能够自动地转化为秩序化的合作行动,合作社发展的社会基础和政策环境制约着合作社的组建方式及其领办人角色的差异。
(一)龙头企业领办合作社的现实政策基础
龙头企业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全国出现了农产品“卖难”的情况,山东潍坊和河南信阳等地区出现了解决农产品销售难的新的组织方式。在农业产业化发展趋势下,农产品加工、贸易企业通过签订合同与农户建立稳定的供销关系,较好地带动了农村经济发展,这些企业后来被称为“龙头企业”①蒋颖:《中国农村合作社法律制度发展研究》,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第20页。。农业产业在纵向一体化中,龙头企业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通过产业链条的优化和资源整合,龙头企业具有合作社所不具有的制度优势。较之于合作社,龙头企业在农产品加工及出口创汇等方面具有比较竞争优势②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10号)后,农业部于3月26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政策出台情况进行介绍,对龙头企业在中国农业产业化的地位和作用作出了经验总结。从统计数字来看,龙头企业提供的农产品及加工制品占农产品市场供应量的1/3,占主要城市“菜篮子”产品供给量的2/3以上,并且出口创汇额占全国农产品出口额的80%以上。发布会的主要内容刊发在《中国合作经济》2012年第4期。,这也是龙头企业获得政府部门扶持的直接原因。
农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部委于2000年10月8日联合发布了《关于扶持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的意见》,龙头企业被视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力量”,重点龙头企业可以享有基地建设、原料采购、设备引进和产品出口等六个方面的扶持政策。2006年10月农业部等八部委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意见》也为龙头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扶持政策。农业部和中国农业银行也于2010年5月5日发布了《关于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解决龙头企业融资难问题,加大对龙头企业的金融服务支持。国务院于2012年3月6日发布了《关于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为做大做强龙头企业提供扶持政策。
龙头企业与农户建立利益联结的方式主要是农业订单。在双方协商的基础上,龙头企业与农户签订农产品购销合同,议定合理的收购价格,形成市场交易性质的购销关系。但是,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这种合同关系是不稳定的,对龙头企业而言,一对多谈判的交易成本也是较高的。而分散化的农户也缺乏与龙头企业进行有效市场交易的谈判力。因此,农户通过组建合作社提高市场交易能力,并通过组建的合作社与龙头企业进行市场谈判。通过将“公司+农户”的模式转变为“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农户提高了参与农业市场竞争的能力,发挥了合作社助推农户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同时龙头企业也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农产品来源,并降低了签订和履行农业订单的交易成本。龙头企业作为农业纵向一体化的组织形式,通过与农户的联合把生产、加工、销售整合为一体,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作为纵向一体化方式中的第一选择,并被纳入地方政府首要的“招商引资”任务之内,成为地方政府干部根据量化GDP增长率来审核“政绩”的一个关键部分③[美]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149页。。
但是,“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也是相对不稳定的,在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之间也存在着利益不一致。龙头企业是以谋求最大化的资本收益为利益诉求的,与合作社和农户是一种利益对立的市场交易关系。合作社及其农户社员缺乏与龙头企业进行平等议价的能力,与龙头企业的利益分歧始终是存在的。也就是说,龙头企业与合作社、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是不稳定的、易变化的。对于龙头企业而言,如何稳定和固化与合作社及其农民社员的关系是制约自身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后,龙头企业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具有强烈领办合作社的经济动力。而我国现行政策也是鼓励龙头企业领办合作社的。国务院《关于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国发〔2012〕10号)要求在农业产业化发展中,引导龙头企业创办或领办各类专业合作组织作为基本原则之一④国务院于2012年3月6日发布《关于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第19段。,并提供相应的扶持政策。龙头企业领办合作社成为特殊社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决“公司+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中的利益分歧,实质上是将农业产业化中的“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外部关系内化到合作社内部,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内化于合作社中⑤张晓山:《大户和龙头企业领办合作社是当前中国合作社发展的现实选择》,《中国合作经济》2012年第4期。,从而导致合作社中除了传统意义上的自然人社员之外,还存在着营利法人社员。
从市场主体的法律资格来看,我国现行立法也是认可龙头企业等营利法人组建合作社的。中国第一部地方合作社立法《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第12条最早确定了组织和个人加入合作社的资质要求①《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是由2004年11月11日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的,2005年1月1日起实施,并于2009年11月27日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进行修改。。《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及其他地方立法和政策文件也对营利法人加入合作社作出明确的规定。浙江台州《关于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若干意见(试行)》在规定合作社的性质与组建中,确立社员可以是法人,包括农产品加工企业、供销社或者技术单位。但是基于合作社的自然人社员基础,该部政策文件要求合作社必须坚持以农民为主体,以劳动联合为基础。
(二)龙头企业领办合作社的利益诉求
龙头企业利用自己的资金技术和市场优势带动其他农户组建合作社,这种合作关系已经突破了国际合作社联盟(ICA)倡导的社员单纯劳动联合的制度设计,形成了龙头企业的资本资源和普通农户劳动合作的制度框架,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合作社发展初期融资不足和经营管理能力不高的缺陷,使得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关系由加入合作社之前的利益对立的交易关系转化为相互合作的商业伙伴和利益共同体。
龙头企业领办合作社的动机相对单一,核心是要建立企业的原料基地或者培育企业的消费客户群体,是从龙头企业的经济利益出发的,表现出一个进攻性的商业战略②苑鹏:《基层供销合作社领办合作社与龙头企业领办合作社有何不同?》,《中国合作经济》2007年第12期。,体现出有别于普通农户社员的利益诉求,集中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龙头企业表现出实际控制社员的倾向。合作社民主治理的基础是一人一票的投票权制度,每一个社员享有均等的投票权。但是,均等化的投票权机制容易产生社员的搭便车行为,社员对合作社业务发展和管理参与表现出理性的冷漠。社员参与合作社的实际效果未必如法律制度设计所期望。而龙头企业具有强烈的控制合作社的经济动力,即使是龙头企业作为社员也只享有一人一票的投票权,但其可依据自己的资本资源、人力资源和社会关系资源而具有一定的市场风险管理能力,也愿意承担合作社的组织成本。相应的,龙头企业希望通过对合作社的实际控制获取更多的资本收益。
第二,龙头企业表现出对获取股息等资本性收益的偏好。我国合作社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社员的股金可以获得股息收入。按照出资额比例获得的股息收入最高可以分配利润的40%。这种资本收益的分配政策大大激励了龙头企业对资本收益的利益诉求。我国这一规定也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国台湾地区现行《合作社法》第22条规定,社股年息不得超过一分。而根据美国《凯普—伏尔斯蒂德法》第291节的规定,农民、种植业者等以互助目的而组成的合作社若想获得反垄断审查的豁免,对社员的股份或者股金分配的利息是不得超过8%的,否则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
第三,龙头企业表现出实际控制合作社经营权的倾向。龙头企业借助于市场影响力带动普通农户组建合作社,但是控制合作社经营权的动力是不变的,即以此达到发展自身能力的目的。尤其是现行政策又允许农民专业合作社入股、兴办社有企业,在这种政策导向下,龙头企业创办或者兴办的合作社就有可能参股龙头企业,形成交叉持股。但这种合作社与龙头企业对接的后果是,合作社很有可能陷入龙头企业的实际控制,从事风险较高的投资业务,或者为龙头企业提供担保,这同时也降低了普通社员的预期收益。
发展合作社的初衷是希望社会弱势群体农户能形成互助组织,维护其自身利益。然而,实践中的合作社的形成和发展又不得不借助于相对强势的龙头企业等力量。也就是说“强者牵头、弱者参与”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的必由之路③黄忠胜:《转型时期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行为研究:基于成员异质性的视角》,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5页。。但是,强势营利法人社员和弱势自然人社员的利益诉求并不一致,这必然会对合作社的互助性质及其制度结构产生影响。
三、龙头企业领办对合作社原则的影响
在企业理论中,所有权人在利益上的一致性是某种所有权安排成功与否的关键④[美]亨利·汉斯曼:《企业所有权论》,于静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80页。。合作社作为一种企业组织之所以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成功,根本原因在于社员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诉求:通过加入合作社获得合作社提供的便利服务。而以龙头企业为代表的营利法人加入合作社与其他普通社员的利益诉求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就对合作社原则产生较大的影响,形成一系列的异化行为。
(一)龙头企业领办对合作社互助原则的影响
社会弱势群体组建合作社是以社员之间的劳动联合作为基础的,也就是人的联合。社员在合作社中的角色是多重的,兼具投资者、消费者、管理人员等身份。社员的积极参与成为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现代合作社立法的一个趋势是赋予对合作社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社员多个投票权,从而突破了一人一票的制度安排。同时,部分国家合作社立法也规定,对于在特定年限内没有参与合作社业务活动的社员作出自动退出合作社的处理。这些激励和约束机制实际上是为了确保社员的互助劳动,促进合作社的发展。
但是,龙头企业加入合作社后,合作社在单纯劳动联合互助的基础上形成了劳动与资本联合的新合作机制。这种劳动与资本的合作有助于合作社的快速成长。很多合作社就是在龙头企业已经形成一定的市场规模之后,借助其市场力量而发展起来的,普通社员可以获得比较稳定的产品销售渠道,并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将农民组织起来。从这一方面而言,龙头企业加入合作社并没有改变合作社的互助性质,只不过是把传统意义上的社员劳动联合转变为社员之间劳动与资本的合作。在法律性质上,公司和合作社是不相容的。公司作为营利法人与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合作社存在着许多制度上的差异。但在企业所有权结构方面,典型的公司只不过是生产者合作社(producer cooperatives)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或者说是资本合作社(capital cooperatives)①[美]亨利·汉斯曼:《企业所有权论》,于静译,第15~20页。。
当然,合作社内社员劳动与资本的合作机制是不稳定的。资本的逐利本性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很容易侵蚀劳动合作的基础。集中体现在龙头企业的主营业务与农户的经营业务是一种产品上下游关系,农户的劳动集中在初级农产品的生产方面,而资本则主导了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农产品加工和经营环节的利润被资本所占有②仝志辉、温铁军:《资本和部门下乡与小农户经济的组织化道路——兼对专业合作社道路提出质疑》,《开放时代》2009年第4期。。另外,龙头企业基于自己的资金实力和利益诉求导致农户与龙头企业之间不是相互依存关系,而是农户附属于龙头企业。龙头企业操纵着合作社,而弱势普通农户的权利无从保护③苑鹏:《对公司领办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探讨——以北京圣泽林梨专业合作社为例》,《管理世界》2008年第7期。。农户只是龙头企业的合同工,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和剥夺也就不可避免④苑鹏:《“公司+合作社+农户”下四种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探析——从农户福利改善的视角》,《中国合作经济》2012年第7期。。因此,龙头企业加入合作社对互助性质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合作社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在营利法人社员和其他普通社员之间的划分和界定,即龙头企业和普通农户以社员身份建立的利益联结机制。如果普通社员仍然主导性地享有合作社剩余权利,仍是合作社事务的控制者和合作社服务的受益者,那么,龙头企业加入合作社并不会改变合作社的经济互助性质,并且有助于合作社的快速发展。但现实情况是,我国现行合作社立法和政策对龙头企业异化行为的规制是不完善的。
(二)龙头企业领办对合作社制度结构的影响
按照国际合作社联盟(ICA)倡导的合作社原则,合作社是一个由社员民主控制的组织。社员大会实行一人一票的决策机制,管理人员由社员大会民主选择产生,并对社员负责。在通常意义上,理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均来自社员,并且监事会成员是没有任何薪酬的,而理事会成员可依据合作社章程的规定给予一定的薪酬,或者没有任何薪酬。这是合作社民主机制的当然体现。但是,龙头企业趋于控制合作社进而对社员大会的决议机制、对理事会和监事会成员的构成及其薪酬产生不当影响:
第一,龙头企业以社员的身份加入合作社对社员大会的决议机制产生影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没有区分资格股社员和投资股社员(主要是营利法人社员)。这意味着龙头企业作为社员享有一人一票的基本投票权,并且可依据投资额的大小享有多个附加表决权。另外,龙头企业以社员身份参加社员大会行使投票权的表决事项是否受到限制成为另外一个关键问题。龙头企业可以利用自己的实际控制力有可能操纵社员大会会议,侵害普通农户社员的利益。
第二,龙头企业对理事会和监事会产生一定的控制影响。龙头企业趋于控制理事会和监事会,是龙头企业控制社员大会的延伸。选任理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属于社员大会的职权之一。相对于非常设机构的社员大会,龙头企业更趋于实际控制理事会和监事会。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26条仅仅限定了理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必须来自社员这一约束条件。这意味着理事会成员和监事会成员均可来自营利法人社员。更为重要的是,龙头企业作为社员担任理事会成员和监事会成员的数量并没有受到明确的限制,其薪酬也没有特别的规定。
第三,龙头企业对合作社之间可以合作以及与其他企业之间的对接产生一定的影响。按照国际合作社联盟(ICA)倡导的合作社原则,合作社之间可以合作,即合作社作为社员组建新的合作社,形成“自下而上持股、自上而下服务”的合作社网络体系。但是,我国现行政策除了鼓励合作社之间开展联合之外,还鼓励合作社入股或者兴办龙头企业,实现合作社与龙头企业的紧密对接。在这种政策取向下,龙头企业实际控制的合作社更趋向于与龙头企业建立经济联系,并向龙头企业输送不当利益。
(三)龙头企业领办合作社异化行为的矫正路径
龙头企业领办在合作社的社员资格、社员民主控制、社员经济参与等方面偏离了国际合作社联盟(ICA)倡导的合作社原则,即合作社的民主机制和自我服务的本质规定性发生了明显的漂移,并对合作社的发展产生影响。但是,这种漂移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下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国家立法和政策不应当强制性禁止或者限制,而应当合理引导本质规定性的漂移①黄祖辉、邵科:《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及其漂移》,《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从全球合作社的实践来看,并非所有国家的合作社立法均是允许营利法人加入合作社成为社员的。全球合作社立法模式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绝对禁止原则。伯利兹《合作社法》、印度《联邦合作社法》、我国台湾地区《合作社法》、马来西亚《合作社法》、泰国《合作社法》等采取这种立法例,合作社社员原则上以自然人为主,非营利法人或者政府部门可以加入合作社。第二种是相对禁止原则,如匈牙利《合作社法》、肯尼亚《合作社法》、纳米比亚《合作社法》、巴巴多斯《合作社法》等。采取这种立法例的合作社原则上禁止营利法人加入合作社,但是立法授权社员大会或者合作社章程约定营利法人加入合作社的条件。第三种是允许营利法人加入合作社的原则,但对营利法人加入合作社的资格,以及营利法人社员的权利做出特别的限制,如德国和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首都直辖区、昆士兰州、维多利亚州等的合作社立法。从中国合作社的实践发展来看,我国合作社立法已经采取第三种立法例,但是缺乏完备的法律规制。
从法律制度设计的角度而言,对营利法人社员的规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在营利法人发起组建或者加入合作社时,对营利法人的数量及其投资者的资质条件进行限制,以确立营利法人是在与合作社及其他社员先前经济联系的基础上开展资本和劳动的合作的。第二个是对营利法人加入合作社后成为特殊社员的权利进行限制,以区别于其他普通社员,这也意味着营利法人社员并不享有完整意义的自然人社员权利。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对营利法人社员的规制路径与国外合作社立法是不同的。国外合作社立法中除了对法人加入合作社的资质条件作出特殊的规制外,往往会通过投资股的方式进行规制。但是,国外合作社立法中确认的认购投资股的社员除了法人组织外,自然人社员也是可以认购投资股的。大多数国外立法之所以采取这种立法模式,原因在于国外合作社为了解决合作社的融资问题而发行投资股(包括优先股),但对投资股社员的权利进行限定。从法律移植的角度来看,国外投资股社员法律制度对我国龙头企业领办合作社的特殊社员制度具有借鉴意义。我国龙头企业领办合作社的目的也是为了获取资本收益,与国外投资股社员的利益诉求没有本质上的差异。
四、龙头企业作为特殊社员加入合作社的资质条件限制
矫正龙头企业领办合作社的异化行为,首先要对加入合作社的龙头企业的数量进行限制,与此同时,对龙头企业投资者的资格作出特别的要求,使龙头企业与合作社之间建立多维稳定的利益关系。
(一)龙头企业作为营利法人加入合作社的数量限制
龙头企业领办的合作社出现两种不同类型的社员,即自然人社员和营利法人社员。在“一人一票”的民主机制下,如果营利法人社员的数量没有受到严格的限制,自然人社员的权利保障就会变得孱弱。
从国际合作社立法实践来看,对营利法人加入合作社进行数量限制的方式主要包括以下两种:第一种是明确规定营利法人加入合作社的最高限额。以匈牙利立法为典型,匈牙利《合作社法》原则上是以自然人作为社员,但是合作社章程规定营利法人可以加入合作社。但根据《合作社法》第4条的规定,合作社中营利法人社员的数量不得超过自然人社员的数量,即最高不得超过总社员人数的50%。
第二种是不对最高限额作出明确的规定,而是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作出特别的限制。在非洲国家中,加纳和毛里求斯的合作社立法明确规定合作社的社员仅限于自然人,但如果征得合作社注册官的书面同意,公司法人能够以自己的专利或者其他技术对合作社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或者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条件,也可以加入合作社。这种个别处理的制度设计实际上也是对营利法人加入合作社作出数量上的限制。
尽管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的合作社立法没有作出数量上的特别限制,但在实践中,加入合作社的营利法人主要是专业型的中小企业,与我国龙头企业对农业大市场的引导影响力存在很大的差别。即便如此,日本还是对加入农业协同组合的小规模农业法人作出特别的要求。根据日本现行《农业协同组合法》第2条规定,社员包括个体农户和专业经营农业的法人,但是经常性员工超过300人,或者资本金或投资额超过3亿日元的法人不包括在内。从日本法律制度演变来看,日本最初规定的社员仅仅是农户,后来才逐步把特定范围的营利法人吸入过来①Akira Kurimoto,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in Japan:An Institutional Approach,Journal of Rural Cooperation,vol.32,no.2,2004,pp.111-128.。
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合作社法》第7(a)条授权章程规定单一社员购买股金的最高限额。对单一社员持有股金的限制,在其他国家(地区)合作社立法中也有明确的规定。我国香港地区《合作社条例》、台湾地区《合作社法》和尼泊尔《合作社法》、菲律宾《合作社法》、新加坡《合作社法》、伯利兹《合作社法》、牙买加《合作社法》、喀麦隆《合作社法》等明确规定单一社员持有的股金最高不得超过总股金的20%。这种对单一社员持有股金最高额的限制实际上起到了保障社员在股金上的均等性,防止个别社员利用其出资额进而控制合作社的作用。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15条确定了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成员不得超过成员总数的5%,但并没有对单一社员持有股金的比例作出明确的规定,也没有要求合作社章程作出限制。这种制度安排存在的问题在于,5%的限制不仅包括营利法人,而且包括非营利法人,这就导致加入单一合作社的营利法人由于数量少而缺乏来自其他大社员的制约,而处于绝对控股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控制5%比例保障农民社员主体地位的制度安排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因此,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15条应当作出修改,确定龙头企业等营利法人社员不得超过社员总数的5%。在国际实践中,非营利法人加入合作社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甚至是在法人中,只有非营利法人才可以加入合作社。同时,《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增加对单一社员持有股金最高限额的规定,限制的比例可以为20%。我国最早的地方合作社立法《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第13条已经明确规定,单个社员或者社员联合认购的股金最多不得超过股金总额的20%。另外,出资额较大的社员享有的附加表决权的比例最高限额也是20%。
(二)营利法人的投资者同时是合作社的社员的法律要求
龙头企业和合作社之间的利益不一致实质上体现为龙头企业的投资者与合作社的社员存在的紧张关系。如果龙头企业的投资者同时也是合作社的社员时,那么,原来利益对立的紧张关系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消解。在实践中,龙头企业多是由当地的农业大户等投资组建的,在地域上与合作社的社员存在着共同联系②于春敏、孟飞:《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发展及对草根性的规制》,《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甚至是同一农户。因此,龙头企业的多数投资者同时也是某一合作社的社员,那么,龙头企业领办合作社出现的利益纷争就会大幅度降低,利益的一致性将会促进龙头企业和合作社的协同发展。在这一方面,爱尔兰的合作社立法提供了经验借鉴。
爱尔兰现行合作社立法允许合作社持有其他公司的股份,同时也允许其他公司加入合作社成为其社员。但爱尔兰《信用合作社法》第17条规定,一个法人组织的多数成员是某一信用合作社社员的话,这个法人组织才可以加入该信用合作社成为社员。营利法人加入合作社后,并不享有特殊的社员权利,除了不得担任合作社理事或者监事外,与自然人社员的权利相同。爱尔兰立法虽然没有对“多数成员”作出准确的界定,但这种事前审查机制有效地推动了营利法人和合作社的融合发展,建立起多重利益联结,并通过投资者和社员的重合对利益联结进行固化。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合作社法》第69条、首都直辖区《合作社法》第66条、昆士兰州《合作社法》第65条、维多利亚州《合作社法》第71条等没有对公司等营利法人加入合作社作出特别的要求,但在合作社理事会的要求下,营利法人社员必须提供本公司股东姓名或者名称的清单,以及股东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数额等。澳大利亚合作社立法实行的是事后审查机制,通过对营利法人投资者情况的熟知来判断该营利法人的运营对本合作社发展的影响。
相比较而言,事前审查机制在保障龙头企业领办合作社的利益一致性上具有制度优势,但这种比较制度优势很可能降低龙头企业带动的积极性。而事后审查机制启动的条件是一般农户社员在理事会中居于主导地位。如果营利法人社员实际控制理事会,事后审查机制则无法得到有效的实施。我国现行合作社法律和政策并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未尝不可引入这一制度安排。立法授权合作社章程作出营利法人的多数投资者同时是合作社社员的具体比例,采取事前审查机制的方式,使营利法人的营利取向和合作社的互助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融合。
五、龙头企业作为特殊社员享有社员权利的限制
龙头企业领办合作社的目的与其他普通社员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也意味着,龙头企业作为特殊的营利法人社员的权利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确保普通社员享有合作社的剩余权利。
(一)营利法人社员的投票权
龙头企业组建合作社后是否享有投票权?按照国际合作社联盟(ICA)倡导的合作社原则,社员当然享有一个投票权。从国际合作社立法实践来看,对营利法人社员是否享有投票权主要有三种立法例:第一种是完全禁止营利法人社员行使投票权。营利法人社员在社员大会不享有投票权,但是赋予其参加社员大会旁听的权利。第二种方式赋予营利法人社员仅对特定事项享有投票权。营利法人享有投票权的内容限制在理事会成员的选任上,对于其他事项则不得享有投票权。第三种立法例是赋予营利法人社员以投票权,但对于投票权的行使作出数量限制①马跃进:《合作社的法律属性》,《法学研究》2007年第6期。。营利法人社员在行使投票权的内容上与其他社员相同,但营利法人社员行使投票权的数量不得超过合作社投票权总量的特定比例②Hagen Henr,Guidelines for Cooperative Legislation,Geneva: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2012,p.86.。
那么,我国合作社立法应当采取哪种模式呢?《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17条采取了第三种模式。营利法人社员可以根据其出资额或者交易量(额)享有附加表决权,但是不得超过基本表决权总数的20%。同时,合作社章程可以限制附加表决权行使的范围。但是问题在于,社员根据出资额享有的附加表决权和根据交易量(额)享有的附加表决权对合作社发展的影响是不同的。现代合作社立法根据社员对合作社的贡献赋予多个投票权实质上是解决一人一票的搭便车行为,提高社员参与合作社活动的积极性。而合作社对出资额较大的社员给予多个投票权则是基于解决合作社融资不足的考虑。尽管欧洲《合作社指令》(第1435/2003号)同时采取了这两种法律制度,但是分别进行了法律规制。另外,部分国家仅仅根据社员的贡献赋予多个投票权,而禁止根据社员的出资额赋予多个投票权。瑞典的立法部门拒绝接受欧洲《合作社指令》(第1435/2003号)有关投资股的规定,认为合作社的基础是资格股社员而不是投资股社员。尽管投资股社员为合作社提供了资本,但是仍然不得享有投票权。因此,我国合作社立法的完善应当对社员根据出资额和交易量(额)享有的多个投票权制度分别作出规定,而不是笼统界定。而对于营利法人社员的限定应当仅仅是根据出资额的大小而享有特定比例范围内的附加表决权。
(二)营利法人社员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营利法人社员担任理事会和监事会成员是其在社员大会享有投票权的自然延伸。如果营利法人社员试图控制合作社的话,他必然控制理事会和监事会的组成。但问题是,营利法人担任理事会和监事会成员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利于提升合作社的管理水平和市场适应能力,但与此同时合作社也容易被营利法人社员所控制而成为其开拓市场的工具,合作社中的其他普通社员则被边缘化。因此,合作社立法应当采取折中的立法方式,允许营利法人担任理事会和监事会的成员,但是对其担任理事会和监事会成员的人数作出限制。对于投资股社员担任管理部门和监督部门的法律问题,欧洲《合作社指令》(第1435/2003号)第39条和第42条也是采取开放的态度,但是投资股社员担任合作社监督部门和管理部门成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四分之一。
另一个法律问题是,营利法人担任理事会成员或者监事会成员是否享有薪酬回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从比较法来看,大多数国家的合作社立法禁止为理事的工作支付薪酬,或者支付有限的薪酬,但是担任监事的社员是没有任何薪酬的,即使是在允许支付给理事薪酬的国家。例如德国《合作社法》第24(3)条规定了理事会成员可以获得薪酬收入,但是该法第36(2)条明确规定,监事会成员不得获得任何薪酬回报。营利法人社员担任理事或者监事的主要经济动因并非是为了获得薪酬回报,而是为了控制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因此,合作社立法应当禁止向担任理事会成员和监事会成员的社员支付薪酬,但对其为了履行职责而开展合作社业务管理活动发生的相关费用应当由合作社支付。
(三)营利法人社员的股息分配权
与公司股东的股息权利不同的是,社员获得股息收入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否则,合作社将会异化为与公司制度无差异的资本企业,但却同时可以享有政府部门提供的扶持政策。但是,如果社员股金没有收益的话,则又会导致社员出资数量的不足,无法维持合作社的持续运行。因此,社员享有适度的股息收入成为合作社立法的关键。
我国现行立法与国外法律制度设计存在很大的差异。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37条对可分配盈余作出了明确的规定,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分配方式。首先按照社员与所在合作社之间的交易量(额)进行分配,但是返还的总额不得低于可分配余额的60%。其余的部分主要以社员的出资额进行分配。这种立法例实际上是采取了按照交易量(额)和出资额分配相结合的方式。国外立法则主要采取按照交易量(额)分配的方式,而对于股息的分配则是受限的,并且在分配顺序上也是先分配股息,其余部分再按照交易量(额)进行分配。并且社员分配的股息数额受到立法或者监管部门的严格管制。
社员股金资本收益的限制性也是被国际合作运动所认可的。国际合作社联盟(ICA)在“1937年罗虚代尔合作原则”中确定的七项合作原则之四就是资本的有限收益。这一原则又被国际合作社联盟(ICA)1995年“关于合作社特征的声明”所确定。当然也有部分国家(地区)的合作社立法规定社员的股金不分配股息收益。博茨瓦纳《合作社法》、中非共和国《合作社与农业互助组织法》、南非《合作社法》、毛里求斯《合作社法》、纳米比亚《合作社法》、斯威士兰《合作社法》、赞比亚《合作社法》、马来西亚《合作社法》、尼泊尔《合作社法》、菲律宾《合作社法》、新加坡《合作社法》、巴哈马《合作社法》、巴西《合作社法》,以及我国香港地区《合作社条例》、台湾地区《合作社法》等确立了向社员分配的股息不得超过特定比例的要求①WOCCU,Guide to International Credit Union Legislation,Madison:World Council of Credit Unions,Inc.,2008,pp.12-308.。
从这些立法例来看,合作社立法对社员股息收益的限制实质上是淡化社员出资的资本性,转而以社员促进合作社发展,即以社员与合作社之间的交易量(额)作为主要收入分配的标准。在这一方面,社员来自合作社的收入与社员附加投票权的配置机理是一致的。如果没有给予这些对合作社发展做出较大贡献的社员以较大的分配收入,则附加投票权的配置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利益激励基础。对于营利法人社员而言,现行合作社立法也应当主要采取根据交易量(额)进行盈余分配的原则。《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存在的问题在于依据出资额向社员分配盈余的比例过高,而且分配顺序有待于调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17条确定了合作社可以根据出资额向出资较大的社员赋予附加表决权,只是附加表决权数量不得超过基本表决权总数的20%。但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37条的规定,出资额较大的社员却可以享有最高可达40%的分配盈余,这造成了同一社员在不同规则下的利益差异。营利法人社员可以充分利用这一制度设计的缺陷获得较高的资本收益,而其他普通社员的主体性则会进一步削弱。因此,我国合作社立法的完善应当降低依据出资额向社员分配盈余的比例,并调整盈余分配的顺序,在向社员分配资本收益之后,再向社员依据交易量(额)返还合作社盈余。
以上三个方面从社员权利限制的角度对营利法人社员享有权利的内容进行了分析。这也意味着,合作社立法中营利法人社员权利没有受到限制的部分与其他普通社员享有的权利相同。
六、结 论
政府部门扶持龙头企业领办合作社实际上是试图借助商业资本下乡的力量提高农村小农的组织化能力②仝志辉、楼栋:《农民专业合作社“大农吃小农”逻辑的形成与延续》,《中国合作经济》2010年第4期。,但在制度效果上并未能解决小农在市场上的弱势地位,反而因为龙头企业这一中间商的控制更加边缘化。这种龙头企业盘剥小农的发展路径并没有因为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实施而逐步弱化或者消除,反而在政府部门加大对合作社提供财政资金扶持力度的情况下异化行为更为突出。而现行立法和政策不足以抑制这种趋势。因此,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修改和完善刻不容缓。在尊重现实选择和路径依赖的基础上,合作社立法应当关注龙头企业领办合作社产生的异化行为,坚持合作社劳动互助的基础上适度引入资本和劳动的合作,并确保普通社员享有合作社的剩余权利。如果龙头企业领办的“公司+合作社+农户”的产业组织模式转变为合作社主导的“合作社+公司+农户”,那么,农村小农将是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的最大受益者,合作社的经济社会功能就会得以真正完全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