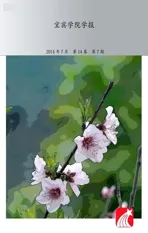世俗与超俗
——基于《庄子》和《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
2014-03-12刘亚明
刘亚明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071)
在《逍遥游》里,庄子终于实现了他的理想世界,借助于“抟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庄子把自由推向了绝对,这是一种超尘绝俗的自由,与尘世没有瓜葛;是一种无所旁待的自由,无需依赖他物;是一种绝对的自由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个性得到完全的解放。这种不接地气的自由是审美的、神秘的心理体验,为一代又一代纤弱而又容易受到伤害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庇护。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庄子的自由又每每受到排斥,这体现了庄子自由哲学根深蒂固的缺陷:对现实的无能为力与无动于衷。
任何一种诱人的理论都是一种指向于实践的理论,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在理解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康德的学说中,他也把实践理性的领域称之为自由的领域。在与个人理性日益张扬、科学蓬勃发展和世俗化倾向越来越强相伴随的宗教的全面溃败、超验的自然法学说资源的日益枯竭的大背景下,规范与事实之间承受着逐渐增强的张力。以民主观念的转向为例,在古典民主理论为代表的“大多数人的统治”的价值判断在近代的熊皮特那里则直接转变为一套纯粹的程序。[1]11而这种民主现代转向则在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那里得到了更为明确的阐释:“多数人统治,仅仅作为多数人统治,就像那些为此而指责它的批评者是一样的愚蠢。但它从来就不仅仅是多数人统治……多数用来成为多数的那种方式才是更重要的事情……换句话说,关键的需要在于改善进行争论、讨论和说服的方法和条件。”[2]376-377
无论多么“形而上”的理论,如果脱离了与事实的链接,就丧失了实现的可能性而化为空想。任何一种理论只不过是在为我们描绘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限度,这个限度接近于理想值,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一个可能性的国度。因为在柏拉图看来,这个国度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只不过是糟糕的现实中的条件尚不具备而已。庄子的自由体系似乎无法摆脱现代理论的诘难:超俗的理论是否是可欲的?
一 一个吊诡现象
世俗化的兴起是宗教作为中世纪秩序合法性源泉资格的丧失而产生的结果,世俗化的进一步发展则更是导致了宗教的全面溃败,在公共事务中再也看不到宗教的身影了。现在的问题是偏居于私人角落的宗教所造成的合法性真空应该由谁来填补?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本篇所关注的是宗教作为西方现代文明得以产生的参与力量之一,是经过怎样的一个过程而对西方世界现代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样的论据来自于马克思·韦伯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作为一种宗教,与庄子相比较,似乎更应该具有“超俗”的性质,然而吊诡的是,新教成为了世俗的资本主义精神促进者,这种强烈的反差原因到底何在?庄子为什么处于世俗之中却有着脱俗的倾向,而新教关注于彼岸世界却成为了导致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力量之一?这种不同的原因到底何在?
二 新教与世俗
在罗马帝国晚期,外族的入侵导致罗马帝国秩序失范,伴随而来的是不断的战争和无尽的苦难。作为人们心灵的安慰品,基督教成为了人们心灵世界得以抚摸伤痛的工具。为了解释虔诚的信教和不断的灾难所带来的巨大反差,奥古斯丁阐释了他的上帝之城和原罪学说。人类祖先在伊甸园犯下的罪行一代代传给了他们的子孙,世间的种种灾难就是上帝为了惩罚人类的精心布局。但是,虔诚地笃信上帝在虔诚者、非虔诚者和不信教者之间造成分野,一个是上帝之城,一个是世俗之城,这两个城在平日里隐而不现,直至末世审判。但虔诚的信仰并不能免除灾难,因为作为“上帝选民”的那一部分是上帝随意抽取的,并不取决于你的虔诚程度,即便这样,虔诚的信仰仍然不可缺少,因为我们面临着末世大审判,这个大审判中,地上之国和上帝之城将要分离,虔诚信教的人则最终归于上帝之城。至于为什么上帝随意抽取自己的“选民”,似乎蕴涵于这样一种意味中:上帝是至高无上的,是人的理性所无法企及的,如果按照虔诚程度来划分人们的“选民”与“非选民”的标准,在世俗的人世间就能够有一种明显的标志将被人类所区分和认识,这不符合上帝至高地位。上帝的意志是人类的理性无法加以把握的,是神秘的。即便这样,后来的发展表明,人类试图在世俗间找到这种区分的努力一直在继续,这源于他们的一个信念:对上帝的虔诚一定能够在人世间找到标志,因为这种信念也来源于上帝冥冥之中的启示。这种信念为改革后的新教注入了一股强劲的世俗之风,这也标志着新教产生资本主义精神的原初萌动。
在整个中世纪,宗教是社会结构的合法性源泉。上帝的至高无上保证了这种合法性的延续,世俗的政权也借助于这样的合法性而得到自己权力的巩固。在托马斯·阿奎那那里,在传统的自然法之上又加上了永恒法和神法。虽然融入了人类的理性,但永恒法高高在上,上帝还是唯一的合法性源泉。路德的宗教改革架空了教会机构,主张信徒通过《圣经》而直接与上帝联系,教会不再掌握有“救赎”的独断权。原罪意识导致了人们的极度紧张和过分压力,“救赎”则是缓解这种心理压力的唯一通道。
为了获得救赎,为了给上帝增加荣耀,新教徒们需要实践生活的理性化。“在加尔文教里,一般信徒的伦理实践丧失了它那无计划的、不系统的特征,而被模塑成一种逻辑一致的、有条理的对他的生个生活的组织……救赎,然而恰恰就是这个原因,他在现实的实践生活进程被彻底理性化了”[3]74,在这种理性的组织下,人们进行有节制的控制,对抗感情而造成的某种禁欲主义造就了一种新的人格:警醒和自知,而这又进一步摧毁了自发本能的享乐,从而摆脱了自然状态进入到高级状态,“正如这种积极的自我控制构成了一般而言的修道士美德的最高形式,这一积极的自我控制也构成了清教所定义的实践生活理想。”[3]75
而“旧约”的理性定义对新教徒也产生了很大影响,“预定论”使得信徒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工具,是神意的执行者,这就意味着能够发现救赎的记号,这就把信仰和世俗伦理连接了起来。在建立起来的有条理的理性伦理组织中,人们通过“善工”获得了得到救赎的确定性,与加尔文教的初衷相反,信仰获得了一种商业气息,“与加尔文的原初教诲相反,清教徒知道上帝为什么这样或那样决定。因此,使生活神圣化的努力就这样几乎获得了商业的特征。”[3]79善工成了获得救赎的手段之后,为了尽天职而获得财富在道德上不仅是允许的,而且也变成了一种道德期待,相反,为了安逸和享受而获得的财富则在道德上值得怀疑。[3]105这样就产生了合理获利的道德观念,并用它来挑战财产的非理性使用,成为了一种商业道德。这样,一种基于新教的禁欲主义就被转化为世俗的功利主义。韦伯把他的这种诠释称之为“可能性”研究,用以区别那些独断的唯物论和唯灵论分析,“如果这两种分析声称的是调查的结论而不是说调查的准备阶段,那么它们对于揭示历史真相没有什么帮助。”[3]119
“不将毫无节制地获利贪欲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能等同于其‘精神’。相反,可以将资本主义视为对这种非理性的动机的控制,或者至少等同于对这种欲念的理性缓解。尽管如此,资本主义的特色就是通过追求利润体现出来的,而且实际上是在资本主义企业中以一种理性的、持续的方式来追求利润,反复不断地追求利润,因此他追求的是获利性。”[3]4在韦伯看来,获利行为不仅在古代欧洲,而且在古代亚洲各国也都有体现(比如说在中国),这种资本主义是一种古老、持久和普遍的现象。另外一种资本主义被称为投机资本主义,主要指在古代和近代所从事的通过战争、海上掠夺或是强迫劳动而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不过,现代西方在现代还发展出一种完全不同的资本主义类型。这种资本主义在西方以外的其他地方都不曾见到……是对自由劳动力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的组织为基础的。”[3]7这才是韦伯真正想要讨论的“资本主义”,“西方资本主义所有的这些独特性所获得的今日的重要意义,归根结底来自它们与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的关联性。亦即可转让的有价证券的发展以及通过证券交易市场的投机活动的理性化。”[3]8
如此可见,新教伦理导致现代西方社会独一无二的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以自由的劳动力组织为基础,这种理性的组织来源于新教伦理。最终,作为宗教的新教在世俗中结出了商业化的果实,而庄子的“逍遥游”则无可避免地把人们引向个人的世界,对现实世界的疏远导致了庄子的学说远离了现实的大地而高高飘在天上。
三 庄子与超俗
按照人们一般理解,宗教是人类社会早期面对不可抗拒的外力而产生的,大抵从中华文明的早期,商周时期开始曾出现过“天”“上帝”等概念,但并没有发展出系统的宗教体系,即便本土生长的道教和外来的佛教都没有能够在中国取得像基督教在西方世界那样的统治地位,相反,他们却随着政治力量的青睐与否而沉浮不定。中国的主流文化承袭了“子不语怪,办乱,神”(《论语·述而》)的传统,抱有“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的务实态度,而对彼岸世界不感兴趣,形成了中华文明特有的人文主义倾向。在崇尚“知天命而用之”的荀子那里,更是没有了宗教的容身之地,因为在中国儒家思想家看来,现实的世界靠积极的人为和深度介入社会才能治理好。在哲理化程度较高的道家那里,“道”的至高无上性也没有给上帝留下位置。在老庄眼里,“道”是万物的总根据,是万物之所以为万物的原因,是万物运转变化的驱动力,是一种没有意志的律令,与上帝根本不同。
庄子试图在主观的世界里齐物我,同是非,等贵贱,最后抵达绝对自由的无何有之乡,这是依据于“道”的结果。由于道的至高无上性,立足于道,庄子是在俯视整个世界。站在道的至高点,一切常用的价值尺度将陷于崩溃,整个世界都变成了一个齐一的世界。庄子这个观点是普罗太格拉“人是万物的尺度”命题的反题,从人本身而定的尺度只能是相对的尺度,绝对的尺度是“道”,“以物观之,物自贵而相贱,以道观之,物无贵贱”。这似乎是一种绝对的平等,这种近乎于等同的平等思想其外延是无所不包的,从人类社会到自然界,从细小的微生物到庞然大物……
出于这样的体认,庄子完全处于超然地位,宇宙不再是人类独有的家园,是万物共享之世界,世界也不再以人类为中心,人类社会也不再是庄子优先考虑的对象。为了契合于道,庄子试图剥夺人类的智性、试图褫夺人的社会性,把人从社会性的自觉之人改造成自然性的本能之人。只有通过“心斋”“坐忘”等方法,人们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才能最终到达无何有之乡。
虽然没有宗教彼岸世界的观念,但庄子这种缺乏实践指向的思维进向把人引向了内心世界,最终走向脱俗,这与新教的切入现实的功能形成了吊诡现象。庄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思想,由于关于庄子本人的资料实在是少之又少,只能靠后来人的猜测与推断,与他同时期的孟子并没有提到庄子,或许真的就像后来朱熹说的那样 “无人尊之,只能在偏僻处自说”。即使这样,庄子生活的大体社会背景可以略知一二:战争与动荡,社会的大变动与大整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庄子本人独特的心理感受或许可以还原为柏林说过的一段话:
我是理性与意志的拥有者;我构想目标也希望追求这些目标;但是如果我受阻而无法实现它们,我便不再感到是这种状况的主人。我可能受自然规律组织,受偶然事件、人的活动、人类制度常常是无意阻止的结果。对我来说,这些力量太多了。我应该做什么才不至被它们碾压?我必须自己从那些我知道根本无法实现的欲望中解脱出来。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疆域的主人。但是我的疆域漫长而不安全,因此,我缩短这些界限以缩小或消除脆弱的部分。我开始时欲求幸福、权力、知识或获取得某些特定的对象。但是我无法把握它们。我选择避免挫折与损失的办法,因此对于我不能肯定地得到的东西绝不是强求。我决意不欲求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如果我在我的心中已经扼杀了我的自然情感,那么,他无法让我屈从他的意志,因为我剩下的一切已不再会屈服于经验的恐惧与欲望。我仿佛做出了一个战略性的退却,退回到我的内在城堡——我的理性、我的灵魂、我的“不朽”自我中,不管是外部自然的盲目力量,还是人类的恶意,还是人类的恶意,都无法靠近。我退回到我自己之中,在那里,我才是安全的。[4]183-184
在自由主义大师柏林看来,“这是传统的禁欲主义者与寂灭论者、斯多葛派和佛教圣人、许多宗教或非宗教人士的自我解放之法。他们借助某种人为的自我转化过程,逃离了世界,逃离了社会与公共舆论的束缚;这种转化过程能够使他们不再关心世界的价值,使他们在世界的边缘保持孤独与独立,也不再易受到其武器的攻击”。通观庄子的文章,这样的分析大抵上可以解释庄子为什么会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而没有介入到社会实践中去。庄子深深感到个人面对整个社会时的那种无力感,个人所面对的既定社会习俗和流行观念就像一张巨大的网络,天下所有人尽入其中。要想在社会中追求自己的自由,遇到的阻力是巨大的,相反,通过消除自己的欲望而专注于内心世界则是成本低廉的选择。
庄子告诉我们:通过“坐忘”“心斋”等方式,可以体会到“道”的存在,并在《逍遥游》中提出了自己的理想人格:“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穅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这个理想人格体现了庄子的价值追求:扬弃世俗,提升自我,达到一定境界之后,能够不为任何事物所动,也不能被任何外力损伤,很好地印证了柏林所说的那一段话。这样,庄子的思想反而为中国历史上受到挫折的人提供了一个庇护所,有了某种宗教功能,而西方经过宗教改革的新教则成了人们积极尽“天职”的精神动力,成为了促进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参与性力量。
结语
当然,对庄子和新教的理解,不同的人可能作出不同的理解,假若本文的理解基本上符合逻辑,韦伯的分析也没有太大的偏差,那么这样的现象真是令人惊奇。中西文化的不同特质有待于后继者的不断探索,在中西文化的不断勘对和交流中,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
参考文献:
[1] Frank Cunningham. Theories of Democracy:a critical introduction [M].London: Routledge,2002.
[2]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童世骏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3]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苏国勋,覃方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4] [英]柏林.自由论[M].胡传胜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