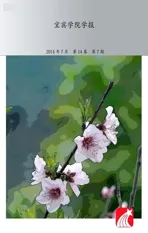康德先天范畴与张载德性之知
2014-03-12程洁如
程洁如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 北京 100872)
康德认为知识有两个来源:一是感官获得的感觉经验,一是人脑固有的先天认识形式。并且,“无内容之思维成为空虚,无概念之直观则成为盲目”[1]71,二者在知识的形成过程中缺一不可。其中,人脑固有的先天认识形式包括感性直观形式和先天知性范畴。感性直观形式即时间和空间;先天知性范畴是康德依据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表确立的包括存在性与非存在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等在内的十二对范畴,这些先天范畴好比有色眼镜,人们对于客观存在的外部世界的感知总是通过有色眼镜(即先天范畴)来实现,先天范畴是人们获得经验的条件。
张载的认识论同样认为知识的获得是“内外之合”的过程。“人谓己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内外之合也”[2]25,“知合内外于耳目之外,则其知也过人远矣”[2]25。而“内外之合”的结果是为了达到“闻之见之而知之审,不闻不见而理不亡”[3]124的境界。即知识分为见闻之知和德性之知,见闻之知是通过耳目等感官与外部事物相接触而获得的具体的知识,是“耳目有受”的结果;而德性之知“合内外于耳目之外”,不起于见闻,是天赋的道德良知,属于“心中之理”。而“天下之物皆用也,吾心之理其体也;尽心以循之,则体立而用自无穷”[3]121,即心中之理与天下之物是体与用的关系,只要我们通过“尽心”的心性体验来体悟心中之理,则能够进一步获得关于天下之物的知识。因此,即使“不闻不见”,仍然可以“理不亡”。
康德的先天范畴与张载的德性之知同为认识论中的范畴,二者虽然形成于不同的时空,彼此之间存在着差异,但仍然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康德的先天范畴与张载的德性之知的比较可从先天性、“思维”在先天范畴的经验对象、德性之知体悟过程中的角色以及目的和价值取向四个方面比较。
一 先天性的同一
康德认为人具有先天认识能力,并且与经验论和唯理论片面强调感性认识或者知性认识不同,康德主张把感性认识与知性认识结合起来。即人的先天认识能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先天感性直观形式(即时间和空间),一是先天知性范畴。认识首先通过先天感性形式获得关于认识对象的杂多表象,然后通过先天知性范畴对获得的杂多表象进行综合获得知识。先天知性范畴在认识形成的过程中赋予获得的杂多表象之间以“关系”,是由感性直观获得的杂多表象通往知识之间的津梁。
然而,先天知性范畴作为获得知识的一个条件,并不从属于认识的对象,也不能够通过经验来获得。作为纯粹的知性概念,它们是先天的,并且先于经验存在于人的大脑中,将人的直觉置于纯粹的知性概念之下,客观存在的外部事物总是通过纯粹的知性概念(即范畴)来被感知。从这个意义上说,先天范畴与认识对象和经验无关,而是先天地存在于认识主体的思维中。正如康德所说:“一切知识虽以经验始,但并不因之即以为一切知识皆自经验发生”[1]27。有一种先天的知识,它不根据任何经验,却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特点。康德在这里虽然特指的是数学,但是范畴作为纯粹的知性概念,同样也是不根据经验、先天却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
张载将知识区分为见闻之知和德性之知。“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2]24,即见闻之知是感官与具体事物相接触的过程中获得的知识,是后天形成的关于具体事物的知识,“非德性所知”[2]24。而德性之知“不萌于见闻”[2]24,不能够从经验也即感官与事物的接触中获得,也不是关于具体事物的知识。它超越感官与经验,既不能直接从经验中获得,也不依赖于耳目感官,而是源于天赋,属于道德良知的范畴,只能通过孟子提出的尽心、知性、知天的心性体验来体悟。
从某种程度上说,见闻之知相当于通常所说的感性认识,但是德性之知却不同于针对感性认识而提出的理性认识。因为理性认识虽然是通过抽象思维来实现的,但这种抽象思维是建立在感性认识所获得的感性材料基础上的,仍然与经验有关,离不开经验。但德性之知超越经验,不直接与经验有关,它只能通过主体神秘的体悟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德性之知也是超越感性经验的先验知识,与康德的先天范畴都独立于经验而具有先天性。
同时,康德的先天范畴和张载的德性之知不仅在先天性上同一,都独立于经验而先天地存在于主体自身中。并且,二者都具有先天的潜在性。“德性之知”作为道德范畴内的知识,不是作为明朗化的知识直接显现在主体自身中,主体只有通过不断向内的心性体验才能体悟到德性之知。并且由于每个主体的修养不同、心性体验的程度不同、所体悟到的德性之知也不均等,康德的先天范畴虽然由明确的十二对范畴构成,但这十二对范畴在对感性纯直观所获得的杂多表象进行综合的过程中也不容易被认识主体所察觉。主体并不是对杂多表象先进行量的分析,再进行质、关系和样式的分析,而是同步进行。如同我们看到一个杯子,不会先看到它的颜色、再看到它的材质等,最后才意识到这是一个杯子。因而范畴在经验对象的过程中也表现为潜在的存在。不同的是,德性之知虽然源于天赋,但是作为区别于见闻之知的知识,属于知识的领域。而先天范畴虽然也属于知识的范畴,但更多地表现为获得知识的途径以及为所获知识的合理性提供依据。
二 “思维”的中介作用
康德的先天范畴被确立起来后并不是被动地存在于知性之中,等候被发觉,而是积极地参与人的整个认识过程。先天感性直观获得关于认识对象的杂多表象之后,先天范畴便通过“直观中把握性的综合”、“想象中再现性的综合”以及“概念中认知性的综合”三个程序将感性直观获得的杂多表象进行综合,从而获得知识。在这个过程中,先天范畴作为“预设”先天地存在于人的大脑中,并且自发、主动地发挥作用。
同时,这种自发性、主动性与认识主体思维的主导作用分不开。先天范畴作为认识主体的先天认识形式,只是大脑中的一种“预设”性的存在,它在知识形成的过程中不能孤立地发挥作用,而必须要有思维的参与。也就是说,对杂多表象的综合是思维与先天范畴综合作用的过程。一方面,如果没有先天范畴,思维无法对对象有清晰的认识,更无法把感性直观确定下来的杂多表象理解为知识的来源。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思维的综合能力,人就无法把先天范畴应用于杂多表象,先天范畴正是借助于思维的知性能力来参与认识的过程,在认识的过程中,思维充当了先天范畴与杂多表象的中介。
张载德性之知的体悟也离不开思维的中介作用。它不是由具体的经验知识概括而来,而是依赖于主体自身的内在自觉和体悟,也就是尽心、知性、知天的心性体验。虽然这种自觉、体悟和体验不是正常的思维活动,但也必须有思维的在场。具体来讲,张载认为对德性之知的体悟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实现的:一是“大心”。“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2]24,“大心”即意味着主体需要扩展自我思维的能力,把自我之心当作认识对象,使自我之心达到与“理”的合一。二是“尽心”。“故思尽其心者,必知心所从来而后能”[2]25,张载在这里吸收了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的思想,但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并不是在同一平面展开,所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4]101,尽心是知性进而知天的根本,只有尽心,才能够知性,进而知天。即万物的本性都来源于天赋,只要向内体验到自己的本心,便能够与万物的本性相通,进而达到天人合一。德性之知作为天赋的本性,也必须通过思维向内体验的过程才能体悟到。因此,不论是“大心”还是“尽心”都离不开思维的参与。
继承了张载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提法的马一浮先生也认为:“若不入思惟,所有知识都是从闻见外烁的,终不能与理相应。即或有相应时,亦是亿中,不能与理为一。”[5]20意谓从闻见外烁的知识即见闻之知不能与理相应,即使有时能够与理相应,也不能够与理为一,因此,只有通过思维才能体悟到理,与理相应,进而与理为一。思维的向内体悟是获得德性之知的途径。换言之,只有通过思维的向内体悟而获得的德性之知才能够与理相应,进而与理为一。这也说明了思维对于德性之知的必要性。
虽然康德的先天范畴和张载的德性之知都需要思维作为中介,但思维在康德的先天范畴和张载的德性之知那里却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先天范畴和德性之知都是来源于天赋,具有先天性,但德性之知并不是在每个人那里都表现为明朗化了的知识,而只是潜在的存在,它需要主体不断地向内体验本心才能够获得。所以,思维是在主体向内体验本心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充当的是尽心与德性之知之间的中介。而先天范畴则是作为纯粹知性概念直接先天地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思维的作用只存在于先天范畴对杂多表象进行综合的过程中,充当的是先天范畴与杂多表象之间的中介。
三 目的性的同途殊归
康德以前的认识论把感官看作一块“白板”,认为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是对象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我们才能获得知识,所以要检验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必然要把知识与对象相对照,让知识符合对象。而休谟的怀疑论打破了这种认识论的合理性基础。他把知识分为两大类:关于观念的知识和关于事实的知识。关于观念的知识与经验无关,所以只要符合自身的法则便具有普遍必然性,但它提供的只是概念上为真的知识,无法推出人类的全部知识;关于事实的知识虽然与经验有关,但经验具有偶然性,它是由人的各种感觉印象或者部分人的感觉印象组合而成的,但如同我们不能看尽所有的天鹅后才认为天鹅是白的一样,我们不能穷尽所有的经验。这样,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就成了问题。
为了解决知识的普遍必然性问题,康德在认识论上进行了“哥白尼式的倒转”,认为如果知识符合对象行不通,那不如让对象来与知识相符合。康德认为人在获取知识方面具有主动性,我们在认识世界时并不是一块“白板”,而是会把自己特定的认识形式加入到经验中。即我们的知识确实来源于经验,但在经验之前,主体自身已具备一套认识形式。这些形式先于经验并且作为形成经验的条件存在于人类的大脑中,从而使知识具有了普遍必然性和先天性。因而,在检验知识与对象是否相符时,让对象符合知识也就是主体固有的先天认识形式。同时,知识的形成包括感性接收质料和知性整理质料的阶段,感性接收质料阶段的先天形式是感性直观(即时间和空间);知性整理质料阶段的先天形式是先天知性范畴。先天范畴作为主体固有的知性的先天形式,它的目的是为了担保知识的普遍必然性问题。
张载虽然将知识划分为德性之知和见闻之知,但两者的地位并不平等。“人本无心,因物为心。若只以闻见为心,但恐小却心。今盈天地之间者皆物也,如只据己之闻见,所接几何?安能尽天下之物?所以欲尽其心”[2]333。见闻之知是人的感官与外界事物相接触而获得的知识,由于外在事物总是个别的具体的存在,所以通过“见闻”而获得的知识只是关于具体事物的知识,是小知。而盈满天地之间的都是物的存在,如果只以见闻之知为知,则不能够穷尽天下所有的事物。因此,德性之知是必要的,如前所说,德性之知作为“心之理”,与“天下之物”是体与用的关系,“体立而用自无穷”,体悟到本心的理也就穷尽了天下万物之理。即德性之知不是通过感官经验获得的关于具体事物的认识,而是建立在“大心”、“尽心”的心性体验基础上的知识,是超越见闻之知之上的大知,因而“能尽天下之物”。
然而,德性之知“能尽天下之物”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确保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中国古代的认识论总是和修养观联系在一起,张载关于德性之知和见闻之知的划分同样是以人的修养为最终目的。“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2]24。他肯定见闻之知的存在,但又认为见闻之知束缚了圣人的修养。圣人应当不以见闻之知为知,而是通过“大心”以及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的心性体验来体悟德性之知,进而达到对于天理的体悟。同时,张载还将人性划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人生而俱有的,是纯善的;而气质之性是人生之初所禀受的阴阳二气的差异所形成的,是有善有恶的。因此“学者必须变化气质”。这样,张载便为圣人的修养功夫提供了两条进路:一是由气质之性反到天地之性;一是由见闻之知上升到德性之知。
四 价值取向的迥然不同
康德的先天范畴要解决的是整个知识大厦的合理性问题,而知识的合理性问题并不直接包含道德和价值的取向。在休谟的怀疑论使经验论和唯理论都陷入困境,无法担保知识的普遍必然性时,康德试图通过在认识论上设定进行认识活动的主体自身具有先天的认识形式,来担保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先天认识形式即感性直观和知性范畴,在经验之先并作为经验的条件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中,使我们在追求知识时能够先天地经验对象。这样,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就得到了保证。因此,先天范畴的确立只是为了构成知识合理性的基础,并不包涵价值的取向。即便是在关于主体意识的论述过程中,侧重的仍然是主体意识在知识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而不是主体自身的塑造问题。
从先天范畴本身来看,知识也不存在价值的取向。康德依据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表来确立自己的范畴表,但他不满意形式逻辑空洞的形式。首先改造了亚里士多德范畴表中的一些逻辑形式,并赋予其新的内容,确立由量、质、关系、样式四个部分组成,同时每个部分包含三种判断形式的逻辑判断表。并进一步以判断表为基础,根据判断表中逻辑形式的分类确定范畴的分类,确立了与判断表一一对应的范畴表,即范畴表也是由量、质、关系、样式四个部分组成,每一部分包含三对范畴共十二对范畴。以“样式”部分为例,它包括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存在性与非存在性、必然性与偶然性三对范畴,这些范畴本身并不涉及道德和价值的问题,而只是用来预设感性直观获得的杂多表象之间的关系。因而康德能够进一步将范畴表应用到自然界,创造自然科学普遍原则表。因此,从范畴表确立与应用的过程以及十二对范畴本身来看,好像都只关乎逻辑,而无关乎道德与价值。
而在张载那里,“德性之知”包含着道德修养的成分,有特定的价值取向。宋明理学家们认识论的核心主要集中在人所以为人的规定性方面,总是脱离不了人的道德性和伦理性,而对于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则关注得比较少。即使涉及到外在于人的客观事物,其目的仍然是为了人的道德性和伦理性的存在寻找依据。张载的认识论作为宋明理学语境下的产物,自然脱离不了时代环境的影响。他的见闻之知作为人的感官与外物相接触而获得的知识,已经关注到了人之外客观存在的万事万物。但见闻之知并不是他认识论的最终目的。他认为我们不应当局限于见闻之知,而是应当通过不断向内的心性体验去体悟天赋的天德良知,即德性之知。由于对德性之知的体悟发生在主体之内,必然涉及到主体自身的修养问题。因此,对德性之知的体悟是主体自身不断修养进而达到与理合一的过程。它侧重的不是知识形成的过程,而是主体自身的塑造过程,主体塑造自身的过程中必然包含着一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
从德性之知本身来看,张载认为“诚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闻见小知而已”[2]20。德性之知不是关于具体事物的“闻见小知”,而是“诚明所知”之“天德良知”。“天德良知”本来就属于道德的范畴。至于“诚明所知”,张载首先区别了“诚明”与“明诚”:“自诚明者,先尽性以至于穷理也,谓先自其性理会来,以至于穷理。自明诚者,先穷理以至于尽性也,谓先从学问理会,以推达于天性也”[2]330。德性之知作为“诚明”所知而非“明诚”所知,其“尽性”以至于“穷理”的过程,必然也只能通过德性的修养才能达到,而德性修养的过程必然以某种价值为取向。同时,张载又进一步将“诚明”解释为“性与天道不见乎小大之别也”[2]20,“不见乎小大之别”意谓主体的认知要达到与理为一、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与理为一、天人合一的境界便为人性本善以及仁、义、礼、智、信等儒家伦理思想的合理性提供了根据。因而,张载在《西铭》中进一步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人生境界观,认为天地万物一气,与我同性,都是我的同胞,因而应当把儒家的仁爱推广到万物人类。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载的德性之知以儒家的伦理思想为价值取向。
结语
康德的先天范畴作为大脑固有的先天认识形式,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将以往的知识符合对象转变为对象符合认识主体的先天认识形式。张载的德性之知作为区别于见闻之知的天德良知,通过认识论二分的方式为主体自身的修养提供了道德的进路。二者都属于认识论的范畴,都是主体先天固有,不直接与经验有关。并且,先天范畴先天地经验对象的过程以及德性之知体悟的过程都需要“思维”的参与。但二者毕竟产生于中西方不同的哲学语境,在目的性以及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差异。先天范畴要解决的是科学知识的合理性问题;而德性之知追求的是主体自身的修养以及对天德良知的体悟。同时,先天范畴并不直接包含价值的或道德的取向;而德性之知属于道德良知的领域,以儒家的伦理纲常为价值取向。总体说来,先天范畴与德性之知的异同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虽然存在差异,但也并不是不可通约的,而可通约之处不一定表现在哲学体系的建立,哲学问题的解决方式上,更多的是表现在问题意识上。
参考文献:
[1]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M].蓝公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2] 张载,章锡琛校.张载集 [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 [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 孟子.孟子 [M].朱熹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5] 马一浮.秦和宜山会语 [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