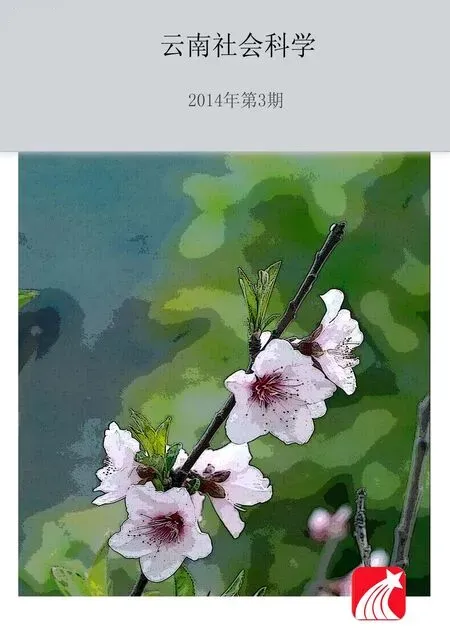乡土的消失:当代文学中的乡土叙事
2014-03-12郑迦文
郑迦文
关注今天的文学创作,会发现一个不争的事实:乡土的消失。这不仅指题材内容的转变,也指“想象故土”的方式,更是指现实生活以及文学意境的改变。《中国文情报告(2012-2013)》中指出:“在2012的长篇小说中,最令人为之惊异的,还是乡土题材的式微与变异,那种传统意义上的乡土小说已经很难找到了。与乡土生活有关的长篇小说写作,更多地为那些描写城乡交叉地带的城镇生活的作品,以及那些带有田野调查意味的纪实类作品所替代。这种变化也许带有某种标志性意义,即旧有的乡土文学写作,开始走向终结。乡土文学的时代转型由此拉开了它的新的帷幕。”[1](P3)这里所指的乡土文学,“是指那种以乡土社会为舞台、以乡土人物为主角的相对纯粹的乡土题材作品”[1](P23)。如果将乡土文学置于整个当代文学的叙事中进行考察时,则可以发现:消失只是一个结论,考察其是如何消失的,却是一个命题。
一、乡土文学的三大基本品格
站在“乡土”的本意上追溯,乡土的消失其实是乡土文学出现的起点。
从社会学来看,“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2]。在这个基层中,人们是一种“差序结构”,如“一枚石子投入水中”所引起的水波状结构,在其中,人与人是熟识的,人与泥土的关系是亲近的。它所包含的是整个基层社会,囊括了所有乡绅、文人(朝堂之外)的生存空间,也正是这样,在古代文学中常常看到的是“朝”与“野”、“出”与“入”,“穷”与“达”的对立。从“田园将芜胡不归?”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再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的感叹,甚或是“大隐隐于朝,小隐隐于市”的出世原则,“进”“退”之间,发生改变的并不仅是乡土的转换,而是“天下”与“我”之间的转换。文人与土地之间密切的关系,使得“乡”是每一个文人最终的归宿。因此,南帆先生曾这样描述:
中国古典文学并没有明确地将乡村视为一个文化空间。长河大漠,孤烟落日,细雨微风,春花秋月,这一切在文学之中如此自然,以至于如同生活本身。换一句话说,文学之中并未出现另一种相异的文化空间,人们无法根据框架之外的内容觉察框架的存在。‘他者’的阙如必然导致‘自我’的模糊。相对于乡村的城市并没有显出抗衡的意义。相当长的时间内,文学并未意识到,城市从属于另一种文化结构、社会关系以及另一套生活经验。[3]
这也正是为什么“五四”时期围绕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而展开的一系列以解放、觉醒、改造为目的的叙事中都表现出这一个共同的特点:记忆中的乡土。然而又表现出三种具体的倾向与品格:第一种是乡土病或者换言之故乡的悲歌。在日常生活及风俗描写中发掘乡土社会中文化传统所产生的精神的弊病。如鲁迅笔下未庄、鲁镇中生活着的祥林嫂、还是阿Q、抑或是闰土、甚至华小栓。精神的麻木、精神胜利法、人血馒头,或者如蹇先艾《水葬》中描写的“老远贵州”的沉塘恶习,于在贵州仅生活三年,六岁就离彼去京的蹇先艾,对“老远贵州”的叙述,更多的其实并不是叙述一个关于乡土的事实,而是对乡土疾病的回忆与文学想象;第二种,是以茅盾的《春蚕》《秋收》《残冬》等作品为代表的“农家苦”的乡土文学品格,尽管这也是在故乡的意义上描写,但如茅盾自己所说,他的创作尤其留心的是“穷人的眼泪”[4](P13)。在他的多部作品中,反复讲述的其实都只是同一个故事——老实、勤奋的农民无法维持基本的生计,以及由此而催生出的反抗的萌芽;第三种,则是曾为批评家们所诟病的乡土趣的描写,它侧重于乡土中的地方色彩描画,在周作人的笔下津津有味地描绘着《故乡的野菜》,烟雨中别致的《乌篷船》等美食、风物,而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等作品中也大量地出现了诸如“三月三看鬼火”等充满田园情趣的乡土叙事。这三种基本叙事品格,尽管裹挟了各类新文学人物、流派甚至党派之间的观点、态度的冲突与书写,然而它们却共同地奠定了新文学对农民世界,即乡土叙事的三种书写方式。
如果说乡土病描写中强调的是作者的胸臆隐现的乡愁——即启蒙和疗救的必要性,而在农家苦的描写中强调的是农民革命的合法性的话,那么乡土趣则更加着重表现田园牧歌中的乡土情。然而无论强调的是哪一端,乡土都是以回忆或想象的形式出现,并藉由此形成了新文学中的一大文学类型,的确,当叙事者早已不再同构于乡土这个生存空间,也不再承载朝与野的联结者,而成为出离于乡土之外的观察者、批判者时,真正意义上的乡土文学还存在么?
二、乡土文学的基本姿态:回望与延续
翻开萧乾在1935年时写下的“虽然你是地道的都市产物,我明白你的梦,你的想望却都寄托在乡村……嫌都市的烦扰,你难道就不讨厌乡村的单调吗”[5]一文,对比2010年回乡的梁鸿写下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教书,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意的文章,一切都似乎没有意义。在思维的最深处,总有个声音在持续地提醒自己:这不是真正的生活,不是那种能够体现人的本质意义的生活。这一生活与自己的心灵,与故乡,与那片土地,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6]可以发现,在这一类的主流文学创作中,充满矛盾的胸臆,以及回望的姿态从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尽管乡土文学无论是作为一个批评术语还是作为文学创作本身,在1940年代也一度被顺理成章地替换为农村题材的作品,然而前文所述的三种基本品格,却一直延续在创作的脉络之中,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各自演绎出新的成果:苦的品格走向新的一面,即过去的苦与今天的甜的对比叙事,翻身颂歌唱出了革命的冲动和激情,诸如《创业史》《金光大道》等类型的乡村叙事比比皆是;还有一些小说,尽管也塑造了农家的苦但这种苦更多地被替换为人生的苦和磨难,如《平凡的世界》;而趣的品格,则演绎出汪曾祺小说中那种唯美化的乡土抒情,《受戒》中萌动的小和尚与农家女的真情,甚至《大淖记事》中抚养受伤恋人与生病的夫妻的巧云,尽管其中也不乏地方民俗的描写,然而终究是对人性美的赞赏替代了乡土中的地方色彩,美得超越了时空;“病”的胸臆,其实一直或隐或现地贯穿着整个乡土中国的文学叙事的始终。它或者微观如《陈奂生上城》中对陈奂生因病获县委书记安排住进招待所的经历与性格描写中,所延续的国民性改造的问题,或者宏观如《白鹿原》,从家族叙事的角度,两大家族之间几代人的纠葛出发,将大的国家历史融入家族的叙事,这既是家国一体的重构,更是对传统乡土社会的致敬。这种文学上的回归,或许是进城多年的作家们在想象乡土、批判往日的乡村伦理后,惊讶地发现相较于城市日新月异发展的快速,乡村的时间过于缓慢,缓慢到积淀的最基本的文化结构并没有改变,即乡土中国的“超稳定文化结构”,即“在中国乡村社会一直延续的乡村的风俗风情、道德伦理、人际关系、生活方式或情感方式、世风代变……无论政治文化怎样变化,乡土中国积淀的超稳定文化结构并不因此改变,它依然顽强地缓慢流淌,政治文化没有取代乡土文化。”[7]对这种超稳定结构的描摹,在叙事上彰显了作者描摹历史、书写现实主义的野心,但同时也令乡土文学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它所包含的胸臆——不再是淡淡的乡愁,而是通过重现历史的乡土,消解那些过分唯美的回忆,同时将那曾经被批判的乡土民俗的趣味、传统乡土文化结构的博大精深完整地呈现出来。其后的《笨花》《古炉》等,实际都是一种乡土再造的尝试,在传统、稳固的乡土社会结构中,乡村的政治不再是真正意义层面上的政治,就如《古炉》(上)中的狗尿苔,在他眼中的“文革”前后的大时代,不过是平日积累的矛盾在契机中的爆发,没有一个善良的完人,更没有一个真正的坏人,但他们却相互用强斗横。这个限于一隅的乡村政治并未与大的政治接轨,但却包含着农村长期以来的贫穷化和不平等,“贫穷容易使人凶残,不平等使人仇恨”。这与其说这是一部还原“文革”时期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小说,不如说是探讨乡土中国的超稳定文化结构的破裂。
三、乡土的消失:“被遗忘的农民世界”
2013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在其颁奖词中瑞典文学院盛赞“莫言作品将一个被遗忘的农民世界生动展现在人前,甚至不惜用刺鼻的气息刺激感官,既冷酷无情得教人目瞪口呆,又参合令人愉快的无私,他笔下没有一刻枯燥乏味。”姑且搁置这些判断中的溢美之词,“被遗忘的农民世界”的判断中其实包含两个方面的追问:当代文学中有着怎样的“农民的世界”? 它是否等同于乡土文学?乔纳森·卡勒曾经说过:“小说比任何一种文学形式,甚至比任何一种文字,都更能胜任愉快地充当起社会用以自我构想的样板。”[8](P284)
在这个意义上,莫言确实像鲁迅、沈从文等经典作家一样,用文学的想象构筑起乡土——山东高密乡。但他的乡土更多的是表达作家自我内在的焦虑与恐慌。以《蛙》为例,尽管将深远地影响了我国几代人的重大国策——计生政策置于高密乡的背景下,甚至在结构与形式上都进行了创新,将庞大的农村生育史的梳理置于姑姑的一生的回忆之中,但更像是莫言自己所说的,他笔下的故乡和真实的故乡不同,“是一种文学的情感的反映”。莫言虚构了一个关于命名的乡风民俗,“先生,我们那地方,曾有一个古老的风气,生下孩子,好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命名。譬如陈鼻、赵眼、吴大肠、孙肩。”[9]通过命名中的人名(村民)与器官(身体)的同构,使得这部历时七年完成的作品,与其说在讲述一个乡村医生的故事,不如说是在用文学为生命致敬。开篇饥饿的孩子吃煤的描写,以及《丰乳肥臀》等作品中,可以看出莫言的乡土想象中植根于灵魂深处的“饥饿”记忆和对生命的野性的赞美。借用孙慧芬在《生死十日谈》中所写道的:“这条逶迤在黄海北岸的回乡路我们不知走过多少回。最初是二〇一国道,后来变成了高速公路。我们的目的地总是连着路的两端,要么是从滨城到翁古城,再到青堆子,要么是从青堆子到翁古城,再到滨城。在乡下时,以为这条以翁古城为连接点的路通着的远方,就是世界,可在城里住了一些年之后,猛然发现,乡村才是世界,才是世界的远方,因为在城里待烦了、待久了,最想回的就是乡村。”当文学在路的两端(虚构与非虚构、城市与乡村)分别构建乡土叙事时,这是否就是文学想象本身的暧昧之处?
然而,一边是非虚构在创作与重要文学期刊专栏的推动下形成潮流,拒绝过度想象和凭空想象的创作方式,带来了当下最真实乡村形态的描写:如果说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从口述史的角度切入并描绘了道路对村庄空间的改变的话,孙慧芬则在其《生死十日谈》中通过死亡这一沉重的话题,呈现了村庄中人的生计方式改变后所带来的乡村的死寂。蓬勃的“废墟”——“望着院子前方大片的断壁残垣,这都是谁家的?第一次以有意识的眼光去观察村庄,惊讶地发现,以我家为起点,往前看,竟是一大片连绵的废墟。”这种荒废,既源于乡村在城市化、现代化、工业化发展中逐渐的消解;另一边则是关注当下的作家,竭力呈现的是城乡之间的乡村描写,如刘震云“目前乡村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没有人反映,许多中国作家还停留在对乡村的童年回忆里。不过就算别人不写,我会把这一块补起来。”在他的《我不是潘金莲》中描写的就是城乡交错地带的小城镇李玉莲告状的故事。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应当把乡土文学看作是人与泥土的联系所产生出的文学想象,它始于文学创作主体们进城以后的回望与想象,在乡土叙事的或隐或现的延续之中,最终却因农民与泥土关系的最终改变而成为一阕悲歌。
综上,面对当代文学中庞大的传统文学创作实绩,将乡土的消失落实到某一部具体的小说或某一个具体的时间点,都会造成对当代文学的误读、误判。绵延数千年的乡土作为一个现实空间,尽管在革命和战争的作用下,一步跨入了农村的行政建制空间,但是,作为一个文化空间,乡土从回忆的起点开始,就一直纠葛于农村题材的叙事之中,这也是为何当我们要考察文学中的乡村时,总在乡土、农村与乡村之间裹挟不前一样。应该说,对于乡土小说的创作而言,作家们回望的姿态从未停止,但基于乡村“超稳定文化结构”的瓦解和改变,原来乡土小说创作中基于乡土社会内核的三种品格都随着乡村的变化而消失,剩下的是作家自身的忧虑和焦虑。焦虑的是这种迅猛变化下无处安放的乡村:旧的已经彻底被破坏,新的道德文学次序却尚未建立。面对这样的乡村世界所开展的文学想象,乡土确实早已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