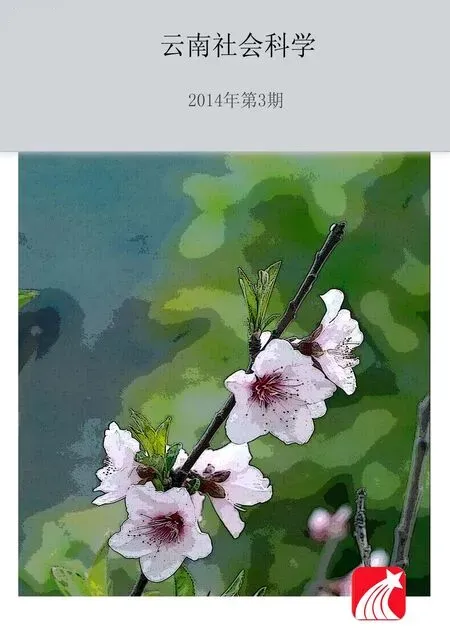论西部边地文化小说叙事的现代性焦虑
2014-03-12金春平
金春平
现代性一词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鬼魅四射而扑朔迷离的概念,它不仅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价值诉求,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准则。按照福柯的说法,现代性是一种文化理念和思维方式,是“一种态度”,“一种由特定人民所作的自愿的选择”。[1](P430)正因为现代性是一种集体认知态度,决定了无论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还是不同个体,都可以对现代性做出自己的理解和实践。但总体而言,“现代性作为一种推动现代化的精神力量,具有三个层面,即感性层面、理性层面和反思超越层面”,“现代性不是其中某一个层面,而是三个层面的整体结构。”[2](P1)与此类似,马泰·卡林内斯库则将现代性分为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并对二者进行了区分:“一方面是社会领域的现代性,源于工业与科学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胜利;另一方面是本质属于论战式的美学现代性,它的起源可追溯到波德莱尔。”[3](P254)而中国西部“边地”,是一个相对于“中心”的命名,它包含着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的边缘性。从地理上考察,西部边地的自然地理与气候条件相对恶劣,在其影响下的西部边地民众也孕育出独特的生存方式和生命观念。从经济角度考察,西部边地又是与“东部繁华中心”相对而言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而且由于物质生活的匮乏,民众的精神状态和民族性格也呈现出了封闭却坚韧的特点。从文化的角度考察,西部边地是与汉民族中原文化而言的异质性和边缘性文化体系[4]。在纵向性的自成体系和横向性的文化互补当中,西部“边地文化”就成为一个形态不断演进、内涵不断充实的带有历史性和时间性的概念。对于身处多重文化空间的西部作家而言,他们既可能表现出对物质现代性(都市文明)的向往,将感性解放作为现代转型的旨归;也可能表现出对乡土封闭形态的启蒙批判,将文化改造作为西部转型的理想;还可能表现出对现代文明诸多弊端的反思与批判,将理念层面的互相制衡作为理想王国,即现代性本身的多维向度,最终导致了西部作家在现代性问题上的分化,以及多元叙事形态,从而在思想发展上形成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继承又冲突的共存局面[5]。多元文明的并存,使叙事主体能置身于不同的文明形态视阈,对最具话语霸权的现代性理念和实践效果进行多元角度的观照和反思,但差异化的理解,也使西部小说的叙事主体认知呈现出普遍的“现代性焦虑”,在折射出中国作家主体性建设困境的同时,也让“文学何为”这一基本命题得以深化和反思。
一、个体与群体:“人文主义”与“革命主义”
现代性的基本内涵,毫无疑问包含了“民主”与“科学”两大主题。而对“民主”的理解,要么滑向对“个体”价值的强调,其潜在的参照价值体系是“非现代性”的封建“专制”体系;但也可能滑向在民族公意的基础上,建立民族共同体,其潜在的参照价值体系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家姓天下”。因此,以民主为核心基点,强调个体价值的“人文主义”与强调民族价值的“革命主义”之间就必然产生内在裂隙,并常表现为“个体自由”与“政治统摄”之间的内在矛盾。“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的西部作家构成,主要是外来的“右派”流寓知识分子,这些作家集体性地对“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苦难进行咀嚼与回味。反观历史政治、反省人生历程、质疑政治灾难等是他们这一时期创作的主要内容。而在一系列的历史记忆与政治回顾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受难者对自身曾经的历史身份与阶级身份的认定,甚至可以说,回归历史情境与政治记忆的首要任务就是确认自身的群体归属。虽然政治身份的认同焦虑不仅仅是西部作家的独有困惑,但当中所贯穿的强烈的对阶级性生存和政治性归属的基本诉求,却由于身处“西部边地”这样一个有着政治重负与历史因袭的文化环境而显得相当典型。
政治体验的生存焦虑表现在小说中,就是当那些“归来者”以回忆的方式反思那段历史噩梦时,对自己在受难期间的身份归属进行的自我辩驳与体验思考,其典型体现就是“人文主义与革命主义”、“个体自由与政治统摄”之间的身份困惑。人文主义在文本中化身为知识分子精英,革命主义在文本中化身为西部底层民众,二者之间是“民间愚昧与知识文化”的教育与反教育,是“政治驯化和思想个体独立”的置换与反置换。这种共存于同一个体的精英与大众之间的身份焦虑,不仅包含着“右派”知识分子归来之后对“文革”造成人的身份失落的历史荒谬的批判,也包含着在特定历史时期政治信仰不断侵入人的原有思想独立体系时,人的无意识反抗的精神生存困境。而通过这样的身份焦虑的曲折表达,西部作家不仅实现了对历史的反思,而且传达了对完美人性的坚守。这种身份焦虑的表达,其“机智”之处在于:它在“右派”改造的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和信仰认同的服膺之下,在貌似迎合意识形态和“左翼”话语的表象下,利用自身的人格分裂困惑和身份焦虑表达,策略而潜隐的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那段荒谬历史的制造者。而身份焦虑突破过程中的精神洗礼、思想改造、人性辩驳,都是传达历史荒诞给人带来的精神剧痛的隐晦表征。其中对个体自由的束缚与向“低级”文化的被迫学习的心灵伤害,都是这种身份焦虑表达的最终指向,这在张贤亮、王蒙、董立勃等作家的文学世界尤为明显。在他们的作品中,政治身份的焦虑主要体现为启蒙者与大众化、个体性与一统化、批判性与合法化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启蒙者的基本原则是对现存社会的否定性,对现实的背叛与超越,“按其先进的主张,它是大拒绝——对现状的抗议”。[6](P54)但是中国社会对启蒙现代性的追求,由于过于急切的现实功利性,放弃了对哲学、宗教和艺术形而上层面的关注,却将希望寄托于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认为唯有它们才能实现民族的复兴。那么在这种感召之下,作家和文学也理所应当的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维护工具。这样,启蒙者的个体性就要让位于政治意识的群体性,启蒙者的批判性就要让位于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于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整合性与个性启蒙身份的独立性就试图寻求一种新的整合,“在通常的情况下,只要一诉诸言谈,作为‘小我’的他就悄然隐去,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则是‘大我’——意识形态”。[7](P345)西部小说就在这种艰难的文本整合中呈现出了明显的裂隙,以国家化的合法外衣隐藏了个体化的批判质疑。
张贤亮小说的叙事立场,在政治合法化的外衣下面,隐藏的却是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与对这场改造运动的“质疑”。体现在作品中就是知识阶层与底层大众之间的错位,由此造成的是西部底层大众的“贬抑化”和知识分子受难者的“神圣化”。在《绿化树》当中,作为“右派”分子的章永璘,本应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需要被教育者,但在“崇尚文化”意识的马缨花看来,他却是一个拥有文化知识的精神优越者,“你是个念书人,就得念书。只要你念书,哪怕我苦得头上长草也心甘”。政治优越者身份的马缨花与政治遗落者身份的章永璘,通过知识这一中介,完成了“愚昧”的“大众”与“文化”的“圣人”之间不平等地位的置换。同样,《土牢情话》中的乔安萍与石在之间源于知识魅力的爱情,《河的子孙》当中的韩玉梅因文明之物——手表而许身于科长等等,都表明了张贤亮在政治改造的合法性外衣下,隐藏的却是知识分子身份优越于底层大众的自信。而作品中所谓的正面人物,特别是女性人物虽然由于西部地域的封闭和传统道德的束缚而呈现出善良淳朴等优秀品质,却因为在文化层面的盲目而无法与知识精英达成精神交流,“政治的导师”最终沦为了知识精英落难的“异化”对象。
董立勃的《白豆》在政治合法化的外衣下,隐藏着对政治“合法”性的质疑,体现出“几乎所有的政治,都要把自己的欲望、利益和理想普泛为大众所共有的,而且是永恒的。……它们的这种‘打扮’带有明显的‘遮蔽性’,即政治愚弄和欺骗”的深刻批判性,[8]在小说中主要体现为政治理性对自然人性的扼杀。当女主人公白豆被迫与人结婚时,“恋爱自由与婚姻自主”可以成为组织营救她的理由;而当马营长看上了已订婚的白豆时,却对吴大姐说:“恋爱自由,婚姻自由,这个道理,你这个妇女干部不会不懂吧。吴大姐说,这我懂,我懂了。马营长说,懂了就好。”[9](P52)作品中老杨因他人威胁而不得不放弃白豆时,“共产党员”这一属于政治正面色彩的身份,却可以成为掩盖自身无奈失败境地的挡箭牌:“我尽管很喜欢白豆,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应该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9](P32)。相反,当马营长试图强奸白豆时,他同样用这个正面身份作为掩盖非人性的理由:“干部工作很紧张,有时候见到女同志,也会开开玩笑。”[9](P157)此外,作品中的杨来顺就具有“革命者”与“小农”双重身份。他虽经历了革命思想的洗礼,但却难以摆脱小农意识的束缚,他没有因为政治的同化而建立起一个革命者应有的思想观念和革命素质,却在世俗斗争中失去了农民本应具备的诸多优秀品质,最终成为一个无赖式的怪胎,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同化与小农个性无法弥合的异化人物。
因此,对于历经政治炼狱的西部作家而言,政治意识形态以它的强制性和神圣性为现实抹上了一层温情的外衣,成为作家在特定历史时期意识形态领域无可辩驳的强大话语权威,一切行为与事件在“政治”与“人民”的宣言下变得合理而合法;但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却由于启蒙思想与批判思想而不断的质疑着政治行为的合理性,不断揭示着诸多虚假表象下的不真实领域,于是国家意识形态的统摄对个性言说自由的束缚,以及个体自由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反抗,最终造就的不仅是“无形的话语权力垄断产生的隐性统治权才是今天政治权力施展的主要手段,……话语权力的垄断已经成为政治权力特别是一元政治权力体制不可或缺的前提”,[10](P280)还有西部作家在小说中所表现出的特殊政治环境下知识分子个体化的政治现代性焦虑。
二、理性与感性:“启蒙批判”与“世俗狂欢”
现代性的内涵,包含了“感性的解放”与“理性的制约”。但由于中国的现代性带有“外迫性”,而非出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内源性”,即西方现代性的入侵,才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推向历史轨迹。因此,现代性在中国本土呈现出了较为矛盾的状态:一方面,出于物质现代性的全民诉求,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经济成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唯一价值,物质感官的解放,终于从政治为纲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物质感官享受获得了国家甚至是法律层面的合法保障;但另一方面,中国文学的价值资源普遍来自于传统的道德伦理,包括儒家的“重义轻利”的价值体系,因此,对于物欲泛滥甚至是物役的束缚,中国作家普遍采取了以道德伦理为核心的中国式“启蒙理性”批判的立场。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中青年小说家所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的社会语境,最能引起他们关注的,则是在此背景下西部城乡世界不断演绎的诸多人生的悲欢离合。西部乡土世界的沉滞与动荡,西部人在社会转型当中心灵的安守、人性的制衡和物欲的诱惑等等现实情境,都使西部作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介入的姿态进行着审视与思考。虽然他们在不断的探索和矫正,但不得不遗憾地说,西部小说作家直到新世纪,其创作的整体价值立场依然是模糊的,甚至在个体作家笔下,价值立场表现出前后矛盾和背离(如石舒清、陈继明等)。现代性焦虑在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中,非西部作家所独有,但能够像西部小说这样,将不同的文化体系,诸如农业文明、都市文明和后现代文化等不同文化因子,将现代性的感性、理性和反思—超越等不同层面同时吸纳并被不同的作家所演绎,这在中国当下文坛格局中是鲜有的,而这种文化的多元与焦虑在西部中青年作家中,具体表现为“启蒙批判”与“世俗狂欢”之间的焦虑缓释和抉择。
世纪之交以来,封闭已久的西部边地同整个中国大地一样,经受着文化开放的冲击,其中对西部乡土冲击最大的当属市场经济的蔓延,它所激发出的是长期被政治话语所压抑的对物质欲望和消费欲望的释放。这一以物质解放即感性解放为主导的文化潮流,冲击着深处边远西部传统的乡土文化联接的人伦关系和乡土伦理,最终给西部中青年作家带来的是文化混乱和价值迷失的焦虑困惑:传统的乡土伦理被人遗弃背离,宁静沉滞的乡土生活开始动荡,而如潮水般涌来的所谓都市文化和现代文化也并未带来预想的实践效果,甚至他们一度怀疑在西部以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为根系的文化机体上,新兴文化能否生根发芽,这些新兴文化是否是一场喧嚣闹剧和虚幻蜃楼。西部中青年作家在面对这一措手不及的文化侵袭时,陷入了难以明晰的价值认知和文化焦虑当中,由此也形成西部作家价值立场与文学叙述的分化与动荡。对于这样的身份焦虑与价值混乱,一些西部作家也试图进行文化精神的重建和心灵家园的寻觅,“那些文化上灾变性的大动乱,亦即人类创造精神的基本震动,这些震动似乎颠覆了我们最坚实、最主要的信念和设想,把过去时代的广大领域化为一片废墟(我们很有把握地说,这是宏伟的废墟),使整个文明或文化受到怀疑,同时也激励人们进行疯狂的重建工作”。[11](P3)
多元文化的夹击,迫使成长中的西部中青年作家最终以理性的姿态来定位和确立自身的生存处境和身份归属。面对现代消费语境下精神坚守的脆弱与崩溃,摆在西部作家面前的选择,要么融入市场潮流,要么坚持乡土伦理,要么反思乡村与都市的正负效应,“如何在多元文化构建进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如何在‘现代化演进’与‘民族性自守’之间定位好自身的叙事指向平衡点,是许多民族作家所面临但又不得不解决的文化难题”。[12]然而,“清醒地选择、确立自身的某一‘位置’,又使另一些作家从惶惑、紧张中走出”。[13](P236-237)也就是说,焦虑的身份必然引导作家寻找自己的身份归属,尽管充满了游移与不确定性。但边地文化空间的多元性所提供的价值选择,毕竟让西部作家在当代文学大环境的混乱与西部文学小环境的驳杂中,不断逼近和切近了自己文化身份的位置,这种倾向性在西部小说创作中,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便逐步显露出一种“保守主义”的叙事倾向——回归乡土传统,贴近西部底层,挖掘西部风情,吟咏心灵诗意,将对激进时代的疲惫跟踪转为放慢脚步固守大地。
如果说固守乡土的立场刚刚确立,那么,当西部作家将审美视野重归于生长于斯的西部大地时,他们对西部现实的困惑显得更为焦灼。因为,在文化浪潮的冲击下,西部传统的价值体系已经分化和崩溃,继续坚持农业文明时代乡土的“静”与“美”已经成为一个奢侈的理想,尤其是中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高歌猛进,也使西部作家在内心质疑着精神的坚守与物质的进步到底孰重孰轻。最终他们从自身的叙事经验出发,认识到文学的独立与批判精神对社会的警醒,仍然可以起到一定的文化启示作用,他们有责任和使命对生长于斯的西部大地所日日发生的现实巨变与西部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灵魂变迁发出自己声音:“一切有能力思考的人,都应该对社会发言,何况作家”,[14]“关于土地和苦难——谁也不能否认,这两样,是文学的基本母题。生活在西部的作家,距离土地和苦难更切近,因而写得更多,这不应该受到非议。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情形更是命运,而非策略”,[14]“作为作家,我们是没有能力帮助他们怎么样会好一点,或变成什么样就更好了。作家的本事就是写出能引起读者共鸣,甚至震撼的作品来。”[15]这些作家自述都表明,他们选择了不为“什么”而写,只为“写”而写。在这样的创作理念下,西部中青年作家将文化热情、民间话语和人道主义情怀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三个资本,以消费主义时代罕见的群体精神去审视现代化进程中,西部人在多重文化形态共时共存的境遇下的精神震荡与人性变迁。其中既包括了书写西部人对诗意生活的追求,也审视了西部人群人性弱点的根源,以及西部乡土民众进入城市之后的文化冲突与心理震荡,他们孜孜以求地构建着一片纯净而丰富的西部文学世界。由此,西部小说也实现了一次文学性的“换血”:即从80年代西部文学在急躁与刻意的“发现”与“标榜”边地特征,到90年代以较为平静和自然的姿态“表现”与“咀嚼”着西部世界,西部文学由此从“刻意化”的地域性特色构建,逐渐呈现出“自然化”的本土化自然特色。
从典型性来看,西部小说就是当下中国文学格局的一个缩影与标本;从示范性来看,西部作家在面对西部本土人世方面,在立场的模糊中,也无意或有意地形成了一些个性独特而深有寓意的审美特征与价值倾向,这不仅标志着西部小说家在一度的身份焦虑中,对自身身份属性的逐渐明朗,即回归大地、回归底层。而且这种价值立场是对现代文学传统的一种有意识的承继,其对西部人在当下多重文化挤压下的人性变异与灵魂动荡所进行的形而上思考,使西部小说在紧贴西部乡土大地的表象之下,内蕴着对现代文化反省的批判光芒,这在当下文坛各种思潮纷纭迭起但却价值含混的境遇中,显示出一种独特而坚韧的内敛式品质。
三、守望与突围:“边缘叙事”与“主流话语”
现代性在中国的发生,常与“前现代”和“后现代”交织在一起,并在彼此的冲突和缠绕中,逐渐凸显和展示出现代性的话语权威。现代性在中国社会,表现为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在文化领域,化身为乡村文化向都市文化的转型;在地理领域,呈现为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的跨越;在文学领域,表现为“边缘写作”向中东部地区的“主流写作”靠拢、逼近和融合。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培植民众的持久认同,占领文化领导权的制高点。而能否得到民众广泛和主动的认同,是决定特定文化主体当下生存权利和未来处境的关键因素”。[16]对于作家而言,文化演进和地理分布的不均衡,使中东部地区作家能较早关注、涉猎和思索现代性在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中的命运和走向,并通过自身的文学创作,形成较为稳定的文学理念,产生持久的文学影响力。而对于那些崭露头脚、身处大陆腹地的后起作家而言,能否跻身于文坛中心,不仅涉及到了自己的写作命运,也涉及到了自身写作能否被主流文坛认同的问题。这一问题对于西部作家而言,关联着他们在当代文坛的话语声音;对于当代文学格局而言,则涉及到了文坛力量的互相牵制和力量均衡,甚至牵涉到中国文学版图重绘的史学命题。“话语总是某一制度或者组织利益的代言,大众媒介作为最发达的意义表达体系和社会话语的组织者,自然成为社会各种力量角逐的战场”。[17](P138)而西部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权力的疏远,自然使他们在当下以媒介主导的“新型意识形态”的权力格局下被抛掷于一个尴尬的位置。当大多数中东部作家在本地区以积极努力的姿态介入文学圈的时候,对于广大的西部作家而言,他们跻身文坛主流的道路却异常艰难。无论是从西部省份行政体制对文学创作的有意扶持,种种地域文学口号的树立与标榜,还是作家自身对主流奖项和荣誉的珍视,都可以看出西部作家发自内心的渴望自身创作和作品价值被主流文学认可的急切与焦灼。
西部中青年作家的小说类型主要是乡土小说,而乡土题材的集体倾向却又与当前的“新新中国”的“城市喧哗”与“现代演进”相异,这同样是西部作家除却地域偏远之外备受冷落的文学成因。在中东部地区作家急切的表现和描绘着“现代化”和“大都市”的社会景观之时,对于西部作家而言,他们依然生活在乡村人口占据绝对多数的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包围的边地乡土世界。西部的城市尽管有了很多的现代都市符号,但由于西部边地文化的封闭性与悠久性,乡土文化在西部边地仍然有着一定的话语权力和文化份额,西部的现实情形仍以乡村文明为主导。因此,对于西部作家而言,他们不仅要面临如此情状的一个文化事实与生存现实,而且作为一种体制内的精神创作活动,又不得不考虑自身价值的被认可。但从西部作家本身的文化储备和理论资源来看,与中东部地区的作家相比,他们对暧昧模糊的后现代文明有着天然的隔膜,因此,他们只能将视野转向对本土世界的深入思考。于是他们将“西部乡土”特有的文化传统、人文精神、乡土情怀和审美理想等融合在一起,构成起了一个独特的西部文学世界,以此作为走向主流文坛和跻身文学中心的叙事特色和实践筹码。尽管他们以策略的叙事方式提供着异质的文化要素,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文学资本,但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尤其在中东部与西部地区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文化权力发展存在巨大步伐错位的“中国国情”之下,西部作家无论是从自身的文坛话语权,还是自身作品的受众群体广度,都普遍性的有着渴望跻身但却被拒之门外的身份焦虑。尤其是当中东部已经在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的势头之下,西部作家仍然以遥远西北人为了基本的生存而苦斗的内容为主题,这样的文学表现自然容易受到冷落。但这个真实声音的表达,却也恰恰构成了西部文学得以存在和具有发展潜力的内在价值所在:首先,它充分显示出西部作家与乡土大地的文学传承与精神联系,这是他们的文化母体与精神家园;其次,西部乡土小说的美学资源与文学思考在当下的城市喧嚣中可以提供复归人性的文化能量;再次,西部乡土小说在当下普遍低迷而下滑的精神维度中,却表现出关注现实与凝望本土的文学品质,这既是西部作家在边缘与中心的焦虑中,始终不改的文学命题,同时也是其可贵之处。尽管时至今日他们的这种边缘与中心的焦虑仍然存在,但其立足本土、追求精神纯粹的文学品质正逐步得到主流文坛的认可。西部作家在当前的文学格局中,更多面临的是如何在本土题材中实现普泛性的价值观照,而且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作家提供了这种价值理念成功实践的范式。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由于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的逐步开放与革新,全球性的不同文化也在中国这个刚刚复苏的古老土地上开始了自己的文化表演与生存竞争。面对政治记忆、乡土转型与边缘处境的审视,不同作家笔下之所以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结论和判断,之所以他们对政治、文化、地域的现代性转型充满着决绝与犹疑混杂的暧昧态度,归根结底,还是源于创作主体对现代性的认知差异,对“现代性”本身概念的多重性的理解差异。对于西部小说而言,这种对现代性问题的不同认知所带来的现代性焦虑,不仅体现在西部作家在当前文坛格局中的思想观念认同与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而且体现在西部作家面对西部乡土世界和萌芽期的西部城镇等文化象征物时,所构建出的不同内涵的文学审美世界的价值判断。同时,在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思潮迭起的文学演进中,西部文学逐渐呈现出继承乡土文学对现代性探索的这一传统主题的典型文本意义的同时,始终保持着对西部乡土世界的现代性进程的弊端进行独有的远观性与警惕性审视的立场,呈现出与东部各种以“新”和“后”命名的文学思潮演进相异的整体固守性姿态,构建着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和超越”的“论战式美学”的实践典范。从这一意义上考察,西部小说的边缘叙事,恰恰体现出对现代性的感性发展和理性发展进行艺术、哲学和文化制衡的最前卫的“审美批判”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