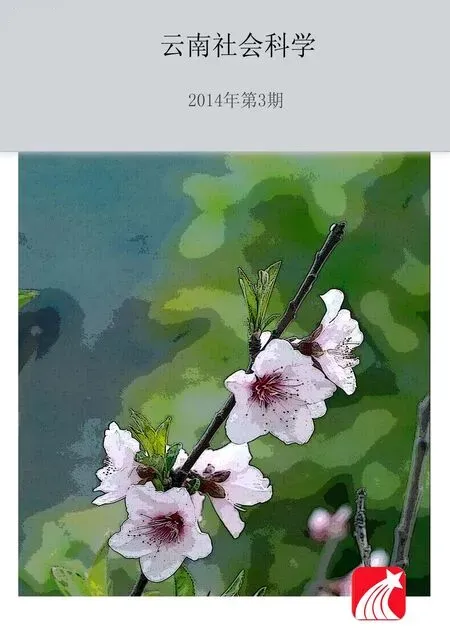清末民初民族报刊的文学观照
2014-03-12刘家民
刘家民
近现代以来,报刊逐渐成为人们了解世界、宣传新知、启蒙民众的重要媒介。清末民初时期,由于民族灾难日益加剧、国家形势日益严峻,创办报刊成为当时的社会要求。此一时期,除汉族精英人士创办的各种报刊外,少数民族人士和官方政府也开始积极致力于民族报刊的创办。少数民族报刊最早出现在1902年。此一时期的民族报刊虽以民族国家团结一致、救亡以及开启民智等政治目的为主,但也蕴藏了丰富的文学因子,甚至含有非常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学元素。清末民初民族报刊与文学,特别是与少数民族文学具有怎样的关联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1902~1920年为时限,来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一、清末民初民族报刊考察[1](P42~142)
晚清最早出现少数民族人士的办报活动,是在1902年。这一年满族人英敛之创办了《大公报》。创办地在天津。英敛之本名赫奢礼·英华,满族正红旗人,是晚清较有影响的人士。1905年留日满族宗室创办《大同报》,1909年满族子弟在北京创办《中央大同新闻》。1906年,在回族中深有影响的《正宗爱国报》创刊,它是在回族先进知识分子和开明宗教领袖的共同促进下创立的,创办人是丁宝臣,创办地在北京。1907年,回族著名社会人士丁子良创办了《竹园白话报》,地点在天津。1909年,回族人刘孟扬创办了《民兴报》,1912年后她又创立《晨报》、《白话晚报》、《白话晨报》等。1907年,回族人张兆麟创办《醒时汇报》,1909年,又创办《醒时报》,地点在沈阳。《正宗爱国报》、《竹园白话报》、《民兴报》与《醒时报》被时人誉为“四大回族报纸”。1908年,回族留日学生创办《醒回篇》。1913年,回族人马太璞创办《爱国白话报》。1914年,著名社会活动家张子文创办《京华时报·附张》。1916年,《清真学理译著》创刊。
白族、彝族、蒙古族、藏族、朝鲜族等也在同一时期创办报刊。白族著名诗人、学者赵式铭先后创办《丽江白话报》、《永昌白话报》、《云南日报》等,尤以《丽江白话报》影响深远。《丽江白话报》创刊于1907年。彝族人安键1917年曾与人合作创办《斯觉报》,同年又创办《新党报》。蒙古族最早的报刊是《婴报》,创刊于1905年,创办人为贡桑诺尔布。1907年,《蒙文报》创立,由喀喇沁亲王主办。1908年,《蒙话报》创办,由吉林省政治调查局承办,庆山、路槐卿主办。藏族最早的报纸是《西藏白话报》,创办于1907年,创办人是耿豫和张荫棠。朝鲜族在20世纪初开始出现宣传抗日爱国的报纸。1909年,《月报》创刊,1910年创办《大成团报》。此外,《韩族新闻》(1911)、《新兴学友报》(1913)、《延边实报》(1915)等报刊也在朝鲜族人民中有一定影响。
偏居一隅的新疆在辛亥革命前夕出现了自己的报刊。《伊犁白话报》是新疆最早的民文报纸,创刊于1910年,主编为冯特民,以维蒙满汉4种文字出版。1912年,《新报》创办,后改名为《伊江报》(1913)。此外,《伊犁日报》(1913)、《觉悟》(1918)等也是当时新疆重要的报纸。
近现代少数民族报刊除了有各族、各地区相关人士创办外,当时的官方政府也主动创办一些针对少数民族的报刊。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面对日益严峻的边疆形势,开始筹划对边疆民族的教育宣传,报刊就是当时的举措之一。《新闻》是民国成立后政府主办的最早蒙文报纸,创办于1912年。同年,《蒙文大同报》创办。蒙藏事务局在1913年领导创办《蒙文白话报》、《藏文白话报》和《回文白话报》。《蒙文白话报》停刊后,改名为《蒙文报》(1915)出版。《朔方日报》(1920)是较晚出现的一份官办蒙文报刊。
少数民族报刊创立的情况还包括由外国人创立的报刊。如以蒙古族、俄罗斯族、朝鲜族等为对象的蒙古文、俄文、朝鲜文报刊。实际上,在少数民族地区,自创的汉文报刊以及内地广为传播的汉文报刊都是存在的,这些无疑对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活产生一定影响。
二、清末民初民族报刊的特性分析
清末民初民族报刊的创立带有强烈的功利性,而这些功利性大多都与民族主义、启蒙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在宗旨、内容上表现得非常显著。《大公报》的宗旨为“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2]在英敛之看来,西方之强盛在于思想先进,民众智慧大开,因此,引入西方思想,开启国民智慧,移风易俗,实现国家富强就显得尤为重要。《大公报》除以“大公”之心勇于揭露清王朝和民国政府的弊病,还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回族最早的报纸为《正宗爱国报》,据张巨龄先生的研究成果,“该报以唤起人们‘合四万万人为一心’、‘让黄脸面,黑头发’的中国各族人民‘痛痒相关,爱国如命,保卫中华万万年’为宗旨,并将‘尚实’、‘提倡公益’、‘劝学’、‘劝工’等四件事,列为办报的‘六大主意’中的重要内容”。[3]从上述介绍来看,该报的民族主义精神是不言自明的。近代以来,回族的特殊政治际遇、居住环境的恶劣、经济的落后,迫切需要回族人民实现自我的救赎和国家的救亡。报刊的创立就是回族有识之士为实现上述目标做出的切实行动。最令人钦佩的是其主要负责人丁宝臣,他因为勇于揭露时弊而献出生命。白族人赵式铭主持的《丽江白话报》在发刊词说,“只有认清形势,奋发猛醒,发展教育,造就爱国国民,才能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直到今日之下,地方被人占了,权利被人夺了,人民被人欺侮了,再要听天,再要安命,那洋人就要搬进房里了”。[4](P75)内蒙古最早的蒙文报纸《婴报》“以启发民智、宣扬新政为宗旨。主要刊就国内外重要新闻、科学知识、内蒙古各盟旗政治形势的动态及对时局的短评……对宣扬新政、启发民智,对内蒙古地区的社会发展、民族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4](P89)
官方主办的少数民族刊物政治功利性更加明显。以《藏文白话报》为例,该报发刊词说:“蒙、回、藏之于汉、满同为皇帝子孙,同为优秀贵族,而实由数千年墨守君主专制之政体故。譬如甲族称帝不利于乙族,乙族称帝不利于丙族,且甲族称帝利于甲族之帝,并不利于甲族之人民;乙族称帝利于乙族之帝,并不利于乙族之人民。于是甲族与乙族争,乙族与丙族争……可翘足待国事亦然,对内之竞争力日强,对外之竞争力日弱,亦非人类不能合群也。”[5]“今幸共和国体告成,万众一心,扫除数千年君主专制余毒,以建此灿烂庄严之中华民国。……蒙、回、藏不能离中华民国别自称蒙、回、藏;中华民国不能离蒙、回、藏别自成其为中华民国。蒙、回、藏享有权利与汉、满平等合于选举与被选举资格,无边陲歧视,无种族谬说”。[6](P165)
据王梅堂先生的研究,该报先后登载有《论中国政府为西藏的患难兄弟》、《论佛法足以发挥共和之精神》(第一期)、《论改用阳历之理由》(第二期)、《论竞争为天演之公例》(第三期)、《论民国教育宗旨以告蒙藏同胞》(第四期)、《论蒙藏两族人宜遍习汉文汉语》(第五期)、《论商业关系以告蒙藏及内地人民》(第六期)、《辨惑》(第七期)、《论宜从本国之统治权》(第八期)、《论五族人民宜注重国家之观念》(第九期)、《论蒙回藏宜速遣弟子来内地读书》(第十期)、《蒙藏社会亟需改良说》(第十一期)、《中央政府对于满蒙回藏之感情》(第十二期)、《论蒙藏宜协力进行以固国基》(第十三期)、《蒙藏事务局改院之利益》(第十六期)[7]。
《藏文白话报》的大致分析表明,民族主义是如何作用于报刊的。实际上,作为一种受压迫民族国家自觉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一经借助于现代传媒就很快成为整个社会、各个民族思考民族国家问题的参照标准。
清末民初民族报刊功利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现代早期少数民族报刊创立的历史背景。从最早于1902年英敛之的《大公报》到20年代的《朔方日报》,中国在此期间一直处于积贫积弱的境地。虽然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中国的弱者地位没有丝毫改变。因此,此时在边疆出现的少数民族报刊带有政治性特色就不难理解了。第二,更为重要的是,此一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严峻形势使得此时的少数民族报刊必须凸显民族主义精神,坚定地维护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以蒙古族来说,可以发现此一时期蒙古文的报刊相较其他民族为多。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1911年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蒙古人士宣布外蒙古独立,内蒙古也受到了很大影响。因此加强民族国家宣传就显得格外重要。这些报刊中既有内蒙古爱国人士创办,也有民国政府创立的。这些对反对分裂起了重要作用。第三,早期报人的国外经历也是这些报刊带有功利特性的重要原因。早期的报人几乎都有在国外的经历,作为弱国子民,这些体验与民族主义精神很容易产生关联。第四,少数民族地区相对落后贫困也容易形成相关报刊的民族主义特性。如前所述,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内涵是民族的觉醒,而对少数民族民众觉醒的启蒙则成为早期办刊的重要任务。启蒙在康德看来,“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8](P22)在康德的眼中,人不是缺乏理智,而是不能以勇气与信心去运用自己的理智。而报刊充当的就是开启智慧工具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少数民族民众,开启智慧、认识自我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与其他民族的比较实现的。
如果说清末民初民族报刊在中国的发展是其顺应了当时社会的历史需要的话,那么,如何将毕竟是新鲜事物的各种新思想迅速让边疆民族民众接受,文学方式,尤其是少数民族喜爱的文学形式与文化思想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清末民初民族报刊的文学表征
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已经被学界广泛研究,但这些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汉族的现代传媒,且大多针对作为现代文学媒介的现代传媒。少数民族现代传媒与文学的关系虽然也有学者做过零星的研究,但总体上研究成果则极为匮乏。论及清末民初民族报刊与文学的关系,就必须考虑的问题是这些民族报刊与文学关系的表征是如何体现的?
首先,清末民初民族报刊为现代文艺的发生提供了鲜活的历史语境,营造了特定的文化氛围。清末民初民族报刊通过及时刊发国内外最新动态,发布国内时事政策,评议国内外见闻,为边疆各族人民,特别是各族觉醒人士打开了接触外界的窗口。报刊快速的传播,尽管远在边疆也能够感受到整个国家、世界时刻发生的巨大变化。这对边疆人民的精神触动很大。尽管边疆民族民众不识字率很高,但他们可以通过边疆民族知识分子阶层快速了解到各方面的情况。当时的报刊既针对大众,也服务小众,小众传媒于是应运而生。“所谓‘小众传媒’是现代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概念,是现代传媒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指的是由精英知识分子主办的、具有精英文化特征的、为高级知识分子阶层读者而办的报纸,它不追求广大市民读者的购买阅读,也不以发行量作为办刊的唯一目标”。[9](P25)现代早期少数民族报刊不仅向大众读者传布及时信息,而且还力求实现一定阶层的读者对“特定事业”的积极参与。办报人与读者的共同行动,对社会民族变革的亲身体验,这些促成了报刊相对其他现代媒介更大的优势,也使得报刊成为各界人士了解世界、感知变化的最有效媒介。更重要的是,人们为了传播这些内容往往借助于文学的形式,相应地,文学的创作也深受这些传媒的影响,既包括主题思想,又有语言形式等。当我们在民族报刊研究中加入了文学维度后,以往的以西方标准为依据的纯文学概念就需要重新认识,现代文学应该提倡一种“大文学观”。“总的来看,现代传媒语境中的现代文学,其生产机制主要是在两种不同的文学观念的对立和融合中建立的,一是超越‘纯文学’观念和范畴的‘大文学’;一是建立在西方文学理论基础上的文学(诗学)理论”。[9](P54)这里的大文学是指以现代传媒为基础建构的文化场域所形成的文学生产机制。虽然少数民族现代文学有自己的特色,但大文学的观念对少数民族现代文艺仍然是适用的。
其次,清末民初民族报刊自觉采用文学手段,一些民族性文学元素是其中的重要成分。清末民初民族报刊为传播政治观念服务,积极采用各种文学元素。文学之于报刊,能够在满足读者趣味、求知的同时,提供较大的想象空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报刊中的“文学”具有仪式般的特性。“报纸只不过是书籍的一种‘极端的形式’,一种大规模出售,但只有短暂流行的书。或者我们可以说,报纸是‘单日的畅销书’吧。尽管报纸在其印行的次日即宣告作废——奇妙的是最早大量生产的商品之一竟如此地预见了现代耐用品容易作废的本质——然而也正是这个极易作废之特性,创造了一个超乎寻常的群众仪式:对于作为小说的报纸几乎分秒不差地同时消费(‘想象’)”。[10](P34~35)
考察清末民初民族报刊,就会发现文学性因素主要体现在语言、体裁以及表达方式上。首先,这些报刊的语言以白话文为主,大多词义浅显、新鲜活泼,很受民众喜爱。其次,这些报刊大量采用评论、小说等体裁。评论针砭社会时弊,小说化抽象为具体。《大公报》刊载大量翻译作品和原创作品,以小说和诗歌居多;《正宗爱国报》刊发的一篇篇时评鞭辟入里;《民兴报》“议论公正,词义浅显,新闻准确,小说新奇”[4](P59);《回文白话报》经常刊发论说、杂文、小说等文学性较强的内容;《丽江白话报》不仅论说发人深省,还刊发佛教故事以及戏剧《莲花生传奇》、《苦越南》等,对社会产生较大影响;《大成日报》内容以论说等警醒同胞;《伊犁白话报》经常在第四版刊载小说等,虽然语言离现代白话还有距离,但已经朝语言的浅近做了可贵的努力。据安凌的研究,现存《伊犁白话报》共刊载9篇小说[11];《新闻》开设“论述”等栏目;《藏文白话报》在13期中刊登小说11篇。这些小说“内容短小精炼,风格新颖,引人入胜”[7](P71)。再次,在表达方式上,除一般性文学方式外,民族性文学形式格外引人注目。《竹园白话报》除文风亦庄亦谐外,经常以宗教故事的形式论说;《京华新报·附张》专辟“雷门鼓”,以故事喻说各种知识;《蒙话报》设立“杂俎”专栏,登载一些寓言故事,启发民智;《丽江白话报》也采用过以佛教故事说理的方式。民族性文学方式的采用,不仅有利于思想的传播,而且发掘了少数民族的独特性文学方式,对少数民族现代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清末民初民族报刊的少数民族文学资源与白话文运用具有特殊意义。在清末民初民族报刊中,经常为了宣传的需要运用少数民族传统文学资源,少数民族文学因之登上现代传媒,这对少数民族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虽然借助于民族传统文学资源,但在文学主题、语言以及文学表达上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这些对少数民族现代文学的出现有积极作用。就白话文来说,当时白话逐渐成为现代社会最为通行的话语方式。值得注意的是,与汉族轰轰烈烈的白话文运动不同,大部分少数民族民众的语言并不存在严格的雅俗之分。这是因为诸多少数民族文字出现的时间较晚,口头语言始终起着主导作用。即使在存有少数民族文字的民族,民众的日常语言依然在文字的使用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感慨:“古代文学之形容事物也,率用古语,其用俗语者绝无。又所用之字数亦不甚多,独元曲以许用衬字,故辄以许多俗语或以自然之声音形容之,此自古文学之所未有也。”[12](P164)不仅元剧如此,明清时期少数民族“俗文学”也是少数民族文学的主流。各种口头传承的民歌、史诗、故事、戏曲,以及少数文人创作的小说、子弟书等均以民众鲜活的日常语言来承载。当然,文学作品用日常语言(白话)并不代表其等于日常语言,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种现实存在的艺术化。譬如少数民族的许多民间诗歌也很讲求规则。在少数民族地区,当底层民众的日常语言成为一种媒介语言时,其收获的不仅是民众对自己智慧的肯定,更是一种自己作为一种主动力量的象征。麦克卢汉对此有过精辟论述。“印刷术发现了生动逼真的民族疆界,印刷书籍的市场也是由这样的疆界圈定的,至少对早期的印刷商和出版商是这样的情况。而且,能够看见母语穿上可以重复的、相同的技术衣衫,也许在读者的心中会产生一种统一和强烈的感情,每个人和操母语的其他读者分享这样的感情。前文字和半文盲的人的国家是迥然不同的”。[13](P427~428)如果从福柯关于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来阐释,可以说,少数民族的白话作为报刊语言,是少数民族由他人言说向自我言说的转变,是民族话语权的象征。它既对传统的权力秩序形成某种挑战,同时又能够鼓舞少数民族作为统一国家一员的自豪和责任感。而小说逐渐成为各民族主要的文学类型,恰恰反映出民族主义精神影响下权力关系的重构。然而,白话文的使用又无形中“制造”出一种矛盾,即话语使用主体对言语的操纵与话语来源主体的反操纵的潜在分裂,民族文学语言所代表的主体言说与主流文学语言的强势同化与遮蔽。作为一种文学的媒介,少数民族现代文学一开始就游走于被动与主动、边缘与主流的复杂纠葛之中。
四、清末民初民族报刊的文学化成因
报刊的文学化是报刊本身的要求。报刊与传统传媒的差异在于,它要直接与市场连接。为了赢得读者,采用文学化手段是必然之路。借助文学化方式,报刊不仅在语言文字上生动活泼,而且可以使报刊内容新鲜有趣,这就极大增强了报刊对读者的吸引力。即使是传递实效新闻的内容,适当的文学性成分能使其更加引人注目。因此,清末民初报刊不仅采用一般性的文学手段,而且还积极利用民族文学资源,这对促进思想的传播、民智的开启以及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发展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清末民初的报刊文学化是时代要求和传统使然。清末以来,以报刊文学化手段宣传改革、改良以及救国的实践鳞次栉比。文学的功利化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特色,并长时间主导现代社会文学实践。梁启超倡导的“政治小说”可以说是其典型代表。时代状况要求报刊的创立多含功利目的,而文学是充当这一工具的有效方式之一。文学的功利性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体现。文史哲不分以及文以载道的文化传统,使得文学极易为目的服务。少数民族文艺与民族生活紧密缠绕。清末民初民族报刊的文学化就充分利用文艺的传统特性为时代要求服务。
清末民初民族报刊的文学化受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文学实践的影响。清末民初的少数民族有识之士不仅很早就注意到报刊的重要作用,而且还积极在报刊上发表作品,亲自体验报刊文艺实践。在这些人当中,英敛之、丁宝臣、张兆麟、张子文、刘孟扬、丁子良以及赵式铭等较有代表性。在报刊上发表作品既加深了他们对报刊的深入认识,又使其在办报中不自觉地将文艺的因子融入报刊之中,使报刊充分发挥对本族人士以及其他受众的政治及文学影响。
综观清末民初民族报刊与文学的关系,报刊首先呈现的是文学与报刊的相互关联,文学是为了满足政治目的。这样的文学无疑距离后世的纯文学还有很大距离。当然,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深处其中的个人和民族深受影响极为正常,这也是笔者在考察、研究中经常发现各族文艺明显趋同的主要原因所在。但正如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即使各个民族面临着共同的时代命运、承担着共同的历史责任,用文艺表现出的各个民族的“历史表征”也是充满差异的。正是由于各个民族的个性使然,才使得我们今天在面对现代的作品时,应该努力回到历史的情境中,回到各个民族的历史灵魂中去,这样才不至于大而化之、笼而统之。其次,清末民初民族报刊促使文学出现了一些现代性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这些报刊文学的主题和形式上。少数民族文艺的功利性自不待言,但这些主要是与本民族事务结合在一起的。歌谣在一些少数民族的婚丧嫁娶中广泛使用,史诗、故事既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又能够起到娱人心目的效果。至于一些特殊的文艺,其作用更是被人神话。清末民初民族报刊促使少数民族文艺功利服务对象的转移和扩大,即由本民族日常的事务转变、容纳民族国家的事务。报刊还促进了文学在语言形式等方面的现代发展体现在白话文的选用、小说、戏剧等现代体裁的采用等方面。报刊与文学的相互作用,既有早期报刊提供的示范,又有报刊自身特性造成的新型文学规约。清末民初民族报刊促发的这些文艺思考对我们思考少数民族现代文艺的萌发、民族文艺资源的现代转化具有重要价值。真正的少数民族现代文艺作品等到20世纪20年代左右才见诸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