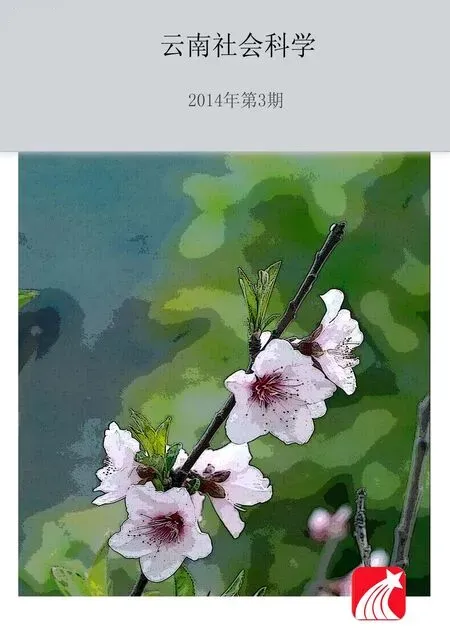中国古代乡约道德教化精神的理性审视及现代性重塑
2014-03-12韩玉胜
韩玉胜
乡约是一种旨在乡村地区开展的道德教化形式,真正意义的乡约肇始于宋代《吕氏乡约》(又名《蓝田吕氏乡约》或《蓝田乡约》),系当时儒家士绅为组织基层民众共同应对天灾人祸、改善社会风尚,而自发兴起、自动主持、自愿参与且具有一定强制性,并书之于通俗、简明文字的“契约性”文件。其道德教化精神在于,通过沿革古礼勾勒出乡村社会的理想道德愿景,籍以约束人之日常行为、处事态度、礼仪规范,影响人之心意态度、情感归依、意志品质,进而达到完善德性、塑造人格以及和谐乡村生活的功效。
然而,在当时基层社会丰富的现实生活中,各种势力纷繁复杂、相互博弈、此消彼长,使得乡约道德教化之初衷未能得以自然生长,而是充满难以克服的价值困境,直至最终徒具形式而不复存在。置身于现代生活历史境遇之下,紧密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有感于当下农村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以理性眼光来重新审视乡约,借鉴其历史经验,汲取其历史教训,对于现代生活背景下“新乡约”的探索创新大有裨益。
一、价值困境:道德情感与实践理性的价值紧张难以调适
以道德教化思想展开的历史逻辑之主线对中国古代乡约的理论演进与实践发展进行总体回顾,就会发现:自诞生之日起,乡约即存在着难以克服的价值困境,主要表现为道德情感与实践理性的价值紧张难以调适。对此,可以进行三个方面的理解:
第一,道德理想主义的“儒治”与刑政治理的“吏治”刚性杂糅。毋庸置疑,乡约意图借助于古代礼学范式、礼学精神为当时乡村道德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蓝图文本和寻求有力的道德支撑,此教化理念带有浓重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反映了乡约立约者天然的“儒治”情怀,即借助于农村社会强大的社会舆论力量和人之本能情感习性的调节来保障乡约的有效实施,“约其情而治之,使乡之人习而行焉”[1](P592),从而实现一种自觉的道德秩序。例如,对于违约者乡约则倾向于采取“忏悔改过”之类的处罚方式,即便大部分乡约都普遍存在着保障其有效实施的“罚式”,也只是起到象征性作用,用于警告劝诫、息讼止争,并无实质内涵。然而,随着官办乡约的出现,政治力量逐渐介入并成为乡约真正的制定者和实施者,使得乡约与保甲、社规、社学等基层管理制度相结合。但是,这种结合毋宁说是一种刚性杂糅。原因在于,当时统治者出于加强社会控制和稳定统治秩序的考虑,不可能让基层民众的道德热情过于泛滥,必定运用政治手段干预乡约和进行功利主义的剪裁,即保留乡约的道德理想形式而掏空其道德教化之精神意涵,并填充以实质的政治内容。如此,就会出现这样一番景象:乡约的立约宗旨是“儒治”,意在“劝人向善”,而官方调节侧重“吏治”,意在“防人为恶”,“儒治从教化上做起,吏治从刑政上做起”[2](P131)。那么,德主刑辅、礼乐治理、劝化向善的“儒治”与为政以法、刑政治理、防人为恶的“吏治”之间的矛盾该如何调节?这两种看似严重对立的价值理念如何协调一致?是“儒治”服从于“吏治”,还是“吏治”服从于“儒治”?从乡约的发展历史看,似乎其未能找到一个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更多时候陷入“儒治”与“吏治”的刚性杂糅而难以自拔。
第二,美好道德愿景与具体实践效果之间的张力难以维继。起初,乡约的立约宗旨在于通过“礼仪教化”引发人之内在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的转变,“以成吾里仁之美”[3](P567)。那么,对于乡约这种极具现实指向的教化形式,判断其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莫过于考察其实际推行状况,即美好的道德愿景是否收到了意想的实践效果。然而,就实践性而言,古代乡约并没有想象的那样成功。宋代《吕氏乡约》推行尚且能够秉持道德教化初衷,但实际影响过于短暂,随着北宋被金人所灭,乡约只是昙花一现。到了明代,乡约的发展受到朝野重视,一些名臣大儒参与到乡约的制定和推行中来,其中最成功的莫过于王阳明的《南赣乡约》,之后官办乡约蔚然成风。这种风气的直接后果是极大地发挥了乡约的实践性功能,过度延伸了其实用主义价值向度,必然导致其道德教化功能的急遽萎缩,致使二者之间张力难以维继。此外,民间社会复杂的社会背景使得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环境中从事道德教化绝非易事,那些倡导乡约的儒者常常陷入难以克服的精神困惑。例如,由于乡约的倡导者往往是世家大族的士绅官僚,而族约族规、家训家规成为可以乡约仿效的范式,但族约家规毕竟不同于乡里规范,那么,乡约的制定到底是“乡里利益至上”还是“家族利益最大化”?如果不能恰当处理这个问题,乡约就难免成为宗族家规的原搬复制,甚至沦为大族望户沽名钓誉之举的工具。也就是说,乡约的教化事业,除了受到政治因素影响之外,还会遭受来自民间社会各种因素(如宗族家规、民间宗教以及地域文化等)的困扰,面对不确定的社会现实以及民间非儒学的强大实力,那些乡约倡导者依靠儒家文化的力量整合基层社会道德秩序的理想往往受挫,故而常常萌生道德无力感,产生以上困境也是在所难免。
第三,“多数原则”与“志同道合”之间的艰难道德抉择。在乡约的制定和推行过程中,立约者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理论和实践难题,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协调最大限度地吸纳乡民自愿入约(即“多数原则”)与达成最大限度的道德共识(即“志同道合”)之间的关系。这种矛盾关系在早期乡约已初露端倪。例如,朱熹在修改《吕氏乡约》的顾虑就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点。朱熹曾就《吕氏乡约》的可行性与好友张轼商讨,张轼回信道:“昨寄所编祭仪《吕氏乡约》来,甚有益于风教。但乡约细思之,若在乡里愿如约者只得纳之,难于拣择。若不择,则或有甚败度者,则又害事。择之,便生议论,难于持久。”[4](P426)于此,张轼道出了乡约实施的“两难困境”:如果对入约者不加以选择,必会将做恶之徒吸纳进来;如若加以拣择,势必议论纷纷。如黄书光教授所言:“即便地方士绅有余力从事教化,但在确定教化对象时也要遭受诸多精神考验,以致常常处于矛盾之中。”[5](P306)也就是说,乡约团结了一批志同道合之人,松散的出入制度又使得那些亟待教化之人游离于乡约之外得不到教化,这才是乡约的关键症候所在。
总体而言,乡约道德教化思想的开展自始至终未能摆脱价值选择的紧张格局,一直处于美好愿望的诉求(道德情感)与现实效果的要求(实践理性)的困境难以调适。这种难以调适的困境可以用“内忧外患”之遭遇来形容:作为立约者既要处理乡约自身理论“内在紧张”关系,又要应对现实政治势力功利主义剪裁的“外部挑战”。这种“内在紧张”与“外部挑战”相互叠加的矛盾格局促使乡约不断调整自身,既要为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作辩护,又要面对政治压力作出妥协姿态,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道德憧憬和政治现实之间徘徊,不断推动着乡约的理论演进和实践发展,也不断促使难以摆脱的价值困境日渐凸显、愈演愈烈,并最终导致乡约不复存在。此过程值得深思。
二、理性解构:伦理价值与法理价值的理性扬弃相得益彰
如何对乡约的历史难题与当代意义进行不同诠释,从而获得学理启发,以服务于当代新农村道德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
第一,历史转型:传统道德教化场域瓦解与农民群体道德世界变化。岁月流转,靠“熟人社会”[6](P9~10)和习性秩序维系的传统乡村形态正面临着急遽转型,现代意义的乡村形态和生活方式已然成形。因此,农村日常生活世界日益呈现出“陌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甚至“弱熟人社会”的特征,而传统“熟人社会”所营造的教化场域正面临瓦解,正如卢风教授所言,“美德必须在一个具有稳定生活传统的道德共同体中培养”[7]。随着乡村社会的历史转型,乡村的道德生活也在悄然改变,不良社会风气沉疴泛起: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子虚乌有的风水算命,求神拜佛请巫婆;传统道德观念淡化,婚丧嫁娶盲目攀比、铺张浪费、摆排场、比阔气,礼仪风俗流于形式;精神生活匮乏,赌博现象屡禁不绝,投机心理日益增长,好逸恶劳作风盛行;功利主义思想潜滋暗长,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大行其道。显然,传统乡约无力应对此番乡村巨变,也无力找到引导当代乡村道德生活的可行之方。
第二,“消解论”VS“解构论”:对乡约历史难题与当代意义的不同诠释。面对乡约所遭遇的历史难题和当前困境,我们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对待这份精神文化遗产?近年来,乡约引起了学界的足够重视,出现了大量相关研究成果,并呈现出具体学科研究的差异性。但是,学界整体呈现出“消解论”研究现状,即立足于乡约整体消解的历史轨迹而进行“消解”地理解,也就是相对独立的理解。例如,社会学研究者注重于乡约社会情境与社会关系的理解[8];历史学研究者往往聚焦于乡约的资料考证、文献梳理、历史演变以及社会原因的探讨*参见段自成、常建华、曹国庆、董建辉等人研究成果,诸位学者对古代乡约的研究既有充分的史料考证,也有详尽的历史分析,为我们全面详尽地了解古代乡约奠定了基础。;法学研究者则敏锐地觉察到近代以来乡约的消解趋势,主张在当今法律法规基础上进行“重整”,将法理内置于新型乡约的范型之中[9]、[10];政治学研究者则侧重于乡治理论的把握[11]。显然,学者们认识到了乡约的多维内涵,有助于我们从不同视角透视乡约的多重价值。但是,这种“消解”地理解乡约能够形成分门别类的“管窥”认知,却难以形成跨学科式“综合”理解,从而也就不可能在关系意义上对乡约之价值进行整体把握,甚至会模糊乃至忽视乡约价值困境的真正原因。笔者认为,应对乡约进行“解构”的理解,所谓“解构”就是进行“建设性”的分解以及重构,而不是一律予以分裂式瓦解,即对乡约进行分裂或解体之时,能够保留其重要价值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关系结构。在此理解的基础上,乡约可以呈现出多重关系,而参照乡约历史流变以及所面临的价值困境,笔者认为,从“德刑之辩”的历史镜像中剥离出在关系中把握伦理价值与法律价值的乡村社会情理法则,并能够积极围绕这一法则,探索现代农村背景下的新思路、新方法、新内容,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如何解构:伦理价值与法理价值的双向解构与双向认知。立足于“解构论”,我们就可以对传统乡约的价值困境与历史衰变进行更为理性的理解:无论是那些乡村士绅出于道德教化之初衷,通过沿革古礼勾勒理想的乡村道德教化蓝图,还是官方出于社会控制的目的,进行功利主义的剪裁和干预。本是各司其职,无可过多厚非。但根本问题在于,二者不是决然对立的关系,而是相得益彰的互补关系,只有二者充分结合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效用,形成整体效应。否则,如果只注重伦理情感,则容易造成情大于法的人情干扰而难以形成有效约束力,也就难以真正地维护契约者的现实利益;如果只注重法理精神,而不顾及当事人的现实感受,则难以形成真正说服力。显然,无论是当时统治者,还是儒家士绅,都未能认真对待这一问题,也就未能在伦理与法理互动基础上探求合理的乡村模式。当然,限于历史条件,他们不可能自觉发现和解决这一问题。对于现代研究者而言,必须理性审视乡约涵盖下伦理与法理之关系,而不是仅仅选取有利于学科研究的资料,以支撑某些独立(伦理或法理)的学理观点或学术兴趣。也就是说,必须对乡约进行双向解构与双向认知,既要遵循合情的伦理原则,更要遵守合理的法理原则。在此基础上,才能克服乡约的历史难题并顺利完成古代乡约的现代化转型。
三、现代性重塑:现代生活背景下“新乡约”的探索创新
目前,当我们立足于现代生活背景下新农村建设丰富的理论与实践,面对当前种种亟需调整的失范行为和失范现象以及亟待解决的各种现实道德问题之时,就会发现,现代农村所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也就更需要一个类似于乡约的文件来进行组织协调,而历史记载的乡约此时已无法发挥现实功效,必须进行彻底的现代化重塑,所谓“现代化重塑”是指探求兼具道德意识与法律精神、致富理念与奉献精神相结合、经济发展与生态环保相协调、乡土情感与现代思维相接轨的“新乡约”成为解决当前农村现实问题的有益尝试。
第一,“新乡约”应该着眼于培育兼具道德意识与法律精神的新农民,引导民众组成文明守法的伦理情谊群体。面对由于当前农村经济结构、利益关系以及生活习性的变迁而带来的农民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意识、行为准则等方面的深刻变化,“新乡约”的制定者不仅应该敏锐觉察到农村社会面貌的重大变迁,也应该考虑到乡民内在情感意识的更迭嬗变,将“新乡约”发展成一种既能反映农村社会现实又能照顾村民感受的“伦理情谊组织”。“伦理情谊组织”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对乡约的称谓,他认为现代乡约组织应该继承传统文化的伦理本位意识,建立一种熔铸理性与情感、伦理精神与道德情感结合的组织。毋庸置疑,梁老极为强调道德情感与道德意识对于乡约组织的维系作用,此思想对于“新乡约”的建立极具启发意义。也就是说,“新型乡约的制定必须强调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着力于乡土社会中的‘人’,符合乡民的习性与审美情趣,融汇乡土社会的‘情’、‘理’价值,以此来寻求建设一个精神共同体”[12]。与此同时,“新乡约”是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新乡约”,其应该与当前农村社会的法律法规相协调,但不应与法律法规等量齐观,更不应该“喧宾夺主”,而应形成对现有法律法规的有益补充。同时,乡约作为一种地方性非正式制度也可以为法律制度的创建提供新的素材,补充新鲜血液,进而在某种条件下经过某种程度转化可以成为正式法律制度。即便“新乡约”的某些内容不能够被法律制度所吸收转化,仍不失为一种调节地方具体事务、规范地方道德生活的一种有效手段,弥补某种程度上国家法事无巨细的法律真空。
第二,“新乡约”应该积极探索致富理念与关怀精神相结合的新思路,倡导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并茂的生活方式。“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对于那些基本温饱都无法解决的农民群众而言,精神层面的道德教养根本无从谈起。“新乡约”应该致力于调动农民创造积极性,鼓励他们在创造物质财富的社会实践中发挥聪明才智,为实现富裕安康的美好生活而奋斗。对此,政府要增加投入、积极倡导,为新农村模式搭建更高平台和提高更多优惠政策,并定时组织调查研究、宣传教育、检查验收、跟踪服务等一些列具体工作,并逐步将政府主导转变为村民自发、自觉、自愿的乡村建设运动。与此同时,“新乡约”应该在农村倡导关怀精神,通过创建文明村、树立先进学习榜样、“友爱互助月”以及利用节日开展道德教育活动等多种实践形式,培养乡民的集体意识和奉献精神。也就是说,“新乡约”不能停留于死板的条目规章设定,而应组织开展着实有效的实践活动,如此,才能够进一步增强乡村居民的认同感、安全感和归属感,达到友爱互助的文明村风。
诚如《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所指:“公民道德建设的过程,是教育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以活动为载体,吸引群众普遍参与,是新形势下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13](P169)
第三,“新乡约”应该注重经济发展与生态环保相协调,共建经济富裕又充满诗意气息的乡村居所。当前我国乡村地区,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招商引资的带动,乡村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相应的问题也逐渐凸显,尤其是生态环境问题迫在眉睫。例如,大量使用化学农药化肥导致地下水污染严重、生态失衡,危及人畜安全;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以及生活垃圾转移到农村,导致各种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叠加,新旧污染相互交织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危害农民身体健康与财产安全的重要因素。“新乡约”的制定不能无视这些现实问题,要积极配合各项政策法规,利用各级各类新闻媒体予以正确的宣传引导,形成有效的社会监督和社会舆论氛围。当然,重要的是调动农民积极性,让他们真正参与到“新乡约”制定中来。也就是说,“新乡约”要致力于确立一种新的价值观,让民众能够认识到“正确的东西”与“真实的东西”之区分,“单纯正确的东西还不是真实的东西”[14](P926),不能为了粗放的经济发展而忽视乡村的原初内涵——居住功能和生存功能。因此,如何共建经济富裕又充满诗意气息的乡村居所,这才是乡村发展的价值归属所在。
第四,“新乡约”应该着眼于乡土情感与现代思维接轨的思维模式,既要开拓乡民的现代视野又要积极培育其乡土意识。面对当代中国农村正经历着的全面而深刻的现代化变革,“新乡约”应该着眼于增加现代化内容,积极宣传环保意识、生态意识、文明理念以及可持续发展观等具有现代化气息的观念,鼓励民众破除陋俗陈规,积极参加娱乐身心、陶冶情操的各种文化活动,积极追求健康文明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但是,现代化也极具摧毁性。现代社会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始料未及的速度和难以想象的彻底不断解构着一切神圣的事物,创造着一个新奇的世界。可以说,现代社会是一个“祛魅”的社会,它消解了科学和知识的神秘性、神圣性、魅惑力,对社会中所谓崇高儒雅、美德典范、宏大叙事持悬疑或疑虑的文化态度。在这种社会样态之中,那些曾经一贯信仰或受追捧的人、事、物、情感、文化、定论都要被重新审视。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之下,乡村也难以逃脱现代性的洗礼,现代价值观念正以前所未有的彻底性解构着乡村的传统,现代化的负面效应正以始料未及的速度侵袭着现代乡村。例如,乡村正在单调盲目地复制着城市里的一切,逐渐丧失自己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底蕴;农村的一些风俗礼仪渐渐流于形式,并慢慢被乡民遗忘。面对这种现代化的“遭遇”,“新乡约”不能不觉察到这些征兆,在鼓励农民享受现代化成果给人们带来的便利之时,也要注重培养乡民的乡土意识和乡土情感,时时提醒那些出门在外的游子要感恩乡村、感念父母。也就是说,“新乡约”所提倡的与现代化接轨,并不是一味单调地追求现代化,而是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建立寻求某种平衡,立足于农村实际,面向未来发展,二者缺一不可。
总的来看,通过解构传统乡约教化精神,在批判现代农村生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乡约”与当前农村的现实需求极为吻合,此“新乡约”将成为一种新的载体,既能进一步规范配合国家法律的基层实践,形成有效的外在规约和他律精神,又能继续强化村民主体自身的德化修炼,形成一种新的内在自觉和自律意识。质言之,“新乡约”将成为一种新的农村教化题材,成为农村社会道德舆论宣传的重要阵地,促进新的村貌村容村风得以形成。当然,“新乡约”的制定和实施也必定困难重重,既要克服其历史上所遭遇的尴尬价值困境,又要摆脱现代性所带来的种种不适,既要引领现代化的潮流,又要照顾难以割舍的传统。令人欣慰的是,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村发展,并给予农村地区以前所未有扶持,将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权益、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重点。无疑,这些成为农村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也为“新乡约”得以制定和实施提供了政策保障和发展方向。一些地区已经自发尝试“新乡约”的制定和推广,相信随着“新乡约”的逐步推广,农村生活将更加和谐,农村的明天会更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