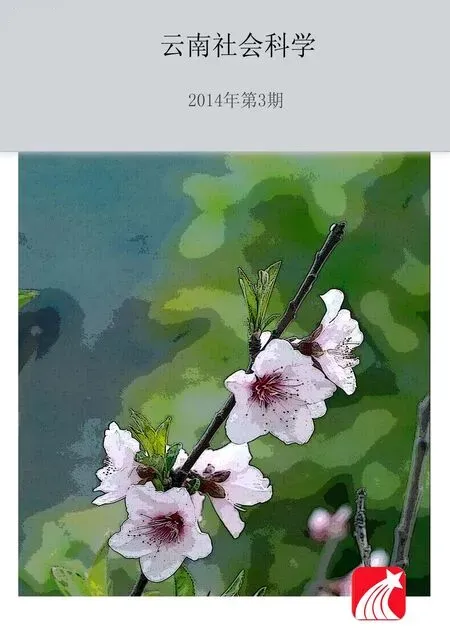论生态刑法的从属性原则
2014-03-12安柯颖
安柯颖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生态刑法具有突出的地位和作用。源于刑法的谦抑性和行政刑法(经济刑法)的从属性原则,作为行政刑法分支的生态刑法,也应当遵守从属性原则的要求。然而,关于生态刑法从属性原则的理解和实现,又存在不少似是而非的观念,有必要从生态刑法的概念、规范、目的、实现等层面,对生态刑法的从属性原则作出系统诠释。
一、从属性原则的含义与内容
从属性,亦称附属性、补充性,是指一个事物附属于另一个事物的属性。具体到生态刑法从属性原则的理解,需要结合经济刑法、行政刑法和环境刑法的相关问题进行说明。
1.从属性原则的含义
在行政刑法抑或经济刑法的研究中,有学者明确提出了经济刑法的从属性原则。具体到从属性的含义,周建军教授指出,经济刑法的从属性亦称附属性,根据法定犯的原理,证券犯罪(经济犯罪)对象也该产生于行政法规的证券范畴,证券犯罪(经济犯罪)行为的违法性应该取得证券行政违法与证券刑事违法的统一[1](P78)。对此,向泽选教授指出,在德国,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一是概念上的从属,如刑法上的用语“水源”、“水资源保护区”等,需以环保行政法上的解释为依据;二是法规指示,如违法使用应经行政许可的设备,至于哪些设备的使用应经行政许可,应依照有关环保行政法规的规定而定;三是空白构成要件,空白构成要件和法规指示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基于立法经济的考虑,直接引用行政法的规定,前者则是将行政法上的禁止或命令规范纳入刑法规范,与其他构成要件结合成一体,形成完整的犯罪构成要件[2](P22)。不难看出,在经济刑法、环境刑法中,从属性不仅具有一个事物附属于另一个事物的属性,而且存在前后两个事物共同作用实现某种功能的目的。
2.从属性原则的内容
源于刑法的谦抑性和生态刑法的具体情况,生态刑法从属性原则的内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生态刑法的从属性源于刑法的谦抑特性。落实到生态刑法的谦抑性,需要解决生态刑法启动的必要性和生态法益保护的目的性。首先,生态刑法的启动应当是必要的。生态刑法的启动要以生态行政法规的违反作为前提,同时存在生态行政法规不足以保护相关生态法益的情况,其首要的任务是促进生态行政法规的立法,而不能急功近利地直接使用刑罚手段。其次,生态刑法的启动必须符合恢复生态法益的目的。生态法益的目的是指生态法益的恢复,包括人类在内的生态系统的基本利益,尤其牵涉到共同生存、发展的利益,需要得到生态法律系统的共同保护。
第二,生态刑法的从属性,核心内容是指保护生态法益的刑法规范从属于生态行政法律规范的基本性质。这种从属性主要表现在生态刑法规范的法益、概念以及其他规范要素的附属性。其中,法益的附属性是指生态刑法所保护的,只能是生态刑政法律法规保护的法益的一部分。概念的从属性是指生态刑法的概念,尤其生态法益保护的专门概念,需以相关的生态行政法律规定为依据。其他规范要素的从属性,包括空白的生态刑法立法和指示性的生态刑法立法,生态行政法律法规可以对生态刑法规范起到补足作用,也可以成为解释生态刑法规范要素的基础。以《刑法》第341条规定的“非法狩猎罪”为例:“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的……”其中何谓禁猎区、禁猎期、禁用的工具,具体的时间、区域、工具等等,都是非法狩猎罪的构成要素,但这些要素的理解抑或解释,不是刑法本身能完成的,只能从相关的行政法律法规中寻找依据。这就是生态刑法规范附属于生态行政法律、法规的典型表现。
第三,生态刑法的从属性原则,关键要组织起系统的生态法律体系。生态刑法的从属性原则,不是为了说明一个法律从属于另一个法律的问题,而是为了说明前后两个事物(或者说法律)共同作用,实现某种功能的目的。落实到生态法益保护的从属性,关键的问题就是要组织起保护生态法益的“堤坝系统”。
二、从属性与生态(法)优先的关系
一般说来,从属与优先之间是矛盾的关系。但是,论及生态法律的原则,学界经常提到生态优先的原则。
1.生态优先原则的提倡
曹明德指出,生态优先原则是在处理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上,要确立生态环境保护优先的法律地位[3](P227)。曹教授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他一些学者也发表了类似的观点,杨群芳指出环境优先原则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环境保优先与环境恢复优先,以环境保护优先为基础,以环境恢复优先为补充。环境保护优先包括自然资源的利用、保护和环境保护的优先,是指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当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相冲突时,应优先考虑环境利益。环境恢复优先是指在环境损害救济中,应把恢复受损环境放在一个优先的位置。这里所说的“优先”是指应预先设置纯环境损害的救济制度与措施,在人们开始进行有可能带来纯环境损害的活动之前,预设、预留必要的环境恢复应对措施与必需的环境恢复费用,以保障对纯环境损害的救济及时顺利地进行[4](P62~63)。
综合上述两位学者有关环境保护优先抑或生态优先的代表性论述,除了对生态优先原则具体内容的阐述方式略有不同之外,二者对生态优先原则的核心内容——“当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相冲突时,应优先考虑环境利益”的坚持是非常明确的。笔者认为上述提法存在对生态优先原则的表述不够准确的问题。
首先,关于生态优先原则的具体理解,学界存在一些其他具有代表性的表述,赵旭东认为:生态优先的基本内涵是指在环境管理活动中应把环境保护放在优先位置予以考虑,在社会的生态利益与其他利益冲突时,优先考虑生态利益。一般讲,应至少涵盖以下具体内容:首先,在环境管理活动中,优先保护人的生命健康、保障居民生活、劳动和休息的良好生态环境;其次,当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发生冲突时,优先考虑生态利益;最后,各种经济开发活动,不应对其他自然客体和整体自然环境造成损害[5](P66)。也就是说,赵旭东认为生态优先原则不排除优先考虑生态法益的保护,但是,在维护生态平等的同时,也要兼顾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兼顾经济发展的观点也得到了一些具有先进环保理念官员的支持。2011年9月1日的《中国环境报》刊载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的文章指出:我国水电开发与环境保护已经形成了“生态优先、统筹考虑、适度开发、确保底线”的原则共识。为此,在依法划定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禁止开发的区域,国家和地方主体功能区规划、生态功能区划等确定的禁止开发区域以及濒危、珍稀、特有保护动植物的重要生境等生态敏感区,布局水电梯级。对于可能直接导致敏感目标消失或珍稀物种灭绝的梯级电站要坚决取消[6]。不难看出实务部门也认可生态法的生态优先原则,但是,在生态优先原则的理解和执行中,也考虑到了确保底线,并统筹多方面因素(必然包含经济方面的因素)进行考虑的思想。
比较以上几个方面的内容,可以说,第一,生态优先是指当生态法益与经济利益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应当作出偏重于生态法益的考虑。第二,从相对主义的角度来讲,法益衡量解决公共问题的基本思路。落实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中,当二者发生冲突,必须通过妥协的方式来解决,一类利益必须让位于另一类利益的主张。笔者并不主张绝对的生态优先应当成为生态法和生态刑法的原则。
2.生态优先与生态法优先
生态法优先是指在保护生态法益的堤坝体系中,生态行政法律法规优先于生态刑法的地位和属性。因此,这里的生态法是狭义上的生态法,是指生态刑法以外的生态规范。生态法优先的要求主要有两点:第一,生态行政法律规范体系应当优先于生态刑法而得到构建。万丈高楼平地起,对生态行政法律规范而言是紧接生态刑法规范的底层规范,对生态刑法规范的形成与理解具有基础性抑或配置性的作用。第二,生态行政法律规范应当优先作用于生态法益的系统保护。生态法益能不能率先动用刑法规范,如果能,那就是生态刑法具有独立性;如果不能,那就是生态刑法具有从属性。这一点,在经济刑法的从属性与独立性的争议中已经做出了说明。作为行政刑法分支的生态刑法,必须从谦抑性和保障法的角度出发,坚持从属性原则。
三、从属性原则的立法及其实现
1.从属性刑法保护生态法益的应然性
总的来说,在生态法益的堤坝体系中,生态刑法是终极手段,它只能作为前置程序、措施、规范的坚强后盾,在前置程序和手段失效后最及时有力地跟进,它能积极地实现国家对生态犯罪的预防作用,遏制破坏生态的行为。具体说来,处于从属性地位的生态刑法也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反作用性质。
第一,生态刑法保护的后盾性。更多的时候,刑法是存而不用的后盾。尤其生态刑法的作用,原则上应该体现在对相关行政行为的跟进和管制。因此,可以说刑法规范是保护环境与资源的最后手段,但绝对不是最重要的。
第二,作为保障法的生态刑法,应当在保护生态法益的堤坝体系中与其他法律共同发挥作用,才能更好地实现充分保护生态法益的目的。
考虑到生态法益的重要性质,应当建立一个以生态法益保护为价值取向,以环境权为调整核心,结合行政、民事法律规范,并以生态刑法为终极手段的生态法制体系。至于相关生态法律法规的重要程度,宪法、行政法以及刑法所构成的公法体系是保护生态环境与资源的法制体系中最基本的、最强有力的部分。同时,民商私法体系所构成的以受害者本身维权为出发点、以惩罚侵权,对环境侵害的受害对象进补偿、恢复的救济措施为主要内容的生态保护法律屏障也很重要。刑法则以其严厉性而成为前述所有这一切手段得以生效和发挥功能的终极手段,以及在前述措施无效的情况下动用的保障手段。因此,相关法律体系应当是一个公法、私法互相协调、补充的法律系统,只有它们共同发挥作用,才能有效防止、遏制和惩处破坏生态法益的行为。
第三,作为保障法的生态刑法,最终保护的还是生态法益。法律与利益发生联系的纽带是利益主体的行为,因此法律主体的行为与一定的利益追求相关联,人们努力奋斗所追求的一切都与其利益相关。法律对正当利益的保护是通过设置适当的行为标准来完成的。生态刑法体系的建立有利于实现公法和私法共同对生态保护的目的,但是,生态刑法保护的毕竟是生态法益,也就是说,处于从属性地位的生态刑法并不需要保护一切违反生态行政法律法规的行为,只有严重侵犯生态法益的行为才有可能是生态刑法的规制对象。
2.生态刑法立法的从属性
在刑法立法的问题上,国内长期存在旺盛的立法需求[7](P35)。然而,正如那“七八个部门管不住一头猪”抑或“十几个部门管不住一头猪”的说法,刑法立法的情况依然堪忧。考虑到这样一些情况,生态刑法立法既要实现充分保护生态法益的目的,也要克服刑法万能的思想,坚持生态刑法立法的从属性原则。
第一,重视生态伦理的研究和宣传,奠定生态刑法立法的伦理基础。尽管我们将生态刑法划入了行政刑法的范畴,但是,自然犯与行政犯的区分是相对的。根据张明楷的观点,自然犯是指侵害或者威胁法益的同时明显违反伦理、道德的传统型犯罪;法定犯是指侵害或者威胁法益但没有明显违反伦理道德的现代型犯罪[8](P79)。在马克昌的《比较刑法原理》中也对自然犯、行政犯的定义作出了专门的介绍:所谓自然犯,是指无需依赖法律的规定,在其性质上违反社会伦理被认为犯罪者,也称刑事犯;所谓法定犯,是指本来并不违反社会伦理,根据法律的规定才被认为犯罪者,在由于行政取缔的目的被认为犯罪的意义上,也称行政犯[9](P97)。根据两位学者的意见,行政犯和法定犯的区分,主要在于是否具有“伦理的违反性”。当然,伦理违反的判断并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为此,张明楷在自然犯的界定中提出了“明显违反伦理道德”的措辞。这一措辞是基于伦理在两类犯罪的存在并不是截然分明的实际情况,因此相关措辞是严谨的。此外,伦理的观念也是发展变化的。就像酒后驾驶的问题,以前不违法,现在构成危险驾驶罪。入罪之前,根据个体差异,在喝酒不多、行为人认为足以控制的时候,不犯罪也不违法,普通民众也没有发出否定性评价。对于普通民众的价值判断,属于道德范畴。如今公众对酒驾的态度普遍认为是不道德的。这就是普通民众的道德观念的变化,会随着社会发展和法律规范的变化而变化。伦理、道德的观念是发展变化的,为此刑事犯(自然犯)的内核不是个定数——这就决定了自然犯和行政犯之间的伦理界限不是确定的。
因此,我们说生态刑法属于行政刑法,并不是说生态犯罪就没有伦理基础,或者说伦理对生态犯罪的成立、治理没有太大的影响。实际上,在生态犯罪的成立、治理以及生态刑法的构建中,相关伦理基础的发展和理解都将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生态犯罪的成立或者说独立的生态法益的保护需要改变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强势观念,因此,需要加强生态伦理基础的研究和建设,并以此为基础促进生态行政法律法规的建设,最终实现生态刑法立法的突破。其次,在生态伦理的建设中,既要消解人类中心主义的不利影响,也要防范激进的生态伦理的干扰。激进的生态伦理的干扰,例如不考虑人类利益、忽视利己情感的生态伦理主张,由于不符合生态伦理发展的规律以及治理生态犯罪的政策,最终不可能获得立法、司法的支持。最后,生态伦理的研究和发展构成生态刑法立法的基础,这既是生态刑法立法的规律,也是从属性原则的体现。因此,我们曾以利己情感为主线专门论证了生态伦理的发展,也是为我们的生态刑法立法奠定了相关的伦理基础。
第二,生态刑法立法需要率先进行生态行政法律法规以及生态地方性法规的建设,并以此为基础推动生态刑法的立法。
第三,生态刑法立法应当加强附属刑法立法。附属刑法,是指按规定附属在经济法规、行政法规等非刑事法律中的有关犯罪、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称。1997年刑法典出台以前,我国颁行了大量的附属刑法。但是,根据有关学者的意见,1997年以后的刑法立法采取了集中于刑法典的思路。这不仅导致了频繁修改刑法典的后果,造成了法无定法的弊端,严重影响了刑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而且违背了以多元手段解决复杂的刑法立法问题的原则。
考虑到犯罪问题的复杂性,刑事犯的罪刑规范要素比较稳定,很少修改。但是,行政犯的规范要素很容易随着伦理、情感、经济发展等其他方面的因素发生较大的变化,因此,行政犯大多采用附属刑法立法的方式。根据黄明儒的介绍[10](P229~234),将行政犯规定在独立于刑法典之外的独立法典的模式,也称警察刑法模式。典型的如1926年奥地利的行政刑法,奥地利的行政刑法典包括实体刑法、程序法和执行法,体系相当完备。根据各行政事务的需要,在相应的行政法规(尤其在附则中)中直接规定违反相关行政法律规范的后果,包括罪名、法定刑等。这种模式在日本的行政法律规范中也得到了广泛运用,如日本《邮政法》第78条的“阻碍邮政罪”、日本《道路交通法》第117条规定的“道交法救护义务违反罪”,等等。
比较后可以发现,行政犯具有突出的事务性和管理性,犯罪的性质、内容具有多变的特点,原则上应当采用附属刑法立法的方式。当然,一些内容稳定的行政犯罪,如《刑法》第133条之一规定的“危险驾驶罪”,原本只是违反交通行政法规的行为,只受行政罚(我国的行政法,严厉程度未必低于很多国家的违警罪的后果)的处理,但是,现在已经正式成为刑法典中相对稳定的罪刑规范。对生态刑法立法而言,在生态伦理,尤其在独立的生态法益尚未成为人类利己情感的稳定内容之前,不该采用类似于自然犯立法的方式,直接在刑法典中作出相应的罪刑规定,而应当采用行政犯的立法方式,有必要的时候,率先在行政法律中配置相应的罪刑规范,从而实现生态刑法立法的从属性要求。
四、生态刑法司法的从属性
生态刑法司法的从属性主要体现在生态刑法规范解释的从属性。生态刑法规范解释的从属性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生态刑法与其他生态法律法规之间是一种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一方面,处于生态法律堤坝体系顶尖的生态刑法,是生态法律体系的保障法,反映了刑法对民事、经济、行政法律法规的补充性。另一方面,生态刑法规范中的犯罪成立要素,原则上来源于生态民事、经济、行政法规中的不法行为类型。因此,相关生态民事、经济、行政法律法规体现出了其他法律法规的反作用力。生态刑法与其他生态法律法规之间,不是单向的保障作用和地位,而是双向作用的桥梁关系。其中,其他生态法律法规承载了生态刑法规范的法益对象,作为保障法的生态刑法没有独立的作用对象,而是对生态法律法规所保护的对象进行二次作用抑或保护。
第二,生态犯罪的成立以违反生态法律法规为前提。与自然犯独立进入刑法典抑或构成犯罪不一样的是,生态犯罪的成立是以生态法律法规的违反作为前提的。没有生态法律法规的违反,就没有生态刑法作用的基础。换句话说,生态犯罪的不法判断来自于生态法律法规的违反。因此,在对生态刑法规范进行解释的时候,需要结合生态行政法律法规进行体系解释。
第三,生态犯罪构成要件的用语抑或措辞的含义原则上不得超出相关民事、经济、行政法律法规中相关措辞含义所能涵盖的内容。否则,就违反了相关法律用语的明确性,有悖于行为人的合理期待。
第四,在空白罪状下,生态不法行为的判断须以违反生态民事、经济、行政法律法规为前提。但是,不以生态行政法律法规中“追究刑事责任”的措辞为依据。众所周知,行政法律法规中,存在大量的“追究刑事责任”的宣示。这些宣示,表明了立法者的倾向性意见,但不能独立构成完整的刑法规范,也不是生态犯罪的必要条件。
以《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为例,第94条规定:“海洋环境监督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难看出,本规定与《刑法》第9章“渎职罪”的相关规定之间存在一定的竞合关系。但是,不管《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4条是否存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宣示,都不影响《刑法》第9章的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环境监管失职罪等犯罪行为的成立。换句话说,没有《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4条的规定,海洋环境监督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构成犯罪的,照样可以启用《刑法》第9章的相关罪名定罪处罚。没有相关宣示,也不影响相关犯罪的定罪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