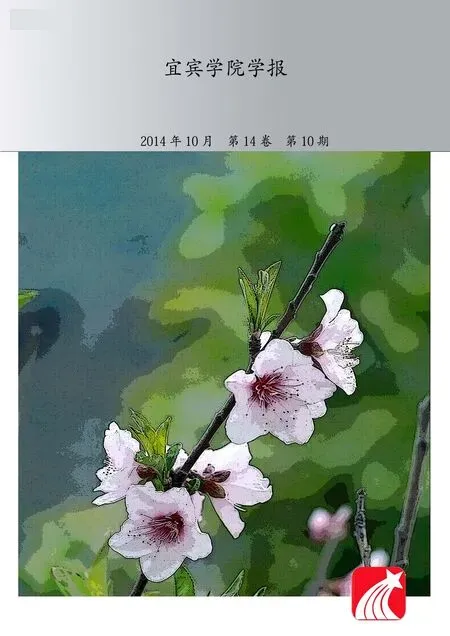身份、地域文化在建构厄勒克特拉情结中的影响
2014-03-12杨芳
杨 芳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心经》(1943年)是张爱玲的代表作,小说中漂亮女孩许小寒狂热地迷恋着自己的父亲许峰仪,最终许峰仪移情于与女儿长相相似的段凌卿,这段乱伦之恋才不了了之。女主人公的迷恋体现了”厄勒克特拉”情结。同时代,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历时40余年创作出的一部经典小说《洛丽塔》(1955年)里的女主人公洛丽塔也有着相似的厄勒克特拉情结(Electra complex)。幼时父爱的缺失导致洛丽塔不由自主地依恋“父亲式”的男性(亨伯特教授),寻找比自己年长的人物作为自己的爱恋对象(奎尔蒂)。厄勒克特拉情结即指恋父情结,弗洛伊德认为,“人早在幼年期就已经有了性欲”,对异性双亲有一种本能的依恋欲望,男孩把母亲当作恋爱的对象而把父亲当作情敌,女孩则正好相反。这样男孩就产生了“俄狄浦斯情结”,女孩就产生了“厄勒克特拉情结”[1]。作为同时代的极富争议的作品,历来褒贬不一。本文运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对两部作品进行对比研究,探讨不同性别身份和地域文化对构建“厄勒克特拉情结”的异同。
一 《心经》和《洛丽塔》中的厄勒克特拉情结
《心经》女主人公许小寒和《洛丽塔》中女主人公洛丽塔人物形象在外形、性格有许多相似点。在她们身上都呈现出一种美,这种美都引起了“父亲式”的人物关注。如在《心经》里的小寒“她的脸是神话里的小孩的脸,圆鼓鼓的腮帮子,小尖下巴,极长极长的黑眼睛,眼角向上剔着。短而直的鼻子。薄薄的红嘴唇,微微向下垂,有一种奇异的令人不安的美”[2]67。洛丽塔的形象均是教授自白中个人意念的产物,她虽不是一个自在人物,在文本中没有出现洛丽塔的视角,是沉默缺场的,但通过亨伯特自白的分析,仍可以发现这个具有独特气质的女孩儿的成熟魅力。在亨伯特眼中,她是“小宝贝”“小公主”,是拥有蜜色肌肤的性感少女。比尔利兹中学里,普特拉辅导员曾对亨伯特说“她是个可爱的孩子,但性成熟的过早让她很苦恼”[3]306。正是由于她们的美,她们不仅吸引着“父亲式的人物”,同时也吸引着许多同龄男生的追求,然而她们却对同龄异性表现出厌倦。《心经》里许小寒对龚海立的态度即说明了这一点。在性格上,许小寒和洛丽塔都表现出了同样的叛逆,如《心经》里的小寒对母亲的态度,小寒在劝母亲阻止父亲婚外恋无果后,对母亲说道“你别得意!别以为你帮着他们来欺负了我,你就报了仇……”[2]90《洛丽塔》里也描述到“洛丽塔把天真和欺诈、妩媚和粗俗、阴沉的愠怒和开朗的欢笑结合到了一起,只要她愿意,可以成为一个叫人十分恼火的小淘气”。她们的叛逆来自“厄勒克特拉情结”的压抑。小寒生日聚会,她对父母的态度迥异,问及母亲时,她答道,“不要紧的,我母亲也喜欢热闹,她没有来招待你们,一来你们不是客,二来她觉得有长辈在场,未免总有些拘束”。而对于父亲,许小寒则表现完全相反的态度。对于“你请你的朋友们吃饭,要我这么一个老头儿搅在里面算什么”的回答,许小寒的反应却是“白了他一眼道:得了!少在我面前搭长辈架子”,对父亲的姗姗来迟,许小寒语气里充满责备[2]71-72。
在两部作品中,两个主人公以自己的方式不断表现、释放“厄勒克特拉情结”的压抑。许小寒爱自己的父亲,当父亲要离开她到绫卿身边时,小寒质问许峰仪,“我有什么不好?我犯了什么法?我不该爱我父亲,可是我是纯洁的”。之后又哭道,“你看不起我,因为我爱你!你哪里还有点人心哪——你是个禽兽!你——看不起我!”[2]91相比之下,洛丽塔对亨伯特教授表现更多的是依恋而不是爱。从小失去父爱的她,父亲的缺位迫使她在现实生活中找寻父爱的影子。在亨伯特教授出现后,她依恋着他,并最终勾引了扮演“父亲”角色的亨伯特教授。洛丽塔的恋父有些不由自主,她不自觉地想要接近这个风度翩翩的男人。如眼睛里进了沙,要让亨伯特给她舔出来。在去夏令营的时候,她突然抬头望来,冲回“我”的房间,“气喘吁吁,踏着重重的步子,正好到了,接着便扑到我的怀里”[3]102。《洛丽塔》中表现洛丽塔深层的恋父情节更多表露在她热烈地爱上了克莱尔·奎尔蒂,奎尔蒂是一个放浪形骸的剧作家,洛丽塔被他的才华所倾倒,并最终在奎尔蒂的帮助下逃离了亨伯特的束缚。相反,对同龄男生,洛丽塔也表现出明显地厌恶。在亨伯特举行的一场有男孩子的舞会后,她表现出极度的厌烦和疲惫,并发誓她还从来没见过如此叫人讨厌的一群男孩子[3]314。弗洛伊德认为:在人格发展的第三阶段,即生殖阶段,儿童身上发展出一种恋母情欲综合感,这种心理驱使儿童去爱异性双亲而讨厌同性双亲。于是,女孩把父亲当作性爱对象而把母亲当作情敌,这样就产生了恋父情结[1]。这种恋父情结导致其不自觉地与父亲亲密和对母亲的嫉妒,延伸到恋爱层次表现出更愿意和父亲类似的身份的人恋爱,而对年龄相仿的男子表现出不屑和厌恶。就如在《心经》里,即使非常优秀的同龄男子龚海立的痴情也无法打动许小寒。
由于“厄勒克特拉情结”的影响,在许小寒和洛丽塔身上明显表现了对母亲的排斥,把母亲作为情敌。“对于小女孩来说情况也大致如此:她对父亲产生情感依恋,想要除掉母亲并取而代之”。[4]292《心经》里许小寒一直把母亲当作情敌,小说一开始,同学对许小寒的感觉,“只听见她满口的爸爸长爸爸短。她母亲呢?还在世吗?”“在世”“是她自己的母亲么?”短短几句话,许太太在家里的多余人角色便凸显了。母亲偶尔打扮下想要吸引丈夫,却被小寒嘲笑。洛丽塔知道母亲爱着亨伯特,潜意识里让她对母亲产生反感。黑兹太太为了和亨伯特单独相处,支开洛丽塔,她立即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并和母亲起了争执。
“我觉得你臭烘烘的”,洛丽塔说。
“这意味着明天不会有野炊了”,黑兹说。
“这儿是个自由国家”洛说。气哼哼的洛丽塔嘘了一声离去以后,奇异的惯性仍使“我”呆在那儿未动,黑兹太太在抽她今晚的第十支烟了,又抱怨起洛[3]71。
文本中,洛丽塔和母亲的争执从未消停过,直至母亲车祸去世。由此看来,恋父情结在《心经》和《洛丽塔》中都有非常明显的表现。
二 性别身份对建构厄勒克特拉情结的影响
同样是表现“厄勒克特拉情结”,张爱玲的《心经》和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在表现上却有着明显的差异,作家的性别身份对建构作品有比较大的差异。在《心经》中,女作家张爱玲把更多自己的感情投射到作品中。张爱玲家世显赫,是李鸿章的孙女。母亲在她4岁时离家,父亲成为她童年生活的唯一真实存在者,父亲是满清遗少,虽浪荡不羁却满腹经纶,是张爱玲的启蒙者,她后来对文字的迷恋亦是受父亲影响。由于母亲的离开,张爱玲深深地迷恋自己的父亲,以至于后来继母的出现让她非常反感。她在自传体散文《私语》里写到:姑姑把父亲要再娶的消息告诉我的,当时是在一个小阳台上,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我的这个继母就在我的眼前,我就会把她从这个阳台上推下去,让她摔死掉[5]106。张爱玲18岁时在继母挑拨下遭父亲毒打,离家出走投奔母亲,后来再也没有回到家里,但她仍然走不出父亲的阴影,并让这段经历成为创作的源泉。在弗洛伊德看来,童年创伤性的遭遇将影响到成年后的性格。张爱玲与胡兰成和赖雅的恋情亦说明如此。在张爱玲许多作品中表现了这种“恋父情结”倾向,如《多少恨》《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里都讲述了女性和比自己年长很多岁的男性情感纠葛的故事。《心经》作为张爱玲表现“恋父情结”的典型,把乱伦之恋发挥到极致。由于作家的性别身份,在《心经》的乱伦之恋中更多表现出许小寒对父亲疯狂直露的爱,父亲的移情和母亲的劝说使小寒被迫放弃。许小寒的反抗是被动的、消极的,反抗到最后只是妥协,表现了当时女性在男权社会的地位是微乎其微的。表面上这是一个有关“恋父情结”的故事,但是透过这一带有“恋父情结”色彩的故事,作者所深入探讨的是现代社会中女性的生存处境、地位与命运。许小寒“厄勒克特拉情结”的产生是由父亲许峰仪纵容出来的,最后由于父亲的离开不得不被迫消解。透过女性作家张爱玲的笔调,女性在选择中的无助与无奈深刻地阐释出来了。作为男性作家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构思《洛丽塔》中洛丽塔的形象却更被动。在叙述视角上,洛丽塔在小说中几乎没有明确的话语和行为,完全隐匿在亨伯特的个人叙述中,整篇文章都是亨伯特的自白,小说中洛丽塔的形象是亨伯特教授意识描写的人物,洛丽塔属于不自在人物,读者只能通过亨伯特的叙述了解洛丽塔的“厄勒克特拉情结”。洛丽塔的这种形象,是亨伯特童年记忆的投射,是他重新虚构之后的幻象,是沉默并失语了的镜像。视角的设置展示了男权对女性自我生命经验以及主体意识的遮蔽,反映了男性对女性的评价与控制。纳博科夫否定洛丽塔有原型人物的猜测,这和《心经》的情感映射不一样,文本中充满了更多关于纳博科夫“流亡”主题的讨论(纳博科夫出生于俄国,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最后辗转到美国),“蝴蝶意象”的执着(纳博科夫一生痴迷于蝴蝶,有评论说洛丽塔是纳博科夫塑造的一只变态蝴蝶),社会道德问题的反思,而对于“厄勒克特拉情结”的建构却是无意为之。无论是《心经》还是《洛丽塔》里的人物虽然表现了“厄勒克特拉情结”,但作者并不以表现恋父情结为主题,而是展现更多关于作者自己的思考,个人的经历和社会存在对作品的影响很大。《心经》和《洛丽塔》表现的恋父情结只是情节内容,不能构成分析文本的主要依据,不同性别作家依据自己的经历和社会存在对“厄勒克特拉情结”建构进行了超越。
三 地域文化对建构厄勒克特拉情结的影响
不同地域文化影响着作家对文本情结的把握和阐释的主题。两个文本中的女孩虽然都表现了“恋父情结”,但结局却是大相径庭的。《心经》中的“不伦之恋”因许峰仪的移情而过早地“扼杀”了,《洛丽塔》中的“不伦之恋”却曲折跌宕,亨伯特用“强制”的方式控制洛丽塔,并强迫与之发生性关系。可以说,《洛丽塔》更直接和露骨地展现了“乱伦”主题,所以该书一经发表便引起了极大争论,出版后在一些国家明确列为禁书。
出生在都市化的上海且受到现代主义影响的张爱玲在《心经》中大胆地表现了“厄勒克特拉情结”,但这段不伦之恋受到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也不得不消解。儒家文化对国人的影响根深蒂固,即使是思想相对开放的张爱玲也只能消解掉这段不伦之恋。同样在张爱玲其它作品里,这种类似的爱情最终都以悲剧结束。许小寒与父亲许峰仪之前的感情有太多的伦理负荷,文本中多次揭示了这种罪恶感,“小寒——那可爱的大孩子,有着丰泽的,象牙黄的肉体的大孩子……峰仪猛力掣回他的手,仿佛给火烫了一下,脸色都变了,掉过身去,不看她”[2]。最终许峰仪把感情转移到段绫卿身上,小寒也在母亲的安慰下意识到这种罪恶感。许太太从风雨中把她接回来,并细心周到地安排时,小寒终于痛苦地央求她母亲“你别对我这么好呀!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小寒的罪恶感也随之产生了[2]95。而《洛丽塔》中的女主人公却主动引诱了男主人公,由此开始了两年多的同居生活。由于亨伯特的束缚和管制,洛丽塔逐渐厌倦这种不伦之恋,并决心逃离他。但她的“厄勒克特拉情结”并未消解,感情转移到理想角色的父亲式的人物——奎尔蒂。奎尔蒂也是有着恋童癖的剧作家,他要求洛丽塔为他拍摄色情影片,洛丽塔拒绝了他的变态要求,被赶了出来,最后无奈之下嫁给了同龄的狄克。洛丽塔“厄勒克特拉情结”的消解更多的是她追求物质利益和为生活所迫的结果。小说中多次提到洛丽塔充满天真和欺诈,并在早年就尝试了“交欢”。相比而言在作品中,洛丽塔比许小寒更具主动性,洛丽塔从最初的无意识恋父到最后有意识主动反抗;而许小寒是从最初有意识反抗(许峰仪的移情)到最后被动地放弃,文化的差异影响了两位作家对女主人公性格的把握和情节的设定。中国五千年儒家文化,伦理道德深深地影响着国人,即使作为西化开放的许小寒骨子里也摆脱不了伦理束缚。美国属于新兴国家,二战后的美国似乎更加“雄心勃勃”,庸俗文化的传播媒介、混乱的教育刺激和浸染了洛丽塔,使她成为一个爱慕虚荣、贪图享乐、棘手暴躁的粗鄙女孩。
同样在主题上,《心经》和《洛丽塔》不同程度反映了作者对自己所在社会的思考和批判。张爱玲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她以华美绚丽而略带凄凉的笔触直揭沪港两地男女在殖民地化过程中新旧交错的现实人生,揭示出处于现代环境下仍然顽固存留的中国式封建心灵的文化错位。张爱玲用这种“错位和犯冲”的不伦之恋反映了当时在租界区这种特殊环境生活的国人混乱不堪的现状。许家是一个带有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许峰仪身上既有封建思想的陈腐又有新派的伪善。太太的年老色衰使他不自觉地对女儿产生了好感,受到伦理压迫不得不转移恋情,找了贫寒家庭出生的段凌卿做情妇。许小寒在这样的家庭长大,形成了“恋父情结”,最后因为父亲的遗弃被迫消解。通过文本我们可以看出许峰仪代表的男权社会对许太太、许小寒、段凌卿所代表的女性地位的压迫。所以,《心经》反映了女性在男权社会的无能为力,现代社会的女性的生存困境、地位和命运值得我们反思。同样是文化批判,《洛丽塔》在序文里小约翰·雷博士的说教说明这个作品是“以更大的警觉和远见,为在一个更为安全的世界上培养出更为优秀的一代人而做出努力”[3]4。该作品谴责了美国庸俗的文化媒介,混乱的学校教育,漏洞百出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弗洛伊德性学说的异化者们[6]。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商业广告和电视传播对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青年一代成为了“消费大军”,在他们身上显示了消费的狂欢。在这种文化的浸染下,为了物质利益他们可以出卖自己的童真、青春乃至婚姻。洛丽塔作为当时青年中普通的一员,他们失去了对社会的判断力,随波逐流,最后沦为庸俗滑稽的一代。同样学校和家庭的教育也混乱不堪,比尔利兹学校强调的是学生约会和交往能力而不是科学知识。自私的母亲和虚幻的父亲将她的“家庭梦”打碎,洛丽塔在扭曲的环境中长大,形成自负、欺诈、自私的性格,她渴望“父亲的爱”,但最后却因为这种“爱”让她失去了作为孩童的快乐,死亡成了她最后的解脱。
结语
总的来说,由于性别身份和文化差异影响了作者对“厄勒克特拉情结”的建构。我们用“厄勒克特拉情结”分析作品时,同时还应该注意两个作家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超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过分强调人的性本能和生物性特征,而忽视了人的更丰富人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文化环境,强调了人的性心理“情结”和潜意识对创作的潜在影响,而忽略了时代、民族和社会文化背景对创作的更深刻的影响[7]。
参考文献:
[1]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务馆,1984.
[2] 张爱玲.心经[M]//张爱玲文集.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3] [美]弗拉基称·纳博科夫.洛丽塔[M].主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4]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讲演[M].周泉,严泽胜,赵强海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
[5] 张爱玲.私语[M]//张爱玲文集.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6] 刘爱琴.《洛丽塔》:人性畸态与死亡叙事[J].齐鲁学刊,2007(4):107-110.
[7] 张建宏.“情结”学说的演绎和超越[J].外国文学研究,2003(1):98-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