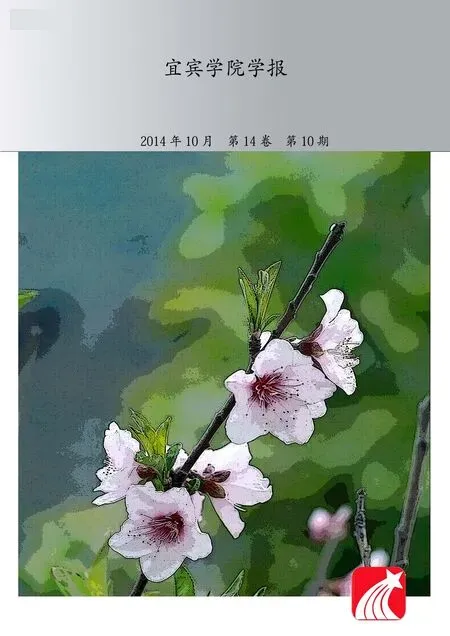唐君毅、牟宗三二先生论罗近溪之学
2014-03-12李瑞全
李瑞全
(国立中央大学 哲学研究所,台湾)
阳明学成为明代之显学,主要是得力于王龙溪与王心斋泰州一脉,特别是罗近溪,世称二溪之学之风流天下所致。二溪自然是以阳明学为根基,两者所继承与发扬阳明学之处,却也各具特色,于王学实有进一步之发挥与深化之处。但二溪之学也引致刘宗周之“虚玄而荡,情识而肆”的批评。黄梨州批评二溪均为流于禅学,有失王门正宗之旨。唐君毅、牟宗三二师对二溪之评价虽有出入,但均以二溪为王门正宗,其中之异同,富有启发性,实有值得细论之处。本文只能专就二先生对罗近溪之诠释而论,至于二先生论龙溪之比较,则待另文为之①。
一 牟宗三先生之评价:以无工夫之工夫为胜场
牟先生早期在《王阳明致良知教》一书,曾在书末引述阳明申论良知之天理意义之后,对罗近溪之学有如下之提示:
此即由致良知中披露感应之几而透涵盖原则与实现原则也。儒者之学大端是以契此为至上了义。不向知识方面而趋也。而最能契此者便是罗近溪。罗氏学大端为二:一、从工夫方面说,拆穿光景,全体放下,浑是知能呈现。二、从本体方面说,人之知能与乾坤知能扣紧为一而说之,以明生生化化之仁体。学问至此,便是无言之教。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更无有能加于此者,亦无有可减于此者。加则为过,减则为不及。离则为曲而悖,吾认良知教之最善开发者以此。而吾亦即言至此以终篇焉。②
牟先生此一时期认为罗近溪之学是阳明学的最高发展。牟先生之评述分为工夫与本体二面。就工夫方面,牟先生认为近溪能进而拆穿光景,使王学不致于流为玩弄光景之害。就本体方面,牟先生认为近溪更能秉承阳明良知即天理所涵之感应之机而贯彻阳明学之彻上彻下之教,更能体现良知之涵盖天地与创生宇宙之义。相较牟先生同期评论龙溪的部份,对近溪之评价显然更高。牟先生亦已点出近溪之所以能从体上展示阳明学之归宿在于以人之知能与乾坤之知能合一,以仁体之生化之义贯通人之良知与天地之良知为一之义。牟先生更誉之为不可加减之学,达到最高的无言之教之境地。此直是以近溪之学为良知教之圆教。
但牟先生在此书中并没有就近溪之学作申论。而在继后之《宋明儒学的问题与发展》一书中,牟先生原拟在中篇申论龙溪与近溪之学,但全篇详论了龙溪之四无说,却只在最后一节略提点了近溪的大意[1]292-293。此节之标题为《十三、良知教之显义、密义、内在义、与超越义:下转罗近溪》,但只写了一大段,似乎有未完之意③。但在此,牟先生正式对二溪之不同评价作结:
在圆而神之一片灵光中,一切皆内在而平铺,此即为显教。然无尽之悲怀、无尽之肯定,则显超越之敬畏,此即显而密矣,内在而又超越矣。此为良知教中之“密”义与“超越义”。此义龙溪不能及,而近溪则及之。故次龙溪而言近溪。[1]293
牟先生在此期对龙溪之评价为只具阳明学之形上的证悟一面,不具有超越的证悟一面,故有虚玄而荡之弊④。因此,此最后评语亦一再指出龙溪为不能及阳明学所具有的内在而又超越的义理,不能即显而密,而近溪则能及之。近溪不但更能承接阳明之学而发扬之,且能达至真正圆融之境,已超越龙溪之学。此对近溪之誉如前书所说,实推崇极高。
而此文最后有一大段放于文末之括号之内,似为说明近溪之学之纲要:
(由无尽之悲怀,无尽之肯定、超越之敬畏,所显之“密”义与退藏于密之“密”义不同。退藏于密之密是万归一,摄客观于主观,而撮于一点,此是正面说,亦是形上之证悟,龙溪雅言之。而与超越义相连之密义,则是由超越的证悟而知命以言之,此是反面说。超越的证悟两头通,自体现习化事成言,则为圆而神之内在;自无尽之悲怀、无尽之肯定言,则为知命之超越。)[1]293
此文以龙溪之形上之证悟只能达于摄客观于主观,集中于良知之灵明一点,亦只能达致良知教之正面之申展。至于近溪则更能兼良知之超越义与密义而从反面说,以达至内在之圆而神与超越之知天知命之最高境界,而为龙溪所不及。但牟先生并没有进一步地申论近溪义理之内容。其后,在《心体与性体》三大册中亦未再提此义。
直到《从陆象山到刘蕺山》一书,才在此书第三章“王学之分化与发展”之第二节“王学底分派”中的“再看泰州派底罗近溪”中正式论述近溪之学[2]232-245。此时,牟先生已对龙溪的评价有所提升,不再以为只限于超越的证悟,认为四无句是四有句之调适上遂,而为阳明之嫡子。虽然此一评价尚未至最后期以圆教的观点称誉龙溪,却也改变了对二溪的不同评价。牟先生在此一小节综述泰州派王心斋与王东崖之取向后,评论近溪之学时,首先提及近溪之特色在破除光景的表现,如下:
顺泰州派家风作真实工夫以拆穿良知本身之光景使之真流行于日用之间,而言平常、自然、酒脱与乐者,乃是罗近溪,故罗近溪是泰州派中唯一特出者。[2]237
并再次以近溪与龙溪比论:
如果以罗近溪与王龙溪相比,王龙溪较为高旷超洁,而罗近溪则更为清新俊逸、通透圆熟。其所以能如此,一因本泰州派之传统风格,二因特重光景之拆穿、三因归宗于仁,知体与仁体全然是一,以言生化与万物一体。阳明后,能调适上遂而完成王学之风格者是在龙溪与近溪,世称二溪。[2]237⑤
此时期,牟先生以龙溪与近溪并列,都是能把阳明学调适上遂的嫡子,并无此优于彼之论。对于近溪之学的主要特色则仍然是以破光景与仁体生化,与万物一体之义称之。至于近溪何以特重破光景,牟先生指出,因为阳明学于心、性、天、理、道等之分解已尽:
故顺王学下来者,问题只剩一光景之问题:如何破除光景而使知体天明亦即天常能具体而真实地流行于日用之间耶?此盖是历史发展之必然,而近溪即承当了此必然,故其学问之风格即专以此为胜场。[2]239
牟先生进而指出,罗近溪之破光景工夫在于破除工夫上的僵持,而求全体放下,即破除工夫之紧张性,“以工夫难得凑泊,即以不屑凑泊为工夫”,“解缆放船,顺风张槕”,轻松自然,使工夫无工夫相。牟先生说:
罗近溪底工夫即在此处用心,其一切讲说亦在点明此义。以此为工夫底中心,则一切分解的讲说,如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之层层关系底解说,皆只是立纲维,立实践底轨辙,而真正地作起来,却无分解的轨辙可言,而却是须进一步达至那无工夫的工夫,亦即吊诡的工夫。此若说是轨辙,则乃是吊诡的轨辙,而非分解的轨辙也。对此而言,那一切分解的纲维皆成外在的、表面的,只是立教之方便也。真实切要之工夫唯在此一步。此罗近溪之所以能“一洗理学肤浅套括之气,言下便有受用”之效也,亦吾所以谓其“更为清新俊逸通透圆熟”之故也。[2]240-241
此是从实践工夫上称许近溪之表现,即所谓“工夫难得凑泊,即以不屑凑泊为工夫”之无工夫之工夫,吊诡的工夫。此是泯除工夫之僵固相,复归于平实之自然境地。文中虽已用了吊诡的工夫,非分解的轨辙等词,已近于说其为圆教义之表现,但牟先生此时似尚未从圆教之非分解的视野来衡量近溪之工夫。
对于前文及上文所提及之近溪之本体论上的特色,牟先生没有再进一步申论,反而认为此已为程明道所,并认同黄梨州之说“此即足以示罗近溪之特殊风格当从拆穿光景说,不当从其归宗于仁,言生化与一体说也。此后者明道早已尽之矣”[2]244。由此可见,牟先生完成《心体与性体》三大册之后,认为存有论上之圆顿之教义为程明道所已尽发,而非近溪之胜场,故没有再进一步申论近溪此方面之义理。如此,近溪之特色乃收缩而为工夫实践上的表现,反而不及龙溪之能在本体上推进阳明之四有教。此一进一退,影响了牟先生最后论定儒家的圆教时,以阳明、龙溪之学,配以明道、五峰与蕺山为主,而近溪则不与焉。此为牟先生对近溪最后之评语。
二 唐君毅先生之评价:以仁体贯彻本末人我之圆教
唐先生认为王心斋之泰州派与其他王门之不同主要在于心斋之精神是“直面对吾人一身之生活生命之事中讲学”[3]382。由此而得安身,安家国天下为乐。泰州派之当下之安身之教,以道即在鸟啼花落,山峙川流,在捧茶童子之自然回旋中见,故能使人当下即有所启悟。唐先生以为此“即先正面的悟此良知之本体之乐,以成其工夫之教。而与龙溪之重正面的悟良知本体之一点灵明,以成其工夫,正有相类之处者也。”[3]383心斋父子固启人极众,但此一回归良知之自然境界之平平,却有流于“情识而肆”之弊。真能秉持泰州派之精神而发挥王学者则只有罗近溪。唐先生说:
若更能循此身之本,与家国天下之末之“本末一贯”之意,而于此识得仁体之贯于此本末之一“生”之中,而畅发阳明大学问一文之旨,以言大人之身之另一型态之悟本体即工夫之学者,则罗近溪也。[3]385
换言之,唐先生认为罗近溪之学乃依泰州派之安身之义,进一步以仁德之生生之化贯通本末,而以悟本体即工夫之学为教,既与龙溪之重正心先天之学,即本体即工夫之义相接,亦足以秉承和发展阳明“大学问”之即生命之贯通本末而言大人之身,以成良知之教。
罗近溪曾有“学有以用功为先,有以性地为先者”之区分,类乎龙溪之由工夫以复本体之诚意之学,与即本体为工夫之正心之学之二面。近溪之以性地为先之学直以当下之言动即是仁体之表现,至于以用功为先则不免于意念有所执持,已自僵化而有流于玩弄光景之弊。因此,近溪之学以“性地为先”者,即自信当下之表现即为良知本体,即仁体之挺立,虽平平无突起相,但却当下即是良知之发用。此与龙溪之所主之先天之学无异。
罗近溪更取传统之孝悌,而益之以慈,以孝悌慈三事皆为人之所生而有之良能,故能于日用伦常之中即显发出良知本体之天理,即仁体之呈现。除了近取于身之外,唐先生认为近溪亦同时能推广心斋之本末一贯之学于天下国家,以臻于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之呈现:
近溪则依此本末一贯之学,更“联属家国天下以成其身”,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谓“身大,则通天下万世之命脉,以为肝肠;通天下万世之休戚,以为髪肤。病痛痀养,更无人我,而浑然为一,斯之谓大人而已矣”(盱坛直诠卷上)。此大人之所以能合家国天下,以万物万世为一身,为其大学问,则由于此身之生,与其外之天下人之生、天地万物之生,原互相感应孚通,而不可二。此即昔贤所谓仁体之合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3]386-387
此可谓补充了牟先生所鲜言之近溪论孝悌慈与仁体之义。换言之,近溪之性地为先之即本体为工夫之学,不止与龙溪之言一念灵明,以自悟本体而为工夫相通;亦更进而依仁体之生化之德之显现于一人之身、一人之生命,乃能通于天下人之身、天下人之生命,感通不断而为一。故唐先生评断近溪之学“与龙溪重言良知与一念灵明,以自悟本体之旨通。然此中近溪之学、与龙溪之自悟本体之道,仍有不同。”[3]387
唐先生认为由此可进而指出近溪与心斋和龙溪之差别:
近溪之悟性地、或良知本体为工夫,既不同心斋之悟良知之觉有乐,而未畅言此乐之依于仁者,亦不同龙溪之只在心之灵明上参究。然其于日用常行处,当下提撕,以见“当下本体”,谓此中无往非道,并谓念庵之“不信当下本体,则无下手处”,则近龙溪。[3]389
唐先生在此表示,近溪之有进于心斋与龙溪之处是能以仁体,以生化之道,以日用平常之孝悌慈,建立当下即是之义理,以此当下本体而开展工夫,为工夫之下手处。唐先生认为近溪之仁体,特重其“无强”“无尽”“无期、恒久”之义,以言仁体之贯通人我内外,古往今来之胜义。唐先以为“此可谓本于明道识仁、象山宇宙即吾心、与慈湖己易之说。然三义并举,则近溪之言也”[3]432,可谓对近溪之本体论方面之义理推崇极高。
如前所述,近溪之工夫之申论亦极具特色。在工夫上,近溪著名的“工夫不能凑泊,即以不凑泊为工夫”之无工夫之工夫,回归日用平常之平平,彻底消除了工夫相与由此而有的僵化。近溪此种日用平常之工夫容易让人以为近溪轻许人以自然而化,缺少艰难。唐先生认为此乃误解。盖近溪早年尝因以求烔烔之心而有心火之患,因而深切于玩弄光景所产生之心魔,而思有以治之,故其破光景之表现特别亲切而深刻。唐先生说:
近溪言悟道,即在现在日用平常之言动中,悟后之工夫,则在于此道之恭敬奉持,不自瞒昧,平淡安闲,以顺此道。此则在近溪之答人问语处多可见。[3]438
又与龙溪比论而评曰:
近溪之论工夫,则可谓善于自性体平常处,提掇良知良能,而又能知敬畏小心义者。此其所以别于龙溪,而在泰州学派中最为迥出者也。[3]438-439
唐先生最称许近溪之工夫论之特出之处,既能显良知良能之平常日用之自然,又能不放失而谨守敬畏之意,仁智合一,语意圆足,不致流于龙溪之重智而忽仁之失。唐先生更举出近溪之性地为先之教,实极高明而道中庸,有诡谲相即之妙:
故近溪言心尝谓“镜面之光明与尘垢,原是两个,吾心之先迷后觉,却是一个。当其觉时,即迷心为觉;则当其迷时,亦即觉心为迷。除觉之外,更无所谓迷;而除迷之外,亦更无所谓觉也”。此则不取禅道与龙溪之心如明镜之喻;而近起信、华严、天台之迷觉一心之旨。[3]390⑥
近溪不以镜喻心之迷觉,而打并为一,直以迷觉只是一心,则两者有相依相即之义。唐先生以近溪此段论述,为近于起信论、华严、天台之圆教之义,而优胜于龙溪之心如明镜之喻。
唐先生认为近溪之学有一统贯宋明儒学之圆融尽至之表现,兹引述如下:
总观近溪之学,远承明道,以求仁为宗,而喜于赤子之良知良能,家家户户之孝第慈,百姓日用而不知之视听言动上,指点仁体。其重当下悟入,似象山慈湖龙溪。而象山慈湖龙溪,皆只重“心”重“知”,未真重当机指点仁体。阳明言良知,因即仁者之好恶;然阳明既以致良知标宗,即不免下启龙溪重知而忽仁之失。近溪直下以仁智合一,语意乃复归圆足。其言人之良知良能,即乾坤知能,本于阳明人之良知即天地万物之良知义,亦颇同龙溪一念灵明从混沌里立根基之语。皆阳明学之向上一着之推扩。既识良知良能原是乾坤知能,乃本“复以自知”“时时中出”之义,以言人之迎迓天机,而大顺天用,则周程张朱之本天道以言人道,亦皆可以立。至其破光景之虚幻,言灵明之不可孤守,而必归于应物以显仁。言仁体呈露后之恭敬戒惧工夫,言识得仁体之不可“侈然顺适”,则亦未违宋儒主敬之教。言圣心之不了,则儒者担当世运之精神见。是皆可救治彼坐享现成良知者之弊。[3]440
此为唐先生对近溪之学之总评价。
三 二先生对罗近溪之定位
如上所述,牟先生对近溪之学早期推崇备至,认为是最圆熟的王学之境界。此似近于唐先生之基本评价,亦是此一期间二先生互动频密,而意趣接近之共同观点。正如牟先生对龙溪之评价随其中国哲学诠释之发展而改变,牟先生亦经历对罗近溪的不同评价的表现。基本上,牟先生于完成《心体与性体》三大册之研究后,以明道之一本论为宋明儒学中最圆顿、境界最高之圆教。因此,牟先生亦称许近溪之能本知体与仁体为一,义理亦通透圆熟,但却以只是明道之后学,不算自立新义,故最后之评价只重其工夫上之破光景,发挥无工夫之工夫,只成为工夫论之圆说。而且由于日后牟先生据天台宗而立之圆教判准成熟,龙溪成为阳明学之真正的调适上遂之发展,是更有进于阳明之分解而达于别教一乘圆教之境。相形之下,牟先生对近溪之评价相对降低,不在牟先生所构造的宋明儒之圆教系统之内。此于近溪之孝悌慈之为贴近日用伦常之当下即是之义与乎觉迷一体之旨,有进于阳明龙溪之处,似乎正视不足。
唐先生的评价则前后相当一贯,甚至后期更多推崇。唐先生论近溪之学主要以心斋与龙溪为对照,以显示近溪之特色,和有所进于前人之处。虽然唐先生以为近溪的仁体与生化之论,俱继承明道、象山与慈湖而来,但能整合三者为一通贯本末内外之学,亦是一大综和发展。唐先生特别推崇近溪仁体之论为其能仁智合一,内外本末贯通之义理,认为近溪之学已超越了心斋与龙溪,实已臻至圆教之境地。唐先生也特别重视近溪在工夫论上的贡献,而最主要认为近溪实结合了良知良能与敬畏之意,是真能从平实而展示高明之论。
结语
从上可见,牟先生基本上是从本体论上评断近溪学之地位,而唐先生则从工夫入手。因此,二先生之评价有畸轻畸重之差。牟先生后期之眨抑近溪之说是以明道在此一圆教义上已先行,且真能盛发圆教之一本论,近溪则没有任何义理之新猷可说,故仅置于泰州门下为一大家,但未能与于宋明儒学之圆教系统。然而,观乎唐先生引述近溪之“迷觉一心”之义,则近溪亦当有进于龙溪之处,而可补阳明龙溪之诡谲相即之义之不足。唐先生一本哲学家之承先启后之发展模式,以诠释评断近溪之学的贡献。唐先生之评价相当重视近溪学在工夫论上是否能主客圆融,特别是接近朱子之持敬之义,似依一系统之是否能有进于朱陆之胜场而汇通为一。最后唐先生乃据此而极度推崇近溪之为圆教之义。然而,近溪固然有进于龙溪之四无说之只立先天正心之学,近溪于工夫上亦只较龙溪为更细密而切近,然近溪重心体之明与智,仍偏向阳明之心学,与伊川朱子持敬之论实有距离,此中尚多有待析论之处。
注释:
①本文是作者于2009年9月25-28日,于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中央大学哲学研究所,台湾师范大学国际与侨教学院,东方人文学术研究基金会,鹅湖月刊社合办之“第八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之论文。本文原有未完之意,未及详论,今只于最后引用唐先生评近溪一段,以及略为校正文句,或待日后再增补其余。又,在会议上,原初拟以唐、牟二师对王龙溪与罗近溪,世所谓“二溪”之诠释和评论为题,但由于时程紧逼,会前已于另一会议发表了牟先生对龙溪之评价,部份会出现重迭,故本文宣读时改为专以罗近溪为题,先作一比论。关于牟先生对龙溪之评价,请参看本人之《龙溪四无句与儒家之圆教义之证成——兼论牟宗三先生对龙溪评价之发展》一文。该文原发表于国立中央大学儒学中心主办,于2009年4月17-18日在中坜国立中央大学举行之“宋明理学会议”,经修后于儒学中心发刊之《当代儒学研究》第六期(2009年7月),131-147页刊登。
②参见牟宗三所著《王阳明致良知教》,此书原于1954年4月由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出版,其后收入《牟宗三先生全集》第8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之第二部,引文出自此部第102页。
③杨祖汉于《宋明儒学的问题与发展》之出版说明上也指出此文在罗近溪部份似未写完,参见此书第215页。
④详论请参见《龙溪四无句与儒家之圆教义之证成——兼论牟宗三先生对龙溪评价之发展》一文。
⑤引文中黑体为原文本有,下同。
⑥此文虽置于同书第十六章《罗近溪之即生即身言仁,成大人之道》之前,但唐先生表明第十六章乃是收录更早期的一文而成,故此段引文之论可以说是唐先生对罗近溪最后的论定。
参考文献:
[1] 牟宗三.宋明儒学的问题与发展[M].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3.
[2] 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嶯山[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9.
[3]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M].香港:新亚研究所,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