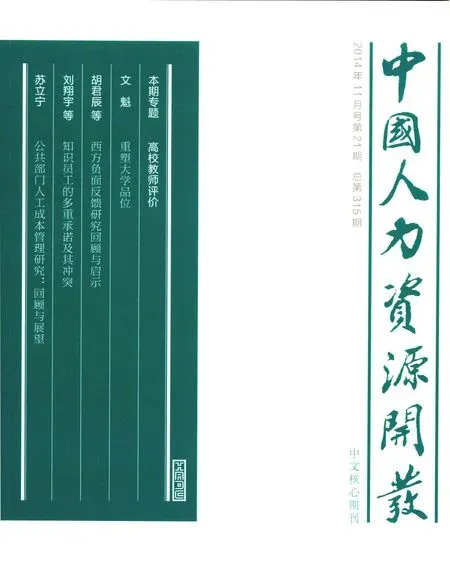群体反生产行为诱因分析——基于SIMCA 视角的多案例研究
2014-03-10孙博董福荣
● 孙博 董福荣
自有阶级社会以来,诸如偷盗、邻里吵骂、毁坏他人财产等越轨行为就一直存在。当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此类越轨行为也随之跨越组织边界进入到工作场所。理论界将这类危害组织及其成员利益的越轨行为统称为反生产行为。随着技术进步和组织结构变革,反生产行为呈现出多样性、普遍性、反复性、隐秘性等特点,对企业利益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危害也日趋严重(张建卫、刘玉新, 2008)。据统计,美国企业每年因为雇员偷窃而造成的损失高达500 亿美元(Coffin, 2003),大约有75%的雇员承认至少有过一次某种形式的反生产行为(Case, 2000)。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我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在这种环境下,相当一些人心态变得浮躁、行为时有偏常,致使各种反生产行为层出不穷。诸如 “韶关旭日玩具厂群体斗殴”、“通化钢铁群殴”等事件,给相关企业的正常经营和声誉造成了重大损失,甚至威胁到社会和谐与稳定。近年来,理论界关于反生产行为的研究虽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大多数研究集中在个体层面,对来自群体和组织层面的影响甚少关注(刘文彬、井润田, 2010)。鉴于此,我们基于社会心理学角度,从群体层面出发解构群体反生产行为的形成,并提出相应对策。具体而言,在集体行动社会认同模型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 SIMCA)(Van Zomeren et al., 2008)的框架下,结合我国新闻媒体报道的典型案例,从群体情绪、社会认同和工具理性三个因素出发,分析群体反生产行为(Kelloway, 2010)的形成原因,并据此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群体反生产行为防控建议与干预对策。以期深化反生产行为研究,为相关企业提供借鉴。
一、反生产行为研究溯源
尽管,反生产行为是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但工作场所有害行为却由来已久,如1520 年麦哲伦在其环球航海之旅中遭遇的多次船员罢工(Klotz & Buckley, 2013)。工业革命后,国外学者曾对反生产行为进行过研究。如1811 年英国以毁坏生产机器著称的“卢德运动”以及后来泰勒和梅奥在工厂里观察到的“磨洋工”现象等。Mangione 和Quinn(1975)首次提出反生产行为(Counterproductive Behaviors)一词,并认为它是一种雇员不作为、破坏资方利益的行为。上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前,国外学者关于反生产行为倾向于研究某一具体行为,如破坏(Mangione & Quinn, 1975)、偷盗(Greenberg, 1990)、旷工(Johns, 1994)、迟到(Blau, 1995)等,并没有认识到不同行为之间的共性,对反生产行为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在这种情况下,Robinsion 和Bennett(1995)提出了整合反生产行为研究的观点,并将反生产行为按照对象(个人或组织)和行为严重程度予以分类,明确界定工作场所越轨行为是一种违反组织规范,危害组织及其成员利益的行为。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对这种分类提出了质疑,Berry 和Sackett(2007)指出人际越轨行为与组织越轨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相关(R=0.62),Bennett和Robinson(2000)也认为行为危害程度的划分只是量的衡量,并非有质的区别,故行为危害程度不宜作为分类纬度。此后,Kelloway et al.(2010)基于Klandermans(1996)的社会抗议模型提出了反生产行为的行为人数维度以替代危害程度纬度,即群体行为和个体行为两个纬度(见下图1),这种分类法将反生产行为的研究引向了群体层面,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

图1 Kelloway et al.(2010)的反生产行为分类
我国学者关于工作场所越轨行为的研究始于2002年,刘善仕从组织行为和员工管理的角度系统地介绍了工作场所越轨行为。随后,许多学者就工作场所中“反生产行为”(郭晓薇、严文华, 2008; 张建卫、刘玉新, 2009; 张永军等, 2010)或“越轨行为”(毛军权, 2003; 杨杰等, 2004)从概念内涵、影响因素、模型介绍等不同方面做了大量研究。我国理论界关于解释反生产行为形成的研究虽然起步晚,但也取得了许多有益成果。如刘文彬(2009)认为不同类型组织伦理气氛对雇员越轨行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刘玉新等(2011)基于自我决定理论阐述了组织公平对反生产行为的影响机制;王石磊等(2013)就家长型领导对80 后员工越轨行为的作用机理进行研究,并指出了压力感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组织支持感、组织幅度的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国外关于反生产行为的研究有向群体层面发展的趋势,而国内的研究却仍停留在理论引进和整理前人成果阶段,关注点大多集中在个体层面,对群体反生产行为的诱因、形成机制以及行为解构研究过少。尤其是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敏感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突出,群体反生产行为发生频繁,大量现实问题亟待正确认识,亟需科学预测和有效控制,以促进企业和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
二、基于SIMCA 视角的典型案例剖析
(一)SIMCA 模型
一直以来,群体行为得到了包括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等学科学者的关注。虽然理论界有许多关于解释和预测群体行为的研究,但在预测模型的构建上观点各异。其中,以工具理性和社会认同的双路径模型(Simon et al., 1998)、工具理性和群体情绪的双路径模型(Van Zomeren et al., 2004)较受推崇,却又难免偏颇。Yzerbyt et al.(2003)研究发现, 社会认同过程同样也会影响群体成员的情绪体验。在这种情况下,Van Zomeren et al. (2008) 通过分析整合了前人研究,并提出了集体行动社会认同模型,该模型包含群体情绪(groupbased emotion) 、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和工具理性(instrumentality)三个影响个体参与集体行为的前因变量(Kelloway et al., 2010)。
群体情绪是个体对与所属群体相关情境或事件的功能性反应,如群体因受到不公平待遇,而产生的群体愤怒、恐惧、焦虑等情绪(Van Zomeren et al., 2004)。社会认同是指个体以所属社会类别身份、群体成员资格来定义自我,也可将其看作是一种认知机制, 即从“我”到“我们”的自我认知再定义(陈浩等, 2012),当群体成员都以群体身份定义自我时, 他们会做出一些趋同或类似的行为;工具理性是个体决定是否参与群体行的主要动因之一,是对参与群体行动成本和收益的心理计算(Klandermans, 1984)。简而言之,SIMCA 框架的核心思想认为群体情绪、社会认同和工具理性都会直接诱使群体行为发生,并且社会认同也可以通过工具理性和群体情绪间接影响个体参与群体行为(陈浩等, 2012)。社会认同提供了不公体验的群体分享基础,促进情绪的扩散和群体情绪的形成,激发个体参与群体行动;同时,社会认同也能作用于工具理性,通过较强的认同感向相对无力的个体灌能,并提高背叛群体的成本与合作的收益(Klandermans, 2002)。因此,社会认同在工具理性、群体情绪与群体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Kelloway et al., 2010)。
某种程度而言,反生产行为可被视为一种抗议行为,即个体或群体因为组织或个人的某些危害其利益的行为而作出的维权抗争(Kelloway et al., 2010)。因此,在SIMCA 框架的基础上,我们认为群体消极情绪的产生和扩散是群体反生产行为的关键诱因之一,个体不公体验会转化为一系列消极情绪,造成内心的紧张感,继而产生平复消极情绪的行为意向;社会认同的作用则主要体现在群体社会规范对个体的影响上,包括直接影响个体参与群体反生产行为,以及间接通过情绪扩散和提高背叛群体的成本与合作的收益来影响个体行为。工具理性则是个体对参与群体反生产行为的成本与收益的主观感知,这种心理计算决定了个体是否参与群体行动,并促使群体反生产行为由意向转化为实际行动(张书维等, 2012)。
(二)针对组织的群体反生产行为
针对组织的群体反生产行为既有罢工、集体工资谈判,也有群体打、砸、烧、抢等非法行为(Kelloway et al., 2010)。
1.背景。2009 年6 月26 日凌晨,在广东韶关旭日玩具厂宿舍区内,部分员工因事发生摩擦,继而在厂区内斗殴,最终造成120人受伤、两人死亡以及工厂生产设备尽毁。此事件起于该厂一名离职员工在网络上发布污蔑新疆籍员工的不实言论,致使部分本地员工误信而产生“排外”情绪,当新疆籍员工得知“排斥”原因后心生不满。事发当晚,几名新疆籍员工性骚扰本地女工以发泄不满情绪,本地员工看见后予以制止,双方因此发生争执,人员越聚越多形成对峙局面。在得不到有效调解的情况下,这场对峙最终升级成为群体斗殴、打砸工厂事件。
2.群体情绪的产生。实际上,在该群体反生产行为事件发生的过程中,不公感知是个体情绪产生的关键因素。新疆籍员工因感知到“歧视”而心生不公平感,这种不公平感使部分新疆籍员工产生“委屈”和愤怒的情绪,出于消除这种内心“委屈”和报复本地员工的目的,产生了报复性行为意向。
3.社会认同的促进作用。社会认同通过员工自我认知机制,提供了不公体验的群体分享基础,加速不满情绪的扩散和群体情绪的形成;同时,较强的社会认同能给与相对无力的个体灌能,并提高背叛群体的成本与合作的收益,促使更多的个体参与群体行动,更多个体的参与又会降低群体反生产行为的单位成本,而增强个人参与群体反生产行为的动机。在该群体对峙、斗殴过程中,情感认同和规范认同作用于不同个体,促使个体参与群体活动。对群体具有高情感认同的个体看见群体成员被欺负后,群体身份的自我意识使员工自觉加入对峙以维护群体利益,而另一类非自愿加入斗殴的个体则是迫于群体规范的约束和受到来自群体成员的压力,害怕不加入斗殴而被视为“异类”,事后受到谴责或攻击,这种规范认同提高了个体背叛群体的成本,使个体放弃“搭便车”而加入群体反生产行为。
4.工具理性的作用。个体对参与群体反生产行动的成本与收益的心理感知,决定了自身是否参与群体反生产行动,并促使群体反生产行为由意向转化为实际行动,当个体认为自身参与群体反生产行为有助于群体达目的,更多的人参加群体反生产行为有助于目标的达成、收益的提高、单位成本的降低时,个体参与群体反生产行为的动机越强。在由口角之争逐渐升级为更为严重的拳脚互殴、打砸工厂的过程中,很多平时厌倦工厂枯燥生活以及曾受到工厂不公平待遇的员工,对工厂表现出低认同和低承诺,尤其是当看见参与群体行动的人越来越多后,在存有“侥幸”心理和“法不责众”的想法下借此“浑水”趁机报复组织,参与了打砸工厂和毁坏生产设备等群体反生产行为。
(三)针对个人的群体反生产行为
针对个人的群体反生产行为有群体侵害、抗议、围攻等形式(Kelloway et al., 2010)。
1.背景。2009 年7 月24 日,通化钢铁集团因股权调整而引发群体事件,刚上任的通钢集团总经理陈国军被抗议工人打死。该事件起因于通钢集团部分离休员工对私有化的抵触,他们号召员工集会以抗议集团股权调整,在没有得到有效回应的情况下,言语抗议升级为破坏生产线。随着事态严重化,股东委托集团总经理陈国军平息抗议,但其失当的言辞激怒了抗议人群,最终陈国军被群殴致死。
2.群体情绪的产生与扩散。实际上,个体对企业私有化决策的不公感知是这起群体反生产行为的起点,管理层决策过程的不透明和决策结果未尽及时告知义务,导致了程序不公和信息不公,因而给员工造成了严重的内心不公感和消极情绪,为平复这种内心紧张,继而产生抗议行为意向。
3.社会认同的促进作用。抗议行为由离休员工率先发起,离休群体对企业有深厚的感情,不愿看见昔日效力的国企被私有化,这种情感认同让离休员工对集团私有化没有“袖手旁观”,他们积极组织离休群体进行抗议;随后,在职群体中的部分个体因担心企业私有化后利益受损,也加入到抗议中;与此同时,在职群体中的部分“中立”个体也迫于群体内部规范而放弃“搭便车”。最终,在情感认同、利益认同和规范认同的作用下离休群体与在职群体中的大部分员工组成抗议群体,用行动抵制企业股权改革。
4.工具理性的作用。在言语抗议无效、参与抗议的人数增多的情况下,个体对参与群体反生产行为的成本与收益进行了重新评估,参与行动人数的增加提高了行动成功的可能性,提高了预期收益,同时也降低了参与群体反生产行为的单位成本,这种心理计算促使了抗议行为的升级,他们策划冲击生产区、堵塞原料运输线以扩大事态引起社会注意,从而逼迫管理层就范。随着事态的发展,陈国军失当的言辞点燃了群体对组织的“怒火”,现场抗议者将企业代表陈国军视为不公源,将所有对组织的不满以极端形式加之其身。
(四)小结
从以上案例分析可知,群体情绪能较好的预测群体反生产行为的发生,而群体情绪的产生源于对不公平的感知和社会认同的情绪扩散作用,其中不公可具体表现为分配不公、程序不公以及人际不公,对不公程度的感知又存在个体差异,并不是所有个体感到不公后会立刻产生行为意向;社会认同在群体反生产行为发生的过程中不仅起直接影响作用,也可通过影响群体情绪的扩散和工具理性,间接促使个体参与群体行动,并以情感认同、利益认同以及规范认同等三种不同类型单独或交互作用于个体;工具理性则是个体决定参与群体反生产行为的利弊权衡或成本与收益的心理计算,也是群体反生产行为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当个体预计自身参与群体反生产行为有利于表达诉求和争取利益,预期有更多的人参与群体反生产行为,以及更多的人参与群反生产行为有助于达到目的时,自身参与群体反生产行为的可能性将增加,而更多人的参与也会提高群体反生产行为的破坏力。
三、控制思路与干预对策
基于以上案例分析,我们认为对群体反生产行为的预防和控制可以结合群体情绪、工具理性和社会认同等主要影响因素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实现。具体而言,宏观层面发挥政府、工会作用;微观层面发挥人力资源管理的作用,善用招聘,加强培训,引入员工参与决策和普法教育,以防控群体消极情绪的产生与扩散,降低群体行为收益预期,减小社会认同的负面影响,从源头防控群体反生产行为。
(一)防控群体消极情绪的产生与扩散
1.立法规范,加强检查
通过立法规范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尽量减少或杜绝企业诸如拖欠工资、工作歧视等引发雇员消极情绪的行为,避免群体消极情绪的产生与扩散。同时,加强对企业违法行为的监管和打击,保证法律的执行效果。劳动监察部门的监管方式应以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相结合,以保障法律法规落实到位。如有必要可会同社区、行业工会和相关部门联合开展检查,以强化监察力度。对检查后仍不合格的企业,应加大复查力度,针对问题特别严重的个别企业,有选择性地使用行政干预,如果必要可移送法院强制执行。
2.舆论监督,及时干预
强化舆论监督作用,现在各种媒体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而通过媒体正面引导和对企业不正当做法的及时曝光,可以促使企业采取措施,改进工作,预防群体消极情绪的产生与扩散,使许多反生产的行为得到及时和有效遏制。对劳动纠纷也应做到及时、有效地干预和协调,防止矛盾扩大化。劳动监察部门可联合企业工会和街道办事处形成劳动情报网络,做到对所辖区域企业劳动舆情的掌握,提高纠纷处理反应速度。同时,在处理纠纷上应把握分寸,对劳动者的合理诉求应予以满足,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对不合理的要求,应做到耐心疏导,在不损害企业核心利益的情况下做出一定让步,以引导劳动者情绪的宣泄;对非法行为,则坚决予以打击,保障企业的正当权益和正常运营。
3.员工参与,民主管理
许多群体消极情绪起于不公感知,其中分配不公、程序不公以及人际不公属于组织可控因素,企业可提倡员工参与管理,并做到信息及时公开,以有效消除雇员不公感知、预防群体消极情绪的产生。具体而言,企业可按如下几个方面实践:第一,建立重大决策会议旁听制度,有选择的选取各层级员工代表参与公司重大决策或重要会议;第二,完善意见采纳机制和沟通渠道,让员工能够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第三,建立雇员参与奖励机制,鼓励员工积极、正确地参与企业的经营和管理。
4.善用招聘,加强培训
防范反生产行为的发生,也可以从招聘做起,选拔具有较好情绪管理能力的员工,从源头把控群体消极情绪风险。大量研究表明,个体因素能较好地预测反生产行为的发生。员工对不公平待遇的感知和处理能力存在个体差异,个体因素中的年龄、价值观、文化素质、个性敏感性等因素能影响个体对不公待遇的感知;个体因素中的情绪稳定性、归因风格、控制点等人格特征则影响个体对不公平待遇的处理。因此,企业可利用情商测试、人格特征测试等技术结合压力面试和背景调查,选拔性格宜人、情绪稳定、自控能力强、沟通能力好的员工,提高工作群体情绪管理水平,降低群体消极情绪风险,以有效预防群体反生产行为的发生。
加强自我冲突管理能力的培训,合理引导员工表达情绪,增加群体表达诉求的途径。首先,企业需要加大对员工进行自我冲突管理培训的力度,提高员工处理来自工作和生活中所遭遇的冲突、歧视以及不满的能力,防止群体消极情绪的产生;其次,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利用内部沟通渠道合理引导员工发泄情绪,让冲突双方将所有矛盾以及不满通过合法的途径和有效的平台,转变为“善意”的对抗,企业管理者也可以通过内部协商、仲裁等多项外部控制措施及时化解潜在威胁,干预消极情绪的扩散。
(二)降低群体行为收益预期
严苛的人员招聘程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群体情绪管理水平,减少了因为个体因素而导致的反生产行为,但仅仅依靠自我约束显然难以最大程度消除反生产行为。因此,有必要利用外部控制加强对员工行为的监督,增加员工对参与群体行为的成本预期,降低员工对参与群体行为获利的估计。首先,企业可以通过细化工作说明书来明确各岗位员工的职责,并界定各种有害行为的性质、类型、严重程度及其奖惩标准。其次,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技术监控手段对员工行为予以监督,例如,视频监控、设立检查岗位等。最后,建立配套执行机制,用奖励强化组织所倡导的积极行为,通过惩罚增加员工参与群体反生产行为的成本。
对员工进行普法教育,提高员工对群体反生产行为危害的认识,增加个体对参与群体反生产行为的成本预期。企业可以加强相关法律知识培训,引导员工合理运用法律武器保护合法权益,用正当途径来表达不满和诉求,让员工了解群体反生产行为对社会、企业以及自身的危害,以提高员工对群体反生产行为成本预期。
(三)减小社会认同的负面影响
在群体反生产行为中,非正式组织的社会认同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降低社会认同的负面影响能有效防止群体反生产行为的形成。对此,企业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构建积极和谐的企业文化,宣传和引导员工学习组织文化、组织规范,间接影响员工内在价值观和思维模式,提升员工对组织的承诺,减小非正式组织社会认同对员工的影响;二是“改编非正式组织”,将企业中以同乡、同学等为纽带建立起来的非正式组织的意见领袖纳入到工会管理体系中,担当一些实质性的职务,真正让非正式组织在企业中拥有合法的代言人,传达群体利益诉求,逐渐将非正式组织正式化、规范化,提高社会认同的正面作用。
四、结束语
虽然群体反生产行为影响程度大、破坏力强,并且随着技术发展和组织变革还呈现出多样性和隐秘性等特征,但应对的思路也有很多。本文在SIMCA 的框架下从社会认同、工具理性和群体情绪三个因素出发,分析了针对个人、组织的群体反生产行为的形成。然而,不可置否,群体反生产行为形成的影响因素不止于此,对群体反生产行为的解构也不限于社会心理学视角。我们也坚信,随着实践发展和理论研究深入,将会有更好、更全面的解释理论出现。
1. 陈浩、薛婷、乐国安:《工具理性、社会认同与群体愤怒——集体行动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载《心理科学进展》,2012 年第1 期,第27–136 页。
2. 郭晓薇、严文华:《国外反生产行为研究述评》,载《心理科学》,2008 年第4 期,第936–939 页。
3. 刘善仕:《企业员工越轨行为的组织控制研究》,载《外国经济与管理》,2002 年第7 期,第19–23 页。
4. 刘文彬:《组织伦理气氛与员工越轨行为间关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年。
5. 刘文彬、井润田:《组织文化影响员工反生产行为的实证研究——基于组织伦理气氛的视角》,载《中国软科学》,2010 年第9 期,第118–129 页。
6. 刘玉新、张建卫、黄国华:《组织公正对反生产行为的影响机制——自我决定理论视角》,载《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1 年第8 期,第162–172 页。
7. 毛军权:《企业员工越轨行为及其组织控制的经济学分析》,载《管理现代化》,2003 年第4 期,第47–50 页。
8. 王石磊、彭正龙、高源:《中国式领导情境下的80 后员工越轨行为研究》,载《管理评论》,2013 年第8 期,第142–150 页。
9. 杨杰、凌文辁、方俐洛:《工作场所中越轨行为的定义,特性与分类体系解析》,载《心理科学进展》,2004 年第3 期,第472–479 页。
10. 张建卫、刘玉新:《反生产行为的理论述评》,载《学术研究》,2008年第12 期,第80–90 页。
11. 张建卫、刘玉新:《企业反生产行为:概念与结构解析》,载《心理科学进展》,2009 年第5 期,第1059–1066 页。
12. 张书维、王二平、周洁:《跨情境下集群行为的动因机制》,载《心理学报》,2012 年第4 期,第524–545 页。
13. 张永军、廖建桥、赵君:《国外组织公民行为与反生产行为关系研究述评》,载《外国经济与管理》,2010 年第5 期,第31–39 页。
14. Berry C M, Ones D S, Sackett P R. Interpersonal deviance, organizational deviance, and their common correlates: A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7, 92(2): 410–424.
15. Blau G. Influence of group lateness on individual lateness: A cross-level examina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5, 38(5): 1483–1496.
16. Case J. Employee theft: The profit killer. John Case & Associates, 2000.
17. Coffin B. Breaking the silence on white collar crime. Risk Management, 2003, 50(8):40–41.
18. Greenberg J. Employee theft as a reaction to underpayment inequity: The hidden cost of pay cut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90, 75(5): 561–568.
19. Johns G. Absenteeism estimates by employees and managers: Divergent perspectives and self-serving perception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94, 79(2): 229–239.
20. Kelloway E K, et al. 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 as protest.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 2010, 20(1): 18–25.
21. Klotz A C, Buckley M R.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 targeting the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Management History, 2013, 19(1): 114–132.
22. Klandermans B. How group identification helps to overcome the dilemma of collective action.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02, 45(5): 887–900.
23. Klandermans B. Mobi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Social-psychological expansions of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84, 49(5): 583–600.
24. Mangione T W, Quinn R P. Job satisfaction, counterproductive behavior, and drug use at work.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75, 60(1): 114–116.
25. Robinson S L, Bennett R J. A typology of deviant workplace behaviors: A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stud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5, 38(2): 555–572.
26. Simon B, Loewy M, Stürmer S, Weber U, Freytag P, Habig C, et al. Collective identific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8, 74(3): 646–658.
27. Van Zomeren M, Postmes T, Spears R. Toward an integrative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 a quantitative research synthesis of three socio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8, 134(4): 504–535.
28. Van Zomeren M, Spears R, Fischer A H, et al. Put your money where your mouth is! Explaining collective action tendencies through group-based anger and group efficac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4, 87(5): 649–664.
29. Yzerbyt V, Dumont M, Wigboldus D, Gordijn E. I feel for us: The impact of categoriz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on emotions and action tendenc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3, 42(4): 533–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