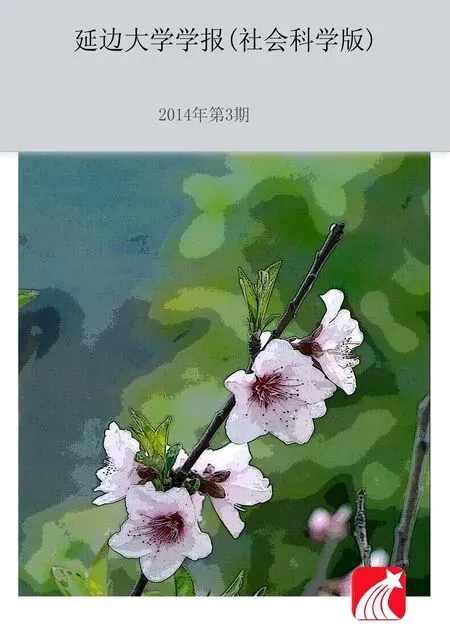鸭绿江、图们江国境问题研究动态
——以中韩两国学界为中心
2014-03-06金春善
金 春 善
(延边大学 民族历史研究所,吉林 延吉 133002)
中朝两国毗邻,自古以来关系密切。但是,两国间的疆域随着历代王朝的交替和国家的兴衰而频繁变迁。自明末清初开始,鸭绿江、图们江逐渐成为两国间相对稳定的国境。尽管如此,两国间的国境纷争依然存在。例如,1712年“长白山定界碑”的竖立,1885年的“乙酉勘界”,以及1887年的“丁亥勘界”等。直至1909年《中韩图们江界务条款》(又名《间岛协约》)缔结,中朝两国的国境纷争才暂时告一段落。但是,由于《间岛协约》缔结时朝鲜政府的外交权已被当时的日本所篡取,因此该条约的有效性始终存在争议,中朝两国间的国境问题由此也成为历史遗留问题。现今,鸭绿江、图们江问题依然是中韩两国学术界的重要研究课题,相关的研究成果颇丰。
本文通过分述历代中朝两国边界的变迁和“无人地带”的设置、“长白山定界碑”的竖立、“乙酉勘界”、“丁亥勘界”等,从宏观方面概述中韩两国学术界关于鸭绿江、图们江国境问题的研究动态。
一、历代中朝疆域的变迁和“无人地带”的设置问题
(一)历代中朝疆域的变迁
疆域是一个国家为完成其固有使命而有效行使其排他的管辖权的空间。[1]但在封建时代,历代王朝的疆域伴随着其军事力量的强弱而不断变迁。历史上的中朝疆域也不例外。到了明末清初,鸭绿江、图们江成为中朝两国事实上的疆界。尽管如此,由于中韩学界在高句丽和渤海问题上分歧严重,导致两国学者在历代中朝疆域变迁这一问题上也是矛盾重重。
从中国学界①来看,杨昭全、孙玉梅的《中朝边界史》一书中写到,公元前1027年周武王统治时期,商朝的贵族箕子带领族人向东迁徙,以王险城(平壤)为中心建立了箕子朝鲜,燕国建立后以浿水(清川江)为两国疆界。西汉时期,汉武帝征服卫氏朝鲜,设置了汉4郡,其南端邻接辰韩、马韩、弁韩。东晋时,中国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高句丽南起牙山湾,东部经由乌岭、竹岭抵达平海,与百济、新罗接壤。618年,高句丽的南部疆域进一步拓展,其西北达汉江以北,东北至歃原、端川一带。668年,高句丽被唐朝所灭。735年,唐朝将浿江以南的区域赐予新罗,浿江开始成为唐朝和新罗的疆界。其后,新罗、高丽持续推进北拓政策。到了辽、金时期,高丽的北部疆域越过清川江抵达鸭绿江流域。元朝统治者曾致力于恢复朝鲜半岛内的领土,并将大同江流域划归其管辖之下,但到了元末明初,高丽乘中国新旧王朝政权交替之机大肆扩张领土,将其西北部领土拓至鸭绿江南岸。朝鲜王朝建立后,继续积极向北拓展领土,在图们江南岸先后设置庆源、钟城、会宁、庆兴、稳城、富宁6镇,将其北境拓至图们江南岸。[2]
从韩国学界来看,俞政甲在《北方领土论》中认为,古朝鲜的疆域西至现今中国北京附近的滦河,东北达黑龙江以北地区,囊括现今中国河北省东北部一带、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和朝鲜半岛全部。高句丽全盛时期的疆域北至黑龙江,西达内蒙古,东至沿海州,南接牙山湾、迎日湾。渤海的版图最大时,东至沿海州,西达辽东半岛,南接大同江至安边一线,北部沿松花江顺流直下至黑龙江。高丽时期,徐熙在江东6州筑城,尹瓘在女真部落一带修筑9个城,李成桂率兵占领了于罗山城(奉天)。高丽在恭愍王时期疆域最大,抵达辽阳、沈阳一带。朝鲜王朝时期,自世宗16年至世宗22年(1434-1440)在图们江沿岸设置了6镇,自世宗15年至世宗19年(1433-1437)在鸭绿江沿岸设置了4郡,基本上奠定了现今的国境基础。俞政甲还主张“‘雷孝思线’国境说”,②认为混江(佟佳江)西侧的大小鼓河水源至鸭绿江、凤凰城的地带以南为朝鲜半岛。[1]
(二)“无人地带”的设置和“雷孝思线”问题
一般来说,中朝国境问题源于“长白山定界碑”的碑文“东为土门”。因此,现今中韩学界的争论主要是围绕“间岛领有权”问题而展开的,即“图们江国境说”和“土门江国境说”。但除此之外,鸭绿江北岸的“无人地带”近年来也开始成为中朝国境问题的议题。这里所说的“无人地带”,是指清朝在17世纪中叶对东北实行封禁时设立的边墙(或边栅)同鸭绿江之间的空旷地带。这一时期设立的边墙主要有盛京边墙(又名老边)和柳条边墙(又名新边)。当时,清朝将边门以东、以南地区称为“边外”。以此为界,长白山以北地区悉行封禁,严禁民人出入。结果,鸭绿江和图们江北岸广阔地区逐渐形成“无人地带”,并最终成为清朝和朝鲜之间的军事缓冲地带。
在韩国学界,申基硕的《间岛领有权研究》、俞政甲的《北方领土论》、金得榥的《白头山和北方疆界》、梁泰镇的《韩国边境史研究》、金炅春的《鸭绿江、豆满江国境问题研究》、卢启铉的《间岛是谁的土地?》、任桂淳的《白头山定界碑和朝清间的乙酉、丁亥国境会谈》、李日杰的《“间岛协约”和间岛领域权问题》等学术成果都将“雷孝思线”视为清朝和朝鲜的国境,其主要依据如下:
第一,杜赫德的《中国志》中用以标注“无人地带”的点线即是清朝和朝鲜间的国境线。③
第二,Pere Regis在《朝鲜王朝地图》中虽然没有标注“无人地带”属于朝鲜,但从杜赫德的《鞑靼中华全图》中的插画《朝鲜王朝地图》及其“PING-NGAN”的文字标注等来看,“无人地带”为朝鲜领土。
第三,据《朝鲜王朝实录》、《通文馆志》、《同文汇考》记载,朝鲜政府曾数次抗议,要求清政府驱离“无人地带”的所有清人,而清政府也采取严厉措施,严禁流民进入“无人地带”。
总之,韩国学者根据“雷孝思线”,认为长白山以东、图们江以北的约6 000平方公里和长白山以西、鸭绿江以北的约19 020平方公里的广阔地区是朝鲜的领土。
金得榥对当时清朝设置“无人地带”的原因归纳如下:1.当时,明朝的残余势力毛文龙与朝鲜进行联合,威胁清朝统治的后方,因此清朝需要军事上的缓冲地带;2.清朝为保护长白山及其周边的“三宝”。[3]此外,部分韩国学者主张,清朝与朝鲜本无国境,“江都会盟”中双方才设定了彼此间的国境。为使朝鲜不在清朝的后方进行敌对活动,清朝将“雷孝思线”以南的地区划归朝鲜。[3]
如上所述,韩国学界一般将“雷孝思线”视为清朝与朝鲜间的国境,但对“无人地带”究竟是在“雷孝思线”以南还是以北的问题上众说纷纭。
从中国学界来看,学者们仅从清朝封禁政策的层面研究“无人地带”,④而关于“雷孝思线”的专题研究几乎未涉及,即仅将柳条边墙和鸭绿江之间的“无人地带”看做是清朝推行封禁政策的一环,与清朝、朝鲜间的国境问题没有任何联系。此外,在“无人地带”的性质和作用方面,与韩国学者持不同的观点:
第一,“无人地带”只是清朝封禁区内的一部分。[4]根据封禁区域的范围和内容,中国学界将其分为大圈、中圈、小圈三类。其中,大圈包括“盛京以东,伊通州以南,图们江以北”,即整个东北地区;中圈指柳条边墙外(东边道)的地区;小圈则是封禁区域内设置的各种围场。“雷孝思线”以南,即“无人地带”的鸭绿江以北、图们江以北的地区全部被划为围场,是清朝的封禁区域的中心地。其中,鸭绿江以北当时被称为“东边外”,是专产皇室贡品的围场,出于国防上的需要,这一地区的封禁与其他地区相比甚严。此外,图们江以北地区更被视为清朝的发祥地,严禁民人出入。[5]由此可知,中国学者认为“无人地带”不是清朝和朝鲜商议设定的,而是清朝出于推行封禁政策和建立两国间军事缓冲地带的需要而形成的,而且“无人地带”的长期存在在于清朝的封禁政策。[6]
第二,清朝不在鸭绿江北岸建立军事设施或设置官署,而是将其变为“无人地带”,其原因在于丁卯、丙子之役之后清朝对其军事力量的自信,以及朝鲜国力的逐步衰弱。清朝认为八旗军机动性强,而且朝鲜每年都会向自己供奉大量财物,朝鲜国力势必逐渐弱化,因此在鸭绿江北岸未设任何军事或民事机构。⑤
第三,“无人地带”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与清朝对朝鲜的“字小之恩”和朝鲜政府推行的“瓯脱”政策关系密切。[7]乾隆年间,为阻止朝鲜人“犯越”满洲,清朝兵部和盛京将军数次奏请强化边疆守卫,建议在鸭绿江北岸建立军事设施。但是,乾隆皇帝始终以对朝鲜“字小之恩”未予允准。结果,1869年,朝鲜政府向清朝呈送咨文,内有“乞贵部不斳捶劳,使敝邦江外之地,栅路去处,奉今下饬旨,毋敢更肆违越,实为幸甚”之语,主张鸭绿江北岸是朝鲜的领土。对此,张杰在其《清代鸭绿江流域的封禁与开发》一文中,认为虽然清朝在鸭绿江北岸设置了“无人地带”,但始终享有对这一区域的开发和管辖权。例如,1686年,清政府以“展荒”的名义“移凤城边门于山南,拓地15里”,即开拓柳条边外鸭绿江北岸的荒地。[6]1731年和1746年,奉天将军为阻止朝鲜边民“犯越”奏请在莽牛哨(今辽宁省宽甸县古楼乡)设置哨所,巡查边境。1869年,都兴阿上疏称,“叆江西岸一带,南北四百余里,与朝鲜仅一江之隔”。[6]
如上所述,中国学者认为,一般相邻两国都会在彼此接境地带设置行政机构、驻屯军队,但清朝与朝鲜却没有这样做,这一方面是因为清朝的封禁政策,另一方面则在于朝鲜的禁越政策和“瓯脱”政策。
二、“长白山定界碑”的竖立和乙酉、丁亥勘界
(一)“长白山定界碑”的竖立
关于“长白山定界碑”的竖立,中韩学界争论的焦点首先在于“长白山定界碑”的性质。1711年,以朝鲜人“犯越”并杀害清人的“李万枝事件”为契机,康熙帝派遣部员和乌拉总管穆克登前往凤凰城进行处理,并令其勘查中朝边界。但是,穆克登一行并未得到朝鲜方面的帮助,第1次查边失败。1712年,穆克登再次奉旨查边,在长白山竖立了定界碑,其碑文如下,“乌拉总管穆克登,奉旨査边。至此审视,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
现在,中韩学界关于“长白山定界碑”的性质看法不一:一是认为“长白山定界碑”具有“定界”的性质,二是认为“长白山定界碑”是单纯的“穆克登碑”或“纪念碑”。从韩国学界来看,申基硕承认“长白山定界碑”,认为碑文具有构成条约的要素。[8]刘凤荣认为,国际间的条约一定要遵守,1712年穆克登奉康熙帝的命令在长白山竖立的定界碑即是一种条约,因此理应遵守。[9]与此相反,梁泰镇对“定界碑”的名称提出异议,认为“定界碑”缺乏民族主体性,应改称为“长白山石碑”。[10]其理由是,康熙帝强制性地将鸭绿江和图们江以北的地区划归清朝,以及定界碑竖立时穆克登强迫朝鲜代表朴权等的事实,说明“长白山定界碑”在国际法上是无效的。此外,卢泳暾、金炅春也否认“长白山定界碑”的法律效力,认为中朝应以鸭绿江下游的凤凰城至沈阳、辽阳一线为界,[11]“间岛”、“西间岛”地区被中国单方面占领,指出中韩建交前一定要提出并解决这些问题。[12]事实上,韩国大部分学者认为“长白山定界碑”是清朝单方面强制竖立的,缺乏民族的主体性,否认据此将“西间岛”地区划归清朝的史实,否认“长白山定界碑”具有“定界”的性质,主张将其改称为“石碑”。但是,朴容玉认为“长白山定界碑”竖立时根本不存在韩国部分学者所主张的穆克登威胁朝鲜代表的现象。[13]
从中国学界来看,有些学者主张穆克登勘界立碑实质就是中朝定界。宋教仁在1908年出版的《间岛问题》一书中,认为穆克登与朝鲜方面的往复文书具有近代边界条约的性质。台湾的张存武、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的杨昭全等学者认为“长白山定界碑”具有“定界”的性质,这一主张获得了诸多中国学者的赞同。张存武在《清代中韩边务探源》一文中认为,“丁亥勘界”时清朝代表秦煐引用礼部致朝鲜咨文,“此去特为查我边境,与彼国无涉”,否认穆克登之行的目的是定界。然而,尽管缺乏相关史料,⑥但穆克登之行的目的确为定界无疑,其理由是康熙帝命令穆克登务将“边界”查明来奏。在这里,“査明边界”实即“会勘边界”。此外,当时清朝礼部向朝鲜方面指出“会同査勘,分立边界”,定界后朝鲜政府向清朝谢恩,“严两地之禁防,指水位限;表一山之南北,立石以镌……用作永图”。由此可知,“穆碑”确为“定界碑”无疑。[14]杨昭全在《中朝边界史》一书中认为,在清朝、朝鲜两国国界不明的情况下,康熙帝单方面派遣穆克登踏查国界的做法是不妥当的,但双方都派遣代表踏查彼此间的边界,这实际上是在“划界”或“定界”,因此应将“穆克登审视碑”视为“定界碑”,但清朝也因此丧失了长白山一半的主权。[15]另外,刁书仁的《穆克登查边定界考辨》认为,穆克登查边定界的根源在于中朝边民的私自越境以及由此频频引发的外交纠纷。倪屹的《穆克登碑性质辨析》认为,穆克登所立石碑履行了定界的有关程序,获得了当时中朝双方的承认,属于宗藩定界碑。此外,金春善的《延边地区朝鲜族社会的形成研究》、李花子的《康熙年间中朝查界交涉与长白山定界》、倪屹的《“间岛问题”研究》等著作、论文也主张穆克登查边时所立石碑为“定界碑”。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学界关于穆克登的评价问题。学界认为,因定界碑问题而丧失领土的主要责任在于康熙,但是肩负查边定界重任的穆克登也不能推卸责任。
与此同时,有些学者主张自乙酉、丁亥勘界开始被视为“定界碑”的“长白山定界碑”应更名为“穆克登审视碑”。吴禄贞在1908年出刊的《延吉边务报告》中指出,“长白山定界碑”不是“定界碑”,其理由如下:1.穆克登领受的康熙帝的旨意是“查边”而非“定界”;2.朝鲜政府派出的代表均没有勘界的权限;3.从两国代表的相互关系来看,双方并不是共同勘定边界;4.碑文中的“审视”不具有“划界”或“定界”之义;5.虽然朝鲜接伴使朴权在复文中写到“大人查明交界,分水岭上立碑为标”,但是这只是客套话而已。[16]这一主张对中国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截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部分学者将“长白山定界碑”称为“穆碑”,现在的王崇时、徐德源等学者仍然持此观点。王崇时在《19世纪前中朝东段边界的变迁》一文中认为,穆克登勘界并不是清朝与朝鲜间的正式勘界,只是清朝单方面的边境视察,“穆碑”不具有定界的性质。[17]徐德源在《穆克登碑的性质及其设立地点与位移述考》一文中认为,“穆碑”不是清朝一方所立或是由清朝、朝鲜双方共立的“定界碑”,而是清朝钦差审视鸭绿江、图们江水源的标志物和证明到达奉旨查边的关键地点、完成查边任务的纪念碑。徐德源还提出了“长白山定界碑”竖立时缺乏双方官员进行划界谈判的记录,以及“长白山定界碑”的上部仅刻有“大清”二字,落款所刻“朝鲜”二字并非与“大清”二字并列,表示两国并未有共同立碑之意等诸多观点。[18]
此外,陈慧在《穆克登碑问题研究》一书中,一方面承认“穆碑”在客观上起到了定界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认为“穆碑”本为“审视”而立,称之为定界碑有所不妥。[19]
(二)土门江、豆满江和“间岛领有权”问题
迄今为止,围绕着“长白山定界碑”,中朝间的国境纷争涉及许多具体的问题,但其核心问题可归结为“长白山定界碑”碑文中的“东为土门”的释义问题,即碑文中的“土门”究竟指的是哪条江?土门江和豆满江(图们江)是两条不同的江还是同一条江?这不仅是“乙酉勘界”时清朝、朝鲜两国代表争论最激烈的问题,而且也是现今中韩两国学界持不同见解的主要原因。
1881年,清朝在“北间岛”地区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积极劝诱老百姓前往开拓。这一时期,以1880年的“庚辰开拓”为契机,朝鲜北部边民大量移居“北间岛”地区。1882年,吉林将军要求朝鲜方面召回“北间岛”地区的朝鲜移民,朝鲜方面对此表示同意。但是,1883年,在敦化县知事向朝鲜钟城、会宁两邑发去关于刷还图们江以北朝鲜移民的公函后,朝鲜西北经略使鱼允中和地方官员要求重勘“长白山定界碑”,并主张土门江和豆满江(图们江)是两条不同的江,土门江以南地区为朝鲜领土。据此,朝鲜高宗向清朝发去公文,要求重新踏查两国国境,以明确双方疆界。于是,1885年和1887年,清朝和朝鲜先后进行了“乙酉勘界”、“丁亥勘界”。
土门江、豆满江“两江说”最初是由朝鲜钟城、稳城、会宁、茂山等地的边民所提出的。“乙酉勘界”时,朝鲜方面的代表李重夏据此主张“土门江国境说”。
在韩国学界,金鲁奎的《北舆要选》、洪世泰的《白头山记》、洪良浩的《北塞纪略》被誉为研究朝鲜北方领土问题的最珍贵史料。[20]现今韩国学者关于北方领土问题的学术成果大多以此为基础,主张土门江、豆满江“两江说”,其特点概括如下:1.土门江和豆满江是两条不同的江;2.定界碑碑文中的“土门”不是豆满江(图们江),而是土门江;3.即使土门江为豆满江,土门江的上游不是红丹水或石乙水,而是红土水。[21]
20世纪90年代中期,韩国部分学者坚持“土门江国境说”,但其论据却有所发展。朴容玉根据《朝鲜王朝实录》,认为当时的朝鲜政府把图们江称为“土门”和“豆满”,朝鲜官员朴权也把“土门”认为“豆满”,在立碑当时曾经就立碑位置的准确性向穆克登提出了疑问。刘凤荣认为穆克登定界的土门江是指松花江上流,其依据主要是1885年中朝勘界时,双方官员发现穆克登碑立于长白山天池南麓十余里处,碑东连接的石、土堆恰恰是松花江支流黄花松沟子。姜锡和认为,在立定界碑当时,中朝两国都把“土门江”和“豆满江”混为一谈,勘界时李重夏已经认识“土门江”和“豆满江”并不是一条江,主张中朝分界线并不是土门江——松花江——黑龙江,上游为土门江、下游为海兰江以南地区,即豆满江和海兰江之间为朝鲜领土。[22]
与此同时,韩国个别学者认为1712年穆克登最初认定的土门江是图们江。裴佑晟在《朝鲜后期国土观与天下观的变化》一书中,认为定界时土门江与图们江本属同一条江,定界后朝鲜政府以土门江为松花江上流,以流入图们江(豆满江)的海兰河作为分界江等主张是朝鲜王朝后期被夸大的领土意识所致。
在中国学界,吴禄贞在《延吉边务报告》一书中,从历史上的证据,敕命上的证据,碑文上的证据,女真语和汉语上的证据,音韵学上的证据,中国人、朝鲜人俗称上的证据,朝鲜议政府公文书上的证据,日本方面的证据等8个部分论证了图们、土门、豆满实为一江。其后,中国学者大都以此为基础进行研究。
杨昭全根据历史文献对土门江、豆满江(图们江)进行了详细考证。图们江,《辽史》中作“陀门”,《金史》中作“统门”,元朝时称“爱也窟河”,明朝时上游称“啊也苦”,而下游称“徒门”,清朝时称“土门”,《圣武记》中作“图们”,《水道提纲》中作“土门色禽”。“图们”,满语作“万”之意;“色禽”,满语之意为“河流”。历史上,陀、统、陀门、统门、图们、徒门均指一江,韩国称之为豆满江。[15]此外,仔细分析1882年朝鲜高宗向清朝礼部送去的咨文,不难发现:1.朝鲜政府承认土门江(豆满江、图们江)为中朝界河;2.朝鲜政府承认朝鲜边民开垦、移居图们江以北地区的行为是非法的;3.朝鲜政府要求清政府刷还图们江以北的朝鲜移民;4.朝鲜政府表示严厉禁止本国边民非法越境。由此可知,当时朝鲜政府事实上承认图们江(土门江)是彼此间的国境。[15]
张存武认为,豆满江在清朝时称之为“土门江”,满语也称“土门乌拉”。朝鲜称之为“豆满江”,西洋宣教师称之为“Toumen River”。虽为同音异字,但实际指的是同一条江。《康熙皇城全览图》中的朝鲜部分是穆克登与何国柱根据从朝鲜获得的地图所制,因此长白山山脉的很多部分与实际有所不同,而这使得康熙帝以后中国地图的相当一部分与实际出入较大。[14]徐德源根据《肃宗实录》的记载,认为当时朝鲜政府深知土门江、豆满江实为一江,因此在其实际控制的甲山一带设有镇堡把守,得出了朝鲜的东北边界是长白山地区以南而非长白山地区南半部的结论。[23]张存武也主张,朴权在被任命为接伴使之后,根据当地百姓所说的“两江连陆之处,道里遥远……即无地名标识,又无文字可据,且闻土人辈皆以白头山下空旷之处认为彼地云”的事实,认为自朴下川开始包括图们江所有水系在内的惠山以北的长白山地区全部是清朝的领土。[14]陈慧的《李重夏与“土门、图们两江说”》、《穆克登碑文中的“土门”即今图们江》,对徐德源的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和补充。此外,于逢春的《图们、土门与豆满、豆漫之词源与译音考》从语言学方面对此进行了详细辨析。
此外,中国学者还对“土门、豆满两江说”的来源进行了研究。张存武的《穆克登勘定的中韩国界》认为是穆克登错定松花江支源为图们江初源所致。徐德源的《土门、豆满两江说驳考》则认为“两江说”是随同穆克登勘界并筑设图们江源界标的许梁、朴道常以讹传讹所致。孙春日的《中国朝鲜族移民史》认为,它是18世纪以来朝鲜实学派掀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在中朝国界问题上的反映。李花子的《18、19世纪朝鲜的“土门江”、“分界江”认识》从18世纪之后朝鲜实学派的主张分析了“两江说”产生的思想根源。
中国学者所主张的土门江、豆满江“一江说”在清朝、朝鲜间所签订的各种条约中也可找到切实的证据。1882年,清朝和朝鲜签订了《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其中第5条规定:“兹定于鸭绿江对岸栅门与义州二处,又图们江对岸珲春与会宁二处,听边民随时往来贸易”。这说明清朝和朝鲜再次重申鸭绿江、图们江为彼此的国界。[15]1883年6月,双方签订了《吉林朝鲜商民贸易章程》(《会宁通商章程》),其中第1条规定:“两国边地,以土门江为界”,第5条规定:“吉林既于土门江边之和龙峪、西步江两处,设立税局、分局”,第11条规定:“吉林与朝鲜,以图们江为界”。据此,杨昭全认为当时两国已经将图们江(豆满江、土门江)作为事实上的国界,[15]而朝鲜王朝将土门江、豆满江看做两条不同的江,或将海兰江看做是土门江的各种主张,只不过是朝鲜王朝借韩民业已定居“北间岛”地区的事实,妄图实现其领土扩张的野心罢了。[15]
在关于土门江、豆满江“一江说”的所有证据中,中国学者认为最有力的证据是李重夏的《乙酉状启别单》。1885年,李重夏在“乙酉勘界”结束后向朝鲜高宗王上奏《乙酉状启》,阐明了土门江、豆满江“两江说”。不久,李重夏再次上奏《乙酉状启别单》,指出了“乙酉勘界”时朝鲜方面的主张和存在的问题。
“松花江与豆满江下流相距为千余里,宁古塔、吉林等地皆在其内,则有难的持某地是白遣……金宗瑞驱逐野人,开拓六镇,始以豆满江为界,详在《国朝宝鑑》金宗瑞上疏中是白遣……康熙壬辰定界,誊录中是白乎。所其时往来之路,论难之语,专以豆满江为限是白遣。备边司有关文曰,土门江华音即豆满江……豆(满)江为界又分明是白齐……我国同日之争执即未审旧迹之致……此事本经界使臣鱼允中之北行也,听一二居民之言,送人塌来碑文后,更不详考文献,周察形便,遽谓豆满江北是我地。”
据此,中国学者认为,“乙酉勘界”时李重夏明知土门江、豆满江为一江,但因惧怕朝鲜政府降罪,于是坚持土门江、豆满江“两江说”,并将此责任推给鱼允中。[15]
据杨昭全、孙玉梅的《中朝边界史》,袁世凯在致李鸿章的报告中写到:元山监理承认以松花江、海兰江为界是错误的,但不得不按照朝廷的旨意行事。金允植也承认土门江、豆满江、图们江是同一条江的不同转音,土门江上流的几个水源中,如果以西豆水为界,朝鲜茂山的一半将划属清朝;如果以红丹水为界,茂山的长坡等地将划属清朝。但是,红土山水在茂山附近汇入红丹水,进而流入图们江,如果以红土山水为界,图们江以南将划归朝鲜茂山,以北则划归清朝,对双方都有所便宜。此外,对于越境定居的朝鲜移民,袁世凯提出了“借地安置”的政策,并主张安排专员管理。[15]
综上所述,中国学者通过分析研究朝鲜王朝时期的资料,批驳了朝鲜王朝时期朝鲜政府的主张和现今韩国学者的有关见解,主张“间岛领有权”纷争的产生原因是朝鲜政府在无力刷还“北间岛”越垦韩民的情况下捏造的土门江、豆满江“两江说”。
在“间岛领有权”纷争中,土门江(豆满江)上流地区筑设的石堆、土堆、木栅等也是两国学者所关注的焦点。这是因为自“穆碑”至茂山以西两国边界不明的地方筑设了石堆、土堆、木栅等边界标识物,它们并非与图们江上流的红丹水相连,而是接于松花江上流的“土门”(中国称黄花松沟子)。对此,韩国学界认为,连接“穆碑”和松花江上流的边界标识物是当时朝鲜政府认真按照穆克登的指示筑设的,没有任何的可怀疑性。[24]
与此相反,中国学者对石堆、土堆、木栅等边界标识物的筑设经纬和真实与否提出了诸多见解。王崇时在《19世纪前中朝东段边界的变迁》一文中,指出当时穆克登踏查的土门江的源流并不是朝鲜方面所坚持的土门江上游,而是图们江(豆满江)的上游红丹水,这从朝鲜接伴使朴权向其政府的报告中也可得到印证,“临江台近处有一水,来会于大红丹水,明是白山东流之水,此乃真豆江,而钦差所得水源,乃是大红丹水上流也”。此外,当时洪致中在上疏中所谓的穆克登错把向北流入中国境内的一条河指为图们江源的报告反而是错误的,穆克登确认红丹水是豆满江的上流,只是错将“豆满江”写成了“土门江”。[17]相反,李花子的《康熙年间穆克登立碑位置再探》参照朝鲜文献和奎章阁地图,认为穆克登认定的图们江源次派应为红土山水。倪屹的《穆克登原址考证》指出,穆克登勘定的图们江源不是红丹水,而是松花江支源黄花松沟子。徐德源在《长白山东南地区石堆、土堆筑设的真相》一文中,认为现在部分学者只知道与中朝边界争议有关的石堆、土堆在长白山东麓的黄花松沟子一线,但不知道长白山南部地方另有一处筑设的石堆、土堆。为论证这一史实,首先,徐德源分析了《同文汇考》原编卷48疆界篇(《敕使问议立栅便否咨》、《设栅便宜呈文》)、《肃宗实录》三十八年六月三日条等史料,指出穆克登提出的设栅地区是“于茂山、惠山相近此无水之地”,这与康熙帝上谕中的“鸭绿江、土门江二江之间的地方知之不明”相互吻合。同时,根据《肃宗实录》三十八年六月三日条的记载,认为穆克登所认为的土门江上流是红丹水。[25]其次,徐德源论述了石堆、土堆、木栅等的设置过程及其真伪。据《肃宗实录》三十八年十二月七日条记载:穆克登离开后,朝鲜方面随即由李善溥、洪致中在国境不明的地区设置石堆、土堆、木栅等,但工程还未进展到大红丹水水源地便停工了。另据《乙酉状启别单》⑦记载:李重夏在与清朝勘界官员的会勘过程中,发现了隐没于丛林中的石堆、土堆、木栅等,但并未将其告知清朝的勘界官员。由此可知,这些石堆、土堆、木栅等确实是按照穆克登的指示筑设在“定界碑”至大红丹水之间。此外,两国勘界官员在勘界时踏查的木栅并非最初按照穆克登的指示所修筑的木栅,而是许梁、朴道常在没有得到政府允许的情况下擅自改筑的。对此,当时朝鲜政府将许梁、朴道常拘拿,交备边司审问。⑧徐德源认为,两国官员在勘界时所确认的木栅是伪造的,真正的木栅不在长白山东麓,而在长白山南部。但是,朝鲜政府为将土门以南、图们江以北的地区划归朝鲜,有意隐瞒了真正的边界标识物。⑨此外,刁书仁的《康熙年间穆克登查边定界考辨》、马孟龙的《穆克登查边与皇舆全览图编绘》、陈慧的《清代穆克登碑初立位置及图们江正源考论》都坚持这种观点。
中国学界在论述“间岛领有权”问题时,一般将焦点集中在“丁亥勘界”,这是因为此次勘界时清朝、朝鲜两国的见解相当接近。关于“丁亥勘界”的成果,中国学界认为有三:1.确定土门江、豆满江、图们江为一江;2.确定茂山以下至入海口以图们江为界;3.商定逐步踏查茂山以西至石乙水和红土山水合流处。此外,“丁亥勘界”之所以未能彻底解决图们江源流问题,全在于朝鲜政府“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立场和态度。[15]对此,张存武认为,“丁亥勘界”时,清朝主张在红丹水和鸭绿江源健川沟间东西横截划界,致使谈判未能继续开展。当时,朝鲜并不反对以石乙水和圆池水为界,而是反对清朝自石乙水至鸭绿江源横截划界。换言之,如果清朝所设界线系自石乙水经“穆碑”至鸭绿江源,朝鲜反倒不一定反对。[14]但是,张存武认为,当时无论所定界水为红土水、红丹水还是渔润江,清朝在此次定界中损失甚大。⑩
(三)“十字碑”问题
迄今为止,韩国学界关于“十字碑”(华、夏、金、汤、固、河、山、带、砺、长)问题的研究鲜有涉及。笔者认为,这与韩国大部分学者对“丁亥勘界”持否定性态度有关。韩国著名国境问题专家梁泰镇在《韩国国境史研究》中指出,“国界问题应得到当事国的认可后方能产生效力,但是‘丁亥勘界’并未得到当时朝鲜政府的承认”。[26]与此相反,中国学者对“十字碑”的设置过程及具体位置都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其代表成果是杨昭全、孙玉梅的《中朝边界史》。该书指出“十字碑”并非穆克登查边后所立,而是清政府在1887年“丁亥勘界”之后在长白山定界碑和朴河之间竖立的。此外,该书对“十字碑”的具体位置也进行了考证,“华”字碑在小白山顶,“夏”字碑在小白山东麓沟口,“金”字碑在黄花松甸子接沟处,“汤”字碑在黄花松甸子尽头的水沟处,“固”字碑在石乙水水源地,“河”字碑在石乙水、红土水合流处,“山”字碑在长坡浮桥南岸,“带”字碑在石乙水、红丹水合流处,“砺”字碑在三江口之图们江、西豆水合流处,“长”字碑在图们江、朴河合流处。关于“十字碑”竖立的时间,该书认为由于史料匮乏,因此无法进行准确的考证,但可确定为1888年至1889年间。[15]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中韩学界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争论大体上主要有四点:
第一,“无人地带”(空旷地带)的设置和“雷孝思线”问题。
韩国学界认为杜赫德在《中国志》中用点线标注的部分即为国境线。杜赫德的《鞑靼中华地图》中的插图《朝鲜王朝地图》下的文字标注“PING-NGAN”,以及《朝鲜王朝实录》、《通文馆志》、《同文汇考》等文献中的相关记载,都说明“无人地带”属朝鲜的管辖范围。此外,“无人地带”是清朝与朝鲜在签订“江都会盟”时,清朝以朝鲜不在清朝统治的后方进行敌对活动为条件,将“雷孝思线”以南的地区划属朝鲜,并以此作为两国间的军事缓冲地带。
与此相反,中国学界认为“无人地带”不是清朝与朝鲜商定的,而是出于清朝实行封禁政策以及建立军事缓冲地带的需要而形成的。此外,“无人地带”的长期存在是因为清朝对朝鲜的“字小之恩”和朝鲜政府积极推行的“瓯脱政策”。
第二,“长白山定界碑”的竖立问题。
从韩国学界来看,申基硕、刘凤荣等认为“白头山定界碑”具备条约的构成要素,具有法律效力。与此相反,梁泰镇、卢泳暾、金炅春等认为“白头山定界碑”是清朝单方面竖立的,缺乏民族的主体性,由此“西间岛”地区也划归清朝,因而否定“白头山定界碑”具有定界的性质。
从中国学界来看,吴禄贞认为“长白山定界碑”不是“定界碑”,而应称为“穆克登审视碑”。王崇时、徐德源等认为穆克登勘界不是清朝与朝鲜共同开展的,而是清朝单方面的边境视察,因而“长白山定界碑”不是“定界碑”,而是清朝钦差审视鸭绿江、图们江水源的标志物和证明到达奉旨查边的关键地点、完成查边任务的纪念碑。与此相反,张存武、杨昭全、李花子、倪屹等认为康熙帝上谕中的“査明边界”实即“会勘边界”之意。此外,当时清朝礼部向朝鲜方面指出“会同查勘,分立边界”,这说明“长白山定界碑”具有定界的性质。尽管中国学界关于“长白山定界碑”的性质存在一定的见解差异,但都认为“长白山定界碑”的竖立使得中国丧失了长白山一半的主权。
第三,土门江、豆满江和“间岛领有权”问题。
韩国学界一般主张土门江、豆满江“两江说”。从相关的研究成果来看:1.坚持土门江、豆满江是两条不同的江;2.认为“长白山定界碑”碑文中的“土门”不是豆满江(图们江),而是土门江;3.认定土门江即是豆满江,土门江上流不是红丹水、石乙水,而是红土水。在这些观点下,韩国学者认为自土门江至松花江、黑龙江以南的地区应该是韩国的领土。此外,对于“丁亥勘界”中所取得的成果,韩国学者认为这是宗主国清朝压迫藩属国朝鲜的结果,因而对“丁亥勘界”的成果持否定态度。
中国学界主张土门江、图们江(豆满江)“一江说”。其根据首先是历史文献中的相关记载,“陀门”、“统门”、“图们”、“徒门”都是不同历史时期对土门江、图们江、豆满江的不同称呼。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豆满江,清朝称之为土门江,满语称土门乌拉;朝鲜称豆满江,西洋宣教师称“Toumen River”,这些称谓都是同音异字,实际是指同一条江。此外,从1882年的《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1883年6月的《吉林朝鲜商民贸易章程》中的相关规定来看,两国实际上将图们江(豆满江、土门江)作为彼此间的国界。当时,朝鲜政府根据钟城府使、会宁府使的上书,或将土门江、豆满江看做两条不同的江,或将海兰江看做是土门江,中国学者认为这不过是朝鲜政府借韩民业已定居“北间岛”地区的实际,妄图实现其领土扩张的野心罢了。此外,与土门江相连的石堆、土堆、木栅等边界标识物是朝鲜地方官员伪造的,真正的木栅位于长白山南部,而非长白山东麓。
第四,“十字碑”问题。
韩国学界关于“十字碑”问题鲜有论及。与此相反,中国学界将“十字碑”看做是“长白山定界碑”至图们江江源两国国境不明地方的重要边界标识物,将“十字碑”的竖立看做“丁亥勘界”的重要成果,对“十字碑”的竖立经纬及其具体位置都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注释:
①谭其骧的《关于历史上中国边界和边疆的若干见解》认为,中国的边界(疆域)不仅仅指中原王朝的边界,边疆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的边界也包含其中。谭其骧的《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的疆域》认为,中国的版图应该是清朝统一中国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前的国土范围,即18世纪5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这一时期的国土范围。
②雷孝思线是指法国地理学家唐维尔在其《新中国地图》中标注清朝与朝鲜间“无人地带”的点线。金得榥在《白头山和北方疆界》中指出,当时奉康熙帝之命前往满洲测量之时,由于雷孝思神父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将这些点线称之为“雷孝思线”。
③杜赫德在满洲与朝鲜北部的地图上,把满洲与朝鲜地图上的黑山岭—宝髱山—头道沟—十二道沟的诸水与松花江西大源的诸水形成的分水岭——长白山,以及长白山支脉混江(佟佳江)西侧的大小鼓河水源至鸭绿江、凤凰城的地带连接起来,并对此作了如下说明:“朝鲜的西部边境位于凤凰城的东边。此时,清朝已经征服朝鲜,讨论在长栅与朝鲜边界之间设立无人地带。地图上划出的地区就是无人地带”([日]篠田治策的《长白山定界碑》,乐浪书院,1938年,第22-25页)。
④当时,当地人称“无人地带”为“苏勒荒”,满族语为“空闲”之意。
⑤见张存武的《清韩陆防政策及其实施》(载《中朝边界研究文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1998年,第633页)。此外,张存武认为当时柳条边墙实际上成为中国的“边”,1637年在三田渡和约中清朝强迫朝鲜“新旧城垣不许缮筑”,修缮南汉山城时朝鲜向清朝假报“为防止日本的侵略”,才得以批准。从上可以分析,清朝认为没有必要在“无人地带”设置军事设施。
⑥当时,清朝总署为了把图们江地区的中朝国境问题引为鉴戒,翻阅了《皇朝三通》、《会典事例》等资料,但是并未找到相关线索。据传言保管在内阁的案卷在道光二年(1822年)的一场火灾中被全部烧毁,吉林将军宁古塔府都统署保管的档案,因时间太长导致霉烂。为此1885年10月11日,吉林将军希文向总理衙门报告:“宁古塔署远年档案, 业于同治十三年七月间被贼入塔焚毁无存。虽有康熙五十一年来文行文档案,详査档内,并无康熙五十一年乌拉总管定界归案”(杨昭全、孙玉梅的《中朝边界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264页)。
⑦见李重夏的《乙酉状启别单》:“故穆克登但认为碑东沟道是豆满上源而立碑,而刻之曰‘东为土门’,故我国于穆克登入去之后,数年为役,自碑东设土石堆,东至豆满江源……坡则设木栅,以接于碑东之沟,而随称之为土门江源矣。今则数百年间,木栅尽朽,杂木郁密,旧日标限,彼我之人皆不能详知,故致有今日之争辩。而今乎入山之行,黙察形址,则果有旧日标限,尚隐隐于丛林之间,幸不绽露于彼眼,而事甚威悚,其实状里许不敢不详告。”
⑧见《肃宗实录·卷52》(三十八年十二月七日条):“两国定界,何等重大,而乃以一二差员之意,擅定疆域于朝廷所不知之水,此则且加惩治,以重疆事。”
⑨见徐德源的《长白山东南地区石堆、土堆筑设的真相》(载《中朝边界研究文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1998年,第757-765页)。张存武的《清代中朝边务问题探源》认为,当时清朝祭祀长白山并非在长白山,而是在吉林城西的温德恒山,指出勘界时秦煐等人所谓的土石堆是清朝为祭祀长白山所设路标的看法是错误的。
⑩见《承政院日记·册25》(肃宗三十八年六月二十日条):“定界后彊域增拓,诚为幸矣。”
[1] [韩]俞政甲.北方领土论[M].汉城:法经出版社,1991.25,56-110.
[2] 杨昭全.朝鲜历代疆域始终未逾鸭绿江、图们江[A].中朝边界研究文集[C].长春:吉林省社会科学院,1998.526-527.
[3] [韩]金得榥.白头山和北方疆界[M].汉城:图书出版,1988.46-54,55.
[4] 董万仑.光绪初年吉林东部边疆的开发[J].北方论丛,1980,(1);林世慧.近代东北危机与清末的移民实边思想[J].黑河学刊,1987,(2-3);杨昭全.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史料汇编[Z].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张杰.清代鸭绿江流域的封禁与开发[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4);张存武.清代中韩边务问题探源[A].中朝边界研究文集[C].长春:吉林省社会科学院,1998.
[5] 孙春日.解放前东北朝鲜族土地关系史研究(上)[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32-33.
[6] 张杰.清代鸭绿江流域的封禁与开发[A].中朝边界研究文集[C].长春:吉林省社会科学院,1998.665,667,675.
[7] 张存武.清韩陆防政策及其实施[A].中朝边界研究文集[C].长春:吉林省社会科学院,1998.652.
[8] [韩]申基硕.间岛领有权研究[M].汉城:探求堂,1979.
[9] [韩]刘凤荣.长白山定界碑和间岛问题[J].白山学报,1972,(13).
[10] [韩]梁泰镇.韩国的国境研究[M].汉城:同和出版公社,1981.129.
[11] [韩]金炅春.朝鲜后期国境线一考[J].白山学报,1984,(29):10-12.
[12] [韩]李日杰.间岛协约和间岛领有权问题[A].韩国的北方领土[C].汉城:白山资料院,1998.91.
[13] [韩]朴容玉.再论长白山定界碑建立与间岛领有权[A].朝鲜时代北方关系史论考[C].汉城:白山资料院,1995.1054.
[14] 张存武.清代中韩边务问题探源[A].中朝边界研究文集[C].长春:吉林省社会科学院,1998.555,529-576,565,564.
[15] 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193-196,160-161,240-241,246,248,251-252,310-311,314-315,338-357,36.
[16] 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R].沈阳:奉天学务公所, 1909.
[17] 王崇时.19世纪前中朝东段边界的变迁[A].中朝边界研究文集[C].长春:吉林省社会科学院,1998.510,508.
[18] 徐德源.穆克登碑的性质及其设立地点与位移述考[A].中朝边界研究文集[C].长春:吉林省社会科学院,1998.599.
[19] 倪屹.“间岛问题”研究[D].延吉:延边大学,2013.
[20] [韩]梁泰镇.韩国国境史研究[M].汉城:法经出版社,1992.132;[韩]赵珖.资料注解[A].韩国的北方领土[C].汉城:白山资料院,1998.224.
[21] [韩]申基硕.间岛领有权问题[M].汉城:探求堂,1979.37-74;[韩]金得榥.白头山和北方疆界[M].汉城:图书出版,1987.85;[韩]梁泰镇.韩国国境史研究[M].汉城:法经出版社,1992.6-102;[韩]俞政甲.北方领土论[M].汉城:法经出版社,1991.111;[韩]金炅春.鸭绿江、豆满江国境问题研究[D].汉城:国民大学校,1997.68-82.
[22] [韩]姜锡和.讨论议题[A].韩国的北方领土[C].汉城:白山资料院,1998.209-221.
[23] 徐德源.土门、豆满为两江妄说驳考[A].中朝边界研究文集[C].长春:吉林省社会科学院,1998.766-768.
[24] [韩]金炅春.鸭绿江、豆满江国境问题研究[D].汉城:国民大学校,1997.56;[韩]梁泰镇.韩国国境史研究[M].汉城:法经出版社,1992.128.
[25] 徐德源.长白山东南地区石堆、土堆筑设的真相 [A].中朝边界研究文集[C].长春:吉林省社会科学院,1998.757.
[26] [韩]梁泰镇.韩国国境史研究[M].汉城:法经出版社,1992.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