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赏析
2014-02-06周玉明
周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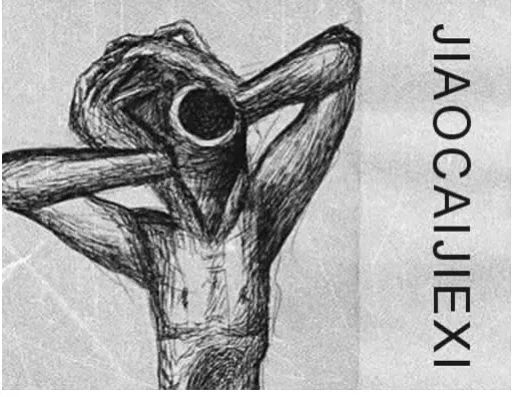
在繁花锦簇的词学世界里,活跃着众多多情妩媚的女性形象。她们或为“人比黄花瘦”的侯门思妇,或为“垆边人似月”的小家碧玉,或为“记得小萍初见”的歌姬舞女,群芳尽现,妖娆无比。作为领一代风骚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的此类词作,大多以体谅与同情的态度描写女性,把女性作为自身命运的代言者,寄托着宦海浮沉的身世之感。王国维认为“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欧阳修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男子作闺音”的写作范式,但又摆脱了花间、南唐以来穠丽绮靡、幽闷萦怀的香艳习气,严格遵循“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传统,将词予以雅化,追求温柔敦厚、委婉含蓄。在词作中,欧阳修不知不觉地流露出他的学问、修养、胸襟、品格以及他的人生经历,从而使读者生出超越爱情的联想,看到作者的感情本质。
欧阳修的女性意识成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可以从当时的社会风气、婚姻观念、女性地位等作多角度分析,而单就欧阳修本身对女性的态度来讲,是跟他的成长经历分不开的。
欧阳修四岁失怙,与寡母郑氏相依为命,郑氏“世为江南名族……恭俭仁爱而有礼”(《泷冈阡表》)。女性主导的家庭环境养成了欧阳修仁慈、多情和细腻的品格。而成年后与三任妻子的生离死别、悲欢离合的情感体验,更使得欧阳修对爱情有着超乎常人的深刻理解。词人对母亲的敬仰,对三次婚姻的悲欢体验,使词人对女性情感有着深入细致的体察。他词中的许多女性形象,其实就是词人对自己情感生活的艺术化观照。
且看词中。首句“深深深”三字写出了那个女子与外界隔绝、形同囚居的处境,不但暗示了主人公孤身独处的境遇,而且还有心事深沉、怨恨莫诉之感;“深几许”于提问中满含怨艾之情;“堆烟”极写视线之迷茫,衬出人之孤独寡欢;“帘幕无重数”,写闺阁之幽深封闭,这是对大好青春的禁锢,是对美好生命的戕害。显然,主人公虽然有着优裕的物质生活,但是精神上极度苦闷。这三个字既是对庭院的直接描写,更是主人公心理的深入剖析,景写得深,情写得更深。就像一组电影镜头,读者的视野随着“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由远而近,逐步推移,渐行渐深;又折返回来,走进高墙深远,走进一个贵族佳人心事深沉、怨恨莫诉的内心世界。空空的庭院里只有一个孤零零的女子,期盼的人哪里去了?佳人登楼远眺,她的目光透过重重帘幕、堆堆柳烟,向男子经常游冶的地方凝神远望,但是唯有堆烟杨柳,层层雾气遮住了企盼的视线,男子寻花问柳的“章台路”就更看不到了,遑论那个薄情的背影呢?眼前美景道不得,“帘幕重重”,究竟多少重,一言以蔽之:“无重数”即“无数重”。深深庭院中,已宛然见到一颗被禁锢的与世隔绝的心灵。然而锁得住的是她的视线,锁不住的是她的一颗痴情的心。
人儿走马章台,花儿飞过秋千,有情之人、无情之物对她都报以冷漠,怎能不让人伤心!这种借客观景物的反应来烘托、反衬人物主观感情的写法,正是为了深化感情。词人一层一层深挖感情,并非刻意雕琢,而是像竹笋有苞有节一样,自然生成,逐次展开。天然浑成、浅显易晓的语言中,蕴藏着深挚真切的感情。“乱红”意象既是眼前暮春之景的实摹,又是女子悲剧性命运的象征。这种完全用环境来暗示和烘托人物思绪的笔法,深婉不迫,曲折有致,真切地表现了生活在幽闭状态下的贵族少妇难以明言的内心隐痛。
很显然,《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中所塑造的是一个贵族女性,她温婉文静、内向贞洁、深情而又庄重。重重帘幕、深深庭院、堆烟杨柳中,她备受感情的折磨和煎熬,登高望远自伤情,唯有主动压抑自己,才能够勉强排解愁怨。在她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温柔敦厚,正是文人所需要传达的正统情思、优雅情趣。即便用深美闳约、酝酿最深,因而“其言不怒不愤,备刚柔之气”来形容亦不为过。
欧阳修善于淡化人物外在形象刻画,着力于将传统的代言体转化为个人情感抒发,借助人物自身特有活动,勾勒出女主人公独特的心理过程,探索女性心理的微观感触,把她们的心理活动剖析到更深的层次。冯煦《阳春集序》评价晏殊写闺怨词说:“俯仰身世,所怀万端;缪悠其辞,若显若晦。”而欧阳修则显得既内敛压抑而又直观外露,妇女内心复杂的思想感情与细腻的内心世界,在他的笔下显得层次分明,个性鲜明,耐人寻味。
本词上片通过想象丈夫在外的一些不轨行为,表达思妇对丈夫的想念;下片则以门掩黄昏的特写镜头,表达妇人的孤独与苦闷,构思奇特,重点揭示了贵妇人内心的孤寂愁苦的命运和心理状态。“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眼望远处,心中却潮波澎湃。正如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中所说,在接受冯延巳影响方面,“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俊”,是俊爽、俊秀;“深”,是深沉、深细。这些女子生活的全部重心就在于等待,生命的亮点只在于那个曾经深爱如今远离不归的男子。在这个贵族女性身上,我们看到是哀怨守候,却又痴而不怒,更多的是对爱情的忠贞执着,专一痴情,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中“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特征。“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欧阳修认为,人的相思之苦与外在的各种景观没有多大关系,“花不语”“乱红飞”,一切痛苦的根源只在人生的缺憾和人天生的“痴情”。诚如其《玉楼春》所述:“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痴情女子“无计留春”的感伤并没有获得“风月”的同情,却更加令人为之叹惋。
诚然,北宋时期,士大夫多蓄养歌姬以作佐欢玩物。居庙堂之高,他们以政治家和士大夫的身份出现;而处歌席上,他们又以风流文人甚至是“多情种子”的面目出现。他们以男性欣赏的眼光去写歌妓舞女的花容月貌、莺声柳姿、娇情媚态,追求心理上、精神上的愉悦和享受,文人的艺术趣味也多放在了“香闺绣房”。我们相信,位高权重、养尊处优的欧阳修亦恐难免此俗。然而倘若就此将他归入频涉秦楼楚馆,留恋“章台路”的薄情男子,又似乎不尽合情理。
他曾经写过《采桑子》十首,全是写颍州西湖携妓游湖的事。当是时“急管繁弦,玉盏催传”,姑娘们嘻嘻哈哈闹成一团。秀水与娇娃在侧,他的目光却投向她们又掠过她们,滞留于绿波间,随风起灵感,诗句缓缓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走出来,十首词俱有空灵感。“行云却在行舟下……疑是湖中别有天。”在悠悠吟哦中,我们却读到了另一种深藏的况味。
承上所述,唐宋词中向来有“男子作闺音”的传统。清代田同之在《西圃词说·诗词之辨》里面提到:“若词则男子作闺音,其写景也,忽发离别之悲。咏物也,全寓弃捐之恨。无其事,有其情,令读者魂绝色飞,所谓情生于文也。”欧阳修个人深厚的文化底蕴使他的男子作闺音的作品也符合他的身份趣味,缠绵悱恻的同时又高雅蕴藉。据此,欧阳修又似乎是将自身转化为女子的角色,在对异性的观照中隐含着对自身身世命运的观照。
从文本层面上来看,这首词似乎仅是写一个侯门贵妇暮春时节的哀怨:情人薄幸,任性冶游而自己又无可奈何。美景不常在,青春难常驻。美好的事物总是匆匆凋零,自身命运无法把握,从而表达出对人生匆匆而无奈的深刻体验。而这种女性对青春易老的仇怨与欧阳修仕途坎坷、人生无常的失落是有相同之处的。欧阳修眼前有痛说不得,因此借助女子之口、道自家之心声也就显得合情合理,他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家之块垒。欧阳修把相思这一普通话题转换到人生哲理的层面,超越了单纯的单纯的闺怨离恨而扩展为对命运的扣问。甚至有人认为“‘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也。‘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寐也。‘章台’,‘游冶’,小人之径。‘雨横风狂’,政令暴急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为韩、范作乎。”(《张惠言论词》)。
泪光莹莹之中,花如人,人如花,最后花、人莫辨,同样难以避免被抛掷遗弃而沦落的命运。贵妇人的丈夫见弃、孤独伤感、有容无人悦,也正对应着欧阳修的年华虚掷、怀才不遇、壮志难酬。沦落之悲,不言而明。叶嘉莹说:“在欧阳修那些风月多情的作品中,我们可以体会出他心性中所具有的对人间美好事物的赏爱之深情,对生命之苦难无常的悲慨,以及他在赏爱与悲慨交杂的心情中对人生的感受和态度。”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从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鲁迅先生为我们指出了赏析诗词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知人论诗(词)。欧阳修四岁丧父,家境贫寒,历经挫折,却始终坚忍不拔,终成朝廷重臣,平生抱负得以一逞。《醉翁亭记》里,看他饮酒行令,看他投壶对弈,看他陶醉在山光水色之中,他难道真的忘记自己的志向了吗?那又何必在《伶官传序》中,恳切地提醒当权者“满招损,谦受益”,“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呢?满腹经纶、志存高远、兼济天下,却难有施展抱负的机会,空余惆怅和伤痛,剩下的有怨、有恨、有苦、有悲,那种孤独、伤感和文中寂寞的女主人公神韵相合。所以,与其说这首词写的是闺怨,倒不如说是词人以一首《蝶恋花》,借独居深院的女子来表达自己被统治者抛弃的怨、恨、伤、悲。
“思妇怀人”也罢,“伤春寓意”也罢,“寄托身世”也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一篇文本意旨的解读总是多样性的,而意旨的歧义也正是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