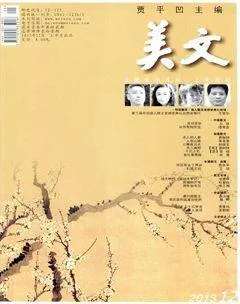文学观点
2013-12-29
蒋峰:
我能总结的写作秘诀并不多,照药方子抓药就不是文学了。有一句话我一直警惕,很适用——永远不要从故事开头写起。
这是我的写作圣经,也是我开头恐惧症的缘由。不是插叙倒叙那么简单直接,那些绕一圈还得从开头讲起。翻译成文学理论可能就是隐藏叙事,但是老隐藏容易自作聪明,读者会感觉被戏耍。找个节点讲,学会控制,别忍不住倒叙插叙,也别藏着掖着,隐藏的效果就出来了。(《文艺报》)
周篷桦:
没有细节虚构的文字,能够组成一个完整的文本吗?不能。我甚至固执地认为,绝对真实的记录是没有的,包括日记。日记还有个人化的误解、误识和误差,何况一篇艺术性强的散文。但我同时认为,散文的虚构是有底线的,我不妨举例说明:去年我曾读到一篇怀念刚去世的母亲的散文,是一位熟识的朋友所作。他把当了一辈子农民的母亲写得高大完美,说他母亲是村里的养蚕能手。我读后立即给他打了个电话,让他节哀顺变,说了一堆安慰的话。但没想到他在电话那端大笑起来,说:“纯虚构。”(中国作家网)
桫 椤:
外界说文学被边缘化,有些作家自己也认为文学被边缘化了。其实文学一直在它本来的位置上,只不过是它的参照系即社会对文学的需求发生了变化。现在我们的长篇小说每年要出版3000部以上的实体书,这个数量是惊人的;而网络上的小说数量更为庞大,这是多么繁荣的文学景象,完全不是被边缘化的样子。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些大量的文学作品,是否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我想大多数会被淹没,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的文学性偏低。当然,不可能所有有文学性的作品都会成为经典,但经典应当成为每个作家创作的追求。把握文学性,就要有经典意识,要以经典作品的文学性为标准衡量自己的创作。传统作家如此,网络作家也要如此。网络文学经过10多年的发展,经典化目前已经成为非常迫切的一个问题,网络作家尤其要强化经典意识。(《文艺报》)
杨献平:
当下文学面临的困境主要有三。一是时代本质快速变异。时代因素,或者说时代背景下的人性深度和人生幽微,“此刻我在”的人心向度与精神困境,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参悟不透时代本质,对自身所在时代的不了解或者隔膜,思想深度与认知判断素质能力的迟滞、随从和守旧,是当下文学写作自身面临的第一困境。二是电子化和简短化的阅读方式正在加速阅读革命。手机阅读的携带方便、海量存储、有声有色和书籍的文字密集枯燥形成鲜明对比,构成了当下文学需求或者说“消费”方面的不利因素。三是个人性的从众意识是限制作家个人创作不断上进、创新的第一障碍。文学大环境之下,总是有一些潮流,一波一波,无有休止。主流媒体倡导哪些,评论家看好哪一类题材或某一种创作方向,很多作者便会群起效之,作品同质化严重。
回到文学,回到自我。(《文艺报》)
孟繁华:
孟繁华认为,中国读者在其获奖之前之所以对门罗不够重视,与阅读习惯有关。他说:“中国社会百年来一直处于剧烈变化之中,读者愿意接受与社会问题密切关联的文学作品,希望从中寻找社会问题的答案。门罗讲的则是日常生活。她对女性心理的描写,是我们过去所读作品中缺乏的。但她和女性主义没有关系,并不颠覆男性话语。她采用了一种非常个人化的写作。”(《中国青年报》)
北村:
中国作家的创作生命期普遍比西方作家短,通俗地讲,主要原因可能是缺乏“问题意识”,或者说他的问题更多的与社会政治历史,或情感身体感官相连,而非人性精神。这也是他们比较热衷于现实还原写作和自然感官描摹的原因。如此,随着时代更易变迁,经验退出历史舞台和身体健康衰残,创作力便自然地衰退。(新浪微博)
麦家:
都说写书就像养孩子,其实不像的,书可以重写,孩子不行。如果养孩子可以像写书一样推倒重来,天下的父母或许有一半都想重养孩子,包括我。我对孩子小时候要求很严,现在想来真的没必要,小时候让他玩就行了,陪他玩就好了。
想象力是每个人都拥有的,但现在有很多人陷于生活的理性,已经放弃想象了。想象不到更好的自己,更好的生活,哪怕只是短暂的一分钟,这才是可怕的。(腾讯微博)
王敖:
诗歌理想是一个投影仪,过热会把里面的灯泡烧坏。我现在要做的是把手里的长诗写完。其实能写诗,已经是一种自我肯定过的理想状态。这是任何赞誉和现实利益都无法兑换的成就,继续写作是最大的奖励。
我们可以想见很多大诗人在文明的瓦砾间的身影,散落的残篇,或者本来就没写完的作品,背后是无数的文化赝品的浪潮在合唱。而某一首诗磨损的躯壳,也许曾经无比精美,现在就像一个空罐头盒子,以时速50公里的速度,在某个高速公路附近随风飞行,偶尔磕碰出几个音符。你听到了就听到了。(《新京报》)
徐则臣:
人们常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一种新的阅读和传播方式也的确需要文学发生与之相应的变化,经典也往往要做出顺应和引领时势的尝试;但经典同时也在做着与时势反方向的运动:它要以此来开拓艺术和思想的可能性疆界,为现时代文学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省示和预言,告诉我们这个时代及其文学的局限。
也许我们最终抵抗不了这个全球化的潮流,但为了一种好文学的尊严,为了一项矢志坚守的事业,我们的确应该认真考虑一下,如何与经典站在一起,成为这个平滑、肤浅的时代的坚定的反抗者。(经典的反抗——中德作家论坛发言提纲)
马未都:
文学是否即将死亡,这是一个严肃又沉重的话题。有学者认为今天微博的140个字符,无法完全彻底表达其文学性,会使读者智商下降。而我们的文化遗产唐诗五绝仅20字,七绝28字;宋词16字令仅16个字,《忆江南》27字,《如梦令》33字,元曲《天净沙》28字,这都离那140字远着呢,这些高智商的创作,至今还使文学爱好者如醉如痴,如痴如迷。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文学伴随人类文明而生,不会死亡;但文学的形式会依次死亡,《楚辞》来了,《诗经》(形式)死了;汉赋来了,楚辞死了;骈文来了,汉赋死了;唐诗来了,骈文死了;宋词来了,唐诗死了;元曲来了,宋词死了;(明清)小说来了,元曲死了;电影来了,小说死了;电视剧来了,电影死了;游戏来了,电视剧死了,只不过这种“死亡”是相对而言。文学像一个不死的灵魂,依次依附于文学体裁生存,只不过随着文化的普及,文学越来越通俗,越来越世故,越来越谄媚,所以就越来越无趣而已。(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