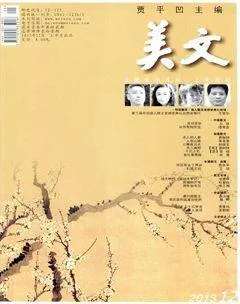用生命书写
2013-12-29李三槐

李三槐
1941年3月生于陕西省周至县。1964年从西北政法大学哲学系毕业。国学学者,中国思想史、中国新闻史学者。先后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人文杂志》总编等职。
为挚友荣庆校阅《从新闻黑洞跳进又跳出》这部248万多字的四卷本著作,感触奔涌。归结起来,这部书是他用自我生命书写出来的华彩结晶。
我甘心情愿为他的书当“助产士”
我从任《人文杂志》编辑的20世纪70年代起,就编发过荣庆的文稿——《秦马小史》《秦国四贵及其覆亡》《张载卒年卒因考》《郦道元遇难地阴盘小考》《王老九的诗歌风格及其流派》《王陆一和他的〈战区巡察报告撮陈〉》等。知道他在民间文学、民俗学、地方志与国共两党史料的征集上用力甚勤。当时曾有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陈元方先生想调他到省上做方志研究;新闻学家、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何微先生想调他到省社科院做党史研究;教育家、陕西省教育厅副厅长权剑琴与左嘉猷两先生想调他到省厅做教育学研究等动议。最终,荣庆进了《中国新闻社》,走上了对外新闻记者岗位,但始终没有减弱对文学、史学、民俗学研究的兴趣。70年代初,他就对我披露心迹:“想写一部揭示民族秘史的长篇小说《绣岭》。”我几次三番劝他:“你从事学术研究可能取得的成就会更大。”
荣庆此生曾两度遭受了常人不易挺直腰杆生存的艰难困苦:一次因抵制“穷过渡”,受顶头上司打击报复;一次在作记者后因写“内参”揭露某些地方官员的不正之风,受内外上下纠结打压。逆境之中,他还有文学梦、学术梦么?
2008年,68岁的他与旅澳学者刘婷博士合著的开启性边缘学科专著《新闻民俗学》(两卷本、83万字、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杀青后,我受其嘱托,做了该书的编审与校阅工作。
读着书稿,我吃了一惊,深为他不坠初志和献身人文科学的执著与毅力所感动,也心甘情愿为之效力。记得荣庆在《新闻民俗学》导论里说:“本书在学术上要处理的症结是,构建新闻民俗学学科体系中国际视野与中国特色之间的矛盾。”这条红线贯穿于这部专著始终,显示了一个学人高远的生命寄托。
在《新闻民俗学》校改、付梓的同时,荣庆又像一匹驰骋疆场的奋蹄老马,要对自己的“笔墨人生做个交待”——从历年撰写的三千余篇文稿中,挑选四百多篇,结集成册,拟交作家出版社印行,并再次嘱托我做《从新闻黑洞跳进又跳出》一书编审与校阅工作。由于这部学术性、文学性兼容的著作涉及学科广泛、学术议题复杂,加之我做编辑养成的“吹毛求疵”习惯,弄得作者将不少篇章推倒重写,大删大改,个别文章乃至“割爱”舍去,竟然延迟预定出版周期数年而在所不惜。他对我的“咬文嚼字”与某些不留情面的质疑不但不恼,还鼓励说:“我在西安再也找不到像你这么爱挑剔、能挑剔的好编辑了!”与前次不同的是,他要我写篇序文。我逐卷逐篇逐段逐句读了这么一个四卷本大部头著作,深深地感觉到,这部文集,是作者为文化振兴而呐喊的文本,是一位学人生命在笔端流淌的记录。
生命是什么?古今中外的学人众说纷纭。生物学认为,生命是蛋白质与基因存在的一种形式。物理学家普里高津认为,生命是一个耗散结构,任何生命都要与外界环境不断地交换物质和能量。哲学家说,生命是一个由物质和能量构成的对立统一体。“万物各得其所,生命寿长,终其年而不夭伤”。(《战国策·秦策三》)“人之所宝,莫宝于生命。”(《北史·源贺传》)荣庆与我是同代人,经历了中国20世纪40年代迄今的所有社会变迁。他敬畏生命,珍爱生命,坚持不懈地记录自我生命存在于社会的轨迹、感悟、心声,辑而为《从新闻黑洞跳进又跳出》。
将《从新闻黑洞跳进又跳出》作为整部书的题目。所谓“新闻洞”,借自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有关报纸“是一个在有一定之规的封闭系统中的强迫性选择”。“新闻洞能自然而然的反映社会注意事项的轻重缓急”。作者在《中国新闻社》《报刊之友》《陕西旅游》《企业信息报》《香港商报》《今传媒》等媒体当记者期间发表的3000余篇作品,都是经过媒体在“封闭系统中的强迫性选择”,及时传播了中外受众急需的新闻信息。在编选本文集时,从中打捞出来一部分,做第二次“封闭系统中的强迫性选择”——择其较有史料价值、学术价值、鉴赏价值而选录入书。
荣庆用“新闻黑洞”作为书名,意在何处?
“黑洞”——由一个只允许外部物质和辐射进入而不允许物质和辐射从中逃离的边界即视界(event horizon)所规定的时空区域。“黑洞”是超级致密天体,它的体积趋向于零而密度无穷大。由于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物体只要进入“黑洞”一定距离的范围内即“黑洞”的引力场内,就会被吸收掉,连光线也不例外。“黑洞”吸进物质时会发射出X射线。引力场会使时空弯曲。当恒星的体积很大时,它的引力场对时空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从恒星表面上某一点发的光可以朝任何方向沿直线射出。而恒星的半径越小,它对周围的时空弯曲作用就越大,朝某些角度发出的光就将沿弯曲空间返回恒星表面。等恒星的半径小到一特定值(天文学称“史瓦西半径”)时,连垂直于其表面发射的光也可捕获,此时恒星就变成了所谓“黑洞”——像宇宙中的“无底洞”,任何物质一旦掉进去,“似乎”再也不能逃出。天文科学家猜想,“黑洞”跟白矮星和中子星一样,很可能也是由恒星演化而来的。“黑洞”特异于别的天体,具有人们无法直接观察到它的“隐身术”。
荣庆提出“新闻黑洞”,指新闻作品易碎、易逝,犹如天体“黑洞”所具有的“隐身术”。
而“从新闻黑洞跳进又跳出”指什么呢?我曾想过很久,也与他讨论过。
根据广义相对论,空间会在引力场作用下弯曲,好像光仍沿任意两点间最短距离传播,但走的已非直线,而被强大的引力拉得偏离直线方向。而在“黑洞”周围,空间变形成为“曲线”。这样,即使是被“黑洞”挡着的恒星发出的光虽有一部分落入“黑洞”中消失,可另一部分光线会通过弯曲的空间、绕过“黑洞”而到达地球。这样,地球人类仍可观察到“黑洞”背面的星空,就像“黑洞”不存在一样。进而言之,有些恒星不仅朝着地球发出的光能直接到达地球,它朝其他方向发射的光也可能被其附近的“黑洞”强大引力折射而到达地球。如此说来,地球人类不仅能看到该颗恒星的“脸”,同时还能看到其“侧面”乃至“后背”。显而易见,荣庆的“新闻黑洞”提法,借天文学“黑洞”打比方,对一部分落入“黑洞”中消失的作品如“川”(河)似的永远“逝者如斯夫”,而让另一部分如“光线会通过弯曲的空间、绕过‘黑洞’”而到达地球”的作品,供人们继续观察其“脸”、其“侧面”乃至“后背”。作品结集了,提供了读者阅读的方便,而如何“观察”、思辨,又当另论了。
从“新闻洞”而“新闻黑洞”,进而“从新闻黑洞跳进又跳出”,这种将形象思维、意象思维、逻辑思维联结贯通做学问的方式,已成为荣庆读书与写作的经验、习惯。我说他在“用生命书写”,除了指他实实在在写自我生存体验外,也指他的作品里流露着的这种思维方式。
为这么一部四卷本巨著作序,从何说起呢?想来想去,不如将几年来的看稿札记,约略集纳,作为导读,给读者提供一些阅读方便,就叫《用生命书写——看稿絮语》吧!
《报坛撷英》卷校阅札记
新闻记者是新闻事件的记录者、观察者。只有实录事实、洞察真伪,运用背景揭示事件本质,才能使新闻在转化为历史的过程中少一些迷茫与伪装。新闻从业人员能做到此点者,可称为报坛英才也。荣庆以此自勉,也以此结交同行。
荣庆将司马迁誉为记者之师,特别推崇司马迁纪事“不虚美、不隐恶”,“善叙事”,做“良史”的“实录”精神。在他看来,记者犹如活跃的氧元素,活泼而善“化”;又如戏台上的“八角身子”,生旦净末丑哪个缺了补哪个,是全挂儿把式;还像六国贩骆驼的,七十二行、三教九流之人,哪个都能搭上话。而对事实则必须准确、真实,返璞归真地呈现人物、事件及其环境变迁的本来面目;力避随意抑扬、爱憎任由己出。《一个老红军的落叶归根》,是写中国人人皆知的革命前辈习仲勋的。作者没有溢美之词,而是从富平迤山习仲勋陵园的观感说起,再介绍民众剧团与《梁秋燕》的诞生、毛泽东对习仲勋曾经的器重、精心策划与保护李先念等回延安、冒风险保护西安城墙、“文革”在大街上之所见与长篇小说《刘志丹》事件本末、在金家巷第二次见到习仲勋等,环环相扣地写出了这位老红军与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每则传奇故事都蕴藏了民心。《难忘哟,那一场“雄雌之风”》,是中国当代社会转折期的一个缩影,也是作者人生转折点的一份真实记录。《国殇》《黄帝陵诗文背后》《克林顿访陕追记》《风雪旅韩日记》《报道西北大开发战略的回眸》与《3·16车祸内情》《西安火车站爆炸案始末》《西安芦荡巷姚宅存世秘闻》《西安半坡遗址损坏严重》《汉长安城遗址遭严重破坏》《黑河啊黑河,救命的水》《骊山母亲啊,我为您“讨”来七字批语》《为秦兵马俑受损呼吁》等,流露了他记者生涯中意气风发、无所畏惧的为民请命、勇于担当的作风。
荣庆还试图打破同行是冤家的陋习,为诸多记者、编辑树碑立传。记者的文章常有振聋发聩、一纸风行之效,但记者为人、为学及其生存状态,却是“灯下黑”,很少为社会所了解。作者从清末女杰秋瑾、辛亥革命与报业元老于右任、民国报坛宗师张季鸾、为老百姓办《老百姓》报的李敷仁、当代新闻学界旗手何微与甘惜分的卓越贡献与高尚人生,到作者同时代的新华社记者王兆麟,中央电台记者贺俊文、甘肃日报社记者武扬、岭南报人张跃虎,陕西日报社记者杜耀峰、杨玉坤、吉虹,宝鸡日报社记者宁丽君、刘斌,陕西省报刊审读员薛耀晗、贾保民、张羽、王宗义,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邱程光,德国王安娜与美国史沫特莱、海伦·斯诺,出身名门、自学成才的李铠博士等的从业脚步,“说故事”似地活灵活现、娓娓道来。读了他写这些人的“列传”,便会明了“记者”是什么样的人。他将同行作为“类的样本”来探究,以其是否忠实地记录历史为标准加以衡量。“卖石灰见不得卖面的”惯常社会现象,在他笔下成了“惺惺相惜”、同行相亲。
当记者不仅需要精通新闻知识和所采访行业的专门知识,成为某领域的专家,并需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转化为具有一定权威性的专栏作家、杂家、文化学者。阅读本卷作品,可以看出荣庆在这方面的进取与努力。他撰写的《王老九的诗歌风格及流派》《王老九之死》《贺丙丁和他的诗歌》《农民诗的对话》《黄土文化独特人性的破译与解密——评长篇小说〈陕西楞娃〉》《散评〈半阁城〉》《〈金城关〉及其他》《跟进老舍还原消失的那个北京——略说〈满树榆钱儿〉》《梦,在那并不遥远的地方——与网友话文学》《听平凹说三毛》《几多李广——“电视李广”出奇死》《电视连续剧不是连环画》等篇,涉及诗歌、小说、散文、游记、随笔与电视剧诸多创作与欣赏的“时兴”文学话题,集中反映了作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深刻思考。就我所知,他的文学批评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但并未将之作为主攻方向,故而文学评论时有时无、时断时续。读者由上述作品可以看到,作者对中外名著如饥似渴地吸纳与咀嚼,时出创见。在文学批评园地,他是最早、最系统研究农民诗人王老九的诗风及其流派的学者。在《农民诗的对话》里,他依据当代市场化、城镇化、国际化进程中文艺思潮的多元,从学术高度为农民诗做了深入浅出的定义,开创性地为农民诗提出了五条标准;在《农民诗和农民诗的历史分期》里,将新中国成立迄今的农民诗划分为三个时期评估,并对中国城市化中的农民诗走向做出预测,填补了我国农民诗歌研究领域的空白。同时,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简论了中国现代诗近百年的得失及当下的困境与出路,虽为一家之言,但也鞭辟入里,发人深思。
作者对《陕西楞娃》《半阁城》《金城关》《满树榆钱儿》四部长篇小说的评论,直击节点,纵横比较,以赤诚坦荡的语言和洒脱睿智的文笔展现了文学评论上的开阔视野。他认为小说是运用语言形象地虚构故事、塑造人物以反映社会现实和揭示人性的文学体裁,并对当代小说创作粗制滥造的问题提出了五条纠正、引导的建议。他就文学批评界有学者将小说重故事情节泛化为“罪”的现象指出,这与中国小说史的文本成果不相符,也与中国人的阅读习惯相悖离。主张作家用坐冷板凳和痴迷艺术的心态,创作本民族“史诗”式的小说,不必因了追求“功名利禄”和市场效应去制造“短命作品”或“文化垃圾”。荣庆有的放矢地强调了文学作品的语言问题。在他看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小说艺术成就的高低,首推语言。语言不仅是作家与读者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还是构建小说“楼宇”的基因。上述四部新出版的小说,作家对本民族的语言都怀有深深的敬畏心。他断言,中国21世纪不朽的文学作品,将出在甘坐冷板凳的“文学宗教圣徒”手里,归根结底,取决于小说家语言艺术水平的高下。
本卷及其他卷还散嵌了作者写的几十首古体诗及民歌体诗。这种编排方式不比将诗收集在一起易读,但却保留了其诗最初发表的原貌,易于读者连同散文、随笔文本与题记一块儿领悟诗的背景及其真谛。他说:“诗是诸种文学题材中最凝练、最讲律动的艺术表达形式。”又说:“不管古体诗词、山歌民谣还是自由诗(新诗),都追求空灵、抒情、节奏铿锵、韵律优美。”本书虽然选录他的诗作较少,但都大气磅礴,清新欢快,意境深沉,宛如行云流水而时出涟漪,体现了作者在真诚与浪漫兼容里跋涉的创作境界。
“振叶以寻根,观澜以索源”。荣庆主张文学创作应形象思维、逻辑思维、意向思维三种思维模式兼容。他认为,《周易》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把复杂的宇宙人生图景展示为一种可观之象,便是中国传统的意象性思维。而当代时尚的“快餐文学”,与“文以载道”相悖,患了“意向思维贫乏症”。
《人世镜像》卷校阅札记
每个人的一生,不管其社会地位与出身、归宿如何,都是所处时代的缩影。其生其死、其荣辱贵贱,对当世后世都是一面镜子。《人世镜像》卷里所收篇章,涉及大人物,也有小人物;有精英,也有落魄者;有当代人,也有辞世者。读者阅他人事迹,照他人影像,剖他人心迹,同时也照自我影像,剖自我心迹。花花世事“走马灯”,读来会饶有兴味。
作者采写《毛泽东水晶棺的由来》和高端人物王震、萧克、李瑞环、王光英、杜义德、郑斯林等的特稿与报道,从平凡的视角出发,将引语、对话、叙事、背景、白描与形体语言相结合,拨开了他们身上神秘的“光环”。读者从亲切、质朴的字里行间,当会明事悟理。《蜗牛风波》《邱会作谈十六年囚徒生活》《吴桂贤畅谈往事》《再访吴桂贤》《姚连蔚“失踪”与近况》等,通过采访当事人,揭开了“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如毛泽东主席夫人江青,14岁当红军后来成为林彪集团骨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的邱会作将军,由纺织女工而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吴桂贤,由工人“造反派头目”而出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姚连蔚的一些奇闻逸事及其政治沦落的境遇。这些篇章曾为中外媒体广泛转载,如今已成为研究“文革史”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
《“东陵大盗”和他的儿子》,写盗掘清东陵的孙殿英将军独生子孙天义教授畅谈乃父及自我人生。《一片秦声浑不断——台北秦腔实验剧团西安寻根》《台湾国策顾问向中共献策——赵耀东西安考察追踪》《江南遇害始末》《渝生寻母、认父(柏杨)记》《万里碧空孤帆远——张学良公馆开馆侧记》《蒋介石题黄帝陵碑的重刻》《丘逢甲谒黄帝陵》等,故事感人,充满了台湾海峡两岸信息阻隔时期难割难舍的同胞情谊。《西安卫星测控中心访问记》《“三十而立”,志在明天——记航空航天部第四研究院》《中国飞机城巡礼》《瞻顾西北天桥》《丝路第一关》《访吴瑞》《数学奇才王国俊》《中国电子科学家的摇篮》《“神箭”之母——访中国空军导弹学院》《走访西藏民族学院》等,是荣庆最早揭开其人其事神秘面纱的作品。由于材料翔实客观,不少为当事人口述亲历,作者运用高屋建瓴、纵横交错结构,生动简明、深入浅出解析,将诸多高难度的题材,用剥茧抽丝、直达枢奥而又灵动风趣的方式呈现给读者。如今读来,还令人击掌称奇。
本卷所收为书法家、画家、高僧、高道、教师、医生、导演、戏剧与影视演员、体育明星、海外华人华侨写的特稿,重在解析各人的生活环境、人生经历、鲜为人知的内心世界及其过人的毅力,将“追星族”要追的“秘闻”,还原为切切实实、明明白白的人物原生态。作者用事实告诉人们,名人都是由无名而来的。每个为民族复兴而奋争的人,都可以转化为有作为有成就的人。
《人世镜像》卷末尾收的16篇随笔、杂文和《骊山记胜》附录诸篇小品,与前面的人物特稿、专访的题材、文风截然不同,夹叙夹议、嬉笑怒骂而酣畅淋漓。刘勰《雕龙·杂文》云:“详夫汉来杂文,名号多品:或典诰誓问,或览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讽谣咏,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经五四运动鲁迅、瞿秋白、李大钊、陈独秀、刘半农等人经营,杂文已成长为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事变或社会倾向的一种文艺性论文。我深知荣庆文笔犀利诙谐,在特定政治环境下长时间不愿意在杂文园地里耕耘。本卷所选录的《樗祭》《耍猴猎猴杂说》《耗子闹夜》《说扎势》《说酒》《人老了》等文,在调侃中针砭时弊,鞭挞丑恶,求索真理。《属龙说龙》《解读壁虎》《西安应复名长安》《口号与网上口号》《白居易吟居宅》诸篇,在充满知识趣味的字里行间曲折冷峭,入木三分,讽喻辛辣。
《天地走笔》卷校阅札记
唐代李复言《续玄怪录》云:“吾已得炼形之术也,其术自无形成而炼成三尺之形,则上天入地,乘云驾鹤,千变万化,无不可也。”《天地走笔》卷所说“天地”者,并非探究仙玄者流“上天入地”之幻术,而所收尽为游记、散文、随笔,均是作者游历祖国山河和境外名胜之实录、观感。
荣庆曾对网友说:“史籍是活的故事流逝之后留下的符号,后人要令它复活,就需要考辨、发掘,并用新的视角表达。我尝试将纪实性、学术性、文学性糅合起来,不知道社会效果到底如何?”对散文创作,他有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如说:“人物纪事的散文难写,弄不好会如小小说或小说。两者的区分,只在小说有故事情节纵向贯穿并由矛盾冲突演进。而人物刻画与细节、心理、对话描写,还有形体语言,与散文并无区别。人物纪事的散文也常以第一人称抒情,较小说的情感显露,也浓烈。”“散文贵在抒情,贵在刻画人物细节中抒情。艺术的真实在细节,因而在细节中抒情者,乃情真意切。”他在评点大岩屋《野猴走亲戚》时说:“用童话解析人类回归自然保护地球生态的课题,动了脑筋。现在很多童话作者腹中空虚,离孩子又远,写的童话‘人话’太少,一个劲搬日韩欧美的外国货,什么奥特曼、变形金刚之类,有什么故事性、文学性、科学性呢?令人生厌!”
他的散文理论,贯彻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
本卷选录荣庆的游记散文最多,这可能与他当记者时将旅行作为新闻报道方式的职业习惯有关。尽管离开了一线采访岗位,他每有出游消闲机会,总会在记“行”、记“动”中,描绘所见佳境、所闻异事、所吐快语、所出奇思妙想。由于学识功底厚实,思维敏捷,文笔灵动散漫,故所写散文游记不同于记者,多了学术深度;不同于学者,多了流光溢彩的韵致;不同于作家,多了现场感与理性的沉思。
荣庆年逾古稀赴澳大利亚探亲中创作的《金合欢国里且徜徉》《黑天鹅啊,“命定”的精灵》《揽得澳洲月,带回古长安》《格里芬湖畔那座山,那座大厦》《我与考拉合影》《悉尼歌剧院的遐想》《大洋路看洋》等,将异域风情、文史掌故、山河瀚海、虫鸟花卉揽于笔端,时而拈来与祖国物事比较,收放开阖自如。即使写香港、澳门的《九龙城寨的最后一瞥》《大屿山礼佛》《香港赏灯》《“试向番僧问,谁能识此关?”》《澳门莲,常相忆》《海湾搅胜》等,一景一物亦随其身行目视而呈现异趣横生的动态美。写境外的篇章虽然不多,但在字里行间洋溢了对故土、祖国的眷恋和对中华文化的挚爱。
荣庆写大西北的游记题材甚多。从新疆的吐鲁番、天山、喀纳斯湖,甘肃的敦煌、阳关、永登、石马坪、麦积山、南郭寺,到宁夏的西夏王陵、中卫,内蒙古的成陵,大漠草原、数千年史迹与英豪业绩,在他笔下,发前人之所未发,温古而出新知,抒个人之感慨与情思,一切都变“活”了。写江南的篇章并不多,《张家界走笔》《年逾古稀登武当》《西湖觅戏》《千岛湖观日出》等,却面对前人一写再写的套路,作者另辟蹊径,如在西湖寻找千百年戏曲故事的脉络遗迹,在千岛湖观赏喷薄而出的朝阳,故能出奇制胜。
作者是秦地人,书写三秦游记多乃情理中事。这同工作间隙与友人、节假日与家人出行方便有关。他勤奋,踏进名山佳境,决不空归。所到之处,总会将人们耳熟能详的景象、物事来个“冷不丁”的自考、自问、自答。由于写时不落俗套,心得不同凡响,学识宏博,文笔优美,让人读来忍不住神情一振。《紫柏山问道》《拜将坛上读韩信》《金丝大峡谷畅行曲》《仙娥湖泛舟》等陕南游记,《统万城,一部沙埋一千六百年的大书》《镇北台上望长城》《白云观看大河》《红碱淖乘舟记》《貂蝉与米脂婆姨》《闯王行宫游》等陕北游记,着眼于情境交融中的地理人文史迹考证、钩沉,文散旨远,言浅意深,别具一格。写秦岭与关中的《在河之洲》《龙门朝圣》《华山红豆》《西上太白峰》《秋风习习傥骆道》《玉山行》《驱车五丈原》《周家大院观光记》《寻访杨虎城故居》《磻溪钓鱼台的隐秘》《龙门洞探微》《回望郑国渠首》《关山草原:一本厚重的史册》等人们所熟知的名胜地,作者采用陌生化的手法,即从游人熟视无睹中寻找其不熟悉的视点,在开掘中出新出彩出奇,形成“故地故景出新章,异情异趣费思量”的文本。
本卷选录荣庆写景状物的纯散文《我家的蟹爪莲》《塞柳》《紫荆》《银杏啊,银杏》《藤》《雪中牡丹》等,篇目虽少,但用托物寄情的象征手法,自然而不牵强,巧妙而不涩枯,深沉而富情趣,显示了学识、历练及人格力量的厚积薄发。他写的叙事散文《吾母最爱牡丹花》《碑》《洋洋》《看泰戏》《我的书斋》《买书》《圆梦马球场》《想见母亲》等,在洒脱轻松的笔调里,描绘故事细节,勾勒生活画面,顺势抒发母子情、父子情、母女情、爷孙情、民族情、家国情,写得那么深入肺腑,动人心魄。
荣庆平日不苟言笑、学人式沉思冷峻的外表与狂放不羁、作家式激情澎湃的内心,在散文里和谐统一了。
《骊山记胜》卷校阅札记
本卷原以《骊山的天籁地籁人籁》为名,取自《庄子·齐物论》子綦曰:“女(汝)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后人常以天籁指诗歌不事雕琢,得自然之趣。作者借“骊山的天籁地籁人籁”包含了故乡的时空,兼及对骊山史事、人物、景致、逸闻探本溯源,务求归真之旨。印刷前夕易卷名曰《骊山记胜》,则较为平实易懂。
本卷将作者有关骊山的散文、随笔、札记辑录在一起,读来不乏人文科学的深沉思忖与美学享受。
《从骊山到天水追索中国八千年文明》《骊山温泉利用史揭秘》《周武王征商簋》《骊山烽火戏诸侯与西周灭亡》《骊山秦东陵考及报道》《铜人与铜人原》《秦始皇陵地宫》《秦始皇地下陈兵军幕》《秦俑修复掠影》《秦始皇铜立车的清理与修复》《秦兵马俑一号坑复掘写真》《重回人间阅春色——秦始皇兵马俑坑全貌前瞻》《骊山鱼池湾》等篇,直接取材于田野考古。但荣庆并未囿于勘测、发掘资料,而是将现场观察、考古文物、前人成果、文献记载与自我学识参详比较,连类求同,鉴别索异,做力所能及的探究与考释,发现他人未揭、未明、未道之秘。即使考古新闻,也不是有闻必录,人云亦云,而是着力于探求历史的真实面貌。这类文章大多依据最新的考古发掘资料,论证充分,学术含量高,见解独到,又文笔晓畅,鲜活耐读。例如,一些外国学者对“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尚且提出质疑,为什么作者竟然从家乡骊山开始,“追索中国八千年文明”?这是异端邪说、虚幻浮靡之论么?读罢文章,你就会尽扫心头云翳而豁然开朗。又如学界对依据神话传说论定中国人使用地热水始自秦皇、汉武尚且犹豫难决,为什么作者敢于说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原始先民就使用温泉了?读了《骊山温泉利用史揭秘》你也会心中了然而踏实。
状写天籁地籁人籁的原始本真,是人文学者的科学探索过程,需要求真的立场与严谨的治学态度,来不得半点虚伪与文过饰非。荣庆对自己或他人过去所写文章中的误判、误书或存疑问题,实事求是,勇敢面对,决不自欺欺人。本卷所收《郦道元及其遇害地阴盘驿亭再考》一文,是他自己纠正自己几十年前发表在综合性学术刊物《人文杂志》上关于此事考据失误的专文。虽然那个失误似乎已被学术界接受、并被国内一流郦学家在其专著中引用,但作者还是采取了“做一个本色的不掺假的学人”的态度,写了这篇“再考”的自纠文章。
骊山的历史文化名山地位,使一系列发生在这里的重大事件进入了权威的历史教科书和学术著作。作者在撰写本卷的一些篇章时,遇到了与某些前人、名著、权威学者观点相冲撞或相悖逆的问题。他没有回避与偷巧,而是以科学态度与无畏精神,著文直陈己见。如《骊戎国与“骊姬之乱”》一文,他提出与顾颉刚先生的不同看法;《杜甫与新丰杜甫沟》一文,他提出与郭沫若先生的不同看法;《“秦置丽邑”考辨》一文,他提出与林剑鸣先生的不同看法;《秦都栎阳》一文,他与当代国内一些著名学者争论;《扁鹊与骊山扁鹊墓》一文公开否定了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省方志的记载;《骊山秦始皇坑儒谷》及答《少年文史报》读者问,力主秦始皇两次坑儒说;《他的名字与辛亥革命连在一起》一文,力主郭希仁是爱国而开放的陕西辛亥革命元勋、“近代大儒”,不能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那样定性为“反动”人物等。不管最终争论结果如何,其坚持唯物史观,坚守学者本色,追求真理,不盲目迷信权威的文人风骨,令人感佩。
秦始皇兵马俑是谁发现的?西汉灞桥纸的发现是真的吗?谁在保护西安明城墙上功不可没?诸如此类议题,因功利与权位的缘由,曾先后在媒体触发过激烈争论。作者在《骊山寻宝者》《他与洛阳铲相伴终生》《多好的武老,多好的长者》等篇章里,以大量事实作深入的科学考辨,得出了合乎实际的结论。《雄哉,伯雄!》与《寻找撬动地球的支点——魏效荣印象》等散文,在和盘托出人物个性中解析了两位骊山籍学者攻取世界难题的执著。《骊宫葬梅妃及〈梅妃传〉略考》一文,依据相关史籍,考证梅妃其人,提出自己的创见。《“骊宫祸胎”表里》《唐梨园弟子在骊山的故事》,幽默风趣,蕴藏思辨,别具文风。《骊山虎斑石与兵諫亭》一文,对西安事变这一改变中国历史轨迹的重大事件中各当事人居功诿过的歧说,作者逐一鉴别比较,发表了客观真实的独到见解。他说,这就是人籁,有了人籁,才可能揭示地籁、天籁。
KiNEbsZbSl6U1gl57N1qxOgHEwyvsiAa7I62DWdAAnw=读《骊山记胜》卷,深感作者在绘景记事中,运用诗文、典籍、文物考古、地望勘验、人物对接印证等综合分析、辩证思考的方式,坚持当本色学人,写本色文章的标准,书写了与骊山相关的女娲氏、周武王、周幽王与褒姒、秦孝公与商鞅、骊姬、扁鹊、秦始皇、吕不韦、李斯、赵高、秦二世、邵平、汉高祖、项羽、冯衍、班婕妤、杨沛、贾洪、郦道元、唐太宗、李靖、张俭、马周、韦嗣立、唐玄宗与杨贵妃、梅妃、僧一行、李白、杜甫、王维、王昌龄、储光羲、杜牧、李商隐、王建、段秀实、张载、苏轼、赵统、康熙、鲁迅、胡景翼、冯玉祥、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等人物的作为。用这种科学态度写出的散文、随笔、游记、小品,形式活泼,内容真实,学识博雅,耐人寻味。从一定意义上说,《骊山记胜》卷也是一部绚丽多彩的地方性历史地理著作。它弥补了史志文献的缺失,足可以作为一方乡土教材和旅游指南之用。
一个人的生命有限,其对社会贡献的大小,并不能以官位高低、金钱多寡、处境顺逆决定。刘荣庆的两卷本《新闻民俗学》四卷本《从新闻黑洞跳进又跳出》,还有手头正在修改、编辑的《中国古代戏剧史述略》《长安美术通史》《报人说报》三部著作,集中反映了一个学人的“中国心”“民族情”。他外表瘦削却在艰困的生存中奋力书写。事物相反相成。老子云:“上善若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此乃柔德也;故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坚。”要征服、摧垮、磨灭这样似乎羸弱得不堪一击的生命,其实是很难很难的。这就是我与荣庆相识相交40余年体察之所得,也是我看稿之后想表明的心语。是为序。
附刘荣庆先生《题记》:
周至李君三槐,本余挚友,乃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退休学人。此序乃其连续不辍三个春夏秋冬披阅拙稿之札记也。弟妹刘佩兰扶病鼓励夫君为友无私效劳。《新闻民俗学》《从新闻黑洞跳进又跳出》两书300余万言里,也渗透了三槐、佩兰伉俪的心血。感恩无以为报,赋诗以铭:莫道人情如纸薄,天赐挚友谁胜我?两度困厄君扶勉,三尺书稿汝披阅。自古序文多应景,罕见心语娓娓说。人生但逢一知己,敞开胸襟共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