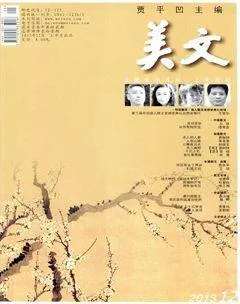有风景和温度的世界
2013-12-29杨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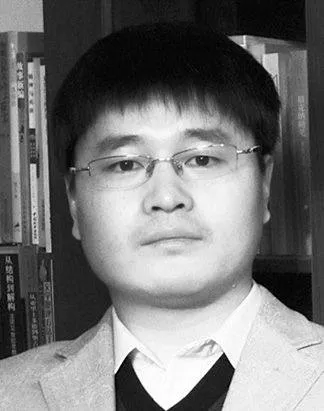
杨辉
1979年生,陕西蓝田人。陕西师范大学文艺与文化传播学在读博士,西安科技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教师。发表论文及小说多篇,著有《终南有仙真》《小说的智慧》《骊山释道》等。
若以“作意”论,唐兴顺的散文,大抵可以归入“性灵”一路,也有些“闲适”的味道,但却不似坊间的帮闲文字。虽说志在山林,毕竟还“心存魏阙”,若无这般怀抱,大概没必要“脱开社会网络,由情任性,把只属于草木虫鱼、虎豹豺狼平等的那个自己袒露出来”“解去社会盔甲,剥掉面具伪装,进入精神的后花园”,做个自在的“自然人”,能作裸体之舞,去唱自然之歌。有淡泊情怀,具平常心,且“把心比做一面镜子”,因为四季的来复,阴阳的配合,昼夜的循环而升腾坠落,藉此“实现精神上的华贵与完善”。此等用心,与卓吾老“凡为学皆为穷究自己生死根因,探讨自家性命下落”庶几近之,也不乏欧阳修“止于润身”的文学意趣。
但这一类文章,的确“易学而难工”。自然山水,原本无“境界”,无“气韵”,无“道理”,所谓境界气韵道理,全在人心妙悟。恽南田《题洁庵图》说:“谛视斯境,一草一树、一丘一壑,皆洁庵灵想之所独辟,总非人间所有。”乃画家“游心之所在”,这“游心之所在”,便是其独辟之境。境界之出,总还要归到“人心”二字。此亦是考校作者人格识见,境界修为的紧要处,无此则开口便俗,落笔即入他人窠臼。反之,也最见智慧性情。
唐先生多年来苦心经营自家山水,有雄心把太行山尽收囊中。大约得了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胸襟,“私下里以为所见山川之物,心有所会者,已被我据为己有。”对“美景美物,用目三观:上、中、下,形、态、神,不迁不移,已裹囊中矣。”即便“别人讥我痴顽,我却以满腹山川为富,以藏而不露为珍,很是有些得意。”有此心胸,伸纸弄笔,写景状物,自然不难“妙发性灵,独拔怀抱”。举凡山水草木、烟霞泉石,无不活泼泼如在目前,且多有意味生趣,是唐先生文章的显眼处。如《山林访谈初记》等篇章,是可以做博物志、精神史来读的。
因着对古寺“殿前无灯凭月照,山门不锁待云封”一联的欣赏,唐先生感慨道“我们红尘中的文人这样摆弄那样摆弄,终究弄不出大气来。”“大气”的确不是能“摆弄出”的。贾平凹先生谈文章做法时曾说,佛是“修”得的,不是“炼”出的。文人喜好摆弄,所失也在一“炼”字。大约是为根除此弊,唐先生写《梦幻山顶》时,就少了些摆弄心,多了一份呈现的自然。“暮色降临时,天上的星光如万千灯盏分外明亮,村后有一道土岭朦朦胧胧,那暗影的轮廓很像一头卧着的熊猫。村庄正好被挽在它弯曲的怀抱里。从时间上看夜色应该加深时,山顶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黑暗,星星更多了,光亮之色如流霜萤火似乎反倒更重了。站在那熊猫的头部向山下望,看到盆地里的万家灯火,在盆地边沿与天上的星群相互连接,天地成为一体。” “走在山崖边上的小路上,看到山下灯火已熄灭了许多,月亮却从盆地的一片黑暗中升腾起来。曲曲折折的山檐上已经抹上了一线光亮,眼前一些人家的房脊上,墙体的上半部分有的也被月亮照上了。而且这光亮正在渐次扩大。”这样有灵性,有韵味,几达意与境浑,物我两忘的文字,如今很少有人能做了。
看谷子的老人身上大约寄托着唐先生对土地和劳作怀旧式的热爱。而云儿的出场,一如沈从文先生《边城》中的翠翠,结局却如同《长河》中夭夭命运的续写。这一思路,与诗人海子“麦地”“乡村”之喻颇为相似,也有着贾平凹先生早年作品的理路情思。以此思路描画人事,或许暗含着唐先生对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的巨大隐喻。但他是否有接续已然隐去的沈从文传统的用心,不好判定。这类作品的出现是否意味着当代文学乡土叙事诗性精神的重启,一时也难有定见。但唐先生内心的矛盾和文字的志向,倒不难领会。
唐先生自谓在当今文坛,最心仪的是贾平凹先生,不但折服于贾先生的才情,还喜欢其“传统的美学取向”。读罢唐先生大部分旧文新作之后,我以为,唐先生不仅得了贾先生文章中的禅思,也以自己的方式重启了古人山水诗文的意趣。我爱读唐先生的文字。全因他的文章中,藏着一个有风景和温度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