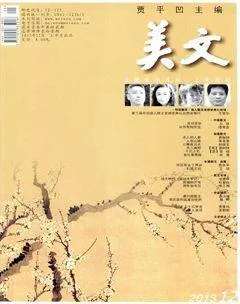烛光映照《柴达木手记》
2013-12-29甘建华

甘建华
生于1963年,湖南衡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湖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衡阳日报社高级编辑,衡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系客座教授,南华大学衡湘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出版《西部之西》《天下好人》《铁血之剑》等十余部著作,先后获得“青海省首届青年文学奖”“湖南省第三届十佳新闻工作者”等荣誉。
如果李若冰从中央文讲所结业后,直接走进《人民文学》的大门,作为编辑,他一生会有什么建树,这就不得而知了。至少在我看来,他不会深情而专注地将柴达木的神奇瑰丽与拓荒者的勇敢豪迈展示给千百万读者。同时,柴达木作为“中国第二个最可爱的人”的崇高荣誉也不会如期而至,不会对他抱有特别的感激之情。他在柴达木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以致于强化了我们对于生活的感觉。我们无法设想柴达木可以没有李若冰。
事实上,他是整个盆地创业春秋的忠实见证人。他热爱柴达木,对柴达木的一切了若指掌。作为当年的一名勘探副大队长,他“与地质、测量、钻井、地震、重磁力等地球物理勘探者在一起的时候,几乎忘记自己是一个文学工作者,而想的最多的是勘探工作的进度、成果和发展”。穹隆背斜构造的圈闭状况,探井的地层和储油条件,地震发现的潜伏构造,等等,他都以自己的目光观察过,无一忽略。
他最早的笔名叫沙驼铃——这是他在延安时的用名。有一次,在延安南门外,他蓦然发现一支长长的骆驼队,昂着高高的头颅,驮着很重很重的东西,一步步地走向沙漠深处。骆驼队远去了,可那丁当丁当的驼铃声,还在他的耳边鸣响,以致时常回响在他的梦中。这是一种机缘,也是来自心灵的召唤,良心的声音和对未来的信念,不允许一个作家不听从这种召唤,使命感和内在的动力激励着他去经受磨难,创造出令人眩目的奇迹。追随骆驼的踪迹,他只能自觉不自觉地奔往大漠戈壁。偏远的陕北山沟,寂寥的河西走廊,人迹罕至的柴达木,荒芜的松辽盆地,不为人知的古潜山油田,以及正在开发的大港油田和渤海湾、塔克拉玛干,都留下了他风尘仆仆的足迹,写下了大量的散发出沁人心脾的石油芳香的作品,以此成就了他的名家之路。
要是不嫌麻烦的话,我们把李若冰的全部作品仔细地读一遍,那么就会发现,他至今问世的著作,只不过是他对这个世界和生活的见识的极小一部分。他那博大恢弘的思想和广博精深的知识尚在不断表达中,最健全的理智促使他永远创造,泽被后世文人。
对于我来说,李若冰是我的文学向导,甚至可以说是我不断追求的征途上一盏迢远的明灯。在冷湖四月的夜岚里,因为停电,我借着大红烛阅读《柴达木手记》,为一颗自由的灵魂而激动不已。三个通宵达旦,烛泪状如假山。透过烛光,我依稀看到了五十年代一位英俊的青年作家,纵横驰骋在广袤无垠的西部大漠。茶卡、噶尔穆、大小柴旦、阿尔金山、冷湖、茫崖,在印上他的足迹时,也烙印了时代的履历。那个时代需要忠实地记录奇迹、变化、脉搏,李若冰做到了这一点,并让我们饱览了盆地的风光,分享了戈壁的豪情。
要写李若冰是困难的。尽管他自谦为“一个普通的文学战士”,然而他作品的魅力却长期留在人们心中,产生隽永的回味。读他的作品,我们仿佛面对昆仑和祁连两座雄伟高峻的大山,只有用心默读,反复咀嚼,才会有幡然醒悟之感。
唐代边塞诗开一代新河,其主要特征便是新的题材内容的选择与艺术境界的升华。在悲壮雄浑的胡笳声中,我们不但看到边关狼烟与将士骁骑,也感应到了祖国西北边陲的壮丽河山。可以说,李若冰与岑参、高适一脉相承,但他更集中、更广泛地描摹了柴达木的景与人,表现了创作与时代的自然和谐。
我的父亲甘琳,一位五十年代深受李若冰影响,为他笔下的雪山、盐湖、戈壁、草原所倾倒的军转干部,毅然辞掉家乡的舒适工作,踏上了漫漫西去长路。他床头摆着的《柴达木手记》,如今已经破损卷边,成了弥足珍贵的纪念品。父亲对我说:“读这部作品,青年时觉得平淡无奇,中年时似有所悟,到了退休之际重读,由不得人击节赞赏,掉下一腔热泪。”在跟父亲进一步交谈后,我体验到了五十年代勘探队员特有的激情,也明白了不可替代的李若冰的魅力。
产生经久魅力的作品,一个重要的因素,不外乎情感的全部投入。对作家标准的衡量,在社会主义文艺看来,不仅应探索生活的美,更应把人类隐秘的情感揭示出来,洞烛它们别于一般的内涵,进一步加深对生活的理解。
作为柴达木的历史见证人,李若冰参与了不同时代的盆地岁月。他数次西进,迎着高寒地带的风尘,以一个自愿的勘探者──自然美和人物心灵美的勘探者的身份,踏遍戈壁,收获甚丰。
李若冰的作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写的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亲眼看到的和心灵感到激荡的事物。”
我随手翻到《油泉子赞歌》,一段文字深深地吸引了我:
原油呈墨绿色,从井孔喷出来,抛在黄沙上,阳光一照,琳琅满目。这时候,我眼望着井口,体会了一种幸福的心情,这就是等待喷油的那一瞬间的心情。你心跳着,等待着,突然,油喷起了,你多喜欢呀!可是,它又落下去了,于是你又心跳着,等待着。……我的朋友,这原油是我们勘探者的血汗结晶,这原油是从沉寂了万年的荒漠里喷起来的啊!
油泉子是柴达木盆地第一个石油探区,勘探者抹去了大沙漠的荒凉景象。最拨人心弦的乐曲,是油从井底喷起的时候。在这里,李若冰那无法比拟的激动心情,通过朴素的语言表达感染了我们。在常见的记载中,原油都被称为黑石油。但在李若冰诗意的眼光中,原油居然呈现为墨绿色。为此,我请问过许多专家,他们想了想,颔首赞同。
类似以上的独具慧眼不计其数。“勘探者的血汗结晶”,这样金子般的语言,折映出作者的才情,也反射出他对拓荒者的崇高敬意和对新生活的热爱之情。
李若冰的作品完全有权利称为柴达木极具价值的文献资料。在文化沙漠上,李若冰之后,我们很少见到如此真实、充满激情和文采的作品。李若冰对盆地的一往情深,也正如他在一封文艺书简中所谈:“这儿每一片戈壁,每一条河流,甚至那一棵棵骆驼草,和一簇簇白刺花,对于我们都是亲切的、可爱的。”
在其名篇《在柴达木盆地》中,李若冰这样写道:
通往西北方的道路是荒凉的。一个人也看不见。前面是一望无际的戈壁。那被狂风吹起的小沙丘,和戈壁中孤独低矮的小树,时常会叫人迷惑一阵子。有时候,突然,眼前会闪过去一群惊慌的黄羊儿,它们飞跑着,白色的尾巴像小流星似的。有时候,一群野骆驼横立在大道上,痴呆地了望着,当人要接近的时候,它们才摇摆着头,拖起步子,向山野迅速地却又笨拙地跑去了。
到过柴达木的人,尤其是五十年代挺进柴达木的勘探队员,都会惊叹作家那种非同一般的洞察力和写景状物之功力。在准确、简朴的叙述中,我们也洞悉到了李若冰对自然环境的粗细勾勒和对自然美的由衷赞叹。黑格尔认为:“自然美只是为其对象而美……为我们,为审美的意识而美。”当李若冰全身心倾情于自然时,大漠、戈壁、黄羊、骆驼等具象物也折射出了作家的深情挚爱。这是现实主义的深远影响,也是浪漫主义的熏陶所致。
遗憾的是,当年随处可见的生物,譬如野骆驼,如今基本上绝迹了。今天乃至以后,倘若重读柴达木的历史,我们只能从李若冰的作品中了解到这些了。李若冰作品的魅力,其中之一盖在于此。
在长期的野外生活中,李若冰袒露赤诚的胸膛拥抱柴达木,这有别于那些离不开都市生活的作家。在那些人的笔下,柴达木作为蛮荒之地迄今依旧偏居西北一隅,菱形山系围绕的20万平方公里土地,无所谓过去与现在,更难以看到诱人的前景。他们的语言滞涩,文思枯竭,当然也就不难理解了。注重向人民学习的李若冰,立足现实的高地鸟瞰柴达木,以宽广的胸怀容纳一切,既看到了严酷的生存条件这一面,同时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宝藏的不断被开发。他有一句话已成为名言,常被各级领导干部所引用。他说:“谁只要来到柴达木盆地,谁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们的去处。”
我曾在冷湖待过七个年头。在那七年中,我作为一名记者,自始至终关注着那儿的一切,经历了诸多磨难和隐痛,努力去把握当地的结构与精神。关于冷湖的历史变迁,我尽可能相信文字记载。可以说,我查阅了那儿尽可能找到的各类资料,包括无甚价值的《革命造反》《红色电波》等“文革”派性报纸。但是,我很少见到真实、客观、公允地描述当地的文章。李若冰是例外。第一篇状写冷湖的作品,即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便是李若冰的《冷湖的星塔》。这篇文章使我知道了五十年代冷湖开发初期的热烈场面,也让我了解了冷湖最初的英雄人物。他诗意的才能再次凸现,竟将井架上亮着灯的钻塔,骄傲地谓之“冷湖的星塔”,确乎形象不过,使人感觉亲切无比。该作写于1957年9月26日,地点茫崖。从时间上可以知道,李若冰当时没有回他的工作单位西安作协参加反右,后来果然被迫写了检查。
多年后,冷湖油田浅层构造油藏基本打尽,挥师西去尕斯库勒。塔顶闪烁着灯光的只有高达43米的电视发射塔了,人们依然叫它“冷湖的星塔”。
由此我又想起另外一件事。李若冰为我们形象地勾勒过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地方,让我们的眼前不断幻化出其规模和形式,以及当时的具体存在状况。
因为工作需要,我常常来往于冷湖与花土沟之间。经过大风山,在相对高度不大坡势平缓的凤凰台下,有一个人称老茫崖的食宿站。叫它老茫崖,是区别于青新边界上的盛产石棉的茫崖镇。茫崖在蒙语中是“额头”的意思,由此可以想见它的地形地势。上了年纪的冷湖人总是不无自豪地提到它,仿佛在那儿待过就是一种资历。事实也的确如此。关于那段岁月,他们大都讲得比较笼统,缺乏一种叙事才能,我难以勾画出一个“帐篷城市”的全貌。何况我后来见到的只有为数不多的供来往旅客休憩打尖的几排旧土坯房,油田的几名工人,来自青海、甘肃两省的老乡,做着一种时好时淡的生意,借以打发各自悠长的日子。很冷落,也很寂寞,甚至有那么一点与世隔绝的味道。倒是那有几百上千亩的芦苇、白茨、红柳、梭梭大草地,在祁漫塔格雪峰下,展示出一种纯属荒漠的牧歌情调。然而岁月无声,老茫崖兀自孤独地立定于地球的一角。
后来,在李若冰的《茫崖——拓荒者的城市》中,我终于找到了完全的谜底。这篇文章将柴达木第一个石油基地显影出来了。以帐篷组成的厂房、商店、医院、专家招待所、中心实验室、住宅区,等等,俨然一个正规城市,逐渐复原在我们的眼前。其时,晚霞普照,黄沙漫漫,电影《董存瑞》正在上映,影院里人已挤得满满的;文化宫内正在演出工人们自己编排的歌舞;不远处的自流井旁,繁茂的小草覆盖着戈壁,情侣们正在漫步谈心;而一座亮着晕黄灯光的帐篷里,总地质师王尚文正在放大镜下观察一块乌色宝石……
这座前后存在过4年的万人“帐篷城市”,曾经庄严地承担过历史使命。相信那时定然吸引过不少文人墨客,竞相歌颂,反复吟咏,掀起过一次诗界革命。俱往矣,流传下来的作品如今只有李若冰这一篇了。这不仅是地名学上的发现,也是文学应当接近人民的具体实践。茫崖市在李若冰的笔下,闪耀出拓荒者最初的豪情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也闪耀出了昔日戈壁的奇光异彩。茫崖是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一座帐篷城市,理所当然地为全国人民所知,召引大批有志青年纷纷奔向异地,开拓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李若冰的柴达木,不管是风雪严寒,还是烈日炎炎,都同样引人入迷,心旷神怡。他的目光一刻不停地追随着自然之美与情感之花,最终将心灵感受传达给读者。他的倾诉和激情,是只属于他个人的。
“南昆仑,北祁连,山下瀚海八百里,八百里瀚海无人烟。”这是1954年之前柴达木的真实写照。
一旦大批拓荒者深入进来后,严酷的自然随之便发生了惊绝人寰的奇迹。以一个目击者和参加者的身份,李若冰将各种人物推到我们的面前,蔚为壮观地组成荒漠人物画廊。慕生忠将军、朱夏总地质师、功勋老人依沙阿吉、勘探队长葛泰生、青年地质师顾树松,等等,他们是柴达木的第一代精英人物。很难设想没有他们,柴达木的历史该如何书写。
这些精英人物,有的已经死去,有的因健康原因调到内地油田,也有的如红柳般将根深深地扎进了盆地深处。在冷湖的时候,我时常见到顾树松,这是一个精明强干、脸上老是挂着微笑的小老头。瀚海岁月,戈壁春秋,他已成为油田的总地质师。他是李若冰的“可爱的勘探朋友”,两人相识于酒泉盆地,再遇于油泉子探区。在《油泉子赞歌》中,李若冰讲述的一个故事至今还在冷湖人中间传诵,冷湖很少有人不知道这个故事的。
这是今年(按:1957年)一月,正是柴达木最冷的时候,零下三十度左右。小顾在调到油泉子以前,先帮助油砂山探区定井位去了。从茫崖基地到油砂山,有九十公里。他一个人,不戴帽子,就骑着一辆摩托车,直奔油砂山。他又爱开快车,不管冷风怎么刮得耳朵呼呼叫,仍然放大油门,用每小时六七十公里的速度飞驰着。他翻过了大山,穿过了戈壁滩,不及两个钟头的样子,就爬上油砂山了。但是,当他把井位定好以后,忽然,觉得耳朵发痒了。他一摸,麻麻木木,还有些肿疼哩。显然,他没有戴帽子,遇到冷风,又开快车,耳朵冻坏了。他还在摸,医生一看,忙说:“快不要用手摸了,再摸,就要掉了!”又连忙给他打了两针,叫他在帐房静静地憩着。半天,他再也不摸耳朵,再摸,耳朵掉下来可不是好玩的了!这一次,经验匪浅,他大概永远也不会忘记自己这段经历吧!……
想象得出来,当时面对这位朋友,李若冰一定持着又疼又爱的心情。他轻轻地触摸了一下顾树松的耳朵,说不准还责怪了几句呢:谁叫你不戴帽子的,活该!李若冰是这样的一种人,他满怀着的深厚感情,只有在面对理想一致的朋友时才会流露些许。一般地说,平时他是能注意保持自己风度的。
顾树松在这次耳朵差点被冻掉的当年底,被一场政治风暴刮到了生活的最底层,身负沉冤二十载。海晏河清的时代来临后,远在西安的李若冰给他写来了热情洋溢的信。信中说:“愿你重展翅,建设柴达木!”历史考验了两位朋友的真正友谊,也证实了李若冰对勘探岁月和勘探者的崇高敬意。
建国以后的多年,直至粉碎“四人帮”,把知识分子、科技工作者作为群体形象致力歌颂的,很少有出《柴达木手记》之右的。忠实真理,需要漫长的时间考验。而时间,总是公正无私的。在艰苦的地域创造辉煌业绩的知识分子,具有一种他人不能媲美的献身精神。朱夏从海外归来,丢下温暖的家庭去了荒漠,穿着十斤重的“铁鞋”,奔波在广袤无垠的盆地。葛泰生率领一个普查队,深入大漠腹地,因为没有沙漠生活经验,几天以后,驮的粮食吃完了,骆驼也饥渴得死了,人也迷失了方向,但最终忍住了饥饿和困苦,寻找到了一个很大的储油构造,摸索着回到了驻地。面对着这一个个英雄形象,李若冰几乎不能自抑地颤抖着写出故事,故事的深层揭示出了隐之于心的奥秘,那就是“为祖国找到大油田”的理想。理想不是外衣,而是切实的行动,它沾满了岁月的风尘,轻轻一抖,就有金箔闪烁。
酣睡了千万年的处女地上,《勘探队员之歌》终日飘扬在柴达木无遮无拦的风景线里。许多人倒下了,又有更多的人赶来了。那一块块矿石,一瓶瓶原油,一包包滑石粉,无不蕴含着一段艰苦卓绝的经历,无不凝结着勘探者的智慧,无不浸透着他们的血珠!冬夜的情思是一种高贵的情思。倾心于勘探者的李若冰,不断地从前者身上汲取力量。《柴达木手记》不但给那块遥远的地方注入了最好的诠释,也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宝库,成为独具特色的流光溢彩之作。
1991年11月8日,西安雍村。我首次登门拜访了李若冰先生,望着这位令人尊敬的“老柴达木人”,我的心里自然十分激动。他恬淡雍容的举止,轻轻而不乏力度的话语,对往事不尽地追忆,我想这是他多年的荒漠生涯所致。而只有经历过大悲大喜的人,才会出现这种神情。一部近20万字的作品,曾经唤起了无数青年对柴达木的初恋,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人们源源不断地西进,并在那儿获得一份珍贵的生活纪念,为此我们感激他,感激那部永远闪光的《柴达木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