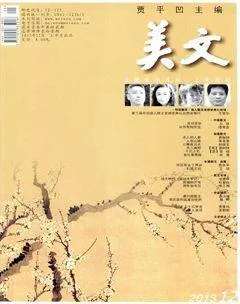疼痛的芦苇
2013-12-29杜爱民

杜爱民
现居西安。著有《非此非彼》《眼睛的沉默》《马语》《西安往事》《你的城市以西》等。现任西安市文联副主席。
关于大学精神和大学使命,学界多年前已展开过集中的研究和辩论。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学术共同体,涉及学校自治、教授治校与学术自由、思想独立这样的理念,也必然在文化源头上形成自己不同的指向。所谓现代“乌托邦”与没有围墙的大学之间,与当代中国大学教育现实情况所突显的问题性和问题意识都大异其趣。也许在这个问题上,目前,用下定义的方法无法得到谁都承认的结果,但这并不妨碍围绕着大学所形成的对话交流共同体的生成。也许正因如此,李浩先生才会有对于《课比天大》的言说。
与既存方式不符但又遏制不住的东西应该是能给思维以原创动力的东西。《课比天大》属非学术类的跨界写作,多以随感和片段式的思维来触及大学教育的根本,在其中李浩先生绕开了对于大学理念的宏大叙事,从现存大学教育诸多问题的交汇点入手,展开自己的反思。这些思考是零散的,即时性的,贯穿于作者的日常生活当中,其背后携带着自己不断的追问:即究竟在现实的环境中,做什么,才能有助于中国的大学教育水平的提高。
仅仅提出问题,指出其中的弊端和体制方面的缺陷还远远不够;同样,涉及当代大学教育,只从理念上进行梳理也会显得欠缺。李浩先生面对的大学问题,首先是一个个人实践的问题,从个体所处的位置和行为实践出发,来感受、认识、思考,并且改变个人范畴内的行为方式,以此来获得使既存问题得到改变的可能。
指出应试教育的种种积弊是比较容易的,重要的是解决这些问题,代之以科学教育的路径究竟又何在?李浩在《课比天大》中,记录了自己从事研究、教学、游学以及参与学校管理过程中的诸多感受与思考。“既特立独行,又滋兰树慧”,这是台湾大学校徽的启示,也是他对傅斯年的解读。在台大及傅馆、傅室和傅园、傅钟面前如缕的意绪,让他看到一介书生,将毕生精力投入学术共同的构建与管理,推动现代国家的学术自由、社会民主、政府清廉、体制规范等应当从何来担当,无疑,傅斯年的例子给了李浩以启示,也为他在此基础上展开自己的思考和个人实践提供了坐标。
谈及大学精神与大学教育,自然会形成东西方之间的文化比较,这几乎成为论及此类问题的一个固定的范式。中国的教育在脱离了苏联模式之后,尚未完全走出新的道路,拥有国子监传统和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大学,如何克服早期“速成教育”,苏联式的专业学科划分,以及当下的短视与急功近利和日趋官僚化的治理方式,必然会拿中世纪以来形成的欧洲大学传统相比较。这其中的差异和距离是明显的,也往往是在这样一个对比的语境中,才形成了当下各自对于大学改革的治理方案。李浩先生也是沿着这一路径,来展开自己对于大学的思考,所不同的是,在他的方案中,吸取了更多的中国传统与经验,那些依然有活力的思想资源,成为他构织新的大学教育网系的重要结点。
“塑造有思想的公民”或许是最大的公约数,在此基础上,李浩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教育观点:即以圆整思维来克服线型思维的单向度,建立复杂立体的科学思维,清理进化论在教育思维方面消极影响;突出大学教育的超越立场,让大学只对永恒做出承诺。围绕着对于学生的培养,李浩对育人为本,熏习树材,成己立人,顺天致性、先识后艺、知能并重、深思明辨、慈爱自觉、民胞物与和参赞化育等这些源头活水里的教育文化资源,如何在现今的大学中得到有效的贯彻,给出了自己的主张。他并非只是坐而论道,而是结合现今大学课堂教学,通识教育,经典研读,以及教材的多元化等具体实践环节上如何应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而使对大学的思考能够深入到教学实践的要害上,既有清晰的理论分析,又有操作层面的刚性设计,读来令人深受启发。
跨界式的片段思维写作,意味着另一种更为深广的历史感的汇合。与纯学术的写作不同,作者不再躲藏在文本的背后,不再是一个冷漠而又高高在上的主体。李浩在书中自称自己是一棵疼痛的芦苇,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对话者,时而以反智的方式重建被理性剔除的思维本身,时而又用自己的坚忍来经历内心黑夜式的精神体验,时而又以思维断路的火花来点燃体悟认知的烈焰。在《课比天大》里,有一个新的向度,即作者作为写作的主体,同样还在与自我的关系中得到了新的构建,而文本,正是自我与他者和外部世界相互交织的见证之地。诚如笛卡尔所言:一个作者要想通往真理,只要成为任何一个能够看到显现之物的主体,就足够了。从这一点出发,回到关于大学教育的话题,《课比天大》展现出了能够看得见和听得见,在当下真正的难度,也映射出大学教育的改革,在今天更多地应当从“无用之用”去入手。
可以把李浩在《课比天大》里的写作看成是他自身面对可能之事所做的准备。书写者把看到或听见的东西转变成了“组织或血液”;他的文本意味着自己对于所关注之物的凝视,并且已将目光对准了自己未来的读者,即那些有可能成为《课比天大》发出之后的准收信者,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