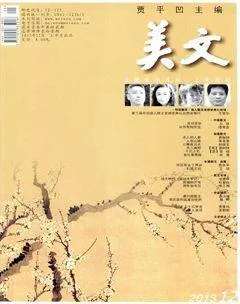天人幽明
2013-12-29宣树铮

宣树铮
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旅美文学评论家、资深编辑,曾任纽约华文作家协会主席,自由撰稿人。出国前任苏州大学中文系主任。给《世界日报·副刊》专栏写作7年;主办《彼岸》杂志7年;2007年至今一直为《侨报周刊·纽约客闲话》专栏撰稿。
翡 翠
当年拿到移民签证,除了可按规定在中国银行兑换几千元美金外,余下的人民币就“移”不出来了。向朋友打听什么地方有黑市换,朋友道,换什么黑市?何不带一些东西到那边脱手,还能赚几个钱呢!言之有理。但带什么呢?庄子《逍遥游》上说,宋国人贩帽子到越国去卖,不料“越人被发文身无所用之”。就怕货不对路。于是多方咨询,结果众说纷纭。有人说带丝巾桌布,有人说景泰蓝、紫砂壶,也有人说不如带珍珠项链、双面绣……这时候,在美国探亲一年归来的同事徐姐悄悄跟我说:“我劝你带翡翠,美国华人圈里的太太们好这玩意儿,容易脱手,带也方便。”徐姐还告诉我,她去探亲时就带了两颗翡翠戒面,赚回一张机票。不由人不动心,那就带翡翠。上哪儿弄翡翠呢?文物商店柜台里摆出不少在卖,但这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送上去挨‘宰’的茬。买这玩意儿离行家不行。就在这当口,两位朋友同时向我推荐了诸老先生,诸老吃了一辈子古玩文物翡翠宝石饭,都成了精了,如今退休在家。朋友和诸老是莫逆之交,一牵线,诸老满口应承,约了时间上门细谈。
诸老家在市中心的一条逼仄小巷里,两辆自行车交驰而过时,行人必须靠边鹄立。找到门牌号,一扇不起眼的小木门,像衣柜门,我按了门铃。从深远处传来铃声叮咚,接着是咯咯咯,咯咯咯,下楼梯的声音,咯得人心焦。开门的是一位老太太,眼睛眯得很吃力。我自报家门,老太太说“一直在等你呢!”我明知故问了一句:“你是诸师母吧?”诸师母领我摸上贴墙的小木楼梯。说“摸”,是因为门一关,又没有窗,暗昏昏如进洞穴,只有楼梯顶上落下一片黯淡的灯光。咯咯咯,上了二楼。诸师母说,二楼女儿女婿住着。咯咯咯,上了三楼,楼梯口亮着一小盏灯泡。房门正对楼梯,诸老站在门口,花白头发,中等个儿,清瘦矍铄,玳瑁边眼镜后面目光炯炯。进门靠墙一张八仙桌,墙上一幅山水中堂,笔意苍古,画两侧的对联是何绍基的字,诸老和我在八仙桌两侧坐定,诸师母倒了茶就退回去坐到双人床上。寒暄过后,诸老说:“带翡翠是好主意,黄金有价玉无价,遇上有眼缘肯出价的就脱手,不合就留在身边,保值。”诸老提起一年多前就帮苏大一位出国探亲的教授买过翡翠,一问,正是徐姐。我直截了当告诉诸老准备拿出多少钱买翡翠。诸老沉吟道:“我有数了。这样吧,我建议你还是买些戒面。如今老货是很难弄到了,只能买新货。好在郊区翡翠工场的人我极熟,我马上托他们物色,以中高档次为主,质量你放心,有我,价钱比市面上便宜一半是最起码的了。一有消息,我就通知你。”我说一切就仰仗诸老了。大家端起茶杯喝茶,算是说定了。
接下来就闲聊。我请教诸老,“祖母绿”这名称是怎么来的。诸老说,祖母绿在元朝叫助木剌,后来叫成祖母绿了。还有个说法,说祖母绿其实是驻马绿——绿得惊心骇目,马见了都要停蹄驻足。诸师母插言道,新中国成立前某家太太每次上麻将桌头上就插一支祖母绿凤头簪,照得满头乌光锃亮,赛过上了油,打牌的手气也旺。诸老朝诸师母摆摆手,摇头一笑。诸老对苏州城里原先那些世家大户的家传珍宝心里有一本账。新中国成立后,这类人家相继败落,不少珍品都三钱不值两钱卖了糊口,诸老上门看货,几乎踏遍了各家的门槛。谁家的碧玉提梁壶,谁家的朱砂斑宣德炉,谁家的成化五彩优缽罗花盘,谁家的康熙豇豆红柳叶瓶……记得清清楚楚。诸老说,“这些东西见过一面一辈子也忘不掉。”而这“谁家”都是有名有姓有地儿的。后来诸老又谈起伪造出土玉器,如何造黄土锈,造血沁,造黑斑·……“外行难免上当,”诸老用留起的长长的小指甲轻轻搔着眉毛,“这就靠见多识广,全凭经验来鉴定了。”差不多聊了两个小时,这才告辞,诸老送到楼梯口,诸师母送我咯咯下楼。
一个星期后,诸老来电话,要我去看货。跟上次一样,诸师母领我上楼,入室坐定。诸老使个眼色,诸师母从挨着南窗的一口玻璃橱里取出一个朱漆小圆盘放到桌上,诸老揭开盖在上面的宝蓝绸帕,下面一溜八颗翡翠戒面衬着铺在盘底的白绸帕碧油油放着光。诸老说:“我是按档次排放的,一号到八号。这一号二号是上品,三号也是上品,四号到八号,都属中上,”诸老翘着兰花指将一号二号捡起放入我掌心,“看翡翠要自然光,你到窗前仔细看看。”我托着翡翠小心翼翼挪步到窗前,说实话,这辈子我还从没有这么谛视过翡翠。绿得那么清匀朗润,又那么幽邃贞静,又那么灵动闪光。这绿可以配黛玉的凄俏,可以配宝钗的端丽,可以配湘云的憨美。这绿是万山深处的千寻碧潭,是让朱自清惊诧的“梅雨潭的绿”,让人沉迷摇荡,生出遐想,感到不可抗拒的诱惑。我似乎正纵身跃入碧潭,我感到了绿的柔滑,绿的凉意……“我仔细看过了,还真挑不出什么毛病,只是二号的一侧有些塌,不过镶成戒指就看不出了。”诸老的声音将我从碧潭中喊了上来。回到座位,我将翡翠放回漆盘。诸老指着三号说:“别看它小一点儿,也没有一号二号翠,但透,尤其中间的绿,布得玲珑娇俏,有韵有致。这三号就像个讨人喜欢的伶俐小姑娘。”三号比一号二号小了一圈,通体透明淡绿,在这淡绿中散布着星星深碧,恰似浅浅的一池清水,水中绿萍点点。诸老将每一颗都大致作了评论,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单子,放到桌面上,用长长的小指甲指着上面开列的每一颗的价格,加起来的总数和我准备投入的钱相差无几。“放心,物有所值!”诸老目光炯炯地看着我。
三个月后,这八颗翡翠戒面揣在妻口袋里跟我们一起到了美国。虽说中老年的东方女性偏爱翡翠,但合适的买主是可遇不可求的。好在我们也不急于求售,既然可以保值,何妨珍藏着,什么时候雅兴勃发,就取出来观赏观赏,在这碧潭中沐浴乡愁。但日子一久,兴致渐见淡薄,就很少再取出来观赏了。大约在到美国的第四个年头的春天,才迁入新居,那天望着窗外千树吐芽,万绿攒动,心尖微微一颤,竟想起了翡翠。于是找出来,先观赏一号,左看右看总觉着不对劲,一潭腻绿,原来的神采灵气哪儿去了?妻看了也有同感,她又举起对着阳光一照,不由得“啊”一声,照见了一丝裂纹。再看二号,裂纹没有,但背面出现了白点,成了柳絮池塘。人老珠黄,莫非翡翠也会在岁月中老去?八颗中间只有三号没有变,依然是个讨人喜欢的小姑娘。我们不甘心,拐了几个弯问到一位懂行的。行家说,像翡翠这类东西作伪的方法很多,可以注射颜色,可以上油,可以激光处理,科学越来越发展,作伪也越来越专业,一定要仪器才能检测,光靠眼睛,光凭经验老到是绝对不行的。不过他估计我们这几颗翡翠还不是赝品,只是加工过了,日子一久,渐渐露出了庐山真面目。除了苦笑,我们还能怎么样?自然也起过念头,将翡翠带回国,再去按诸老的门铃,讨个说法。但后来几次回国都没有带,实在怕尴尬——不管是诸老骗了我们,还是诸老被别人骗了,面对翡翠都是尴尬。
不料去年回国,我还是去按了门铃。这些年,苏州市区街巷改造日新月异,偏偏诸老的那条小巷仿佛被遗忘了。那天我走过这条逼仄小巷,两辆助动车噗噗噗,擦身交驰,我赶紧退避,像壁虎一样贴到墙上。但我发现自己贴的不是墙,而是一扇小木门,像衣柜门,这不是诸老家吗?我至今都不清楚当时怎么就会伸手去按门铃的。等听到隐隐传出来叮咚铃声就后悔起来,赶紧走吧,又觉不妥。门开了,露出一张中年妇女的脸:“找谁?” “诸老先生还住这里吗?” “我爸爸啊,过世好几年了。” “是吗?诸师母呢?” “也走了。请问你是哪一位?”我告诉她,我是外地回来,路过,顺便想看看诸老,向他讨教讨教,早先诸老帮我物色过翡翠,我也没有好好谢呢。中年妇女叹道:“别提什么翡翠了。当年苏大一位老师移居国外托我爸爸买翡翠,爸爸又托了翡翠工场的老朋友帮忙,结果拿来的翡翠是做过手脚的。爸爸没有看出来。过了两年才知道,就此气出了病,老说自己这一辈子白活了,脸丢尽了。”我道:“这也不算什么。” “就是啊,现在假的比真的还真,你能分得清吗?老人家就是想不开,郁结在心里,人越来越瘦,一年以后就走了,肝癌。”我的心陡地沉重起来,这翡翠怎么引出了肝癌?如果我不买翡翠,或者不找诸老买翡翠呢?我有些迟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对方我就是那个托她父亲买翡翠的移居国外的苏大老师。然而,中年妇女已缩回头轻轻关上了门。
江南韵
小学毕业那年暑假,父亲找人介绍了一位姓郭的先生给我补习国文。郭先生是一所补习学校的国文教师,单身一人住在学校里,说好每天下午两点至四点我上门求教,为期一月,束脩五元。
学校在一条小巷里,原是私家大宅,巷口是一家茶馆。第一天我提早赶去,只见大门敞开,门厅里坐一位老汉,像是门房,晃着蒲扇在哼《空城计》。我说我是来补习的,找郭先生。老汉将我从头看到脚,大概捉摸我是不是“司马发来的兵”,后来蒲扇一挥:“进去吧,郭先生在办公室里。”我闯进“空城”,绕屏门,越天井,登大厅,大厅右侧的厢房上钉着牌子:“办公室”。
郭先生三十光景,白面书生;他问了我一些情况后,从抽屉翻出一份油印讲义,算是教材,上面是三则古代寓言:《鹬蚌相争》《狐假虎威》以及《东郭先生》。郭先生逐句解释,我咬着牙不让自己打哈欠。钟敲三下,郭先生不讲了,我想该休息一阵子了。不料郭先生却说道:“今天就到这里。”我吞吞吐吐道:“不是两点到四点吗?”他看着我,像在斟酌什么,随后说:“你,听过书吗——说书,评弹?”“听过。”“我带你去听书去。”我也开始斟酌了,万一父亲知道了怎么办?可是父亲怎么会知道呢?于是我点了头。郭先生牵起我的手就往外走,过门厅时,老汉直了直身子说:“郭先生听书去啊?”我被牵到巷口茶馆,见茶馆门口挂着牌子,下午有两档书,大书(评话)是《英烈传》,小书(评弹)是《玉蜻蜓》,两点一刻开书,票价七分。郭先生跟茶馆的人很熟,点点头就进去了。
书场里方桌长凳,人坐了八九成,郭先生牵着我找两个空位坐下,堂倌送来一壶茶,两只茶盅。这时书台上醒木“啪”一响,说大书的艺人道一声“明日请早”,兀自下台走了。跟着说《玉蜻蜓》的上场,男女双档,男的中年,女的不过二十上下,身材苗条,穿一身月白短袖旗袍,素素净净,如一弯新月。照例女的先唱一曲开篇,然后书归正传。四点一刻散场,我直接回家。父亲问我:“先生教得怎么样?”我回得很干脆:“当然好。”
第二天,郭先生一见我就问:“昨天,《玉蜻蜓》听懂没有?”我说,“听当然听得懂就是不知到底讲的什么故事。”“坐下,我给你讲。”于是郭先生介绍全本《玉蜻蜓》,金贵升如何,三师太又如何,徐元宰又如何如何,又是庵堂认母,又是听堂夺子,等等。到他讲完,我取出讲义,昨天《东郭先生》一则还没解释完,狼已出得口袋,东郭先生正性命交关呢!谁知郭先生一点儿不急,又问我:“昨天的开篇能听懂多少?”我说,“只听出一句,好像是‘双双月下渡长江’。”郭先生笑了:“这是有名的开篇《杜十娘》。”他一边说一边拉开抽屉摸出一本《弹词开篇集锦》,一翻就翻到了《杜十娘》。郭先生把书摊在桌上,用笔点着字念给我听:“窈窕风流杜十娘,自怜身落在平康,落花无主随风舞,飞絮飘零泪数行……”后来索性讲解起来:“窈窕”作何解,“平康”何所指,为何说“落花无主”、“飞絮飘零”,讲完也就三点了。“走”,他站起来,把集锦交到我手上,“带着。”我心领神会,小书童似地跟着他出了校门。这天那“一弯新月”换了一身粉红旗袍,艳得如一片绯云,唱的开篇是《秋思》,咿咿呀呀,呜呜嗯嗯,要不是那册集锦,我一个字都听不懂。郭先生在我耳畔轻声说:“她唱的是祁调,祁莲芳。”
第三天,讲完《东郭先生》,郭先生又取出一篇讲义《冯谖客孟尝君》,说道,“明天就讲这篇。现在我给你讲讲昨天的《秋思》。”照例三点整出校门。
以后竟天天如此,先讲一节讲义,跑跑龙套,然后讲评弹。郭先生先后介绍了《描金凤》《珍珠塔》。原本他还要介绍《白蛇传》《三笑》,我得意地告诉他,许仙白娘娘,唐伯虎点秋香这些故事,我在念小学前就知道了。另外,郭先生讲了评弹的“说、噱、弹、唱”。三点一到,师生默契,赶赴茶馆。那“一弯新月”每天换一身行头,五日一循环。她常变换着唱各种曲调,这时郭先生就会凑近我耳朵一一指点,这是薛调,这是严调、蒋调、俞调、徐调……半个多月下来,《集锦》上的一些开篇我竟然能背出来,甚至能偷偷在心里哼上几句。有一天散场后,郭先生和几个熟人闲聊,我站一旁听。聊着聊着一位竟哼起了《宝玉夜探》:“隆冬寒露结成冰,月色朦胧欲断魂……”我脱口而出:“不对!是‘月色迷蒙欲断魂’。”大家朝我看,“这小朋友还是小书迷,小行家,看不出!”郭先生高兴地摸着我的头:“是我学生,他懂不少,很聪明。‘欲断魂’下边是什么?”我不假思索:“一阵阵朔风透入骨,乌洞洞大观园里冷清清……”这天,我几乎是飘回家的。
一个月匆匆而去,最后一天我按父亲的嘱咐谢了郭先生。郭先生连连摇头:“惭愧,就没有讲几篇文章。”我突然想安慰他几句:“你教我懂得了评弹。”郭先生认真起来,“这倒也是。不懂评弹就不能算道地的苏州人。你现在知道了,唱起来多优美,真正的江南韵,而且是江南第一韵!”他轻拍桌子哼着“丁格隆地冬,德勒隆里格隆地冬”,后来索性唱起了《杜十娘》:“窈窕风流杜十娘……”我也跟着他轻轻唱起来:“她自赎身躯离火坑,双双月下渡长江,那十娘偶尔把清歌发,呖呖莺声倒别有腔……”叫人回肠荡气,唱到最后“青楼女子遭欺辱,她一片浪花入渺茫,悔煞李生薄情郎”,两个人已唱得脸红耳赤。这天,郭先生带我最后听了一回书。书场出来,郭先生拍拍我肩膀说:“好好学习,以后有机会再一起听书。”然而,这机会再也没有出现过。第二年,郭先生所在的那所学校撤销了,郭先生也不知调往何处,从此相失于世途,看来命里注定只有一个月的师生缘。但40多年来,我对评弹的爱好始终不衰。我得感谢郭先生,是他,让我懂得了江南韵,成了个“道地的苏州人”——虽然我知道现在的苏州人已没有多少喜爱这江南韵了,所以对自己之是否“道地”也怀疑起来。
围 围
都叫他围围,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名实姓,也没有人想知道他的真名实姓。围围矮个子,罗圈腿,走起路来,两条腿不是直里往前迈,而是一左一右画着圈向前围去——围围这名儿就这么来的。
上世纪60年代初,我被发落到西北边城教中学,老教师向我介绍当地风土人情时,特别提到几位乡野草间的传奇人物,围围就在其中。围围是农村社员,但都知道他有未卜先知的本领。围围的未卜先知不靠相面测字、占卦问卜,他也不懂什么紫微斗数;你问他,他就答,像课堂上学生答问,而且三言两语,绝不啰嗦。远近常有人找他问事,只是每次只能问一桩事,不收钱,只收上门礼物。
围围未卜先知的传闻很多。冬天晚上,附近社员找上门来,才进院子,人还没有见,围围隔窗子喊过话去:“毛驴丢了?不碍事,天一亮自会回来的,掉两个耳朵尖。”果不其然,天亮回来了,驴耳在戈壁上冻坏了,日后两个耳朵尖掉了。
有一个年三十的农村大小伙,小时候让芨芨草戳瞎了一只眼睛,说不上婆姨。大小伙带了一条羊腿来找围围,让他指点终身大事。围围说:“十天后,套上驴车,带上‘刀把子’,往东三十里,运气好能捡个婆姨。”——当地人称白面馍馍为“刀把子”。十天后,小伙子套上驴车,带上“刀把子”,往东进了戈壁。走了近两个时辰,真见到个二十光景的大姑娘守着包袱坐在半截颓圮的土墙根里发呆。姑娘是甘肃民勤人,扒火车上新疆,结果投亲不着……大小伙送上“刀把子”,姑娘上了驴车,就这样捡了个婆姨。那是大饥荒的上世纪60年代的事。事后一算路程,也就是三十里。
最玄的是,兵团一位首长的守寡老娘,长期眼痛,百治无效。最后首长坐了吉普车来找围围。围围说:“去把你大(父亲)坟头上那棵芨芨草拔掉。”首长回去,到大坟上一看,真长了棵芨芨草,就手拔掉,老娘的眼睛从此不痛了。首长问围围,想要些什么?围围说想要两个吉普车上换下来的轮子。首长给了两个新轮子。所以围围的驴车不是一般的胶轱辘,是地道的汽车轱辘,方圆百里,独一无二。
对诸如此类的传闻我当然嗤之以鼻,无非是边城绝塞的迷信愚昧。每次议论这类传闻,总想给它一个合理主义的解释。比如捡婆姨的事,你敢说不是围围知道有个投亲不着的姑娘,于是就叫她在三十里地候着?学校里教俄语的霍老师是本地人,说起围围就啧啧称奇。我和他常为此抬杠。老霍说,他原先也不信,有一回特意跟朋友上围围家,存心去试一试。围围坐在炕上,看了他一眼,道:“‘储搭子’里揣着四元两角钱,八两粮票,来试我围围?”“储搭子”是当地土话,口袋的意思。老霍自己都不清楚只袋里有多少钱钞粮票,于是当场摸出来点,竟分毫不差!“你怎么解释?怎么解释?他懵对了?你也懵给我看看!”我虽然没法解释,但坚持“唯物主义”:“总而言之,你不是被懵了就是被耍了。说不定跟你一起的朋友偷偷看过你的口袋,告诉了围围。”“不可能!”老霍叫起来。谁也说服不了谁。老霍道:“哪天我带你去见见围围。”
围围是上山公社的社员,住在靠山的戈壁上。打县城骑自行车差不多要一整天,一路又是上坡。所以尽管老霍说了几次“哪天我带你去见见围围”,这“哪天”始终是未定之天。一直到“文革”前一年,支援夏收,我和老霍一起到上山公社戈壁地割麦子。割了半个来月,完成任务,原说次日公社派拖拉机送我们回城,不料晚上来了通知,说明天拖拉机来不了,要我们多待一天。老霍来找我:“围围离这儿不远,走路半个来小时,明天我带你去,去不去?”我回答得很干脆:“为什么不去?”
第二天我们吃了早饭上路,先拐到供销社买了两包饼干。天清气爽,纤尘不染,放眼望去,戈壁空旷,村落稀疏。老霍指着一个村点:“围围家就在那里,”他早打听好了。走了半个钟点就到了。这村点总共十来户人家,院墙互不相挨。围围家院墙外立着一排钻天杨,潇洒挺拔。院门开着,望进去,一明两暗三间土坯房。一头黄狗朝我们汪汪吠了两声就呜呜个不停。屋里走出一个五十好几的妇人,朝我们点点头:“来啦,进屋去。”她自己却往外走,出了院门,黄狗跟着出去了。老霍告诉我,那妇人肯定是围围的老姐,围围和姐姐住一起,全靠她照料。
我们一踏进屋,就听见咳嗽声从左边蓝布门帘里传出来,咳嗽过后是沙哑的说话声:“中学的两位老师吧,进里屋来坐。”我们掀门帘进去,只见炕上坐着个人,正抽莫合烟,个头就像十二三岁的娃娃,无疑就是围围了。我感到吃惊:围围干巴起皱的脸上竟闪着一双明亮温润的大眼,像戈壁上两眼泉。简直不可思议!围围一身泛白的蓝布中山装,整整齐齐,纽扣扣到脖子根。
“坐下”他指了指靠墙的桌凳,桌上备着烟茶。围围看着老霍说:“这位霍老师四年前来过。”又看了看我说:“这位老师初次见面。”老霍指着我问围围:“你看这老师是哪儿人?”“你是塞北,他就是江南,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老霍得意地碰了碰我胳膊。“两位老师是不是要问什么事?我马上就要上公社卫生院去。”
老霍先问:“我该朝哪个方向去找对象?”老霍快三十了,别人跟他介绍过几个女的都没有成功。但听他这一问我忍不住嘿哧笑出了声,他也想吆车三十里去捡个婆姨?这小子!围围一双大眼盯着老霍看,缓缓道,“哪儿找婆姨?到你走过的路上去找,你们同过路啊。”这双大眼转到我脸上:“这位老师有什么要问的?”我本不想问什么,只好临时扯个题目:“你看我往后这辈子怎么样?”“过十年再说。人要会熬,熬才能出头。”说完这几句,围围就一言不发只管抽烟。
人也见了,话也问了,我示意老霍:走吧。我们将两包饼干放桌上,起身告辞。围围两条腿一伸,顺炕沿挂下,两手再一撑,就跳到了地上。他个子到我胸前。他送我们出屋,迟疑了一下,又送我们出了院子,两条腿画着圈,一左一右往前围得飞快。
往回走的路上,我笑着提醒老霍:“留点儿神,这可是走过的路啊。”“要同过路的。”我们又抬起杠来。我说围围的话摆明是江湖诀。但老霍觉得迟早会应验的,回头一看就会恍然大悟。“你说,”老霍问我,“围围还没有见我们人,怎么就知道我和你是教师?”我说:“我们上这儿都割了半个月麦子了,围围能不知道?猜也猜得出来。”“他怎么会知道你是江南人?还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看人的模样我也能懵个八九不离十!
第二年“文革”一开始,围围就成了牛鬼蛇神被公社造反派揪出来游乡。据说,游乡前一天,围围就给自己糊了顶高帽。第二天造反派问他:“谁告诉你今天要游乡的?”围围答道:“不用人告诉我。”游乡的时候,他罗圈着腿,围着步子,走得挺利索。后来又听说,围围是口里来的逃亡地主;再后来,干脆就不再听说了。
“文革”结束,老霍告诉我,围围在“文革”中死了。老霍在“文革”中成了家,女方是小学同班同学。“围围说我的对象在我走过的路上,跟我同过路,真说着了。”老霍感慨万千。这一回我没有跟他抬杠,我想起了围围说的“过十年再说”。“文革”不正是十年?而且总算熬过来了。难道围围那双不可思议的大眼睛真能遍观过去未来,洞悉天人幽明?我实在不愿意相信。
祈 梦
1月8日夜,我梦见了父亲:父亲瘦削的身影正从我房间出去,手扶门框站了好一阵,一闪而逝。我起身推开椅子追出房门,门外本该是一个空房间,但这会儿成了一条灰绿的小河,父亲的身影已在河对岸了。河上没有桥,河里没有船,周围没有人,我喊,没有声音。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已在一条昏暗的长弄堂里了。我慌慌张张朝弄堂一头奔去,奔出弄堂,原来是地铁出口,眼前灯光闪耀,俨然是曼哈顿的夜景——蓦然醒来,头脑清澈如水晶球,马上记起了1月8日可不正是父亲20周年忌辰?而梦里父亲手扶门框的身影不正是22年前的一幕?那是我今生的恨事!
1979年春,我从新疆调回苏州,父亲心满意足:总算耄耋之年有个儿子守在身边了。打我上大学算起,二十来年中,父子相聚的日子不足十一。童年时对父亲的敬畏固然已消化在自己成长的岁月中,但还是留下了隔阂的残渣。平时除了谈几句日用家常,或者听父亲偶尔讲讲父亲认为必须让我知道的深埋的往事,其余的话题实在也寥寥。有一次父亲问我:“你念中文,当初学校里教不教作诗填词?”父亲指的自然是旧体诗词。我说:“不教这些的。”“那么平仄也不懂了?”“诗词格律是要学一些的,也是皮毛。”“那么你们5年都学些什么?”我看出了父亲的失望。我想告诉父亲学了些什么,但又觉得徒费口舌,于是笼统地说:“要学的东西其实再一个5年也学不完。”父亲摇了摇头。
父亲的生活很规律,每天早饭后,休息一阵,正9点拄了拐杖上街转转,这一转差不多要11点光景才回家。当时苏州街道不像现在,街面虽然铺了柏油,人行道依然是七高八低的碎石,硌脚,而且窄,两边的住家店铺再稍加蚕食,行人就被纷纷逼下街面。有一年父亲被一个姑娘骑自行车从背后撞倒,卧床数月,从此父亲上街一律靠左走,这样不需防备后方偷袭,只要避开前方攻击就可以了。父亲说,“这也叫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我和妻每天上班,两个孩子上小学,买菜做饭托付给女佣王妈,一个六十开外的乡下妇女。我上班比较自由,如果没有课,不开会,上午打个招呼,下午就可以关家里,躲进小楼成一统,看看书,备备课。这时候,父亲很少打扰,偶尔到门口张望一下就走了,听脚步声就知道。
有这么一天我正在房里看书,听到脚步声响了几回。在我靠在椅背上小憩仰望天花板的时候,脚步声进了房间。父亲站到我跟前说:“有句话要跟你们说。”我问什么话,父亲说:“我看王妈的手脚不干净,要留个心眼。去年大圆桶里的汤婆子、脚炉都不见了,再也没有找到——”“说不定‘文革’中弄掉的。”我说。“不会,1976年冬天汤婆子还拿出来用过,1977年开始用盐水瓶了,汤婆子这才不用,一直放在圆桶里的。这不去说它。昨天我打开几只箱子,几件小人穿的毛线衫、毛线裤统统不见了。这还是前两年你大姐织的,本来要寄给你们,后来一直说你们要回来了,就没有寄。清清楚楚放在箱子里,没有动过。我看你给王妈说说,让她心里有个数。别让她觉得一家都是糊里糊涂的大好人,以后就更不得了了。”我摇头:“我不去说,没有证据,怎么咬定是她?”“那还能是谁?还有一回我发现大橱的抽屉被人开过后,再没有关严。我开抽屉总是关严的。还要用手摸摸合缝了没有。你们还没有回来,你说还能是谁?”“不见东西了没有呢?”“就是这话,记性不好了,少了东西也不会知道了。所以后来就上锁了。”我想,老年人就是多疑。父亲说:“看人只要看眼气,看王妈的眼气,一双肉里眼,就知道是个厉害角色。”
父亲所谓的“眼气”,大概是指一个人眼睛里流露出的人品的优劣善恶。说实话,我也不喜欢王妈的“眼气”,女儿第一回见王妈后就偷偷说:“王妈像只老猫,眼睛最像。”但毕竟不能以“眼气”定人善恶。我哗啦哗啦翻起书来,说:“我看算了吧。”父亲一定看出了我的不以为然和不耐烦,说道:“不要嫌我啰嗦,你们的东西也乱放,没有个数——”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有些反感,口气生硬:“也没有什么值钱东西,谁要拿就来拿!”父亲沉默了一阵,说:“既然这样,算我多嘴,自讨没趣。”我说:“本来嘛,何必自寻烦恼?真是王妈手脚不干净,也防不胜防。家里杂古隆冬、乱七八糟的东西拿掉一些也清爽一些!”
父亲淡淡一笑,没有再吭声转身朝房门走去,走到门边,扶着门框站了好一阵,自言自语道:“人老了,不值钱了,连小辈都看不起了。”缓缓走了出去。我知道我伤了父亲的心,父亲的自言自语让我心酸,后悔得不行。我真想出去向父亲赔个不是。我想象自己从椅子上起来,出房门,跟父亲说:“别瞎想,怎么会看不起自己的父亲呢?要不,我去问问王妈怎么箱子里的毛衣不见了?”但我到底没有从椅子上站起来,自然,更没有去问问王妈。
半年后,王妈自己辞了工,说是要回乡下带外孙。我们另外找了个女佣,也是乡下来的,年纪也近60。那时候都叫女佣为阿姨,阿姨烧的菜不如王妈,但父亲说:“看阿姨的眼气就知道是个老实人。”每天端菜上桌时,阿姨总要不好意思地说上一句:“我不会做菜。”父亲倒也不苛求,有时还接上一句:“吃到肚里都一样。”
阿姨做了将近一年时,父亲过世了。1月8日正是隆冬季节。料理完后事也就近春节了。春节时阿姨回家七天,回来后谈起了王妈,原来王妈和阿姨住在相邻两个村子。阿姨听王妈村子里的人说,王妈在苏州帮人家的时候,东家送了她不少东西:鞋被衣帽、外套棉袄、汤婆子、脚炉、漆盘、木盆——她外孙穿的毛衣毛裤也是东家送的。王妈的女婿隔两个月骑自行车上一趟苏州,回来时王妈总让他捎不少东西。妻说,一定是约好了日子趁父亲上街的空当来出赃的。
二十年来,我也正渐渐老去,一想起父亲就想起这往事,想起父亲手扶门框的自言自语。这是我今生的恨事。我真希望能有机会当面向父亲表示我的悔疚,甚至我的敬畏,但已是不可能了。我没有想到还有梦,在父亲二十周年忌辰我做了这样的梦!如今我祈求下一个梦,在梦中我一定要追上父亲,向他表示我的悔疚,甚至我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