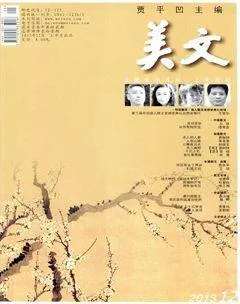从传奇到传说
2013-12-29诸荣会

诸荣会
江苏溧水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某出版社副编审。有作品发表并入选《中国散文60年》等选本。出版散文集等十数种。曾获“紫金山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她出现在当年的上海滩,本来就如同从天上掉下来一般,随即她又借助偏师而异军突起,一夜爆红后再多面出击、跨界成名,一路风风火火,令人眼花缭乱,实在如一则精彩的传奇。
她后半生——如果她有后半生——却只存在于传说中。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这样的事情即使是发生在一个一般人身上,也是极其罕见和不可思议的,何况是发生在一个有着多种身份和各种光环的名人身上呢?
然而,事实上她真就是这样,似乎只在一夜间便人间蒸发了,并就此再也没能重回人间。
——她就是胡萍
一
“胡萍”——这个平实而又普通名字,我们今天怎么看似乎都像是属于某个邻家小妹,让人难以想象这个名字的主人竟是民国时期的一位社交名媛,因为这个名字既没有一些明星艺名常沾的那种香艳,也没有多数作家笔名常显的那种风雅,可是,她确确实实是民国时期上海滩上的一位社交名媛,同时又是一位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跨界作家。仅仅凭这,我们就不能不说,她确是一则传奇。更何况她从出道,到成功,到成名,直至消失,每一步都充满了传奇色彩。
胡萍1910年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普通市民家庭,好在父母还算开明,并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他们见小姑娘长得聪明伶俐,到了启蒙的年龄便将她送到了学校去读书。胡萍果然不负众望,读书成绩一直很好,当她读进了长沙当时很有名的长沙女中时,自己似乎隐约觉得自己原本并不是做小市民的料,并认定自己的人生舞台并不在小户人家的坊灶之间,甚至不在她生长的这座湖湘名城长沙,而是中国最大最前沿的都市上海,在它那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间。
但是,在那个时代,长沙可是离上海太远太远了,尤其是在一个贫家女孩子的生命中,更是处于那遥远的人生地平线上,她如何从自己的长沙到达别人的上海的呢?好在她有她自己的计划和心思。
再落后的世界,总有相对时尚的角落;再封闭的角落,它也总有通向外面世界的窗口,更何况这长沙怎么着也算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湖湘名城呵!当时长沙城里唯一的一家咖啡馆便正是这样一个全城最时尚的角落,而在她眼里更是最有可能通向世界的一个窗口。于是,胡萍成了这家咖啡馆的一名女招待。这在当时无异沦落了风尘,不但闲言碎语一时一起向她袭来,而且家里包括父母在内也对她的职业选择表示坚决反对,她的这一选择也无异于是对于整个家族的大逆不道。但是她才管不了这么多,或者说她压根儿就没管这么多,行动上更表现为是一种深思熟虑后的义无反顾。她要将这间咖啡馆,当做自己主动出击人生的一个起跑器,既然已一脚踏上,岂又退下的道理,唯有等待那一声发令的枪响,便冲向那既定的目标。
这声枪响,说来还真的有一天让她给等到了。
胡萍是那家小咖啡馆最勤快的女招待,她每天上班比谁都早,下班比谁都晚,这自然让老板十分高兴。而对于胡萍来说,她之所以这样,可并不是为了在老板面前讨一点好,并为之多得几个加班费,而是她为了获得更多离开这间小小咖啡馆的机会——尽量在咖啡馆里多待些时间,自然机会也会多一些。
1926年底的一天,胡萍又是第一个来到咖啡馆上班。而这一天注定将成为胡萍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她将咖啡馆的门刚打开,就见一位客人已等在门口了。胡萍赶紧热情地将客人迎进门,并招呼着坐下。客人说,他与一位朋友约好在这个咖啡馆见面,由于是初次见面,怕迟到不礼貌,所以就来早了点儿。攀谈之间,胡萍将客人点的咖啡端到了客人面前。此时,照理作为服务生的胡萍就该退下离开了,但是自从这位客人进门时,她似乎就断定,这位客人或许就是自己人生的贵人——此人气质儒雅,但是眉宇间又透出一种阳刚之气,再加上言行得体,举止从容,一看就能看出是来自大地方、经过大场面的主;再加上,此时整个咖啡馆里也没有别的客人要去服务,所以胡萍并没有当即离开,而是主动地与客人搭讪了起来。客人对于眼前这个年轻漂亮,又显得伶俐可爱的小女孩似乎也并不讨厌,当她显得冒昧而大胆地“敢问客人姓名”时,竟然真的如实地自报了家门,说自己也是长沙人,叫陈瑜。当胡萍听到陈瑜这个名字时,几乎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她知道“陈瑜”便是田汉在老家时的原名,只一瞬间,她就确认眼前的这个男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剧作家、“南国剧社”的创始人田汉!她激动得一时几乎说不出话来,因为她心里知道,自己等待的这个贵人终于到来了。
胡萍几乎是有点儿词不搭义地表达了自己人生最大的愿望,田汉面带微笑地听她讲完后,或许是想到当年离开长沙时也曾说过的话,“我不做塘里的鱼了,我得到江里去海里去!那里才是我活跃的地方呀”,或许是看到眼前的这个女孩聪明伶俐,没准还真是个可造之才,于是只简单地经过一番考问后,便当场决定将胡萍招进自己的南国剧社。
就这样,胡萍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就此闯进了上海的戏剧界和电影界。就这样,一个从长沙咖啡馆里走出的女招待,将在上海滩完成她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人生嬗变,并绽放成一朵美丽而另类的传奇之花。
二
然而,胡萍来到了上海,迎接她的最初并不是闪烁的霓虹和美妙的夜曲,而是满城的枪声和弥漫的硝烟。那是“四·一二”政变。好在枪声很快就停息,硝烟也很快散去了,只是这座有着东方巴黎之称的不夜城,竟一时笼罩在了白色恐怖之中,而就是这种恐怖的白色世界里,胡萍却成了一朵摇曳其中的红色花朵,让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宋之的为她留下了一篇著名的报告文学,题目就是《红姑娘胡萍》。我们今天真该感谢宋之的,正是这篇文章,使得今天的我们似乎看到一位一身鲜红的少女,正穿越历史的烟尘走进我们的视野。
当然说胡萍是一位“红姑娘”,首先是她特别喜欢红色,她似乎走到哪里都是从头到脚一身红,“口唇红,衣服红,腮帮子也透着点红”;其次是有人说她的思想也有点“红”。
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她的“贵人”田汉,后来之所以有能力,也有资格为未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写出国歌,本身就是足可以说明他本质上是一位很“赤化”了的剧作家,胡萍“近朱者赤”,实在是太自然而然了。

再则,“红”也曾是30年代的“上海摩登”之一,当时的许多年轻人,都以喜红色鞋帽、穿红色衣裙、谈红色话题、具红色思想为一种时髦,本来就是为追逐时尚而才来到上海的胡萍,岂能落在人后!
只是当政变过后,风向突变,那本是满大街的红色竟似乎一夜间便褪去了,满上海似乎就只剩下胡萍这“万绿丛中一点红”了。她依然一身红妆地在上海的十里洋场上四处招摇,如一只飞舞着的红蜻蜓,也如一团燃烧着的红色烈火。
胡萍的“红”是人尽皆知的,她终获得“红姑娘”的名头也是当之无愧的。
然而,在演艺事业上,胡萍起初并没有像传说的那样一炮走红。
由于她毕竟没有学过表演,更没有任何演出实践,胡萍开始时只能在田汉的特别关照下出演一些小的舞台剧中的小角色,如“大道剧社”的《街头人》《乱钟》等小戏中的有关角色。难能可贵的是,这些角色她竟然都能胜任,这让田汉和一些关心她的人看到了她极大的艺术潜力,当然也使她自己获得了自信。
常言说,一个人走向成功是离不开“四人帮”的,即四种“人”的帮助和帮忙:一是本人努力,二是贵人相助,三是高人指点,四是同人(仁)相逼。在事业上胡萍本人的努力是自不待言的,而田汉无疑既是她的“贵人”也是她的“高人”。
1928年,田汉写成《苏州夜话》,并由南国剧社排演,胡萍在其中出演主角,凭借她的天赋才气和刻苦,终于通过该剧的演出一举成名。虽然《苏州夜话》是一部舞台话剧,但是胡萍自然的表演风格,让一些电影界的人士,看到了她身上暗藏着的电影表演的潜质。“明星影片公司”很快便邀其加入,自此,胡萍正式开始了她水银灯下的一段最光彩的人生。
此时,胡萍离事业成功,就差这“同人(仁)相逼”了。
果然,兴冲冲加入明星公司的胡萍,受到了同仁的无情排挤,一段时间内,无论大小角色,竟然都没有“适合”她的,她只能在明星公司坐起了冷板凳。无奈之下,她只好去“走穴”。1931年,她先后在“友联”和“白虹”分别参演了《海上英雄》和《绿林艳史》两部影片,但都是其中的小角色;再加上影片本身也不成功,所以也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导演汤杰或许出于同情,邀请胡萍主演《满园春色》,可惜剧本本身平庸,胡萍的表演也难以出彩,公映后也同样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此时在明星公司的胡萍,似乎已被“逼”进了一个死角,毫无退路了。
怎么办?
不是没有 “适合”的角色和好剧本吗?行,我自己写!
胡萍拿起了笔,自己创作电影剧本,并要求自己主演。
就这样,胡萍在明星公司自编、自演了她第一部重要的电影《姊姊的悲剧》,也为自己一生中写就了又一堪称传奇的一笔。任何时候,那些身姿妙曼、外面华贵、光环笼罩的明星,勿庸讳言,他们中有许多人,其实内心空洞,本质上与花瓶并无多少不同,偶有能动动笔的,多半也只能写些业内轶事、自身回忆传记之类,能写出像样作品的实在稀罕。所以胡萍的这一招,无疑是一次偏师借助;而在战场之上,有时候借助偏师,恰恰能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胡萍果然一下子切入了上海影业。
《姊姊的悲剧》不但充分展示了胡萍令人惊异的文学才华,更是她表演才能的一次充分发挥;影片公映后大获好评,不但一举奠定了她电影明星的地位,更获得了一个“作家明星”和“明星作家”的称号。
1933年,胡萍又在田汉的介绍下,进入了“艺华影片公司”,当然,这次与当年进入“明星”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此时的胡萍俨然已是上海滩一颗耀眼的新星、演艺界大腕,谁还敢排挤她?谁还能排挤她?于是她从进“艺华”的第一天起就是“艺华”的台柱。她一连在那儿主演了《烈焰》《女人》《黄金时代》《人之初》《时势英雄》等影片,进一步确定了她在上海滩一线明星的地位。同时,胡萍在事业上取得极大成功时,又正式加入了由田汉发起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
至此,胡萍作为上海滩一名当红明星,真是从里到外都红透了!
不过她及“艺华”也曾为自己的“红”付出了一定代价。有一天,胡萍正在公司的摄影场紧张地拍戏,突然周边警笛四起,随即一群不明身份的人闯进了摄影场,见什么砸什么,见什么人打什么人,一会儿工夫,好好的摄影场一片狼藉,不,简直就成了一堆废墟。这些人砸完了,也打累了,扔下一纸落款为“上海电影界铲共同志会”的“警告信”扬长而去:
对于陈瑜(田汉)、沈端先(夏衍)、卜万苍、胡萍、金焰等所导演、所编剧、所主演之各项鼓吹阶级斗争、贫富对立的反动电影一律不予放映,否则必以暴力手段对付,如艺华一样,决不宽恕……
不久田汉被捕,胡萍离开“艺华”,转入“新华”。
胡萍在上海滩书写的这则传奇远还没有结尾!
三
左翼文艺的被围剿,田汉的被捕,让一些左翼文艺工作者陷入了一时的恐慌。而此时的胡萍,仍一如既往地以一身红妆出没于上海滩的十里洋场,以左翼文艺家的身份,出没于各大歌厅舞场,如一只飞舞着的红蜻蜓,长袖善舞于上海的高楼大厦间。宋之的在《红姑娘胡萍》中为我们描写了这样一个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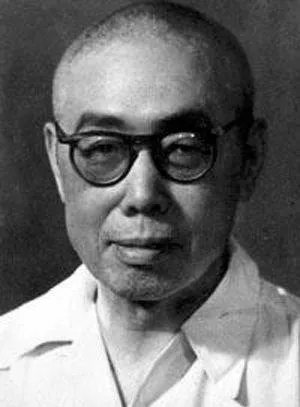
胡萍就在这时候,看了看表:“哟,10点钟了,我还有个约会,得赶快走!”
我的朋友开着玩笑:“这样急,大概是赴情人约会吧!”
“鬼话!一个朋友请我到‘大沪’去跳……”停了一会儿,“不,我要回去睡觉了。我每天晚上10点钟睡觉……”(宋之的《红姑娘胡萍》)
要知道,那时上海的舞厅,多数如今天的“KTV”一般,那儿的一切,多半有点色情和半色情,或许正是因此,胡萍无论是说起,还是前往,都有点遮遮掩掩和此地无银三百两。
然而,此时她一点儿也不遮掩和避讳的是,她出没于那些灯红酒绿之处时身边比以往多出的那个小伙子。小伙子名叫阿唐,是一位南洋华侨子弟,在上海求学。或许是由于太迷恋胡萍的那一身鲜红,或许就是前世欠下了一份情债,他在胡萍的那一身红装面前似乎永远都是自惭形秽样子,所到之处,完全成了胡萍的一名护花使者——每入舞池前,他急忙接住她脱下的红外套和红帽子,从舞场离开时,他又恰到好处地递上;舞场中央胡萍翩翩起舞,引得全场鼓掌时,他也跟着鼓掌。当有人当着他的面向胡萍说肉麻的献媚话、作越轨的举动时,他也只当没听见没看见,最多或笑笑,或怒目而视。在许多人的眼里,这正是一对金童玉女。

也许这一切只是胡萍的一种自我保护的伪装吧,因为与此同时,人们又不时能够读到她时常发表在报端的影评、杂文等,泼辣而不失犀利的文笔,直指现实;不仅如此,即使是那个阶段,作为一名演员,她该接演的戏照接、照演。
田汉被软禁南京,却仍被允许演戏,于是他便正好利用这一机会,邀请上海的一些左翼演员赴首都“大演其戏”,当然“其戏”正是一些左翼戏剧。但是一些左翼文艺工作者心存忧虑,或者还心存恐惧,对于田汉的邀请纷纷婉拒,如金焰、王人美夫妇,都以电影公司赶戏为由婉拒。胡萍却欣然前往,出任《复活》一剧的女主角,在南京演出。
在“新华影片公司”,胡萍主演了史东山编导、田汉编剧、史东山导演的《青年进行曲》,还与周璇等合作演出了《狂欢之夜》,这些影片都曾轰动一时、广获好评。
正在此时,侵略者的枪炮突然间打破了上海滩歌舞升平的梦想。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后,可怜的上海这座有着“东方巴黎”之称的都市很快沦为了一座“孤岛”。
张爱玲也被困在上海这座孤岛之上,若干年后她说出了大体上这样一句话:有没有那样一座城,城破了,却是为了成全一个人。或许此时的上海正是“那样一座城”,而此时的胡萍,也与张爱玲一样,正是那“一个人”。
身处“孤岛”的胡萍,其人生的传奇注定还将继续书写下去。
四
1937年,“孤岛”的上空飘荡起悲怆的“夜半歌声”,让这座浸泡在苦难中的城市,记住了电影中那个出身地主,风姿绰约、心地善良的女子李晓霞,历史也因此永远地记住了胡萍这个来自咖啡馆的湘妹子,记住了她的美丽、聪慧和才华,也记住了她的叛逆、正义和善良。
勿庸讳言,如果不是《夜半歌声》,胡萍身上的红色,或许早已在人们的记忆中褪去了,真也说不定!
《夜半歌声》作为一部电影,早已成了经典,为后来的多位电影导演反复重拍,至今还被人们津津乐道;那1937年的原片,也早已被人制成了DVD,至今还能从音像店里很容易地买到。但是,一般人对它的定义是“中国最早的恐怖片”。然而,只要是看过的人,看后或许会真的会大吃一惊,只是这“一惊”,并非真是它的情节是多么的恐怖——我们的胆子早已让好莱坞的恐怖片吓大了,一部70多年前的恐怖片哪能这么容易吓着我们呵——而是为它恐怖片外衣下原本包裹着十分严肃的主题,这原本是一部思想左翼的“进步”影片。这里不妨将《夜半歌声》的大体情节作一个简要的复述:
一个剧团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来到一座十分破败的剧场,他们准备在这儿排演一部新剧。男主角孙小鸥在排练时,听到后台的阁楼上总是在半夜传出优美的歌声。他不禁循声爬上落满灰尘的后台阁楼,几经周折,终于发现躲在上面的一个蒙面人,那夜半的歌声正是此人唱出的。此人名叫宋丹萍,本也是一名优秀的歌唱演员,难能可贵的是他思想进步,积极从事进步演出,并在共同的艺术和思想追求中与一个叫李晓霞的女孩深深相爱,可是这李晓霞是一个地主的女儿,他们的爱情遭到了地主家庭的反对,宋丹萍因此竟遭到恶霸汤俊镪水烧脸。被完全毁容的宋丹萍,不仅无法再做演员,更怕吓着心爱的人而不愿再与李晓霞见面,就传出话去给李晓霞,假托已死去。谁知善良的李晓霞得知噩耗,心理崩溃、精神分裂,只有听到宋丹萍的歌声才能暂时安宁,于是宋丹萍只好躲在这个离李晓霞住处不远的这座剧院里日日为李晓霞在夜半歌唱,如此已经十年。知道真相后,孙小鸥自然对于宋、李两位都十分同情,宋丹萍在艺术上则给了孙小鸥许多帮助,于是孙小鸥就常去替宋丹萍安慰李晓霞,李晓霞神智渐清。正当事情向好的方向发展时,当年的恶霸汤俊又出现了,他到剧场观剧时,竟然侮辱并向女演员、也是孙小鸥的女朋友绿蝶开枪,宋丹萍奋不顾身地从阁楼上跳下与之搏斗,搏斗中汤失足摔死,宋丹萍也被烧死。
我这里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将《夜半歌声》的情节复述一遍,目的是为了替读者证明两点:
第一,从全剧如此情节不难看出,胡萍所饰演的李晓霞一角,在影片的戏份并不算太大,她之所以能获得人们如此地追捧,主要是因为她在剧中完全是纯洁爱情、美丽心灵和善良品质的化身,人们喜欢她连同饰演她的演员胡萍,原本是自然而然;当然这与胡萍在影片中的出色表演和成功塑造也是分不开了,因为我们也不能看出,影片中李晓霞的戏份虽然不多,但是却十分难演,从一个天真可爱的少女,到一个精神分裂的病人,直到最后康复后,又一次面对爱人真正的死亡而陷入绝望,这样的情节,对于一个演员的表演来说,是具有十分的挑战性的。最终人们对于李晓霞和胡萍的喜爱,当然也反证了胡萍的表演是成功的。
第二,从全剧如此情节也不难看出,这是一部思想左翼的进步影片,如果它不是恰恰出现在如张玲所说的那种“城破”的前后,即使披着一个“恐怖片”和“商业片”的外衣,或许也是很难获得公映的;而如果不能获得公演,历史在今天或许也会忘记这位70多年前的“红姑娘”的,正是因为这部影片,使得胡萍攀上了她艺术上的顶峰,与此同时,也使得她的社会声誉同样达到了顶峰,而这又为她将与现实生活中的所作所为形成一个巨大反差设定了前提——与电影中的李晓霞相比,现实生活中胡萍的表现实在是与之太大相径庭,太判若两人了!
阿唐父母本是南洋华侨,战争完全打断了他与他们联系,自然也打断了还只是一名学生的他生活中的惟一来源,似乎忽然之间,阿唐便由一名南洋公子哥儿变成了上海滩上一名身无分文的小瘪三;偏偏又祸不单行,有一天,阿唐忽然间觉得自己眼前一黑,且越来越黑,最终竟双目失明了。跑了几家医院后,医生也说不出个病因,个个束手无策。阿唐从此只能端坐家中,惟有唉声叹气、以泪洗面。就这样,陷入困境的不光是阿唐与胡萍的生活,还有他们的爱情,此时本已同居的他们,一切都应了“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古话。早已在胡萍内心急剧澎胀起来的欲望,与摆在面前的残酷现实,一起挤压着她的心,让她难以喘息。担任着她人生中“贵人”与“高人”双重身份的田汉,此时仍被监禁着自身难保,更给不了她任何的帮助。当然不难想象,此时更希望得到安慰和帮助的是正处于黑暗中的阿唐。然而,胡萍正是在这时做出她的选择,或者说是抉择,是决断。有一天,被黑暗包围着的阿唐,似乎觉得家里有点儿异样,于是他在家摸索了起来,发现胡萍的所有衣服都已不在,他明白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可怜的小伙子呆呆地在黑暗中坐了许久,慢慢去摸到了电灯开关的拉线,拉亮了电灯,但一个20多岁的生命之火却就此熄灭了——阿唐将自己的手指竟然伸进了电灯的灯头……

生活中的胡萍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女陈世美,也成了对她塑造的那个李晓霞的一种背叛,一种讽刺,一种侮辱!
胡萍人生的传奇,至此也差不多快写到结尾了,就差一个最后的句号。
五
抗战全面爆发后,武汉一时成了正面抗战的中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也设在了那儿,就是这个战时属军事机构(虽说属“政治部”)的“第三厅”,厅长竟然是著名的文人郭沫若,于是大量欲投笔从戎的文化人纷纷来到汉口。
胡萍这一只曾经在上海滩高楼大厦间飞舞的红蜻蜓也飞到了武汉一镇,只是她那一身标志性的“红妆”自然脱去了,她声称从此以后“不爱红装爱武装”,“亦在第三厅兼有职务,背起武装带,着了军服,出现于各处公共场所,并且口上声声谓将从事救亡工作到底”(宋之的《红姑娘胡萍》)。
然而,不久武汉又失守,国民政府的机构随即进行所谓“大撤退”,可人们在大撤退的队伍中却没有看到胡萍的身影,且再也没有看到,她如同从人间蒸发了一般,“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胡萍传奇人生的这个句号,算是就此就打上了——当然,这本身或许也算是她为自己的传奇人生写下的最后一笔。
然而,传奇结束了,传说却开始了——
有人说她成了一名特工,曾打入侵华日军内部工作,可由于不幸暴露而过早地牺牲了,也就是说胡萍终成了一位抗战英雄——初听来,这一说法不但与胡萍曾经是一位“红姑娘”的人生逻辑暗合,而且也符合当时社会潮流和历史推进的逻辑,因为像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那个时代确实并不罕见,如近年来由于电影《色·戒》而被人们重新提起的郑萍如,即是一位这样的英雄,且她最终确实也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随着一些当初的目击证人逐渐浮出水面,尤其随着近年来一些有关档案的解密,她牺牲时的一些具体情况,还是被逐渐披露了出来。如果胡萍真的如传说的那样,我想她牺牲的具体情况多少也总得会有一些披露了吧?可这样的披露我们从没见到,至少是时至今日,所有“英雄胡萍”只是一个传说而已。
有人说新中国成立后还在长沙看见过她,甚至还有人说在“文革”后还在长沙看见过她,当然,此时的胡萍早已褪去了身上的所有“红色”,完全沦为了长沙城里的一个普通小市民——如果这确是真的,似乎也并没什么奇怪,许多当初曾大红大紫的明星,或因曾经沧海而参透世事,看破红尘,或因烂漫之极而铅华洗尽,复归平淡,原本既不违生活逻辑,也不乏历史实例,如当年红遍海上和京城的“天下第一老生”孟小冬,事实上最终不成了杜公馆里的一名老妈子了吗?何况她还能穿越“文革”等历史风暴,如果真能活下来,身上原有的颜色,即使再深也会荡然无存,这实在是不难想象。然而这一切只是听到“有人说”而已,不但看到的“人”到底是谁并不清楚,甚至连“说”的人到底是谁也不清楚!因此,“小市民胡萍”也只是一个传说而已。
似乎最可信的是一个叫潘孑农的人,他自称在1942年的某天在重庆看到过胡萍:某高档住宅区附近的一条幽静的林阴大道上,一辆高级轿车从远处轻轻驰来,路边停稳后,一位很有绅士风度的中年男士从车上下来,将一旁的车门拉开,一位衣饰华贵、气质不凡的少妇走下车来……此情此景让潘孑农大吃一惊,因为那中年男人是当时国民政府的粮食部部长,而那妇人竟是胡萍。潘某人是个影评人,对影界人士自然比较熟悉,更不必说像胡萍这样的大明星,更是不会陌生,想来他不会看错人。然而,这毕竟只是他一个人自说自画,并无第二个目击者,最多只能算作是一种对实情的“孤证”,而孤证任何时候都是不能太当真的;相反,反倒很容易让我们据潘某人的影评人身份而产生这样的“小人之心”——会不会是他为了使自己的影评更有卖点、更吸引人、更有说服力,这才杜撰出这么本是子虚乌有的一幕,作为他卖文为生的一个噱头呢?因此,“官太太胡萍”也只是一个传说而已。
惟一见诸报报端的白纸黑字,是1936年6月出版的第13期《电影新闻》上曾发表的一篇《影息香港·行踪神秘的胡萍》文章,文章说胡萍在武汉失守后的“大撤退”中,悄悄脱去了军装,并辗转到了香港,又恢复了她那身标志性的红色装扮,甚至于有时还会女扮男装,出没于香港的歌场舞厅……一切说得有鼻子有眼。但是文章最关键的一句话:“据说胡萍在香港结交了一腰缠万贯的富家郎。”一个“据说”,终又让“富婆胡萍”也只是一个传说而已。
就这样,胡萍从上海滩的一则传奇,最终成了一个传说,且恐怕将是一个永远的传说。所以有人将胡萍的一生比喻成一出折子戏,只有开头,没有结尾。
胡萍到底最终结局如何?至今没有确说。
一代名媛才女,一代明星作家,莫非恰在某个不为人知的时间,又恰在某个黑暗的角落,竟不为人知地死于非命了?
如果真是这样,那真是胡萍的大不幸!
然而,即使真是这样,谁又能说这样的不幸中不也有几分幸呢!
站在今天,回望胡萍既戏如人生又人生如戏的短暂一生,她的这场人生大戏的确只是一场折子戏,但是折子戏也自有折子戏的好处和妙处呵,因为那是从一整部大戏中截出的最华彩的段落——胡萍以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在现实的舞台和人生的舞台,同时轰轰烈烈地演绎了自己的角色,绽放了自己的美丽,甚至燃烧了自己的生命,这难道还不够吗?她那一袭摇曳在历史天空中的红色身影,将永远会让后世那些有意无意走近的人艳惊,难道这还不是她人生一种最大的幸福吗?如果再说的具体一点,胡萍戛然而止的生命,虽然少了人们惯常渴望的“大团圆”结局,但也就此斩断了她一不小心留下的那条“女陈世美”的小辫子——她人生的这幕大戏若在众目睽睽下再演得长些,更长些,就是这条小辫,或许将会被人通过拽着它而将她拽上歧路,或许会干脆要了她的命,一切都有可能——如若那样,她生命的这种戛然而止,难道不也是她的一种幸福吗?廉颇老矣,美人迟暮,既是生命的无奈,也是人生的悲凉;胡萍不知所终的人生,虽然少了起承转合的路数,但同时也少了这份无奈和悲凉,更何况就此还多了那么多传说,且这些传说说不定还真能够传至永远,这难道不也是她一种不幸之中的幸运吗?这样的幸运,这世界上能有几人能够享有呵?
安息吧,胡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