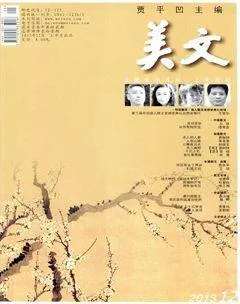芳邻翠翠
2013-12-29东珠

东珠
1978年12月28日生于吉林省敦化市黄泥河镇五人班村,为吉林省作协会员。现任吉林市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财富江城》栏目组编导。
翠翠又要走了,还特意嘱咐我,不用等她吃晚饭,她今晚不回来了。可愁死我了!她有一个老姨在市里一家医院上班,每到周末她就去老姨家改善伙食、吃香的喝辣的。我最头疼的就是翠翠不在家,真愁啊!我怀疑我的白头发,都是趁翠翠不在家的时候,背后偷袭我并占领了我的脑壳。翠翠是我的芳邻,睡在我的右侧。她在,我还有人气。她不在,我极有变成鬼的可能,因为我这屋里住着一群画皮。先前我是把她们当人看的。可是一个月后,这群画皮成天在我的房间不定时出没,导致我的观念渐渐转变了,我得把她们正式当鬼看了。我都是记者了,得有这个觉悟。翠翠临走时向我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让我到别的房间避避难。她刚刚扶正的睫毛俏皮又真诚,她的睫毛患有先天性“倒睫”。我从来不知道,睫毛还能生病。现在,她的睫毛被当医生的老姨扶正了,一根一根都很敬业。我苦笑,我最讨厌寄人篱下了!我曾经有过这样一段经历:那年我几岁,我记不得了。总之我先被火车托运到山东,寄存在一个冬天冻死人的土屋里。又被火车托运回东北,寄存在外公家。而后,又被转运到二姑家,继续寄存。不到一年的时间,我被倒了三倒,差点吐血。现在这床就是我的家,哪也没有家好。但是翠翠走了,这《聊斋》版的女子宿舍,就剩我一个观众了,我还必须得看,要命!我是一个胆小的人!
红娘子,又在侍弄她的脚丫。大红睡袍,像一个大写的“L”装着她。她这英文的造型,与她那侍弄脚丫的农夫形象合二为一,感觉真的很二。我发现了,她最大的领地,就是她那十个脚趾——她的十垄地。她还有一个毛病,就是总在地头逗留,那脚趾甲修了又修。她如此珍爱自己的脚,路还是没有走好,居然也离婚了。所以现在,一修脚,她就会想起男人。或者说一提起男人,她就一定得摸脚。现在又开始了——唉,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坐出租车回家,那司机相中我的脚了,说什么也不让我下车!唉,你知道吗?我家那个贱人,当初也是相中我的脚了!唉,你知道吗?我是净身出户啊,我就是要这口志气!唉,你知道吗?现在那个小娘们就住在我们家!唉,你知道吗?是我把她接到我们家的,我这样做,他还是不满意,他这个贱人……贱人,是她的结束语。每次说到“贱人”,我们就有指忘了,因为这时已经修到小脚趾了。然后,她稍稍停顿一下,又开始修另外一只脚,同样把男人踩在脚下——唉,我告诉你,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咔嚓!男人是什么德性,我最知道了,咔嚓!全世界的男人都死绝了,那才好呢,咔嚓!她说话总是带音效,咔嚓咔嚓个没完,剪碎的红脚趾甲到处乱飞,长发像门帘子一样垂到床上。我就等着她那个小脚趾来救我。我很想弄来一把铡刀,把那孱弱的小指甲刀替下来。我觉得,只有铡刀才能配得上她的恨。我的肚子鼓了好几次,我想让她闭嘴,因为我还没有嫁人呢!她这样把男人咔嚓得一无是处,就等于把我嫁人的决心活埋了一样。我的话骨碌到舌尖,又咽回去了。我想她不是三只脚,两只脚剪完自然会闭嘴。红娘子,是我给起的名。她年纪不大,比我大十多岁。在这种情况下,我叫她娘,那是背叛。我叫她娘子,又没有那个许可证。所以我叫她红娘子,既符合她春心荡漾的外形,又符合她结婚又离婚的现代史。红娘子在我们女子宿舍,是床笫派的掌门人。她黑天白天都穿着那件大红睡袍,从来不换,也不轻易走出女子宿舍一步。眼圈纹着眼线,眼线不褪色,比她的婚姻长寿。她就睡在我的左侧,一个红衣画皮。
白娘子,在吃麻辣烫。一只手紧拎着装麻辣烫的塑料袋口,一只手用筷子把里面的菜,一叶一叶地像吊宝一样吊上来。她很怕红娘子的脚趾甲混进口袋里,所以尽量缩小自己的就餐范围,一直躲在门后偷吃。门后,一张小木桌,一个垃圾桶。但是,吃粉条很不成功。那粉条是滑头!路途稍一遥远或是坎坷一点,就容易半路改道,掉到垃圾桶里或是小木桌上,拜拜了。如此,白娘子的嘴就得伸得老长,才能把粉条收入胃袋,又是吹又是亲,连哄带骗。一根粉丝把她折腾得直淌汗珠。白娘子表面很人烟,与红娘子恰巧睡对床。她头发向后盘着,不是向上盘。皮肤是咖啡色,单眼皮。她对衣服的要求非常苛刻!最喜欢穿白色的连衣裙,裙子上什么缀饰也没有,针脚都不能抛头露面,最多只是一粒扣子。白娘子的嘴很守谱,一直喜欢麻辣烫。白娘子,也是我给起的名。因为在女子宿舍,这些离了婚的女人们,多是隐姓埋名住在这里,你无论如何是得不到真名的。真名太容易出卖她们。她们经过一次情感的抢劫,已经多多少少学会了一点自卫的基本常识。她们被婚姻一脚剔出家门,手里没有什么像样的武器,一切皆空,就只剩下一个真名是真的了,再也不能弄丢了。隐去真名还有很多其他的好处。比如,那些曾经与真名同生共死的称谓——泼妇、精神病、黄脸婆、小破鞋、潘金莲、糟糠、怨妇、荡妇等等,也确实需要回避一下。再比如,面对一些临时产生的新男友,假如用真名去赴约,极容易泄密,碍手碍脚。情史不同于创业史,一个女人经历太多总让男人胡思乱想、左右猜疑、上下打听,然后就是放弃,怕是一个烂货或是一个贱货。关于烂货和贱货的问题,她们曾开会研究过,我是旁听。当时白娘子的观点非常明确——哪个烂货不是男人制造?哪个贱货不是男人收购?这个世界最大的悲哀就是,男人渴望外遇,又害怕遇到烂货和贱货。她那医生的嘴,就是手术刀,割向男人,恨不能把他们阉割了!但是,白娘子显然受过高等教育,说起自己的家事不像红娘子那样口无遮拦,歇斯底里。她的嘴也很小资,男人在她的嘴里,是另一个版本。等到红娘子的两只脚都修完了,她开始说了。首先,从脖颈处发出一串笑声,预示这是喜剧——你们知道吗?我前天回家,我就这样笑嘻嘻地给我们家老万打个电话,我说老万啊,我想我们的儿子了,我还有一双高跟鞋落在家里了,我要回家一趟,你赶快准备一下。你们知道我为什么给他打这个电话吗?因为我怕那个女的也在我家,哈哈哈!我们家老万忙得滴溜溜转,像接圣驾一样!你们猜怎么着?老万说我还是一朵狗尾巴花,哈哈哈!那不就是得瑟吗?便宜吗?贱吗?走了不说了!她总是这样戛然而止,很抽风。她是医生,手术刀用错了地方,一刀一刀,把自己的婚姻宰割得清汤清水,最后只剩下了一种颜色、一张床、一碗麻辣烫。除此之外,她还有几个临时男友,她今天如此谈笑风生,笑傲围城、把前夫老万玩成皇宫的太监,全是那几个临时男友的功劳。爱情不空巢,才能叫得更欢。谢天谢地,红娘子和白娘子,均没有说出“尸体”的字样,这就等于救了我了。
但是到了晚上,我依旧不敢睡觉。因为红娘子没事就去厕所,啥也不做,一去就是半个小时,然后踩着朦胧的月色,晃晃悠悠地飘上床。她推门的声音特别瘆人,一小寸一小寸地刮我的心,一根一根地抽我的筋。阴风又度鬼门关,我这个大活人死的心都有了!白娘子晚上根本不脱衣服,随时准备接圣驾。手机短信像蛤蟆一样,一个一个地往里蹦,叫得一样欢,也不知道谁家的澡堂子更大。睡觉是不可能了!我只能把这样的夜,当大年夜过了。两个鬼一个人,我得好好想想,我这个人是怎么一失足走进了鬼屋呢?我又把自己刷新了,我是记者了。这样,我就迎来了我生命中第三次大迁徙——从江北岸迁到江南岸。距离是一座桥,桥下是一条江。我对江没有感觉,因为江上人烟稀少,而我需要削尖脑袋往人堆里扎。我扎进去,才有活路。我的脚趾不被踩掉,才能跑得更快。上学时我是学校里的长跑冠军,长发飘飘。现在我也是,我从农村跑出来,甩掉一大批锄友。我从裤店跑出来,甩掉一大批裤友。我又从手机大市场跑出来,甩掉一大批机友。再往前推算一下,我也是第一个从俺娘的肚子里跑出来,我是老大。我这样不停地逃,不停地跑,不停地刷新自己,是因为我不想如此短命。世上最无情的就是商业,想甩你,理由是钞票。想爱你,理由还是钞票。它只认得钱。与它万里长征,年景好的时候,它是人民币。年景不好,它就是冥币。这些短命的营生,拖着我的长腿,早晚得把我拖垮。我的终级目标是与笔友同伍,与他们赛跑,最好孤独求败。但是现在的我,充其量只是一个简易的铅笔拧、或者是残缺的橡皮擦——经过一次考试,我是记者了!电视台的大门向我敞开了!要到达那扇门,需要经过一条江和一座桥。那江叫松花江,那桥叫吉林大桥。我依旧很矜持,面对江,我没有投怀送抱。我只是对出租车司机说慢点开。我的眼泪哗哗地流,我知道松花江有这个承载能力。那个司机说,到电视台上班,应该高兴啊,你说你怎么还哭上了呢?我不做声。那个司机又问,是走后门去的?能在电视台工作可不容易啊……我还是不做声。在我百感交集的时候,我不太喜欢第三者。过了桥,我便不再哭。因为我知道,离开了广阔的水域,我的眼泪将无处安放。我把自己刷新了,我要换一个女子宿舍。电视台的椅子有我的一把,江南岸的床却没有我一张。一想到这里,我就苦笑:全身上下,只有屁股高枕无忧。再一想,这城市里大多数人的情况都是这样的——看局部,很精彩。看全部,很荒唐。我还记得我刚来时,房东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说我是记者。房东想了一下,就把我安排在了这里。唯一的好处是,这间房子向阳。可是,与这群女鬼画皮住在一起,向阳有什么用呢?
晚上不睡觉,胃也不睡。大肠小肠都在胃的指挥下值夜班。天还没亮我就饿了。一饿,我就很想翠翠。只有天快亮的时候,那两个女鬼才会睡着,她们非常遵守鬼的规则。房东也养了几只鸡,但不为鬼服务,从不会起大早打鸣,一直与人保持着相似的作息。我依旧不敢看她们,用俺娘的话说,看到眼里就挖不走了。我只能看天,天空的星,被黑夜吃得所剩无几。碎星残片,就等着阳光来收拾。我就等着翠翠来收拾,翠翠是我的阳光。我一直认为我很强悍,遇到翠翠后我才知道,我也会柔弱。是她的出现,让我身上雪藏了近一年的女性元素日益凸显。因为在以前,我虽然是顶着一张女人皮,却一直是以老爷们的悲壮行走人世的。翠翠来自附近的一个小山村,她还有一个妹妹。她家是养兔专业户,满山的兔子,特能生育,卖个十几只就够过活一阵子。所以,翠翠没有太多的生存压力,她唯一需要做的,是以长女的身份赡养父母,在村里大声说话,扛起父母没有生出男孩的遗憾。翠翠很努力,也很独立。翠翠有一个口头禅——哈西得勒。与扎西得勒只差一个字。遇到翠翠,与我相依为命的吃、住、行这三大件都被她改善了。我在吃上是个天生的相思苦命,我一旦相中什么,就会一吃到底,从不思改换。特别是那些青梅竹马的食物,野葡萄、大煎饼、饺子、面片、疙瘩汤等等更是相思甚苦。目前我想吃饺子没有条件,因为我刚当上记者,刚从手机市场来到电视台,收入上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时候,我把里外兜翻遍,也凑不出一碗饺子。再说,今年过年我回过家,我把所有的积蓄给了俺娘。我只有交上“钱”这个公粮,俺娘才能安心,有钱作证,她知道我会生活得很好。我是借了一百元钱,交了六十元的房租。余下的四十元,我给自己下命令,不许吃午饭。一个饥饿的我,昏沉沉地挣扎在中午,不管是回忆早晨,还是期待傍晚,都有食物在等着我,我很受用这种安排。在这样的情况下,翠翠要带我去认识一种饭菜身兼两职、且相对实惠的食物——麻辣烫。她七拐八拐把我领到一个小屋子里,她请我。我吃了一口,吐出。我说这是猪食吗?她说,你再接着吃。我很饿,一碗还是剩下了很多。那确实是猪食的味道,也是猪食的做法。我做过猪食,野生的灰菜、柳蒿、蒲公英等等,还有新磨的玉米面一起下锅,心情高兴时我会加上两根胡萝卜。我是猪最好的厨师,同一口大铁锅,我给家里人做完饭,直接填上水,再给猪做饭,然后再给狗做饭。牛不用,牛喜欢吃鲜草,滴着水珠的那种——那都是小时候的事了。第二天,翠翠还要带我去那里,她用耐心循循善诱,希望我变成她的麻友。我这次没有吐,居然有一点点适应了。第三天,翠翠又带我去,她改变我像改变沙漠,一定要长出绿洲来。这回我吃着吃着突然有感觉了,舌头开窍了,结果汤也没剩。第四天,我主动要求再去。她大笑着说哈西得勒,我说什么来着?只用三天保证让你上瘾!我也笑,猪就是这样喂肥的。接着,她又带我到东市场吃皇后。她说芒果是皇后。我被长相另类的皇后吸引了,我瞬间变成朕了。翠翠买了两个富态的,亲手剥了皮递给我。一口下去,我又马上吐出来了,这皇后身上,有一股浓烈的松油子味。松油子,在俺的老家,俺用它引火,闻着味道一直不错,可那只是鼻子的专利,把嘴插上去就不行了,屡战屡败。翠翠还不死心,说你再吃一口,再吃一口试试吧。我是说什么也打不开我的嘴了,牙在那紧紧咬着,像护栏一样圈着舌头。怕不保险,我的唇也紧紧闭着。看来让这个皇后下榻我的身体很困难,翠翠最后把两个皇后全吃了。我说我只喜欢吃那些宫女——李子、沙果、香水梨等等。后来,我果然吃到了!还是南方的宫女,又漂亮又珍贵。翠翠在一个花窖上班,她的专业是园林。一有时间,她就带我去花棚里拈花惹草。这一行是一举两得,一是我可以在这花房草窝里,缅怀一下逝去的童年。二是我可以吃到金橘。偌大个花窖,只有两棵金橘树,那是翠翠的领导格外宠爱的。但是,翠翠更宠爱我。她嘱咐我不能一下子全吃光,要一个一个地吃。我说领导发现了怎么办?她说如果发现了,就说金橘树生病了。我笑得不行了,她的意思是说,金桔树生病了,孩子夭折了,一个一个往下掉,谁也没招儿。
房东咣咣敲门。她在敲门这件事情上,一直坚持得很好。房东一进屋,便挥舞着大粗胳膊说“你你”晚上别走,我有事。她说了两个“你”,而我的屋里有三位房客。我明白了,她是让那两个女鬼别走随时待命。白娘子在吃五香瓜子,红娘子在看一本言情杂志,研究男人为什么不着调。白娘子吃瓜子非常执著,不管买回多少,只要一开吃,必须见底。从吃瓜子这件事情来看,她比较适合去挖井或者抓虱子。我有很多次看见她,手里拎着瓜子,一边吃,一边大摇大摆地行走在夕阳里,身后的瓜子皮像小蛾子一样飞舞。人约黄昏后,要是不让她吃完,约会也会溜号。我躺在床上看一本纯文学杂志,里面写到了面包圈,我一看到食物,胃就会条件反射。我无法控制我的胃走出身体,到楼下的小吃铺里去采购。本来,我的胃是很不待见面包圈的。因为我这中式的嘴巴,一直拒绝西洋景。但是今天,这本杂志改变了我。一个面包圈,书上写的,一元五角钱一个。书上并没有对面包圈的味道做出细致的描写,但这并不妨碍我去想象它的味道。我小的时候,吃得最隆重的一次甜食,就是半根麻花。那是在一个非常炎热的中午,为了吃麻花,我先吃了四张大煎饼,把胃垫得高高的,让饥饿够不着。然后,我才开始吃那半根麻花。从家一直吃到学校,二里地的距离,我精准的计算了吃法——踏进教室的那一刻,手里刚好剩下最后一口。我要让所有同学参观我吃那最后一口麻花的样子,那是一种炫耀,也是一种遮蔽。最后一口,可以让同学们把它想象成一整根麻花、或者是两根。只有我自己知道,那是半根。而后,我再也没有吃过甜食。再后来,我的胃也很有志气,渐渐与甜食意断情绝。今天我的胃想在甜食这里再续前缘,它还在楼下的小吃铺里逡巡。它等着我去买单,我要满足它。因为我一直欠着胃一份甜食,我还口口声声四处宣扬我不爱甜食,那只是一种自尊罢了。
两个小时后,房东的事初见端倪了。房东要在我的屋里大摆宴席。大鱼大肉都来了,蛏子蚬子也来了,五颜六色的蔬菜也来了,烟酒也来了,塑料椅和大圆桌也来了。电饭锅蹲在窗台上,像要大便的样子。这话十分不雅,但房东那口锅,形象确实很差。我的屋子就那么大,用俺娘的话就是“屁大点的地方”。它们都来了,这屋子显得拥挤不堪。那我也不走,这是我的床我的家。房东大呼小叫,用舌头又把绿娘子和灰娘子圈拢到我的屋里。看来确实是出大事了,因为灰娘子都来了。灰娘子梳着一个门帘子一样的齐刘海,把眉毛活生生埋掉。穿着露着腰沟的卡腰裤,平时一张嘴就是“啊呀妈呀”,是典型的东北小老娘们。她自己经营着一个服装床子,她平时的造型就是背着一个大麻袋一样的黑口袋,像作案一样日夜不需要睡眠。房东一招呼,她就来了,眼睛瞪得溜圆,生怕跑了客源,这是职业的习惯。她从来不提孩子,不提丈夫,她只提裤子!提完了就使劲跺脚,然后再满楼寻找能装下她全身的镜子,左照右照后,突然立定,乍呼呼地说上一句,啊呀妈呀我又瘦了,真闹心。这种自卖自夸、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的毛病,也是职业病。绿娘子的情况比较特殊,别的女人离婚了,都是无家一身轻。她不是,她还带个孩子。拖个油瓶子离婚,又住到像贫民窟一样的女子宿舍里,很难炒出“再婚”这盘菜。她倒是有一口好锅——她在银行上班,这在我们女子宿舍就是高收入了。但是,她的长相很不吉利,脸如浅水池塘一样,里面养着五官,一切都是走下坡路的样子,成天哀怨着,饥渴着。不像白娘子的豆包脸那样饱满,也不像红娘子的糖饼脸那样平坦。绿娘子与灰娘子,也是我给起的芳名。绿娘子,我起名的灵感来自床单被罩。绿娘子特别喜欢一种草包一样的绿格子床单被罩。在女子宿舍,由于每个人的地盘实在有限,换个床单被罩,就像装修一样。绿娘子装修完毕的时候,拖着她那个小油瓶,各屋奔走相告,然后我们纷纷去她的床前瞻仰祝贺并使劲摸索,尽量找出适合的赞辞。晚上,她就与她的孩子,一齐裹在这草包里,过一种离婚落草的日子。
我开始装睡,眼睛一闭,任耳朵遭罪。太阳快下山了,翠翠还没有回来。白娘子破天荒脱了衣服,只穿吊带。当然这些信息都是我听来的,我离她们太近了,每一种声音都能尽收耳底,一个屁声也不曾落下。她们吃饭的声音,吧唧吧唧的大嘴片子,像挑衅一样,仿佛在一遍遍地问——饿不饿?馋不馋?想不想吃?开始她们说话,主语是“我”——我家是我先出的轨,怎么啦?谁规定就不许女人先出轨了?这是白娘子的声音。接下来是绿娘子——我家的冰箱、电视、凡是值钱的,都让他卖了,我们娘俩是啥鸡巴毛都没有!我就剩那个小鸡巴孩了!绿娘子带头骂人了,导致她们谈话的主语全变了,变成了“他妈的”。他妈的我有时真想一刀杀了他——红娘子又在摸脚,因为我听到了她把手伸向桌子底下的声音。他妈的我都麻木了,我天天上货睡大通铺,男人摸我这里,我都没反应了!累啊——这是灰娘子的声音。他妈的我真想爬起来把桌子掀了——这是我想说的。接下来演的是战争片。啤酒瓶子像手榴弹一样,乒地一声接一声,弄得全屋鬼哭狼嚎。我假装说梦话,又翻个了身。我不能一声不出,我怕她们把我忘了,倘若最后全都喝疯了,把我当男人打成肉饼,那也是白挨揍。我翻的那个身,技术含量很高,因为我做出了电影慢镜头的特技效果。我总是做梦,对这样的表演非常拿手。我弄明白了,这就是传说中的离婚沙龙。房东忙活了一下午,把泪水汗水全滴上,炒了这一大桌子离婚宴。她还要做总结性的发言——咱们女人不容易,都说女人能顶半边天,现在咱就顶个破锅,过这缺牙露齿的日子。那也得好好活,男人那鸡巴玩意儿,有的是!一抓一大把!来喝酒……她们总是对准男人的命根子说事,又用香烟点燃与乳房有关的话题。半根烟过后,她们开始谈房事,各种版本争相登场。房事是脱衣舞,堕胎是舞下囚,妇科病是什么?我不想听了。我不得不起床,我说我去趟厕所。然后我就再也没有回来……
很晚很晚,翠翠回来了。我从厕所听见她细碎明朗的脚步向我走来,我的天亮了!我的屋里已是烟雾弥漫,她们全部醉倒了,只有啤酒瓶子没醉,无奈地直着脖子在桌子上硬挺着——我沮丧地向她叙述这一天一夜的遭遇。我混沌困倦的身心,急需换一个环境。我觉得我中病毒了,整个人死机了瘫痪了,急需翠翠来杀毒。翠翠一边开窗一边放烟,哈西得勒,这样下去可不行!这多影响咱们以后恋爱结婚生孩子,这是多大的阴影!咱们换个房间吧!翠翠比我小,但在决定大事的时候,我比她小。也是因为有她,我才学会去做那个“小”。一直以来我总是装大,太累了。一个人如果总是硬撑着,早晚得把心弦挣断。以前,我打针吃药找她,打雷害怕了也找她,想打牙祭解解馋也是找她。今天打发这群女鬼画皮还得靠她!她连夜寻找房间,最后南征北调,好歹周旋出两张床,我和她连夜搬了过去。我们两个睡对床,我和她终于过上了人的日子。从此,我再也不想离开翠翠这个芳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