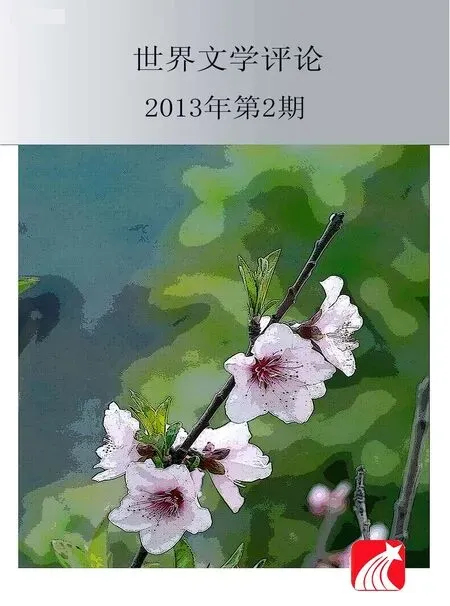王尔德与无为而为
2013-11-15徐海华
徐海华
王尔德与无为而为
徐海华
英国作家王尔德是东方文化的崇拜者,他对庄子“无为而为”思想的吸纳尤其值得关注:王尔德对庄子思想的认同并非只停留于表面,而是领悟“无为而为”思想的本质,将其运用于文学创作及他的文艺批评,这坚定了自身的价值判断;并使其成为他艺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看似矛盾的文艺观及创作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但同时,王尔德对于“无为而为”思想的接受不是全盘的吸收,而是出现了既吸纳又背离的复杂现象。
王尔德 庄子 无为而为
Author: Xu Haihua
(1971- ), A Lecturer in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of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ster of Arts.Research Areas are English Literature and Literature Translation.19世纪末西方文化传统开始出现断层:基督教信仰动摇、理性主义渐趋没落。人们寻觅新的视角、新的价值判断来重新审视人类自身以及各种文化形态,试图在处于动摇、崩溃之中的传统价值体系之外,重新建立起人类的精神家园。越来越多的西方文人、艺术家将目光投向东方,试图找寻理想的典范。
王尔德,一个生活在崇拜并且迷恋东方艺术品的国度中的艺术家,其本人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喜欢东方的小物品,经常谈起东方情调,从中国花瓶、折扇、孔雀羽毛到各种奇花异草,都是他热衷收藏的物品。“牛津大学时代的王尔德就开始成为中国青瓷的收集者,他用中国花瓶装点房间,并发现让自己配得上这些青瓷瓶是越来越难了”。他看中国人的生活无处不散发着优雅的气息。画家比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采用东方绘画的线条与黑白,为王尔德名噪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剧本《莎乐美》作插图,更为此剧平添了一层东方色彩。王尔德精心构建的带有东方色彩的生活空间与艺术世界,以其生动、直观的形式表达着王尔德的审美理想;他认为,东方艺术代表了一种绚丽多彩的表层的美。他对中国艺术的偏好非但迎合他的唯美主义原则,体现了他对“纯形式美”的爱好,更是借这异域之美来实现唯美主义超越现实的艺术理想。
当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的英译《庄子》于1889年问世,立刻受到西方学界的重视。崇尚东方文化的王尔德对于次年读到的距离他2 000多年前的中国古代哲人——庄子著作的英译本大加赞叹,并为此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位中国哲人》的文章,尤其对庄子的“无为而为”的哲学思想推崇备至。庄子哲学所体现的形而上的思辨色彩、怀疑精神和敢于反叛的批判力量,与王尔德的离经叛道的思想契合,使得王尔德自觉接受了遥远东方的这位庄子的哲学思想。在王尔德接触庄子作品后的第二年,他在著名文论篇《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中,就“无为而为”的重要性做了专题评论,“上帝的选民,活着就是要无为而为。行为是有限的、相对的,而悠然自得地坐着,静静观望,在孤独和梦境中徘徊漫步的人,他们的想象才是无限的、绝对的。”(赵武平《王尔德全集》卷4,431)在他眼中,庄子像古希腊早期那些晦涩的思辨哲人一样,信奉对立的同一性。他在《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中所主张的无感觉、一种纯粹的内心想象的静观、无为的思想,是对庄子思想在精神深处的认同。他肯定了基督上帝的存在,从而否定了人生的有限性,以便使人的生命摆脱了感官的束缚,在想象的世界中达到无限。然而,这位在无为中拥有盼望,在宁静中寻觅永恒的王尔德,与先前的那位创作《道连•葛雷的画像》的现世主义者是多么的大相径庭。在他的这部代表作中,他借亨利之口说,“你只有有限的岁月可以真正地、完全地、充分地享受生活”(赵武平《王尔德全集》卷1,26),“生活吧!让你身上美妙的生命之花怒放吧!什么也不要放过。要不断探索新的感觉。什么也不要怕……一种新的享乐主义——这是我们时代的需要”(赵武平《王尔德全集》卷1,26)。他似乎已否定了生命的彼岸,将人生仅仅放置于现世的感官世界之中,现世的享乐已然为其生命的主旋律。人们应如何看待王尔德思想上的这种矛盾性呢?长期以来,王尔德一直被视作是一个充满矛盾并自觉体现其矛盾性的作家。同时代的另一位唯美主义作家及评论家阿瑟•西蒙思(Arthur Symons)曾评论道,王尔德“不断说出敏锐而对立的观点,向我们证实了相反的东西也同样可以是真实的东西”。在《道连•葛雷的画像》一书中,王尔德借亨利之口宣称:“人生的目的是自我发展。充分发展一个人的本性,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世上的目的。”(赵武平《王尔德全集》卷1,22)这与庄子无为学说中的涤除人为,做一个静观宇宙的“至人”异曲同工。王尔德借他者来认知,看到了庄子无为思想的现实意义。小说《道连•葛雷的画像》中的主人公道连•葛雷,可以说是唯美主义人生艺术观思想的一个典型的体现者,而他的画像则可以说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道德观念的一种物化形象。道连•葛雷最为关心的是如何才能够摆脱道德的制约,以便自由自在地进行感官的体验与历险。小说再现的是唯美主义艺术人生的悲剧,它深刻地揭示了唯美主义者在道德意识浸透于社会每一个角落的情况下,其个性的尴尬和毁灭。现代人的所作所为在庄子“无为精神”的对应下可悲可感,王尔德借助这一哲学思想对19世纪末英国盛行的功利主义以及政府专制行为对人的个体的束缚提出尖锐的批评。
王尔德对于庄子思想的深切感悟,成为他艺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看似矛盾的文艺观及创作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但不能忽视的是,对王尔德来说,庄子倡导回归的自然原始状态,是令人惊奇的单调乏味;绝对未经加工的条件,亦足以使人们丧失个性。王尔德张扬个性的理想在现实人生中、大自然中破灭了,他开始了新的追求:将艺术和美视作个性得以张扬的“无忧的殿堂”。他反对艺术模仿现实,主张创作过程中的创造性想象;他还反对创作中感情的直接流露,主张以自觉的人为因素加以控制。他为个性的自由、主体性的实现开辟出一片远离世俗的世外桃源。艺术成为一种独立的、只为自身而设的形式,艺术家可以完全不必再去关注社会人生,甚至是自己的内心情感,而只将目光投向纯粹的艺术形式。在这种对现实人生和自我的绝对超越之中,艺术家终于在一个纯粹的形式世界中找寻到了自身个性的自由。尽管他未能欣赏庄子的“天籁之美”——“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未能赞同“无为”思想的生发点——天人合一、顺应自然。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王尔德似乎从遥远而古老的东方哲学中汲取到某种灵感,获得某种启示,甚或以为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
注解【Notes】
[1]周小仪:《消费文化与日本艺术在西方的传播》,载《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4期,第5页。
[2]Beckson, Karl.(Ed.).Oscar Wilde: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0, p.96.[3]见《庄子•外篇 •天运》。
赵武平:《王尔德全集》卷4,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1页。
赵武平:《王尔德全集》卷1,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Oscar Wilde, the famous British writer, is a follower of Eastern culture. What deserves to be mentioned is that Oscar Wilde imbibed Chuang Tsu's "Thought of doing nothing"(a Taoist concept of human conduct). He did not linger on the surface of the thought, but tried his best to tap it .He applied this kind of thought to his literary creation and literary or art criticism, and made his own judgment of value more steadfast.
Oscar Wilde Chuang Tsu Thought of doing nothing
徐海华(1971- ) 女,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讲师,硕士, 研究方向为英国文学、文学翻译。
作品【Works cited】
Title:
Oscar Wilde and Chuang Tsu's Thought of Doing No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