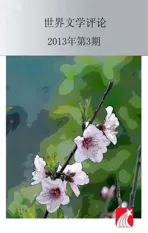艺术还原轴心时代的东方法制本相*
——《大秦帝国》的再评论
2013-11-14张祖群
张祖群
艺术还原轴心时代的东方法制本相——《大秦帝国》的再评论
张祖群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等于小说和影视艺术;同样,小说和影视也不等于历史。历史真实是艺术真实的基础,真正理解电视剧《大秦帝国》的关键在于摒弃暴力血腥和“文革”批评话语,从艺术的角度还原轴心时代的东方法制本相,还原当下经济社会改革的法制趋向和大一统的历史本意。通过舞台的英雄悲剧、银屏的幻灭喜剧,可以充分理解我们这个民族所走过的上下五千年艰难历程。历史 艺术 法制趋向 大一统 《大秦帝国》Author:
Ph.D. Zhang Zuqun is associated professor and master tutor in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He is a postdoctoral fellow at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and Research scholar at College of Art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He majors in cultural geography heritage tourism and cultural industry.从《雍正王朝》到《大明王朝1566》,从《北平无战事》到新《三国演义》,从《楚汉风云》到《楚汉传奇》,从《大秦帝国之裂变》到《大秦帝国之纵横》,古装电视剧《大秦帝国之纵横》总投资达1.3亿元(吴晓东),迈入“知名导演+豪华阵容+高科技+高投资”组合的“亿元电视剧新时代”;敢于下本钱、高投资,又形成一部“大手笔、大制作、大阵容、大情怀、大看点”的史诗作品。历史剧《大秦帝国》(第一部《裂变》)播出后,学术界对其毁誉参半,批评者有之,赞美者亦有之,笔者在这里主要针对第一部,同时也结合刚播出的第二部《纵横》,做一个学术回应。
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一)批评者的典型观点
《大秦帝国》的严重缺陷在于缺乏对秦帝国反人道、反文明的暴力专制的深刻反省(李衍柱《弘扬中华原生文明的悲壮史诗——评孙皓晖的〈大秦帝国〉》,38—43)。秦国法制固然有尊王、反智、愚民的局限,但是也有奖励农耕、激发生产力、缓和生产关系的重要进步意义。如果从百姓没有享受到法制之进步的角度,单一性批判,不免使人想到了“文革”话语权的重现。更有人认为《大秦帝国》是在过度吹捧秦始皇,不惜一再吹捧,如同惊天谎言(史式 43—46)。“文革”的尊神造神运动好像又复出了,他们是在批判作者和小说本身,还是在影射“文革”?有人认为历史主义不是根基是陷阱,孙皓晖是拿历史上落后战胜先进的例子来鼓吹暴力,是搞暴力崇拜和国家主义(董健口述,高子文整理 70—73)。有人认为作者对暴君的赞美是最粗俗的、最糟糕的(李建军 80—86),因为要尊重生命、尊重真理,摒弃暴力和血腥。
(二)赞扬者的典型观点
有人认为作者将自我的个人精神体验、对历史的重新解读有效融入独特的艺术境界,重现大秦帝国的辉煌历史(安晓东195—197)。它继承与超越了中国“史传”、“诗骚”的传统,以极强的可读性展示细节的真实,多样化运用夸张、怪诞、反讽与狂欢化诗学原则,坚持历史现实主义的开放性和未完成性辩证统一(李衍柱《历史现实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孙皓晖〈大秦帝国〉艺术特征论析》,3—13)。它通过弘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华民族精神,通过一幕幕威武雄壮的英雄悲剧、一幕幕历史丑角的幻灭喜剧,书写了秦人的气度、描绘了秦人的风采,展现秦国的意气风华、气吞山河和起伏跌宕。
笔者不想褒贬这些观点差异,只是从影视美学的角度,剖析小说已经改编的电视剧之美;同时跳出影视之后,探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张祖群《试论〈大秦帝国〉的影视美学特征——基于历史正剧的讨论》)。
二、变法的背后固然有暴力存在,也是历史的进步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商鞅和一千个大秦帝国。商鞅变法是秦国历史长河中的分水岭和转折点,是秦国逐渐强大的第一块基石,更是华夏文明史中第一次将法治的理念变为现实、第一次建立法律完备的法治国家的伟大试验,特别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华夏民族的一个族群当中确立起坚定的法治信念和守法精神。所有这一切,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都是极其宝贵的财富。对于商鞅和秦孝公的这场改革,有几个细节需要我们思考:①秦国开始应该选择法治与民主的改革,还是人治与独裁的社会?②改革到底是拥戴激进式的还是渐进式的?③变革中需要什么样的人物?是迫切需要还是已经出现一位铁血改革人物?
卫商鞅和秦孝公渠嬴梁生死相扶造就了一个强大的秦国,可谓铁血手腕强制进行法治立国,扫除一切保守势力,包括扫除势力强大的皇亲国戚。这是这场改革得以推行的重要人力保证。历代中国王朝,国力的保存,必须依靠军事实力人物,同时,改革最大阻力者也可能是军事实力人物。公子嬴虔就是一例。嬴虔有“断指血书复生”的硬伤,后来劓刑沉沦20年假死后的复出复仇,最终都为商鞅之死定下了灭亡镣铐,但是若没有嬴虔和秦献公在世时,弱秦之国可以在河西与实力远远超出自己的魏国虎狼将士周旋吗?弱秦能打破六国几乎分秦的弥天阴谋吗?几乎能抵抗帝国一次次愈加猛烈的进攻吗?商鞅变法之后,嬴虔有最后20年仇恨之火,准确说是始终“阴魂不散”后。嬴虔最后重启朝政,复活后成为甘龙老族势力复仇与灭仇、新政与新法派较量、一方新君与两方死臣的势均力敌天平的最后均势打破者!从嬴虔的人生轨迹变化来看,任何一个时代改革中尤其要注意掌握权力的关键人物。
2400年前的商鞅变法无疑具有限制王权的雏形和民主社会的萌芽。在政治上削弱既得利益群体势力,进行重新分配。在经济上使部分奴隶变为农民,奖励农耕和征战,提高生产力。在军事上打破“拼爹”的世袭垄断,使有功者得赏,有错者受罚,形成上下阶层流通的通道和良性的竞争机制。后世的君王和统治者为了巩固他们的地位和权利,退缩于进步的社会波涛之外,逐渐逾越于法律之上,鱼肉百姓,士学工农商只能以儒学作为互相制衡的武器,削弱法律对君王帝王以及上层贵族的限制,也削弱了民众对于统治剥削阶级和既得利益者的反抗,法制民主社会就这样被扼杀在摇篮中了。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很有意义。战国七雄的政治博弈书写了轴心时代的大历史:公元前422年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公元前409年赵烈侯用相国公仲连进行改革;公元前382年楚悼王用吴起实行变法;公元前360年齐国起用邹忌“谨修法律而督奸吏”实行改革;公元前354年齐国以孙膑为军师,发动桂陵之战;公元前342年马陵之战齐国战胜魏国;公元前351年韩昭侯起用申不害变法;公元前356年和前350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公元前361年魏惠王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公元前354年魏国起兵伐赵,次年破邯郸,齐国围魏救赵;公元前352年魏韩联军攻齐、宋、卫;公元前351年魏赵结漳水之盟,魏将邯郸还赵;公元前350年魏反攻秦,秦孝公在彤(今陕西华县西南)与魏惠王相会修好;公元前342年魏国三战皆败;公元前314年燕国内乱,齐攻燕后退兵;公元前313至前311年楚国三次攻秦均败;公元前306年楚国灭越;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公元前287年赵魏韩燕楚五国攻秦,秦割地求和;公元前286年齐灭宋,引燕秦韩赵魏围攻;公元前278年燕昭王死,太子燕惠王即位,齐国大败燕军;公元前280年楚国攻秦欲收回巴国,败;公元前279年楚国被秦败于鄢(今湖北宜城东南);公元前278年秦破楚都郢,屈原投汨罗江自尽;公元前241年楚国迁都到寿春。越是征战的年代越是思想浮现涌出的年代,一个文明的创生期和战争、国家统一联系在一起,往往是最有活力的、最富创造力的。秦人历经800年从西迁陇右到统一天下,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从附庸到封国,从王国到帝国,从西陲到关中,从雍城到咸阳,从巍巍始皇陵到宏图遗恨未建成的阿房宫,秦王朝的物质遗存、制度影响和天下雄心至今为人所称道(梁云、蔡庆良 30—38)。通过考古出土的秦钱流通区域可以看出,正是因为商鞅变法,国力猛增,关东、西南和西北几大秦钱流通区域的开辟使得秦人不仅扩张政治版图,而且超越关东六国的经济实力,将六国连横抗秦、秦国偏安一隅的政治地理格局被打破,使得秦统一中国具备强大的经济地理基础(陈隆文 83—87)。《大秦帝国》也不例外,诠释了这个道理。秦文明是统一的主流政治文明,固然汉承秦制,“秦文明”从属于广义的汉文化范畴,秦文明创立的单一制帝国国体和独裁专制政体(叶文宪26—30),2000多年为封建中国所继承,几无改变。但是这不是否定秦文明作为中国的“原生文明”的根本理由,当然也不是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五四”以后主流话语权的非秦、尊孔,其实历史在是反复的游移思想中失去了基本的话语根基,用一元文明抹杀多元文明的存在是不可取的,因为创建大一统的秦国铁血文明是中国文明史的根基(孙皓晖,第5期,78—81;第3期,55—59)。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中国历史的时空中,分裂占大约2/3的时间,统一占大约1/3的时间。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统一是王朝更迭不息的主流政治目标和主流政治话语。
历史上中国任何一个王朝,几代君主之后,都是积贫积弱,变法改革者千万,数不胜数。然千万例中成功者仅二:秦商鞅变法与明张居正变法。二者变法相隔千年,流传千古,不同之处是商鞅变法之后,人在政在,人亡政亦在,政通人和,继续以法治国,依法治国,法不留情,疲弱之秦终成强国劲旅;然而张居正变法之后,人在政在,人亡政息,除却自己满门查抄,长子自缢身亡,三子自杀未遂,家眷十数人饿死之外,张居正推行的“考成法”、“一条鞭”法悉数推翻如旧。两者之比,于今仍有折射之意者唯有商鞅变法。当今之中国,推行以法治国,中国进行了制定相应法律法规的高潮,要建立一种制度,这种制度能够制约我们的执政者和权力之印,一个国家建立了一套完善行之有效的制度,执政者不搞特权,执政者在制度的制约之下工作,公民在法制前提下有条不紊地工作生活,这个国家才是有救了。只有以强大的法制为保障,才不会出现文强之流,才能根除改革转型时期社会的种种弊端,使我们步入真正的公民社会、公民国家。在法治和法制建设的轨道上,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遥远。
当然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随着社会发展态势而相应改变,法律的最终目的是用一定尺度奖惩措施来制衡人民的行为,最大程度提升绝大多数人的文化素质,最低限度的减少和规范不道德的行为出现概论,最大限度的保证全民的公正、公平、民主和社会稳定进步运行;包括制定法律本人在内的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的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法律的施行、运行需要不断地改善和完善。“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最终一个国家会依照法律进化成高度民主自由的国家。任何特权阶级、党政、集团、个人都不可能逾越法律之外,依法治国和以法治国,形成一种多利益主体的权利制约!
三、讨论:何为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
2013年播出的《大秦帝国》第二部《纵横》讲述了商鞅变法后秦国日趋强大,国君惠文王虽年轻,但果断任用张仪,再一次君臣携手,纵横捭阖,在风云多变的险恶环境中,一次次突破外交困局和险局,将军事实力角逐与国家综合实力的政治博弈运用得淋漓尽致,奠定了秦国独大乃至统一中国的政治地理基础(郭婷)。张仪、苏秦、四大公子等粉墨登场,百家争鸣,各个历史人物演出了一场热血沸腾的历史正剧。他们在列国争斗过程中上演了一场场大智之战、一场场大勇之战,合奏了一篇又一篇色彩斑斓的群雄争霸、战国邦交的华彩乐章。这里进行《大秦帝国》第一部与第二部的比较:①《裂变》中龙贾被商君打败后放回,而《纵横》出场即有秦魏一场战争,主将是魏国龙贾老将,这两次战争到底是什么关系?前后怎么没有逻辑连接?此是白璧微瑕。②《裂变》里秦孝公嬴渠梁有如海纳百川的大义宽容,任用商鞅进行大刀阔斧的革新变法。君臣之间之肝胆相照、生死相扶为观众所深深震撼。“君为青山,我为松柏”,缔造了君臣携手、荣辱与共的千古佳话,而在《纵横》中,秦惠文王和张仪之间类似的君臣互信、不离不弃的感人情形再次上演,贯穿始终。③《裂变》凭空编造白雪、玄奇的凄美爱情,基本无历史根据,而《纵横》太过注重芈妃,简直就是她的奋斗史和恋爱史,她和他儿子黑武王的剧情太多。④《裂变》中秦孝公嬴渠梁最后为了事业连女人都不要了,只要江山,仿佛是一个不懂浪漫的木头呆子,而《纵横》中秦惠文王表演略显夸张,用力过度,和若干个女人纠结,如同90后的浪漫恋爱史。⑤《裂变》中商鞅变法自强,本想归隐商山,却被自己立法所束缚,被怕“连坐”店家告发,最后被秦惠王处“车裂之刑”,惨遭灭族,而《纵横》中张仪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游说了魏王、楚王、韩王、齐王、赵王、燕王。但是英雄的最后结局,却很凄凉。⑥《裂变》中赵季平为之配乐,赢得观众和业界如潮好评,而《纵横》中赵季平担任音乐总监,其子赵麟为之作曲,再谱荡气回肠的音乐作品。
小说、影视之内是艺术,小说、影视之外要尊重历史。尽管历史真实中张仪与孟子可能没有发生辩论,屈原也不是法家和楚国大司马,公孙衍不是“如犀牛之首,锐不可当”而得名,商鞅也没有被复仇的秦国人活祭(陈辽 15—19),但是历史的真实丝毫不影响影视的艺术真实。例如扶苏、蒙恬和李斯性格中二重性揭示,就是这种艺术真实的流露。只要在尊重历史的主要人物、重大事件、重点地域不变的前提下,为了更加深刻还原历史,何尝不能做一定合理的富有逻辑性的艺术虚构?(刘原34—35)曾一果就是通过诗的文化意向方式复活了秦王嬴政、太后赵姬、将军蒙恬、鼠相李斯、奸相吕不韦、壮士荆轲、反秦义军首领陈,任意买卖奴隶、任意杀害的工匠,无名的兵马俑,还有孟姜女、范杞梁,以及诸多淹没在历史浪潮中有名或无名的人物(曾一果 95—100)。若一定要全部追求100%的真实,历史人物的死在演出中是否得真死?历史事件在历史的当时和偶然之间其实显示不出重要性,需要后来的历史影响来证明它的唯一性,岂不是任何的复原和解读都是毫无意义?历史事件发生的场所早已一去不复返,在影视基地的拍摄岂不是造假?若一定要全部追求100%的真实,那后世人们游览古物、睹物思情,又有何意?今人在遗产地旅游岂不是虚无?这又如何解释如火如荼的秦文化旅游热?例如迄今超过6000万人次前来西安秦兵马俑博物馆参观,迄今179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来参观过兵马俑。为了扩大旅游影响力,在西安临潼区秦文化园区,以秦始皇陵兵马俑“世界第八大奇迹”为主体,兼有秦皇大剧院和大型音乐史诗舞剧《秦始皇》、秦皇温泉度假酒店等,形成一个享受高品质的秦文化旅游综合体(李勇,梁娟)。原本游客很喜欢,按照100%真实的逻辑,这岂不是成了虚无的历史景观?
今人脑子里关于秦国的印象几乎就是“暴秦”。很多人是通过读了《大秦帝国》小说,看了《大秦帝国》电视剧,突然发现其实深深误解了秦国,有些传统的误解是空穴来风,以讹传讹。对于历史要客观对待和中立评说。自司马迁在《史记》里大肆渲染“暴秦”之说,后世史家几乎成为常例,以为秦就等于是暴秦。秦国“焚书坑儒”、秦赵“长平之战”坑杀30万降卒,当然是暴政,但是这些其实是个别事件,《史记》却渲染秦朝暴政为国策。试问,春秋战国,哪一国不暴,哪一国不是以暴易暴?司马迁自小在拥汉环境下长大,偏见于秦,无可非议,且是汉议前朝的主流。文景之治要在主流舆论上胜过秦政,只有非秦、暴秦。可悲的是,后世史家陈陈相应,因袭这种论调。不管《史记》和后世批判秦国暴政苛法的人怎么“书写”历史,秦国在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朝代,他拥有的极高的历史地位应该得到尊重和还原。史无前例的,摧古拉朽的,激进革新的铁腕魄力为后世王朝望尘不及。随着人们对历史的深入探究和对各种文物、遗址的挖掘考证,随着一幕幕历史面纱的揭开,我们应该对2400年前的列国征战历史场景中的秦历史有“新”的公允评价。任何强力的存在,自然有他独到的一面,任何弱国能够自强,自有他独特的成功之处,不是个别历史污点和失误能掩盖他的熠熠光泽的!
在此,请允许我回应一下学术界的批评与赞扬。试问批评者:一部《二十四史》,哪一部不是暴力推动的历史?哪一部不是战争和流血的历史?暴力是历史过程中要付出的必然代价,而不是一种结果。正是因为历史有长期性的暴力,我们才要呼吁和平和非暴力,呼吁不要流血,呼吁渐进式改革。试问赞扬者,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有机体,又何尝不是在这种悲剧与喜剧的转换中,以微笑的方式与自己的过去诀别,从此踏上另外的征程?《二十四史》只在叫人有所不为、让封建社会在超稳定的固步自封中折腾至今,中国历史精彩的一幕早已在唐宋演完,只是至今还没有谢幕(雷电 F1-F2)。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等于小说和影视艺术;同样,小说和影视艺术也不等于历史。历史真实是艺术真实的基础,于历史正剧而言,善于用艺术虚构趋向达到“艺术的真实”,用“艺术的真实”丰富完善“历史的真实”,实现历史认知、审美和娱乐三重功能的完美融合,实现历史戏剧化和戏剧历史化的完美融合(韩业庭,饶翔)。美国思想史家、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于1988年在《美国历史评论》中杜撰出“historiophoty”(影视史学)一词,以区别于传统的“historiography”(书写史学)。如果说“书写史学”是以静态文字和言语意象来表现历史真实,那么“影视史学”则以动态视觉影像和电影论述去表现历史真实和历史见解(张旭鹏)。回到《裂变》,真正理解《大秦帝国》的关键在于摒弃暴力血腥和“文革”批评话语,还原当下经济社会改革的法制趋向和大一统的历史本意。法律是人存在于世的基本规则,一个人掌握得越早越能适应社会。法治社会的到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任何人都无法阻挡!同时我们通过舞台的英雄悲剧,银屏的幻灭喜剧,充分理解我们这个民族所走过的上下五千年的艰难历程。
注解【Notes】
吴晓东:《电视剧亿元时代》,载《商周刊》2013第21 期。
李衍柱:《弘扬中华原生文明的悲壮史诗——评孙皓晖的〈大秦帝国〉》,载《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1期。
史式:《警惕秦帝国的专制幽灵——孙皓晖隔行论史何为》,载《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1期。
董健口述、高子文整理:《〈大秦帝国〉的“反动性”》,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
李建军:《怎可如此颂秦皇——从〈大秦帝国〉看当下历史叙事的危机》,载《南方文坛》2010年第3期。
安晓东:《一种精神的深度对话——论〈大秦帝国〉的主体意识及其接受效应》,载《西安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李衍柱:《历史现实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孙皓晖〈大秦帝国〉艺术特征论析》,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张祖群:《试论〈大秦帝国〉的影视美学特征——基于历史正剧的讨论》,载《世界文学评论》2014年第1期,待刊。
梁云、蔡庆良:《大秦帝国崛起之路》,载《中国文化遗产》 2013年第2期。
陈隆文:《有关战国秦半两钱的流通区域问题》,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8卷第4期。
叶文宪:《不要专制的“帝国文明”——驳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原生文明论》,载《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9期。
孙皓晖:《〈大秦帝国〉对话当代文明》,载《社会观察》2012年第5期。
孙皓晖:《〈大秦帝国〉对话当代文明》,载《现代人才》2012年第3期。
陈辽:《是历史主义,还是伪造历史?——再评〈大秦帝国〉》,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李衍柱:《偶然中的必然:〈大秦帝国〉的悲剧品格》,载《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
刘原:《电视剧〈大秦帝国〉研讨会辑要》,载《当代电视》2010年第4期。
曾一果:《帝国的历史与民族的历史——读小海的〈大秦帝国〉》,载《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3期。
新华社记者李勇、梁娟:《史剧〈秦始皇〉将“再现”〈大秦帝国〉历史》,载《陕西日报》2010年12月3日,第1版。雷电:《与一个词语有关的诸多遐想——〈白鹿原〉中关中方言的思考》,载《唐都学刊》2011年第2期。
张祖群:《〈武则天秘史〉影评:从历史真实到影视真实》,载《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韩业庭、饶翔:《历史剧:应传播正确历史观和价值观》,载《光明日报》2013年10月14日,第14版。
张旭鹏:《电影与历史》,载《光明日报》2013年11月21日,第11版。
Title:
Restore the Axial Age of Oriental Law Nature Based on Art: Writing after Watching the Great Qin EmpireHistory is the history, the history is not equal to f ction and f lm and television art; Also, novels and movie and TV is not equal to history. Historical truth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artistic truth; really understand The Great Qin Empire is the key to discard violence bloody critical discourse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restore the axial age of Oriental law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t, the reduction of the current economic and social reform trend and the unif ed legal system history. Hero tragedy through the stage at the same time, the screen the disillusionment of comedy and fully understand our nation through f ve thousand years of hardships.history art the rule of law trend the great unif ed The Great Qin Empire张祖群,湖北应城人,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博士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党支部书记、副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文化产业与遗产旅游等。主持国家级、省部级等各类课题15项,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多项,出版著作3部,发表核心期刊论文19篇,25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或索引,3篇由CSCD-《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2006年引用。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青年专项课题(CGA12100);北京市属高等学校人才强教深化计划中青年骨干人才资助项目(PHR201108319);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十二五”高等教育科学研究规划课题(BG125YB012); 北京市社科联青年社科人才资助项目(2012SKL027);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2JGB117);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年度“文化产业重大课题研究计划”中标课题“文化产品政府采购研究”(CIRP13020099);北京对外文化交流与世界文化研究基地2013—2014年度青年研究项目“文化多样性:逻辑关系、案例与政策研究”(BWSK201304)。2013年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项目“北京文化多样性研究:逻辑、案例与政策”(2013D005019000005)。本文是张祖群在北京市属高校教师发展基地(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戏剧与影视学专业)研修期间工作成果。特此对指导教师表示感谢。
作品【Works Ci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