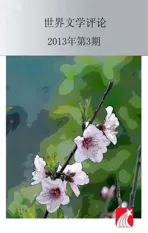台港文学研究的出新和诠释权的“争夺”
——古远清教授访谈录
2013-11-14胡朝霞
胡朝霞
台港文学研究的出新和诠释权的“争夺”——古远清教授访谈录
胡朝霞
古远清(1941— ),广东梅县人。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为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文系台港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先后主持教育部课题、国家社科基金课题4项。在海内外出版有《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台湾当代新诗史》、《香港当代新诗史》、《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当代台港文学概论》、《庭外“审判”余秋雨》等专著。
胡朝霞:华中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
胡朝霞(以下简称“胡”):你在古稀之年迎来了学术著作出版的井喷期。过去你在海内外出版有各类著作多种,近年又有《古远清文艺争鸣集》、《几度飘零——大陆赴台文人沉浮录》、《消逝的文学风华》、《两岸四地文坛现场》、《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从陆台港到世界华文文学》出版。在出书速度上,你称得上是 “刽(快)子手” 啊。
古远清(以下简称“古”):白舒荣和刘红林两位女土称我 “活着为了写书 ,写书为了活着”,这倒蛮符合本人实际。
胡:中国古代有江郎才尽的故事,你年过古稀,有无 “才尽”之感?
古:“才尽”应与年龄无关,而与对研究现状、研究题材和研究对象失却敏感相联系。“才尽”的人往往找不到新的学术生长点。我为了将自己和“江郎”区隔开来,近几年在两岸三地著书时均尽可能出新,如我最近获批准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台湾文学史》,便是为了填补两岸台湾文学研究的空白. 本来,台湾文学研究比大陆文学研究滞后。内地出版过多部《台湾文学史》,最多只写到20世纪末为止。本课题专门研究新世纪的台湾文学,其意义在于推动台湾文学全面深入的研究。过去,台湾文坛流行“自由中国文学”、“台湾乡土文学”概念,其能指只代表主流的三民主义文学或反主流的本土文学,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台湾文学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新世纪的台湾文学”则试图去除因省籍情结而导致历史误置和意义歧见,在多方面的考察和沟通中完成不分省籍的台湾文学总体化,为“中华文学”在台湾的复兴提供理论支撑。
胡:作为当代文学史家,你单枪匹马写作“六史”——《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台湾当代新诗史》、《香港当代新诗史》、《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 所奉行的是“私家治史”准则吗?
古:私家治史观点和文笔容易得到统一,不必为贯彻领导或主编意图,将个人见解消融掉。当然,利弊总是并存的。私家治史虽然可以较充分地表达个人观点,但也不是没有任何拘束,个人见解都可以尽情发挥。毕竟在体制下的书写,不能无所顾忌。且个人写史也难以集思广益;对有些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可能难以写得深入。而且,工程太大,个人时间精力有限,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
胡:你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最近获“全国台湾研究会”第四届台湾研究优秀成果专著奖。你能否谈谈此书的写作初衷?
古:《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的写作有小小的希冀:在为两岸文学史写作提供原始材料以补充、完善现有当代文学史不足的同时,还企图用这部著作,引起当代文学史写作是否应加入关系史的思考。
拙著是从文学关系史切入的另类历史叙事,是一种非传统型的文学史。写作的着力点不在为作家作品定位,不以作家作品分析评价为主,不以建构典律为目标,而是抱着回顾与解读的态度,审视两岸文学关系从对立到亲和、从反叛到回归的发展过程,用“大叙事”与小细节相结合的笔调描述,不追求体系的严谨和完整性。在这本书里,无论是《春江水暖鸭先知》,还是《谁先偷跑谁就赢》,均将主流文学史遮蔽的某些史实或以为只需要“大而全”而不需要“零件”的材料展示出来,使两岸文学史真正成为一部多视野、多角度的多元共生的文学史。
胡:“两岸文学关系史”的内容很丰富吧?
古:可以说既丰饶又贫瘠,既单纯又复杂。“丰饶”是指两岸文学关系史所要面对的是两地文学的对抗与隔绝、开启与曲折、互动与冲突、封锁与突围。“贫瘠”是指无论在两蒋时代,还是民进党执政时期,作为同根同种同文的两岸文学,由于政治的干预,均没有产生像鲁迅那样的大师级作家。说其“单纯”,是指两岸文学关系在任何时期都受政治制度的制约,交流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下进行。“复杂”是说两岸认同的“一中各表”,有各种不同的诠释,具体到“台湾文学”的界说上,则有五花八门的表述。
胡:你这本书在分期上有什么特色?
古:毕竟篇幅有限,《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要在四十多万字的篇幅中把近六十年的两岸文学关系内容都写进去,谈何容易。为解决这一难题,也为了使读者有较明晰的认识,本书将两岸文学关系分为四段:军事主宰时期两岸文学关系的对抗与隔绝,和平对峙时期两岸文学交流的开启与曲折,民间交流时期两岸文学的互动与冲突,新世纪两岸文学关系的封锁与突围。在写作方法上,力求有宏观概括力和锐利的思想冲击力,如《民间主导与官方阻挠的二元格局》、《终止“勘乱”对两岸文学关系的影响》、《两岸对台湾文学诠释权的“争夺”》,均让读者不会因细节的叙述妨碍对全局的了解,不会因为有可读性而影响论述的深度。尤其是在《导论》中,注意历史意识与当代视野相融合;在《两岸文学的“互文”问题》中,注意问题意识与比较方法的结合;在《受制于政治价值观的文学现象解读》中,努力让理论阐释与文学史实互为呼应。当然,一涉及敏感问题的评价,就会引发争议,比如张爱玲的著作权属于台北皇冠出版社还是属于张爱玲在大陆的亲人,以及两岸文学谁的成就高、繁体字与简体字谁优谁劣,两岸均有不同看法。对这些看法,完全可以求同存异。拙著的表述,只是一家之言,欢迎持异议的读者、学者提出讨论和争鸣。
胡:《两岸四地文坛现场》共分挑剔大陆文坛、质疑香港文坛、争鸣台湾文坛、修补澳门文坛4部分,充分体现了你敢向权威挑战的风格和善辩的才能。难怪《名人传记》介绍你的学术成就时,将你称为敢于抵制不良文风的“学术警察”。
古:乍看这个称呼,以为姚文元又卷土重来了,其实,“学术警察”与姚文元打棍子完全是两回事。“学术警察”一词,出自哈佛大学教授杨联升之口。有人说我也是一位不为人们所注意和重视的“学术警察”。这大概是因为本人曾向某名人打假。如在评某名人的他传和自传时,多次指出其诸多伪造自己历史之处,由此被对方告到法庭。我给对岸出的《台湾新文学史》著者挑错“送大礼包”,做的亦是互相敬畏、互相监督、互相批评类似“学术警察”的工作。
在这个急功利的年代,在拉帮结派的文坛,陈平原说,“学术警察不仅没有成为榜样”,反而常常遭受误解,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并被迅速边缘化。钱理群也说:“公心不在,正气不彰,一切苟且马虎,这正是当下学术危机的一个重要表征。在这个意义上,呼唤‘樊骏式样的学者’,也具有同样的迫切性。”现在确实需要更多弘扬正气,批评弄虚作假和苟且马虎的文风,力挽学术危机的“学术警察”。
胡:在苏格兰爱丁堡举行的欧洲汉学会上,有一个小型圆桌座谈会上的主题是“由谁来编写《香港文学史》”。面对坊间出版的《香港文学史》及文体分类史,清一色出自内地学者之手这种无情现实,国外汉学家们责问香港学者:“为什么你们自己不去写本地的文学史?”到会的香港中文大学王宏志回应道:“《香港文学史》不一定要由香港人来书写”。
古:如果香港学者不了解香港文学或虽了解而评价时“党同伐异”,的确没有资格写。写文学史,本不应查户口、分地域,像早期的《中国文学史》就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写的。台湾地区文学史的编写现状也和香港差不多。为什么台港地区的文学史本地的学者基本不写,要由他人来写?说起来原因复杂。以香港而论,香港学者的学术观念、方法与内地不完全相同。如香港中文大学卢玮銮教授认为:许多原始资料还未整理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不应急于写。另一方面,在香港某些大专院校,研究香港文学不如研究内地文学、台湾文学地位高。传统偏见认为,研究古典文学比研究现代文学“身价”高,研究内地文学又比研究香港文学“意义”大。在台湾,不少教授醉心于参加各种文学活动,缺乏经济效益的学术专著写作极少有人肯干。
台港文学史由第三者来写,自有其长处。不少香港作家、学者身在“江湖”之中,不像外地人那样容易看清文坛内幕。不少学者还是圈子中人,由圈中人执笔写本地文学史必然会少写或不写圈外之人——即使写也可能多带贬词。由局外人写,自然可以减少“派性”,以较公正、客观的态度评述文坛的是非与功过。内地学者研究香港文学,20年来走过一条重政治功利到向着审美价值倾斜的曲折道路。他们的著作尽管有史料缺陷或错漏,但总的来说,包容性较大:不论是雅文学还是俗文学,不论是本土作家还是南来作家,不论是学院派还是非学院派,都能尊重他们的创作劳动,给予应有的文学地位。总之,编撰《香港文学史》最理想的人选应该是熟悉香港文学、占有资料充分、对香港文学研究深入、态度又公正客观的学者——而不管他是哪个地方人。
胡:台湾著名诗人洛夫说, 你的“《台湾当代新诗史》不论就史料的蒐集与运用、历史的钩沉与分析都能见到你的卓识、且敢于触及一些敏感的政治层面,实属不易,可以说不论大陆或台湾的诗歌学者、评论家,写台湾新诗史写得如此全面、深入精辟者,你当是第一人。你在书中批评了台独诗,必然会招致对方的强烈抵制,也可能受到你未提及的小诗社小诗人的不满,好在你在自序中已有了心理准备”。有道是:写文学史必须有智者的慧眼、仁者的胸怀和勇者的胆魄。在胆魄方面,你不怕某台湾诗人说《台湾当代新诗史》送到废品收购站还不到一公斤哩。
古:有道是不批不知道, 一批做广告。写台湾新诗史挨“骂”,本是意料中的事。古继堂的同类书出版20年,在受到许多赞扬的同时,也差不多被某些人骂了20年。正如一位台湾作家所说:“古继堂的《台湾新诗发展史》早已引发审美疲劳,怎么又来了一个姓古的,你烦不烦呀,你这两股(古)暗流!”故我有自知之明,在《台湾当代新诗史》书末写道:这是一部不能带来财富,却能带来骂名的文学史。这是一部充满争议的新诗史,同时又是一部富有挑战精神的文学史——挑战主义频繁的文坛,挑战结党营诗的诗坛,挑战总是把文学史诠释权拱手让给大陆的学界。
胡:内地学者在疏理香港文学发展线索,寻找香港文学发展规律,给香港作家作品定位,改变人们对香港文学知之甚少、甚至认为“香港是文学沙漠”的看法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内地学者研究香港文学,限于主客观条件,存在着哪种局限性?
古:注重香港文学的特点不够。有时用内地的评价尺度来要求香港文学。如有些人偏爱现实主义,尤其是偏爱批判现实主义,对揭露香港阴暗面的作品情有独钟,对写“东方明珠”所放出的光辉一面或用现代主义写成的作品,缺乏应有的热情。另有“中原心态”。对“南来”作家在香港文学所起的作用评价过高,对本土作家在香港文学发展中所作的重要贡献重视不够。此外是史料错漏较多。有的不属史料而是由于人情因素干扰,评价欠科学等等。
胡:对这种毁誉参半的《香港文学史》,有无“重写”之必要?
古:目前“重写”的条件还欠成熟。应该说,《香港文学史》的编写还处在探索阶段。现在出的几部《香港文学史》,还未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如果真的要“重写”《香港文学史》,依愚之见,靠香港学者似乎不现实。据香港文学研究专家黄维梁透露:香港艺术发展局曾悬赏三百万元请港人编写香港文学史,然而重赏之下没有勇夫,至今连写史的一点踪影都没有。之所以等不到,不妨回顾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艺术组组织本地学者编撰香港文学史时,“会议终于没有好好地着手寻找‘谁来编文学史’,而演成‘大家怎么看编文学史’了。”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难以选到最具资格的人。众所周知,“香港文学界门派甚多,目前还未有几多人能做到兼容并包及具备了文学历史的纵观水平……再说,要等一位能沟通各派作者文友,而个人文学思想又能兼收并蓄的编写者,谁也不知道将会在什么时候降临大地、光临香港。”既然香港难觅“能沟通各派作者文友”的学者,既然他们把香港文学史的诠释权拱手让给别人,外地学者便“空降”香江文坛,当仁不让地写了起来。
胡:在当下名目繁多、乱花迷径又不被众多香港作家、学者认同的香港文学史研究中,香港当代新诗史仍是十分寂寞的领域。你告别杏坛后,在赋闲中居然让《台湾当代新诗史》“下蛋”,生“第二胎”《香港当代新诗史》。可台湾诗坛与香港诗坛有明显的文化差异,你怎么可以把“香港新诗史”看作是“台湾新诗史”的“直系亲属”呢?
古:台湾、香港本来就有被“割让”的相似历史遭遇。在地理位置上,两地均属大陆的“离岛”。在意识形态方面,两地均不存在什么“社会主义主旋律”。他们的新诗比起内地新诗来,有太多的同质性。何况作为跨文化城市的香港,那里有不同背景的文化经验共存和交汇,比如在台湾诗坛颇为活跃的叶维廉、余光中等人,便是香港诗坛的要角。不是我故作谦虚,《香港当代新诗史》对我来说确是“拣”的。毕竟写完了《台湾当代新诗史》,写《香港当代新诗史》就顺理成章,下笔也顺畅多了。说“拣”或说下笔“顺畅”,决不是说香港新诗史容易写或暗含渺视香港诗人的意思在内。相反,香港新诗界有不少璀璨的名字,他们的光环逼使我总是睁大眼睛去审视他们。我既庆幸自己和这些相识或不相识的诗人心灵是如此贴近,但我又担心自己的拙笔不能将他们的文学成就一一道出。当然,《香港当代新诗史》并不是《台湾当代新诗史》的附庸或骥尾,两者有各自的独立性,但台港新诗确有“亲戚”关系,可参看该书第二章第一至四节。
胡:你写了四种台港文学分类史,有无“难言之隐”或“难以释怀”的事情?
古:如果说要有什么难言之隐,是无论在台湾还是在香港,山头“艳帜”高挂,不少圈内人互相瞧不起圈外的作品,以忽视别人的存在为荣。他们不读别人的作品却非常看重别人读不读自己的诗作及读后又如何评价。如果你真的去评价,评了他不同山头或不喜欢的诗人,他就有可能编织各种流言,说评者与被评者幕后一定有交易。
本来,在内地做新诗史研究,既不可能带来财富,也不可能带来太多的欢乐。写作过程,既枯燥又折磨人。为了查一条注释,常常花掉一个昂贵的下午。我过惯了寂寞清苦而孤独的书斋生活,到生命之秋仍不打算放弃“买书—评书—写书—出书—出游”这一嗜好,也算是一种坚守。
胡:有境外学者批评你是“典型的国内研究香港文学的传统派”。
古:这评价或许值得我反省,但并不符合我现今的研究立场。如果有人问我的思想光谱,我定位为趋向开放而非教条的评论家。在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高峰论坛上,我做了《重构“香港文学史”》的学术发言。这发言是我最新的学术观点。这观点,在传统派看来,我也许属新潮派,而在某些香港学者看来,我又有可能像古继堂一样被划入“拥抱教条马列主义美学残骸的学者”。我自信,在内地学者中,我还是比较注意香港文学特点的,并没有用内地的标准去生搬硬套。
胡:两岸存在着 “争夺”台湾文学诠释权的问题吗?
古:在黄山召开的海峡两岸苏雪林研讨会上,展出了台湾出的苏雪林《日记卷》,总计15册。这《日记卷》最先是安徽大学中文系沈晖征得苏雪林教授本人同意在祖国大陆出版的。正当苏氏日记装箱运回时,被台湾有关方面发现,连忙追回,说此日记的出版权在台湾而不在大陆,于是只好改由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主持整理出版。如果说,苏雪林《日记卷》还只是两岸整理权、编辑权、出版权之争的话,那两岸对台湾文学的诠释权之争,比这激烈得多,时间也长得多,屈指一算已快30年了。
胡:两岸的台湾文学研究竞争,无论台湾文论家如何认为他们的研究成果如何胜过大陆,但谁都不能否认,在《台湾文学史》的编写上,他们交出的成绩单不多。
古:眼见大陆一部又一部厚厚的《台湾文学史》及其分类史的出版,在占领大陆乃至台湾某些院校讲坛,某官员惊呼:台湾学者如再不急起直追,台湾文学的诠释权就拱手让给大陆学者了。他们不允许也不甘心大陆学者的观点占领台湾的教坛、文坛。于是有各式各样假借学术名义对大陆学者的抨击。如有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台湾文学史》的评价之争。一些分离主义的评论家们,认为大陆学者连什么是“台湾文学”都没弄懂。在他们看来,“台湾文学”就是台湾人用台湾话写台湾事的作品。而《现代台湾文学史》入评的作家有一大半不是“台湾人”而是大陆人或曰外省人,因而余光中们的作品应从台湾文学史中删除出去。至于评价的标准和对许多作家的定位,他们也无法赞同。本来,《现代台湾文学史》有许多缺陷,对此完全可以批评。可台湾的某些本土评论家的评论角度不在于此,而是在向大陆学者“争夺”台湾文学史的诠释权。台湾某本土作家在批评辽宁版《现代台湾文学史》和福建版《台湾文学史》时说:大陆学者在进行台湾文学研究时,把台湾文学看成是中国文学的一环,是传统华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老调重弹,认为这是大陆学者“不了解台湾民族主义的结构”,是“从政策性立场出发”否定了这一“民族主义结构”。他在文章中提出台湾作家的“双重性民族结构”和台湾文学中的“民族主义结构”的主张。这种论调,马上引起辽宁学者张恒春和福建省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的集体回应。福建的学者认为: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难免有狭窄、浅置、误差的一面,但说“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是“老调”,这个观点正是那位评论家自己过去坚持的。所不同的是,他现在看风使舵,由主张“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环”而改为主张“台湾文学国家化”了。
胡:台湾文学研究不能由政治主宰,但却无法摆脱政治的影响。陈芳明新出的《台湾新文学史》,你如何评价?
古:这本书框架全新,分期有特色。比起叶石涛过于简陋寒伧还不是正式的文学史《台湾文学史纲》来,在时间上多写20年,且不局限于岛内单一族群的狭窄立场,视野显得相对宽阔。
可陈芳明的出发点不对, 他声称写《台湾新文学史》是为了“抗拒中国霸权的论述”。在开列祖国大陆出版的并不全面的《台湾文学史》书目后,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把“台湾文学边缘化、静态化、阴性化”。他尤其对大陆学者赞扬台湾诗人思念祖国母亲的论述极为反感,认为读大陆学者写的《台湾文学史》,就好似读“外国文学史”。这种“颠覆”未免危言耸听。他反对把台湾文学“阴性化”,而他的“阳性化”无非是“台湾文学的自主性、独立性,台湾文学决不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之类的陈词滥调。 在论述反共文学时,陈芳明竟说“反共文学暴露的真相,尚不及80年代伤痕文学所描摹的事实之万一。反共文学可能是虚构的,但竟然成为伤痕文学的‘真实’。”这真是语出惊人,可惜与事实相差十万八千里。陈芳明口口声声说要用“以艺术性来检验文学”,这使人想起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的附录中吹嘘自己的书是“打破一切政治枷锁,干干净净以文学为基点写的文学史”,可司马长风当年未做到,现在陈芳明也未必能做到。在有政党的社会里尤其是像台湾这种政治抓狂、乱象丛生、选举的喇叭声和鞭炮声不断在书桌前响起的社会,要走“纯艺术”、“纯学术”的道路也难。如要坚持不食人间烟火“为学术而学术”,这就像鲁迅当年讽刺的“第三种人”那样拔着自己的头发希望离开地球。陈氏在第十一章中对大陆伤痕文学与台湾反共文学所作的这种非学术比较,不仅掉进了“蓝营”意识形态的陷阱里,而且还给大陆学者说的两岸文学一脉相承提供了最佳佐证。
胡:你不能否认《台湾新文学史》史料丰富这个优点。
古:可因为太“丰富”了,来不及一一查证。这本书号称“历时 12载,终告成书”,其实中间作者写了许多文章和书。它并不是“十年磨一剑” 的产物,而是匆忙的产物。书的封底上还有什么“最好的汉语文学,产生在台湾”,这纯粹是商业广告用语,在书中根本未进行论证。作为一本严肃的且具有相当水准的文学史著作,完全用不着借世俗的方法去推销。许多章节尤其是最后写到新世纪台湾新文学只有“文学盛世”的空洞赞美而无实质性内容,这就好比不尽职的导游,他带人到号称“奼紫嫣红,繁花争艳”的景点,只说你们自己欣赏吧,自己却溜掉了。像这种仓促成书的做法,就难免带来许多史料差错。如第306页云:王蓝担任过中国笔会副会长。其实,“中国笔会”是中共领导下设在北京的文艺团体,王蓝任职的是由国民党主控设在台北的“中华民国笔会”。第266页说孙陵写歌曲《保卫大台湾》时任《民族晚报》主编,这里有四个错误:不是歌曲而是歌词;不是任职于《民族晚报》,而是供职于《民族报》;不是任《民族晚报》主编,而是任《民族报》副刊主编;不是任副刊主编时写的歌词,而是在这之前。
胡:既然你“活着为了写书 ,写书为了活着”,继《古远清文学世界》、《古远清这个人》、《台湾文坛的“实况转播”》、《谢冕评说三十年》在陆台港问世后,那你还有哪些新书出版?
古:将有《澳门文学编年史》、《当代台湾文学辞典》、《有朋自大陆来——访台日记》、《战后台湾文学理论史》在台港澳及内地出版, 届时一定送你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