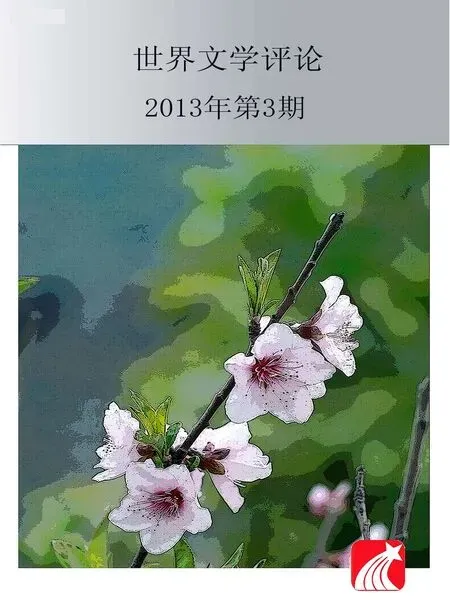为西方寻求“黄帝疗法”:印度海外作家的中国形象*
2013-11-14尹锡南
尹锡南
为西方寻求“黄帝疗法”:印度海外作家的中国形象
尹锡南
印度旅英作家库纳尔·巴苏的中国题材小说《黄帝疗法》是典型的后殖民作品。巴苏以典型的“东方主义”视角进行中国题材的历史演义。他对中国或中国人的形象塑造,体现了后殖民作家对于中国文化的刻意误读。库纳尔·巴苏 《黄帝疗法》 印度作家 中国形象Author:
Yin Xinan is a research fellow at Institute of South Asian Studi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His areas of interest are Indian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西方学者认为:“形象(images)与真实(reality)并不必然且从未相符,总是存在无限的真实。观察中国的人们所作的事,似乎只是通过他们自己的背景、意识形态、偏见和体验过滤眼中所见的一切。”(Mackerras 2)这也是西方作家描述中国、印度、日本等东方国家的艺术生态。深受西方叙事传统影响的印度旅英作家库纳尔·巴苏(Kunal Basu,下简称“巴苏”)便是这样一位作家。他是近年来继维克拉姆·赛特之后又一位少见的涉及中国题材的海外印度作家。印度驻华大使馆主办的中文杂志《今日印度》曾经介绍巴苏的中国题材小说《黄帝疗法》(The Yellow Emperor's Cure)的“魅力”所在:“这一次,历史小说大师带给我们的是《黄帝的疗法》。也许这是他最雄心勃勃的小说;小说涉及一定的文化和历史时期,是一部充满异国情调、诱人、新奇而又极具吸引力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中,你能发现调情的外科医生、致命的疾病、迷人的女子和一个个神秘之谜,所有这些都将让您对这该书爱不释手。”(佚名 32)此处以《黄帝疗法》为例,对印度海外作家的中国书写进行简析。
一、创作起源
巴苏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并在印度和美国接受教育,现为英国牛津大学教授。他在2001—2011年创作并出版了五部小说(集),即《鸦片职员》(The Opium Clerk,2001)、《微图画家》(The Miniaturist,2003)、《种族主义者》(Racists,2006)、《日本妻子》(The Japanese Wife,2008)和《黄帝疗法》(2011)。其中,第一部长篇小说《鸦片职员》和最新长篇小说《黄帝疗法》均与中国有关,另外几部小说与日本、非洲等地有关。可以看出,巴苏对于跨文化写作非常着迷。巴苏的作品受到读者的欢迎。小说集《日本妻子》中的一篇同名小说《日本妻子》还被拍成电影并获奖。2012年3月1日,印度驻华大使馆与北京国际协会(BIS)联合举办了巴苏最新畅销小说《黄帝疗法》的读者见面会。见面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主播周柳建成与巴苏进行了对话。到场读者也与巴苏进行了互动。
面对别人询问《黄帝疗法》的创作动机,巴苏答复说,他的这部跨文化作品产生于一次偶然的经历。几年前,他在北京参观一家中药博物馆。当时,博物馆里没有中外游客,他便独自一人在博物馆大厅里游逛。幸运的是,玻璃橱窗里的展品有英文标签,所以,他便花了一个小时略带困惑地浏览和思考可以治疗地球上各种疾病的方法。在博物馆展出的书中,他发现了一个英文译本,这是由德裔美国历史学家维斯(Ilza Veith)于1949年出版的《黄帝内经》英译本。后来他了解到,这是世界上关于《黄帝内经》这本古老医书最早的外文译本。刹那间,电光火石般,身为小说家的巴苏脑海里闪现出一位欧洲医生的艺术形象。时间是是19世纪末,地点是北京。这位欧洲医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苦苦搜寻治愈梅毒这一危害人类数个世纪的顽症的东方秘方。“在博物馆里,当一个年轻的欧洲医生访问中国,以求找到梅毒疗法的故事开始在我脑海里成形时,我开始构思故事要点:动机、角色和故事背景。为什么他会来中国?难道是因为对东方疗法的强烈质疑?可能他有一个患此病的病人,或是因为遭遇梅毒悲剧的打击?谁能帮他找到一位中医名师?我想象他生活在北京的颐和园,颐和园在当时是慈禧太后、朝廷和清朝客人的住所,外国游客经常将它形容为全中国最浪漫的地方。在颐和园的一个私塾里,他从一位身穿农姑衣裳的年轻女子那学习中医……随着学习的进行,安东尼奥开始对师傅着迷;对师傅的好奇超越了他对梅毒的兴趣。瞧!故事就这么诞生了。我火速冲回酒店,迅速将情节写下来。”(佚名 32)
以上便是巴苏的《黄帝疗法》的诞生背景。该小说以欧洲人的探险之旅或发现之旅为主线,渲染出一幅幅诡异莫测、歪曲变形的近代中国人形象,具有典型的文化隐喻和文化内涵。
二、中国之旅的文化隐喻
《黄帝疗法》的故事始于1898年,这是中国近代史与世界近代史的关键时期。这一年,美国发动了旨在夺取西班牙殖民地——古巴和菲律宾的美西战争。这是进入帝国主义时期,列强重新分割殖民地的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此后不久,美国加入到侵略中国的行列中。同样是在1898年,中国发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史称“百日维新”的戊戌变法运动。戊戌变法以悲剧性的失败而告终,但是作为一次重要政治变革,它将永远载在史册。在反洋教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义和团实力不断壮大。反帝爱国的义和团战士与“八国联军”殊死搏斗,不幸失败。巴苏十分精明地将小说置于这样一种动荡不安、战火纷飞的历史背景中。
《黄帝疗法》中的男主人公是风流成性的葡萄牙外科医生安东尼奥。1898年的一天,住在里斯本的安东尼奥接到父亲的女仆罗莎·埃斯科巴的一封急信后,匆匆地赶回家里。他惊讶而痛苦地发现,父亲患了梅毒。父亲怎么染上梅毒也成为不解之谜。他的知交阿尔弗雷德·马丁医生告诉他,此时的西方“文明世界”尚不能治愈其父的三期梅毒。从阿尔弗雷德·马丁那儿,他获悉,东方世界的中国有一部古老的医学典籍即《黄帝内经》。关于这部医学经典,阿尔弗雷德·马丁说:“黄帝是黄种人的统治者。他的医学法则比我们的老祖先还要古老。中国医生仅仅凭借将手放在病人手腕的方法便可辨识其病症。”(Basu 18)从阿尔弗雷德·马丁的话中得出启示,救父心切的安东尼奥突发奇想,可否采用《黄帝内经》记载的疗法治疗西方的梅毒?他的脑海里总是思索着“梅毒的中式疗法”。中国船员免于梅毒感染的奇闻坚定了他远赴中国寻求神奇疗法即“黄帝疗法”的信念。他遂告别重病中的父亲和女友爱丽丝等人,乘船奔赴当时尚属葡萄牙殖民地的中国澳门。
在澳门的葡萄牙总督堂·阿方索及其夫人朵拉·埃尔维拉为安东尼奥接风洗尘。朵拉·埃尔维拉和丈夫建议安东尼奥到北京去学习中文,并拜见慈禧太后的御医徐医生,从他身上或许能打开治疗梅毒的中国疗法的大门。朵拉·埃尔维拉叮嘱熟悉北京的葡萄牙人将安东尼奥带到北京,并拜会徐医生。主人为安东尼奥在颐和园安排了住处,并安排两个太监照顾他的起居饮食。
安东尼奥的求医之路从徐医生教他把脉而非直接传授治疗梅毒的“秘方”或曰神奇的“黄帝疗法”开始。徐医生的想法是,先用一年时间让他学习内经的基本原理。面对急于学会梅毒疗法以返回欧洲拯救濒临死亡的父亲的安东尼奥,徐医生仍然不温不火。他告诉安东尼奥:“治疗病人你得服从原则,仅仅掌握规则还不够。你必须相信气,如相信全身的气在五脏六腑中传播迁移。否则,你没有资格当医生。”(Basu 90)安东尼奥并没完全信服,与之展开辩论。这说明,以此二人为代表,西医和中医的观念亦即中西方文化观产生了分歧和交锋。
此时,安东尼奥在华打交道时间最长的主要对象亦即他的“内经师傅”、实为徐医生妻子的傅蜜现身了。她“身体力行”地教安东尼奥识别人体各个经脉。除了与徐医生和傅蜜打交道外,安东尼奥还与当时在北京的“小欧洲”团体过从甚密。这些人中包括一些来华的传教士。
随着义和团反洋教运动的蓬勃开展,北京和天津的局势一时间混乱不堪,外国势力侵略中国的力度加大,中国陷入了严重的主权危机中。各国在华公使齐聚一堂,商议如何对付义和团与慈禧太后的事情。1900年8月14日,随着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仓皇出逃。在这一系列风云变幻的历史事件中,安东尼奥是亲历者、见证者。他见证了义和团进入北京城时的混乱景象,也目睹了外国传教士等各种在华势力龟缩一隅以求自保的可怜惨状。安东尼奥为了保护一些中国人免遭义和团的“滥杀无辜”,将他们带进外国使馆区的安全地带隐藏起来。
在这种混乱的背景下,安东尼奥与他深爱着的傅蜜终于有一天失散了。其实,这是傅蜜为保全安东尼奥使出的故意出走计,以使安东尼奥离开颐和园回归欧洲人团体,以求生命安全。安东尼奥也不明白,为何自己来到中国,却屡遭厄运?在太监王生来访之际,安东尼奥终于弄清了自己与傅蜜失散的真实原因。
女友爱丽丝为了寻找安东尼奥来到了中国。爱丽丝告诫安东尼奥离开北京奔赴天津,因为他保护了很多中国人的生命,义和团战士不会轻饶了他。安东尼奥听信了女友的话,遂乘船到了天津,然后准备回国。此刻,安东尼奥如同《印度之行》中的菲尔丁和阿德拉等人一样,准备回归欧洲文明世界。未能完成来华寻求“黄帝疗法”的使命,他懊恼地踏上归途,内心深处波澜翻滚:“一切往事过后,离开中国时,他作何感想……然而,深奥莫测的神秘之幕似乎已经拉开,自他离开法库尔达德医院起,这种神秘像一个失去母亲的孤儿般纠缠着他。这种神秘使他越来越远离中国。”(Basu 324)神秘的“黄帝疗法”自此成为难以破解的“东方之谜”。
在20世纪初战火纷飞的北京,安东尼奥寻求治疗欧洲梅毒的古老“黄帝疗法”以失败告终,这便意味着暂无东方秘方拯救西方社会物欲横流的痼疾沉疴。这种艺术姿态与T·S·艾略特(以下简称“艾略特”)试图在《荒原》中表达的文明反思或曰文明批判有些类似。《荒原》第三章《火诫》寄托着艾略特试图以佛教思想拯救西方文明于水火之中的良好愿望。艾略特想在古老东方的智慧资源中寻求清新凉爽的“济世良方”,以扑灭愚昧者心中的欲望之火。为何安东尼奥的寻求之旅以失败告终?巴苏在书中并未言明。从小说的背景描叙中,读者不难有所感悟:①以安东尼奥为代表的欧洲智者怀着虔诚之心远涉重洋,来到北京拜师学艺,以解西方自身病入膏肓的痼疾“梅毒”;②西方来华传教士却想感化中国人皈依基督教,在华的欧洲商人强取豪夺中国的物质财富,八国联军更是欲借先进的军事技术征服中国,这便将中国视为弱者、学徒或剥削对象。这种虔诚学艺和傲慢称霸的极不对称的心态,预示着安东尼奥为代表的西方智者寻求东方智慧必然以灰暗的结局收场。安东尼奥成为这一结局的“牺牲品”。
安东尼奥和徐医生及傅蜜的个人交往是东西文化对话失败的一个缩影。《黄帝内经》所代表的中国文化思维与安东尼奥借西方医学原理所表达的另一思维存在激烈的碰撞,这便使小说充满了艺术而现实的张力。例如,徐医生认为,人体本来是纯洁的,疾病是邪恶的入侵者。医生便需像战士一样,掌握战而胜之的秘诀。这说明,通晓疾病入侵的机理方可治疗疾病。这便是中医治本的思想体现。徐医生还认为,对求法心切的安东尼奥来说,梅毒恰如外国人眼中那些义和团“拳乱分子”,必欲剿之而后快。对此,安东尼奥的答复非常坚决:“必须找到对付梅毒和义和团二者的方法。无论是义和团或梅毒,归根结底,都将以同样的方式彻底击败它。”(Basu 187) “同样的方式”便是安东尼奥所说的By force(用武力)。按照《黄帝内经》的思路,“治未病”是一种以预防疾病为主的思想。其中的《素问·上古天真论》认为:“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张湖德2)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则告诫人们:“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凿锥,不亦晚乎。”(张湖德3—4)显然,这种预防为主的中医理论不是安东尼奥短期内所能理解或欣赏的。经过徐医生和傅蜜这两位中国“内经师傅”的悉心调教,安东尼奥在一年多的学习中大有长进,但突如其来的持续战乱打乱了他的正常学习进程,而义和团运动高涨和八国联军侵华则进一步粉碎了他的学艺之梦,并导致他最后被迫离开中国,留下一颗壮志未酬的心。虽然说这种大致基于历史真实的艺术叙事似乎可以解释安东尼奥的失败之旅,但他的西医思维和徐医生、傅蜜等人的中医思维的激烈碰撞绝不亚于当时东西方政治、军事和宗教习俗等方面的全面对峙,也似乎影射了晚晴时代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家们关于东西方文化、政治体制、军事体制、经济制度等各个方面如何融合与借鉴的持续争论。如何破解东西对话的文化僵局,似乎是《黄帝疗法》的深层内涵之一。
安东尼奥与傅蜜的交往以失败告终。爱丽丝的身影似乎代表了西方文化,她将在中国已经身心疲惫的安东尼奥接回了欧洲。在此,读者不难发现E·M·福斯特在《印度之行》中所描写的那种相似情节。在《印度之行》中,阿德拉小姐带着对印度的好奇心来到东方,但却在马拉巴山洞里遭遇了厄运,一场突如其来而又匪夷所思的“强暴”事件破坏了她与印度文化的心灵沟通。她只得退回欧洲文明的基督教世界寻求慰藉。“经过了数年理性主义的熏陶,阿德拉已经恢复了基督教的晨祷。这似乎没有什么危害,是通往灵魂世界的一条最容易走的捷径,她可以把苦恼完全寄托在祈祷上。”(福斯特 237)此后,小说中另一人物菲尔丁离开印度,途经克里特岛到达意大利。菲尔丁在回忆“贫困的印度”时,无法忘怀的是那种“混乱的文明”带给他的无尽困惑,而威尼斯的“和谐”使他心旷神怡。因此,安东尼奥和阿德拉、菲尔丁等动机单纯的欧洲人在各自的东方旅行中,均感受到无法回避的“文化休克”,而爱丽丝、基督教和威尼斯等带有拯救性质的“文化符号”则充当了抚慰其各自灵魂痛楚的角色。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安东尼奥来华学习神秘莫测的“黄帝疗法”,与其说是一次地理上的中国之旅,毋宁说是殖民主义时期西方知识分子的心灵之旅。这便是《黄帝疗法》的文化隐喻所在。它的隐喻功能还在于,这是印度海外作家借用英语载体和西方思维所创造的一种典型的后殖民文本,其中彰显了作者挥之不去的主体意识。这种后殖民意识曾经贯穿了殖民主义时期许多英国作家的印度书写与中国叙事。
三、中国人形象的文化内涵
巴苏在接受专访时说:“我总觉得自己在‘局内人’和‘局外人’这两种角色中辗转。在小说的某些部分,欧洲人是局内人,而中国人是局外人,而在小说的其他部分,情况则发生了逆转……我既不是中国人,又不是欧洲人,所以写作之时毫无束缚,能自由从一个场景迅速转换到另一个场景。”(佚名 32)巴苏喜欢以游离于欧洲视角和中国视角之外的第三视角即印度视角,随心所欲地进行中国题材的历史演义。他的这种视角其实没有摆脱萨义德所批判的“东方主义”立场。
在后殖民理论看来,所谓“东方”(the Orient)是欧洲学者的一种叙事话语。对西方而言,亚洲代表“遥远、静寂、陌生的异域”。“这样一个东方静默无语,可被欧洲用来实现自己的计划……这样一个东方无法抵抗为其设计好了的计划、形象或描述。”(萨义德 123)东方是被欧洲人观赏猎奇的对象。东方是西方的被动参照物。“西方是积极的行动者,东方则是消极的回应者。西方是东方人所有行为的目击者和审判者。”(萨义德 142)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并非真实存在的东方图景,而是一种“东方化的东方”。其中存在着福柯式知识与权力互为连理的运作逻辑或思维生态。东方还是一种女性化的弱者,有时还是一种被色情化的对象。在这种心理基础上或叙事逻辑中,欧洲代东方言说,为西方展示东方的“神秘”:“如果东方能够表述自己,它一定会表述自己;既然它不能,就必须由别人担负起这一职责,为了西方,也为了可怜的东方。”(萨义德 28)这样一来,东方便成为一种刻板的畸形对象。
在巴苏以“东方主义”心态描述中国人形象的过程中,对于贯穿故事始终的女主人公傅蜜的细致描摹占有突出位置。
安东尼奥与他的第二个“内经师傅”、后“堕落”为其情人的傅蜜之间的身心交往浸透了“东方主义”色彩,形象地诠释了后殖民文本中知识与权力的潜在运作逻辑。在作者巴苏的艺术安排下,风流成性的安东尼奥迷上了自己的中国女师傅,并与之乐而不倦地行夫妻之实。这一对跨文化师徒亦即跨国恋人的情缘最初是在傅蜜“惊世骇俗”的教学实践中拉开序幕的。在巴苏笔下出现了这样匪夷所思、耐人寻味却又十分契合白人男性欲望的描述:“她转身背对着安东尼奥,将自己的衣袍掀到腰部以上,然后斜着身躯以食指,沿着她雪白小腿肚的曲线,一直追溯到柔亮的大腿、裸露的臀部和弧形的背脊,直到她紧闭的双眼为止。她保持着这种姿势,以便他观看,然后将衣袍放回。”(Basu 108)不仅如此,傅蜜还让安东尼奥站在凳子上,并让他当面脱光自己的衣裳,赤身裸体地接受关于《黄帝内经》的医学训练。于是,安东尼奥和她相当自然地跨越了师傅和徒弟、男人和女人、白人和黄人的诸多界限。这种疯狂的色情迷恋使安东尼奥陷入困惑。小说叙述道:“当他稍微清醒时,他纳闷,自己是谁,在东方阁楼(oriental pavilion)里干了些什么?万里迢迢,跨洋过海,究竟是什么事情使他来到中国?他试图回忆自己的恶梦和迷乱梦幻,并纳闷为何自己的身体兴奋躁动、激情四溢,焕发出如此甜蜜的爱的芬芳。”(Basu 121)傅蜜告诉安东尼奥:“他们说,我们是颐和园千万阁楼中的唯一一对恋人。”(Basu 145)这种语言便是巴苏代中国女性进行自我叙事的典型一例。巴苏对傅蜜的色情化塑造,在英国著名作家保罗·司各特的《中国爱楼》(The Chinese Love Pavilion)里,有着十分相似的表现(Scott 310)。 “中国爱楼”也是一块招徕色情生意的广告牌。在这里,女性是不在场的,是缺席的。她们真实的声音被遮蔽和悬置了,其心理意识被过滤后畸形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便是“东方主义”的艺术手法之一。
安东尼奥由于迷恋傅蜜,遂向她提出按照中国风俗结婚的请求,但却遭到傅蜜的断言拒绝。她有些悲伤地微笑道:“一个外国人要娶太后的仆人。你怎么会这样想?在中国,这是不可能的事,这是一千年也不会发生的事!这还是危险的事。”(Basu 232)在与傅蜜走散以后,安东尼奥一再地想念着自己的中国情人。这是书中的两个句子:“He was ready to meet the invisible…he expected to meet Fumi in the most private pavilion in all of China。”(他想拜见隐身者……他盼望在全中国最隐秘的阁楼中邂逅傅蜜。)(Basu 267)这里的“隐身者”指慈禧太后。叙述至此,巴苏笔下的中国女性形象的文化复义不言而喻。这位似乎有血有肉但却最终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安东尼奥视线中的东方女子,恰如《消失的地平线》中那位身穿汉服的美女罗珍神秘莫测。罗珍虽已90多岁,但却宛若绝色少女。关于罗珍的“神奇”之美,主人公康韦告诉同胞马里森道:“马里森,她的美貌尽管与世界上其他美女一样,却只能存在于那些不知道如何估价她的人手中。她是脆弱的,她只有存在于脆弱的东西被人珍惜的地方。如果将她从这个山谷带走,你就会发觉她马上像回声一样消逝得无影无踪。”(希尔顿 314)其实,安东尼奥无法将傅蜜带入自己熟悉的西方文明世界,表明了这位中国女子只能是巴苏所创造的艺术形象,是与罗珍一样诡异奇美的“东方魅影”。这种形象所蕴涵的神秘冷艳或异国情调增添了她们被男权话语世界所观赏的东方“魅力”。
在巴苏“东方主义”叙事中遭到歪曲的还应该包括傅蜜的第二任丈夫、安东尼奥的首任“内经师”徐医生。安东尼奥从徐医生的妹妹李霞那里得知一个惊人的内幕消息,即傅蜜和徐医生实为夫妻。后来,安东尼奥造访住在乡村茅舍的徐医生时得知,傅蜜实乃已经在战乱中亡故的荷兰人雅克布的妻子,她虽改嫁给徐医生,但内心里却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外国丈夫。他教傅蜜学习《黄帝内经》,为了保护她又娶了她。但傅蜜却水性杨花,不尽为妻之责,在宫廷里肆意妄为。通过这样的叙述可以发现,巴苏一方面创造了一个色情化的中国女性形象,另一方面描摹了一个软弱无能的中国男子形象。换句话说,徐医生虽然贵为御前太医,又享外国人的“内经师傅”之誉,但却属卑琐无能的生理与心理羸弱者。按照当时的中国风俗,他的妻子与自己的欧洲徒弟即安东尼奥的跨国情实为私通而已,而他却显然是这一事件的幕后策划者,这于情于理极其荒谬,但却居然成为《黄帝疗法》中的艺术真实。
对于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人称“老佛爷”的慈禧太后,巴苏的描叙显然乏力。小说中提到她时,几乎均以“隐身者”(invisible)这个带有神秘色彩或恐怖气氛的词汇进行描叙,这使她的形象具备了充分刻板化的特征。不仅如此,书中某处还以西方人的语气对慈禧太后进行色情化描叙:“他们认为,不久,你就会陷入一位满洲诱人色女的控制中。你在颐和园呆得越久,老佛爷就越可能抓住你陪她悄悄享乐。你可能会失去文明风度。”(Basu 160-161)
关于对安东尼奥的两个贴身仆人的描写,小说也极尽艺术矮化之能。他们不仅愚蠢、愚忠,还在危难时刻需要安东尼奥的舍身庇护。他们对欧洲主人无微不至地陪侍照顾,影射了清廷太监的可悲可笑,并在更广的意义上影射了晚清朝廷以西方白人为主子的无奈而残酷的“黑色幽默”。印度读者评价道:“可想而知,巴苏只是用服侍安东尼奥的太监来制造笑料。”(Anantharaman)
关于中国人的集体形象,小说借澳门总督堂·阿方索的口说道:“中国人的神秘莫测犹如深海难解。这会骗过那些声称很了解中国的人。没有人了解中国人,这便是明明白白的事实。”(Basu 51)书中还借欧洲在华人士的口对黄帝进行了色情化描叙,称其为 “色情文学之父”。“黄帝与1 200名妻妾性交,然后带着纯洁的灵魂升入天堂。与众多女子性交,男人会获取无限多的阴气,这将延年益寿、治疗疾病,即使他年届八旬,仍有能力生儿育女。”(Basu 195)这种对黄帝的夸张描写延续了对东方色情化的书写传统。
巴苏不仅在人物塑造方面存在着东方主义迹象,在场景描绘等方面同样如此。他将当时的颐和园描述为美丽的处所,但又安排了很多色情或恐怖的事件在此发生。徐医生不仅被某些欧洲人解读为神秘间谍,其住处更是充满神秘色彩。慈禧太后治下的中国是一派荒凉凋零的肃杀气氛。这些场景描叙充分地渲染了中国人的神秘恐怖和色情懒惰等特性。
总之,与众多的西方人物相比,小说中出现的为数有限的中国人形象要么显得神秘莫测或恐怖可畏,要么显得色欲无厌或羸弱无能,要么显得滑稽可笑或愚不可及。即使是奋力抵抗八国联军的义和团战士,也以仇视洋人并滥杀无辜的野蛮人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这体现了作者下意识中对中国人物形象的东方化姿态。或许这并非巴苏本意,但其长期居于英语文化圈、持久亲近西方话语的生活体验,使其中国题材小说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浓烈的“东方主义”气息。这便是巴苏将《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与傅蜜等为代表的中国人形象作为“消费符号”进行艺术加工的自然结果。
作为印度海外英语作家群体的重要一员,巴苏对中国形象的艺术刻画不仅在西方世界、也在印度国内有着众多的英语读者。这便对中国形象的海外传播制造了某种阻力。据了解,巴苏作品在印度颇有阅读市场,《印度教徒报》等印度英文媒体多次介绍《黄帝疗法》。如何积极正面而又适度地向外部世界传播中国形象的积极一面,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也是应对巴苏等人对中国进行负面书写的必需措施。
注解【Notes】
*本文属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以来印度中国观的演变研究”(12XGJ006)的阶段性成果。
Anantharaman, Latha. Little Insight, Less Entertainment, The Hindu, February 5, 2012.
佚名:《库纳尔·巴苏与〈黄帝的疗法〉》,载《今日印度》2012年2月。
Basu, Kunal. The Yellow Emperor's Cure. New Delhi: Picador India, 2011.
[英]E·M·福斯特:《印度之行》,杨自俭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
[英]詹姆斯·希尔顿:《消失的地平线》,罗尘编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Mackerras, Colin.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Scott, Paul. The Chinese Love Pavilion.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 1960.
张湖德:《中医养生康复名著选读》(医经分册),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
Title:
A Western Search for the Yellow Emperor's Cure: Indian Writer's Image of ChinaKunal Basu, an Indian diasporic writer whose latest novel on China, i.e. The Yellow Emperor's Cure is a typical postcolonial text. Basu interprets modern Chinese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ientalism. His image of China and Chinese f gures ref ects the post-colonial writers' misreading of Chinese culture.Kunal Basu The Yellow Emperor's Cure Indian writer Image of China尹锡南,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副教授。作品【Works Ci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