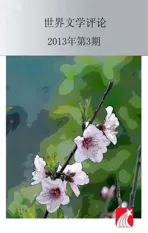隐喻与反讽:白先勇《纽约客》系列中的空间解读
2013-11-14蔡晓惠
蔡晓惠
隐喻与反讽:白先勇《纽约客》系列中的空间解读
蔡晓惠
空间批评为解读白先勇《纽约客》系列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些短篇小说文本中的空间不仅仅是一种地理上的现实存在,也是一种文化建构和价值反应体系。本文通过分析文本中的空间隐喻和空间反讽,阐释了空间在表达作者精神旨趣和价值观念中的重要作用。空间批评 白先勇 《纽约客》 空间隐喻 空间反讽Author:
Cai Xiaohui,born in Dingzhou City of Hebei Province,is currently a doctoral student majoring in "Literary Theories and Criticism" in School of Literature at Nankai University, as well as a lecturer in General English Department of Nankai University, Whose major research interests are "Literature Written by America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 and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ies and Criticism".空间理论兴起于20世纪70—80年代,亨利·列菲伏尔是此派理论最重要的思想先驱,而其作品《空间的生产》更是空间理论兴起的标志性事件,在该书中,列菲伏尔开创性地提出“(社会)空间是一种(社会)生产”(Lefebvre 26)的观点。继列菲伏尔之后,其他学者如米歇尔·福柯、迈克·克朗、戴维·哈维、爱德华·索亚等也分别从政治、地理、文化等不同领域对空间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当代西方空间理论极大程度上解构了传统的空间观念,打破了原来时间和线性叙事一统天下的独霸局面,改变了空间的附属地位,赋予其本体性,在学术思想界开启了令人瞩目的“空间转向”(spacial turn)。空间转向不断波及和渗入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领域,也为文学研究开启了新的研究视域和理论生长点。美国学者菲利普·韦格纳在《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一文中提出“空间批评”的概念,他认为,“对全球历史空间维度的关注,会改变我们对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实践的思考”(韦格纳 168)。文学作品的空间批评中,突破了传统文学研究中将空间视为“空荡容器”的观点,着力于研究空间及空间隐喻背后的文化、历史、民族身份、权力等多层次的逻辑关系;文学作品中的景观和生活空间更大程度上作为一种意义系统、指涉系统、象征系统得到阐发和诠释。白先勇赴美之后的《纽约客》系列短篇小说表现出强烈的空间意识:①这些小说的题目清晰地展现了作者身处异域的敏感,如《芝加哥之死》、《安乐乡的一日》、《上摩天楼去》;②小说文本中大量的美国城市生活空间和景观空间的描写也不仅仅是一种地理上的存在,更是与作者的文化建构、身份认同、价值体系、精神旨趣紧密相关,这正暗合了空间批评的思路和理念。因而,空间批评为解读白先勇的《纽约客》系列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研究思路。
一、空间隐喻
在中国文学传统中,隐喻不仅是一种妙笔生花的修辞方式,更是根植于国人集体无意识中无时不在发挥作用的思维习惯和描述方式。出国之前,白先勇早已在中国文学传统中浸淫日深,中国文学传统中讲究言外之意和隐秘含蓄的审美趣味对白先勇的濡染熏陶深深影响了白先勇文学作品的呈现形态和方式,也包括白先勇笔下的空间书写。白先勇《纽约客》系列中,无论景观空间还是生活空间,常常可以做象征性解读,这些空间意象和象征与作家的主观情感以及作家对西方世界的体认水乳交融,形成一系列意蕴深远的文化表征空间。
(一)地下室:文化边缘人的生存隐喻
《芝加哥之死》中的吴汉魂,来美六年获得博士学位,却在与妓女罗娜春风一度后,自沉密歇根湖。吴汉魂所栖居的地下室,“空气潮湿,光线阴暗,租钱只有普通住房三分之一”(白先勇 《芝加哥之死》,67—76),恶劣的生存环境,不仅形象地表现出以吴汉魂为代表的中国留学生在西方社会中现实生活的窘迫,更是吴汉魂们在中西文化夹缝中的生存隐喻,象征着一个与美国文化、中国文化相隔绝的“真空带”。这个位于芝加哥城中区南克拉克街的二十层楼的地下室,与故乡台北隔了千万里,在这里,曾经情真意切的恋人由亲切熟悉到慢慢疏离,最后终于嫁做他人妇,留在吴汉魂手里的是一捧“又温又软的纸灰”和回不去的记忆;在这里,他辜负了母亲的殷殷企盼,让母亲带着憾恨而终也没能回去看她一眼。恋人和母亲的离开象征着吴汉魂对母体文化的所有维系被一一斩断,故乡,或者母体文化对吴汉魂来讲,已经失去了任何吸引力。虽然,吴汉魂在个人简历中把自己定位为“中国人”,但是显然,无论是事实上,还是心理上,吴汉魂已经背离了中华母体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他者。那么,吴汉魂向往的西方文化又当如何呢?白先勇在小说中多次提到地下室的窗口:吴汉魂读书时,“尘垢满布的玻璃窗上,时常人影憧憧”;冬天下雪时,雪把窗户完全封了起来,吴汉魂便觉得“像爱斯基迷人似的,很有安全感”。窗,众所周知,是人们从一个封闭空间从外界获取信息的一种途径以及与外界沟通和连接的出口。吴汉魂地下室的窗口,便隐喻了吴汉魂对西方世界的了解和认知,一方面,对于窗外灯红酒绿的芝加哥都市文明,吴汉魂不是不为所动的,也曾经“分神”向往;另一方面,对于西方世界,他又是隔膜的(“尘垢满布”的玻璃窗不可能使他认清外面的世界)甚至是排斥的,因为只有窗口被雪完全封闭,他才会觉得安全。吴汉魂走出地下室,进入灯红酒绿的芝加哥,才发现这对他而言,完全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他从来不曾属于这里;与妓女罗娜的接触更加深了这种陌生感和隔阂感。对于西方文化,吴汉魂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他者”。那个远离中国母体文化也与西方文化隔绝的地下室,吴汉魂不愿回去也回不去了,死亡似乎成为这个处在中西两种文化边缘人的唯一结局。而吴汉魂所栖居的狭窄逼仄的地下室,在现实生存空间的表层意义之上,也获得了一种形而上的象征意义,隐喻着“吴汉魂”们与中西文化双重隔离的边缘境遇。
(二)摩天楼、地下酒馆:西方都市文明的象征
“摩天楼”是在《纽约客》系列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它“既有高度发达的现代都市文明的傲人光环,又闪烁着玻璃和金属的冰冷光泽”(朱立立 62)。《谪仙怨》里的黄凤仪迷失在纽约钢筋混凝土的丛林中,仰头看见“摩天大楼一排排往后退,觉得自己只有一点点大”(白先勇《谪仙怨》,307—312),摩天楼给人心理上巨大的压迫感,不由让人觉得渺小和迷失。《芝加哥之死》中的“幽黑的高楼,重重叠叠,矗立四周,如同古墓中逃脱的精灵”,摩天楼给人感觉诡异、神秘甚至夹杂着死亡的气息。在《上摩天楼去》中,摩天楼更是一个贯穿始终的空间意象,枚宝初到纽约,看到曼赫登上的大厦“像一大堆矗立不动,穿戴深紫盔甲的巨人”(白先勇《上摩天楼去》,299—316);与被西方文化熏陶异化的姐姐见面之后,一个人去看帝国大厦,看见它“高耸入云,像个神话中的帝上,君临万方,顶上两筒明亮的探照灯,如同两只高抬的手臂,在天空中前后左右的发号施令”。摩天楼的形象高大、威严,甚至如神明般令人膜拜,但同时它也冷漠、遥远、不近人情,甚至带了几分粗暴和专制。摩天楼所唤起的心理感受,始终与主人公的身份认同密切相关:黄凤仪屈从于美国文化,“完全忘记自己的身份”认为自己变成一个“十足的纽约客”,容忍着西方人对自己面目模糊的身份判断和东方主义解读,在地下酒馆的色相交易中,甚至转化成有商业价值的东方情调;摩天大楼没有带来压迫感,反而是自由和放纵,这似乎是一种微妙的暗示,“放弃中国身份与放纵堕落之间有微妙的平行同构关系”(朱立立 64) 吴汉魂作为中西方文化的双重他者,在文化选择之痛中迷失了方向,摩天楼便成为葬身之所的幽灵;摩天楼更是充分具象化了初到美国的枚宝所感受到的西方文化的侵略性、攻击性。摩天楼成为了一种符号性的空间,隐喻了强势高高在上的西方文化与卑微渺小的中国人的对立。
酒吧是西方文化的一个典型象征。《谪仙怨》中的地下酒馆,“里面挤满了人,玫瑰色的灯光中,散满了乳白色的烟色”。《芝加哥之死》中的红木兰酒吧充满了“呛鼻的雪茄”和“泼翻的酒酸”和“女人身上的浓香”,“空气闷浊”,“座地唱机一遍又一遍地播着几个野性勃勃的爵士歌曲”,白先勇通过声觉、视觉、味觉等多方面细致地构建了一个充满肉欲和沉沦气息的声色场所。这样的一个空间符码象征了作家对西方文化的体认,暗示了作家在文化认同上的态度:在作家貌似客观冷静的第三人称叙述中,透露出对声色犬马灯红酒绿的西方世界的厌弃。
摩天楼、地下酒馆共同构成西方文化的空间符码,作家在对空间赋形的过程中,空间的地理性表征总是与作家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个人情感紧密融合在一起的。在白先勇的文学空间想象中,芝加哥和纽约等美国大都市被建构成喧哗、浮躁、冷漠、色情的异质空间,正是通过这一系列深具文化内涵的文学表征空间,表达出白先勇的身份焦虑和文化忧患。
二、空间反讽
除了在文学空间建构中运用隐喻和象征手法,白先勇在《纽约客》系列中还多次将反讽艺术化用于文学表征空间中,通过空间反讽,拓展文本的意义内涵,使读者穿越文字的表面进行深入思考,对文本的主题和深层意蕴有更好地把握。
反讽(irony)是一个流行于西方文学批评界的术语,它经历了从古希腊文论经由德国浪漫主义到新批评的一个递膳生衍的过程。以新批评反讽话语转型为分界,反讽又分为古典反讽和现代反讽,“古典反讽主要是作为一种文学修辞手法来运用,而现代反讽则不仅是一种文学修辞手法,而且扩展成了一种文学结构原则而运用……古典反讽的运作机制是在说‘与本意相反的事’这一逻辑前提的指导下,拉开作品表层意义与深层意义之间的距离以便对需要否定或讽刺的现象或命题做出含蓄而更强烈的否定或讽刺;而现代反讽的运作机制主要是将相反或相对的异质因素并置而创造出一个动态的张力结构,从而揭示现实世界或精神世界的某种荒谬的悖论性处境”(马金起 41)。本文正是从“现代反讽”的意义内涵上使用反讽这一概念的,即本文的反讽更强调互相矛盾的或异质的元素之间的并置或对立,而不是单纯指一种“言在此意在彼”的讽刺性言语,正如浦安迪所言,它是“作者用来说明小说本意上的表里虚实之悬殊的一整套结构和修辞手法”(浦安迪 123)。
在空间批评的视野中,以“反讽”作为切入空间的方式,本文大胆提出“空间反讽”这一概念:空间反讽是文学作品中的空间因素与反讽艺术相结合的产物,他是蕴含在空间描写、空间对比或者空间与人物言语行为以及叙事情境相对照而产生的一种暗含嘲讽、否定意味和揭蔽性质的委婉幽隐的修辞策略和结构方法。本文后面将运用空间反讽这一概念对《纽约客》系列进行考察。
(一)空间描写中的反讽
空间反讽的第一种形式是存在于空间描写语言中前后的矛盾悖谬,前面说了一层意思,而后面的描述却明显带着否定和自相矛盾的因素,它是一种叙述中的言语反讽,通过或隐或显的对立两项,尤其是叙述语调与叙述内容的乖离,揭示出作者字面意义之后的隐含意指,在大部分情况下,它以“直接矛盾式反讽”(irony of simple incongruity)出现,其特点是“将两个矛盾陈述或不协调意象不加评论地并置在一起”(Meuek 90)。白先勇的空间描写中,经常出现空间比喻联想和空间描写的悖逆乖离,在喻体和喻义的矛盾统一体中体现了浓郁的反讽意味,生成了强大的艺术张力。试看几个例子。《安乐乡的一日》中,小说开头描述安乐乡时是这样写的,“市容经过建筑家的规划,十分整齐。空气清澈,街道、房屋、树木都分外的清洁。没有灰尘,没有煤烟”(白先勇 《安乐乡的一日》,330—345),照常理推断,这本应该是一幅清新宜人的景象,这个小镇环境幽雅,非常宜居,然而接下来的几句话却发人深思,“好像全经卫生院消毒过,所有的微生物都杀死了一般,给予人一种手术室里的清洁感”,干净整齐的宜居小镇唤起的居然是卫生院和手术室的恐怖联想,喻体和喻义之间产生巨大的意义断裂和悖谬,反讽意味油然而生。在这种空间反讽中,安乐乡的冷漠色彩和非人本质昭然若揭,作者对这一处所谓安乐乡的质疑和批判也不言自明了。类似的例子还有多处:“城中的街道,两旁都有人工栽植的林木及草坪,林木的树叶,绿沃得出奇,大概土壤经过良好的化学施肥,叶瓣都油滑肥肿得像装饰店卖的绿蜡假盆景。草坪由于经常过分的修葺,处处刀削斧凿,一样高低,一色款式,家家门前都如同铺上一张从Macy’s百货公司买回来的塑胶绿地毯。”在作家貌似客观冷静的克制性陈述中,字里行间却充满了反讽,“假蜡盆景”和“塑胶绿地毯”是对“绿沃”和修葺严整的林木草坪的辛辣悖反以及小镇过分人工化而缺乏个性的揭伪去蔽,从更深层次来讲,是对西方文明冷漠和非人化的深深质疑。
(二)空间情境反讽
情境反讽主要是指存在于叙事结构中的事态或事体本身呈现出的反讽性,“情节的发展或与小说人物的预想背道而驰或者干脆连读者的如意算盘也完全打破;小说的氛围营造与人物的内心流露极不和谐,两者形成巨大的反差;小说人物或叙述者表现出来的思想、言语和行为超出了常规,与流行的社会观念与公认的行为准则构成了突出的矛盾……使小说的场景显现出反讽意味”(杨钧 65)都属于情境反讽。而空间情境反讽则是文本中的空间描写与人物的思想行为、故事情节的发展或者小说的氛围营造等因素悖逆乖离、相互矛盾而构成的反讽。在白先勇《纽约客》系列中,空间情境反讽比比皆是。
布鲁克斯曾说,反讽就是“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歪曲”(布鲁克斯 379),而空间反讽便是空间描写对于一个陈述语或情节的明显歪曲或背离。《安乐乡的一日》,从题目中,读者会自然联想起桃花源式的黄发垂髫、怡然自乐、亲戚邻里和睦相处的平安喜乐景象。然而,读者从作者充满反讽意味的空间描述中得知,所谓的安乐乡,不过是一个被现代文明物化异化、人际关系冷漠疏离的世界,故事中的主人公依萍在这个叫作“安乐乡”的小镇里丝毫称不上安乐,她在社区与西方主妇的交往并不愉快甚至让人身心俱疲,与女儿的冲突也昭显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和价值冲突。小说主人公寂寞、压抑、恐惧、绝望的处境以及明褒实贬的空间描写是对“安乐乡”的无情解构,其中的反讽意味不言自明。
《谪仙怨》分为两部分:①黄凤仪写给母亲的一封信,采用第一人称内聚焦叙事,黄凤仪自叙在美国的生活;②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叙述,由叙述者描述黄凤仪在酒吧的真实生活图景,叶维廉先生在评价白先勇的小说曾说,白先勇很善于开启一个幻象,然后在一起突起的惊觉中打破幻象,生出张力(这虽然是就《安乐乡的一日》而发,但是似乎更适用于《谪仙怨》);黄凤仪自叙的生活与全知叙述者的空间描述形成强烈的反差,制造出真实与幻象相对照的反讽情境。在黄凤仪的自叙中,她在纽约自食其力甚至能够赚钱侍养母亲,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认为自己是个十足的纽约客;在感情上,也是个清洁自守的好姑娘,不能原谅男朋友的一次出轨,因为“一个女孩子对那种事情看得很认真的”,这个幻象的打破很大程度上是由第二部分对于黄凤仪工作环境的工笔细描完成:风雪交加的夜晚,纽约第六街Rendervous的地下室里“早挤满了人,玫瑰色的灯光中,散满了乳白的烟色,钢琴旁边,立着一个穿了一身铁甲般银亮长裙的黑女人,正在直着脖子,酸楚急切地喊唱着:Rescue Me!” 混乱暧昧的环境和肉欲氤氲的氛围与黄凤仪自叙的生活完全不符,读者的阅读期待遽然落空。黄凤仪在酒馆里的举止行为更加深了真实与幻象的不协调:所谓自由的纽约客不过是酒吧里的卖笑女;所谓的自食其力不过是皮肉生意;所谓的“对那种事情很认真”原来是“连没长毛的小狗儿也拉进屋里去”。作者在叙述策略上所营造的真实与幻象之间的反差造成强烈的反讽效果,然而,“伴随作品的创作和阅读的不是机智的笑声, 而是一种难以解决反讽作品中的矛盾的痛苦和困惑”(丁柏铨,周晓扬 366)。通过反讽而揭露的黄凤仪的异国处境,在读者心中唤起的,不仅有对一个年轻女子在异国他乡谋生艰难而“哀其不幸”的同情心理,还有对于一个丢弃个人和民族尊严而自甘堕落者“怒其不争”的痛恨心理。
三、结 语
在传统的文学批评中,空间被当作空空荡荡的容器,内部了无趣味,上演着历史与人类的真实戏剧;空间不过是一个舞台,人们的焦点则对准时间以及时间中的事件。文学的空间批评颠覆了这一概念,赋予空间本体性地位,空间在文学的意义生成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诚如迈克·克朗所言,“在文学作品中,社会价值与意识形态是借助包含意识形态因素的地理范畴来发挥影响的”(克朗 60)。空间批评为重读白先勇的作品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撑:在白先勇的《纽约客》系列中,无论是具有强烈隐喻色彩的空间意象还是充满反讽意味的空间描写,都是作者表达精神旨趣和主题意蕴的方式,小说里的空间建构与意义建构形成某种形式的互动,在极具个人色彩的独特文化表征空间中,白先勇建构了自己的中国怀想和美国想象,同时,作家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念也在空间建构中得到了释放和阐发。
[法]Lefebvre, Henri.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1991,p.26.
[美]菲利普·韦格纳:《空间批评:批评的地理、空间、场所与文本性》,载《文学理论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页。
白先勇:《芝加哥之死》,载《白先勇自选集》,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
朱立立:《身份认同与华文文学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白先勇:《谪仙怨》,载《白先勇经典作品》,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
白先勇:《上摩天楼去》,载《寂寞的十七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马金起:《论古典反讽与现代反讽》,载《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10期。
[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Meuek D.C. Irony.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Ltd. ,1979.白先勇:《安乐乡的一日》,载《寂寞的十七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杨钧:《试论小说中反讽的四种类型》,载《学术交流》1994年第6期。
[美]布鲁克斯:《反讽—— 一种结构原则(1949)》,载《 “新批评”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丁柏铨,周晓扬:《新时期小说思潮和小说流变》,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Title:
Metaphor and Irony: An Interpretation of Bai Xianyong's "New Yorker" Short Sto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ial CriticismSpacial criticism in literature provides a new approach to Bai Xianyong's New Yorker short stories:the physical space in these stories is not only a substantial existence, but also a ref ection system of cultural ideas and values. Through text analyses of the spacial metaphors and spacial ironies in these short stories, the importance of space in expressing the author's spiritual pursuits and cultural values is fully illustrated.Spacial criticism Bai Xianyong New Yorker spacial metaphors spacial ironies蔡晓惠,原籍河北定州,现为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南开大学公共英语教学部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美国华人文学。作品【Works Ci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