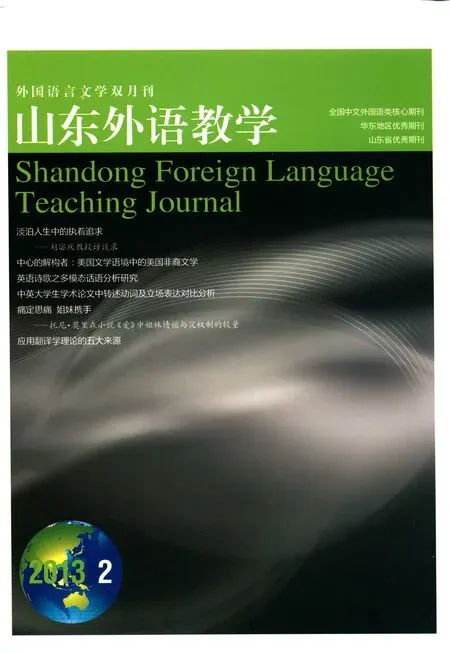诗歌翻译的认知意象编码
2013-10-24钱志富倪捷鸣
钱志富,倪捷鸣
(宁波大学外语学院,浙江宁波 315211)
1.0 引言
诗作为一种主情的文学体裁形式,具有独特的文学魅力。诗歌缘生于情感,借助修辞性的超常结构语言,表达诗人独特的认知感受和审美情趣。苏联文艺理论家日尔蒙斯基认为“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况“汉诗词曲之真妙,妙不在长篇累牍,千行万行;亦不在叙事述理,参破天机,而在其穷情写景,物我交融”(转引自辜正坤,2003:53),诗歌精妙凝练的语言因此也成为诗歌翻译的一大难点。既然“情动于衷而形于言”,诗人往往为了吟咏或诗人性情而创造出陌生化的语言,一种能让读者感知驻足甚至流连忘返的语言(钱志富,2009:123),译者在译诗过程中深受这种特殊语言形式的束缚,追求单纯语言形式的转换已属难事,兼顾音乐韵律的协调更是难上加难。为此,诗歌翻译历来译者寥寥,评者济济,一人译而数十人、百人评。(赵朝永、邵志洪,2009:95)诗歌翻译固然困难,也并非不可翻译。诗歌的可译性以诗歌意蕴的可阐释性为基本前提,由于诗歌的意蕴是一个意义符号系统(sign system),因而作为其中的意蕴要素——意象是可译的。为了实现诗歌意象在目标语中的再现,译界曾尝试各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其中以E.Pound为主要代表的“意象派创译”翻译方法风靡一时。尽管如此,由于意象派译者过分注重意象的重新创造,随意性过大,在侧重意象之“象”,遵循源语语言表层结构和客观表达手段的同时,忽视了诗人在“意”上表现的主观情志,译者容易陷入“创诗”的怪圈之中,译作往往丧失原作特有的文学内涵。随着当代译学跨学科方向的多元发展,认知语言学逐渐成为探讨诗歌翻译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认知语言学是一门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兴学科,其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人们在与现实世界互动体验的基础上认知加工的表征载体,在对语言进行统一解释时,着力寻求语言事实背后的认知方式(cognitive method),意象作为其中一种基本认知方式,为诗歌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启示。诗人在创作诗歌时无疑受到认知思维的驱动,外部语言表征背后的认知规律或意义代码应成为译者翻译诗歌时的关注对象。由于译者本身作为认知主体,预先备有与客观世界互动的主观体验,译者作为读者面对原作意象时,势必构建符合自身情感体验的意象。为了忠实于原作,译者必须识读诗人在原作语言形式下所构建的认知意象,解码诗人投射到原作语言表层的认知视域,在源语—译语转换过程中,根据初始认知视域进行焦点调整(focal adjustment),使调整后的意象视域焦点(figure)和原作视域焦点达到最佳相似,形成与原作大致一体的意象,结合语言形式的外在表征,再现原作的文学意境。本文以Langacker认知语法中的意象理论为视角,拟就诗歌意象和认知意象的概念展开论述,探讨四大认知识解因素对译者在诗歌翻译的认知意象编码方面的指导评价作用。
2.0 意象
2.1 诗歌意象
意象是诗歌美学的基本范畴之一。意象在进入诗歌之前只是作为客观物象的直接指陈而存在,诗人创作伊始,由这种物化形态的意象生发,一旦某类意象与诗人的认知情感体验产生共鸣,这类独特的审美意象便诉诸语言文字得以再现。客观物象进入语言系统便被赋予了特殊的诗学功用,用以表达诗人的审美情趣,体现诗歌特有的美学价值。所谓“得意忘言”就是指外在可感的意象挣脱了具体形式的桎梏,拥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意境,成为代替诗人主观情志的抽象物态。
西方文学界对于诗歌意象的构建十分重视。英国诗人T.S.Eliot 1919年撰写《哈姆雷特》一文,评论指出:“表情达意的唯一艺术方式,便是找出‘意之象’,即一组物象,一个情境,一连串事件,这些会是表达该特别情意的方式”,他将意象定义为“客观对应物”(objective correlative)。(转引自 Wimsatt,1970:667)美国诗人Pound认为意象是“刹那间所表现出来的理性与情感的复合体”,他将意象定义为一个外界客观事物射入脑海化作内部主观东西时的“精确瞬间”。(转引自Rainey,2005:95)美国符号论美学家Susan Langer将意象视为表达情感意义的语言符号。以上对于意象范畴的界定无一例外地将意象分为“意”与“象”两大基本要素。从语义学的视角来看,意象可视作诗人主观审美情感的“意”和审美客体穷情写景的载体——“象”的巧妙结合。正如西方文学批评中对于意象的界定,通过联想,文字激发的画面意义和一个物体反映在头脑里的画面意义相互映射。通过两个所指(referent)间的比较,产生独特的审美感受。(胡壮麟、刘世生,2004:167)可见,意象是一种包含意与象的双重结构,是诗人主观认知体验和外界客观物象相互契合的产物。
中国古典诗歌和中国文论对于意象一词也早有论述。先秦的《易经·系辞传》中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记载,相传为孔子所言,认为“意—言—书”是依次递减的过程。“意是超越了表达意义的具体语词,是具体语词的意义经过统一、化约、提纯后的意义”。(宇文所安,2003:31)“意”指的是被人的思想抓住的“概念”,是意欲之言。由于意欲之言与所书之言存在缺口,古人因而在此之间提出“象”的概念,正所谓“寓意于象,由象表意”。魏晋时王弼针对“意—象—言”三级结构,作了哲学上的辨析,提出“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的说法,进一步阐释了意由象生,象由言表的逻辑关系。直到南朝,刘勰才第一次在《文心雕龙·神思》中首先提出“意象”这一复合词。尽管“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只是说完成的工艺品再现了预先的构想,但是语言表层下的内在因子,即具体工艺品背后的抽象构想,已基本具备现今对意象定义的影子。近现代,诗歌意象通常被认为是“诗人的感官接触事物,经过加工、创造,从生活真实升华到艺术真实的形像”(习华林,2001:36),是“融入了主观情感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达出来的主观情意”(袁行霈,1987:63)。
通过中西诗歌意象探微不难发现,意象作为诗歌高度抽象的灵魂,是象的感性物态经过诗人的主观情感体验,借助语言形式表征的诗人独特认知感受。意象是客观现实世界和诗人主观精神世界默契欣合的产物。
2.2 认知意象
认知心理学里的意象指的是人们在感知体验外界事物过程中所形成的抽象表征,这种表征不是丰富的形象,而是删除具体细节的有组织的结构,是客体或事件在大脑里的一种抽象类比物(abstract analogy)。(赵艳芳,2001:131)在心理学界,意象多指一种心理表征,通常被译为“心象”(心理学中的“心象”与认知语言学的“意象”相似)。Kosslyn的双层表征假说认为心象包括表层表征和深层表征两大因素。表层表征是出现在短时记忆中的一种类似图画的表征,深层表征是储存在长时记忆中被用来产生表层表征的信息。(谭业升,2003:18)心象由表层表征到深层表征,通过语言转换,实现言语表达。
认知语言学中的意象概念受到心理学心象说的很大影响。在认知语法中,Langacker(2004)提出认知意象论,认为意象是人脑中情景形成的具体方式,由于人们识解方式的不同,针对同一情景,人们往往会采用不同的视角,选择不同的注意点,突显不同的方面,从而形成不同的意象,产生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①因而,意象通常带有认知主体的主观心理印记。意象的构建是为了表现语境和表达思想,体现主体以不同识解方式建构特定情景的能力,王寅总结意象的定义时指出,“意象是指在没有客观事物在场的情况下留在人们头脑中的印象,人们依旧能够通过想像唤起该事物的意象,是感觉和知觉的心智表征。”(王寅,2011:55)句法结构体现一定的语义结构,语义结构以意象为基础,意象通过外部语言得以体现。认知主体面对同一情景,由于观察角度或焦点视域的不同产生不同的意象并通过不同的表达方式得以再现。例如:
(1)Bruise fade my father.Strength is my mother.
(2)My father’s bruise fade.My mother gives strength.
句(1)取自英文歌曲“I’m OK”的一段歌词,这是一首反对家庭暴力的歌曲,父亲的伤害对孩子的童年留下了阴影,母亲给予的关怀与鼓励帮助她走出了阴影。该句大意是“父亲的伤痕逐渐消失,母亲是给予力量的源泉”。句(2)是笔者对句(1)的同义改写,显然句(1)和句(2)具有相同的客观真值条件,即两个句子的深层结构是相似的,语义内容基本相同。然而,两者的表层结构差异明显,主观突显意义并不相同。两个句子的发话者针对同一情景,即父亲暴打孩子,母亲保护孩子,分别进行概念化,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意象。句(1)的发话者将焦点视域投射在了“伤痛”和“力量”上,并着重突显了这两个部分,即事件的结果。由于意象识读偏向于线性识读,被放置在句首并第一个映入眼帘的词通常具有突出表征的作用。句(1)与句(2)殊异的句法结构反映了不同的语义结构,句(2)在意象编码时,将“伤痛”的来源“my father”和“力量”的来源“my mother”置于突显地位。两个句子体现了发话者不同的观察角度。
从上例可见,不同意象的形成取决于注意力对认知域(如:结果域—“伤痛”和来源域—“父亲”)、视角(如:结果和来源)和突显的选择,导致意象识读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语言对意象不同的编码方式,主体在对意象编码时会受到识解方式的制约。赵艳芳(2001)将其中的识解制约因素大致分为四个参数:选择(selection)、视角(perspective)、突显(salience)和详细程度(specificity),并将其统称为焦点调整。选择指确定观察和表达事物的哪些方面。语言使用者在对一个事物或一个现象进行描述时,往往会选择其关注的侧面。以中文中的“嘴甜”为例,该词表示某人说话亲切,使人听着舒服。中国人在表示这类意思时,选择身体部分中的“嘴”来体现意义,类似的意思在英文中则变成“honey-lipped”或“smooth-tongued”。显然,西方人在选择认知视域的时候,将注意的焦点集中到“嘴唇”或“舌头”上。可见,相同或类似的语义内容会由于注意力对认知域的不同选择,产生不同的表述方式。由于观察者与事件本身存在相对关系,选择不同的参照视角,就可能获得不同的认知结果。例如:
(3)Just then,the telephone rang.It was my aunt Lucy.‘I’ve just arrived by train,’she said.‘I’mcomingto see you.’
(4)Just then,the telephone rang.It was my aunt Lucy.‘I’ve just arrived by train,’she said.‘I’mgoingto see you.’
以上两句虽然运用了不同方向的指示语,即go和come,但是具有相同的语义内容。在句(3)中,发话者以听者实际所在地为参照视角,使用come表示趋向概念意义,而在句(4)中,发话者所在地与听者所在地存在空间距离,发话者以自己实际所在地作为go的视角。由于认知主体拥有不同的认知焦点,处于认知焦点的物体通常被突显出来,而未被突显的部分则处于蛰伏状态。以网上购物商城亚马逊的商标(见下图所示)为例,

若将“amazon.com”作为整个商标的背景,显然“amazon”下方的箭头成为了突显的对象。突显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从a到z的指向意义,暗示from a to z的语义联想,表示商城提供的商品一应俱全。因此,突显可以更好地体现隐藏在表层语言或图像背后的内在涵义。详细程度指的是对同一场景作出的不同精细度的描写,王寅(2011:88)针对牙刷作了不同详细度的分级,即things>object>implement>brush>toothbrush。认知主体在描述一个场景时,会根据不同详细程度选用不用的表达方式。
从以上分析可见,认知意象的形成受到认知主体的认知域、视角、突显和详细程度选择的制约,焦点调整的不同,形成的意象就不同,因而形成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作者作为认知主体参与创作,以现实客观世界为背景,作者自身的情感与创作灵感一旦受到外在具体可感的物象激发,便形成符合自身主观情感体验的认知意象并将其投射到语言上。译者首先作为读者需对原文文本作体验性理解,需根据自身体验解码原文的认知意象并将解码后的意象逆向还原,重新投射到目标语中。在作者与译者(读者)双重互动的过程中,两者的认知焦点视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偏离,相同的语义内容会受到不同识解方式的制约,焦点调整的四大参数会影响译文的形成,导致同一原文形成不同的认知意象。为了使译作最大程度地忠实于原作,译者需根据原文初始认知视域进行焦点调整,以再现原文作者的最初创作意图。以下以诗歌翻译为例,对认知意象的识读和编码作具体分析。
3.0 诗歌翻译的认知意象编码
辜正坤在谈到诗歌意象时,说到了诗人对于语意视象蒙太奇手法的运用,认为“即使是同一个素材,只要改变剪辑的切断和接触顺序,就会产生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作品”。(辜正坤,2003:7)由此可见,诗人对意象进行编码时,会按照自身主观体验和主观意图构思编排。诗歌翻译时,译者需结合自身注意力对认知域、视角、突显和详细程度的选择,逆向还原原作意象,通过调整认知焦点,使译作认知视域与原作认知初始视域达到最佳相似。
3.1 认知域的选择
Langacker(2004)在谈到认知域的选择时,举了“the big blue plastic cup”的例子,认为在描述“杯子”的这个语义结构(或称概念结构)中涵盖了三大基本认知域(认知域可以是基本认知域,也可以是非基本认知域,即复杂开放的百科知识系统):大的/big(空间域),蓝色的/blue(颜色域)和塑料做的/plastic(材料域)。在诗歌翻译中,认知域的选择指的是译者在运用目标语语义结构重新编码原作认知意象时,对意象编码的概念域(conceptual field)的选择。以毛泽东1965年创作的诗《念奴娇·鸟儿问答》的翻译为例,原文(片段)摘录如下: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
对于“炮火连天”这一意象的翻译如下:
译文1:With gunfire the sky is loud(许渊冲译,1993)
译文2:Gunfire licks the heavens(《毛译东诗词》(英文版),1976)
译文1采用“响声隆隆/loud”(听觉域),译文2采用“吞噬/lick”(人体动作域)。可见译文1和译文2选择不同的认知域再现了炮火肆虐,炮声响彻云霄的战乱场面。尽管两种译文的认知域选择有所不同,分别为读者展现了听觉认知意象和动觉认知意象,但都基本转存了原作的意境。再以孟浩然《宿建德江》的翻译为例,原文(片段)摘录如下: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
对于“日暮客愁新”的翻译如下:
译文1:A wanderer’s ache persists.(张廷琛、魏博思,1991)
译文 2:I’m grieved anew to see the parting day.(许渊冲译,2000)
译文1和译文2对于“愁”字意象的识读分别采用了“ache”和“grieve”的译入语进行编码,尽管从表面上看“ache”和“grieve”属于近义词,但是两者对于认知域的选择上拥有不同的侧重点。译文1中的“ache”暗指身体或精神上的痛苦感受,译文2中的“grieve”暗指由于失落而造成的巨大痛苦。译文1侧重于痛苦的来源(身体或精神),译文2侧重于痛苦的程度(轻或重)。从全诗的意境来看,诗人通过舟泊暮宿抒发旅途愁思,羁旅夜泊,日暮添愁,诗人的忧愁自不用说,不管是程度之深还是精神之忧均不同角度地再现了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且基本转存了原作的认知意境。
3.2 视角
苏轼在游观庐山时曾发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感慨,这说明审美主体在面对同一情景时会产生不同的审美视角。Langacker(2004)认为视角指的就是观察情景的角度或位置,视角不同,意象不同,其语言表征也会不同。以温庭筠的《商山早行》为例,原文(片段)摘录如下: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译文1:As the moon sets over thatched inn,the cock crows;
Footprints are left on wood bridge paved with frost.(许渊冲译,2000)
译文2:Cocks were crowing under the moon
In thatched inn.
On the frost fallen on bridge planks
There were men’s footprints.(唐一鹤,2005)
以上的例子呈现了“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共6个独立意象,每个意象在编码时没有采用自然逻辑事理联系的编排方式,意象之间的空间关系没有呈现。译者在双语转换的过程中,考虑到英语必须添加空间关系,必须选择某一意象为参照点来组织其他意象。译文1将“鸡叫”的意象独立出来,译者在描述这一场景时,设定了“月落茅店”的基体和“鸡叫”的侧面,译者似乎是处于置身茅店之外编码原作意象的,译文2将“月”和“鸡叫”组合在一起,设定了“茅店”的基体和“鸡叫月下”的侧面,选用介词in暗示了译者似乎是置身茅店之内观察同一场景的。两位译者对于原作意象的不同编码,可用以下呈现方式表示:

3.3 突显
突显指的是认知主体在面对相同认知情境时,对认知突出一面的表征。突显的细致分类中以指向(profile)与概念基(base)最为重要。一个语言表达中所涉及的认知域为概念基,在认知域中得到突显强化的就是指向。现以孟浩然的《春晓》为例,原文(片段)摘录如下: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译文1:How suddenly the morning comes in spring?
On every side you hear the sweet birds sing.(转引自王永忠、胡国正,2001)
译文 2:This spring morning in bed I’m lying.
Not to awake till birds are crying.(许渊冲译,1988)
译文1和译文2体现了译者对“啼”字认知意象殊异的识读。两个译文拥有相同的概念基,即纷纷洒洒的春风春雨,晴方好,雨亦奇的盎盛春意,然而在听觉域上的认知指向上,两个译文体现了不同的强化突显。sing所指向的听觉认知意象是鸣啭动听的,暗示作者春晨醒来的心境是闲适轻松的,因此译文1编码“啼”这个意象时突显了令人高兴的一面(bright side),而cry所指向的听觉认知意象是凄厉纷迷的,暗示作者被清晨的鸟叫惊醒时,联想昨夜春雨摇落花儿的怜惜与哀怨,因此译文2在编码同一意象时突显了令人哀伤的一面(dark side)。从认知角度来看,由于原作作者的创作意图是描写大自然之美,爱春之极而惜春,若用cry除略显突兀之外,也不符合原文作者爱春的突显面,因此,译文1的认知突显处理对意象的编码更符合原文意境。再如李白的《月下独酌》的英文翻译,原文(片段)摘录如下: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对于“花间一壶酒”的翻译如下:
译文1:An arbor of flowers and a kettle of wine;(Giles译,转引自吕叔湘,2002)
译文2:A cup of wine,under the flowering trees;(Waley译,同上)
通过译文1和译文2的比对分析不难发现,两个译文拥有基本相同的概念基,即花丛间的一壶美酒,诗人形单影只,自斟自酌的孤寂和落寞,然而“花”和“酒”在图形/背景的认知指向上,两个译文体现了不同的突显安排。译文1中的“花”和“酒”通过并列连词“and”得以连接,这样安排的结果使得“花”和“酒”被并置当作了原诗的背景,而译文2中的“花”和“酒”通过方位介词“under”得以连接,这样安排的结果使得“花”自然成了原诗的背景,“酒”成了原诗的图形并得到译者有意的强化突显。首先从原诗语义来看,原诗中出现“间”(一作“下”解,一作“前”解)字即暗示了“花”和“酒”的突显关系,“酒”是被放置在突出表征的位置。其次从原诗创作来看,一向素有“酒仙”之称的诗人李白钟爱“酒”自不待言,当“花”和“酒”一同出现在他面前时,“酒”自然首先引起他的注意,选用译文2既符合原诗的创作意图,也符合原诗的语义指向,相较而言,译文1不符合原文作者对于酒的突显面的安排,因此,译文2的认知突显对意象的编码更符合原文意境。
3.4 详细程度
由于语言具有层次性,不同的词具有不同的范畴等级和纵向层次,因此诗人在诗歌创作中面对同一情景会选用不同详细程度的词,形成不同详细程度的句子,以符合自身的创作意图。译者在翻译时需考虑大致相同详略度的词进行意象编码,以使译作的认知意象与原作意象最佳相似。以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的翻译为例,原文(片段)摘录如下:
古道西风瘦马
译文 1:Ancient road;west wind;lean nag.(Schlepp译,转引自文殊,1989)
译文2:Down a worn path,in the west wind
A lean horse comes plodding.(丁祖馨,1992)
译文1和译文2对于“瘦马”这一认知意象的编码分别为“nag”和“horse”。显然,horse属于基本层级词,而nag属于horse的下级范畴词,nag指的是年老或过度劳累的马(an old or over-worked horse),因此horse—nag形成了上下义词的关系。在“瘦马”这一意象详略度的选择上,译文1的详细程度大于译文2的详细程度。原作通过描写“游子思归图”,传达的是漂泊羁旅的游子思乡之心。疲惫憔悴的游子骑着瘦骨如柴的马匹走在异乡的路上。诗人的原始认知视域显然与译文1的认知视域更为吻合,译文1对于详略度的把握使读者更能与作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再如李白《送友人》的英文翻译,原文(片段)摘录如下:
浮云游子意
译文1:The floating clouds wander every whither as does man.(Lowell译,转引自吕叔湘,2002)
译文2:Those floating clouds are like the wanderer’s heart.(Fletcher译,转引自文殊,1989)
译文1和译文2对于“游子”这一认知意象的编码分别为“man”和“wanderer”。天空中一抹白云,漂浮不定,仿佛行踪不定的友人,任意东西。诗人李白巧妙地将浮云与游子作比,表达了自己对于友人难舍难分、依依惜别的心情。观照原诗呈现的意境不难发现,片段中的“游子”指的就是离家远游的友人,若选用“man”这一基本层级词,友人的形象实在难以捉摸,而“wanderer”(a person who travels around rather than settling in one place)这一下级范畴词的选择所指相当明确,人物的特点也几乎跃然纸上。通过分析,诗人的原始认知视域显然与译文2的认知视域更为吻合,译文2对于详略度的把握使读者更能与作者产生情感共鸣,深刻体会诗人难舍友人之情。
4.0 结语
Langacker(2004)认知语法中的认知意象理论认为,由于认知主体识解方式的不同,针对同一情景,往往会采用不同的视角,选择不同的注意点,突显不同的方面,从而形成不同的意象,产生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本文以该理论为视角,论述了诗歌意象和认知意象的概念,探讨了四大认知识解因素:认知域的选择、视角、突显和详细程度对于诗歌翻译的指导评价作用,提出诗歌翻译是作者与译者双重互动的结果。作者在创作诗歌时会根据初始认知视域,形成符合自身情感体验的认知意象,译者通过语言线索解码原作认知意象。由于受到认知识解因素的影响,译作形成的认知意象与原作认知意象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偏离,译者需调整认知焦点,使原作视域与译作视域达到最佳相似,并通过目标语语言对原作的认知意象编码。
本文对于四大识解因素的论述还不够细致,其中如域的选择方面,不仅包括认知域的选择,也包括级阶(scale)和辖域(scope)的选择;如突显方面,还可探讨突显与文化差异、个人差异和语义结构的关系;如详细程度方面,可细化到词汇层面和语句层面的详略度分析。以上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地分析和研究。
注释:
①本文中提及的意象侧重于Langacker(2004)在认知语法中对于意象的定义,即从描述语义结构的角度来阐释意象,认为语言表达的语义结构是人们各种认知识解能力作用于语义内容的结果,这与Lackoff和Johnson(1999)强调的意象定义,即形成一个概念或概念结构的具体方式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
[1]Lakoff,G.& M.Johnson.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e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New York:Basic Books,1999.
[2]Langacker,R.W.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Vol.I: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M].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4.
[3]Rainey,L.Modernism:An Anthology[M].New York: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5.
[4]Wimsatt,W.K.Literary Criticism:A Short History[M].London:Compton Printing Ltd London and Aylesbury,1970.
[5]丁祖馨.中国诗歌精华[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
[6]辜正坤.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7]胡壮麟,刘世生.西方文体学辞典[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8]吕叔湘.中诗英译比录[Z].北京:中华书局,2002.
[9]毛泽东诗词(英文版)[M].北京:外文出版社,1976.
[10]钱志富.中外诗歌共享的诗歌理论研究[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11]谭业升.意象编码的语言差异与翻译[J].中国翻译,2003,(7):18 -22.
[12]唐一鹤.英译唐诗三百首[Z].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13]王永忠,胡国正.浅析唐诗英译中模糊性的亏损[J].东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65-68.
[14]王寅.什么是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15]文殊.诗词英译选[Z].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16]习华林.意象在英汉诗歌翻译中的地位[J].外语教学,2001,(6):36 -39.
[17]许渊冲.唐诗三百首新译[Z].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8.
[18]许渊冲.毛泽东诗词选(英汉对照)[Z].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
[19]许渊冲.唐诗三百首(汉英对照)[Z].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0]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M].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21]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22]张廷深,魏博思.唐诗一百首(汉英对照)[Z].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
[23]赵朝永,邵志洪.诗歌翻译的认知意象编码[A].胡开宝.跨学科视域下的当代译学研究[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95-106.
[24]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