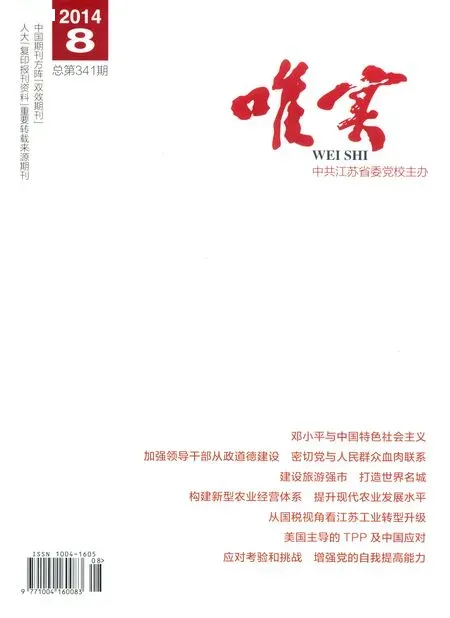“讳”谈一段史
2013-09-12沈淦
沈 淦

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八月,大将李光弼奉命镇守太原,以抗击安禄山叛军。到任之初,他就杀掉了一个恃宠犯法的侍御史崔众。这本来是一个很平常的历史事件,可是三种史书的记载却颇有不同。
《资治通鉴》的记载最为简单:“光弼怒,收(崔众)斩之,军中股栗。”
《新唐书·李光弼传》则详细多了:“会使者至,拜(崔)众御史中丞。光弼曰:‘众有罪,已前系,今但斩侍御史。若使者宣诏,亦斩中丞。’使者内诏不敢出,乃斩众以徇,威震三军。”
《旧唐书·李光弼传》的记叙最为完整:“倾之,中使至,除(崔)众御史中丞。光弼曰:‘众有罪,系之矣!’中使以敕示光弼,光弼曰:‘今只斩侍御史,若宣制命,即斩中丞;若拜宰相,亦斩宰相。’中使惧,遂寝之而还。翌日,以兵仗围众,至碑堂下斩之,威震三军。”
原来,在崔众被杀之前,还有这么一段小插曲:皇帝的使者来了,当他听说皇帝要提升的崔众因为犯了罪而被拘押时,就捧出圣旨让李光弼看,说是皇上已提升崔众为御史中丞了。哪知李光弼根本不买账,冷冷地回答:我今天只想杀一个侍御史;如果宣读了圣旨,那我就杀一个御史中丞吧;如果圣旨拜崔众为宰相,我也只好杀一个宰相了。总之,崔众因为犯了罪,非死不可!而那个使者呢,也被吓坏了,根本就不敢再拿“圣旨”来压李光弼,只得灰溜溜地回去了。
一段普普通通的史料,在这几个著名的史学家手中,为何越写越少呢?我想,或许是一个“讳”字。
本朝人写本朝史需要讳,当代人写当代人尤其需要讳,刘昫与欧阳修、司马光都是写一个已经灭亡了的王朝的史事,为什么刘昫不讳而欧阳修与司马光要讳呢?何况刘昫在名声、才气、成就等方面都远远不如后两人。思来想去,只找到了一个答案,那就是欧阳修与司马光是在为“神圣”的君权讳,为至高无上的皇权讳。
刘昫生活在五代,五代是一个乱世,皇权被相对削弱了,君权自然也没那么“神圣”了。乱世,不但皇权被削弱,士民百姓更是饱受战祸之苦,纷纷慨叹:“宁为太平犬,不为离乱人。”然而,乱世,老百姓不必为一句话而身陷囹圄,读书人也不必为一篇文章而惨遭灭族。皇权不那么强大了,文网也不那么严密了,记下一段李光弼蔑视皇权、怒斩崔众的史实,打什么紧?
然而在欧阳修的时代可不同了。北宋政权虽然未能像唐朝那样完成真正的“大一统”,但毕竟结束了五代十国时的分裂割据局面,皇权大大加强了。无论修史还是写诗词文章,怎能与神圣的皇权相抵牾?欧阳修或许会想:崔众犯了罪,固然该杀,皇上不知内情,提拔他升官,错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照杀无误。你李光弼照杀无误,我欧阳修就不能照记无误?可是你说什么“若拜宰相,亦斩宰相”,这就太过分了。你李光弼不过是一个节度副使,一介赳赳武夫,凭什么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你还把不把皇上放在眼中?若不是“将在外”,若不是国家正值用人之际,岂能容得这种“狂悖”之言,谁能保证你李光弼不遭致杀身之祸!欧阳修显然是很为自己的这一删得意的:既保留了李光弼敢作敢当的个性,又维护了赫赫皇权。
而到了司马光那里,此时的北宋政权更加腐败,各种矛盾更加尖锐复杂,当然也就更加需要维护“神圣”的皇权。或许司马光已深有体会,自己就因为反对变法的言论过于激烈而遭贬抑。总之,司马光连那“亦斩中丞”也容不得了——因为即使你李光弼有理,也不该公然违抗皇上的意旨,不是说“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吗?那么君要臣活,你却不让他活,能算忠吗?不过,司马光毕竟是一个出色的史学家,他深知,李光弼是大唐名将,平定安史之乱,客观上已经维护了大唐王朝的皇权,这段杀崔众的史料,不记是不行的。为了维护神圣的君权,也为了替李光弼这位名将讳一讳——讳掉其“目无君父”的言行,司马光毫不犹豫地挥起了砍刀,砍得一段丰富的史料只剩下“光弼怒,收斩之”六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