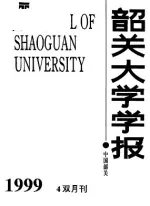浅析晚明小品文对“性灵说”的理论诠释
2013-08-15赵朝芳
赵朝芳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一种文艺思潮的产生,必定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思想相关联。“性灵说”的产生就和晚明当时文坛的创作思想分不开。明代前、后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给文学创作带来了严重的恶果,使诗文普遍陷入了走投无路的窘境。面对这种情况,公安派提出“性灵说”,指出每个时代文学都有自己的特点,必须具有创新性的文学作品,才是好作品。因为诗文都是性灵的表现,而性灵是人所自有,不同时代不同的人都不一样,不能以时代论优劣,不能厚古薄今,而应以能否写出真性灵为依据。
明代中后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期,工商业极为发达,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然而统治者对知识分子采取思想禁锢政策,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被确立为儒家正统思想,人们思想备受压抑。加之当时前后七子倡导复古文风,诗文创作必须引经据典,以阐述儒家思想为宗。这一系列的因素使当时思想界、文学界恰似一潭死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性灵说”应运而生,大放异彩,受到众多知识分子的支持,给当时在黑暗中摸索的文人点亮了一盏灯。对当时的文学创作、作家性情的培养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公安派提倡创新,“性灵说”也一改之前情感求真的单一理论,不仅创作上求真,而且生活态度上也要求自由,要求表现个性,张扬自我。其内核是“性灵、尚真、尚趣、尚奇、尚自然”,这对当时小品文的创作影响深远。
晚明是个思想解放、崇尚个性与追求精神自由的时代,而小品文这种较为自由的文体自然受到当时文学家的喜爱,可谓是晚明一时代之文学。它摆脱了那种创作的纯目的性,功利性,冲破了一切条条框框的束缚,审美性、娱乐性加强。写景状物没有柳宗元游记里的牢骚满腹,也没有苏轼怀古伤今的感慨,只为描述眼中所见,抒发心中所感、所想、趋生活化、个性化,任心而发、纵心而谈,使晚明小品呈现出百花争鸣,百花争艳的景象,而这一切变化无不与公安派倡导的“性灵说”相关。以下就小品文对“性灵说”的理论诠释作具体论述。
一、“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求真
文学作品本身就是一种抒情性的问题,汉代辞赋家扬雄的“言为心声,书为心画”[1]45观就明确要求语言文字就应该淋漓尽致表达人的思想和情感,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创作与主体主观情感之间的关系,创作就是主体情感的流露。“性灵说”也就是情感说,袁宏道推崇“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就是强调真实表现作者个性化思想感情的重要性,反对各种人为的约束以及“粉饰蹈袭。”在他看来,“性灵”就是人的自然的个性,是纯真毫无掩饰的性情。袁宏道在《叙小修诗》里评价其弟文章时称“足迹所至,几半天下,而诗文亦因之以日进。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2]187。心中有情妙笔才能生花,一气呵成。其在另一篇文章《寿存斋张公七十序》文中,又说:“大都士之有韵者,理必入微,理又不可以得韵。故叫跳反掷者,稚子韵也,嬉笑怒骂者,罪人之韵也,醉者无心,稚子亦无心,无心故理无所托, 而自然之韵出焉。”[2]1542在这里,袁宏道强调了为文当有“真性情”,有了真性情的人,即可剥去一切的伪装,还原真正的面目。“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传也,而或者犹以太露病之,曾不知情随境变,字逐情生。”[2]188指出唯有具有真情的作品,才能打动人心,流芳百世。他把创作主体的本然性情当作文学创作的根本,有了这一根本才可能有真正的创作。这一理论也始终贯穿于他的小品创作思想中,也影响着当时的小品文创作家。就连后七子之一的屠隆,与袁中郎交情甚笃,受其影响,其小品文的创作风格也接近公安派,重视情感的表达。在其作品《汤义仍玉茗集序》里,就把对汤显祖的赞美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另一位出名作家焦竑在《题谢康乐集后》中言:“然殷生言,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摹画于步骤者神踬,雕刻于体局者气局,组缀于藻丽者情涸。”[3]89所谓的情,实质就是贯穿文学作品中的情感,一味的辞藻堆砌只会带来“情涸”的弊端。
与袁宏道“性灵说”思想最接近的是陶望龄,其小品创作是自写胸臆,坦率说出心中事,风格清新自然。在《登第后与君奭弟书》曰:“凡自胸臆中陶写出者,是奇是平,为好。”[3]164极力推崇自胸臆写出的作品,所以,他的小品创作能鲜明表达出他的体验,情感。在他笔下,一花一草,一石一木,都是他创作的对象,对它们投入浓浓的情感。与袁宏道同时并是好朋友的江进之,受袁宏道影响很大,也倡导性灵写作,如《敝箧集序》中说“天性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所偶触心,心能摄之,心所欲吐,腕能运之。心能摄境,即蝼蚁蜂虿皆足寄兴,不必睢鸠驺虞矣。腕能运心,则谐词谑语皆足观感……流自性灵,不期新而新,出自模拟者,力求脱旧而转得旧。”[2]1685明确指出,心中有“性灵”流出,即内心有真情流出写出的文章才能脱颖而出,才能不期新而新。其小品文的创作有自己独特的感受和见解。在晚明小品文的创作的,崇尚性灵写作的作家不胜枚举,使得小品文少了那种雄壮的气势和政治教化的内容,无论是游记,序跋,传记等,都是作家情感的一种宣泄,都将自身的情感细腻地表达出来。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能体悟到作家那浓烈的情感。
二、对“趣”的美学追求
明朝统治者为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实行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稍有不慎就会遭到杀头亦或诛灭九族的厄运。当时皇帝不理朝政,宦官专权,大力诛杀异己,致使大部分文人都无意仕途,选择归隐山林寄情山水,或遍览祖国的名山大川,从中体悟个体生命的存在,获得游览的乐趣;加之当时谈禅的风气盛行,老庄自然的思想也深深影响着晚明文人。辞官归隐,把无法排遣的苦闷与追求淡泊宁静的心境借诗文以发泄,且诗文中要表现出“趣”的这一美学内涵。“性灵说”的主题之一就是“尚趣”,袁宏道在其论著中也对“趣”表述的很精确,《叙陈正甫会心集》言“世人所难得者唯趣,趣如山上之色、水中之味,花中之光、女中之态……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为童子也,不知有趣,无往而非趣也,面无端容,人生至乐……山林之人,无拘无束,得自在度日,故虽不求趣而趣近之……率心而行,无所忌惮……迨夫年渐长、官渐高、品渐大,有身如棘,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入理愈深,然去趣愈远矣。”[2]468这里的 “趣” 可不是一般的趣味,而是外界自然现象通过会心者的灵感,作出的反映,是创作主体体验后所得的一种乐趣,是一种无拘无束、自然而然的心境。至此开始,晚明小品文家开始重视诗文之趣,认为无论创作还是欣赏诗文,都不能离开趣,趣是文的生命。竟陵派代表钟惺说“夫文之于趣,无之而无之者也。譬之人,趣其所以生也,趣死则死。”[3]307钟惺把诗文之趣比为人之生命,一个人失去了趣,也就等于失去了生命。晚明文人尚趣,甚至把有无趣味作为诗文的审美标准,所以,“趣”在小品文的创作中无处不在。
晚明文人喜旅游,在自然山水中去获得乐趣,是一种自适的、与山水融为一体的乐趣。由于受袁宏道论“趣”的影响,小品文作家们在文章中都表现出追求“趣”的倾向,把生活中的趣融入作品中,表达出一种自适的情怀。朱之俊与友张明弼一同游览西湖后写下了《雨中初游西湖记》的名篇,他描述西湖“是日也,予谓西湖如绝代佳人,喜亦好,嗔亦好,蓬首亦好,立明处亦好,入暗处亦好,昼见之亦好”[3]377。在这篇文章里,不仅写出了西湖美景的千姿百态,而且还道出雨中游览西湖别有一番情趣。张鼐的小品文,把生活中的各种情趣都在文章中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写居住环境之趣,交友之趣,读书之趣,自然之趣等,趣无不贯穿于他的小品创作中,写的清雅自然。高攀龙的闲情小品表现出他乐于隐居,乐于水居的隐士情怀。他将自己身心融入大自然,提倡勿为物所累,隐居在自然山水中体味人生之乐趣。另一文学家陈继儒在其文章《田园有真乐》曰“田园有真乐,不潇洒终为忙人;诵读有真趣,不玩味终为鄙夫;山水有真赏,不领会终为漫游。”[4]把人生中独特的生命体验都逐一表达出来,是因作者闲居田园,游览大川后的真正体悟。远离朝廷才能真正摆脱政治功利性的缠绕,才能真正获得人生之趣。把游山玩水看成人间至乐之事,全身心投入大自然中去欣赏美景,领略大自然给人的审美享受,曹学佺可算是一代表,《洪崖游稿序》说“游山泽,观鱼鸟,至乐事也,比之游仙焉。夫能遣除万虑,任情独往。”[5]袁氏三兄弟以及受“性灵说”影响的文学家张大复、朱国祯、钟惺、朱之俊、徐芳等,在创作中都践行“趣”这一性灵主旨,阐释一自自适、自在、自得的情怀,同时也表达出对自然山水的热爱。
三、对传统的反叛与消解
明朝前期,程朱理学被推到至高位上的地位,压抑着人们的思想,人们的个性,使整个思想界处于令人窒息的氛围中。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封建专制制度走向崩溃,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政教衰颓,心学禅化,传统儒学消解。由此,学术思想界展开了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和斗争。人们要求打破“存天理,灭人欲”的牢笼,要求个性解放,争取自我的权力,突出“我”的地位,人生世间,要追求一己性情的自适,关注自身存在的意义,充分享受各种自我的乐趣。“性灵说”尚真崇趣,而这一理论的实行必然要突出“我”的地位,标榜自我,张扬自我以及自我享乐,这是对程朱理学人性禁锢的一种反叛与消解。袁宏道在《龚惟长先生》一文中,极言人生的享乐,曰“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2]205其在另一篇同名文章中也言“人生几日耳,而以没来由之苦,易悟无穷之乐哉”[2]228。这种张扬自我享乐的人生态度对其他深受性灵说影响的作家接受,在其作品中表现出尊重个性,张扬个性,挑战传统的思想。
张扬个性,自我行乐影响了大批的小品文作家,著名小品文作家陈继儒直接突出“我”的地位,“我”与“自然”是主体体验的关系,我是主人,自然只是我体验的客观对象;与袁宏道交好的汤宾尹,受其影响,小品文创作体现崇尚自我,喜于清闲的倾向。在小品《徐见可鸠兹集序》里表现得特别明显。他以传神论艺术,大力褒奖徐见可的《鸠兹集》关键就在于他能“吾为吾耳。”他在文章里说:“盛推见可者,或拟以为唐宋,或拟以为周,见可起诀谢曰‘吾为吾耳,安能古人。’”[3]261如此突出自我,显然是公安派思想的翻版;万时华在作品里也表明发挥主体作用,高扬个性。
由于明朝仍以儒家思想为正宗,孔子的“女子为小人难养也”和“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笼罩当时的思想界,使得妇女毫无一点社会地位且备受摧残。著名思想家李贽在其作品《赞刘谐》里诙谐地讽刺一道学者“其人勃然作色而起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子何人者,敢呼仲尼而兄之?’刘谐曰‘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3]42幽默讽刺了道学者们以孔子儒学为宗的思想,是对儒家正统思想的挑战。陈继儒在《侠林序》和《香案序》里,许多方面都与儒家思想相抵触。俞琬轮在文章里不仅赞赏离经叛道的文人,还赞赏钟情于离经叛道文人的女子。
红颜祸水,女色误国这条鞭子已经抽打妇女好多年,到了晚明这个思想解放的时代,袁宏道对这一理论产生了怀疑。在其文章里论到“夫齐国有不嫁之妹,仲父犹云无害霸;蜀宫无倾城之美人,刘禅竟为俘虏。亡国之罪,岂独在色?”[3]138对传统论调的怀疑,也是其“性灵”理论的又一主题。受其影响,谢肇淛也在文章中驳斥妇女亡国论,他反对陈朱理学对妇女的束缚。冲破男尊女卑的观点,认为男女应该平等。他的这一理论始终贯穿于其作品中,《五杂俎·地部》就把这一理论阐述的淋漓尽致,“金陵、秦淮一带,夹岸楼阁,中流箫鼓,日夜不绝,盖其繁华佳丽,自六朝以来已然矣。杜牧诗云:‘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夫国之兴亡,岂关于游人歌妓哉?六朝以盘乐亡,而东汉以节义,宋人以理学,亦卒归于亡耳!但使国家承平,管弦之声不绝,亦足妆点太平,良胜悲苦呻吟之声也。”[6]著名小品文作家谭元春、傅汝舟在文章里直接倡导妇女解放。另一小品文作家支如增还为妇女争取社会地位,争取社会权力,认为妇女应得到应有的尊重。
四、创新与求变
“性灵说”是针对前后七子的复古而发,不仅反对模拟蹈袭,也反对诗文里必须阐述儒家经典的文艺观。鉴于此,文章就必须要求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建立新的文学观念,所以,“性灵说”要求创新、要求有变。“文章新奇,无固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袁宏道《答李元善》)[2]785。这就是要求从复古派的格套束缚中解脱出来,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创造自己的句法调法,名为新奇。在《与江盈科》一文中,他从文学与时代关系出发,阐明文学发展规律,应根据时势的变迁而不断创新。言“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2]306(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1]532。(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他提倡向民歌学习,冲破传统束缚。“诗准盛唐矣,盛唐人曷尝字字学汉、魏欤?秦、汉而学《六经》岂复有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2]188(袁宏道《叙小修诗》)。他既提出每个时代都要有创新精神,又指出必须充分表现各个时代不同的个性。如《雨后游六桥记》,所写虽为传统旧题,却颇能翻新出奇,怜春惜红本是文人墨客之常习,而作者面对满地残红,不见半点悲凄,反而道出各种欢乐,看似冷漠,实则另有深情。其弟袁宗道也崇尚独创,要求小品要“叙事如画,议论超绝”关键是不事模拟,勇于创造,这为小品的创新打下坚实理论基础。“予因思古今真文人何处不自信,亦何尝不自悔。当万波同泻、万家一习之时,而我独有所见,虽雄裁辨口,摇之不能夺其所信。至于众为我转,我更觉进,举世方竟写喧传,而真人灵机自检,已遁之悔中矣。”[3]316(《袁中郎先生续集序》),在这篇文里,谭元春言无论是自信,还是自悔,都是为了不断创新。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写出好作品,一味的因袭模拟只会为后人诟病。卓人月的小品创作气势深沉,见解独特,发人之不能发,其小品《松柏说》就是具体的例子,杨淑山作翻案文章,指责松柏“随时而异”。而卓人月却在文中侃侃而论松柏随时而异的合理性,构思新颖、独特。另一著名小品文家沈承不仅要求挣脱古文的束缚,形式上要求独创,连语言上都要求创新。创新观点对晚明那犹如死水的文坛来说,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了解“性灵说”的内涵,是表达人的真实性情,是人的自然情感的流露,在表达过程中还要求有“趣”、有“新”、有“我”。文学总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政治状况、思想、经济等联系在一起,体现当时的主流。若一味地模拟而失去创新思维,那么诗文只是一种文字的堆砌,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性灵说”对晚明小品的影响巨大,使得小品文挣脱以往古文形式,体裁,创作目的等的束缚,成为一种追求精神自由的独特文体,成为明代一代之文学。历来对“性灵说”及其晚明小品褒贬不一,但是,站在文学史公正的立场,“性灵说”不失为晚明末世黄昏的一首绝唱。
:
[1]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
[2]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7.
[3]尹恭弘.小品高潮与晚明文化[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
[4]杨义.明清小品点评[M].长沙:岳麓书社,2006:62.
[5]马美信.晚明小品精粹[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268.
[6]谢肇淛.五杂组[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