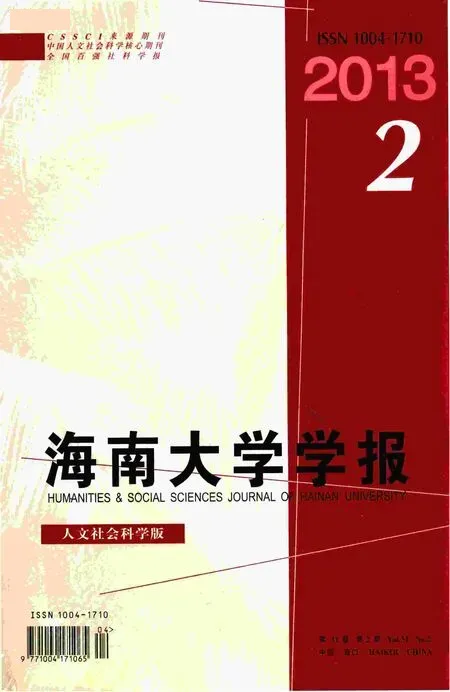明清时期海南三亚回族穆斯林的中国化研究
2013-07-09林日举
林日举
(琼州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海南 三亚572022)
伊斯兰教之载体穆斯林移植于中国大地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漫长历史过程。所谓的“中国化”,是指处在中国社会文化大磁场中的伊斯兰教穆斯林,在主观上保持本身固有文化物质的同时,主动融入中国社会,吸纳有利于自己生存发展的文化因素,促使自身文化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使其群体最终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其文化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一过程,陈垣先生称之为“华化”[1]。
从伊斯兰教穆斯林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来考察,唐元阶段,主要是伊斯兰教穆斯林由“外籍”身份逐渐过渡到“土生”(即世居中国)的历史过程,并在元朝形成了一个回回民族的雏形;明清时期,则是伊斯兰教穆斯林真正实现中国化的重要历史阶段。具体地说,至明代,伊斯兰教穆斯林作为中华民族家族中的一个民族群体——回族真正形成,从明至清两朝,伊斯兰文化逐步融入中国文化体系,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穆斯林真正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之所以发生在明清,是由于这一历史时期具备了其中国化的主客观条件,即明清时期封建王朝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政策,构成了伊斯兰教穆斯林中国化的客观政治背景,是这一外来宗教群体中国化的外因;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内部的积弊,已经造成伊斯兰教的衰微,为保障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穆斯林主动进行变通革新,构成穆斯林群体中国化的主观要求,是伊斯兰教穆斯林群体中国化的内因。
海南三亚回族穆斯林主体,于宋元间来自占婆国,故海南明清时期的地方志仍称他们为“番人”。然而,由于他们在海南岛的繁衍生息历经了元、明、清三朝,已完成了从“外籍”到“土生”的过渡。在教派上,他们原属逊尼派,清代出现中国教派后,则属中国伊斯兰教派中的格底木派。海南三亚回族穆斯林生活区域虽地处南疆,但与大陆各省区的回族穆斯林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伊斯兰教的学缘结构上,他们先与广东、广西穆斯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后又受云南、陕西、甘肃等地的穆斯林影响。正是在此大背景下,明清时期海南三亚回族穆斯林群体逐步地实现了中国化,据有关的史志资料考察,其中国化的途径及表现形式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顺从官府管辖,遵守王朝律法
从唐朝开始至明清时期,历代封建王朝在宽待优容穆斯林的同时,亦加强对其统治。如明朝在治理回回人和对待伊斯兰教事务上,基本策略是“俾转相化导,以共尊中国”[2],除沿袭前代宽待优容政策外,采取了一系列约束的办法。其一,官府对其管理与地方建制相应,将回回纳入坊、厢、里管辖,形成严格的教坊组织,教坊只管理穆斯林宗教和教育活动,不涉及行政、刑律、赋役等,清真寺掌教务必向礼部清吏司申请并履行注册登记手续;其二,政府阻止穆斯林“自相嫁娶”,禁止胡服、胡语、胡姓,实行强制性同化政策,导致诸多回回穆斯林变胡姓为汉姓,改变服饰、语言等方面的习惯;其三,对“导元倾宋”的南方穆斯林及其家庭进行无情打击,打击对象除蒲寿庚的后人之外,还有孙腾夫、黄万石的后人等。此外,平日明代汉族官员,也不时对伊斯兰教与回族进行抨击。
至清朝,在治理穆斯林和处理伊斯兰教事务上,容纳之中伴随着一系列极为严厉的管制措施。一方面,统治集团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存有一定偏见和歧视,统治政策中不乏民族同化政策;另一方面,对穆斯林进行严厉的管束,要求穆斯林服从专制皇权统治。据记载,自雍正年间起,清朝就在西北回民聚居区推行严厉的乡约制度,至乾隆后期,这一制度已深入到西北、西南所有的清真寺。据英国传教士马歇尔·布鲁姆霍尔《中国的伊斯兰教——一个被忽视的问题》一书第13章中披露:“法令强制规定每个清真寺都必须设立一个皇帝牌位,叫做‘万岁牌’。这个牌位要放在清真寺大殿附近的宣讲台上……”①转引自余振贵: 《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第六章,第183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6年。原文见于1910年伦敦英文版,艾沙·图乐新汉译,银川《中国回族古籍丛书》编委会刊印, 1992年。。同时,在大清律法中专门设有处置回回的特别法令,严禁内容包括:结伙行窃、抢夺、斗殴伤人,倡立“邪教”和传习“新教”,私贩玉石、大黄、硝磺、马匹,私造私藏兵器,放高利贷,禁止回回女子远嫁安集延,回汉斗殴伤人,回民驱羊践食庄稼和私铸钱币等。
明清王朝对伊斯兰教的政策,给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造成了极大的外部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为了谋求生存发展,中国穆斯林群体不得不顺从皇权,在政治上接受中国王朝的统治。为此,朱元璋曾说,包括回回在内的色目人“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间,有能知悉礼义愿为臣民者,与华夏之人抚养无异。”[3]海南三亚回族穆斯林与全国穆斯林一样,很早就已归顺中国王朝的统治。因此,明清两朝的地方政府,都将他们编入地方基层组织进行管辖,而他们也与当地居民一样,承担政府的赋税,遵守王朝法律。如《正德琼台志》卷7《风俗·番俗》中记有包括崖州、儋州、万州在内的所谓“外州者”②按:琼州以外的各州。之“番人”,“今皆附版图,采鱼办课”;康熙年间成书的《古今图书集成》卷1380记:崖州“今编户入所三亚里,皆其种类也……今从民俗,附版图,采鱼办课”。关于海南三亚回族穆斯林归顺王朝的史料,乾隆《崖州志》、光绪《崖州志》所载基本上与上述《正德琼台志》、《古今图书集成》相同。另据三亚回族《通屯宗谱全书》记载③关于三亚回族的《通屯宗谱全书》,王献军曾撰文《失而复得的海南回族族谱——— < 通屯宗谱全书> 探研》作详细介绍,该文载于《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 007( 1) : 33。,所三亚里在清代被划为十甲。镌于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如今仍立于三亚市凤凰镇回辉社区清真古寺的《正堂禁碑》,是三亚回族穆斯林承担赋税、严格遵守王朝法律的铁证。该石碑上的“正堂”,是对崖州知府的特称④封建时代称官府听政的大堂为“正堂”,至明、清两朝又特将知府、知县特称为正堂。。这一碑铭记录着当时崖州知府所管辖的海岸范围以及所属所三亚里、保平里、望楼里等近海各埠所承担的所谓“采鱼办课”的赋税。如:
……缘州属沿海东至赤岭与陵水交界,西至黄流莺歌与感恩接壤,共载米五百八十四石二斗零,共编征课银一百六十二两九钱零。近年所三亚里完银六十一两三钱零,保平里完银五十两六钱零,望楼里完银四十二两九钱零。⑤见三亚市凤凰镇回辉社区清真古寺的《正堂禁碑》原文。
在这一碑铭中,还记录着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所三亚里的回族穆斯林蒲儒嵩等与保平里士民徐翰珪(汉族)之间发生争控海面的一场诉讼。关于保平里徐翰珪“具控”的原因和内容,该碑铭中云:
……其海面虽无界址,而各里疍户向来按照各埠采捕输纳,或有异小艇呈请给照,在某处海面采捕,即帮贴其处课粮,交给该管,现该完纳,相沿已久。兹保平里徐翰珪,住居藤桥,欲将藤桥海面归贴保平,因以海面宽窄悬殊,具控前来。⑥见三亚市凤凰镇回辉社区清真古寺的《正堂禁碑》原文。
回族穆斯林蒲儒嵩等人为了维护本里士民的利益,呈状到崖州知府与徐翰珪争控海面。庭讯中,崖州知府经查考后,认为徐翰珪虽有不平之鸣,“但事已经久远,殊难纷更,仍着照旧分管在案”⑦摘录于《正堂禁碑》铭。。为此“勒碑”《正堂禁碑》示谕:
……示谕各该疍户人等知悉:嗣后务宜照旧,各在本埠附近海面采捕,朝出暮归,不得多带米粮,违禁远出或有异籍疍户到境采捕,该埠长俱须查明,呈请给照帮课,亦不得私行越界,强占网步,兹事,如敢抗违,许该埠长指名扭禀,按律究治,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在该碑铭中,崖州知府除了要求各埠渔民在原规定的海面捕鱼作业并按原规定采鱼办课之外,还严格规定不得多带米粮远出捕鱼,不得滋事。自勒此碑示谕以来,三亚回族穆斯林一直遵守官府的规定,从不违禁滋事。这说明他们在政治上已经接受中国王朝的统治,成为当地的臣民而中国化了。
二、中国化的伊斯兰教学说与“二元忠诚”
为了栽培伊斯兰教经学人才,明朝末年,陕西渭城人胡登洲倡导中国穆斯林宗教教育——经堂教育。之后,为了适应在中国环境中生存,处理好崇拜真主安拉与忠于中国帝王的关系,明末清初伊斯兰教理论大师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等,进行了汉文译经活动,创造性地发明了“以儒诠经”方法,以中国传统文化的术语、概念来翻译注释阿拉伯文典籍,用儒家思想阐发伊斯兰教理,把儒家思想融入伊斯兰教经典内容,大胆地提出了“二元忠诚”的主张,将忠主与忠君巧妙地结合起来,成功地建立起中国伊斯兰教的宗教学说。有学者称这一汉文译经之举“实为回教徒以中国文字阐扬回教学术的开端”,“有凿山开石之功绩”[4]。海南三亚回族穆斯林中,虽然未曾出现过著名的伊斯兰教经学大师或学者,但在全国创办经堂教育的影响下,清前期,海南三亚回族穆斯林的清真寺就开始了经堂教育。三亚的经堂教师最初从其他省区请来的,随着本地穆斯林不断北上各省区清真寺游学,本地的经堂教师被逐渐培养出来。就在这一频繁的请进来和走出去的伊斯兰教文化交流中,海南三亚回族穆斯林很快就接受了中国化了的伊斯兰教学说。
自清朝前期起,海南三亚回族曾从中土各省区请进来多少掌教、教师,由于未曾留下相关资料,已无法统计。所幸笔者在三亚市回族社区进行田野调查时,在三亚市凤凰镇回新社区西南角发现了“肇庆府高要县掌教刘老师墓”,该墓的立碑人是清朝乾隆年间的监生、三亚回族穆斯林名士蒲嵩儒,立碑时间是乾隆癸酉年(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这位长眠于三亚回族村落边的“刘老师”,是来自广东肇庆府的清真寺掌教,他在三亚回族清真寺里任教,为三亚回族穆斯林的伊斯兰教发展做出贡献,并在这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时光,此后一直被这里的穆斯林所怀念。至于北上游学的三亚回族穆斯林,在清末以前见于《通屯宗谱全书》记载的共有7人。具体人名详见表1:

表1 《通屯宗谱全书》记载北上游学的三亚回族穆斯林人员情况
海富润于清朝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游学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安徽、陕西,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返回故里路过广西时被拘捕,成为惊动全国的“携带经书案”。从学缘结构上看,海南三亚回族穆斯林伊斯兰教主要有陕西和云南两大学派以及广东、广西、安徽、湖北等派系,此外,从海富润游学返回故里时随身所带的伊斯兰教经书来看,除了“回字经二十一本”之外,还有刘智、金天柱等人著的《天方至圣实录年谱》、《天方字母解义》、《天方三字经》、《清真释疑》等汉文译著。由此可知,他所接受的学问除陕西学派之外,还接受了刘智等南京、江苏学派的经学思想。对海南三亚回族穆斯林伊斯兰教的学缘,日本人小叶田淳在《海南岛史》中记道:“到清代后期的时候,那边的人到广西、四川、湖北、湖南、陕西、南京等地去求学的非常之多,有的成监生,有的举为例贡。”[5]
海南三亚回族穆斯林由于较早就接受了中国化的伊斯兰教经学思想,在实践“二元忠诚”观念中,表现出真诚的态度。据有关资料记载,原羊栏回辉村清真西寺兴建于明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是一座具有中国宫殿式风格的砖瓦结构建筑,其正梁上雕刻着两条卧龙;原羊栏清真北寺兴建于明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礼拜大殿在构造上仿照西寺,正梁骨上也绘雕有两条巨龙[6]。龙在中国封建社会是皇权的象征,清真寺礼拜大殿正梁上出现龙的雕饰,表示对天子权威的崇敬,是对中国王朝正统地位的尊崇。另外,笔者2008年在三亚回族村落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了3块清代伊斯兰教徒的墓碑。这3块墓碑分别是“蒲太公婆墓碑”、“刘太公墓碑”、“刘老太公太婆墓碑”⑨这三块墓碑现收藏于三亚市凤凰镇(原羊栏镇)回新社区原三亚市伊斯兰教协会秘书长海世龙家中。。其中,《蒲太公婆墓碑文》正中竖刻着“清化”二字;《刘太公墓碑文》和《刘老太公太婆墓碑文》正中开头均竖刻着“皇清”二字。“清化”,无疑昭示其先人较早归顺清朝的统治,成为清王朝的臣民;“皇清”,则表示对清朝正统地位的尊奉。
除此之外,笔者还在今三亚市凤凰镇回辉社区清真西北大寺的礼拜堂正门,看到清末候选县丞魏华适于宣统辛亥年(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仲秋赠送的一副楹联,联语曰:
御赐偏南洲,道本真诚,爱国忠君,普天宜有勤王日;恩纶颂北阙,教原清净,食毛践土,秦地大彰扈驾功。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之纲领,即“三纲五常”,其中,“君为臣纲”为“三纲”之首。魏华适的上联中有“爱国忠君”、“勤王”,下联有“颂北阙”、“扈驾”,主旨均为希望此地穆斯林人人忠君爱国,尽力为清王朝效忠,因此首先必须遵从并努力实践“君为臣纲”的纲常。虽然对联是一位封建士大夫所赠送,并时值清末,但是一直被当地穆斯林完好地保存下来,说明这里的穆斯林不但信奉“二元忠诚”,而且勉励自己在行动上真诚地实践忠主与忠君的信条。
三、参与科举致仕
苦读四书五经并通过科举考试入仕,是中国古代社会知识分子的追求。自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不少穆斯林在儒学的影响下,也努力钻研经史子集,通过科举致仕。如宋人钱易《南部新书》丙集中说:“大中以来,礼部放榜,岁取三人姓氏稀僻者,谓之色目人,亦谓曰榜花。”⑩《四库全书》第1036册,《子部十二·小说家类一》卷3,第1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又有元人马祖常《石田集》中记道:“延佑初,诏举进士三百人,会试春官五十人,或朔方、于阗、大食、康居诸土之士,咸囊书橐笔,联裳造庭而待问于有司。”⑪至明清两代,随着穆斯林中国化程度的加深和回族的形成,读诗书应科举致仕的回族穆斯林人数更为可观,甚至在回族穆斯林群体中出现儒学世家,其中明末清初的山东禹城韩姓回族家族就曾出现“一门三知府,父子九登科”⑫《中国回族教育史论集》,第167页,杨湛山《山东回族教育史浅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的现象。
虽然旧时代的史志对三亚回族穆斯林耕读情况的记载甚少,但仅凭有限的资料,也可看到在清代,三亚回族穆斯林有很多人北上游学,为走上仕途而努力过,同时也有某些人成功入仕,有人成为儒学中的生员。如光绪《崖州志》卷16《选举志·诸科》中记载,在明朝“举人材”中,“回村”的蒲盛“以晓占城番字,授鸿胪司宾署序班”。据《明史》卷74《职官三》记载,“鸿胪司署序班”这一官职,是朝廷中专“典传班、齐班、纠仪及传赞”事务的。在清代,据三亚回族《通屯宗谱全书》记载,成功入仕的有2人,取得监生、武生、例贡、附贡的共有27人,其中,一甲改称高家之蒲氏家族1人,二甲改称哈家之蒲氏家族2人,四甲改称刘家之蒲氏家族4人,四甲改称杨家之蒲氏家族1人,五甲改称李家之蒲氏家族3人,十甲改称海家之蒲氏家族15人,十甲改称傅家之蒲氏家族1人,四甲仍蒲家家族1人,十甲仍称蒲家之蒲氏家族1人。具体如下:
高位明,监生,一甲改称高家之蒲氏系统第三代传人;
哈秀林,武生,二甲改称哈家之蒲氏系统第三代传人;
哈应□,例贡,二甲改称哈家之蒲氏系统第五代传人;
刘必恭,监生⑬其墓碑文中称为“恩进士”,见回新村海世龙所藏《刘太公墓碑》之碑文。,四甲改称刘家之蒲氏系统第七代传人;
刘生瑞,州同,四甲改称刘家之蒲氏系统第八代传人;
刘茗菘,监生,四甲改称刘家之蒲氏系统第八代传人;
刘生辉,武生,四甲改称刘家之蒲氏系统第八代传人;
杨景春,例贡,四甲改称杨家之蒲氏系统第五代传人;
李子英,监生,五甲改称李家之蒲氏系统第五代传人;
李春芳,监生,五甲改称李家之蒲氏系统第六代传人;
李春生,监生,五甲改称李家之蒲氏系统第六代传人;
蒲儒嵩,监生,十甲改称海家之蒲氏系统第四代传人;
蒲学嵩,监生,十甲改称海家之蒲氏系统第四代传人;
海士明,监生,十甲改称海家之蒲氏系统第八工传人;
海廷筠,监生,十甲改称海家之蒲氏系统第八代传人;
海廷洁,监生,十甲改称海家之蒲氏系统第八代传人;
海麟玉,监生,十甲改称海家之蒲氏系统第八代传人;
海麟昭,监生,十甲改称海家之蒲氏系统第八代传人;
海大兴,例贡,十甲改称海家之蒲氏系统第九代传人;
海文谟,武生,十甲改称海家之蒲氏系统第九代传人;
海文通,监生,十甲改称海家之蒲氏系统第九代传人;
海文辉,监生,十甲改称海家之蒲氏系统第九代传人;
海文锦,监生,十甲改称海家之蒲氏系统第九代传人;
海文绣,附生(贡),十甲改称海家之蒲氏系统第九代传人;
海文灿,武生,十甲改称海家之蒲氏系统第九代传人;
海德宏,翰林院,十甲改称海家之蒲氏系统第十代传人;
傅怀义,监生,十甲改称傅家之蒲氏系统第六代传人;
蒲文光,例贡,四甲仍蒲家系统第五代传人;
蒲启昌,例贡,十甲仍称蒲家之蒲氏系统第二代传人。
虽然明清两代三亚回族通过科举仕进的人不多,但从中可窥见,苦读儒书、力求进取在该族中已蔚然成风。前述《刘太公墓碑文》有载:“皇清待赠显考醇厚刚直恩进士刘太公之坟”,“皇清待赠”这是清代汉族碑文中的常用格式,“待赠”的意思是等待封赏,即死者生前未取得“诰封”,从中可窥见死者希望子孙高中并建立功业,以使自己获得朝廷的诰封。“待赠”两个字,折射出三亚回族在长居海南的生涯中,在周围汉民族和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也崇尚儒学希求仕进,像汉人一样望子成龙,袒露了其中国式的文化心理。
四、双语与姓名
中土各省区的回族先民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已逐渐以汉语为母语。与中土各省区不同,海南三亚回族至今仍保留其独特的语言,国内学者将其命名为“回辉话”,是中国回族中的特例。虽然如此,回族先民移居海南三亚后,就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磁场中,随着纳入王朝的统治制式、长期与当地汉、黎族交往,他们不但逐渐学会汉语(当时的“官话”)、汉语海南方言,包括当地的海南话、迈话、军话、儋州话等,甚至有人学会了黎语。因此,他们在实际生活中长期使用“回辉话”和汉语双语,而且其母语“回辉话”中也融入了汉语的声调成份和汉语借词。笔者到三亚回族社区进行考察时,除了用海南话与他们交谈外,也用普通话与他们交流。在旧时代,使用某种语言,就是对这一语言所代表的文化的接受和认同,三亚回族在保留回辉话的同时,多方使用汉语和汉语海南方言,是中国化的日常表现。
此外,从语言文化视角观察,姓名虽是个体称谓的符号,但在具体境遇尤其是语境中,人的命名很容易打上时代与社会的烙印。穆斯林原本只有名字,即经名,而无姓氏。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早在唐、宋、元时期,来自阿拉伯或波斯的穆斯林群体中出现了取汉姓汉名者,开始采用经名与汉名双名制。如元人安熙《默庵集》卷4中记述道:“类以华言译其旧名而称之,且或因名而命字焉。”但从总的情况来说,明以前取汉姓汉名的穆斯林尚属极少数,而且多出现在官宦与学者群体中。至明代,由于朝廷以种族革命相号召,厉行民族同化政策,汉语遂成为回族的共同语言,在这种背景下,穆斯林改用汉姓汉名便成为一种潮流。
三亚回族穆斯林何时采用汉人姓名,有关史志并没有明确记载,但在《正德琼台志》卷7《风俗》“番俗”、《万历琼州府志》卷3《地理志·风俗》“番俗”中记载:“其人多蒲、方二姓。”蒲(音Pu),是阿拉伯语Abu之简译,原意为“长者”,是冠于人名前的尊称[7],明代方志记载以蒲、方为姓氏,由此可以推知三亚回族采用汉人姓名可能始于有明一代。根据三亚回族《通屯宗谱全书》以及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的碑刻考证,三亚回族的蒲姓家族自清代乾隆年间起发生分化,有诸多家族改称为高、庄、哈、陈、刘、杨、金、李、江、海、傅、米等姓,其中除了“哈”姓是中国化的回回人姓氏之外,其余诸姓均是地道的汉族姓氏,而原来的旧姓“方”姓已不见于记载。关于清代三亚回族蒲姓家族改为他姓的原因,许多回族老人认为是为了便于在回族群体内通婚。实际上,这是三亚回族穆斯林群体中国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一个标志。
通观三亚回族《通屯宗谱全书》,明清时期三亚回族人姓名已不单纯是一般个体识别的符号,在姓名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其一,各个家族均确定了明确的字辈,这一家庭识别符号,渗透了中国传统血缘亲疏的宗族观念。如:
“一甲改称高家之蒲氏系统”字辈:茂、高、时、定、嘉(登)、位、德(文、荣)、少(中、宗)、俊(或步、望)。
“一甲改称庄家之蒲氏系统”字辈:茂、高、永、可、中、文、崇、怀、国、家。
“二甲改称哈家之蒲氏系统”字辈:成、琼、秀、俊、贤(景、应)、春(书、运)、国(秉)、元(承、荣)、永。
“三甲改称陈家之蒲氏系统”字辈:万、开、俊、国(秀)、朝、廷、子。
“四甲改称刘家之蒲氏系统”字辈:天、留、盛(大、富、会)、月、攀(定)、国、必(德)、生、贤、岳(明、文)。
“四甲仍称蒲家之系统”字辈,一是:玥、正、廷、汝、锡(必)、文、兴(家)、鸿;二是:玥、拔、汝、锡、文、家、鸿;三是:会、华、翰、发、桂、鸿、永、宗。
“四甲改称杨家之蒲氏系统”字辈:春、卫、光、德、景、发、启。
“四甲仍称蒲家之另一系统”字辈:献、显、元、玉(毓、文)、廷(天、龙)、如(文)、绍(德)、贵。
“四甲改称金家之蒲氏系统”字辈:廷、邦、孔、文、光、世、定、满、万。
“五甲改称李家之蒲氏系统”字辈:大、其、开、天(学)、子(嘉)、春(明)、振、显。
“七甲仍称蒲家之系统”字辈:维、朝、文、仕(盛)、殿、家(元)。
“九甲仍称蒲家之系统”字辈:成、琼、秀(有)、俊、德、书(芝)、国、元。
“九甲改称哈家之蒲氏系统”字辈有三个系统:一是:肇、元、学;二是:秀、俊、应、书;三是:成、琼、有、俊。
“十甲改称江家之蒲氏系统”字辈,一是:尚、成、奇(大)、苍、桂、日、万(玉)、德、朝、岳、振;二是:尚、成、荣、文、瑄、兆、元(有)、伟。
“十甲改称海家之蒲氏系统”字辈:尚、成、奇、嵩、中、清(润)、龙、麟、文、德(孝、章)……
“十甲改称傅家之蒲氏系统”字辈:尚、相、子(中)、肇(金)、凤(才)、怀(家)……
其二,每一个家族中所使用的汉名字,体现出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追求。如“一甲改称高家之蒲氏系统”,这一家族的第六代中有这样的名字:位公、位侯、位仁、位义、位善、位德;第七代中有:德孝、德悌。“三甲改称陈家之蒲氏系统”这一家族第四代中有:国仁、国义、国礼、国栋;第五代中有:朝瑞、朝纲、朝纪、朝仕、朝仪、朝杰、朝佐、朝佑、朝光、朝官、世昌、永和;第六代中有:廷尧、廷明、廷文、廷武、廷忠、廷光;第七代中有:子善、子美。“四甲改称刘家之蒲氏系统”这一家族第五代中有:攀桂、攀龙、攀凤、攀圣;第六代有:国才、国相、国选、国光、国典;第七代中有:必中、必恭、必宽、必信、必敏、德光、德照。“十甲改称海家蒲氏系统”家族第四代中有:儒嵩、学嵩;第七代中有:安邦、安国、安政,等等,不一而足。
回族的经名与汉名,分属两种社会功能不同的文化体系,但回族穆斯林个体均兼而有之,表明回族穆斯林为了既坚守宗教信仰本色、又适应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集二者于一身在命名上的兼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其融入中国社会的标志。
观察海南三亚回族穆斯林的中国化进程,可发现他们不但在行动上接受中国王朝的政治统治,在思想上认同接受中国传统道德和伦理观念,努力跻身于中国上层阶层,而且在保持自身民族特点的原则上,认同了中国文化,主动将自己固有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融入中华民族文化体系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三亚回族穆斯林偏于天涯一隅,无论在民族习性还是语言特性方面,都带有自己独特的印记,是中国回族大家庭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然而,这一族群自移居海南岛后,所处的社会政治背景与中土各省区的回族穆斯林基本无异,其中国化的进程和轨迹,基本上反映出中国回族穆斯林中国化的一般进程和规律。
[1]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1[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3.
[2]张廷玉.明史:卷226[M].北京:中华书局,2000:5757.
[3]明实录:卷26·明太祖实录一一丙寅条[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1:0404.
[4]傅统先.中国回教史[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155.
[5]小叶田淳.海南岛史[M].张迅齐,译.台北:学海出版社,1979:313.
[6]姜樾,董小俊.海南伊斯兰文化[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42.
[7]赵汝适.诸番志:卷上[M].杨博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6:3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