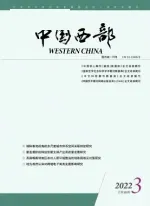民国奇人:马相伯
2013-05-14

他活了一百岁,曾担任过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的高级幕僚,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影响重大。他经历了从晚清到民国的阵痛与巨变,经历了中国的五朝皇帝,见过民国的六任总统。他一生的最大成就是在中国建立了一套现代大学教育的思想体系,创办了著名的复旦大学。之后,他又和英敛之在北京创办了辅仁大学。他桃李满天下,其弟子中有蔡元培、黄炎培、胡敦复、邵力子、李叔同、于右任、马君武、张轶欧等中国政界、教育界、学术界大腕。抗战时期,他以98岁高龄出任抗日“ 老子军”军统(即总司令)。临终之前,他沉痛地说出了这样的话,“ 我是一条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把中国叫醒。” ……他就是民国奇人—— 马相伯!
马相 伯(1840.4.17-1939.11.4), 祖籍江苏丹阳,生于丹徒,中国著名教育家、复旦大学创始人、震旦大学首任校长、爱国人士、耶稣会神学博士。原名志德,又名钦善、建常、绍良,改名良,字斯藏,又字相伯、湘伯、芗伯,字相伯,别署求在我者,晚号华封老人。我国近代伟大的爱国者、思想家和教育家。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之时,马相伯为国家民族命运前途积极奔走,为中华之崛起毁家兴学,不遗余力,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求学忧民 入仕救国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帝国主义武力打开古老中国的大门,拉开了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史的序幕,而马相伯先生,就是于此年诞生在江苏丹徒。成长在战乱纷飞的年代,他见证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和灾难,并且以一颗赤诚的爱国心将一生致力于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
马相伯出生在书香门第,到他的父亲松岩时,兼有亦医亦商的身份,家道还算殷实。由于父母信奉天主教,马相伯生下来不久便接受洗礼,还有一个“若瑟”的教名。幼年启蒙时,他先读天主教的经典,后习儒家典籍。12岁时,他只身来到上海,经友人介绍入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徐家汇设立的依纳爵公学。由于他资质聪慧,刻苦勤奋,犹对自然科学、外语有浓厚兴趣,先后学习法文、拉丁文等,受到意大利籍校长晁德拉的青睐。
1862年,马相伯入主耶稣会创办的初学院,研修中国文学、哲学、神学。1871年,他获得神学博士,并加入耶稣会,授职司铎(即神父)。期间,奉耶稣会之命,他到苏皖各地传道,适逢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躲到之处触目皆是“黄毛白骨”,“一望平芜”。哀民生之艰难,他请求父亲捐赠家产百金,赈济灾民,竟遭到耶稣会禁止。自后,在他担任依纳爵公学校长期间,又发生多起教会干涉学术研究自由之事,遂决心退出耶稣会,投身于社会改革的洪流中。这些都是他前期生活的一些经历,他有强烈的爱国报国之心,但透析国情发现清政府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在将倾斜的大厦上修修补补显然是无济于事了,由此开始了他的创校救国的征程。
毁家兴学 复旦光华
经历了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的失败之后,面对八国联军瓜分中国的惨痛现实,马相伯警醒到清王朝已末日将至。其时,从北京归来年近花甲的他,隐居在上海徐家汇土山湾,面对风雨飘摇的祖国河山,思考着自己大半生的奔走徒劳无功,弟弟马建忠又因为操劳国事心力交瘁而亡故,心中增加了无限伤感。
在学术研究之余,马相伯积极思考欧美强大和中国孱弱的原因,结合当年游历欧美参观几所大学的观感,他恍然悟到:“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之本,求材之道,尤以设立学堂为先。”于是他决心在中国兴办新型教育,培养救国救民人才。起初,他寄希望于教会,毅然拿出位于松江、青浦的家产良田3000亩,捐给天主教江南司教,并立下了字据称:“愿将名下分得遗产悉数限于江南司教日后所开中西大学堂收管,专为资助英俊子弟资斧所不及。”由此可见,马相伯的无私奉献与忧国忧民的爱国情结。天主教会虽然接受了马相伯的捐赠,但是并不办学,真正迈出办学第一步的还是马相伯自己。其时,马相伯居住在徐家汇土山湾,与蔡元培执教的南洋公学距离很近,蔡遂每天去马相伯处学习拉丁文,并组成译社。1902年11月,南洋公学学生反对学校专制压迫,200余人高呼“祖国万岁”集体退学,请求中国教育会负责人蔡元培协助组织“共和学校”。蔡乃请马相伯出面办学,后者欣然允诺并创办学院,定名“震旦”,意为中国之曙光。马相伯认为,创办学校目的在于推
倒科举取士的奴隶教育,而推崇西方格物穷理的自主之学,培养救国救民的青年才俊,“有欲通其外国语言文字,以研
究近代科学,而为革命救国准备着,请归我”。
1903年3月1日,震旦学院开学,学生达100余人。除临近各省以外,云、川、陕、晋各省亦有人前来就学。因反对清廷专制而遭到通缉的于右任,易名为刘学裕,亦被马相伯招至学校,免费提供食宿。建校以后,马相伯亲自任监院(校长),宣布办学三条宗旨:崇尚科学,注重文艺,
不谈教理。
在校务管理上,实行学生自治;在教学方法上,兴“学生自由研究之风”,提倡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倡导启发式教育;在课程设置上,把外语列为必修课,以西方名著作为课本,着重培养译学人才。马相伯坚持“不能把震旦学院办成宣扬宗教的学校,一切宗教教义的宣传均应退出学校的领域”,这触动了天主教会当权者。1905年春,法国天主教会主管阴谋夺取震旦学院,强迫马相伯“住院养病”,派其爪牙南从周接管,“尽改旧章”,妄图改变学校性质。此举引起学生极大的愤慨,决议全体退学。马相伯遂召集离散学生,并与严复、熊季廉、袁观澜等筹备复校。学生也积极配合,公推马相伯为会长,并选叶仲裕、于右任、邵力子、王侃书、沈步洲、张秩欧、叶藻庭等7人为干事,协助复校事宜。
在筹备复校期间,徐家汇天主堂耶稣会盗用震旦学院名称洽登广告,招收学生。为正视听,马相伯与严复、熊希龄商议,决定联合发表声明,澄清事实真相。两份声明于1905年农历5月27日同时见报,马相伯还向社会宣布,复校后的校名改为“复旦公学”。“复旦”二字,取自《尚书·大传》所载《卿云歌》中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即“复我震旦”之意,又暗含“复兴中华”之意。公告登出后,马相伯打电报给他的旧交两江总督周馥,请他助一臂之力。周馥大力支持,暂借吴淞提督行辕作为临时校舍,又拨给吴淞营地70亩为校址,并拨开办费大洋一万元。与此同时,严复、熊希龄、曾少卿、袁希涛、叶景葵等28名校董联名发表《复旦公学集捐公启》向社会募捐。百年复旦,在长江尽头东海之滨,终于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复校后,复旦公学声名远播,莘莘学子不计远近、不辞劳苦前来报考,第一批人数骤增至500人。经过严格的筛选,当面口试,最终录取考生50名。1905年中秋,复旦公学正式在吴淞开学,新老学生共160名。复旦创校之初,各种条件均极为简陋,而临时校舍已初具规模。其时,马相伯已然66岁高龄,除延聘名师授课外,仍自告奋勇,担任法文教授。他终日兀坐高台,口讲指画,滔滔不绝,不以为苦,其诲人不倦、献身教育之精神,无不令学生们感动。在马相伯率领下,全校师生筚路蓝缕,自力更生,终于闯出了一条由中国人独立自主创办新型大学之路。
1905年秋,应两江总督周馥邀请马相伯前往南京演讲君主民主政制之得失及宪法精神,遂辞去复旦校长一职。“一老南天传历史,蔩门百载播芬芳”,马相伯先生为创立复旦大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中国人都不会忘记。
国家之光 人类之瑞
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风雨飘摇,马相伯一直致力于救国救民之改革事业,从不记自身臣服与得失。
1907年4月,于右任等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他为之题词鼓励。是年下半年,梁启超在日本东京组织政闻社,宣称致力于提高国民素质,推动立宪政治施行,特请马相伯担任该社总务员,马立即应允,并于11月赴日本东京、横滨出席政闻社社员大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马相伯参加江浙诸省联军总司令部的工作,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并在民国成立后,任江苏都督府外交司长。
1912年,马相伯赴京任袁世凯总统府高等顾问,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之职。1914年以后,他历任政治会议、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平政院平政等,其间仍然致力于学术文化事业,资助创办辅仁学院、
1919年,80岁高龄的马相伯“厌闻时事”,虽挂有许多虚职,仍旧主要在家从事译作,唯对宗教和教育事业仍很关心,不仅捐献了全部家产,而且将自己历年所积薪金一万元捐给了启明女中。
九·一八事变时,马相伯已届91高龄。他深感国难深重,为救亡呼号奔走,发表《为日祸告国人书》,主张“立息内争,共御外侮”。自1932年11月起,他连续四个月发表了12次国难广播演说。他亲自挥毫作榜书、对联义卖,共得10万元,全部支援抗日义勇军。他先后发起组织江苏国难会、不忍人会、中国国难救济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等爱国救亡团体,被公认为救国领袖、爱国老人。在他家里召开救国会第二次执委会时,他特地写了“耻莫大于亡国,战虽死亦犹生”联语,与与会者共勉。
1935年12月,上海文化界人士组织救国会,马相伯被公认为“救国领袖”他写信给冯玉祥,表示愿以“首领”担保七君子,并在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在于右任的陪同下到南京竭力营救七君子。经过一年多努力,救国会七君子终于在1937年7月末获释,七人与马相伯合影留念,并由沈钧儒题词“惟公马首是瞻”送给马相伯。
民国26年(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日本侵略军逼近南京,冯玉祥、李宗仁劝马相伯移居桂林风洞山。次年,应于右任请,入滇、蜀,道经越南谅山,因病留居。民国28年是他百岁诞辰,4月6日全国各地和有关团体都举行遥祝百龄典礼。国民政府对他颁发褒奖令,中共中央特致贺电,称他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当年风靡中国的《良友》画报,历来凭借时髦的封面女郎吸引读者,却在马相伯百岁大寿那一期,以他的照片做了封面。此刻,这位老人俨然已成为这个国家的象征。

七君子与马相伯、杜重远合影
他给上海复旦同学会的亲笔信有“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老朽何为,流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语。他以前方将士浴血抗战劳苦为念,把各方赠与的寿仪移作犒慰伤兵 之用。还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委员。他在病重时,忧国忧时之情更深。他说:“我只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10月20日,他得知湘北大捷,兴奋异常,夜不能寝,病势加剧,11月4日溘然长逝。噩耗传出,举国哀悼。
1952年,陈毅市长派员陪同马相伯亲属去越南谅山迎回灵柩,安葬于当时新泾区(今长宁区境内)息焉公墓。“文化大革命”中被毁,1984年4月6日,迁葬于宋庆龄陵园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