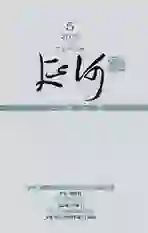幺六
2013-04-29陈家麦
陈家麦
幺六
16,也就是16号,是我的一位消费对象,我是她的一位顾客。
这地方的女人似乎都隐姓埋名,按编号来排,16号念作幺六,当然也会把17号念作幺七,以此类推,好像条形码上的前两位数字,这样念起来倒也顺溜。我不是正人君子,差不多逛过全城的按摩店,也就是敲背店。
今晚我喝了两小瓶红星二锅头,经过大概一个钟头的消耗,酒劲还上头,这样我保持勇气,奔向天堂鸟休闲中心,准备消费一下小姐,我饿了。这地方的二楼是足浴区,作为老顾客的我至今没在这个区消费过一次,这让我多少有点惭愧,可也让我进出店门时有了一种合理的借口,假如遇到熟人,或是我老婆,我会说来洗脚。
总台设在二楼楼梯口,领班是个女的,身体粗壮,像大片中的保镖,她见了我起身招呼,说幺六正在上钟,快了,问我要不要换一个?我摇了摇头。
这就意味着我要等幺六下钟,领班所说的快了,可能按她的职业经验来推算进度。但这种事无法像流水线上制造产品那样精确,比如机器做糕,从磨粉搅拌到喷出糕段每一批次差不多分秒不差。
我口有点渴,正好听到三声有礼貌的敲门声,知道她下了钟接着来上我的钟了。也不用我说请进,她推门进来了。我早已剥下多余的衣服,这一切都是为了节省时间。她“切”的一笑,表示对此十分熟络。
——给你来杯水吧,又喝酒啦,每次都这样,我把东西带来吧?
我点了点头,似乎说话成了多余。
这里所谓的东西就是安全套,我想她又得费一会儿工夫,拿套的同时,会顺便精洗一下自己,这好比刚用过的一只碗来了新顾客又得重新涮一下,总不能把刚用过的碗洗也不洗就端给第二位顾客。这样倒好,最好把刚才那口碗中的残留物彻底清理干净,我明知是不可能的。
记得我跟她几回熟后,她接受了我不戴套的要求,可接下来大概有一个月光景,我又来消费了,幺六说她身上来了盆腔炎,才治好,花了不少钱。当然她没说是我的缘故,这说明此前不光是我没用套。从此,她要求我必须带套,还说不光是一个人的安全。听来不算没有道理。可这规矩没多久还是给我破了。这是我的原因,从进一步来说,我的老婆也有不可推缷的责任。不过,我还是责人先责己吧。
这也是我喜欢她的一大原因吧。那次我有快两个月没碰她了,并不是我不想碰她。我想戒掉这种坏毛病,决心不沾染除老婆以外的女人。要说在这方面我并不是很强的人,我戒持了一个星期,可体内的这方面需求还是来了,总是从弱到强,直到我无法抵抗。那天天还没全亮,我就醒了,被身上的一股膨胀力弄醒了。这晨勃一发作连尿都退位了,我去了趟小便槽,还是无法排出,这种胀力真是莫名其妙。于是,我绕到阳台,也不顾光着上身,推开落地纱窗,进入我老婆与女儿合睡的卧室。我冲了进来,想把昏睡中的老婆掀翻,她终于醒了,见到我这种气势汹汹的样子,最终怕惊醒女儿,才接受了我的请求,可是当我把她当作小便糟一样排泄时,排尿的感觉反倒越强大了,反而那方面的胀力正在萎缩,最终退位,完蛋了,我是说那玩意儿变成漏了气的汽球,叭的一声掉了下来。最后,老婆愤怒起来,骂了句“你有病”。她让我从此别再碰她,这警告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但这一次似乎彻底让我断了与她此念。这不能怪她。
果真没了此念倒也安生,可是接着此念还在增加,而且扰得我入睡前也想入非非,难以剿灭。于是,我想自行解决,脑子里调动各种与此有关的幻象,来推进解决速度,终于让我在这种既折磨又快意中浇灭此念。但这种念头又隔时再来,前仆后继,这种排泄法实际上很不爽,可不得不爽,好比摘了未熟的瓜,瓜会痛的,这是我从最新一本科学杂志上看到的。
我的病该不是越来越重?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病,或者让人治好病。我想到了幺六。于是,当我再次回到天堂鸟,我只好说自己出了一次长差,才回来。幺六没有责怪,只说我又喝酒了,我知道喝了酒我才会把这种谎话说得更圆,可能多少没了胆怯。这次让我遇到了问题,当她的嘴巴滋润我身下那根短枪后,那枪有了进一步冲锋的勇气,可是刚进入战壕,我却兵败了,连头盔都快掉了。我肯求她,要求自己不戴头盔或许会有战斗力,否则不完成这次冲锋,我可能会像肉体炸弹一样自爆。她答应了,有点开恩的意思,我很感激她。果然,我从狭谷渐渐到达纵深部位,越战越勇,终于呐喊出声,昏眩中射出了一串子弹。我拥抱着她,可能让她喘不过气来,连夸她是我亲密的战友——哦,我亲爱的甜品。
“你不是有甜品——爱人吗?”她问,睁大幽幽的双眼,那是两只水汪汪的黑葡萄。
我抚摸着她柔柔的齐耳秀发,如果你是我的爱人多好呵。我抽出一张百元大钞,外加50元台费,其中10元是水果费。我说她辛苦了,并表决心,什么时候与你一起到外边玩玩,玩个痛快,开宾馆……
“好啊,到海边,我从没见过大海……”
隔了一星期,我又来了。
迎接我的是一副生面孔,说自己是幺七,幺六在上钟,问要不要让她来服务,她是幺六的老乡,新来的。
我摇摇头。
幺七领我进这排四间半封闭的小包厢,向隔壁小包厢的幺六通报:“你好了没有,你老公来了!”
听到“老公”二字,我脸面猛地喷血。
幺七催道:“幺六,快点,要不我把你先上了?”
“咋上呢?你身上有的我……全有。” 幺六回道,那个包厢里的客人也跟着放肆地笑了。
我躺下,听到隔壁的幺六有点放大了的哼哼声。
终于那边云消雨散,我等幺六从卫生间回来。
过了一会儿,我还是戴头盔不能前进,她再次施恩,终于让我大功告成,我再表决心,弄得她咯咯地笑了。我知道我是吃了一回饱,才夸厨师手艺棒。
“一起看大海吧!”
这下她笑翻倒床。
是我把她扳转回身,她像看天外来客,我用手晃了晃她眼,她打了个大大的问号。
我要了她的手机号码,并问了问的她的真名,这说明我不是在开空头支票。
“阿玉,是小名。你呢?小平头。”
“叫阿满吧,小名。”
此前我只知她是云南人。
旅程
我俩约定私奔一次,到棒槌岛,对我来说说私奔还不如说是偷欢,是为了投她所好,果然阿玉乐开了花。
记得她还是幺六时,问过我的职业,我说自己常坐在电脑前,又常与客户喝酒,所以弄得身体好糟,需要上这儿来轻松一下。她说你是个白领吧,当时我默认了,出于面子。
其实我是小广告公司写文案的,名片上印的是文案总监,仅有我一人做文案,就像我叫老板为老总,下面没有副总。
天热了,广告业务进入淡季,我向老板请了三天假,说去海岛养养精神,老板同意了,让我24小时开机。
老板说,你带美女了吧!
我谦虚起来,说我这号人,丢在垃圾桶里都没人捡!
老板阴阳怪气地笑了起来。他常拉我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骗老板娘说是业务应酬,这次算是投桃报李吧。
我请好假,阿玉也得请,她店里也有店规,规定员工每月只有来了例假才给假。听到员工两字,我差点笑掉大牙。我教她说这个月的例假来得有点乱。她按此说了,领班让她注意点,大概又给感染了,男人是靠不住的,现在得艾滋病的人这么多……
我还得跟我老婆请假,说这笔业务是外县的,得实地考察企业才能写文案,任重而道远呵。我没说你问一下老板,明知她问了老板也是白搭。
早上,我从家里准备出发,提了一只包,特地往包里装了一只二手笔记本电脑和一只数码相机,还检验了一番,这是为了迷惑一下,是真趟真公差。她知道我每次外出干活这两行头必不可少。还好,我老婆匆匆送女儿上学去了。
到了车站广场,见小香樟树下站了一个露脐装的艳女,压低了贝蕾帽,摘了下大墨镜,朝我抛了下媚眼,又速速戴上墨镜,像开始对应接头暗号。我朝售票厅走去,回头见她提了包,跟了上来。昨晚,我反复向她交待,务必让她与我保持距离10米开外,以及避免引起别人怀疑的蛛丝马迹,我让她一一记了,如果脑子记不住拿笔记,背熟后马上用打火机把纸条烧掉,谍战片你总看过吧?现在这么热播。
一切按我事先策划过的方案进行,包括可能出现的细节,这方面我多少算是行家,她第一步做得不错。我买了一张车票,隔了五分钟,又买了一张,这样两张车票不是连号的。我踱到候车大厅的售报柜,她已在那儿翻看一本《知音》杂志,我假装翻看《故事会》,随手往她另一只在柜外的手塞一张车票,然后我俩各自走开,她走向厕所。
看到她出来时,我已提早在6号窗口排队,她排在后面,我俩用目光作短暂交流。
上了车,她的座位跟我隔了三排。我俩不说话。中巴车驶过第三个小镇,我邻座的驼子老伯起身取下一只沉甸甸的编织袋,传出干虾的味儿。她站了起来,做了晕车难受的样子,一手捂嘴巴,那位老伯刚腾出位置,她就靠了来,还有礼貌地问我能否把靠窗口的座位调给她,又手指了指自己的嘴,似乎孕妇要吐清水的样子,这一切做得滴水不漏。等她坐稳时,我轻踢了下她的脚,很快我也被她反踢了下,这些肢体语言旁人是无法察觉的,但在我心头像有一万伏电流传来。
过了大概一小时,海腥味浓了起来,窗口晃过一排排插竹竿的海塘,水面有太阳光,闪闪亮亮。周边隔时晃过石屋,我知道快要到棒槌镇了。这地方我来过几回,我闭着眼睛都会走。
下了车,落了坡,走进石板铺路的小巷,千年的铁树终于开了花,“嗨”的一声,阿玉靠了上来,被我一把揽了。有人回望,我俩早已摘下墨镜。
棒槌岛
雇了渔民的一条小舢舨,伴随着马达声半小时后渡到棒槌岛。这岛名有意思,形状像妇女捶衣服的棒槌。这里有海滨浴场,还有私人开的小宾馆,那才是我想到达的终极爱巢。
我订了一间夫妻房,当然只有一间大床。房东只抄了我的身份证号码,也不追问我俩是不是真鸳鸯,社会真是开化多了。这里的小宾馆全是渔家屋,石屋石窗石瓦,瓦楞上压着无数块大石头,是为了瓦片不被超级台风刮走。这样的石屋像雕堡一样坚固,房内很干净,雪白的床单,雪白的长枕头,还有小卫生间,太阳能站式淋浴器。阿玉赞了起来,很清洁很安全嘛。
对于阿玉来说,岛上的一切都是新鲜的,她在沙滩上又蹦又跳,被我相机卡嚓卡嚓着。我还发现她是个游泳好手,只不过开头被海浪呛了几口水,很快像条美人鱼一样,舒臂蹬腿,只见迎浪而上的一颗美女头,像只会凫水的白天鹅,弄得我直招手又用双手做成喇叭伏,对着喧哗的涛声大喊大叫:危险——鲨鱼——回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对她如此关心。
阿玉游回来了,站了起来直喘气,身上水珠扑嗽嗽地掉,穿了泳装的身材越发凹凸不平,很诱人,我从没有见过她只剩一尺来布的身子。在天堂鸟,那是半明半暗的灯光,我的手只能穿过她的衣裳。
她说她小时候是只水鸭子,在河谷中游,那水有点甜,这海水么有点咸,托起身来往上抛,这种冲浪运动我靠还真带劲!
我听到自己的脑门上一记响,才还过魂来,赶紧用干毛巾替她擦身吧,我像澡堂里的服务生,擦并无微不至着。她嘻笑着说痒,又说我趁机揩油。
夕阳西下,海滩排档,太阳伞下,我俩吃海鲜。我向她介绍这是跳跳鱼,这是虾菇,这是岩头蟹,这是石板鱼……她吃一口呡口老酒。我开头不想喝,反倒是她来了酒瘾,我也跟着喝,不过这回我不想醉,弄得她一时糊涂。
我说,早点睡。有点急迫地抓了她手,阿玉让我别慌,有的是时间,只怕你子弹不够。说完,朝我做了做鬼脸:“去海滩吧,数星星,我没数过海滩上空的星星。”
没有月亮,天空倒有密匝匝的星星,她还在数,说跟老家数完全不一样,老家有密密的树林,这里多么开阔,天空真大,有这么多星星,眼睛装不下。
我数累了。阿玉靠在一块满是蛤蜊化石的礁岩上,仰躺了下来,眯上双眼,摊开手脚,像个大大的“大”字。
我凑了上来,吻起她长长的睫毛、含羞草一样闭合的眼皮,丰厚的上唇下唇,我小口小口地吻,就像小口小口地吃点心。我的舌头游进她的双唇中,被她张开嘴的舌头接了,吸了进来,两团不同的气息交游一起。原来,舌头跟舌头还可以这样亲密无间。
这是我久违了的吻,就像初吻一样。她说她没有过这样的吻,今天才有。
我想回小宾馆,很急迫。
身世
关上门,插上梢,拉紧窗帘,我俩互剥衣裳,像剥皮中的两只橘子,手拉手走进沐浴室。哗哗的水声,两身合一的摩擦声,沐浴露顺着上身到下身流淌的嘀答嘀答声。
我俩相拥而睡,是两具肉身纠结一起,不弃不离。
肢体语言退居二线,说话居上,听阿玉说身世——
我们村里的女孩子没有姓,我小名叫阿玉,念书时叫依玉,美丽的西双版纳你去过啵?我们的村还向南,靠边境,村口有一棵高大的望天树。
我们那儿女孩子出嫁早,我17岁时,寨里来了一位笑眯眯的阿婶,长辈子们叫她八婶,听说她走南闯北,给很多寨子里的年轻人做过媒。她来我家,跟我阿爸阿妈说,你家大女娃该嫁人了,说我长得那么水灵,该嫁到天堂去,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都说那地方,随便插根筷子都会长成金子。
我不远千里,哪知是来到的地方还是小山村。
嗨,我夫家什么西瓜大王,只是种了三亩七分山地的西瓜,那也是夏天种的。我们老家的人以为我嫁到了福地,其实那是个深山岙,跟云南老家也差不到哪去。我俩的婚房就那么一间土砖房,还是跟婆家人住在同一个小院子里。
我夫家一年到头往土里刨钱,天热时整那三亩七分地西瓜,也整不出几个子儿,我男人也不会动别的门路,倒是成天赌钱想赢别人的钱。
那会儿,我肚里有了娃,不跟他犯劲,别气了我肚里的娃。我生了个女娃,这下他更是拿我当母牛都不如。
我逃了出来,开头想找工作,可我连普通话也讲不顺。于是,我做起这一行,当然我没这么傻,没对婆家说,打死我也不会说。没想到有回街头碰上了我男人,给他揪了去,一路死打。在家没几天,我又跑到另一镇上,又给逮了回去,还是一通死打。我说不出去打工,将来女儿读书找工作这些钱哪来?我就跑到远一点的地方……
我俩说着说着困了,睡了又醒了。夜深,听见惊涛拍岸声。
“去海边吧,我睡不着。”
——我也是。
照片
拍了几百张的照片,记忆卡都满了,大多是阿玉的,也有她拍我的,我把全部照片复制到U盘里。
下午4点10分回到家,我老婆还没下班,我想坚持不躺下,但我的意志不听使唤。我累坏了,像大大透支了力气,就迷糊起来。
我醒了,是被我老婆弄醒的,她在大叫大嚷,女儿在卧室里,想打开门,被她断喝了一声。
笔记本电脑已打开,里面的照片是幻灯式放映的。
“好啊,香港出了艳门照,我们这小地方才出了艳门照,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跟在明星后头舔屁股,你当她是明星啊?这模特儿倒靓倒野倒浪,说吧,陈仓满?要不要把艳照放互联网直播?”
我飞快地从沙发上起来,拿鼠标删图片,直到把图片放到回收站,全部清空。
传来哈哈的笑,是我老婆。她手里拿有一只U盘,又从兜里变出一只,还说有很多很多,藏在阴暗的角落里,就是你——陈仓满先生翻箱倒柜也是大海捞针。
“招了吧,你招还是不招?那个小婊子是不是在天堂鸟?别以为瞒天过海,告诉你,我可是跟踪追击过。告诉你,我可不会闯到野鸡店,这种打脸撕嘴的下三滥勾当怕脏了我手……”
女儿在房里呜呜地哭。
“我招了,我认了,你说吧!”
“离!滚!”
我和她
现在办离婚的效率真高,只要不存在两方财产纠纷,落实好子女的抚养费,街道办事处那位胖阿姨说起这等事,跟学生会背乘法口诀一样。
我每月得给女儿付1000元抚养费,这是我愿意的。但是我没了房,没了分存折里的钱,我只分到1万元,她当这是她给的救济金,我不愿意也只得愿意,铁证牢牢掌握在我老婆——我前妻的铁掌中,天知道她还有多少只备份的U盘。
事情搞定,我跟阿玉说了,这回不去天堂鸟消费她时说,改在江滨公园的小树林中说。
她说离了是好事,她也其实离了,本来她跟她男人就没扯结婚证。
“我攒了点钱,在老家做点买卖。按我们老家的说法,是回乡投资。”
“我做梦都想到这地方,哪怕是变回猴子爬树!”
“这不是梦,我已买好火车票,两张。这回是连座的。我在上,你在下。”
“真的到你云南老家?”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