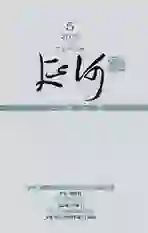流光过隙
2013-04-29黎峰
黎峰

小杨推门进来的时候,我没有立即转身。窗外下着朦朦的细雨,我在看雨丝击打常青藤和绿莹莹的树叶。其实我根本看不见雨丝或者雨点。这是一场酝酿充分的雨,不急着一上来就噼噼啪啪或者哗哗啦啦。它先用个铺垫,像音乐会的前奏, 不急不躁,体贴入微,只和缓细腻地发出蚕食般沙沙的轻响。我看见叶片在雨中的颤动,我本来想用颤抖这个词,但我看得出来,常青藤和叶片们稚嫩多情的小嘴,贪婪地吮吸饱满充分的雨汁,它们不紧张,不害怕,甚至还有几分久旱逢甘霖的欣喜,摇头摆尾,风骚撩人。毕竟,这是一场夏日的雨,来之不易,极其珍贵,前几天气温一度高达三十七八度,我们都动过上天捅个窟窿的想法。我呆站在窗前,呈一副深思或者忧郁状,我希望别人那么认为。
小杨重重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这种肆无忌惮的手法我也用过,在抓住别人把柄的时候。果然,他就举出一封信来。我明知他不会轻易给我,但还是伸手去抓。小杨打下我的手说,怎么办,请客吧?这是个要命的规矩。我还忘了向大家介绍,我们是清一色的男性军校学员,年轻活泼,斗志昂扬。如果侥幸抓住你一封字迹娟秀的来信,他们一定会软硬兼施,甚至不惜采取最极端的方式,达到看信或者得到诸如一根火腿肠、一袋方便面,而或一包香烟,一瓶小酒,一顿饭的代价。我已经比较清楚地看见了信皮,也许我还抖了一下,小杨愈发有恃无恐地笑着。我装成恼羞成怒,说,请个篮子客,你愿意给就给。小杨捏着信跑出去,他在鼓励我去追他,然后讨价还价,逼我乖乖就范。我没有去追。对付这种人的最好办法就是沉默,让他失去衬托,在无聊中失措、枯萎。
信回到了房间。小杨没有走开,他说信里有照片,我反复强调没有,她不可能给我寄照片,我们不可能到达那个程度。小杨固执地坚持,我允许他开信。信皮上是久违了的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字迹,她写些什么我已经能够猜到,她来信本身就是暗示,就是怀旧与眷念。但是她不会给我寄照片,她没有那么大度和煽情。她绝不会的。小杨真抽出一张照片。我没有看到,他抓着就跳开去,说,好漂亮,好漂亮哦,捧着照片连连亲吻,屋里还有另外两兄弟,他们也抢过照片,传递着调笑,传递着亲吻,我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照片终于到了我手头,我发出痉挛的笑。照片是风景,一匹菱形的山梁,有一片麦苗和一棵独立的松树。色彩不太好,底色昏暗,麦苗和松针的颜色淡黄。这不是它们本来的颜色。我到过那座山,是在今年春节。好像是初八那天吧,她打电话来问,你在干什么呢?我说在等你的电话接受召见呢。她吃吃地笑了一阵子,笑声像花瓣,片片飘落,我拾不起来。她旁边好象还有一个人,我问你在哪儿?她说她在朋友家,来了两天了,天天打麻将,没意思透了。然后她又说,你来吧,我们等你。她的朋友在另一个镇里,离我家有四十多公里。我本想坐公共汽车过去,但是早班车要到十点才发,春节没人到那么偏僻的地方去,很难凑一车人。我是打摩的去的。我穿着军装,戴着军帽,戴着皮手套。军装让我威武自豪,皮手套让我暖和,不畏艰难险阻的满天风沙。
那天下午,我们爬照片上的山。山是废弃的山寨,占山为匪的山大王早已作古,没有留下陪衬山石的树木,农民们垦出一块块地,横三斜四地铺在山上,种了一些孱弱的麦子。上山很容易,我们六个人,她,我,她的两个女同学和其中一个女同学的男朋友,还有她同学的妹妹。她穿着高领羽绒服,口袋很大。她不断从里面掏出擦炮来,啪啪,往她同学脚下放。她的两个同学捂住耳朵,吱吱呀呀地叫,去抢,挤成一团,我站在后面,看她们疯闹。爬上山她们就长吁短叹,揉腿捶肩。我站在寨门顶上,看下面。下面是一片村庄,村庄不大,房屋稀稀疏疏。村庄旁边有一条河。河道宽广,泊着一些木筏。我睁圆眼框,努力不让眼球动弹,看了三五分钟吧,河水漫溢铺洒,不断变幻着颜色,淡白色,白色,白金色,绿色,先是星星点点惊乍乍地在我眼里跃动,继而联成一片静止,平了山梁河谷村庄田野,全变成玛瑙的翠绿。眼球酸涨了,我揉了一下,河道回到原来的位置,河水在流动着,我听不见声音。
我掏烟,抽上。我想使自己表现出有思想,或者接近于有思想的样子。果然,她就走过来,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她问,看什么呢,那么认真?我说,你看,那条河。河道弯弯,河水不动声色地流淌。岸边上那片村庄鸡鸣犬吠,阡陌纵横,红砖青瓦含苞欲放,树木郁郁青青,恬静如画,我说多美好啊,假如我是河水,我就泊在那湾里,留住风景。她想说什么,但没说出来。她的同学叫她,小禾,到松树下照相。山梁上就这么一棵树,在地头。地里是麦苗。很浅,刚刚冒出地皮三四寸,油绿绿的小可怜儿。她说,走吧,照相去。我想和她们照张大合影或者和她照张小合影。我没有说出来,我看她。她咯咯地和她的同学逗笑。她说她同学的男朋友,你把小花抱紧点啊,那么保守。她的笑声清脆而明亮,像断线的珍珠,颗颗抛落,诱人去捧接。她的同学也感染地笑起来,她们的笑声极富穿透力,振荡着山梁和麦苗。然后她又叫我过去跟她同学的男朋友合影,她说,你们男子汉照一个,留个纪念。她也照了,抱着她同学的两只哈吧狗,卧在松树根上,摆首弄姿,浑如天成,她不停地对狗说,宝贝,别动。
下山的时候,我紧紧跟在她后面。山路很陡,她穿着高跟鞋,走一步,蹲一下,我说我拉着你吧。她伸过手来,手指细长白腻,像裹紧的棉花糖,我怕捏坏了。我抓住她的手腕,隔着一层羽绒服。我对她说,下午到我家去吧。她说不呢,出来好几天了,明天早上要回家。走过一段路, 我又说,到我们家去吧,我明天送你回去。她说,算了吧,从这边回去比较方便。到了平路上,我松开她的手,她走在我前面,她的背影纤细小巧,头发绾成发髻,象一只小鸟,光溜溜的,自尊高洁盘在后勺上,露出一段白白的脖颈。我看了看,对她说,我初十就要回军校了。她说,我会给你写信的。
下山后天就快要黑了,我说我回去了。她说,不走吧,天都快黑了。我说,来得及。然后我租了一辆摩托车,重新戴上军帽和皮手套,车一跑起来,风就从我耳边呼呼地刮过去,脸上也是风,风像一张网,我一头扎进去却撞不开一道缺口,它只是弹性地后缩,仍然四面八方地包围我。
这是我和她的第二次见面。我现在在开始回忆我们的点点滴滴。也许,我是想向你们讲述一个关于我和她的爱情故事。这故事里不仅有我和她,还有我过去的青春和起起浮浮的梦想。
上初三时,班里调进来一个同学,个子比较高大,叫彭一光,老师把他和我排成一桌。他总是收到好多的信,是另一个镇中学写过来的。上自习课时,他把书盖在信纸上,讨好地给我笑笑,然后写回信。老师过来了,我捅捅他,他就若无其事地放下笔,看书。他挺感激我的,主动报以琼瑶,有回给我看了一封信,是一名叫李小禾的写的。字柔若无骨,纤细灵巧,整整齐齐的豆芽菜。写的是学习太紧张了,老师整天阴沉着脸训人,班里连说个知心话的人都没有,怪寂寞的。彭一光给我说,这是她以前的女同桌。我怀疑是他的女朋友。我们班上那时候男女生青春萌动,敏感好疑,谁多看谁一眼是都有情况,男生跟某位女生说一句话那就是在明显地谈恋爱。我暖昧地笑了笑,彭一光急红了脸,说,真的,我们只是同桌,什么都没有。要不,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他要我写一封信。
我现在已经记不得我写了些什么。好像也是骂学习,骂老师,骂该死的升学考试。大约两个星期后,我收到了回信。那是我学生时代的第一封信。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4月29日,风清云淡,花香扑鼻。我一个人跑到操场上,把信撕开一个角,插进钥匙,沿着封舌拉开,探火似的取出信纸。我看了很久很久,以至于我现在都能把那封信背下来。她说,你的名字真好听,如果不是这名字我都不想给你回信了。她还说,真没想到在初中的最繁忙的时候能认识你这个朋友……我就不往下写了吧,少男少女的信总爱堆砌许多捡来的名句和华丽的辞藻,而它们的意思我们并不真正懂得。比如她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们的友谊海枯石烂。
我在操场上坐了很久很久。操场空旷,微风轻拂,草地柔软踏实,有一股潮湿的、发酵的气息。我看见夕阳在金黄的彩霞中滚动,彩霞绚丽斑斓,喷礴着七彩的光环。我还看见每一个走过的人春晖满面,对我发出不可琢磨的微笑。
直到现在,我仍然难以忘记那天感到的幸福,它像搁置在心里的一块石头,永远不能消解。我就是在那瞬间真诚泛滥,好象是一尾受不住诱惑的鱼,处心积虑等待到感情的网打捞。在那个纯粹的时代,我的每一个日子都充满着阳光和期待,洋溢着桂花的香气和喜悦的笑脸。我捧出最美的词汇奉献给她,我把我喜欢的书都寄给她。我以为我喜欢的她也一定喜欢。我开始写诗,写思念是天上的云,思念是风中的水什么的,我还抄袭过杂志上的爱情诗。我也收到她很多信,现在还保存着。一共三十九封,圆珠笔写的,钢笔写的,铅笔写的,她在每封信的后面都注上,X月X日于晚自习,X月X日于午后,X月X日于家中。她还给我寄过照片和卡片,她在卡片上写到:生命之中总有亘古的缘份,你我在人生的旅途上镌刻出的友谊痕迹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失。那时已经临近中考,我们踌躇满志却又忐忑不安,激情勃发的我们看不到来路的风雨交加。
时光流逝了,我依然在这里。为了直接叙述我们的第一次见面,请允许我做一次简单的跳跃。我在苦苦地追忆。生活淘尽了风霜雨露和雷电霹雳,我不得不打捞纷沓的情感,我记起来了,那是梅雨时节,刚刚知道我从录取通知榜上逃跑,父母一直不肯相信。他们卖粮食卖鸡蛋不穿新衣服不吃荤菜,从一瓣汗里摔出三分钱来,把聪明透顶的儿子送到全县有名的重点中学,怎么就考不上一个高中呢?他们逼我去问学校当局。在一个雨天,我穿着背心,穿着雨靴,走出家门。我到了她们镇上。彭一光和她在同一个镇上,他和我一起去找她。她家在镇供销社里,一栋单独的小楼,听说她父亲是供销社的主任。她那天刚刚洗过头发,批在肩上,我们坐在她家的客厅里,她给我们看她的影集。第一张是她和她妈妈偎在穿军装的人堆里,她说她父亲曾经当过兵,她妈妈早就去世了。那时我还没学会虚伪,没有安慰她,继续翻看。照片上记载了许多高楼大厦,广场商场,海滩岛屿,名胜古迹,都是我没有到过的地方,我很欣赏她在那么多照片上的笑脸。她在一旁撸着头发,隔会儿同我们说几句话。她的声音飘渺轻柔,像从香水瓶里倒出来的,我能闻到一股香气。我偷偷地瞟她,从她的微笑和眼神里,得到无限的温柔,她是一线光,我认住那线光,走过去,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时间板着面孔走它的路,天黑了,我有些气喘起来,她始终没有一些制止我们留宿的暗示。她父亲和她弟弟不是那么热情,她自己下厨做饭,炒了一份丝瓜,我们吃得津津有味。然后我们站在她家的阳台上,谈到我们的分数,她被录取了,彭一光差十多分,准备读议价高中,那几年学校搞创收,允许不上线的考生就读,只是多交两千多元钱。我黯然神伤,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她对我说,要不你也去读议价高中吧,那样我们还可以同学。我不能告诉她家里没钱,那是一个残酷的话题。我感到一阵辛酸的刺痛。我看到墨色的天空布满了棋子似的星星,星星结成一张网,铺在我们的头上。我们不知道天什么晴起来的。
那天夜里,躺在她家的床上,我梦见了她甜甜的笑脸和如云的长发。半夜里我爬起来写诗,我想用诗句去描绘蛇身的彩纹,诱惑她和我,其实我根本不能写到那个份上,我好象篡改了唐婉陆游的《钗头凤》,还录下了“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豪言壮语。
现在想来我真佩服自己孩子气的勇敢,第二天一起床我就交给了她。我问她要了三张照片,准备离开,也许我忽视了她作为一个少女初次经历这种事的忐忑和腼腆,我居然要求她送送我们,她没有答应,我一本正经对她说,但愿这不是最后的见面。然后我挺着脖子离开。多年以后,我读到《堂·吉诃德》总是想起我在阳光下穿着雨靴走开的情形。
我说通父母也上了高中。我只差两分就上录取线,但是校方说,还是要按议价生缴费,城里的舅父通过关系找了一位副校长,同意我每学期只多交一百元。读了一年,那位副校长退休了,校方通知我按规定每学期多交四百元,父母坚决不答应,我回到家里,她也挺惋惜的。父亲开始教我犁田耕地,我在黄土地里明白了阶级的差别,我心犹不甘地放弃梦想,学习做一个老老实实的农民。末路英雄成功的灿烂辉煌,滞重着我的呼吸,日子一天天拉长,在这最需要情感安慰的时候,她写信给我,用精神药草的香雾弥漫我头破血流的现实,我想不出拿什么东西来充斥给她的回信,我也不知道她还有多大的热情。在那些忧伤的夜晚里,我经常做梦我们在同一所学校学习,我们在课堂上递纸条,我们在一起读《红楼梦》,我看见自己化为她眼上的一根眼毛,永远地依附着她。我希望这梦再长,再久。梦醒了,一身冷汗。心为另一层膜裹紧着,所有梦中的欢笑,都是膜外的东西,我鼓不起勇气来向她倾诉。大概就在那时我立下了不混出人模狗样来,不再给她写信的决心。我试图让一些疯狂的念头在心底生长发芽,偷偷地寻找机会开花结果。
我在沉寂很久后写信给她,报告我入伍到了军营。她又和我有一搭没一搭地通信。在那时我感到部队的生活艰苦寂寞,说话办事一本正经,跟电影里的共军一样正直铿锵,是非人类的生活方式。我过得好又不好,一丁点儿现实还行的愉快夹杂着一丁点儿出头之日太远的不愉快,心情反复不断,喜怒哀乐周而复始。时常是在情绪极坏的时候,我才会写几笔前去叩响她的门,淡淡的几句话,鸡零狗碎,也不足以道出我的心情,但是我却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觉得我无论做了什么,在她那里均会获得心灵深处的理解与真正的交流。心灵得到的那种无需解释的默契和慰藉就消失在她无意的问候与闲聊之中,一切如意不如意也瞬间荡然无存,即使存在,对我也不再影响。心情就因此而舒展,像花朵一样,虽然也许将遭受灭顶之灾。
我读了不少富家女贫家汉的爱情故事。套进她和我,我是做着我幸福的梦:假如我能有一个像她那样关心理解安慰我的人,这还不能使我更发奋,更上进吗?我一天到晚像在沙漠里需要一种水分,我觉得只有从她的身上,我才能得到我需要的食粮,才能得到我长途人生奔驰的油料。我给她说,我要按捺住出人头地的野心,用狂热的血撞开另一条光芒四射的路,我马上自学,准备考军校。她说好啊,解放军,等待着你的喜讯。在那些玫瑰色的夜晚,我看见了葵花开满田野,开满山谷,花儿亭亭玉立,翘首期待,等待着威风凛凛的蜜蜂。蜜蜂勤劳勇敢,乐观奋进。
我现在常常想起连队的那一个花园。一路水泥栏杆,两边柳条低垂,八角亭子翘檐翱翔,门户空洞笑口常开,我拿了高中课本静坐于斯,磕磕巴巴地学习,虽然很辛苦,但是我能够忍受,因为她似乎就坐在旁边。有时我拿了她的信,像一只轻快的麻雀,穿过长长的走廊。和风环绕着我,我在静亭里风情万种,心无旁骛地读信。信其实早已看过,我只不过是重复地体味和咀嚼,我希望能够读到我希望的字眼,因为我不敢在信里赤裸裸地写上爱你之类的语言,我含蓄地发一个擦边球过去,让她看清楚,接回来,她似乎比我高明,接一个右边球,打回一个左边球,扑朔迷离。比如她说,又是一年三月三,可别线在手,风筝未上天。她还写过此岸真诚泛滥,彼岸是否丰收诞生一片的诗句。我很难读懂,好象有点什么,又好象什么也没有,当然我是认为有点意思的,当时我以为我们心中间只隔了一层玻璃,彼此的想法能够看得清清楚楚,但是我鼓不起勇气撞碎玻璃。我想到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愿意用一个关心的存在,安慰我寂寞的军营生活,我想设计一个美丽的结局,使我不敢倦怠,为着目标而努力奋斗。
直到今天,我不知她是否发现我不可告人的企图,我整整埋藏了三年,我吃惊我的坚韧不拔。有一天她写信给我,她说她在感情上走了很远,伤害很深,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我知道她说的不是我,她已经到了一所大学。我受命于危难之际,用振人于苦难的崇高化解吃不到葡萄的心酸。她还说觉得自己丑了,发霉了,没人喜欢了。我好象看到了一丝希望,我甚至以为她是在试探。我缺乏军人的直率和行动,我的小心翼翼暧昧不明,我的局心叵测激发她采取主动,勇于冒险。但我判断不清,我不敢用我的自信去伤害她的自尊,我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我曾经在一个夜晚偷偷地溜出宿舍,把身子放倒给一片草地,风大大咧咧,狂噬草尖树叶,虫子低嘤伤心失意,廖阔星空的牛朗织女寂寞孤立,等待拯救和延续,我像一只飞蛾,看到一道温暖的火光,决定义无反顾地焚身自毁。
好象我是在一次酒后给她写信,当时激情如潮,坦露的欲望不顾廉耻,我说我要用我的奋斗青春为她缝制人世间最美的花轿,这是我第一次直白地向她爆出狂热的爱恋,绝有没远兜慢转,我设想信是一颗子弹,射中她羞涩的心脏,她会满心愉悦地拒绝或者迫不及待地回应。她的回信姗姗来迟,我翻来复去地寻找判决,没有,就是没有,她若无其事地谈毕业分配,谈天气市景,一个空虚!我心头血浇的鲜花刚刚捧给她就已经枯萎,我落寞地坐在房间里,真想大声狂呼,谁来救我,谁来救我!我曾经告诉过她,我失去了两次考军校的机会,冷静地想想,我一厢情愿地理解她为何不明确回答,她大概是害怕我的出身山村,亦将归于山村。但是她又没有绝望,不言自明地给予我机会,迫我在现实缩短我们的身份距离。我陶醉于自己的理解,我重新编织生活的光环。我看见我穿着军官服和她在雨中漫步,我牵着她的手,她靠着我的肩,雨水滋润着我们的长长的征途。
当兵第四年我回过一次家乡。我有了三次三等功,但是在部队不能直接提干,信了报纸上的优先安置政策,我专程回去寻找后路。不过看来十个三等功也不能当饭吃。我到民政局去问,他们说,小伙子,农村入伍的不在安排范围。现在立三等功的退伍兵多咧,你还是争取留在部队慢慢干吧,那样才有前途。悲观失望的当儿,舅母给我张罗了一个姑娘。一个圆滚滚的城里姑娘,长得比较丑,舅母说她父亲是镇里的一个什么所长,能够为我找工作,农转非。父母认为漂亮是我们农民无法企及或不屑一顾的东西,说能让我不再回到黄土地里受苦确实不错,三天两头做我的思想工作,我最终还是决定放弃这块天上的馅饼,放弃外来的美好力量,生活在自己的愿望当中去。那时她刚刚分配到县城工作,我没有去找她,我想等着用自己肩上的硬牌子银豆子买一张车票,一张出类拔萃的车票。
小胡现在开始进入我要讲述的故事,他是一柄暗藏的利刃,不经意的脱鞘而出撕心裂肺。他探亲归来请我们同一个县城的战友喝酒,并报告假期的艳遇,他说他交了一个女朋友,在商业局。我酒酣耳热,英姿飒爽,我说世界真他妈的小,我的女朋友也在商业局。小胡先说出他女朋友的名字,我用极大的努力把笑的纹路留在嘴角,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小胡家在县城,据说他父亲是劳动局长。他红光满面地讲述他们一起跳舞,一起吃饭,他还炫耀他们的亲吻。我吞咽着烈酒和毒素,我看见一口井,测不出冷暖,看不出深浅的井,我看见我像一块石子似的掉下去,发出一声响,回音缭绕,启示后人。我还听见静穆的云天传来世纪末的丧钟,一个声音对我说,你死去吧,你死去吧。
我再也没有给她写信,我们像两根直线,谁也没有预料到会在偶然间交错,但是,无限延长下去,我们只能有一个交点。我看到了那个结局,我殚精竭虑地学习遗忘,我好象也哭过一回,并不忧伤,我只是用眼泪洗涤我的年轻的心。我深信时光会冲淡一切,包括自以为是的真情和璀灿辉煌的记忆。我是一头疲倦的刺猥,需要蜷曲成球,竖立起长刺安全地休息。她心有灵犀遥相呼应,再也没有写信来打挠我,我像赌气的孩子真的开始怀恨在心,我曾经掀起一朵欢欣鼓舞的浪花,气势汹汹的风暴一阵狂撕猛咬,我们只有最终各走各的路。
睡眠让我常常回忆她的每封信和每一个暗示,总是在许多念头纠缠不清时,我突然醒来,无望的单恋,匆忙的逃避,留下痛苦的结晶体耀人眼目。我觉得似乎该对她我说点什么,但我不知从何说起。无数的心期在犹豫徘徊中销磨殆尽,我真的开始遗忘,从自己的感情里开始真正的逃遁。
我差不多完整地叙述了我们的爱情,那是草地的沼泽,陷进去我的少年、青春和我一度放逐了的乏味的信念。我想方设法解脱出来,在繁忙的训练中超脱了我的神魂颠倒。我想在此定格灰暗的记忆底片,但是当兵第五年我被保送上军校,离开连队的前夜,我收拾行装,她那一摞信件灼伤着我的手和神经,我不敢相信她曾经给我写过那么多的信,厚厚的一沓,汪洋资肆再次震憾着我,我固执地以为我们的沉寂只是一个悬念,我思考两个问题:
1:她不爱我为什么给我写这么多的信?
2:我是否因为自卑没有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我给她写信,说身份的改变和没有改变的爱恋。这是一个她添一笔就可以完满的圆圈,我想象她惭愧的回首,羞赧的低头,言辞闪烁的回答。她没有给我回信,我以为她已经不在原单位。但是有一天,学员队长叫我接电话,我已经忘记了她的声音,我根本听不出是她在咯咯地笑我的健忘,她很是无奈地报上大名,我听见身体里血脉在沽沽的亢奋,房间里有暖气,汗珠凝结在我的脸上,背上,我能体会到汗水的流动和蒸发。我局促不安地站立,脚下是一片沼泽,粘乎乎的,我说名花有主了吧,她说哪里哪里。我说,怎么样?给个回答吧。她说,你现在很不冷静,等一段时间再说,好吗。本来我想象电影里一样,肉麻地说一些非人类的爱情语言,但队长的目光狐疑,我不敢放肆,我想我还是给她写信吧,信上什么话不能说不敢说呢。
我是一名得令的战士,以每周一封信,每月四个电话的速度向已知名的高地发起勇猛的攻击。我胜券在握,欣然而又谦逊。我用信编织神话和笑话,编织我的梦想和我们的未来。在冬雪飘扬的夜晚,我的笑倨傲火爆,我想象我是一片雪花,度关山,越重洋,滑入她的脖颈,体味她体肤的温馨。她矜持不安,她几乎是小心翼翼地说,反正你春节要回家,回来再说好吗。我为我们的春节设计无数种方案,她预支一份幸福给我,像一块永不会变馊的蛋糕,搁在那儿就是搁着一个愉快,等待我们聚在一起共同分享。
回家给她打第一个电话,她说你还没有冷静下来啊,这么多年了,我对你说了许多真话,也说了许多谎话,包括现在,或许也有几分假言。我们只是初中的一个偶然,那在故做老练。虽然是很认真,但那是在学校啊,学校的日子单纯美丽,情感也纯如白纸却又缤纷艳丽如水彩,我们,我们现在还能有什么……?一切只能是回忆。我说,难道真的没有什么吗?就算没有,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她说她很忙,过两天再打电话给我。
第二次通电话,我说我想见见她,她说太突兀了,她想想再说。
我们的见面就是爬山那天。我们在下山后有短暂的交流,其实我们没有建设性的意见,我们在重复各自的语气,我原来以为她的退缩是因为叶公的好龙,事实上我们都十分的平静,我们惊诧我们的平静。我始终想让一个生动、鲜活的故事充盈我的心,激荡我的激情,而她一直把我当作很好的异性朋友,分享着我的快乐和忧愁,通过我了解另一种生活。认识到这点,我才平静下来认真分析,其实,我们只是相互陪伴的灵魂,我们只能悠悠心会,我很不想承认这点,但我感到这要轻松得多。我们握手再见时,一道阳光穿过我们身体之间的缝隙,我们蓦然一惊,都没有动身走开,我们在等待阳光过去。后来一切好象都过去了,又好象依然在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