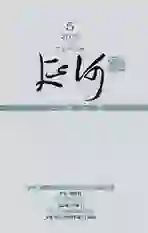肖云儒:一个艺术评论行道里的“玩家”
2013-04-29
“形散神不散”理论的提出,使他少年成名。经过多年不懈努力,肖云儒老师已是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和陕西省政府“德艺双馨艺术家”。
他勤奋钻研,对文学、历史、哲学、戏剧、民俗等等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追求的是自由的精神生命,他是“思想的丰产者”。
他乐此不疲地在各地电视台文化栏目解读西部文化,为西部多个城市做文化代言人,他是“西部文化大使”。
他为人谦和,乐于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思想果实。我在学生时代,曾有幸现场聆听过一次肖老师的讲座,他以《在大地收割思想》为题对文化、对生命进行诗意的深度挖掘,时至今日,依然印象深刻。此次访谈,也算是对此前现场聆听完讲座没有得到提问机会的一次弥补。
当前文学环境是建国以来最好时期
李东:肖老师您好,很荣幸您能接受我们的专访。有人认为文学被边缘化了,典型的例子就是纯文学期刊市场的不断萎缩;也有人认为网络的出现,让文学作品传播更加自由和便捷,文学环境前所未有的宽松。您认为当前文学处于什么样的环境?
肖云儒:你说的这两种情况都存在。两种情况同时出现,还在不断的发展中交织,便正好回答了“您认为当前文学处于什么样的环境?”这个问题。当前文学处于一个历史大拐弯、历史大转型时期,这个时期最根本的特点是现代文学市场的出现和构建。它远不是指图书营销市场。文化市场的深层主体是读者,在创作的价值追求、题材内容、表现和传播手段,乃至语体语感各方面,如何适应读者这一市场主体,是任何作家绕不过去的问题。在这些问题面前,传统的文学创作观和文学传播观正面临严峻的考验,稍稍显出了无所措手足的窘态。而以新传媒为载体的文学,则逐渐显示出了新的文学创作观、文学传播观和文学经营观的力量。
传统的文学创作观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追求传世的,新媒体文学不但手段便捷,最主要是心态自由放松,是即时的、即兴的、当下的,是在即时、即兴和无意中传世的。传统文学的创作和传播主体一般是分离的,传统作家由于对传播、营销的轻蔑和不屑,在现代文学市场中常常主动地处于被动地位。新媒体文学的创作和传播主体则是合一的,是同一个主体之下有意识操控的。这就显出了区别,也预设了效果。
文学环境有主、客观环境之分。当前客观的文学环境虽不能说一切顺遂,还是可以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这不是指自上而下的政策“恩赐”,而是指时代的发展进步、全民文化自觉的提升和社会文化氛围的改善所营造的大文化环境。其实主观的文学环境,即生命冲动和创作心态对创作的影响才更具决定意义。但主观的文学环境要自己涵育和营造。在同一客观文化环境下,不同作家的内心,可能是宽松开放的,也可能是拥堵闭塞的。我不主张作家过多将创作的成败归咎于环境。想想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和伏契克的《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是在什么环境下写的,这个问题会很清楚。
李东:莫言获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个获得该奖的中国籍作家,您如何看待这个奖?在颁发了百余年之后诺贝尔文学奖才首次“青睐”中国作家,您认为该奖“姗姗来迟”的原因何在?
肖云儒:诺奖是一个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奖,虽然我相信评委们会尽量以人类的、普世的坐标公正对待所有的作家作品,但评委自身文化坐标和阅读视野的局限终是避免不了。其中也不能完全排除政治偏见和意识形态偏见。中国作家得奖少、得奖迟,首先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东西方文化的互知和共鸣程度有关。也与我们在国际文化交流和文学交流中的严重入超有关,据说外国作品以中文出版发行的输入总量,成百倍地高于中文作品在国外的出版量。中国文学译介到世界很不够、中国作家宣传到国外很不够。此外,也还与我们中国文学长期被阻滞于时代话语与地域话语,大踏步、大面积进入生命话语、人类话语层面很不够有关。
在亚州,日本和印度的川端康成、大江三健郎和泰戈尔早得过诺奖,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作品确实具有世界一流水平,但也不能排除近代以来日本“脱亚入欧”、印度在殖民地时代传承下来的与英国乃至西方的亲密关系有关。
莫言的获奖当然也一样,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作品确实具有世界一流水平,也不排除他的祖国——中国这些年和平崛起的因素。当一个国家和民族高姿态、高水平进入世界话语场,无疑会增加它的文化和文学在世界话语场中的权重。
李东:您首创了西部文学这一新的文学概念,您认为文化以地域划分的意义何在?西部文学的核心是什么,与其他地域的文学有何区别?
肖云儒:西部文学这个文学概念,是我在中国西部生活了二十多年又有意识地作了四、五年田野调查和案头阅读、思考之后,于1986年提出来的,1988年前出版了这项研究的第一部专著《中国西部文学论》,以后又出了《对视文化西部》。也许因为是国内最早提出,又还言之成理的缘故,有了一些反响,获了中国图书奖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成果奖两项全国奖。
仅从字面看,西部文学似乎是一个地域文学概念,其实我的本意是想借助这个有地域性色彩的文学研究,来倡导一种普适性的精神内涵。我用专章论述了西部的阳刚之气、西部的野性、真性和多维性,西部的生命感、孤独感、悲剧感、文化杂交和心态杂音,西部的“前文化”自然景观和边缘化人文景观等等,所有这些,从深层文化质地上看,既是西部文学、西部文化、西部心理、西部气质上的特色,更是对一个被浓厚的传统文化、庙堂文化弱化了的民族,对一个被现代市场经济文化和新媒体文化严重遮蔽了真性野气的民族,深度的文化救赎和精神救赎。在中国历史上,每当中原在奢靡和安逸中开始萎顿,西部人便进入中原,以它强悍的野性震灭和振奋中华大地。这几乎是中国历史进程一种强弱相间的节奏,是另一种周期率,每隔几百年便会出现一次。
从这个意义上看,西部文学又不仅是地域文学,西部精神其实是中华精神的平衡仪、减压阀,是自古以来多次振奋过我们、今天和今后仍然会振奋我们的优秀的异质文化因子。所以我在那些著作和日后上百场关于西部的讲座中,重点讲的倒是西部与现代的迎合,这种深刻的迎合我整整列了十点。
李东:读书是丰富内心世界的重要途径之一。而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在追求物质生活的过程中,已无暇读书。您觉得当下,如何才能在追求物质的同时,丰富精神世界?
肖云儒:书籍是人类实践经验、知识积累和思考沉淀的科学化梳理和提升,文学作品是对人类内在和外在的世界的描绘,对形象、心象、情象和灵象的艺术再现。读书使人深刻,使人成熟。在一个娱乐化时代,浅表化和缩略化的文化严重挤压着读书与思考,令人万分忧虑却又无可奈何。须知读书从来是自觉自愿的事情,它源于一种内心追求,是无法强制的啊。
不过也要看到另一面,多元、快捷、即兴、即时的新传媒时代,也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和新的发展空间。空间就是机遇。它给写书、出书、发行书的人,给读书的人,以极大的革新提升的可能。我们的精神生产和图书出版正面临着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机遇。以书籍丰富精神世界的手段和途径正在拓宽,正在创新。
“形散神不散”适用于一切艺术
李东:您早在学生时代就提出“形散神不散”的散文创作观点,影响了几代人,而艺术门类是相通的,您的这个观点如何适用与其他艺术门类呢,比如书法、绘画,请具体谈谈。
肖云儒:形神说是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一直就有的。“形散神不散”不但适用于书画,也适应于一切艺术,甚至适用于我们的人生姿态和工作姿态。许多人要我将这五个字写成条幅挂在办公室或家里,他们是把这当作人生和工作的一个信条:心中有专注的目标和按步就班的安排,手脚却不忙乱。虽然“亚力山大”,还能保持散淡从容的态度。
书法,尤其是行草,特别讲究创作过程中的“散”,也就是即兴即时、随兴随意,让书家内心的情绪自如地流淌于笔端。行草当然特别需要厚实的功力,在笔墨、结体、节奏、提按、疏密、快慢、照应和相因相犯上有很多讲究,这些规律是要遵循的,要“不散”的。但应该功夫在书外、功夫在临池之前,一进入具体的书写过程,那“不散”只能通过“散”来表现,谋篇布局的经意只能在不经意中表现。那种形神都散的作品固然不好,乱了章法只能说明功力不到、笔力不逮。而那种形神都不散的作品也欠火候,因为作者还处在拘泥于技法的层面,远没有进入创作的自由境界。
中国画也很讲究“形散神不散”。中国画的散点透视就是一种“形散”,它不拘泥于透视视角之外的真实图像是否能够看到,却把画家想让你看到的都画出来,这种随心所欲就是“形散”。画家心里想告诉你的一定要告诉你,不论现实视角是否可能,这就是“神不散”。中国画和中国戏曲还讲究“离形得似”、“象外之旨”,笔墨重意趣(神凝)而轻形似(形散),戏曲的脸谱程式与表演程式都与实际生活相去甚远(形散),却能更突出的强调出人物的性格、气质和内心活动(形不散)。如此种种,我想恐怕都是一个道理。
李东:著名作家一旦进入书法领域,要比专业书法家更容易被大家熟知而获得市场认可。作为书法家,您如何看待文人书画?
肖云儒:中国书画自古以来就有所谓“院体”、“ 馆阁体”、“文人画”种种称谓,以此标识书画家不同的出身、素养和风格追求。这种分法原本就有些模糊,放到当代社会环境中来,就更显出了简单。现代书家人人都有多重社会角色和多重文化身份,心境、情绪和志趣各异,要固定在那一种称谓中其实是很难的。对“文人书画”恐怕也应作如是观。
现在提出来“文人书法”,我想那是给一些不以书法为专业而酷爱这一行、书艺又还算精到的文化人,或一些文化色彩很浓的名士,发一张进入书法界的入场券,外加一个“山寨职称”吧。“文人书法”含义极不确定,有时甚至恰好相反:“某某的字,那真是文人字!”“某某的字,不过是文人字!”褒贬何等不同。
如果“文人书法”是指书作的人生感、书卷气,即文化含量、比较浓厚,精神境界比较高,愿书界的朋友都能从匠气和术艺中破门而出,进入到“文人书法”大道的堂奥中来;如果“文人书法”只是进入书坛一张很廉价的门票,则文化界、文学界的朋友,首先是我自己,应该敬谢不敏。
追求自由的精神生命
李东:您少年成名,在文艺、社会、历史等多个领域都有自己建树,尤其是西部文化研究方面,可谓集大成者。张爱玲曾说“出名要趁早”,您对这一观点持怎样的态度?
肖云儒:听其自然。“名”不是自己想出就可以出的,不是自己争出来、喊出来的。“名”是自己有所作为,又得到社会认可的结果。所以我不敢苟同张爱玲这句话。你早慧,早有成就,出名早,固然好;你大器晚成不也很好吗?关键是努力和成果能不能到位。至于“出名要趁早”的这个“趁”字,我猜想张才女带有某种调侃,如果不是调侃,便有机巧过甚的嫌疑。
李东: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但您的评论涉猎到文学、哲学、书法、戏剧、民俗、社会现象等等,可见学识之渊博、精神世界之丰富。这种广泛涉猎、乐于钻研的动力是什么?
肖云儒:是对自由的精神生命的追求。是对新的思考领域、新的艺术感受领域、新的知识领域天然的、遏止不住的兴趣。也是我追求的幸福观。
我基本上不是一个执着的种花人,而是一个热衷于赏花的人,也可以说是一个艺术评论行道里的“玩家”。我不想用预设的目标绑架生命的走向,不想用格式化的行为框定人生的行程。正像我热爱旅行,想尽可能多地享用世间风景一样,我希望在短暂的生命中尽可能多的享用人类各种精神文化的美丽。在这种精神行旅中如若有所心得,写出来、说出来可以有益于社会,当然好,即便没有任何建树,只要体味、享用了精神行旅之美,我也很满足。其实那正是我的初衷。我的胃爱吃粗粮,脑袋却得用精粮供养。我希望学习、思考、对新事物永远的追索,成为我的人生过程。我看重过程,不看重最后的得分。
但我十分尊重那些设定一个目标之后,便精心策划、矢志不移为之奋斗终生的执着者,像季羡林、陈景润们。自知无能成为那样的杰出者,也便不去设定那样的目标。面对这些出了大力气、有了大作为的精神劳作者,常常会为自己溺于精神享受而惭愧;而每当躺在床上,扪心自问,又很感到几分自足自适。
李东:有人说现代人没有故乡。作为一名生在江西,长在西安的四川人,您如何理解故乡?
肖云儒:“现代人没有故乡”这话是有道理的。它指的是现代人的迁移和流动成为人生的常态,人们不再像农耕文化时代那样,过分将自己的人生胶着、依附于地缘和族缘之中。许多的人、每年以亿计的人正在离开土地、离开故乡,成为游子。故乡的观念正在淡化。但问题又有另一面,越是失去便越是恩念。乡愁已经成为所有飘泊者心中的流行病和慢性病,日积月累地啃噬着我们疲惫不堪的心灵。所以我想,“现代人没有故乡”后面一定要再加上一句话,“现代人无比思念故乡”。
但后一句话的“故乡”,内涵已多少有了变化,更多具有了精神故乡的念义,那思念也更多朝文化象征提升。四川广安是我地缘上的故乡,虽然没有在那里生活过,嘴里不吐川音,心里却挂念蜀地。一遇到和这块土地有关的信息,便会生出亲切的认同感,根的认同感。记得30年前第一次回广安我那个村,不认识一个人,却在每个人身上感到了自己的影子,便遽然明白了:我真是属于这块土地的。四川是我生命的远古传说。冥冥中带给我文化原型式的思念。
我在江西长大,江西在我心里拉开的是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长长的画卷。这长卷中有许多亲切而又生动的人和故事。清晰的老妈和模糊的老爸,亲友、师长、发小、同学……他们都和我伴行终生。江西是我生命的古代史。
生活了52年的陕西,是我的近代史、现代史。由学校进入社会之后,所有的酸甜苦辣,所有的喜怒哀乐,所有的爱恨情仇,所有的顺当的和坎坷的足迹,都印在这块土地上。我与这块土地血肉粘连,永远永远无法剥离开了。
故乡是我人生飘泊的一条长长的路。我的故乡在路上。
陕西文化博大精深
李东:您被誉为“西部文化大使和形象代表”,也被亲切地称为“陕西文化的吉祥物”,您喜欢这样的称呼吗?陕西文化的精髓在哪里?
肖云儒:要郑重声明的是,第一、这些称号都是好心的朋友,或好心的单位和传媒加于我的,我从未自称自诩过,也从未有过这样的奢望。我感谢各方面的善意和好心。第二、我压根儿配不上这些称号,虽然在这些方面作过努力,尽过一些绵薄之力。我是一个已经老到“古来稀”级别的老头儿,早已过了因称赞而沾沾自喜的年龄。每有人这样说,我通常的反应是,一、大声纠正。二、小声推迟:不敢,不敢这样说。三、不自在,夏天出汗,冬天发热。四、找个发言的机会当众自嘲几句,以给自己因过奖而负重的心减点压。切实的称赞会激发人的自豪自信,过誉常常让人尴尬。
陕西文化是要写多卷本的大部头著作才说得清、说得完的。要说精髓就更难了,需要高水平的提炼和表达能力。我用四个关键词八个字试说一下。
一、开放,这是思维结构层面。从炎黄时代到周秦汉唐,陕西文化自古以来呈开放结构,黄帝时代吸收和传播神农的农耕、仓颉的造字、蚩尤的冶炼,使之成为全民族的文明财富。汉唐的开放和广取博采就更不用说了。
二、创造,这是生命力层面。中华文明许多创造成果,其主体都是在陕西这块土地上完成的,如先秦时老子道文化的传播;秦代的郡县制;汉代独尊儒术,使儒家成为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唐代对佛教的全面融汇,使世界佛教中心由印度东移中华;宋代张载的关学,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与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结合起来,提倡学贵于有用的精神;一直到现代,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十三年和西安事变中的创造精神。
三、有为,这是实践力执行力层面。炎黄时代构建文明、秦皇汉武时代治理社会的执行力,秦的商鞅变法,汉的文景之治,唐的贞观之治等等创新改革中的实践力、执行力都彪炳于史册。
四、忠厚,这是道德和民风层面。早在两千多年前,西行不到秦的孔子就对陕西民风有过“秦地偏而民风正”的赞誉。陕人厚道、秦风淳朴,早已千秋公认,积淀为世人根深蒂固的印象。
李东:2012年,您参与主编了陕西省委宣传部等单位策划出版的《陕西精神》丛书,书中弘扬的“陕西精神”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它的形成基础是什么?
肖云儒:“陕西精神”主要是五句话:爱国守信,勤劳质朴,宽厚包容,尚德重礼,务实进取。这是省上通过各个渠道广泛征集、筛选、提炼出来的,文字稍感平了一点,却反映了陕西精神一些最主要的质地。——这也正是陕西人的表述方式。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精神不可能在短期内形成,它需要千百万人在千百年中长期而反复的实践,需要将点点滴滴的实践结晶为社会普泛的价值观,又需要这种价值观在自然的传播中能转化为更多人的认知定势和行为习惯,最终才逐步形成约定俗成的民风和社会风气。
李东:近年来,有多部陕西作家作品被搬上银幕,像大家熟知的《白鹿原》《高兴》等等。您如何看待文学作品和影视这两种传播方式?
肖云儒:文学作品和影视是两种文艺样式,它们必然各有自己的内在规律和特点,各有自己既区别又交叉的传播对象和传播方式。文学长度不受限制,更为全知全景,它需要经过文字符号引发图像联想。而在由作家的文字到读者心中的图像整个翻译过程中,有着巨大的联想、共鸣和思考空间,因而对读者的文化素质有一定的要求,语言的文学之美也极被关注。
影视受长度限制,受五行八作的观众构成的限制,篇幅和冲突都要求更集中、情节更具故事性,表达更加大众通俗,对娱乐性有相当的要求。它不看重剧本的文学之美,而看重画面、光影的构成和镜头运动之美。
这也许是电影《白鹿原》的改编不能尽如人意的原因。其实我很不同意有些评论说的,电影改编不尽如人意是因为尊重原著不够,恰恰相反,我以为是电影没有大幅度跳出原著造成的。现在基本上是在原著史诗性结构基础上,删掉一些线索和事件,但长篇小说宏大的结构框架并未大动,这是两个小时电影的无法承受之重。改编者似乎还没有找到一种只属于电影的结构,来对原著作根本性的改造。——这当然不是指改造原著的基本精神。
文学从来没有断过代,也不会断代
李东:“陕西作家是否存在断代”这一问题,曾引起文坛的震动和评论界激烈争论,当时您力挺陕西青年作家群。近十年过去了,回过头来再谈论这个问题,您觉得有哪些新变化?
肖云儒:这其实是个伪命题。自有文学以来,文学从来没有断过代,也不会断代。有人、有生命、有生活、有感情冲动,就会有文学冲动,也就会有文学行为和文学成果。争论的焦点其实不是“陕西作家是否存在断代”,而是“陕西青年作家是否不如上一代,是否接续不了上一代的辉煌”。
这就要看怎么看。传播手段多样了,文学观念多元了,读者要求多维了,要求我们有发散的思维、宏博的眼光、宽容多元的美学标准。我感到,从对文学生命本质的理解看,从发掘、拓展汉语文学表现的功力和潜力看,从文学通过各种新媒体在民众中大面积传播的深度和广度看,从作者队伍和作品数量看,当前陕西文学并没有出现断代的问题。至于似乎没有像上世纪60年代初或80年代中期那样出现两个位居全国前列的大作家群,我的看法是,一、当下这个莺飞草长的文学时代,尤其是新媒体写作时代,已经不见得是以大作家群为唯一标准来检验文学繁荣的时代。二、一个新作家群的出现,并不一定是以多少年为周期的,常常是以大时代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以及相应观念的大转型为周期,而且由社会转型到审美转型有时需要一个较长的沉淀过程。
我耽心的倒是,因了观念的过分陈旧或过分超前、过分精英,因了与青年作者、新媒体作者和他们的作品脱节的局限,文学评论自身目光的断代。
李东:时至今日,您已为400多人作过序,在媒体、高校举办讲座500余场,这些乐为他人做嫁衣、乐与他人分享劳动成果的举动初衷是什么?
肖云儒:为他人做嫁衣,其实也温暖了,美丽了自己。为上一代、同一代尤其是下一代写作者服务,共享各自的精神劳动成果,那种满足感和成就感更会加倍加倍地放大。
何况岁月使我在陕西文艺界成为年长者,生命本体渴望传承繁衍的规律,使我那么高兴与年青人相处,为年青人服务。躬身为下一代写作者作桥梁、作梯子、作台阶,就更有了一种长者的幸福。我每每陶醉于青年作者和莘莘学子听讲时的目光,我的生命在他们饥渴的、专注的、思考的目光中燃烧。这哪里是奉献,这是收获。
当然,这种感受并不是我搞评论的初衷,而是来自评论过程和结果的感受。
初衷其实是我在前面问题中回答的,是自我生命在无羁释放中的自如选择:“我的胃爱吃粗粮,我的脑袋得用精粮供养。”“我希望在短暂的生命中尽可能多的享用人类各种精神文化之花的美丽。我希望学习、思考、对新事物永远的追索,成为我的人生过程。我看重过程,不看重最后的得分。”
栏目的高度定位使访谈越来越难做了:一是一些名家不愿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文化成果;二是名家都很忙,即使答应接受访谈,也经常因为忙而一再延期。
联系上肖老师,他告知自己将外出讲学,半个月后返回西安才有时间,并询问是否来得及。作为提前几个月准备的访谈栏目内容,我说明了预定时间并发去提纲。
收到访谈内容时,差不多正好过去半个月,距我预定的时间早了足足一个月。肖云儒老师的态度让我感动。
饱受文化滋养,肖老师年过古稀依然精神矍铄。他说:“我希望在短暂的生命中尽可能多的享用人类各种精神文化之花的美丽。”我想,如果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并为之奋斗,那么人生肯定有别样的精彩。
愿肖老师及所有为文化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者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栏目责编 阎安 马慧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