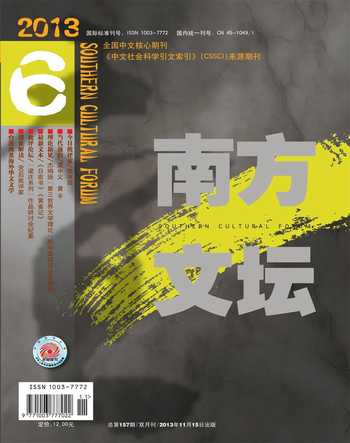记忆的抗议
2013-04-29南帆
这更像记忆,而非历史——韩少功的《日夜书》又一次驱使我考虑二者的差别。记忆显示了更多的个人风格,包括记忆的保存和剪辑;相对地说,历史的叙述遵循谨严的程序和逻辑,诸多段落依据某种内在的链条编织为一个有机整体。由于文学依附历史的悠久传统,“虚构”的特权并没有打消许多作家再现历史的雄心。保持史诗式的开阔视野,勾画完整的历史事件,故事情节大开大阖,人物命运与历史的运行此呼彼应——这是文学追随历史叙事的通常策略。《日夜书》放弃这些策略而更多地倾向于记忆形式。片断,纷杂零散,联想式的跳跃,突如其来的沉思,与理论假想敌辩论,这一切无不显示为记忆的表征。
尽管文学批评热衷于引用“历史”一词褒奖文学,但是,必须承认,文学擅长处理的是记忆。记忆卸下了宏大叙事而栖息于独异的个人风格。当然,《日夜书》回避历史的再现或许别有隐情——文学似乎陷入一个历史的不明地带。许多人心目中,20世纪下半叶的知青运动意义阙如,这个异质的段落无法与现今的历史叙事熨帖地相互衔接——即使对于作为当事人的知青:“他们一口咬定自己只有悔恨,一不留神却又偷偷自豪;或情不自禁地抖一抖自豪,稍加思索却又痛加悔恨。”无论是资深的革命功臣还是20世纪下半叶复出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前仆后继以及种种痛苦、反抗无不遗留下内涵明确的历史回音。现今的历史叙事清晰地认定了他们的是非功过。相形之下,知青运动的历史评价暧昧模糊。尽管《日夜书》之中的陶小布或者马涛终于脱胎换骨,跻身于不同类型的社会精英之列,但是,郭又军的命运显然是大多数知青的缩影。当学位证书、资本和权贵势力逐一瓜分了社会空间之后,众多的郭又军们成为一个尴尬的存在。他们的青春年华没有为后半生提供足够的生活积累。抛到社会的边缘,落落寡合,失业和病痛的折磨,这是多数知青的境遇。时至如今,历史叙事尚且不清楚如何妥善地安顿这一代人。
尽管查阅不到正式的文本,当年的舆论对于下乡插队的初衷存在两种倾向相异的表述:第一,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乡插队有助于驱除城市和学校灌输的资产阶级文化;第二,奔赴广阔天地,城市和学校输送的文化知识将在乡村赢得广泛的用武之地。虽然两种表述不无矛盾,但是,没有哪一种初衷真正获得了乡村生活的认可。《日夜书》之中的知青很快发现,从梁队长、吴天保、杨场长到众多采茶的农妇,多数农民并未表现出可供效仿的高尚道德情操。另一方面,知青拥有的文化知识以及种种时髦的政治兴趣——譬如,伟大领袖的“重上井冈山”意味着什么,或者,第三国际的教训在哪里——与乡村的环境格格不入。双重打击制造了莫大的失望,多数知青迅速丧失了最初的激情。“操一口外地腔的,步态富有弹性的,领口缀有小花边但一脸晒得最黑的,或脚穿白球鞋但身上棉袄最破的,肯定就是知青崽了。”遭受城市的抛弃,同时又不想混迹于鄙俗的农民——这种知青形象混杂了颓废、不甘和悲愤之情。当初,陶小布主动放弃驻守城市的机会下乡插队;数年之后,他不得不开始谋划装病返城。显然,生计的窘迫仅仅是次要原因,无所作为是知青的最大苦恼。
从世界观改造、乡村建设到就业问题的解决,下乡插队乏善可陈。这些大约是社会中止这一场运动的主要原因。有趣的是,文学首先从这一场运动的残烬之中察觉到某种余温。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末的“伤痕文学”通常将下乡插队叙述为可悲的境遇,那么,80年代的“知青文学”出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转向:土地和农民开始作为一种暖人的意象重返文学。当然,必须承认“知青文学”的全部复杂性。没有哪一个作家主张重启这一场社会运动,他们的文学怀念叙述的是某种隐秘的情感收获。“知青文学”不再将土地和农民设计为异己的对立因素,相反,作家开始设身处地地体察农民的疾苦,包括同情地接受农民的各种猥琐、小气、吝啬和粗鄙。显然,这种情感收获无法简明地转换为某种堂皇的口号;我宁可认为,这种情感收获的意义之一恰恰是——抵制各种华而不实的口号。
《日夜书》曾经描述了一批知青“栏杆拍遍”和“拔剑四顾”的英雄情怀:关注东南亚革命形势,考察北约和华约的隐患,充当格瓦拉与甘地的崇拜者,研究可能发生的街垒战斗,某些朋友已经打入革命委员会,另一些朋友正在进入新闻界和哲学界,某某部队看来很有希望,他们想象可以凭借一首《国际歌》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找到同志,彼此相见的时候行礼如仪:一个人举起右拳:“消灭法西斯!”另一些人举起右拳回应:“自由属于人民!”如果说,文化大革命点燃的政治激情主宰了知青的早期想象,那么,乡村生活的逐渐熟悉意味着衡量出这种政治激情与农民疾苦之间的距离。相对于黯淡的乡村景象,如此书生意气近乎笑料。没有口号的青春是乏味的,只有口号的青春是幼稚的。对于多数知青说来,历史无法提供二者之间的平衡。可以预料,炽烈的政治激情受挫之后,冰冷的虚无主义尾随而至。二者的共同形式是夸张。时过境迁,当知青出身的作家启用文学形式抚今追昔的时候,农民的质朴言辞以及田野之中的辛苦劳作构成了无声的反衬。现今看来,“知青文学”开始了一个转折:放弃“文艺腔”的人生姿态,正视农民形象隐含的饮食起居或者人情世故。作为生活内容的基本承担,这一切缓缓地从种种漂亮的辞藻背后浮现出来。
通常,文学是记忆的整理、挖掘、调集和补充。什么力量开启了记忆的闸门?许多场合,现状的不满往往隐秘地转换为回忆的动力。韩少功的《日夜书》显然是一个例证。“多少年后,大甲在我家落下手机,却把我家的电视遥控器揣走,使我相信人的性格几乎同指纹一样难以改变。当年我与他同居一室……”《日夜书》的第一句话已经确立了“不满”/“记忆”相互转换的内在结构。不过,相对于白马湖茶场的岁月,现在还有什么可抱怨的?物质如此丰盛,各种话语体系竞相粉墨登场,形形色色的人生志向正在展示无限的可能……尽管如此,叙述者陶小布——当然相当程度地代表了韩少功——仍然时常感到了不适。小说的后半部分愈来愈清晰地显示,作家的批判锋芒凝聚于当代文化的一个突出的表征:虚伪。《日夜书》之中冒出一个漫画式的人物陆学文。除了逢迎拍马,编织人事关系网络,此公几乎一无所长。然而,这种人物进入仕途左右逢源。作为他的上司兼对手,陶小布几度铩羽而归。当浮夸、恭维和利益交换成为普遍的文化生态之后,坦率和正直就会成为硌人的异类性格。
但是,《日夜书》所涉及的虚伪远远不限于职场或者客厅的口是心非,而是痛感人生舞台的许多表演与日常生活的中轴线相距太远。从浮夸的革命口号、义正辞严的民间思想家到年轻一代风格矫饰的颓废,不实之感始终如影随形地存在。何谓“日常生活的中轴线”?知青生活的历练肯定有助于认识的形成。很难证明那些革命口号或者乖戾的行为多么悖谬,然而,对于土地和农民来说,这一切无非是某种遥远的传说。现今,当房地产动态、金融精英、高科技前沿或者明星绯闻占据了大众传媒的大部分版面时,当代文化还能腾出多少兴趣眷顾那些仍然依赖土地解决温饱的农民?令人欣慰的是,此刻的知青记忆往往不合时宜地出动,某种程度地抵制时尚的覆盖。拥有知青记忆的人倾向于认为,干旱煎熬之后的丰收喜庆与一场足球赛获胜的激动眼泪不可同日而语;解决青黄不接时的饥肠辘辘与教授们国际学术会议上种种社会制度的争论不可同日而语。尽管最为时髦的那一部分当代文化无视如此“低级”的诉求,但是,知青记忆顽强地证明这些诉求的真实存在。
这个意义上,马涛的形象远比陆学文耐人寻味。经历了种种磨难和成功,马涛十分熟悉这个时代的文化秘密。他的自私之所以具有远为“高级”的形式,理论术语的娴熟包装产生了巨大的效用。从内地的监狱到美国的大学讲坛,“民间思想家”逐渐成为他的护身符和获益资本。叛逆者形象始终掩护着他抛弃女儿和母亲,并且巧妙地从感情上勒索妹妹、情人和周围的朋友。马涛自美国返回探亲,一方面声色俱厉地训斥周边的庸俗,另一方面心照不宣地慷慨消费中国官员——他理所当然地想象支付的是公款。郭又军无望地自缢于狭小的卫生间时,他正兴致勃勃地在太平洋彼岸与美国教授切磋理论问题。相对于马涛的各种头衔,郭又军的确微不足道。但是,《日夜书》的感情天平无疑倾向于后者。陶小布不仅始终感念郭又军的真诚,而且,他的琐碎、懦弱和没有出息逐渐凝定为难以忘怀的片断。相反,马涛逐渐在陶小布心目中丧失了魅力。所谓的“民间”业已沦为马涛自我塑造的一个徒有其表的修辞。陶小布清晰地察觉到马涛身上庸俗的市侩哲学,尽管他貌似远离郭又军这些庸众。陶小布之所以对各种理论表演存在精神抗体,知青的记忆功不可没。显而易见,他的思想再也不可能甩下土地、农民这些平凡无奇同时又分量庞大的生活景象而轻松地飞翔。
因此,可以明显地察觉到韩少功对于当代文化轻佻风格的厌恶。这种风格是虚伪的根源。然而,《日夜书》似乎没有花费多少精力追溯这种轻佻风格的来源。革命大口号的遗风?左派幼稚病的征兆?市场与生俱来的投机与哗众取宠?后现代过度的理论游戏不可遏制地繁殖出各种理论家本人也不相信的论点?韩少功并未企图解释,理论为什么甩下了日常景象而独自遨游。他始终葆有浓厚的理论兴趣。《日夜书》的某些片断直接介入了理论漩涡——例如,“泄点”与“醉点”力图与现今流行的性话语对话,还有生与死的独白。《日夜书》避开了韶华易逝、早生华发之类老调,直接谈论“生与死”。“你将回到父亲和母亲那里,回到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那里,回到已故的所有亲人那里,与他们团聚,不再分离。你是不是有一种归家的欢欣?”这是理性对于死亡的无畏逼视。的确,生亦何欢,死亦何惧?然而,某种程度上,这或许可以视为理论对于生命的僭越。上帝将死亡的恐惧植入动物的基因,这是生命自我保护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不惧死亡因而无视危害的物种大约业已湮灭多时。然而,现今的人类理性轻易地识破了上帝的伎俩——那些有识之士不再因为物种保存的责任而忍受死亡恐惧的折磨,犹如避孕技术盗出了性快感而卸下了生殖的重任。这种状况通常被视为理性精神对于肉体之躯的超越。然而,我想指出的是,这种超越同时开启了理论的自我繁殖逻辑。
多数理论发源于人们遭遇的问题或者困惑。电闪雷鸣之后为什么下雨?水温不断地升高为什么形成蒸汽?苹果为什么会从树枝上落下来?如此等等。但是,当理论拥有足够的积累之后,隐藏在概念与命题内部的思辨引擎开始启动。这时,诱发理论的初始动因逐渐退隐,支持理论持续飞翔的动力可能是智慧、学识、争辩的激情、学科逻辑、荣誉或者道德使命;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联系逐渐模糊,术语、公式、特殊的知识背景构成了愈来愈强烈的专业风格。或许很难简单地评估,这是理论的飞跃,还是理论的空转?可悲的是,土地和农民时常在这个阶段成为理论的累赘遭到抛弃。
作为理论的局外人,韩少功没有义务循规蹈矩地恪守理论的演变路线。《日夜书》仅仅在理论轨道上稍作滑行,人情世故的记忆就会及时地截断理论逻辑的延伸。企图在《日夜书》之中找到知青运动历史评价的读者可能很快被马楠与陶小布相爱的动人段落夺走视线。一对情侣如何涉过苦难远比枯燥的论断吸引人。相同的理由,《日夜书》不再复述当年的马涛提出何种惊世骇俗的观点,重要的是告密、跟踪、报警、出逃等种种惊险情节以及随之而来的情感周折。这再度表明,知青运动的理论遗产微不足道,真正存留的是那一片土地带来的情感成熟。不过,这种情感时常出其不意地遭受当代文化轻佻风格的嘲弄。贺亦民是《日夜书》之中一个特殊角色。作为一个街头窃贼出身的技术怪杰,一个敢恨敢骂的爱国主义者,他与陶小布相识于白马湖茶场,并且始终意气相投。然而,这种人最终只能被这个充满了外语单词、学位头衔、行政职务、名目繁多的奖金和各种管理条例的社会吞噬。“我久久说不出话来。我一次次面对他手机、座机、博客、微博、电子信箱里的缄默或空白说不出话来。”无语即是一种抗议——知青记忆酿成的抗议。当然,这时的记忆不再仅仅属于过去。
(南帆,福建省社科院院长、省文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