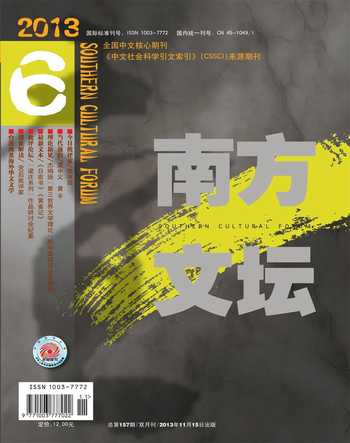思想在行走
2013-04-29魏继洲
行走在世界之上无疑有助于加快个体生命之对象化的进程,否则便无法解释为什么有如此之多的散文家,甚至伟大如蒙田、卢梭者竟然也热衷于以自然的步伐为写作纲领。每一个生命都是具有指向性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生活的世界才被赋予了意义,只不过有人积极主动,目的明确,有人消极被动,意识也有欠鲜明。如果说让生命绽放是天赋的权利,从生存到审美则是一种飞跃,而行走在世界之上不仅为写作者捕捉生命绽放的那些绚丽瞬间提供了足够繁复的视角,同时也使散文写作行为本身具备了个人气质。对于徐治平先生来说,是散文写作使他的生活变得具体而充实,在行走中思考,在思考中寻求个体生命与其对象化目标的不期而遇,在相遇中使生命与那个注定属于它的对象的因缘际会予以呈现。缘结缘散,自然而然,在徐先生营造的个人世界里,写作与生活的边界早已不再泾渭分明,所谓写作不过是关于生活的一种深度体验,或者简直可以说是“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形式,从而在把握我们与自然及其历史的关系的过程中获得更大的自由”①。
一
徐先生坚持散文创作已近半个世纪,与散文相伴的乃是近半个世纪不倦的行走,而行走的直接目的则是尽可能地抵近生活,观察与思考。徐先生的行走于生活之中,如果追溯也许要从遥远的1963年算起,那时候他还是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学子。《在金笋丛生的地方》是他正式踏上散文创作之路的一个标志。这篇散文创作于半个世纪前,但是今天读来仍然不乏扑面而来的清新之气。在一次颇具浪漫色彩的民间采风活动中,他走进云雾弥漫的大瑶山深处,引领读者体验圣堂山隐现在迷蒙云雾里的缥缈神秘,聆听关于圣堂山上的神奇传说,而更大的收获是则是引领读者亲眼目睹了盘瑶族人民群众如何与大山为伴,积极创造新的生活。金笋丛生于神山之上是传说更是预言,因为现实中的圣堂山已是一派生机盎然,当地群众质朴单纯,善待自然,他们因此而有资格享受更加美好的生活。从《在金笋丛生的地方》开始,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未曾离开过徐先生的创作视野,他把写作置于人与自然的接合处,有意无意地充当着弥合二者裂隙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一价值取向许多年来一直未曾变化过,在近作《西山寓言》中,他表达了希望人人都把自然生态视为神灵的心愿,他说:“假如人们像敬畏神佛一样敬畏森林,那将是怎样一种情景呢?”在广西巴马他惊叹于生命之美与自然之美的奇妙结合,人们之所以长寿原来和他们能够淡泊宁静,友善平和,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密切相关,也正是在这里他形成了关于生活真谛的抽象而又具体的概括:“只要活得踏实,活得自在,充分享受自然之趣、生命之乐,这就足够了。”(《叩问生命》)
而《核电站与白鹭村》是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思考的延续。从最初作为奴隶匍匐于自然脚下到作为主人向自然予夺予取,这种变化我们称之为进步。但是文明在削弱自然,所谓人类“进步如同一部只升不降的电梯,全自动、盲目向上的电梯,人们既不知如何走出去也不知它会停在哪里。”②人类演化发展的历史乃是一部创建并不断完善生命扩张的逻辑秩序的历史,唯其如此文明才不会演变成疯狂,遗憾的是现代文明如同被注射了摧毁一切的毒品,正越来越显出盲目和无序。面对人类膨胀无已的贪欲,进行某种理性的反思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却需要更为理性地追问科技与自然的关系:是站在自然主义的立场拒绝一切科技进步,严厉斥责科技进步对自然生态造成的破坏,还是以宽容的心态把现代科技纳入自然变迁的整体之中?当一些生态主义者是把二者截然对立起来之时,徐先生的思考显然有异。在广西防城港企沙半岛,核电站与白鹭村比邻而居,“一头是钢筋铁骨、雷霆万钧,一头是茂林修竹、银羽翩跹。一强一弱,一刚一柔,两者能否和谐相处,共享太平?”带着对切尔诺贝利安全事故的忧虑,他对核电站的建设者进行了深入采访。通过采访他得出了结论:核电建设与自然生态并不必然要成剑拔弩张之势,二者也完全有可能谱出一曲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妙颂歌。科技本身并不具有道德判断的能力,它最终造福或者贻害人间只是取决于具有价值取向的操纵科技的人。
徐先生是一个爱生活同时也对生活负责的人。爱与责任使他选择生活作为研究对象并长期执着于生活的逻辑的探寻,他对生活的思考则因为个体生命与社会生活的耦合而别具了一种思想魅力。认知生活是人生在世不可或缺的要义之一,问题是又有多少人愿意哪怕稍具理性地思考个人、世界,以及个人在世界之上的确切定位?生存之道其实早已寓含在自然自在的生活之中,自是不必劳神费力地去生活之外缘木求鱼,徐先生未曾拒绝平凡琐细的生活,而是热衷于日常生活的审美性体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要向生活庸俗的一面妥协,当人间生活的合理性存疑之时,他的选择是行走——沿着生命进化的来路上溯。许多年来,徐先生流连于祖国的山山水水,体验自然的脉动,感受人与自然的相生相依。他努力寻找着关于生活的自然书写,试图参照自然的脉动来验证生活的合法与否。自然赐予了人间生活并操控其变化的步调与节奏,正所谓道法自然,如果从这一意义上看,回到作为生命源头的自然之中探寻人间生活的真谛就显得十分有意义。徐先生沉潜于生活,同时又主张回归自然,其根本目的乃是回到生活的本源处为重建生活伦理寻找依据。
二
徐先生十分重视在传统中的行走。不管我们承认与否,日常生活不过是那些业已成为传统的经验累积的递相授受。所谓传统有广狭二义,狭义的传统意指人类征服自然的经验累积,而广义的传统却是自然孕育生命的漫长演化过程。徐先生沉潜于生活且视野开阔,他为合理的生活寻找依据,并因此而不惜遍寻古今中外。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对他是有影响的,从他的散文中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道家追慕自然,以人合天的印记,同时其中也不乏儒家的以天合人与佛家的宽容忍耐。他的散文创作中颇有一些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灵感的案例。在《圣种飘香》中,他深入广西横县南山,那里有被誉为“圣种”的白毛茶。对白毛茶的探访似乎是对一种精致生活的寻访,但是真正吸引他的却是当地茶农对于本土茶文化的守护——明代建文皇帝卓锡避难于南山时手植的茶树,俨然已成为一种久远历史的象征。《烧番塔》是关于郁江岸边南国民间风俗的叙事,这一次寻踪民间再现的是南国古代边民抗击侵略者的英雄传奇,广西钦州人刘二(即刘永福)抗击法国侵略者的故事已成为当地八月十五民间风俗的一项重要内容。《南方的太阳》是一篇追溯南方古代民族历史的力作。铜鼓是古骆越人的图腾,也是文章叙事的枢纽,它像天上的太阳照穿了历史的混沌洪荒与当下的村舍祠堂。徐先生跋涉于广西的崇山峻岭之间,寻找古骆越铜鼓文化的踪迹。在一面面铜鼓的器形、鼓面、腰饰之间,他仿佛看到了贵县罗泊湾的“翔鹭排阵”、西林普驮乡的“羽人舞蹈”、横县伏波滩的“龙舟竞渡”。徘徊在北流铜石岭上、宁明花山崖下,他仿佛看到了村村寨寨,稻菽飘香;左江面上,碧波荡漾;高山岭顶,朔风呼啸……透过这一幅幅古骆越民族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他仿佛感受到了南方古代民族创造的灿烂的生活。传统文化中蕴藏有民族大智慧,徐先生并不因传统文化的精粗杂陈而对它表示丝毫的轻视,他以足够的耐心对那些作为传统的遗迹细加分辨,并从中剔析出现实生活的依据。
但是,如果人类的进步不可避免,向狭义的传统告别就是一种必然,徐先生关心的问题是告别狭义的传统以后,前路又该如何去开辟。沿着狭义传统的指引上溯,他最终发现了自然——这个人类语言中含义极为复杂的语词所标示的那个奇异所在。《鹿鸣坳》引人进入了一个生态奇观:“茂密的草木丛中,似乎隐藏着一块块棕褐色的石头。咦,那石头怎么蠕动起来了?定睛细看,‘石头身上有许多白色斑点,有的还在扇动耳朵,甩动尾巴,有的忽地蹿出树丛,四处奔跑。”二十多年前的鹿鸣坳有儿时的伙伴阿欢,却没有鹿,如今阿欢已成为一个有家有业的壮年汉子,鹿鸣坳在他的经营下也变成了一个鹿的乐园。《虎踪》书写了一则温情自然的传奇:云开大山曾经是一个老虎出没的地方。有一年寒冬腊月,山民们聚集在禾堂上烤火,一只斑斓猛虎突然出现在禾堂边,有一农妇仓皇逃回家里,才发现慌乱中竟忘了把孩子抱回来。她“扒到窗口往外张望,只见那孩子还坐在火堆旁打瞌睡,大虫则蹲在孩子身边烤火取暖,两者相安无事。那孩子睡得正酣,身子一晃一晃,脑袋一倾一倾,眼看就要撞进火堆里了。就在孩子即将栽倒火堆的时刻,大虫就伸出前掌将孩子托住。如此数次反复,待那堆木柴炭火燃尽,大虫才悄然离去”。老虎作为百兽之王身上带着未驯的野性,但它们也不乏善良可爱的一面,而人类虽然时常彬彬有礼,有时候却比老虎更为凶残。因为人类的肆意猎捕,如今已经虎踪难觅了。虽然在动物园里还可以看到老虎的身影,但那如羊的温驯不能不让人感到失望。当人类亲手阉割了那曾经极度张扬的雄性之时,这个精彩的世界无论如何是已经变得残缺了。这不啻是人类对自身最大的嘲弄。
站在社会生活的边缘处遥望,徐先生看到了自然的巫魅无限及其生机勃勃。天道人道,原本一脉相承,他深信当自然向人类呈现其无限巫魅之时,却也为人类验证了人事的至理:和而不同,过犹不及。徐先生从未有过鄙视传统的表示,不仅不曾拒绝传统,怀着天人凑合的艺术梦想,他一直在努力进入那个作为生命之本源的广义的传统探究生活的逻辑。传统虽然有广狭二义之分,其实却异流而同源。《易传》有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③
三
徐先生说他的散文是悄悄飞逝的生活彩蝶、隆隆远去的时代沉雷的记录,同时又认为一篇好的散文应该是作家主体意识的坦诚流露。如果说情感是一条河流,那么散文则是漂流在他的情感之河上的几片艳红,几缕馨香。徐先生视写作为生命能量的一种释放,吟唱与行走,体验与融入,一向无拘无束,对他来说写作缘于对世界的感知,散文只是因世界之精彩而感动的产物。在他的散文中总是活跃着一个自我抒情主体,其突出特征是拒绝心灵封闭,拒绝无限放大一己的悲欢,这是一个能够理性看待个人与世界之关系的自我,一个向生活寻求灵感以荡涤内心的自我,一个向自然寻求出路来弥补现代文明之缺失的自我。就整体风格而言,他的散文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外感—内省型写作。具体地说,其基本架构受制于个体对外在世界的感应,其抒情倾向则和情绪与自然环境的协调程度一致。这种形式特征与他总是把散文置于人与自然的接合地带有关。
徐先生从不讳言散文写作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数十年间他走遍了广西乃至祖国的山山水水,近年又跨出国门走向世界各地,行走使他获得了写作的灵感,写作为他增加了生活的乐趣,事实上写作与生活的影响是双向的,正是二者的对立与统一使他的散文具有了深厚的根基。“世界的复魅不是对自然的崇拜,而是一种实践。其手段不在于解决我们现有生活形式的困顿,而是尝试新的方式,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④自然是胸怀博大而富有灵性的,对自然的尊重使他的散文获得了一种外向扩张型的思维方式,从他的散文基本结构模式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种外感与内省的互动。《面朝大海——北部湾生态笔记》以笔记体写广西北部湾的生物多样性,在这部散文集里北部湾生态的多姿多彩通过系列化的叙述对象,如金花茶、白面水鸡、膝柄木、中华白海豚、丁鸡郞、凤凰花、橄榄树等得以全景性呈现。系列化写作是近年来散文形式探索中出现的新现象,就《面朝大海北部湾生态笔记》而言,既可以把它看成多篇散文的汇集,也可以把整个系列作为一篇散文巨制——这并非毫无道理——其叙述的基本架构是作者观察点的迁移。金花茶、白面水鸡以及膝柄木等作为自然的存在物曾经逍遥自在地生存于自然王国里,当它们进入徐先生的视野,也就成了一种审美的存在,但是我们会发现在徐先生的散文叙事中,它们并没有被赋予太多主观化的色彩,它们仍然享有广阔的客观自为的空间,作者是主观的,却是退隐的,他并不把持叙事对象,为所欲为,对叙事的进展起维持作用的几乎是自然的片断在叙事中似断还连的呈现。不过就整个系列来看,这又是作者经过认真构思的有意为之。徐先生的散文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其突出特色在于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是有意识的,既不是主观裭夺客观,也不是客观淹没主观。
就整体风格而言,从徐先生的散文中透露出来的是一种乐观明朗。如果说他的散文凝聚着一种美,那么这种美所呈现的主色调却是积极向上,开阔豁达。散文之中不能没有作者的自我,正是这个自我“把生活的一个片断移植进了起突出强调作用的、被全体生活所衬托的境遇之中;这种选择、这种划界将其源自主体意志和认知的烙印打在了作品身上”⑤。只是这个自我的思想趣味、情感倾向却大有不同,徐先生热爱生活,并致力于理性地认知生活,当他选择了把一己的悲欢融入火热的生活,把个人的思考与迅速变迁的时代结合起来之时,已经意味着生活的多姿多彩将深刻地影响他的散文的抒情底色。在他对生活的冷静观察中,有赞美,也有批评,但他所做出的一切判断无不基于一种理解与宽容,是生活决定了他的散文抒情的基本价值取向。散文集《行走美国》是他2002年出访美国的最大收获。在抵近美国所做的观察中,他首先感受到的是梦幻般美丽的自然风光,在夏威夷瓦胡岛,“天是这么蓝,云是这么白,海是这么碧,沙是这么净,树是这么绿,花是这么艳,路是这么光洁,空气是这么清新”。这纯净的自然让人的身心也变得纯净透明。他也强烈地感受到了美国文化的独特魅力,“美丽与死寂,角逐与梦想,欢乐与恐怖,迟钝与乖巧,强壮与薄弱,富有与贫穷,聪明与愚钝交织在一起”,造就了纽约这座“梦中城市”。在珍珠港他参观了肃穆的太平洋公墓,透过纪念堂的墙壁上镌刻着的一千一百七十七名殉难者的姓名,他看到了美国为人类正义付出的代价,但是,在费城面对独立宫与自由钟他也联想到了马丁·路德·金著名的演说,联想到了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以及美军的虐囚丑闻,同时对美国人宣扬的普世价值观产生了质疑。倘佯在美国的土地上,徐先生时常对中美两个同样伟大的民族,两种同样灿烂的文化进行对比,他看到了我们与美国的巨大差距,也看到了美国文明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我们不必羡慕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不管美国和中国的月亮都是同一个月亮,都有阴晴圆缺。”他的散文之所以呈现出乐观明朗的色彩,是因为他曾经无限地接近过生活,并视与世界的因缘际会如同一则极富蕴含的寓言。
【注释】
①②④[法]莫斯科维奇:《还自然之魅:对生态运动的思考》,庄晨燕、邱寅晨译,87,26,15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③刘玉建:《周易正义导读》,122页,齐鲁书社2005年版。
⑤[匈]卢卡奇:《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吴立勇译,26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魏继洲,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