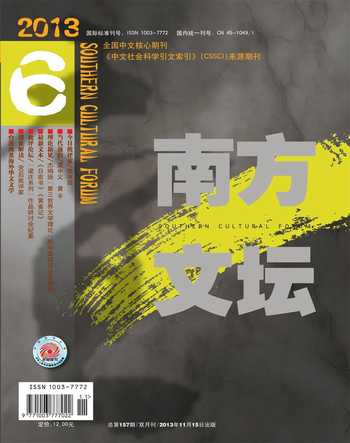台湾新世纪文学的“政治时间”与“文学时间”
2013-04-29古远清
网际革命数位革命眼球革命指尖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将台湾纳入世界文化的总体格局中。对于这一点,主张废弃中文用“台语”写作的本土派不愿也不敢正视。语言本是使文学成为文学的载体和逻辑底线。可因为台湾文学的语言应用问题带来意识形态、省籍矛盾、殖民文化等冲突,使“台湾文学”定义起来歧义百出。远未“定格”的“台湾新世纪文学”,也不可能例外。尽管它同属有争议的话题,但与20世纪台湾文学相比,毕竟出现了不少新质,如“新台湾写实”的诞生、“后遗民写作”、奇幻文学风潮、小说中出现的“后人类”情景、典范转移与作家全集出版、《台湾文艺》吹熄灯号、“反共文学”的终结、“同志文学”热潮降温、后殖民理论的式微、国民党迁台一甲子的历史记忆以及马华作家在台湾的论述。所有这些,促使“台湾新世纪文学”和20世纪台湾文学的不同在于期盼从文本到语言的激烈变革,期盼从形象塑造到文坛结构的重新洗牌,期盼用散文尤其是回忆录去取代小说的霸主地位,总之是期盼突破20世纪文学的规范和权力分配,期盼在创作上寻找与新时代相适应的表达方式。
台湾文学的一次重要转折
“台湾新世纪文学”首先是指“自然时间”或曰“物理时间”①。所谓“自然时间”,系从2000年到《台湾新世纪文学史》写作截稿时间2012年。它已由文学批评的新术语到向文学史概念转移,或者说这是一个在时间层面上有巨大能指的时代概念,其下限还可再延伸,这种策略性往往先验地决定了“台湾新世纪文学”的不确定性。本文使用它只不过是借“新世纪”在人类发展史上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间概念,在对台湾文学运动、思潮、现象、创作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就有关台湾当下文学的异质性与祖国大陆文学的同质性展开探讨,以勾勒出台湾文学十二年来发展的概貌。过去,台湾文坛流行“自由中国文学”“台湾乡土文学”概念,其能指只代表主流的三民主义文学或反主流的本土文学,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台湾文学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新世纪台湾文学”则试图去除因省籍情结而导致历史误置和意义歧见,在多方面的考察和沟通中完成不分省籍的台湾文学总体化,为“中华文学”在台湾的复兴提供理论支撑。
作为“自然时间”的“台湾新世纪文学”,尽管新旧杂陈,游移不定,但不管怎么样,它内含“政治时间”“文学时间”②。所谓“政治时间”,是指解除戒严以来尤其是20世纪末,台湾的政治体制、思想体制、文化体制发生了根本性转轨。组党自由、办报自由、骂“总统”自由,这回的台湾真成了五六十年代“自由中国”的回光返照。可在选举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台湾社会,这自由并非彻底的自由,仅说从选地方官到选“总统”,“办了几十年,到现在大量票源仍遭受国外势力、地方角头、黑道老大、庙宇神棍等等操控。”③其引人瞩目部分是陈水扁执政八年在文化上刮起“去中国化”之风,以及后来马英九所做的远不彻底的“去扁化”所掀起的阵阵波澜。2012年,因小说家黄春明主张用中国语写作而导致判刑两年(缓),“台湾新世纪文学”的政治色彩和文化价值才显得格外突出。所谓“文学时间”,是指在上世纪,文坛是以外省作家为主,发展到新世纪,本土作家已从边缘向中心过渡,三民主义作家包办文坛的传统结构模式,在本土思潮汹涌而来的情势下,发生了明显的裂变。当下,“台湾”的称谓普遍取代了“中国”,“中、台文学的关系,犹如英、美文学之间的关系”④的主张由微弱到增强,“台语文学”正在加足马力向蓝营文学刊物进军。网路文学的繁荣兴盛,则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文坛的权力组成,这使得文学的传播手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如九把刀的小说还有鲸向海的新诗,不但将网络文学铅字化,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正在改变着台湾的文学生态。此外,以短小轻薄、重视传播、文体出新为特征的励志文学或曰新形态通俗文学,如侯文咏、刘墉、几米(绘本)、吴淡如、吴若权的作品,“飞入寻常百姓家”流传甚广。尽管他们的作品因过于大众化而遭到坚守精英立场的评论者的酷评,不过这无法改变他们成为台湾文学一个主要支脉的事实。即使骆以军、郝誉翔、舞鹤等都市作家在他们的雅文学创作中,也或多或少渗有通俗文学的轻薄或创新的理念。正是在这种外来因素的诱导与内部求变的两种合力作用下,文坛的结构及时作了相应的调整。且不说以纯文学为主的大报副刊早就在向文化方面转型,就是纯文学杂志也注重大众文学的需求,更不敢小视网路文学的存在。
在台湾,极少有“台湾新世纪文学”的提法,而在大陆,“新世纪文学”成为各出版社出版系列丛书竞相打出的新旗号,还成为各媒体讨论的热门话题。“大陆新世纪文学”更不似“台湾新世纪文学”那样有复杂的政治文学内涵。如果说,20世纪光复后的台湾文坛最重要的事件是“自由中国文坛”的建立与崩盘,那“台湾新世纪文学”最重要的价值取向是“中国台湾文坛”几乎不见踪影,众多作家不再坚称或不愿称自己是中国人和中国作家。和90年代相比,台湾文坛上的“中国作家”少了,“台湾作家”多了;得奖作品多了,经得起时间筛选的名著少了;文学事件多了,作品的含金量少了;副刊的时尚味浓了,文学味却淡了。当然,“台湾新世纪文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和20世纪的台湾文学尤其是八九十年代的文学有一定的承继与联结关系。在20世纪,台湾文学的本土化论述在向“台独”论述过渡;到了新世纪,这一论述不仅成为本土作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也逐渐被外省作家所吸纳,所不同的是“台独”论述被改造为“独台”论述,即“台湾文学”是与大陆无关的具有独立性的“中华民国文学”,但也不是本土派眼中的潜在的“台湾(国)文学”。可见,“台湾新世纪文学”这一“文学时间”与“政治时间”有诸多地方在重叠和交合。
说到“台湾新世纪文学”与20世纪文学之间,其中有一个重要转折是“八年级”作家对《联合报》《中国时报》文学奖的漠视,对纸质出版物这条文学生产线的冷淡,文坛不再是精英人士的组合,尤其是“台语文学”的张扬、异化及随之而来的狭隘的台湾文学定位。“台语文学”本是方言文学,是台湾文学多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发展到新世纪,“台语文学”被某些本土学者升格膨胀为“正宗的台湾文学”,而用中文写作的作品则被称为“华语台湾文学”或曰“中华民国文学”。由此可见,“台湾新世纪文学”并非处于黄金纪元的黎明,而是近乎黑漆漆的铁器时代。不属启蒙世纪,而是停留在打造所谓“台湾共和国文学”的史前阶段。持这种主张的人陷入内心的荒蛮,中华文化、文明价值及国族认同在他们那里再次面临着生存危机。具体表现在陈映真所主张的“在台湾的中国文学”⑤已越来越少人赞同,像吕正惠那样自称“我是中国作家”的人打着灯笼也难找了。那些不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的作家,在心理上明显地存在着一种严重的自闭倾向。
显然,“台湾新世纪文学”正是处于这种本土化排斥中华文化的阴霾笼罩中。在《台湾文学正名》一书中,“台独”学者李勤岸认为“依照英语殖民世界的模型,母语文学应该正名为‘台湾文学,不只是被称做台语文学、客语文学和原住民文学。此外,目前所谓的台湾文学,指的是使用殖民者的华语写作的文学,是目前台湾文学的主流,应该改称‘中华台湾文学,也就像是在英语殖民世界是用英语写作的文学,是被称为盎格鲁爱尔兰文学,盎格鲁苏格兰文学,以及盎格威尔斯文学一样。”⑥这里把中国国民党称为“殖民者”,把成为主流用中文撰写的台湾文学改称为“中华台湾文学”,而企图让与“中华”无关的“台语文学”独霸台湾文坛。“台独”学者所启动的台湾文学等于“台语文学”这一概念,是“政治时间”的主干部分。
如何认识“台湾新世纪文学”这一概念在“文学时间”中的意义,比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讨论更复杂。作为大陆学者,更愿意把“台湾新世纪文学”中的“文学”看成关键词,而不是把可以大做政治文章的“台湾”作关键词。只有这样,才能探讨中国文学的重构与解构,全球化视野下台湾文学的本土立场究竟有哪些内涵,有关“二二八”的文学创作有无新变化,网络文学到底是精品还是垃圾,多媒体对作家尤其是诗人跨界产生哪种影响,《文讯》杂志的改制是否为“蓝营文坛”的另一种延续或补救,台湾文学馆馆长由绿换蓝后有无新的起色,还有如何将方言文学置于恰当的位置。对后一个问题,能否有另外一种选择方式,即“台语文学”只是台湾文学的一种,而不是把“台语”定位为与“汉语”或“国语”“北京话”对抗的一种词汇,应将其视为作者使用语言方式的一种自由选择,或将其看成发展着、运动着的过程。当作家用“台语”写得累、读者也看得很累时,自然会像宋泽莱那样放弃这种难于看懂、难与不同族群读者沟通的书写方式。这里,不妨读一读施俊州《Tshuē-tshù回家》⑦中的一段:
我驶 1 台铜 kóng-á 车,uì 西海岸 tōng 来 kàu 台 9 线 234 公里 ê 所在。头前 tò 身 kui 甲 ê 芋 á 园,ká-ná 无 siá leh 管顾 ê 款,pha-hng-pha-hng;正手 p ng 1 king 中油加油站,tng leh 放送 Tsóo Tse-l n 怪奇 ê 流行歌,我无停落来 pàng 尿、洗手面,继续驶进前。Uì-tsia 起,tō 有 khah s ng 人 leh tuà ê 地头方面—a……
面对大量的方言有音无字的情况,作者没有用20世纪许多作家的做法生造奇怪的新字。在这段文字中,汉字和拼音也不再各自为政,有合流的迹象,这体现了新世纪“台语”书写的新趋势。但就作者本想用汉语方言之一种的“台语”(多指闽南语)与其母体相割裂和对立,即用“台语”取代汉语,这种出发点并没有改变。吊诡的是,作者写这篇散文时,许多地方用的仍然是汉字即“中国语”。只不过这“中国语”经作者“台化”后,拗口得难于卒读。这种情况说明,“台语”不管是用同音字还是夹带注音,仍然是以汉字为基础,仍然脱离不了中国语言文字的轨道。
当然,在“台语文学”的书写、运动中,毕竟会不断出现质疑、肯定或否定的声音,这不同声音汇合了“文学时间”与“政治时间”的冲突,其中有学术层面,也有所谓“母语建国”的国族认同的层面;有来自本土的力量,也可能来自传统的写作习惯;有可能来自全球化的威逼,也有可能来自本土化的召唤。正是这种不同力量的角逐,构成了“台湾新世纪文学”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这一复杂性,不仅存在于历时性的叙述中,也体现在某种共时性的描述中,如国民党迁台六十年回忆录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⑧一类的文本里。继承自然是一种联络方式,挑战与颠覆同样也是一种另类关联。关联的纽带在于两种文学共处在“政治时间”或“文学时间”中。在时间的意义上,新世纪文学无疑是台湾文学的一次重要转折。现今台湾社会两大政党恶斗,政客们各怀鬼胎,谎话连篇,候选人捶胸顿足发毒誓。统独斗争如此严重,蓝绿对峙如此激烈,想走第三条道路的施明德被骂为“中国猪”而落泪。这种诚信时代的结束,使得骆以军们感叹:我们“都得生活在明目张胆的鬼脸之下”。面对这种局势,作家们无法清高:有的人不是随波逐流,就是奋起抗争,使文坛一片乱象丛生。
新世纪台湾流行一种消费文化,这种文化按照内在的逻辑和欲望需求,把政治的不可侵犯性与权威性毫不留情地粉碎,这表现在“台湾新世纪文学”与20世纪文学的不同之处是消费带有强烈政治性的文学事件然后将其娱乐化。像成功大学“叫兽”闹场踢馆不仅带有政治性,而且有很高的可看性与娱乐性,如蒋为文的大字报 “台湾作家不用台湾语文,却用中国语创作,可耻”用的竟是中国语,其中还有两个简化字。正如政客们议政时在“立法院”上演全武行把政治事件娱乐化一样,作家们也把蒋为文的抗议行为以搞笑方式出之,典型的有小说家张大春的新诗处女作《如果我骂蒋为文》:
如果我骂蒋为文是狗杂碎,
那么,我就既侮辱了狗,
也侮辱了杂碎,
也侮辱了狗杂碎;
所以,我不会这么骂。
如果我骂蒋为文是王八蛋,
那么,我就既侮辱了王八,
也侮辱了蛋,
也侮辱了王八蛋;
所以,我不会这么骂。
如果我骂蒋为文是龟日的,
那么,我就既侮辱了龟,
也侮辱了日,
也侮辱了龟日的;
所以,我不会这么骂。
──那么,我好像只能骂蒋为文:
你真是太蒋为文了呀!
游戏心态、解构台南法官判决的神圣性,是这首诗的文化内核。在表现技法上,作者对黄春明骂“逆子”的五字经进行戏拟、拼贴、改写,所追求的是文本的通俗性,这就是消费文化对政治文学事件所取的嘲弄态度,纯属“鬼脸时代”扮“鬼脸”的游戏作品。当然也有不扮“鬼脸”或抵御“鬼脸时代”的作品,如施叔青的“台湾三部曲”《行过路津》《风前尘埃》《三世人》,不同于“香港三部曲”以黄得云三代家族做划分,而改为以不同的统治政权做区隔,以便更好地表现台湾政权转移时所体现的断裂特征。洪范书店推出六册《陈映真小说集》,其中《归乡》《夜雾》《忠孝公园》,是陈氏停笔十多年后的新作。在这三部堪称红色文学精品的中篇里,陈映真持续发掘人的灵魂和书写被扭曲的意识,尤其是作品中所高扬的反“台独”的爱国主义精神,令人肃然起敬。这些作品,是时代的灵魂之镜,可惜这个时代的政客已越来越怕看到镜中自己的“鬼脸”真面目。这种“害怕”与“鬼脸时代”的来临,与台湾文学正在离中国文学越来越远,同时也与台湾文学向“台语文学”重叠的过程密不可分。
三分天下的台湾文坛
在以往,《联合报》《中国时报》的副刊几乎就是文坛的代名词。谁要当作家,就要在这两张大报的副刊上亮相或得奖,可现在两大报的文学奖不再是进入文化圈的身份证。当今奖项越来越多,仅新世纪设立的就有“总统”文化奖、宗教文学奖、世界华文文学奖、玉山文学奖、法律文学创作奖、海翁台语文学奖、彭邦桢诗奖、台文战线文学奖、温世仁武侠小说百万大赏征文、林荣三文学奖、台湾诗学散文诗奖、叶红女性诗奖、风起云涌青年文学奖、耕莘文学奖、台湾文学部落格奖、台湾诗学研究奖,等等。这种泛滥成灾的奖项,远不具权威性,但文学的出路毕竟在不断延长,传统进入文坛的模式又不断被解构,再加上政治势力与党派竞争的背后支撑,即在做什么工作都难免受到或明或暗的两党斗争影响的台湾,文坛不可能不受选战期间“鞭炮跟喇叭声”的干扰,再多“拜托”也无法脱离社会这个大环境,因而“政治时间”导致台湾新世纪文坛分化为两头小中间大的“统派文坛”“本土派华语文坛”“台语文坛”,或如郭枫所说的“蓝营主流文坛”“绿营文坛”和号称“超越党派”的第三势力:
台湾蓝绿阵营的文学工作,区块划分非常清楚。蓝营文学区块中心在台北,绿营文学区块中心在高雄,南北对峙,各自按照党的政治路线发展。
蓝营主流文坛的创作生态/蓝营承接五十年代以来国民党独占文坛的基础,站在既得利益位置,继续成为台湾主流文坛的掌控者。文学创作路线,继续走脱离现实的虚无路线:生活琐碎的记述、远方异域的描绘、内战历史的传写,等而下之追随美国时尚趣味,制造妖魔鬼怪、饮食男女、情色故事,文学等同货物围绕市场价值向下发展,决策者把畅销行情作为文学的高等标准。⑨
这里讲的文坛“南北对峙”,是客观存在,只不过这“蓝营主流文坛”是没有社址、没有编制但绝非子虚乌有的存在。“蓝营文坛”曾有过三次浮出水面:众多作家参与红衫军运动作诗为文倒扁,另两次不是倾巢出动也算得上是一窝蜂声援差点坐牢的血性作家杜十三、黄春明。至于该“营”的“文学时间”即艺术走向及其特征的概括,难免见仁见智。“脱离现实”或曰超现实、魔幻现实,其实是现实生活的一种特殊反映。像张大春的小说,作者叙述故事时比所有政治家都会“说谎”,都脱离现实,更不用说作者编造情节的能力。可这里的“说谎”,是对政客说谎的嘲弄与反叛,“脱离现实”是对现实的扭曲描绘而非照相式的记录。“远方异域的描绘”所走的也不完全是虚无路线,以骆以军长达四十五万言的小说《西夏旅馆》为例。这是一则台湾现代国民党的流亡寓言,作者选择西夏这个民族来与这段历史互相映照,共同建构这个流亡的寓言。具体说来,它构建的是一个异质时空:一位小伙子入住宾馆,与自称杀妻的图尼克相识,由此打开了通向西夏旅馆与长辈笔下不再存在的西夏王朝奥幻之门。这里有像动画与游戏般的战况实景,有缺少时间流向的事件叙述,还有奇特的人物与事件。这显然不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其诡异文字所建构的是一座文字迷宫。这正如《月球姓氏》无法去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它不过启示读者:人生所面临的问题,有些是无法解决的,我们可做的只不过是选择一种静默的方式,寂静地看着那些故事默默地发生与结束。至于“情色故事”,也不是不可以写,而在于如何写,像钟文音的台湾百年物语第一部《艳歌行》,以单身女性们在台北的欲海沉浮折射八九十年代的台湾社会,就不能把作品中的情色等同于下半身描写。
对“绿营文坛”,郭枫将其称为“南方文学集团”:
绿营各文学刊物,站在反抗者的位置上,最初艰困营运,到九十年代几家刊物、出版社联合发展成规模体系的上“南方文学集团”。文学创作路线,坚持本土意识为核心价值:主要工作在于本土文化的重构、前辈作品的整理、文学理论的建立、乡土抒情的书写等等。基本上团结性强具有革命色彩,书刊旨趣在宣扬以本土为主的理念,不大理会市场的销售量问题。自认是台湾文学的代表,其极端者倡言,“不用台语书写的文学,不是台湾文学”,主张的通或不通,也算是一种本土文学途径。⑩
“南方文学集团”中最重要的是“南部诠释集团” ——这一说法见诸游唤在静宜大学主办的一次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八十年代台湾文学论述之质変》11。游唤说的“南部”、郭枫说的“南方”和“台北文学”的“台北”一样,均非单纯的地理名词。如果说“台北文学”即“蓝营文坛”具有或浅或深的中国意识,那“南部文学”也就是“南方文学集团”更多的是强调台湾意识乃至“台独”意识。他们在党外政治运动的配合下,不断质疑解构陈映真所企图打造的“中国台湾文坛”:先是把“乡土文学”转换为“本土文学”,然后打着绿色旗帜强调台湾文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从而将“本土文学”改造为有特殊政治含义的即与中国文学切割的“台湾文学”。他们不像北部作家不敢公开承认南北文学的对峙,而是处处强调南台湾与北台湾在政治与价值观念的“南辕北辙”,用各人的不同方式向“台北即台湾”的这种政治和文化神话挑战。在“文学时间”也就是批评方法上,“南部”评论家颠覆了“北部”评论家的学院书写方式。
每年搞地方选举时,蓝绿阵营的恶斗在“立法院”照常上演,可外面的社会充斥着变数,如某些绿营文人看到自己原先寄予厚望的民进党既不民主也不进步时,立场就会逆转,像本来同情民进党的南方朔、杨照以及参加过中正纪念堂民主学运的知识分子,一个个改变了原来的信仰,可“南部诠释集团”似乎是铁板一块,也就是郭枫所说的“基本上团结性强”。但既然是“基本”,那就还有过不团结的时候,如浅绿与深绿观点和做法不同之争,有时发展为与人身攻击相差不远的批评。
“南方文学集团”在前辈作家全集的出版方面交出了极为可观的成绩单。他们的出版物不向市场低头,这点难能可贵,遗憾的是他们心目中的台湾作家,清一色是省籍人士,排他性异常突出。
如果说曾任“中华民国笔会会长”的余光中是潜在的“蓝营文坛”的精神盟主,去世前的叶石涛是松散的“南方文学集团”的灵魂人物,那郭枫就是文坛第三势力的主帅。他主办的《新地文学》季刊和《时代评论》,号称“超越党派背景,杜绝政商利益,站在全民立场为台湾社会整体进步发声”。既然不讨好官方,又不要财团支撑,这注定了它是一个弱势群体。为了改变“弱势”状况,《新地文学》广设社务委员,其中绿营人士有不少,以至蓝营怀疑其是绿色刊物,而绿营人士见委员中有大陆作家,其作品大陆来稿占了大头,因而又怀疑其是红色蓝色杂陈的刊物。其实,它是一个企图超越政党宰制的刊物。别看这一群作家居于边缘地位,可活动能力不可小视。这里真正起作用的是既骂国民党又拒绝“台独”的郭枫,另有先绿后蓝的詹澈、在蓝绿之间游走的应凤凰、不同于陈映真但同样坚信“台湾作家用中文写作最好”的陈若曦。“新地”还出版世界华文作家精选丛书,另举办过两次21世纪世界华文文学高峰会议。从第一次出版的丛书看,十二本书中有三位大陆作家,本地的没有一位是独派作家,可见编者所奉行的仍是中国意识路线。
具有顽强生命力的郭枫所领头的第三势力,以前不怕白色恐怖不向强权低头,现在发扬这种独立精神,拒绝加入任何派别,不追逐庸俗,不实行拜金主义,不把形式看得高于一切,这种特立独行的举动在不是玩选举游戏就是玩金钱游戏的宝岛,无疑属异端。可在第三势力很难立脚的台湾,他们要自外于党政集体力量的权力结构坚持自己的文学理想,谈何容易。像陈芳明的《台湾新文学史》出版后,郭枫对著者把史书当作周旋应酬的平台,以及不敢触及某些敏感史实有尖锐的不同意见,但不准备秉笔直书说它是偏颇的、片断的、虚伪的产品,而是用泛论且近乎恳求的方式说明《请给我们一部真实的台湾文学史》12。对大陆学者点名批评陈著蓝绿通吃的文章,该刊有可能是怕对方说自己联手“中共力量”干涉台湾文坛,也只好忍痛割爱。《新地文学》最近革新版面,准备增加评论篇幅,强调独立的文学评论“必须超越党派社团组织、超越师生关爱友谊、超越评论模式窠臼”13,这对把文艺批评不是变成党同伐异就是友情演出的不良风气无疑是一种拯救,可真正实行起来不亚于冒险,比如郭枫本人敢重炮猛轰余光中还有高行健14,在其新著《台湾当代新诗史论》中也敢向洛夫、张默等众多大牌诗人叫板,可该刊如果像王晓波主政的《海峡评论》那样去重炮猛轰“南方文学集团”某些头面人物数典忘祖的丑陋面目,就会让“政治时间”挤掉“文学时间”,从而失却一大批本土读者。正如郭枫自己所说:“这稀少的文学独立刊物主办者,一般要维持文坛和谐的人际关系,不愿轻易碰撞两大阵营的禁忌,取用文稿之际,掂量再三,无形中也是另类的设限。”15
新世纪的台湾文坛就这样由蓝绿外加杂色的三大板块组成。他们割地称雄,谁也不让谁不服谁,但这三者并非井水不犯河水,有时在媒介之间会出现互动的现象,如原为国民党文工会刊物、现改制后的《文讯》,尽管没有也不可能被“绿化”,但也刊用了一些绿营作家的稿件。而林佛儿主编的绿营刊物《盐分地带文学》,其刊名竟是深蓝人士陈奇禄所题。专出本土书的春晖出版社出版的多达五十八本的台湾诗人选集,也有少量的“蓝营作家”如余光中、向明、张默“混”了进来。这当然是“文学时间”战胜了“政治时间”,或者说是由于资源分配问题妥协的结果。
新世纪台湾文坛三分天下的情形,其原因不仅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文化的、文学的。是政治生态的险恶、意识形态争斗的剧烈、财阀霸道收买人心以及文人相轻相斗所造成,这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不过,要补充的是,台湾文坛并非只有三种势力,也有站在海峡那边《向建设中国的亿万同胞致敬》16的作家所代表的“红色文学”。这些文人加战士说到国家大事、民族前途时,真有精卫之坚韧、刑天之勇猛。但他们的口号和行为有时过于极端,某些作品又是政治理念的图解,再加上这些人是散兵游勇,没有自己固定的文学平台,脱离大众布不成阵,特别是有“战神”之称的陈映真生病后告别文坛多年,因而他们无法和上述三种势力角逐而形成四强分治的局面,但这不等于说不会对蓝绿文学构成威胁,如另一位可称之为超级“战神”的李敖以大胆怀疑的精神和反权威的姿态所发起的“屠龙”运动,猛批在蓝营做高官的龙应台,并出版有《李敖秘密谈话录·大江大海骗了你》17。
作为一位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者,我们所关心的不是“政治时间”即三大势力之外的陈映真们的红色文学能否壮大,或谁的势力大,谁对大陆作家开放的园地多,而是从“文学时间”出发看其能否真正超越蓝绿,产生的作品是否优秀,是否经得起时代的筛选。我们从隔岸观察,当代台湾作家的确是幸运的。尽管当前阴霾笼罩“文坛一片晦暗前途低迷”18,但台湾的美丽和富足,这是铁的事实。他们的最高领导人有远见,竟然主张政治为艺文服务,其创作自由和出版自由度均相当高,另一方面生活水平也不输于对岸。有创作才能的作家,只要摆脱国族认同问题的困境,把握住时代前进的方向,就一定能创作出无愧于新世纪这一伟大时代的作品。
【注释】
①②蔡翔:《一烟一纸》,156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
③⑨⑩1315郭枫:《两岸文学的自由创作与独立评论——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谈起》,载台北《新地文学》2012年12月,总第22期。
④林衡哲:《漫谈我对台湾文化与台湾文学的看法》,载《台湾文艺》1986年5月,第100期。
⑤陈映真:《陈映真文集·文论卷》,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
⑥蔡金安主编:《台湾文学正名》,26页,台南开朗杂志有限公司2006年版。
⑦《台湾文学艺术独立联盟电子报》2009年9月29日。
⑧台北天下远见出版公司2009年版。
11《台湾文学观察杂志》1992年第5期。
12台北《新地文学》2011年12月,总第18期。
14郭枫:《繁华一季,尽得风骚》,为1988年6月在台湾清华大学召开的当代文学国际会议上提交的论文。见郭枫:《美丽岛文学评论续集》,台北县文化局2003年版。
16为2012年12 月 26日去世的颜元叔所作。刊台北《海峡评论》1991年第2期。另见北京《中流》1991年第6期。
17台北李敖出版社2011年版。
18郭枫:《请给我们一部真实的台湾文学史》,载台北《新地文学》2011年12月,总第18期。
(古远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学院中文系教授。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世纪台湾文学史论”成果,项目编号:12BZW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