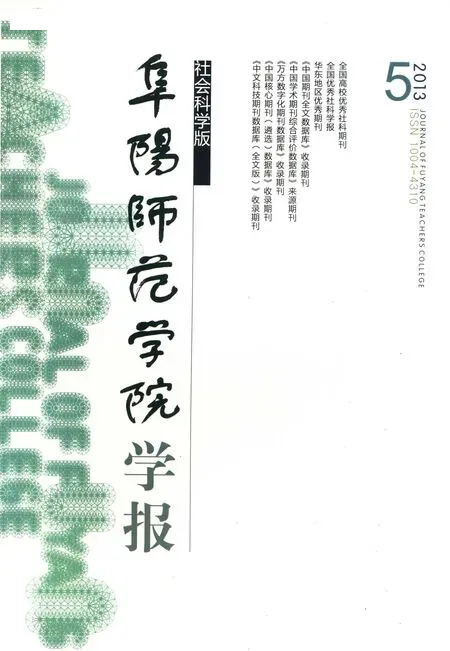近代会党忠君观论略——以洪门为例
2013-04-18雷冬文
雷冬文
(湛江师范学院法政学院,广东 湛江 524048)
忠君观是近代会党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综观近代一些有影响的会党举事,无论是以哥老会为领导与骨干的余栋臣起义所提出的“顺清灭洋”口号,还是唐才常率自立军起义提出的“勤王”口号,无不包含有鲜明的忠君观。虽然颇多的学者对近代会党的忠君观有所论述,但均语焉不详,由此导致目前对近代会党忠君观的认识还非常模糊,也因此使得对会党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中作用的认识存在严重分歧,所以有必要对近代会党的忠君观进行更深入的研究。那么,近代会党忠君观产生的社会根源何在呢?近代会党又是如何践行忠君观的呢?清政府对会党的忠君之举作何反应呢?与此同时,为何又有部分会党标榜“反清复明”呢?这些均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拟以近代洪门为例,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斧正。
一、近代会党忠君观产生的社会根源
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都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近代会党的忠君观也不例外。从社会软控制的角度看,近代会党忠君观的产生,与清廷刻意借助儒家思想来宣扬、推行忠君观有直接关系。
和历代封建王朝相比,清朝向官民灌输忠君思想的强度,为历史上少见,而其灌输忠君思想,又以大力宣扬儒家孝道观为首要,试图移孝作忠,来达到忠君之目的。早在清初,顺治帝即编辑了《孝经衍义》和《御注孝经》,并规定了每月两次的“六谕”宣讲制度。而康熙帝则颁布了以礼教思想为指导的十六条“圣谕”,并要求“每遇朔望两期,(州县)务须率同教官佐贰杂职各员,亲至公所,齐集兵民,谨将圣谕广训,逐条讲解”[1]8。雍正帝更是亲自撰写了以礼教思想为核心的《圣谕广训》,并通过行政系统和宗族体系在全国广泛散发、宣讲。乾嘉时期对孝道观的宣讲也是不遗余力[2]70-81。道光以降,由于民众起义频仍,封建忠孝观受到巨大冲击。为消除民众起义对忠君思想的消极影响,同治元年(1862年),清廷再次倡导宣讲《圣谕广训》,要求“城乡市镇,设立公所,宣讲《圣谕》,务使愚顽感化”[3]447。同治二年(1863年)清廷又一次颁谕“各省学臣,督饬教官,实力宣讲《圣谕》”,以期“经明行修,邪慝不作”[3]540。同治四年(1865年),清廷再一次指示“顺天府五城及各省督抚大吏,严饬所属地方官,选择乡约,于每月朔望,齐赴公所,敬将《圣谕广训》各条,剀切宣示……随时阐扬正教,认真开导,俾士民各端趋向,有所遵循。倘有地方州县及各学教官,虚应故事,奉行不力者,即由该管督抚、学政据实参处,以维风化而振愚蒙。”[3]114
除大力宣扬儒家孝道观外,清廷还竭力推崇程朱理学,究其根本,是因为程朱理学把三纲五常看成是天理良知,人之本性,尤其是在封建皇权受到民众起义严重威胁的情况下,程朱理学客观上有利于强化皇权主义观念。早在清前期,清廷便大量重刊《性理大全》,辑刊《朱子大全》,并由皇帝亲自组织编写理学著作,向全国推广。晚清亦是如此。咸丰年间,咸丰帝大肆召集儒家学者编撰程朱理学讲义,以期“父师以是为教,子弟以是为守,正道既明,群情不惑,一切诞妄之言,无从煽惑”[4]。而一大批儒臣则撰写了大量道德文章,四处宣讲程朱理学,志在“行仁义于天下,使万物各得其分……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乡党”[5]12。直至光绪年间,清廷仍在致力于宣讲程朱理学,希冀“使之家喻户晓,礼义廉耻,油然而生”,“使乡曲小民,群知三纲五常”[6]。
清政府向民间灌输忠君思想的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将关帝信仰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在我国民间社会,关羽被视为无所不能的万能之神,对其的信仰由来已久。最迟始于宋朝,封建政权即已介入对关羽的信仰,明末更是加封关羽以帝号。清王朝也极力将关帝信仰置于政府的掌控中,自顺治朝至咸丰朝,不断封赐关羽多种名号。咸丰四年(1854年),清政府又将对关帝的祀典提高到与孔子并列[7]130。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清政府还将关帝儒家化,使得民间社会对关帝的解释虽然多种多样,“但最为普遍的乃是赞扬他深明大义和忠于朝廷”[7]131。而近代会党也很信仰关帝,视关帝为榜样,其内部文件中有大量学习和颂扬关羽“忠君”精神的诗句,如“今晚新香会旧香,桃园结义刘关张。”[8]308“刘皇请我到华堂,关张义弟伴君皇。”[9]80“忠义堂前排阵势,今日桃园效关公。”[9]83在清廷主导了关帝信仰的情势下,很难说近代会党对关帝的信仰不会受到清廷的影响。
当然,清政府实施忠君教育的举措远不止上述,还有其他一些措施。譬如,为褒扬忠君行为,清政府特意设节义局、忠义局,修忠义录,专门委派人员采访忠义的官绅、士民、妇女,予以表彰;为战功突出、死事尤烈的官员、将领建立专祠;对一乡一邑绅民妇女死伤尤多者,允准建昭忠节孝祠,等等[10]。
总之,在清政府的刻意施为之下,清朝官民无不处在忠君思想影响之下,会党及其成员自然也不例外,忠君观在其思想意识中留下了深刻烙印。如广西会党著名首领张钊、田芳等向清政府投诚时称:“切思英雄遇合,有迟早之不同;官吏用心,有优劣之各异。故梁山三劫诏书,竟成栋梁;瓦岗累抗天兵,终为柱石。自古英雄,其义一也。”[11]960张钊、田芳等以投效朝廷的瓦岗英雄、梁山好汉自喻,忠君思想对近代会党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二、近代会党忠君观的践行及清廷的奖励
近代会党既然受到忠君观的影响,那么他们是如何践行忠君观的呢?总体而言,其对忠君观的践行,不仅仅体现于和平时期对清廷统治的服从,更可以从其协助清廷镇压民众起义的行为中窥探究竟。兹以咸同之际的两广地区洪门为例,略加阐释。
咸同之际,两广地区民众起义频发。尽管学界普遍认为洪门持“反清复明”之宗旨,但面对此起彼伏的民众起义,两广地区洪门在立场上却出现了严重分化,有的洪门组织积极发动或参加了反清起义,如广东有陈开、李文茂等率众举义,广西则有吴凌云、黄鼎凤等率部起事。但与此同时,也有不少洪门组织投身于清军,积极协助清军镇压民众起义。张嘉祥所部即是典型。张嘉祥曾率天地会起事于贵县,道光二十九(1849年)年,所部接受清军招抚,从此死心塌地为清廷效忠,成了镇压两广天地会起义的急先锋,先是助清军剿杀廉州天地会义军颜品瑶所部,“后又助剿颜品喜,异常出力”[12]111,张嘉祥本人亦因此深得清廷赞赏,认为其“投诚以来,效命行间,屡能杀贼立功”[13]315。同时,张还利用自己在天地会中的名头,招降了大量天地会的旧友与太平军为敌,并在与太平军作战时,“率锐卒为前锋,先登陷阵,以勇略著闻……转战数省,所向无敌,战功第一,由偏裨擢升提督帮办江南军务,为清中兴有数名将”。后张战死,“清廷震悼,优恤备至,并谥忠武”[12]111。像张嘉祥所部一样为清廷镇压民众起义出力甚巨的洪门组织不在少数,对此,史料多有记载,不胜枚举,在此略举一二。例如,冯子材本属于广东天地会刘八所部,咸丰元年(1851年),刘八进攻博白失败,冯子材遂率部众千余人投降清军,并被改编为“常胜”勇营,参加镇压粤桂边界的民众起义,后又到江南参与对太平军的作战,屡立战功。张钊、田芳等率部投降清廷后,成为广西清军水师的主力,在江口墟战场、东乡战场等处,积极配合清军围剿太平军,对洪秀全等在广西长期转战山区,实施单纯防御战略,起了一定的消极影响[14]。而当太平军与清军在桂林等地激战之际,两广地区上千名洪门会员主动加入了清军阵营,帮助清军对付太平军,以至于太平军愤然以洪门的“常识”对此举进行了严厉批评:“查尔们壮丁,多是三合会党。盍思洪门歃血,实为同心同力以灭清,未闻结义拜盟而反北面于仇敌者也!”[15]167
由上述我们不难看出,两广地区不少洪门组织在帮助清廷镇压民众起义时,其忠君行为是坚定不移的,此行为绝不能仅仅以“贪生”、“求利”等原因来进行解释,否则我们很难理解张嘉祥、冯子材等人为清廷效力即便献出生命亦在所不惜的举动。对此,著名天地会首领刘永福的临终遗言也有深刻反映,其遗言曰:“予起迹田间,出治军旅,一生惟以忠君爱国为本,无论事越事清,皆本此赤心,以图报称,故临阵不畏死,居官不要钱……只知捍卫社稷”。[16]271
那么,清廷对会党忠君的行为又有何反应呢?其实,清廷并非建政伊始就注意到了会党也有忠君的一面。尽管最迟从康熙时期始,清廷就对会党问题予以了高度关注,但对会党基本上采取的是严厉镇压措施。直至道光以降,清廷始对会党政策有了重大调整,不再一味的镇压,而是剿抚结合,适当吸收一些会党为朝廷效忠,并注意对那些投诚的会党分子进行表彰奖励,以鼓舞其更加积极为朝廷效力。咸丰元年(1851年)三月,咸丰帝曾特意指示钦差大臣李星沅等,要密切关注那些投诚会党分子的表现,如果其“归诚效力,确有明征。既能杀贼立功,即不妨宽其既往,励其将来”[13]第一册,392,并“均著随时奏闻”[13]第一册,352。据此,清廷对立有战功的会党分子均及时予以奖励。仅在咸丰元年(1851年),清廷就多次下令奖赏立有战功的投诚会党分子。该年四月,张钊与头目九人,因带领七百水勇阻击太平军有功,清廷特颁旨“赏给张钊六品顶戴,并赏戴蓝翎”,并表示“此后若更能戮力效命,不难续加优赏”[13]第一册,392。同月,因“张国梁(即张嘉祥)、谢锡祥于悔罪投诚之后”,“能随同官弁杀贼立功”,所以清廷下令“张国梁著以千总补用,并赏戴蓝翎。谢锡祥著赏给六品顶戴”[13]420。时隔三月,又因镇压天地会颜品瑶部有功,张嘉祥被“准以千总即补。投诚宁正冈,准给军功六品顶戴,俟续有功绩,再行擢用,以示鼓励”[13]154。八月,赛尚阿等又上奏清廷,认为张嘉祥“既能择人用间于前,复能协力出奇于后,应请即以守备升用,先换顶戴,并换花翎。壮勇张鸿才出奇用间,歼戮渠魁,实其一人之才(力)。该壮勇本系投诚之宁正冈头目,拨给张国梁管带,张鸿才、宁正冈应请旨以把总补用,张鸿才并请赏带蓝翎,以示鼓励”[13]315。
同光时期,清廷仍注意奖励那些为朝廷立下战功的会党分子。如天京陷落后,冯子材被赏穿黄马褂,封骑都尉世职。原为广西天地会堂主张高友部下的苏元春于同治二年(1863年)投靠清廷后,因镇压苗民起义有功,被授广西提督之职,光绪年间又因抗法有功,晋封为二等轻车都尉,及额尔德蒙巴鲁勇号,赏加太子少保衔。原为三合会首领的陆荣廷在接受朝廷招抚后,在镇压会党起义和革命党起义时屡立战功,后官至广西提督,并被被赏给捷勇巴图鲁称号。
清廷这种对效忠朝廷的会党分子不断奖励的举措,意义非凡,不但能强化那些已经投靠朝廷的会党分子的忠君观,而且还能吸引那些尚未投靠而又急于摆脱不利社会处境的会党分子效忠朝廷,如在广西贵县,“自嘉祥听招抚,大井头惯匪王亚壮、王兴福、王升高等,遂袭其故智,挟制富户铺商,敛银守街,暗窜巨匪卢亚相,统率贼船二十余只湾泊县前,派单开角,并声言打至招安方肯了事”[17]6。
三、近代会党何以会“反清复明”
提及近代会党的忠君观,就不能不言及近代部分会党所具有的一种特殊的忠君观,即“反清复明”的忠君观,其中以洪门最为典型。这一忠君观,与占主导地位的忠君观刚好相反,属于社会反文化的范畴。学术界虽对“反清复明”的忠君观予以了关注,但一直未能阐释某些会党组织何以会“反清复明”。我们认为,该问题可以从多个视角进行研究,如从政治学角度看,与太平天国的榜样效应不无关系;而从社会学角度看,又与近代会党缺乏全国性的统一领导机构因而各地会党的价值取向各异有关。本文拟从儒家文化的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认为该问题的产生与以下两个因素密切相关。
首先,近代会党“反清复明”,至少部分符合先秦儒家的忠君理论,因而能使“反清复明”获得理论上的合法性。对于如何忠君,先秦儒家和汉唐以后的儒家是有区别的,汉唐以后儒家的忠君观强调的是对君主的盲从、绝对服从,而先秦儒家则并非如此。孔子虽然把忠君视为道德价值判断中最为核心的观念之一,并使之成为“君子”修德的主要内容[18],但并不盲目忠君,而是明确摈弃了“事君不二”、“从一而终”的迂腐观念,要求“以道事君”(《论语·先进》。而对如何处理忠君问题,孟子又比孔子大大前进一步,认为:“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如果“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孟子·尽心下》),即对于有过错和危及国家的君主,可以免除其职位,或剥夺其世袭权力[19]。先秦儒家关于忠君的上述理论,成为近代会党“反清复明”的重要理论依据。以洪门为例。洪门《会簿》杜撰了一个关于天地会创立缘由的所谓“西鲁故事”,故事记载,少林寺僧曾帮助康熙皇帝打退“西鲁人”入侵而未受朝廷的封赏。回少林寺后,这些僧人遭到奸臣陷害,但康熙不辨忠奸,致使少林寺院被焚,寺中和尚大多惨死,最后只剩下五人,这五人后来共扶朱洪竹为主,创立了天地会。西鲁故事告诉我们,洪门创始人最初是拥护清朝的,后来之所以从拥护清朝转为“反清复明”,就是因为清朝皇帝的无道。对此,洪门《海底》有副对联曾言:“僧家初起豪强忠勇勤王报国驱西鲁,后继杰士恨氵月(清)无义顺天行道转汩(明)朝。”[10]136按照先秦儒家的观点,康熙杀害有功的少林众僧,显然属于无道之举,有悖于“君臣有义”(《孟子·滕文公上》)之原则,因此少林僧众可以不忌皇帝权威,反对康熙的错误行为。很显然,洪门编造出“西鲁故事”,就是为了给清朝皇帝贴上“无道”、“无义”的标签,从而为自己反君主行为提供一个符合儒家文化的、可以为世人所接受的理由,表明洪门会员并非反对“忠君”观念,而仅仅是反对无道的清朝昏君、拥戴开明的明朝皇帝而已。
其次,近代会党“反清复明”,与“华夷之辨”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华夷之辨”是儒家正统观念中两千余年来一脉相承的思想,有清一代仍复如此。早在清初,王夫之即认为:“天下之大防:华夏夷狄也,君子小人也。”提出华夏夷狄之防,乃“古今之通义”,要求“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道义”[20]502。顾炎武也曾明确指出:“君臣之分所关在一身,夷夏之防者所在天下……夫君臣之分,犹不敌夷夏之防”[21]412。尽管清廷一直试图消除“华夷”观念,但直至晚清,“国人种族观念之郁积”仍相当浓厚[22]146,以至接触了西方先进思想的革命党人都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如浙江革命党人就认为满族“为游牧曼殊之族,暗地乘我朝内乱之时篡了位”,因此要“誓死以逐此丑虏”。并认为“内地的人不分清宗族,一味拍胡人马屁,自命为忠君爱国,叫什么保皇党,专以奉仇为文残害同种的。”还认为“真革命党,惟以报祖宗的仇,光复祖宗的土地,为自己汉人造幸福,不求虚名誉,不惧生死,不畏艰难,必要取回所失的土地为目的,不愿为他族之奴隶,此方为真革命家也。”[23]18-19徐锡麟被捕后也供称:“我本革命党大首领,捐道员到安庆,专为排满而来……我只拿定革命宗旨,一但乘时而起,杀尽满人,自然汉人强盛”。[24]11邹容在《革命军》中则声称要“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25]333,而孙中山在创立兴中会时,也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主张。
革命党尚且如此,会党就更不用说了,“华夷之辨”对近代会党也有着较大影响,此点我们可以从会党的内部文件看出来。如洪门诗歌中就有不少充满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诗句,譬如“把守二门郑其由,招集英雄灭满洲。二门把守招豪杰,大明早复报冤仇。”[10]76“龙泉初出灭情儿,杀尽胡人数万家。”[10]150“清龙无水清龙绝,调转乾坤扶明龙”[9]360,等等。非但如此,洪门举事也带有鲜明的狭隘民族主义精神。如咸丰六年(1956年),吴凌云率众攻破新宁州城后发布安民告示称:“我父老兄弟,遭满奴之蹂躏久矣!严刑苛税,鸡犬无宁日。凌云目不忍睹吾父老兄弟之倒悬,因是联合各异姓兄弟,同举义旗,专讨满奴,以复汉室。”[26]光绪三十二年(1902年),萍浏酸起义爆发,以姜守旦为首的洪福会所发布的《新中国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布告天下檄文》通篇都是种族复仇之辞,号召汉人排满,并引用明太祖北伐声讨元的檄文:“为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陷于夷狄。”甚至声称,只要汉族人做皇帝,不论是谁,都“悃忱爱戴”[27]。而当时的革命党人对会党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是持肯定态度的,蔡锷即认为:“为宗国沦亡,异族专制,不敢显然反抗,故苦心志士组织一种秘密的社会,抵抗恶政府,其用意很好。”[28]481孙中山也认为:“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29]233并说:“鄙人往年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30]70所以“革命与洪门,志同道合,声应气求,合力举义,责有应尽,非同利用”[31]237。孙、蔡等人的言论表明,会党“反清复明”的思想在当时得到了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的认可与支持,而这种认可与支持反过来会更加强化会党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
不过,近代会党所具有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本质上仍属于特殊的忠君思想,即拥护汉族王朝而反对少数民族王朝。
总之,不管近代会党是效忠清廷,还是为“反清复明”而奋斗,都受到了儒家忠君观的影响。忠君观对近代会党的深刻影响表明,近代会党的思想意识仍未能脱离封建主义的窠臼,因而不可能成为革命的主要依靠对象,诚如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总结经验教训时所言:“彼众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借全无,只能望之为响应,而不能用为原动力也。”[32]197
[1]田文镜.钦颁州县事宜[G],许乃酱.宦海指南五种[M].荣录堂重刻本,光绪十二年.8.
[2]常建华.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70-81.
[3]清穆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圣学[G].清文宗圣训:卷6[M].
[5]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1.12.
[6]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G].处分例·禁止邪教.卷132.
[7]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130-131.
[8]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M].长沙:岳麓书社,1986.
[9]李子峰.海底[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0.
[10]张艳.略论咸同时期清政府的道德教化政策[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7,(2).
[11]陆宝千.论晚清两广的天地会政权[M].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33),台北,1964.96.
[12]邕宁县志[M].民国26年刊本.
[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二册[M].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
[14]方之光,崔之.张钊等叛降与金田起义史事考释[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2,(4).
[15]中国史学会.太平天国:第一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6]李健儿.刘永福传[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
[17]贵县志[M].光绪20年刊本.
[18]曾广开.先秦儒家忠君思想的形成与解读[J].中国文化研究,2009,(4).
[19]王国良.从忠君到天下为公——儒家君臣关系论的演变[J].孔子研究,2000,(5).
[20]王船山.船山全书:第十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8.
[21]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全校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3]王征.光绪三十三年浙江办理秋瑾案档案[G].历史档案,2011,(4).
[24]郭美兰.光绪三十三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档案[G].历史档案,2011,(4).
[25]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一册[G].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26]韩水.吴凌云[J].莫乃群.广西历史人物传6[M].广西地方史志研究组编印,1985.
[27]张绪穗.萍浏酸起义中的两道檄文[J].历史教学,1988,(12).
[28]曾业英.蔡锷集(一)[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板社,2008.
[29]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六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0]过庭.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N].民报第1 号,1905,(11).
[31]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2]孙中山.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