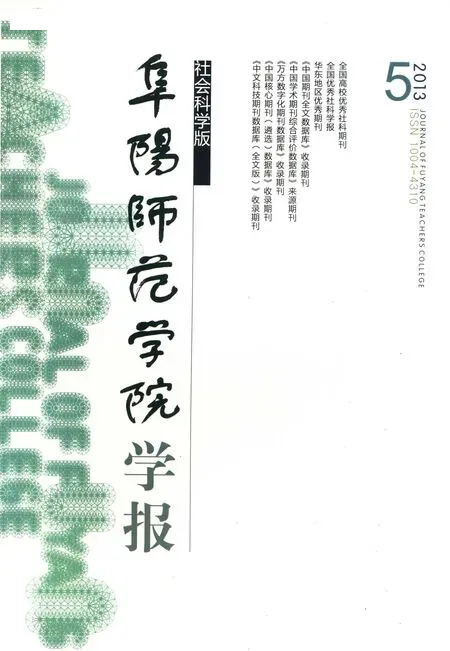学林人瑞粲若花——苏雪林与冰心、谢冰莹关系研究
2013-04-18李灵
李 灵
(四川大学,四川 成都 610065)
20 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有三大著名女寿星:大陆的谢冰心(1900—1999),台湾的苏雪林(1897—1999),旅美的谢冰莹(1906—2000)。三人融东方才女气质与自我体认精神于一体,或婉约典雅,或轻灵隽永,或豪情晓畅,成为新文学一道永不磨灭的绚丽风景。苏雪林与冰心、谢冰莹既是文友,更存真挚友谊。苏雪林认为冰心是“中国新诗界,最早有天分的诗人”[1]76,又夸赞冰心的作品含有“永久的兴味”[1]354。而冰心也在1987年3 月7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入世才人粲若花》里写道:“五四时代,我们的前辈有袁昌英和陈衡哲先生,与我们同时的有黄庐隐、苏雪林和冯沅君。”[2]对苏雪林持肯定态度。苏称许谢冰莹“文笔简洁流利,热情动人”[1]252谢冰莹更是欣赏苏雪林生性“慷慨、豪爽、急公好义、乐于助人。”[3]45“她的写作天才是多方面的,小说、散文、诗歌、神话、文学理论、训诂考据,样样都好。”[3]47她们相互认同,诚心以待,成为现代文坛一段令人回味的友谊佳话。本文通过探讨苏雪林与冰心、谢冰莹的关系,追踪三人亲密友谊的成因,挖掘潜藏于她们性格中的内在真实,剖析其作文上的一些深层理据。
一、相识与友谊
众所周知,冰心成名于上世纪20年代,且文名长盛不衰。自1919年8 月25 日在北京《晨报》公开发表第一篇文章《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又接连发表小说《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超人》,诗集《繁星》、《春水》等,当年20 岁出头的冰心,已经名满中国文坛。三人中,苏雪林与冰心最先相识,1919年就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的苏雪林经常在《晨报》上读到冰心《繁星》和《春水》的小诗,被冰心清新流利,造法自然,而又蕴含深邃哲理的风采所折服。“我既景仰冰心,很想去拜访她,请教请教做新诗的方法,只是自己秉性十分羞怯,竟未敢实行。”[4]但由衷地喜欢终于付诸行动,1928-1929年间苏雪林住在上海,冰心有一次因事去沪,住在当时最豪华的亚东大饭店里。苏雪林闻知后,也不由人介绍,独自赴饭店拜谒。这是苏雪林第一次见到倾心已久的名作家。冰心回北京后,苏雪林还写了几封长信给她,并“劝冰心易母爱为民族大爱,多作长篇史诗,宣扬历史上民族英雄可歌可泣的故事;用以激扬国人的爱国精神。”[4]不知何故,冰心并未回复。一向自尊的苏雪林也未因此怪罪冰心,反而责怪自己鲁莽并感到愧疚。抗战末期,冰心为《中国妇女月刊》总编辑。冰心为着催促苏雪林之稿,曾亲笔写了封短简给苏。苏雪林非常珍视,原想好好保存,但因屡次迁移而散佚。1949年2 月29 日苏雪林从武汉坐船到上海,又经由香港赴巴黎,最后落脚台湾,两位老人至此四十年不通音讯。直到1989年10 月5 日苏雪林发表在《台湾新生报》的《我与冰心》时,才有互通鱼雁的记载:“今借两岸交流的机会,与她稍通音讯,居然获得她的回馈,心里未免高兴。”[4]1990年7 月4 日苏雪林的日记中记载台湾著名民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秦贤次来台南看望自己,“并云八月间将赴大陆,我以为他去探亲,他说自己是台湾人,大陆无亲可探,去是买书、拜谒老作家,如冰心、巴金、吴祖光、萧乾等,余加施蛰存一名,云是熟人,又说萧乾、冰心皆熟人,请代问好,秦叫我带给冰心一点礼物,余赠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精装者一册,又遯斋随笔一册,赠秦遯书一本、文选一册。”[5]当时,苏雪林代请秦贤次告达冰心,在自己《二三十年代的作家与作品》中对冰心共有三章介绍,即冰心的诗、散文、小说各为一章。别的作家仅二章或一章,可见重视。“秦君不久就回来了,说见到冰心,并与她同拍彩照,又带回冰心赠我书两册,一册是《冰心文集》,厚而且大,约有六百数十页,一册名《冰心读本》,好像是给小朋友看的,则薄而且小。两书冰心都亲笔题了上下款,并盖了章。上款是‘雪林吾姊正’,下款是‘冰心’二字。笔致挺秀,十分可爱。”[4]苏雪林得冰心赠书后,非常珍贵,每有客到,必搬出炫耀一番。因为大陆台湾的简繁不一,苏雪林对简体字不很了解,但是为了读通冰心简体横排的两书她特意买了字典,情谊毕现。在苏雪林与冰心晚年数次通信中,苏雪林劝冰心写自传:“像你这样的大作家不写自传是多么可惜。”冰心回信说她正在写,信末总是“亲你,亲你”。杨静宜写道:“只这两个字,就把跋涉过一个世纪的两位老人的心拴到一起,带回到无猜无忌的童年。多么可爱的稚子之心!多么可爱的人间至情!”[6]
苏雪林与谢冰莹的友谊主要建立在苏雪林入台之后,直至苏雪林去世,两人四、五十年情同姐妹。苏雪林1952年7月28 日到达台湾,而1948年夏,谢冰莹接到台湾梁舒聘请她任教于台湾师范学院(后改为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系的书信和聘书,并于同年8 月下旬离开上海赴台上任。苏雪林初来乍到,谢冰莹多方照拂。如苏雪林在武大与袁昌英般,苏在台湾师范大学与谢冰莹几乎日有往来。两人共谈文学,分享教学之事,一起访友谈友,度假散心,十分融洽。两人的友谊以下四方面可证:第一,学林共勉。苏雪林与谢冰莹毕生都追求事业的高峰,倡导女性的独立,反对成为男权社会的附庸。她们在实践自己的人生理想时,互勉互携。诸如苏雪林1952年12 月6 日日记记载的谢冰莹来向其请教《春江花月夜》之韵及作诗之法等探讨写作问题的交往已成为她们为文之乐[7]161-162。苏雪林不厌其烦地为友荐文,“昨日所看谢冰莹我怎样写作,下课回家匆匆阅览,十万字之书居然阅毕,觉得内容内(甚)为丰富,值得介绍”[8],此类例证比比皆是。当遇到学林喜悦之声时,互贺互慰。1957年台湾“中华日报”学术评审会新聘会员苏雪林、谢冰莹都入选,苏难掩兴奋,立即致信谢冰莹共贺[7]282。这种事业途上的互携拉近了两位作家的距离。第二,生活相依。苏谢是生活挚友,旦夕往来,嘘寒问暖,同舟共济,聚首谈心已成为其生活之习。如1962年8 月谢冰莹丈夫贾伊箴自南洋回台,苏雪林送谢毛巾被,谓为谢鸳梦重温之贺礼,并积极为贾先生介绍大学教席职位。谢冰莹1957年想去南洋,苏雪林闻谢之旅费由谢卖女儿钢琴凑足,心里极为自责。她在1957年8 月2 日的日记中写道:“早知如此,余应将美金早日设法带去。譬如方神父率领大专公教学生来台南,彼时托一学生带去,则冰莹可省卖琴之苦矣。唯余生性迟钝,以为他人亦然,且认为冰莹出国,请出境护照不得如何顺利,若等待她护照到手,然后将钱寄去,想不到女兵行动静如处女、出如脱兔,护照居然到手,且一到手即又购得飞机票也。”[7]288而谢冰莹对苏雪林也极为慷慨,曾想将《女兵日记》版税六万元汇给苏雪林,苏坚持不受而已。谢冰莹在台北,苏雪林住台南时,苏每次赴台北均到谢家,看望谢冰莹,并促膝长谈。而谢也不辞辛劳地去车站接送苏雪林。谢冰莹去台南,喜与苏共榻,抵足夜话。第三,鱼雁致音。苏雪林到台南,与谢冰莹几乎日写一信。谢冰莹赴美旧金山,两人通信也极为频繁。如一方久不来信,另一方便心绪不宁。苏雪林因太珍视这个朋友,对于谢冰莹写信像写条子,寥寥数语,不能谈心,殊为恼火,并言以后自己采取同样的态度对之。果然如此后,谢冰莹写便条云盼苏信,否则失眠。两人借通信了解近况,表达关怀。“今日得冰莹信,附来近照一小张,人甚憔悴,为前所未见,可见她旅行美国三个月之劳累,回台湾又不能休息,究竟年龄不饶人,逼出老态,余心为恻然。”[9]谢冰莹晚年患老年痴呆症,苏雪林信件更为频仍,并常为谢暗自落泪。第四,乡愁互慰。苏谢两人都是由大陆入台之人。对于家乡魂牵梦萦,这也无形中成为两人感情的联结点。正如谢冰莹在《故乡的云》中表达的对故乡湖南白云、流水、彩霞、红叶的无限向往般,回大陆,一直是两人的夙愿。1998年5 月,苏雪林以102 岁高龄回到家乡安徽太平,游览了黄山,参加了安徽大学70 周年校庆活动,完成暮年之愿。而谢冰莹直到终老旧金山未能回大陆,逝世前她曾说:“如果我不幸地死在美国,就要火葬,然后把骨灰洒在金门大桥下,让太平洋的海水把我飘回去。”同样的乡愁,诸多的无奈,道出她们内心诉求,也见证了两位老姐妹遥望故乡的思念。
然则,除却文人间正常交往,是什么原因促使苏雪林与冰心、谢冰莹结成亲如姐妹般的友谊?人生艺术理想之相近,行文风格的趋同与接受心理的逆反,对于教义中共通之处的体认,或可窥见一二。
二、原因之一:趋同与逆反
苏雪林与冰心、谢冰莹文章写尽人生的林林总总,世相的形形色色。苏雪林与冰心行文风格有某些神似,苏雪林对谢冰莹之文章有逆反的接受心理,三人的人生艺术理想也相近,正因此才构成相互间的吸引力。第一,行文风格趋同。苏雪林喜欢美文,非常注重文章的语言清丽以及结构的缜密,好用道德的尺度衡量作品内容的高低。她的散文集《绿天》便是清新流利的散文风,剧作《鸠那罗的眼睛》以美文体裁入文。冰心独创“冰心体”,又主张“爱的哲学”,因此在她的文章常有古诗巧化,满蕴着母爱、自然之爱以及童心,饱含哲思。冰心之作是在跌宕起伏中表现对宁静的向往与追求,她用心思澄澈构筑空灵清隽,清幽意远的意境,也不乏庄严与哀思之作。冰心的这种行文风格,本已契合苏之审美标准;而苏进一步认为冰心文字的澄澈与其系统写作思想和心灵的澄澈关系不可分割,这又符合苏之道德尺牍;冰心关照宇宙万物的写作题材,与苏的出世思想也神似;冰心古诗巧用的手法,与苏对于古典文学的偏爱又不谋而合。所以,苏雪林极为夸赞冰心之文的魅力。有苏雪林日记及其评冰心文为证:“看冰心全集、小说集,文笔果然清丽,极见天才,余所不及。”[10]在苏《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这部文学史作品中,她夸赞冰心之诗笔“恬适自然,无一毫矫揉造作之处。”[1]84认为冰心的散文“充满了凝静、超逸,与庄严,中间流溢满空间幽哀的神思。”[1]247在谈到冰心小说盛名时,则用“天资的颖异”[1]348来形容。因而,当冰心的权威受到质疑时,苏雪林便立即举证反驳。如有人批评冰心专一板起面孔冷冰冰地说教。苏辩驳这是思想透彻之人的自然表现,并且这种冷是“夏日炎炎中,走了数里路,坐到碧绿的葡萄架下,喝一杯冰淇淋那么舒服。”[1]80又有人谓冰心诗明秀有余,魄力不足。苏驳斥道:“这实是大谬不然的话。”[1]84通过《繁星三》“万顷的颤动,深黑的岛边,月儿上来了。生之源,死之所!”[1]84之例,说明别人要用很多文字表示的东西,冰心却寥寥数语,用骨髓里迸出的力量感染读者,从而说明“冰心文字力量极大,而能举重若轻。”[1]83又冰心“爱的哲学”被某些人指责“劝饿人食肉糜”,“对社会的幼稚病”,“有闲阶级的生活的赞美”,斥责冰心为“资产阶级的女性作家”,“在她作品里只充满了耶教式的博爱和空虚的同情”时[1]353,苏雪林以尼采式的超人哲学,马克思式的阶级斗争比喻药中之大黄硝朴,用之得当,可以去病症结,但天天用,则适得其反。而将冰心“爱的哲学”比作大米饭,在举世欢迎大黄硝朴之时可能被冷落,但到病人元气稍微恢复,则非用其不可[1]354。以上诸例可见苏雪林对冰心极尽维护,此是两人行文风格有趋同的一面,自然而生文化、心理的认同感,这也是苏雪林晚年与冰心通信后万分高兴,冰心也在给苏雪林之信末附上“亲你”之因。
第二,接受心理的逆反。比对苏雪林、冰心文字中语言的雅致,用古典文学熏陶出的含蓄不同:谢冰莹语言明白如话,不事雕琢,她以唯“真”的审美尺度,认为作品应是现实的反响。因之,她的作品从故事、人物、社会背景都是现实生活的镜子。这位中国第一个女兵作家一扫女性柔美、温婉风格,而将文章写得阳刚悲壮,刚健清朗,豪气毕现,她的文章有“气骨”。曹丕文气说认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谢氏之气如是便为浑然天成。谢冰莹不是美文的践行者,亦非结构缜密的逻辑塑造者,她只是随性地写,不嫌其粗,不避其俗,直爽利落。这与苏讲究词采的瑰丽,结构的严谨大异其趣,但却得到苏真心的赞赏。苏夸谢冰莹文笔具有魔力,“每使读者感觉津津有味,非读个终篇,不忍释手。”[1]252这实是与苏雪林审美之维构成逆反,或者基于一种补偿心理,谢冰莹行文恰好切中了苏雪林未曾涉足之点。谢氏成名作《从军日记》、《一个女兵的自传》均取材军旅真实生活。而谢冰莹《出走》、《理智的胜利》、《一个新女性》等,摹写主人公叛逆顽强地冲破家庭的束缚和世俗的阻力,经过感情地挣扎,克服内心的矛盾纠结,终于自信且无所顾忌地追求人生的绝对自由。这与苏雪林笔下主人公想与旧势力决裂而终于顺从迥异。题材内容的落差,语言的异中之境,让苏雪林读来兴味盎然。无形中摒弃了自己固有理念,而由衷地认同。
第三,人生艺术理想相近。苏雪林与冰心、谢冰莹真挚友谊也源于三位人瑞的志趣相近。她们酷爱写作,笔耕不辍。苏雪林一生都在写中度过,婚姻的失败,更使得她将全部精力投入作文、教书与学术研究。她晚年著自传《浮生九四》,重新整理《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出版,对于屈赋研究孜孜不倦,撰写大量的回忆性散文结集为《文坛话旧》,都标志着她晚年的创作成就。1980年6 月,冰心先患脑血栓,后骨折。病痛不能令她放下手中的笔。她说“生命从八十岁开始”。谢冰莹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中提到“为什么到了八十一,还舍不得‘封笔’?是为了世间还有许多不平、凄惨、悲壮、苦闷、快乐、和未来充满了光明、新希望的事,所以我要写;为了我的无数的可爱的青年和小朋友读者,我更要写!我曾经说过,我要写到呼吸停止的前夕,只要我的脑、手、眼还能够动。”[11]她们用手中的笔不停地为社会鸣不平,赞美人生的真善美,驳斥现实的丑恶假。共同对于写作的敬畏和揭露社会人生的苦难与美好将她们的心联结在一起。
三、原因之二:心灵相通
苏雪林与冰心、谢冰莹都有着宗教信仰,虽不是虔诚的宗教徒,也殊少参加宗教仪式,信仰的也不是同一宗教。但是教义积极一面的类同给了她们精神的寄托即甘于受苦,寻求灵魂的救赎。这让她们惺惺相惜,友谊更深。苏雪林自与天主教结下不解之缘后,她似乎寻求到了灵魂的解脱之道。《棘心》某种程度上,是作者的自传,主人公杜醒秋与作者本身有相似性,小说写到的主人公留法期间因与秦风、未婚夫叔健的情感纠葛,母亲的病重催归,自己又想学成才返,各种矛盾的牵扯,让杜醒秋承受巨大的压力以致病倒。是天主教信徒白朗、马沙给她母亲般的关怀,让她从病中恢复,得到心灵的慰藉。苏雪林认为天主教信仰有三种特点:第一是虔洁、第二是热忱、第三是神乐。她认为教徒的信仰也是人类的精神活动,是生命的火焰,灵性的源泉,感情的迸发,是理性考察的结果。对于教义积极一面的文化认同,苏雪林也体现在自己的作品中,如《绿天》中伊甸园背景的梦幻,《收获》中莎乐美故事原型,《灌园生活回忆》中芥子比喻等都是直接取材圣经典故。
冰心信仰基督教,在大范围内天主教也属于基督教,教义也就大同小异。冰心吸收基督教义中的精华部分诸如平等博爱、牺牲奋进、普度众生等,使其与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接,形成基督爱与个体生命体验的融合。冰心坦言:“又因着基督教义的影响,潜隐地形成了我自己‘爱’的哲学。”[12]天主教与基督教宣扬自由、民主、仁义、义气与道义,主张消除内心的不良欲望,对犯下的过错和自身的罪恶进行忏悔,净化心灵。这些使得苏雪林与冰心能够心灵相通,在作品中宣扬美和爱,并且善于在西方文化研究视野中审视民族自身;促成了她们审美观的趋同即关注弱势群体,希望拯救苦难,抚慰堕落灵魂,改变黑暗人生,追求现实幸福,以达到人道主义关怀。也使得她们作品里时刻流露着童真以及清新、健康的活力。如冰心《寄小读者》,苏雪林散文集《绿天》都是此种审美维度的体现。
谢冰莹皈依佛门,最初始于1954年,她为《读书杂志》撰写长篇小说《红豆》,当连载到第三期,难以继续,于是她倏忽想到观音菩萨,便虔诚地带着日用品到庙里住。叩拜住下后,阻塞的灵感泉涌而至,小说也就如约完成。因此,谢冰莹将此归结为神的指示,并在家里请了尊观世音菩萨,以便每天膜拜。甚至撰写佛经故事如《仁慈的鹿王》、《善光公主》等。1956年拜师后,还起了“慈莹”的法名。[13]晚年,谢冰莹丈夫贾伊箴去世后,因孤独,又住着公寓,倍感凄凉,常诵读佛经以求减轻痛苦。谢冰莹2000年1 月5 日逝世于旧金山。一周后,友人们为其举行佛教仪式公祭。佛教主张的忍受苦难,消除痛苦以寻求解脱之道,与苏雪林信仰的天主教义有着相似之处。晚年老友,一边互传鱼雁,一边通过教义摆脱寂寞,心灵暗合。
苏雪林与冰心、谢冰莹在交往中因着理想相同,兴趣相近,情感相恰,意气相投,而坚固地联结在一起。冰心清丽隽永,谢冰莹则豪放洒脱,但都获苏雪林真心赞赏;她们待友的热情大方而又常存宽容之心让其感知愈深;主张净化心灵、忍受苦难、消除痛苦、传播人道主义精神、寻求解脱之道又使她们找到话语支撑点;真诚的友谊也即应运而生。友情的美好让她们性格展示出天真、可爱、真诚、细腻、温柔一面,也促使她们为社会人生谱写出一段真善美的传奇。
[1]苏雪林.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M].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86.
[2]冰心.入世才人粲若花[N].人民日报,1987-03-07.
[3]谢冰莹.作家与作品[M].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1.
[4]苏雪林.我与冰心[N].台湾新生报,1989-10-05.
[5]苏雪林.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第十四册)[M].台南:成功大学教务处出版组,1999.247.
[6]李瑛.四访苏雪林[J].文史春秋,2004,(11).
[7]苏雪林.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第二册)[M].台南:成功大学教务处出版组,1999.
[8]苏雪林.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第三册)[M].台南:成功大学教务处出版组,1999.289.
[9]苏雪林.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第六册)[M].台南:成功大学教务处出版组,1999.17.
[10]苏雪林.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第一册)[M].台南:成功大学教务处出版组,1999.6.
[11]谢冰莹.冰莹忆往[M].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1.163.
[12]冰心.冰心全集(第七卷)[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463.
[13]古远清.几度飘零:大陆赴台文人沉浮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