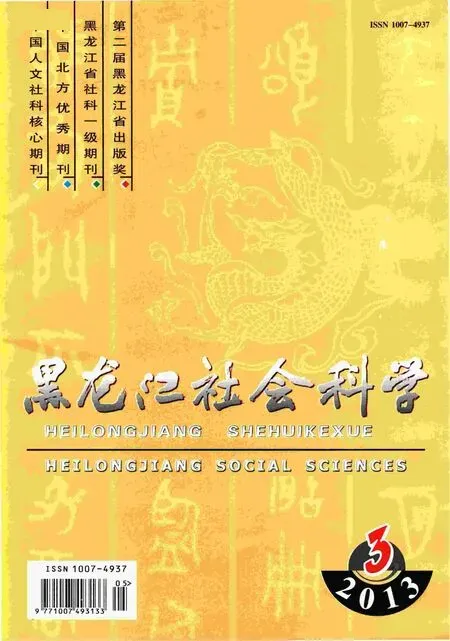素心·猛志·悲慨——论陶渊明人格与文风之关系
2013-04-11蒋文燕
蒋 文 燕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文学院,北京 100089)
关于陶渊明的“素心”与“猛志”,诗人有不少自陈,前代注家亦多有论述,这也是读者最熟知的陶渊明的人格形象。但实际上“他的诗集满纸都是忧生之嗟”[1]200。论家注意到陶诗中的“悲慨”之情,则是自杜甫始。《遣兴五首》其三云:“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枯槁”在这里应释为生活的贫苦。可见,杜甫看出陶渊明生活中也有“恨”,因为坚守理想而生活枯槁,虽不怨天尤人,毕竟天理不公。但对于“素心”、“猛志”、“悲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陶渊明诗歌风格的影响等问题仍值得继续思考和补充。
一、“素心”与“素以为绚”
《移居二首》是陶渊明于晋安帝义熙七年(公元411年)迁至南里之南村不久后创作的诗篇。其中第一首写到诗人与南村邻里交往过从之乐:“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对于诗中“素心”的含义,清人方宗诚《陶诗真诠》云:“素心即淡泊宁静之意。”而所谓“素心人”,宋人罗大经认为“岂庸庸之士”。义熙八年,陶渊明又作《与殷晋安别》,其序云:“殷先作安南府长史掾,因居浔阳,後作太尉参军,移家东下,作此以赠。”诗云:“去岁家南里,薄作少时邻。”此外,萧统《陶渊明传》云:“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浔阳与渊明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浔阳,日造饮焉。每往,必酣饮致醉。”大概殷景仁、颜延之等都是罗大经所言“岂庸庸之士”。或者如作广义的理解,与诗人朝夕相伴的“素心人”也许就是邻里中那些心地淳厚朴实的田夫野老,如《移居》其二所描绘的那样:“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写与新邻同酌佳酿:“日入相与归,壶浆劳新邻。”《归园田居五首》其二写与邻人共话桑麻,“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这样不拘礼节把酒言欢,平常自然、言笑晏晏的生活场景洋溢着浓郁的人情之美。正如朱光潜先生在《陶渊明》一文中所指出的,“渊明是一个富有热情的人,甘淡泊而有之,甘寂寞而未必,在归田后二十余年中,他在田夫野老的交情中颇得以一些温慰。”[1]197所以,“素心人”既是陶渊明对友人、邻里的赞赏,更是诗人人格境界的自我写照。
此外在陶诗中,诗人还多次描绘了“素”之意境:
和泽周三春,清凉素秋节。……检素不获展,厌厌竟良月(《和郭主簿》其二)。
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杂诗八首》其二)。
素标插人头,前途渐就窄(《杂诗八首》其七)。
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饮酒二十首》其十五)。
素颜敛光润,白发一己繁(《岁暮和张常侍》)。
素砾皛修渚,南嶽无馀云(《述酒》)。
白玉凝素液,瑾瑜发奇光(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四)。
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来(《答庞参军》)。
促席延故老,挥觞道平素(《咏二疏》)。
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咏荆轲》)。
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自然景象的纯净素雅,还是人物襟怀的淡泊高远,都是诗人赞赏和追求的境界。这一点也深得同辈诗人及后世文人的认同与追慕。颜延之在《陶徵士诔》序说渊明“长实素心”,江淹《拟陶徵君田居》诗云:“种苗在东皋,苗生满阡陌。虽有倚锄倦,浊酒聊自适。日暮巾柴车,路闇光已夕。归人望烟火,稚子侯檐隙。问君亦何为,百年会有役,但愿桑麻成,蚕月得纺绩。素心正如此,开迳望三益。”在江淹的怀想中,陶渊明的生活呈现出一派疏放冲澹的气韵。所以,淡泊宁静之“素心”是陶渊明精神风貌之一端,而由“素心”酝酿而成的平淡自然也成为陶诗的主体风格。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陶渊明在以自然疏淡之笔描绘躬耕吟咏、读书饮酒、侍亲交友等人生世相时,诗歌时时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焕发出人情的温暖光辉,让人体会到诗人“素心”之中亦有热肠。对于这一特点,清人钟秀的《陶靖节记事诗品》认为陶渊明:“不侪俗,亦不绝俗,不徇人,亦不亵人。”朱光潜先生在《陶渊明》一文中则认为:“渊明之所以异于一般隐士的正在不‘避俗’,因为他不必避俗,所以真正地‘达道’。所谓‘不避俗’是说‘不矫情’,本着人类所应有的至性深情去应世接物。”所以,“素心”既是尘世中的淡泊沉静,亦是归隐后的赤子热肠;既是田园中的怡然自得,也是困顿中的固穷守节。与此同时,“素心”不是离群索居、孤芳自赏,不是不近人烟、废弃事理,不是矫情立异、过激极端。它是从真实平常的生活中历练出的纯粹人格,由人格纯粹而获得的自由意志。“大诗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来的诗是人格的焕发。陶渊明是这个原则的一个典型的例证。”[3]194正是“素心”这种人格境界使得陶诗呈现出“素以为绚”的美学风貌。裴斐《论语讲评》认为:“‘素以为绚’意谓虽不打扮(素)却光彩夺目(绚)。”[2]如将这种认识与陶诗风格相连,则“素”是指其冲澹自然的诗歌风格,“绚”是指诗歌中焕发出淳厚温润的生活底蕴与光彩。
二、“猛志”与“语健而意闲”
凡有素心者,必有铁骨。诗人自言其“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五柳先生传》),“性刚才拙,与物多忤”(《与子俨等疏》),“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萧统传曰“渊明少有高趣”、“颖脱不群,任真自得”、“不堪吏职”、“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陶渊明传》)。论家感叹“湧若海立,屹若剑飞,斯陶之心胆出矣”(黄文焕《陶诗析义自序》)。而这种傲然“心胆”是从诗人的“猛志”中得来的。陶渊明在《杂诗八首》中陈述少志:“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在《读〈山海经〉十三首》中赞叹神人:“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这就是被鲁迅先生称之为“金刚怒目的一面”(《且介亭杂文二集》)。
而陶渊明的“猛志”不仅指诗人济苍生、复故土的宏志,也应当包括他对固穷守节、泥而不滓等儒家理想的坚守。在诗歌中,诗人斩钉截铁地表示“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诙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答庞参军》)。“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影答形》)。“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七首》其四)。“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饮酒》其二)。所以,虽因环境所迫诗人不能实现积极用世的“猛志”,而坚守理想又何尝不是济世之志一种坚韧顽强的延续?因此,读书咏史、吟咏先贤,正是为了保持与他们精神血脉的相连,正如《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所云:“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清人延君寿的《老生常谈》评价这几句诗,“如松柏之岁寒,其劲直之气,与有生俱来,安能不偶然流露于楮墨之间。”在《饮酒二十首》其九中,面对田父清晨叩门,提壶携浆的好意劝说:“褴褛茅簷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而诗人的回答是,“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其语看似婉转,实则“斩钉截铁,劲气勃发,可以想见陶公之为人。”(延君寿《老生常谈》)这首诗与萧统《陶渊明传》所记可以互为佐证,“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
当这种傲然自足的高贵精神和自由意志灌注在诗文中时,使得陶诗在冲澹自然主体诗风之外,同时还有一种豪放劲直的风格。朱熹《朱子语类》首发其论,“陶渊明的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的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3]3325其实陶诗中除了《咏荆轲》、《咏二疏》、《咏三良》等咏史诗表现出一种豪宕之气外,还有为数不少的酬赠诗、咏怀诗、饮酒诗也常出语劲直有力,表现出诗人为坚守理想而自尊自傲的风骨。在《饮酒二十首》其六中,诗人就对世俗的是非标准与雷同誉毁表现出不屑一顾:“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誉毁。三季多此事,达士似不尔。咄咄俗中愚,且当从黄绮。”他骄傲而坚定地表示要像“商山四皓”那样过着避世归隐的生活。诗人还常以“青松”、“孤松”、“松柏”自励,如《饮酒二十首》其九云:“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这仿佛给诗歌也披上了一层苍翠之色。
需要注意的是,诗人的“猛志”大多蕴涵在一种平淡坚定的语调中。平淡源于诗人对理想的坚守,可以放弃现实功利的诱惑,不必与外界任何人去争。坚定是缘自诗人对信念的执著,具有外界任何困苦都无法改变其意志的力量。这也使得陶诗在豪宕的同时还有一种闲定的气韵,朱熹《朱子语类》论曰:“陶却是有力,但语健而意闲。”[3]3327这种闲定的气韵得益于诗人人格境界——素心和思想认识——猛志的涵养,而且是从辛酸苦闷的现实处境中历练而出,所以显得弥足珍贵。
三、“怅恨”与“忧愤沉郁不可一世之慨”
陶诗中多有“悲慨”,这一般不被读者熟知。而引起诗人无限“悲慨”之情的主要原因是生活之苦、失志之慨、迟暮之感和生死之虑,所以在陶诗中诸如恨、忧、怅、悲、慨、愧、凄、怨、苦、辛、焦、悔、不欣、枯槁等字眼曾多次出现,真切地传达出诗人在现实生活中困顿失意的情绪。
在诗人笔下,饥寒贫病是其生活的常态。出仕前除渊明家境贫寒,“少而贫病,居无仆妾;井臼不任,藜菽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颜延之《陶征士诔》)。出仕十年仍然了无改善,“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瑟空宇中,了无一可悦”(《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而归隐后生活实况则是“饥者欢初饱,束带候鸣鸡”(《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氵巽田舍获》)。“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诗人虽不怨天尤人,但也坦白承认,“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躬耕南亩也绝非只是“悠然见南山”般地闲雅自得,“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天灾不断,收获可怜,“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家境的贫穷还不算,诗人一生贫病交加,他素有“脚疾”(《宋书·隐逸传》),“吾抱疾多年,不复为文,本既不丰,复老病继之”(《答庞参军》序)。
除了生活的苦况外,精神上的苦痛更让诗人感慨与悲愤。所以,陶渊明的饮酒诗、咏史诗和咏怀诗在评阅时世、追慕先贤的同时,其实也是借古人的杯酒浇自己心中之块垒。在陶渊明后期的作品中,迟暮之感和生死之虑是常见的主题。例如,“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饮酒二十首》其三);“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岁月相催逼,鬓旁早已白”(《饮酒二十首》其十五);“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杂诗十二首》其一);“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十二首》其二)。诗人长于炼字,善用比兴,将时光的无情以一种惊心动魄的方式呈现出来,充满了悲剧意味。关于死,他似乎有着透彻的思考,“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贤圣,谁能独免”(《与子俨等疏》);“人生实难,死之如何”(《自祭文》)。但实际上亦不免失意怅惘,“流幻百年终,寒暑日相催。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还旧居》);“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己酉岁九月九日》)。“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绿”(《拟挽歌辞》其一)。特别是亲人一一逝去,朋友各走其道,大半与他“语默自殊势”(《与殷晋安别》),所以诗人由伤悼逝者而自念己身。
正如本文开头所言,后世论家自杜甫开始注意到陶诗中的悲苦基调,“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遣兴五首》其三)。杜甫看出陶渊明对现实枯槁生活的怅恨之情,实可谓诗人的异代知音。其后韩愈《送王秀才序》亦云:“及读阮籍、陶潜诗,乃知彼虽偃蹇不欲与世接,然犹未能平其心。”曾巩《过彭泽》云:“予观长者忧,慷慨在遗集。”宋人汤汉《陶靖节诗集注自序》认为,陶渊明《述酒》之作,“始直吐忠愤,然犹乱以廋词,千载之下,读者不省为何语。是此翁所深致意者,迄不得白于后世,尤可以使人增欷而累叹也。”[4]109汤汉认为陶诗以隐语表达“忠愤”之情,以至于后世读者不明其真味。明人毛晋则将陶诗与屈辞相提并论:“讬之忠言以泄忧愁悲思,此予所以每读屈辞陶诗,而为之酸鼻陨心也。”[4]167清人乔亿《剑谿说诗》提出,“读陶诗当察其乐中有忧,忧中有乐。”[4]196沈德潜《说诗晬语》则云:“渊明有忧勤语,有自任语,有知足语,有悲愤语,有乐天安命语,有物我同得语。”[5]现代论家梁启超、朱自清、朱光潜也表达过类似的见解。然而值得追问的是,陶诗中的“悲慨”基调与其诗风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注意到,在这类作品中,以议论入诗是其中不可忽视的表现手法。这大概是由于在枯槁的现实处境中,不甘寂寞的陶渊明也需要急切地表达政治意见,抒发理想抱负,宣泄牢骚愁闷,所以“议论”就成为最直接的表达方式。像《饮酒二十首》其二以反诘发议,表达出诗人对善恶报应之说的责问,铿锵有力,引人遐思:“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尽管如此,他最后还是坚定地表示要固守穷节,因为道义传统因此传立。所以,失志之叹的另一面就是守志之慨。而陶诗中的议论,多数也还是直说的“赋”法。在《拟古九首》其二中,诗人直抒胸臆,表明不愿意与趋炎附势之徒为伍,只在意一生的沉浮,“不学狂驰子,直在百年中”(《饮酒二十首》其六)。诗人对世俗是非标准不屑一顾,“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誉毁”。然而虽是直说,激愤之情却意在言外。因此这些议论性诗句实际上是诗人借助意见来抒情,抒发心中的不平之气。诗人在自身现实的处境与历史贤良的遭遇中找到了情感共鸣,由这种共鸣更坚定了自己当下的价值判断,而后世的读者则从这些价值判断中受到了感情的触动和思想的启发,正如在陶渊明田园诗中受到的感染一样。所以陶诗中的议论因为饱含着生活的辛酸苦闷,融会了丰富的人生体会,寄寓了坚定的理想操守,从而成为一种有效的抒情手段,尽见诗人的性情。对此,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曾明确指出陶诗的议论基于情理,“或问予:子尝言元各诸公以议论为诗故为大变,若靖节‘大钧无私力’、‘颜生称为仁’等篇,亦颇涉议论,与元和诸公宁有异耶?曰:靖节诗乃是见理之言,蓋出于自然,而非为智力得之,非若元和诸公骋聪明,构奇巧,而皆以文为诗也。”[6]总之,陶诗中的议论也是一种抒情手段,而且诗人在表达现实怅恨之情时多以议论入诗,借议论来吟咏性情,使得诗歌具有一种悲慨的审美意味。清人潘德舆的《养一斋诗话》曾云:“陶公诗虽天机和鬯,静气流溢,而其中曲折激荡处,实在忧愤沉郁不可一世之概。”[7]“天机和鬯,静气流溢”是对陶渊明田园平淡自然诗风的概括,“忧愤沉郁”则可视为是对其咏史、咏怀诗悲慨诗风的总结,而“不可一世之慨”则传达出诗人在现实人生中倔强的傲骨和坚定的信念。
综上所述,“素心”、“猛志”与“悲慨”其实是陶渊明人格境界的三个方面。宋人汤汉在《陶靖节诗集注自序》中曾云:“夫惟恶于饥寒之苦,而后能存节义之闲。”如果说“怅恨”是诗人对“饥寒之苦”现实处境的真实反映,而在这样的苦况中“能存节义之闲”则得益于诗人纯粹的人格境界——“素心”和坚定的理想信念——“猛志”的历练与涵养。正是由于对理想的执著与坚定——“猛志”,诗人在面对充满“怅恨”之情的现实苦难时,他仍保持着赤子情怀——“素心”,既有淡泊平静,又富古道热肠。当这种人格境界投注在诗歌创作时,使得陶诗以平淡自然为主体诗风的同时,还具有豪放劲直、悲慨沉郁的风格,呈现出多样化的诗歌意境。
对于陶渊明的精神生活,朱光潜先生认为其《时运》诗序中最后一句话“欣慨交心”是极恰当的总结,“他有感慨,也有欣喜;惟其有感慨,那种欣喜是由冲突调和而彻悟人生世相的欣喜,不只是浅薄的嬉笑;惟其有欣喜,那种感慨是适当地调剂,不只是奋激佯狂,或是神经质的感伤。他对于人生悲喜居中两方面都能领悟。”[1]205然而“欣慨交心”应该还只是陶渊明精神生活的第一个层面,或者说是诗人现实心境的准确传达。在“欣慨交心”之上,应该是诗人“傲然自足”(《劝农》其一)的精神境界,是诗人面对苦难时所获得的一种任何力量都不能剥夺的自由意志。因为这种自由意志,生活的苦难既不能夺去诗人自尊自傲的风骨,也不能减少其怡然自得的情怀。他占据着精神的高度,完成了对苦难的超越。唯其如此,才能更好地体会陶诗的豪放劲直和悲慨沉郁,以及平淡自然诗风中所包藏的骨力与闲定的气韵。
[1]朱光潜.诗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裴斐.论语讲评[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387.
[3]朱熹.朱子语类:卷一四〇[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陶渊明资料汇编: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5.
[5]沈德潜.说诗晬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202.
[6]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102.
[7]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2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