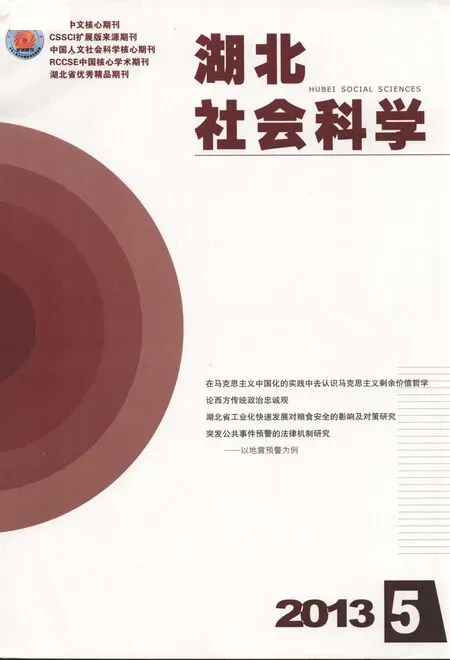载泽与清末立宪
2013-04-10邓春丰
邓春丰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以往学界对载泽的研究,多以《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为中心,对载泽在清末立宪时期的整体活动缺乏关注,其所著《考察政治日记》亦被人忽视。为弥补这一研究缺陷,本文主要对载泽在清末立宪时期的思想与活动做一钩沉和评述。
一
面对日俄战争后日趋严重的统治危机,1905年7月16日,清廷决定派遣“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1](p1)载泽(1868—1930),清王室宗公,初封“镇国将军”,后晋“辅国公”,为康熙第十五子允禑六世孙。他“留心时事,素号开通”,[2](p92)是官僚立宪派主要代表人之一,这是其能入选考政大臣的主要原因所在。
谕旨颁布后,载泽等考政大臣上奏表示朝廷此举可“收富国强兵之效,大局幸甚,天下幸甚。”[1](p2)革命派认为“五大臣之出洋也,将变易其面目,掩其前日之鬼脸,以蛊惑士女,因以食人者也。”[3]1905年9月24日,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带领参赞、随员,在北京正阳门车站“巳刻登车,正拟开行,陡闻轰震之声甚为剧烈,并肩烟气弥漫,窗棂皆碎。”[1](p3)他们遭到革命党人吴樾的袭击,载泽额角受微伤,绍英耳后发际及臂上受伤略重,随员仆从亦有受伤。载泽能躲过此劫实属万幸,“其时,适值日本国内团公使之代理公使馆二等书记官郑永邦送行,泽公起身出外答送,遂免于危。”[4]清廷朝野震惊。慈禧“慨然于办事之难,凄然泪下”,[5](p314)并“责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工巡局、督办铁路大臣等,确切查拿,彻底根究,从重惩办,以儆凶顽。”[6](p2166)
对于革命党人的此次“反满”恐怖活动,舆论哗然。《大公报》认为“我政府即迎其机而速行改革,以绝彼党之望,宣布立宪。”[7]呼吁清政府“当此之际,更宜考求各国政府,实行变法立宪,不可为之阻止。”[8]《申报》指出“五大臣车站遇险,不足为新政之阻力,而反促成立宪之基础。”[9]对清廷而言,“此后改革政体,实行立宪,其时期当必不远。”[2]经此一劫,社会上要求清廷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呼声反而愈发高涨。
最终,清廷派李盛铎、尚其亨会同载泽、戴鸿慈、端方前往各国考察政治。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一行于1905年12月11日离京,1906年1月14日到上海,启程前往日、英、法、比四国考察。他们在法国52天、英国45天、日本29天、比利时16天、美国游历15天,考察完毕后,载泽、尚其亨于1906年7月23日回到北京。经过此次考察,他们认识到专制封闭是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中国要富强,必须学习各国的先进经验。载泽等派人将在四国考察情况译纂成书,计67种146册。这些书籍和资料使清廷最高统治者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更加了解,也增强了他们进行政治改革的决心。
二
通过出洋考察政治,载泽对资本主义文明和世界局势的认识颇有见地。他分析中西治道之不同,“在我曰用中,在彼曰用极。”[10](p564)欧美列邦之所以强大,在于“往往萃十数国学者之研,穷数十百年之推嬗,以发明一名一物,成立一政一艺,不至其极不止。”[10](p564)中国的中庸之道在治国方面存在很多弊端,但能使人皆修勉于道德,举国上下,同力一心。若我们能积极学习和利用欧美列邦“求乎至极”的治国精神,中国一定会经过变法维新而强大。为此他提出:“至于国势民风,彼我之所同异,礼俗政教,有可以相袭、不相袭之故,可得而规度也。”[10](p564)鉴于中日两国自近代以来的巨大差距,载泽指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富国强兵的效果,其根本在于教育普及。更重要的是日本不盲目效仿欧洲,而是注重和本国国情相结合,因此最终取得“以三岛之地,经营二三十年,遂至抗衡列强,实亦未可轻量”[1](p6)之成效。作为由儒家传统制度培养出来的专制王朝的大臣,能做出如此评价,其眼量已卓然高出顽固迂腐的守旧派。但他又提出:“夫法制、政教、兵农、商工,当因时损益,舍短取长,此可得而变异者也;伦常道德,当修我所固有,不可得而变异者也。”[10](p566)即使是作为当时比较激进的官僚立宪派,载泽对政治制度的改革依然保守,这一思想上的局限性直接影响到以后清廷实行政治改革的深度。
回国后,载泽被慈禧和光绪皇帝召见两次,他和其他考政大臣“皆痛陈中国不立宪之害,及立宪后之利。”[11](p14)实行立宪不仅是政体的改变,更是国体和整个专制制度的改变。这将严重损害地方督抚们的既得利益,他们纷纷上奏表示反对,认为立宪“施之我国,则有百害而无一利。”[1](p108)载泽上《奏请宣布立宪密折》进行反驳,他指出立宪“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12](p27)“盖宪法既立,在外各督抚,在内诸大臣,其权必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优,于是设为疑似之词,故作异同之论,以阻挠于无形,彼其心,非有所爱于朝廷也,保一己之私权而已,护一己之私利而已。”[12](p27)此言倒不失为统治阶级内部的有识之论。既然是政治体制改革,内外诸臣应当在权与利两个方面向国家和人民做出相应的让步,即使是最高统治者,也应如此。否则一切都将成为空谈。舆论界对此反响巨大。有评论指出:“吾国之所得由专制而进于立宪,实以此折为之枢纽。”[13](p7)《北京日报》专门发表评论:“余深服泽公高见远识,洞见隐微,且能言人之所不敢言。近支王公,乃有此人,大清国其有赖矣。”[10]针对一些满洲贵族反对立宪的谬论,载泽批判道:“谓满人之言立宪不利者,实专为其一身利禄起见,决非忠于谋国。使其行排汉之政策,必至自取覆亡。”[11](p14)
宪政改革后君权是否会受到影响,是君主及载泽等考政大臣关注的焦点所在。为保证立宪工作的顺利进行,载泽等官僚立宪派主张清廷可效仿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因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虽采用立宪制度,君主主权,初无所损。凡统治一国之权,皆隶属于皇位。”[10](p575)就目前时势而言,实行君主立宪有三大益处:“一曰皇位永固,一曰外患渐轻,一曰内乱可弭。”[12](p28)后世学者多以载泽此言作为依据,批判清末立宪只是一场骗局。笔者认为仅以此点就全盘否定清末立宪有失偏颇,因为任何改革者搞改革都是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清朝统治者所进行的宪政改革亦然如此。综观载泽的立宪思想,维护君权是其核心,其所论并不完全正确,如说立宪后君权不受损害并不符合实际,所言立宪的“三大利”也未必会有那么大的效力。但其立论均从国家前途和大局出发,亦无狭隘的民族偏见,敢于同守旧的顽固势力作斗争,身为满洲的宗室王公,其精神和胆识值得称赞。
面对欧美诸邦及日俄诸国觊觎我国的险恶国际环境,对清廷而言,实行立宪已是刻不容缓之事。载泽希望统治者能坚定立宪的决心,为稳妥起见,他又提出:“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12](p29)戴鸿慈等考政大臣也建议清政府以十五年或二十年为实行立宪之期。地方督抚袁世凯、张之洞、周馥三人也主张十二年以后再正式实行立宪。1906年9月1日,光绪帝颁布《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谕》,正式标志着清末预备立宪的开始。清廷采纳了载泽等人的建议,于1908年宣布经过9年预备后正式实行君主立宪政体。
最终,清廷选择实行日本式的二元君主制政体的缘由众多,既有官僚立宪派的积极争取,更有日本出于政治渗透的考虑,在中国立宪问题上采取积极措施所施加的影响,更有满清王朝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诸多因素在内,但载泽等官僚立宪派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计自四大臣归国以迄宣布立宪,才足一月,其间大臣阻挠,百僚抗议,立宪之局,几为所动。苟非考政大臣不惜以身府怨,排击俗论,则吾国之得由专制而进于立宪与否,未可知也。故说者谓此次宣布立宪,当以泽公等为首功”。[11](p17)
三
在中国召开国会,制定宪法,实行君主立宪是朝野立宪派的愿望。面对不可遏抑的国会请愿运动,清廷于1908年8月27日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其中“君上大权”14条,“附臣民权利义务”9条,要点如下:
君上大权:[1](p58、59)
1.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
2.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
3.钦定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之权。
4.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会之权。
5.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
6.统帅陆海军及编定军制之权。
7.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使臣与认受使臣之权。
8.宣告戒严之权。
9.爵赏及恩赦之权。
10.总揽司法权。
11.发命令及使发命令之权。
12.在议院闭会时,遇有紧急之事,得发代法律之诏令,必得以诏令筹措必需之财用。
13.皇室经费,须经君上制定常额,自国库提之,议院不得置议。
14.皇室大典,应由君上督率皇族及特派大臣议定,议院不得干预。
《钦定宪法大纲》基本上以当时的日本宪法为蓝本,[11](p11)而且在有关君主权力方面比后者更加保守,增加了议会闭会期间君主筹措经费的权力,对日本宪法中规定的臣民的迁徙、宗教信仰、通信、请愿等自由,均未提及。因此宪法颁布之后,遭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立宪派的猛烈抨击,但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它的历史进步性。宪法前言讲到:“君主立宪政体,君上有统治国家之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归总揽,而以议院协赞立法,以政府辅弼行政,以法院遵律司法。”[1](p57)这在保证君权的前提下,也体现了资本主义国家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组织原则。“它所起的承先启后的历史地位,和积极的丰富立法经验,对以后的中华民国的法制建设具有指导的意义。”[16](p221)载泽向清廷所推荐的日本式二元君主制,虽说是宪政中最为保守的一种,但较之完全的绝对的君主制,它又是一种历史的进步。[17]这样一部进步性宪法的问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载泽等考政大臣所宣传的西方宪法思想的影响。清廷在整个预备立宪过程中,始终无法摆脱立宪与君权的矛盾缠绕,既想通过立宪以图自救,又希望君上大权不受损伤,而其致命伤也恰在这里。清统治者颁布这一备受争议的宪法,在宪政改革的道路上又往前迈了一步,同时也使自己陷入更为艰难的处境之中。
四
清末“立宪之根基,莫要于地方自治。”[9]五大臣在英考察时,有英议员提出对中国危害至深的鸦片问题,并表示:“若贵国果能禁种,英议院深表同情,亦议禁印度烟出口。”[10](p626)载泽认为鸦片危害中国甚于洪水猛兽,有能绝禁之者,功不在禹、周之下。今英议员有此态度,可见公道不泯,中国亦可借此逐渐收回中国关税之主权。要解决好这一问题,他提出:“则非竭力创立地方自治不可。且地方自治成立,则立宪之根本已固,可渐图收回既失之国权,内外并营,则鸦片之害,二十年内可望尽绝。”[10](p626)载泽对满洲政府的忠心可鉴,对于中国未来的走向更是时刻挂记于心。
在其《考察政治日记》中,载泽详细记载了英、法、比利时等国地方自治的情况。他对英国的地方自治深为赞赏,认为“至其一国精神所在,虽在海军之强盛,商业之经营,而其特色实在地方自治之完密。”[10](p630)在他看来,“以地方之人,行地方之事,故条规严密,而民不嫌苛。以地方之财,供地方之用,故征敛繁多,而民不生怨。而又层折曲累,以隶于政府,得稽其贤否而奖督之,计其费用而补助之。厚民生而培民俗,深合周孔之遗制,实为内政之本源。”[10](p630)通过载泽等出洋考政大臣的宣传,再加清政府当时已经左支右绌的财政状况,地方自治用地方之款办地方之事的特征深得其心,清政府决定以地方自治作为立宪的基础和富强的根本,地方自治在全国迅速开展起来。虽然这场运动最终并未完全达到改良地方政治之目的,清政府希望借此缓解统治危机的目的也未实现,但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在清末立宪过程中,载泽是皇族中比较坚定的官僚立宪派。1911年5月8日责任内阁成立,他担任度支大臣。皇族内阁成立后,清廷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载泽等上奏表示:“臣等均属懿亲,未便久充国务要职。合无仰恳天恩,俯鉴下忱,准将臣等即日开去国务大臣,另简贤能分任要职。”[1](p600)他们奏请皇帝组织完全内阁,以确保立宪的顺利实行。然而,革命的急风暴雨已经到来,载泽等少数官员的作为对于清廷而言亦是杯水车薪,清政府未能完成自身的缓慢演变,而被革命的滚滚洪流所吞没。
在清末立宪这场改革运动中,作为考政大臣之一的载泽,其思想与实践值得我们关注。君主立宪相对于封建专制制度而言,具有毋庸置疑的优越性和进步性。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推动着社会思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面前,作为满洲王朝的宗室王公,载泽“有心护国,无力回天”,他所期盼的“神皋区夏,振奋之机,会不在远。”[10](p564)、“庶国势进,闻实昭于天壤,传永永而无穷也。”[10](p567)的目标终究未能实现。
[1]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鸽子.隐藏的宫廷档案[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3]思黄.怪哉上海各学堂各报馆之慰问出洋五大臣[N].民报第1号.
[4]泽公幸免炸弹之由[N].申报,1905-10-01.
[5]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8.
[6]论捕谋伤出洋五大臣要犯[J].光绪政要,卷三十一.
[7]论出洋五大臣临行遇险事[N].大公报,1905-09-26.
[8]电致驻日钦使[N].大公报,1905-10-14.
[9]论绅董对于地方自治之责任[N].申报,1905-09-30.
[10]载泽.考察政治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8.
[1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2]载泽.奏请宣布立宪密折[A].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四)[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3]镇国公载泽奏请宣布立宪密折[J].东方杂志第四年临时增刊.
[14]论立宪制度利于政府而不利地方官[N].申报,1906-09-09.
[15]附宪法大纲暨议院法选举法要领清单[A].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C].北京:中华书局,1979.
[16]张晋藩.法律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2.
[17]罗华庆.载泽奏闻立宪“三利”平议[J].近代史研究,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