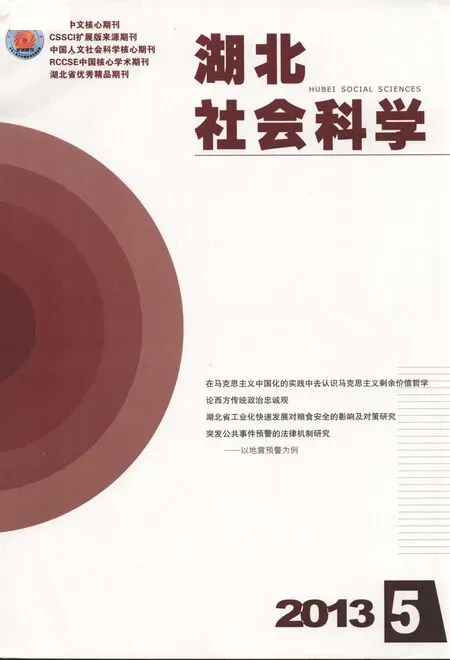论西方传统政治忠诚观
2013-04-10邵银波
徐 霞,邵银波
(1湖北警官学院思政课部,湖北 武汉 430034;2空军预警学院科研部,湖北 武汉 430019)
“有容才有文明,无容则无文明”。任何国家在保持自身政治运行的历史传承和民族特色的前提下,应该学习借鉴世界各国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广泛汲取反映社会历史进步的政治思想理论。西方传统政治忠诚思想渊源流长,积淀深厚,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思考,对现代西方政治文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研究这一课题,汲取有益成分,可以为党的政治忠诚教育,为培养和造就更多“忠诚党的事业,忠贞革命气节,忠实履行使命”的党员干部提供理论参考和借鉴作用。
西方传统政治忠诚观主要是指从古希腊时期到近代资本主义时期,以政治忠诚为核心内容的思想原则和行为规范的总和。纵观西方社会政治忠诚观发展历史,主要分为古希腊、中世纪和近代三个历史时期。
(一)古希腊时期的政治忠诚观。
古希腊时期主要是指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5世纪的1000多年的时间。这一时期,古希腊的先哲们殊途同归地以“‘城邦’(即国家)为政治哲学的主题,从法律、公民职责、政体等视角,深入地研究了古希腊的政治忠诚思想”,[1](p35)提出了 “忠诚于城邦”、“忠诚于法律”、“效忠于现行政体”、“忠诚于优良政体”等政治忠诚理念,规范了公民的政治思维取向,为以后西方政治文明的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苏格拉底在欧洲文化史上的影响巨大,几乎与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所占的地位相同。苏格拉底一生忠爱雅典城邦,忠诚于雅典法律,在他看来,法律是公民与城邦达成的契约,所有公民都要无条件尊重和服从城邦的法律,苏氏还进一步把公民与城邦法律的关系比喻为父母子女的关系,认为法律赋予了公民生活所必须的权利,并通过制裁违法者,呵护公民个体。由此提出,必须坚持以德报怨的原则,即使国家对公民不公,公民也不能报复,在他看来,国家的地位高于父母,既然对父母不能报复,对国家则更不能报复。因而,如果违背了法律,除违背契约,不守信义这一种重罪外,还有两种罪:“不服从生养自己的父母;不服从教养恩人。”这样,违背国家法律不仅仅是在法律上“犯了罪”,而且在伦理上也是犯了罪。
从上述苏氏的观点可知,法律是维护和实现城邦民主政治的重要手段,公民要实现政治民主,管理国家,就必须遵守契约,服从法律。公民服从法律,对法律无限度的、无条件的忠诚,即是对城邦政治的忠诚;遵从法律就是尊重民主政治,忠诚于民主。
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将国家置于各个公民之上,认为国家就其本质而言等同于人,因而要求国家也拥有像人一样的内在的统一性,公民必须服从这种统一性。其政治忠诚观,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通过建立贤人政体,实现城邦政治文明。在他看来,宝贵的美德正是城邦文明的核心价值所在,于是他和其师苏氏一样主张实行贤人政治、以德治国、道德兴邦。在《理想国》中,他甚至勾勒出了一个所谓真、善、美相统一的理想国家的蓝图,但同时提出现存的政治都是坏的,人类的真正出路在于哲学家掌握政权,这种贤人统治下的贤人政体才是最好的政体,才能拯救当时城邦所处的危机。
第二,政府的目的应该旨在寻求老百姓的利益。柏拉图深刻地指出,任何城邦政府不能只顾及自己的利益,只为“强者”的利益,“一个真正的治国者追求的不是他自己的利益,而是老百姓的利益”。[2]柏拉图在论辩城邦政府的目的与职能时提出,理想国家的目标,不是为了某个阶层或集团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奴隶主与自由民)的最大幸福,是为了“铸造一个整体的幸福国家”。柏拉图的这种“民本”思想是他设计理想城邦国家的重要基调,是他的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在人类的思想史上深有影响。
第三,每个阶层的人必须忠于职守、恪守其职。在柏拉图看来,理想国家应由三个阶层组成,即受过严格哲学教育的统治阶层、保卫国家的武士阶层、平民阶层,每个阶层的人们必须各安其分,恪守其职,不可逾越。为了建立和维护国家的正常秩序,柏拉图特别强调,作为国家正义的“银”阶层——保卫国家的武士阶层,更得忠于自己的职位,忠诚于职位所赋予的职责,并全力以赴地做到忠于职守,这才是对国家正义的履行,对城邦的最大忠诚。
亚里士多德是“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是西方最早创立独立的政治学体系的思想家,他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对城邦忠诚的见解,并将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其主要观点是:
第一,效忠于现行政体。亚里士多德提出,公民只有效忠于现行政体,才能稳定城邦的政治。基于这一认识,在《政治学》中,他曾明确提出:“凡是想担任一个城邦中最高职务和执掌最高权力的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效忠于现行政体就是重要条件之一。”[3](p271)
第二,主张公民轮番为政。他认为“人是城邦的动物”,人有天然要过政治生活的愿望,所以不能使某些人终身作统治者从事治理工作,而应该由大家参与政治,按照规定的时期或其他轮流的程序交替执政。这一思想充分反映了亚氏所代表的中产阶级要求参与政治,参与国家事务的政治要求。
第三,城邦的目的在于谋取人类的优良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在本质上是至高无上的社会团体,城邦的存在不只是为了便于交换,防止互相损害等,城邦建立的目的是协调各人,谋取人类的优良生活,这是城邦区别于其他社会团体的本质所在。为此,他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例如,城邦的建立要选择优良的地理位置,要考虑到城邦的内外联系、城邦内各种设施的安排以及军事防卫等各种因素。这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充分表明了,亚氏对雅典城邦的耿耿忠心和良苦用心。通过这种方式,亚里士多德既强调了多样性,也强调了国家共同体存在的必要性。
第四,忠诚于法律。亚里士多德非常重视法律,认为法治由于人治,是最优良的统治者。
总之,好的政治需要公民的服从,民主秩序依赖公民的服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城邦至上”、“忠诚于城邦”、“效忠于现行政体”等政论自希腊之后一直影响深远。“要求对城邦的忠诚,对现行政体的效忠,使人们把全部的忠诚都献给国家,使国家秩序获得合理性,有利于国家秩序和城邦安定”。[4]
(二)中世纪的政治忠诚观。
中世纪主要指5世纪到15世纪欧洲主要国家经历的1000多年的时间。欧洲的封建社会在这一时期里延续了1000多年,这一时期的天主教及其教会占据最高统治地位,政治即是神学的婢女,政治信仰即是宗教信仰。因此,中世纪西方政治忠诚观,主要反映在神学框架下的基督教文化中。
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忠实于基督教信仰和教义,对上帝充满了无限的忠诚、敬意、感恩之情。在《论秩序》中,他提出,上帝是至高至真的,是不可违抗的,人类的肉体应服从于灵魂,忠诚于上帝。他甚至破天荒地指出,上帝的城邦与世俗社会并不冲突,对上帝的城邦的忠诚既能给世俗社会中的公民提供一种信仰、精神寄托,又能使公民将对上帝的信仰、虔诚化为城邦工作的激情、动力。通过神学的理论,他把公民对上帝的信仰与对世俗社会的忠诚达成一定程度的统一,提倡以实际行动来体现和实践对世俗社会的忠诚,同时人们在努力实现上述忠诚的同时,本身也是对上帝的忠诚、信仰。
经院哲学家安瑟尔谟崇尚宗教信仰,相信神的存在。在《宣讲》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本体论论证”,从神的概念直接推出神的存在,认为神不仅存在于人们的思想中,也必然存在于现实中,从而为当时的“神权至上”的理论提供强有力的证据,捍卫了教权高于王权的政治主张,为罗马教会的世界统治进行辩护。与此同时,他还力图调和宗教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宣称人的知识、理性都来自神的启示。这些“教会至高无上”、“忠诚于教会”的思想观念,充分显示了宗教、理性与信仰之间的碰撞与沟通,深刻表明了希腊文明与犹太——基督教文明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更为重要的是,使基督教信仰逐渐走上了理性化的道路,至少使基督教信仰摆脱了一些宗教迄今没有摆脱的对“权威”的盲从与狂热。
托马斯·阿奎纳是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和神学家,他把理性引进神学,用“自然法则”来论证“君权神圣”说。托马斯·阿奎纳进一步认为,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统一体,必须有某种治理的原则和力量才能免于解体,而这个神奇的力量就是上帝。由此出发,提出教会的目的,是追求超自然的善即认识上帝,教会高于国家,世俗服从于教会,皇帝受命于教皇,政治隶属于宗教,其实质是维护封建宗教神学和教会的利益。
思想巨人马基雅弗利,摆脱神学的思想束缚,以“性恶论”为逻辑起点,提出了许多惊世骇俗的言论,但其目的是完成意大利统一大业,摆脱外国侵略,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尊严,其政治忠诚观主要体现在:
第一,君主必须取信于民。在《君主论》中,他指出,君主一方拥有一国之君的威严,拥有法律、朋友和国家的保护,除此之外,如果再拥有人民的忠心支持,那么任何人想要贸然地进行密谋的举动是不可能的。马氏反复告诫,君主必须设法博得人民的好感,否则当君主身处逆境的时候,他自己的安全就无法得到保障。他强调,政府必须保障个人财产和人身的安全作为最高的目标。这实际上隐晦地表达了,手段与目的之间的辩证关系,即君主只有依靠人民,重视分配给人民以利益,才能使臣民绝对效忠于自己。
第二,要建立一支忠诚的军队。他提出,评判良好军队的重要标准之一是“信义”。马氏对“信义”高度重视,这里的“信义”和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忠信”、“忠诚”几乎是同义。
尽管后世对马基雅弗利褒贬不一,但其政治忠诚思想处处蕴含了浓重的人文主义因素,彰显了其真切的救国、爱国、报国之心,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建立强大而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要求。
总的说来,中世纪是神治与人治混合、交融,教权与王权竞争、对抗的时代,人们在这一时代既要服从上帝的权威,又要求效忠于政府,使得中世纪的政治忠诚观在教会和国家的双重控制之间飘摇不定。到底是忠于上帝?忠于教会?还是忠于现实社会的公民国家、国王?这集中体现了在欧洲,传统的权力架构是从多元权力中心相互争夺、相互制约的;客观上反映了现实社会的种种矛盾,人们已从信上帝开始了对国家的疏远,个人利益服从宗教利益;表达了人们对现实社会进行改造的强烈愿望,对公正、平等、自由、民主的渴求。
(三)近代西方政治忠诚观。
近代西方主要指15世纪到19世纪上半期,欧洲主要国家经历的400余年的时间。近代西方政治忠诚观的主要基调是:政府的权力主要来源于公民基于对政府政治信任基础之上的政治权利让渡,政府与公民是一种“代理服务——信任委托”的政治关系。因此,近代西方政治忠诚观主要表现为,“忠诚于国家”、“忠诚于政府”、“忠诚于让渡权利的人民”等,这些理念对现代政治社会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霍布斯是英国理性主义传统的奠基人,也是近代第一个在自然法基础上,系统发展了国家契约学说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其政治忠诚观主要有:
第一,忠诚于国家。霍布斯十分重视对国家的研究,在《利维坦》中,霍布斯把国家比作“圣经”上说的力量巨大无比的海兽“利维坦”。指出公民必须忠诚于国家,服从于国家的法律、国家的权威,唯有如此,公民才能使自己人身安全得到较好的保障,并从国家中赢得他所需要的重要东西即权利。
第二,反对分权,强调绝对地忠诚于君主个人。霍布斯反对分权,主张立法、司法、行政、财政、军事、宗教等权力都应集中在君主一人手中。在他看来,君主应当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是一切法律的制定者和纠纷的仲裁者,臣民只能绝对服从君主,不能有任何的不满和反抗,否则被君主处死是合理的。
第三,保护公民的权利。霍布斯认为,保护公民的权利,使公民财富不断增加,促进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保卫和平,防止外敌入侵是国家元首必须履行的职责。这充分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符合英国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
英国政治学家洛克是第一个系统阐述宪政民主政治以及提倡人的“自然权利”的人,他主张捍卫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毋庸置疑,其政治忠诚思想主要体现在保护私有财产,实行议会制等方面。
第一,政府的目的是保护私有财产。在他看来,“无私产即无私权”,“人们遵守法律和服从政府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5](p75)洛克所谓“政府的目的是保护私有财产”的言论,实质上合乎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因为这其中的“政府”是指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财产”是指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因此,这一提法在当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第二,忠诚于给予政府权力的人民。洛克在《政府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政府的目的是为人民谋福利,必须忠诚于给予自己权力的人民。他倡导权力的分配,认为立法权、行政权、对外权都应受到人民的制约。
洛克的政治思想对后世的政治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他的思想在美洲、法国等地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
英国著名的哲学家休谟,从忠顺的起源、忠顺的限度、忠顺的对象,三个不同视角全面地阐述了“忠顺”的思想,并郑重地提出对执政长官的服从是政治义务。休谟指出,许诺或原始契约是政府忠顺的起源。执政长官的权威是建立在臣民约定服从的许诺基础上的。执政长官有命令的权利,公民有服从的义务。在休谟看来,服从政府是一种道德的义务,更是一种政治义务,他从许诺、公民自身的利益等角度,强调了服从政府的必要性,“人类交往的自由和范围完全依靠于对许诺的忠实。如果没有对政府的服从,那么在稳定财务占有、根据同意转移财务和履行许诺方面,都不可能执行正义”。p152
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卢梭有个重要的政治原则:政治不应与道德分离。他认为,一个国家若不能以德服人,就不能正常地发挥其功能,就不能建立对个人的权威。基于这一认识,其政治忠诚观,主要表现在如下两方面:
第一,主权在民的思想。卢梭认为,国家是民众的结合体,是一个公共的人格,民主国家是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每个公民都是国家权力的主人。卢梭声称,在民主国家中,主权属于全体人民,并为人民的“公意”所指导。他主张,任何公民都可以担任国家的行政官吏。这一思想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几乎对世界各国民主制度的斗争都有重要影响。
第二,臣民应当服从公意。他提出,“如若臣民拒绝服从公意,不履行他们对国家的义务,那么全体就应该强迫他服从,因为这是使每个公民拥有国家,从而保护他避免人身依附的条件,也是形成政治机器并保证它正常运转的条件。”[7](p27)由此可知,在卢梭看来,权利和义务是对立统一的,服从公意是每个臣民必须履行的义务,臣民只有尽其义务,才能实现其权利,维护其权利。
第三,捍卫自由是国家建立的目的。卢梭提出,政府应该排除多数人意愿的影响,捍卫自由、平等和公正。主张建立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主张自由平等,反对大私有制及其压迫;提出“天赋人权说”,反对专制、暴政。
近代西方政治家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以人性恶为假设前提,强调生命、自由、平等是基本的政治德行,把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看作政治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总之,政治忠诚理论的现代化、人性化是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从而确定了西方近代以来政治忠诚关系的基本价值与原则,架构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
综上所述,西方传统政治忠诚观与西方社会的哲学理念、价值观念、政治文化密不可分,历经了从城邦至上到神权政治,从世俗专制到民主国家的对象变迁,并逐步在价值层面上蕴含和发展了公平、理性、责任和民主等基本精神和政治理念,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人应该以一种开放的气度和世界的眼光,积极借鉴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使政治忠诚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政治伦理,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凝聚力量、凝聚智慧、凝聚共识的道德基础。
[1]李好.行政忠诚理论与实践[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
[2]姚介厚.柏拉图的城邦文明论和“理想国”设计[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0).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李建华,李好.中西方行政忠诚的思想渊源及其比较分析[J].船山学刊,2004,(4).
[5]洛克.政府论(下篇)[M].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11.
[6]休谟.人性论[M].张晖,编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
[7]卢梭.社会契约论[M].徐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