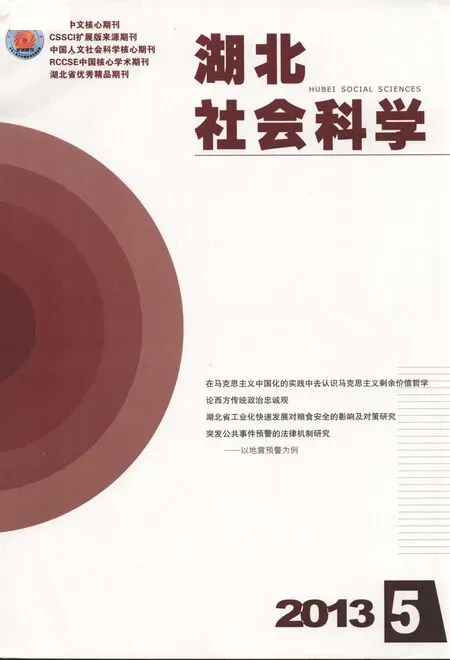非对称性阶级对抗、根本性解构与替代性规划
——论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战略理论
2013-04-10宋晓杰
宋晓杰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开封 475004)
非对称性阶级对抗、根本性解构与替代性规划
——论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战略理论
宋晓杰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开封 475004)
以自我价值稳定过程和拒绝工作为核心的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战略,以资本-劳动的分离辩证法和非对称性的阶级对抗为逻辑原型,融合了对资本结构的总体解构和对替代性社会形式的积极创建。在本质上,它是一个以活劳动-力量-欲望为核心的革命主体理论,是一个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的本源性和共产主义为本质的激进革命传统,也是一个以开放性、非连续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为基础的激进政治模式。因将革命的现实基础和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完全主体化,并立足对历史现象的经验描述,从历史本质论退回历史运作论,它既根本无法实现对历史之谜和历史本质的深层剥离,又无法充分说明政治的逻辑。
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革命战略;阶级斗争;总体解构;前景筹划
五月风暴革命性的乌托邦精神和文化启蒙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后福特制转型,为左翼思潮提供了批判资本主义新的反思起点和激进根基。加上1940年代产生于美国托洛斯基运动并于50年代解体的所谓“Johnson-Forest Tendency”提出工人自主和工人阶级自我运动,反对列宁的先锋政党思想。以此为背景,意大利的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Autonomist Marxism)19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开始兴起,以特洪迪、奈格里、维尔诺和克里弗等为代表。他们立足革命主体性话语,强调后福特制模式下劳动-工人阶级相对于资本-资产阶级的本源性、自主性和充足性,拒绝任何外在于工人运动的组织调解,重构传统左派以夺取国家政权为目的的革命政治学。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纳入全新视域,重估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构架和现代政治思想史的主流传统,并基于对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深入清算,力图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中揭示共产主义成熟的基本条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现代政治传统和革命图景,均作出了极富创见的理解,直到当代仍然对世界范围内的激进运动产生着巨大影响。其革命战略理论既力图批判、反思和解决正统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困境,又旨在寻求完全摆脱资本操控的本源性解放潜能和描绘替代性的前景规划,从而实质性地触及理论和现实层面的诸多关键问题。因此,对它的深入透视,对于完善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全景性认识,审视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和激进政治运动,具备重大价值。
一、革命战略的逻辑原型:资本-劳动的分离辩证法
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解中,资本和劳动往往表现为一种同质性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劳动总是从属于资本的统治逻辑,只是资本发展的动力因素,可以通过理性调节服务于资本的发展。对于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而言,重构劳动对资本的这种力量关系是其思想实验和政治活动的基本前提。他们“持续地关注劳动的力量”,特别强调劳动是“社会性自身的源泉,我们所有的社会关系都被编织在劳动材料之中”。[1](p6)特洪迪便以工人抵抗保持对资本策略优先性,试图将二者的关系建立在劳动一方的优先之上,坚持把工人阶级的斗争看作潜存于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我们以前也是首先看到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后才是工人的斗争。这是错误的。问题必须从上到下翻转过来,颠倒其两极,也要从开端重新开始:首先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2]奈格里持相同观点,“工人阶级,它的破坏,是最强大的力量——首要的是理性和价值的唯一源泉。……控制的形式越是完善,它的内容就越空洞;工人阶级的拒绝越是增强,它就越充满了理性和价值”[3](p118)。于是,活劳动和工人阶级成了价值和理性的唯一来源,资本主义的统治策略和自身的发展史,则表现为一种基于工人阶级斗争的政治性妥协、回应和重构。二者不是二元平行且相互独立的力量实体,分别指向阶级斗争的“自变量”和“因变量”[4](p101)。相反,资本必须借助于劳动,才能实现自身的结构化,劳动内在于资本之中,并构成资本结构解体的根本动力,最终实现与资本的彻底决裂,以谋求自身利益、需求和欲望的完全释放和自我实现。于是,工人阶级的解构和资本主义的重构、工人阶级的“欲望政治学”和资本主义的“禁欲主义”、工人阶级替代性的革命规划和资本主义同质性的化约机制,一开始便作为非对称性的对抗模式,存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中,成为资本主义发展无法回避的固有限制。这彻底颠倒了资本和劳动的力量关系,并以工人阶级-资产阶级非同质非对称的阶级对抗,拒绝辩证的对立关系决定革命主体性模式的传统理解方式。这既体现出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立足工人阶级重构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决心,又将阶级斗争视为历史运行的根本动力。
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之所以能够剥离资本主义的历史之谜,关键在于深刻指认了资本强化对劳动剥削的地方恰恰蕴含着颠覆其统治并实现解放的现实可能性。资本的界限在于资本自身,“资本把必要劳动时间作为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把剩余劳动时间作为必要劳动时间的界限,把剩余价值作为剩余劳动时间的界限;与此同时,资本又驱使生产超出所有这些界限,因为资本把劳动能力单纯作为交换者,作为货币与自己相对立,而把剩余劳动时间作为剩余价值的唯一界限,因为它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5](p406)资本的本性需要通过不断向外扩张来破除自身的内部限制,而资本主义的灭亡正根植于其生产方式的这个固有矛盾,“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6](p269)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内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之中,始终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其必然性和暂时性也只能由这些界限来揭示。
正是从劳动内在于资本之中且反对资本的逻辑出发,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奠定了其革命战略理论的逻辑原型和基本原则。在他们看来,劳动是“所有财富的总体性力量,是生产的唯一潜能和唯一的劳动力和社会性的活劳动”,它既在开放的创构过程中构成价值的唯一来源,又是抵抗资本之总体化控制的唯一领域,并指向超越资本主义交换价值体系的“替代的革命体系之可能性”。[7](p151)劳动概念作为“价值的问题框架”,“和价值相互暗示对方:通过劳动我们可以理解价值创造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劳动作为解释以经济和文化形式贯穿整个社会范围的价值生产之社会分析而产生效用。它应该首先与当代很多把表演(Performance)或操演性(Performativity)①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便认为,表演不同于操演性,前者假定了主体的存在,后者则反对主体概念,而关注主体的建构过程。例如,对性别的判断往往描述在一定的社会规则和规范的无意识制约下进行的主体创建机制,只能体现操演的性质。当作社会分析和社会实践范式的企图区分开来:尽管表演强调预示实践或散漫实践的社会重要性,但我们使用劳动则集中关注价值的创造实践”,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指向一个首要的和根本性的替代方案:它既把自身当作反对资本主义的颠覆力量,又是另一社会的命题或断言。”[8](p7-8)在此,劳动和资本的分离辩证法,将马克思劳动理论的问题框架揭示为基于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之本源性的革命政治学,即超越资本逻辑筹划另类社会的政治构想。
马克思指出,排除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把劳动视为单纯的主体性创构力量或一切财富和文化的源泉,都不啻为“资产阶级的说法”,“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9](p5)从本质上看,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将劳动重构为阶级斗争的革命话语和获得解放的现实根源。这过度突出了主体在塑造历史过程中的本体地位和阶级斗争在历史进程中的根本动力,从根本上消除了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和本质规律,简化了复杂的历史运行机制,从而带有浓厚的唯意志论嫌疑和乌托邦色彩。
二、自我价值稳定过程的革命主体性内涵:内生性对抗和替代性创构
基于劳动-资本力量关系的根本颠倒,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逐渐形成了以“价值稳定过程”(Valorization)和“自我价值稳定过程”(Self-Valorization)的对抗逻辑为核心的第一重革命战略。
在他们看来,价值稳定过程源自马克思的《资本论》,意指资本通过稳定价格机制在劳动中创造剩余价值的过程,即“根植于剩余价值的抽取和生产之上的价值的整体社会结构”[1](p264),抽取和占有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构成其基本特征。它具体表现为对劳动自主性的极权主义控制,以使其成为资本的附属物。这“是持续的极权主义过程,不知道限制和停止。劳动的自主性好像在所有情况下都被归结为极端限制……在价值稳定过程中,资本征服了极权主义之命令的主体性。”[10](p76)自我价值稳定过程则出自马克思的《大纲》(即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指向价值的“替代性社会结构”,它基于“生产共同体的集体需求和欲望”,常被用来描述“相对独立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国家控制,并以地方性和社区性的社会组织和福利形式的实践为基础”,也总是被构想为“创建内在且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性自主性的集体主体性”。[1](p264)它立足工人阶级立场,构成创建逃离资本控制之替代性社会构想和生命形式的基础,并指向超越资本结构且只在工人阶级中才存在的解放力量。
自我价值稳定过程旨在解构资本主义的结构总体,并筹划工人阶级的自由解放,其“集体实践决定了主体意识的统一。……无论从客观方面还是主体方面,我们均无选择,只能从无产阶级自我价值稳定过程的独立观点去重建革命前提之复杂性。”[7](p236)它把自身呈现为一系列非连续性的断裂、飞跃和变革,在资本重构过程中看不到与资本力量相关的连续性,反而在解构资本体系的空间中,充分展现反叛力量的持续增长和不断扩张。“这是当今工人斗争借以直接攻击剥削体系及其政治体制的过程。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化使工人阶级能够将共产主义战略(叛乱和消灭国家)的多样时刻转变为一个过程,并将其统一为规划。无产阶级的自我价值稳定过程便是其综合的、整体的和生产性的特征。”[7](p234-235)因此,在它之中,无论在制度层面还是经济重组方面,绝对不存在政治外在调解的可能性,只有对抗的、分离的和变革性的唯一内生性解答。作为与解构充分连接的“积极的否定力量”,其运行方式是创构性的,即“狙击手、破坏者、缺席者、越轨者和罪犯的连续行动”,“只有财富和贫穷之间拒绝和解的关系强度,……分离正是所追求的,但是它必须在冲突的强力意志中被表达;断裂发送反对现实之解构意志的传递者,欲望竭力使自身成为绝望”[7](p259)。实现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直接源自这个分离过程,“欲望承载着暴力,组织伴随着创新。社会转型的方法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是通过无产阶级自我价值稳定过程,消灭国家和实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体取代的战争……是内在于无产阶级自我价值稳定过程之集体增长的民主和自由的方法。……无论如何,自我价值稳定过程的破坏并不终止于我们即将建立的共产主义专政规律,……而是一个关于现在和未来我们都与共产主义联合的自由规律。”[7](p260-261)因此,立足工人阶级主体性的自我价值稳定过程,始终指向与资本主义非同质的差异,充满了非连续性的断裂和革命性的替代。
由此,奈格里把生产力视为无产阶级的独有属性。它是产生于其动态的形成和重组过程的集体力量与本源性的新趋势,并使劳动力变为创造力。它“既表现为动态的本质、内部的冲突和积极的筹划,又是……回应无产阶级需要以使它们进入自我价值稳定过程之生产网络的能力”,也“在最彻底对抗的独立性中,培育了无产阶级自我价值稳定过程的阶级能力……其创新性的品格意指规划多样性的解答”。[7](p268-269)总之,客观主义和经济主义的理解方式绝不适用于自我价值稳定过程。它既具备革命主体性话语的充足政治内涵,又使资本主义发展史变成“无产阶级自我价值稳定追求的对立面和对它的回应——在与自我价值稳定之效力的关联中的自我保护、恢复和调整的活动”[7](p241)。它超越了单纯反抗资本主义的否定立场,是无产阶级积极筹划自身解放、需求和欲望的激进革命:“自我建构的自我界定和自我决定过程”。[11](p129)从价值稳定过程转向自我价值稳定过程,充分展现了工人阶级脱离资本主义控制并宣告自身自主性的发展趋势。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这与资本的结构总体“没有相似性,也没有语言、逻辑和象征的可转译性”,[7](p236-238)二者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主体力量和组织模式,彼此之间无法通约。
从逻辑取向上看,自我价值稳定过程与德勒兹关于欲望生产的身体政治学极为相似。与萨特和叔本华将欲望视为匮乏但亟待满足的需求不同,德勒兹则将它视为具备生产性的力量和能量的充溢,旨在通过“增值、并置和分离”,以及积极的差异性及其自由生成,“将政治行为从所有统一的和总体化的妄想中解放出来”。[12](pxiii-xiv)自我价值稳定过程之革命意志和欲望的自我充足,解构压抑欲望和差异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获取工人阶级需求的自我增值,在资本主义内部颠覆资本主义自身。于是,“共产主义将出现在资本主义的核心,作为社会形式,它既回答了所有基本的人类需求,又提高和强化了我们的欲望”,革命表现为“对愉悦的集体追求”的“欲望机器”,它不是“基于拒绝资本主义提供的愉悦来断定革命斗争的禁欲主义”,而是把它据为己有,并“强化为共同分享的集体财富。”[1](p7)
实际上,自我价值稳定过程不过是革命主体性和阶级斗争的另一个称谓,即本体性的解放潜能和积极的创构力量,激进革命的社会基础和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被其完全主体化。它立足对历史现象的经验描述,忽视了客观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对主体的根本制约,在其革命政治内部悄然设置了去革命的机制,从而从历史本质论退回历史运作论,根本无法实现对人类社会历史之谜和历史本质的深层剥离。
三、拒绝工作的革命图景:总体解构和前景筹划
对于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而言,劳动和工作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对抗实体,前者既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颠覆力量,又是积极创建替代性社会形式的解放潜能,后者则借助某种外在的政治调解机制来实现对工人力量的严格规划和对自我价值稳定过程的重新整合,以获得资本结构的平衡、稳定和发展。他们往往将资本界定为“通过商品形式强加工作的社会体系”[13](p82)。“工作违背了发展人性和客观环境的诺言……已经成为非理性的社会再生产和扩大了的社会限制之交叉点。束缚——非理性的社会限制——因而处于在工作过程中形成的所有主体意识的基础部分。建立限制和监察的集体主体性是资本主义工作设置的首要指令。自我监察和怀疑阻止了任何逃离的暗示,并先于任何质问体系政治的、法律的或道德的合法性而行动。没有人可以从这个盲目而荒谬的资本主义合法性中逃离。工作的每一个场合和后果都由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指令所‘超越决定’;每一个行动都为巩固价值和权威的等级制度。”[14](p8)因此,基于劳动的本源性与自我价值稳定过程,彻底“拒绝工作”(Refusal ofWork),构成其革命战略的另一核心维度。
克里弗指出,“资本主义是一个拥有两种主体性的社会体系。一个主体(资本)通过强加工作和剩余工作,控制另一主体(工人阶级)。这是在资本主义价值增值的界限中限制人类发展的辩证法。因此,作为独立主体的工人阶级之核心斗争,只能通过拒绝工作打破资本主义控制。这个拒绝逻辑是对抗的分离逻辑,实现侵蚀和摧毁资本的辩证法。在这个解构空间中,革命阶级构建了独立的筹划——自身的自我价值增值。革命既推翻资本,又建构新社会:共产主义……新多元社会之新生产方式的基础。”[10](pxxvii)然而,在现实性上,一方面,资本主义工作极其严格地调控了劳动的革命潜能,并成功将共产主义话语归结为操控技术:“劳动带来自由”,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变种甚至大力宣告复苏和重建,尽管它们只是通过技术手段获得的辅助目标。社会革命的‘伦理’反而已经变成背叛解放的噩梦,未来景象承载了一个可怕的惰性”,二者都因与资本主义的藕断丝连,共同使共产主义成为禁忌,只能“屈服于工作导致的心灵创伤”,以及“被动地假定再投资战略是最少压迫的规划形式”,资本主义的解体似乎伴随着工人阶级自身的解体。[14](p9-10)事实上,拒绝工作作为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只能意味着对工作目标、社会生活模式、权利-自由和现存状况的彻底改造,确切地说,“是对作为结构化生产关系束缚和扭曲创构性力量之资本主义命令的拒绝,因而也是对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生产力或创造力的确认”。[1](p263)
(一)否定性解构和创构性筹划:“拒绝工作”的双重面向。
拒绝工作应具备互为补充的双重面向:否定的解构性和肯定的建构性,“既是反对工作之科学组织的否定表达,也是需要重新占有生产和再生产之社会机制的肯定表达”[1](p84)。前者侧重对资本主义工作体系和工作价值的彻底解构,后者则指向创构性的革命实践,旨在重新型构现存的生产关系,充分展现无产阶级的自身需求和共产主义的革命前景。作为激进的革命主体性模式,它以直接的生产性行动,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施以总体的颠覆和破坏。同时,它又基于“共产主义的战略、战术和筹划”得以重构,并构成自我价值稳定过程的客观基础。于是,“利润率的下降、价值规律的危机和价值规律内在于命令之无差别中的重新阐释,都是其直接(既非连续也非同质的)结果。另外,其连续的效果只能在资本辩证法的反面被发现……成为理解自我价值稳定的钥匙。”[7](p270)
首先,拒绝工作是自我价值稳定过程的一个内容和环节。它把阶级分离的过程和承载“解构-解放辩证法”的阶级斗争,当作自我价值稳定过程的主导形式,同时也揭示出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总体解构创建新集体主体性的可能。[7](p271-272)其次,拒绝工作是自我价值稳定过程的尺度,是衡量社会转型的基本标准。“个人和总体劳动时间的降低,否定地衡量自我价值稳定过程的进步……献身于无产阶级社会自由之再生产的社会有用劳动的增值,则肯定地衡量其进步”,同时,“专注于工作日的普遍缩减,将它与理论的和实践的、科学的和经验的、政治的和管理的以及隶属阶级斗争之连续革命的创新过程相连”,“以拒绝工作衡量劳动的生产性,实现了对资本控制之生产性命令的彻底去魅,否定了仍然是剥削劳动之生产性的可能,并引入使体系失去平衡的标尺——关于自我价值稳定过程日益完善的革命强度之尺度”。[7](p272-273)它在资本主义内部纳入工人阶级的自主性,只能表现为革命之量的尺度和自由生命之质的尺度,从而为判定社会转型提供了根本准则。
拒绝工作包含三个基本主题:拒绝最具异化的劳动、拒绝资本主义的工作、变革生产方式以充分释放无产阶级的创造力,具体展现为阶级斗争的逻辑脚手架,“基于它的实践及其理论的/实践的拓展,动力枢纽应被设定在直接生产中的工人先驱和非直接生产中的无产阶级先驱之间。”[7](p273)它既是“解放的政治学的开始”,也意味着“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共同体”[15](p204)。作为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它“建构主体——因为它在世界中筹划,因为它创建生产方式”[10](p167),这超越了任何意义上的乌托邦幻想,并显示出“一个本质的、集体的、去神秘化的共产主义工作”[10](p165),即消灭工作的后工作。
(二)彻底的决裂和工作的解放:“拒绝工作”的问题意识。
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中,将历史唯物主义指认为以使用价值为核心的生产本体论,认为它创建了劳动和生产的政治经济学拜物教,具体表现为马克思将人类的劳动本质当作自然化的本体,并相信它可以在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中得以实现,因而,“工作的神圣化从一开始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战略的秘密罪行”[16](p36)。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主义理想以劳动和生产的价值稳定过程为基础,将社会关系和社会作用机制的多样性和充足性,完全隶属于工具理性的生产性逻辑和功利主义目的,从而表现出主体性缺失的禁欲主义特征。无疑,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这种批判路径存在极大的相似性。它力图清算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中的客观主义范式,恢复革命主体性话语的逻辑优先,并立足脱离客观历史情势限制的阶级斗争来揭示历史嬗变过程,彻底走出基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矛盾运动的分析构架。它将历史发展过程彻底主体化为基于阶级对抗和纯粹创构性的动态趋势,确实存在唯意志论的嫌疑和相对主义的风险。然而,事实却在于,历史发展绝不表现为基于生活世界内在矛盾的缺失,而走向不确定而偶然的未来视域。
正统马克思主义一般都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集中在生产关系的私人占有制和生产力的无限发展的基本矛盾之上,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最终构成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桎梏。于是,共产主义只能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力潜能的充分释放,它既使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发生根本转变,又将生产方式和劳动过程变成自由的过程。列宁指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仍然存在两个阶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者作为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为保证后者的实现,必须对资本主义有所保留,资本主义的某些工厂法则(特别是泰勒制的生产方式)仍然有效,并且需要铁的工作纪律消除小资产阶级的懒惰、自私和无政府状态。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列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过于保守,仍然保留了工业生产的基本形式和资本主义不完整的生产方式,其对经济增长、工业进步和工作伦理的认同,重复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经济现代化过程的确认。社会主义似乎强化了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则被抽象地想象为对社会主义的单纯超越,从而在本质上实为发展了的资本主义。列宁虽然充分肯定了无产阶级劳动建造世界的能力,但仍然依赖价值稳定过程和生产力的逐步发展,结果将共产主义化约为“与由资本主义引发的工业生产方式相同的政治管理和经济调节新模式”[17](p9)。事实上,这种强调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根本决裂的方式,遮蔽了马克思关于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思想的科学意义: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所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恰恰构成实现共产主义的现实基础和历史条件。同时,作为过渡阶段的社会主义虽然部分保留了资本主义的运行特征,但其实质在于重新占有和规划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整体,最终真正实现人类解放,绝非对资本力量的强化。
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从经济主义和决定论中拯救出来,它立足异化劳动批判,恢复人之主体性和个体的优先。这与正统马克思主义重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强调社会进步、社会和谐和社会正义根植于工业和科学发展明显不同。弗洛姆力图筹划工业主义“机械的-唯物主义的精神”之人道主义的替代方案,认为马克思哲学的目的在于充分实现个体主义,反对工业文明导致的人之自动化和非人化,但仍然把劳动当作基本的人类价值和人类本质。这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之处在于,“劳动对社会生活建构性的中心是以资本主义为特征,并形成了抽象统治模式的最终基础。”[17](p361)因此,人的自我实现和工作行动不可避免地连接在一起,工作是人类能量最富意义的表达和愉悦的真正行动,不仅是获得目的的手段,也是目的自身,只有借助它才能发展人自身。弗洛姆确认了未被异化的劳动,它使工作的世界转向个体生产者可自由控制的合作过程,于是对工作的积极参与成了个体自我实现和获得自由的首要方式。显然,他不但没有拒绝工作,反而强调超越异化劳动的愉悦的工作,以浪漫主义方式试图恢复工作的尊严和价值。在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看来,一方面,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注重个体生产者的主体地位,浪漫地怀念早期资本主义的手工业模式,这与马克思对阶级斗争、生产合作和机器大工业的强调完全相反。另一方面,与筹划工作的解放不同,它仅仅关注从工作中的解放,只能将客观的历史趋势转变成“人类本质的有机展开”,[10](p154)最终仍然部分地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同谋。虽然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正确指认了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本性,但同样未能提供实现工作解放的科学途径和现实基础,仍然将革命固定在某个抽象的政治时刻和虚假的姿态。
总之,以自我价值稳定过程和拒绝工作为核心的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战略,是以一个以活劳动-力量-欲望为核心的革命主体理论,是一个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的本源性和共产主义为本质的激进革命传统,也是一个以开放性、非连续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为基础的激进政治模式。虽然它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和激进革命政治作了极富创造力的理解和反思,更多地看到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对创建新主体性模式的积极意义,却无视这种改变对劳动-欲望-革命所造成的负面效应,无法真正激活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前途蕴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之中的理论张力。它过度简化了政治过程的复杂性,无法充分说明政治的逻辑:反抗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自动运行的自然的自发机制”,而是源自“复杂的社会建构,拥有外在于自身的可能性条件”。[18](p28)
[1]Paolo Virno&Michael Hardt eds.Radical Thought in Italy:a Potential Politics[C].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nesota Press,1996.
[2]Mario Tronti.“Lenin in England”,1964,http://www. marxists.org/reference/subject/philosophy/works/it/tronti.htm.
[3]Antonio Negri.“Working Class Sabotage and Capitalist Domination”[A].Working Class Autonomy and the Crisis:Italian Marxist Texts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 Class Movement:1964-79[C].Red Notes ed.,London:Red Notes&CSE Books,1979.
[4]Finn Bowring.From the Mass Worker to the Multitude: A Theoretical Contextualisation of Hardt and Negri’s Empire [J].Capital&Class,2004,(83).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Antonio Negri.Books For Burning:Between CivilWar and Democracy in 1970s Italy[M].New York:Verso,2005.
[8]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Labor of Dionysus:A Critique of the State-form[M].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4.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Antonio Negri.Marx Beyond Marx: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M].Massachusetts:Bergin&Garvey publishers, 1984.
[11]Harry Cleaver.“The Inversion of Class Perspective in Marxian Theory:From Valoristion to Self-Valorisation”[A]. Open Marxism(Volume II):Theory and Practice[C].W.Bonefeld,R.Gunn,and K.Psychopedis eds.,London:Pluto,1992.
[12]Gilles Deleuze,Felix Guattari.Anti-Edip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Minnesota Press,1983.
[13]Harry Cleaver.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M].Leeds and Edinburgh:AK Press and Anti/Theses,2000:82.
[14]Felix Guattari,Antonio Negri.Communist Like Us[M]. New York:Semiotex(e),1990.
[15]Michela Hardt,Antonio Negri.Empire[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16]Jean Baudrillard.The Mirror of Production[M].St. Louis:Telos Press,1975.
[17]Moishe Postone.Time,Labor,and Social Domina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s Critical Theory[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18]P.A.Passavant,Jodi Dean,eds..Empire’s New Clothes:Reading Hardt and Negri[C].London:Routledge, 2004.
责任编辑 张晓予
B089.1
:A
:1003-8477(2013)05-0014-05
宋晓杰(1980—),男,哲学博士,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奈格里与拉克劳政治本体论比较研究”(12CZX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