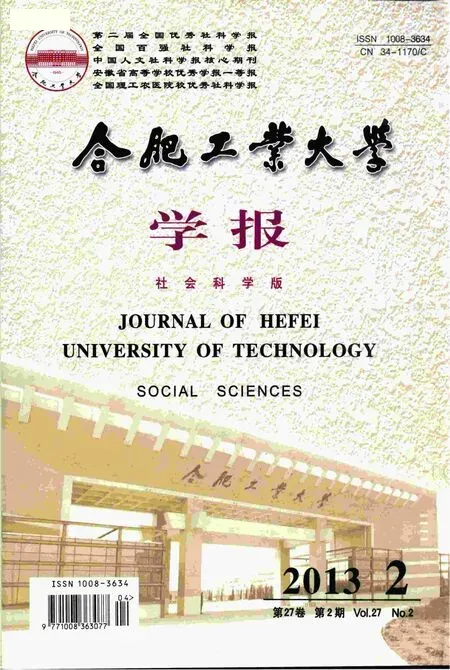安徽书院与桐城派的学术传承及影响
2013-04-07方宁胜
方宁胜, 朱 扬
(1.桐城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安徽 桐城 231400;2.安徽大学 历史系,合肥 230039)
书院是中国古代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书院的发展,得益于官方及民间多种社会力量的交互作用与共同推动。清代安徽书院在宋元明时期曲折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士农工商的共同努力和官方民间的合力推进,逐渐走向鼎盛。几乎贯穿整个清代、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桐城派,与书院教育尤其是安徽书院教育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桐城派重要作家刘大櫆、姚鼐、沈廷芳、王灼、方东树、梅曾亮、管同、刘开、徐璈、光聪谐、吴赓枚、徐子苓、方宗诚、吴廷香、汪宗沂、马其昶等曾在安庆敬敷、歙县紫阳、凤阳淮南、庐江潜川、庐州庐阳、亳州泖湖、宿松松滋、望江大雷、泗县夏邱、祁门东山等各大书院掌教,桐城桐乡书院的创建更凝聚了方东树传人戴钧衡、文汉光等人的心血。可以说,桐城派促进了安徽书院的兴盛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安徽书院为桐城派的传衍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场所和人才培养的基地,这种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关系值得人们认真探讨。
一、桐城派与徽州书院
管同曾言:“安庆东接江东。……其江南过一郡,曰徽州,实宋朱文公故里。之二者,文之源也,应试之辞所从出也。”①(清)管同著:《因寄轩文集补遗·刊刻敬敷书院课艺序》,清道光十三年管氏刻本。由于地缘关系,安庆与徽州自古交流频繁,人文相近,风气相通。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九月十五日,桐城学者、理学名儒方学渐主持新安六邑大会,“聚讲数日,锡以教言。临别复以桐川《崇实会约》授六邑会友。”此后,“紫阳、还古诸书院,遵其成约,定为章程。凡郡邑大夫临会,以是图呈览,咸乐取则焉。”[1]百余年后,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桐城派三祖之一的刘大櫆任黟县教谕,数年后应聘主讲歙县问政书院,并写下《问政书院记》一文。在此期间,饱尝人生艰辛的刘大櫆感受到久违的乐趣。他说:“黟、歙邻近,歙有多英贤,敦行谊,重交游,一时之名隽多依余以相为劘切,或抗论今时之务,注念生人之欣戚,慨然太息,相对而歌,盖余生平之乐无以加于此矣。”[2]58检阅《刘大櫆集》,发现与其交流密切者不下十数人,其中著名者有:
吴定(1744-1809),字殿麟,号澹泉,歙县人。少研经学,刘大櫆入黟,遂从之习古文辞,朝夕相从,孜孜不倦。吴定为文严于法[3]。刘大櫆老归枞阳后,他先后五次渡江拜望。刘去世前半年,虽已病卧在床,但见吴定前来省视,仍强撑病体,勉力为其讲说,并出示自己的文章与其商定去取。刘大櫆曾为其父吴阆撰《吴君墓志铭》,[2]254-255吴定也在恩师辞世后,撰写《海峰先生墓志铭》和《祭海峰先生》两文,极尽赞美之词。著有《紫石泉山房文集》12卷。
程晋芳(1718-1784),字鱼门。歙县人。少问经学于从叔廷祚,后从刘大櫆学古文,与商盤、袁枚唱和诗文,才情丰蔚,诗文并擅。经史子集、天星地志、虫鱼考据,俱能研究[3]。著有《勉行堂文集》6卷。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所引“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之言,即出于程晋芳和历城周永年之口[4]114。
程瑶田(1725-1814),字易田,一字易畴。歙县人。早年从江永精研经学,后与刘大櫆交,“旦夕相从”。刘大櫆称“其所为诗歌,摅词朴直,而寄兴深至,尝谓其有陶潜之风。易田固信余,余亦甚重易田也。”[2]58欣然为其诗集作序,后又撰《程易田琴音序》以赠之[2]50-51。
金榜(1734-1800),字蕊中。歙县人。少有大志,工文词,以才华为天下望[3]5532。从江永学经,与戴震、程瑶田同学[3],复从刘大櫆学古文。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著《礼笺》10卷。刘大櫆曾与之共游黄山,并为其祖父撰《金府君墓表》[2]。
汪梧凤(1726-1772),字在湘。歙县人。好读书,藏书极富。梧凤初识刘大櫆时,已为学官名弟子,为探求为文之秘,拜入大櫆门下,得益良多。其祖父汪景晃墓志铭即为刘氏所撰。有《松溪文集》传世,其中《送刘海峰先生归桐城序》真情洋溢,甚为感人。
吴绍泽(1736-1788),字惠川。歙县人。少与戴震、金榜、程瑶田交往,后师刘大櫆学古文辞,声闻燕越吴楚之郊。刘大櫆为其祖父撰墓表,为其母撰墓志铭,称赞“绍泽恂恂为儒者,明圣人之道,能文章,母夫人之教也。”[2]277
除了上述诸子,刘大櫆的好友兼弟子还有张伦发、方晞原、郑用枚等。与他们的密切交往,也激发了刘大櫆的创作热情,他在徽州时所作文章约占文集的五分之二。虽然徇人之请所作居多,固然难称佳作,但正表明了当地人对刘大櫆的倾慕,以及他在徽州良好的人际关系。继刘大櫆后,他的弟子姚鼐也曾一度主讲徽州。那是乾隆五十二年(1787)八月五日,姚母陈太恭人病逝,姚鼐要为母守孝,遂辞去敬敷书院教职。次年,由安徽抚藩推荐,新安守延主徽州紫阳书院[5]391。姚鼐因需买山葬亲,资金不足,便应聘前往。又因畏惧歙县山险,他在紫阳书院任教不到两年就回到故里,此后不复入歙。姚鼐曾忆及这段短暂的执教生涯,心中不无遗憾:“余始闻方晞原之名自戴东原。东原为言新安士三:曰郑用枚、金蕊中及晞原也。蕊中在京师,与相接最久;用枚、晞原之文,尝得读之,而不识其人。及晞原殁之前一年,余主紫阳书院,用枚以乡试去里不得见,得见晞原,果君子。然以事促归,不及造其灵金山居也。其后余不复至歙,而晞原、用枚相继丧矣。”[4]
姚鼐与徽州学人在学术宗尚上的异趣,可能是他执教紫阳书院为时甚短的原因,但这并不妨碍他与当地学者平等交流。其中最让人称道的是他与吴定(字殿麟)的友情,两人同为刘大櫆的入室弟子,当姚鼐初主梅花书院时,“会殿麟亦有事扬州,附鼐舟,于是相从最久。其为人忠信质直,论诗文最严于法。鼐或为文辞示殿麟,殿麟所不可,必尽言之。鼐辄窜易或数四,犹以为不,必得当乃止。”[4]在姚鼐看来,江永、戴震治汉学,只在于考证文物训诂而已,而吴定锐意深求义理,其文其学立志高远,高于今世,其才虽未必能与其志相副,却不失为当代异士。
姚鼐离开徽州后,继之而往的桐城文士有王灼、吴赓枚等。王灼是刘大櫆的弟子,受古文法,八年之久,刘大櫆在桐城门人中以王灼名气最大。他的“古文冲裕和平,精深温厚,诗文力追往哲,得其精华,味淡声希”[6]。曾主讲东山书院,晚归祁门,旧时弟子复迎之讲学。吴赓枚为姚莹的挚友,晚年“主讲徽、歙、安庆书院,教士论学一宗朱子,学者称春麓先生”。[7]
咸丰元年(1851),姚鼐的高徒方东树以八十高龄往主祁门东山书院。此前,他曾历主廉州海门、韶州韶阳、庐州庐阳、亳州泖湖、宿松松滋各书院,著书立说,文名颇盛,却身无长物,家境贫寒。是年,他的学生、江苏句容人唐治从桐城移任祁门,请其出掌祁门东山书院,以赡朝夕,方东树欣然应允,作诗为谢,云:“朽老精力尽,残生与邻鬼。八十事远客,匍匐井上李。弃隶一世休,成佛七事佹。亦知死道路,无殊在屋里。动相犹未灭,讵免拖泥水。寄谢敬昭州,招魂觊伊迩。”①(清)方东树著:《考槃集》卷二《将赴祁门东山主讲先寄唐鲁泉明府兼示文生钟甫》,清光緒四年《方植之全集》本。二月初,及门弟子十余人为他以及即将赴广西参与赛尚阿军事的姚莹饯行,地点设在友人光律原的遂园。他又作诗两首答谢,曰:“共道衰慵行路难,都忘惜别转余欢。共将小鲁齐名义,敢比为言海水观。”“国子先生老亢颜,招予进学只欺谩。贪言欲报齐桓好,多恐缁衣愧授餐。”②(清)方东树著:《考槃集》卷三《咸丰元年二月将赴祁门东山书院讲席及门诸子凡十人共饯余及姚石甫于光氏之遂园并作为序文各赋诗以宠行余深怀愧恧作二诗答谢》,清光緒四年《方植之全集》本。因为年纪太大,方东树此次特地携门人文汉光、甘绍盘同行,讲学之余,时与门人饮酒论学。“暇日无事,因思谢太傅隐东山,左思、孙兴公皆言经始东山,而五祖居黄梅传法六祖,号东山法门。感此数事,故遂为一诗以见意。”诗曰:“一鸿天首邈难攀,楚越殊观任等闲。我更法门开五祖,高名殷谢欲齐删。”③(清)方东树著:《考槃集》卷三《东山书院题壁》,清光緒四年《方植之全集》本。
虽然方东树临行前,他的弟子们以“临行不知老大身,他日归来卜无恙”相期,④(清)戴钧衡著:《味经山馆遗诗》卷一《偕诸子饯植之师石甫丈于遂园时植之师往祁门主讲东山书院石翁奉命赴粤西军》,清光緒三十年刻本。但他毕竟年已八旬,身在异乡,案牍劳神,纵是微疾亦足以将其击倒。5月24日,他偶感风寒方二日,即告不治,其丧事由唐治经理,次年春归葬桐城。方东树以授徒为生,最终逝于书院,在他的身上,典型地体现了桐城派作家的职业特点和价值取向。
二、姚鼐与敬敷书院
桐城派是一个职业化色彩浓厚的文人群体,其主要特征即是作家众多,传承有序。它的传承大体有家传、授徒、私淑和书院教育几种形式。戴名世、方苞以授徒为主,刘大櫆则授徒与书院讲学并行,姚鼐则以书院讲学终身。姚莹说姚鼐壮年辞官,“既还江南,辽东朱子颍为两淮运使,延先生主讲梅花书院。久之,书绂庭尚书总督两江,延主钟山书院。自是,扬州则梅花,徽州则紫阳,安庆则敬敷,主讲席者四十年。所至,士以受业先生为幸。或越千里从学,四方贤隽,自达官以至学人,过先生所在,必求见焉。”[7]作为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和主要开创者,姚鼐溯源以建文统,讲学以立门户,揭旗树帜,开宗立派,其历时绵长、影响巨大的书院讲学生涯就是最坚实的依托。
姚鼐从京师告退后次年,即乾隆四十一年(1776),应好友朱子颍之邀主讲扬州梅花书院。此后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应邀来到距桐城百余里的安徽省治安庆,主持敬敷书院。该书院创建于清顺治九年(1652),时任江南省操江巡抚李日芃为振兴教育,个人捐银2000两,创办了一所书院,附设义学两所,并以自己的名号命名为培原书院。雍正十一年(1733),朝廷下令各省在省城设立大书院,办学经费由藩库拨付。乾隆元年(1736),朝廷下旨明确省城大书院地位相当于“古侯国之学”,培原书院遂成为全省高等教育机构,院名也改为敬敷。①(清)王毓芳等编:《怀宁县志》卷十二,清道光五年刻本。“敬敷”一词,语出《尚书·舜典》,意为恭敬地布施教化。此后的敬敷书院均由官府操办,书院山长由巡抚亲自选聘,山长同时总领书院日常事务。姚鼐此次担任山长,为时八年。在这期间,他除了继续校订从掌教梅花书院时就已开始编选的《古文辞类纂》外,主要精力都花在教书授徒上。
清代书院官学化程度较前代更加提高,几成为科举的附庸。作为一省书院的山长,姚鼐自然重视时文写作。在他看来,时文与古文关系紧密,时文也是古文的一种,如果用古文之法来写时文,时文也就成为古文。既然科举试以时文,老师教授时文就是职责所系,因此,姚鼐说“应科训徒,不得弃时文”②(清)姚鼐著:《惜抱先生尺牍》卷四《与管异之同》,清宣统元年小万柳堂重刊本。。为了满足讲学需要,姚鼐结合自己的科举经历和教学实践,编刊了《敬敷书院课读四书文》、《惜抱轩课徒草》、《惜抱轩外稿》和《惜抱轩稿》。他把这些时文集遍发生徒,希望他们揣摩学习,以博取现实功名。
为了让生徒掌握古文精要,了解时文技法,姚鼐设定了骈文与散文、古文与时文两大分野。他说:“文家约有二派,自西汉流而为唐宋八家,此一派也。”“自东汉沿至中唐以前,此又一派也。”③(清)姚鼐著:《敬敷书院课读四书文》卷首《序目》,清道光十三年陈用光序本。他认为,前一派主古文,后一派主骈文,而尊古文薄骈文是姚鼐终身不易的法则。这一点在《古文辞类纂》中得到充分体现,其以古文为正宗的思想和意识,影响了此后近二百年桐城派发展方向。与古文、骈文的区分相呼应,姚鼐又对时文的品格进行了详细辨析。他认为明代正(德)嘉(靖)之文出于古文,明代隆(庆)万(历)之文和(天)启(崇)祯云间诸君之文出于骈文,④云间诸君,即云间派。指明清易代之际一个地域性、家族性特征十分突出的文学流派,诗学以汉魏盛唐为圭臬,词学则胎息花间、南唐、北宋,作品师心重情,刺讥现实。代表人物有陈子龙、夏完淳等。参见刘勇刚著:《云间派文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各自为派。正嘉之文虽好,隆历以下亦有优秀之文,其长处在于清真雅正,故此姚鼐甫一到任,即着手编选《敬敷书院课读四书文》。以方苞所选《钦定四书文》为基础,精选明隆万之后时文251篇,旨在使诸生知晓行文体格及因题立义、因义遣辞之法,以之为式,体会时文写作要领。因为自雍正帝降谕提倡清真雅正之旨后,凡科举衡文,无不以此为标准,天下风行,趋之若骛,但作为古文家的姚鼐,对此四字别有心得。他说:“文贵清真雅正,著在功令。然作文者或不尽解。夫所谓清者有三:有气清。气为文家最要事,必其极清,然后能雄、能大。不清,则虽庞然而实痿矣;又有思清,测之窈然而深者,思清也。凡猥浅近者,思不清也;又有辞清。辞欲其典,典则清矣。如汤临川文,可谓极华,然清之至也。所谓真者有三:审经文上下之义,则脉真;深思圣贤之旨,则理真;摹写曲尽,则情真矣。所谓雅者有三:命意雅者,存乎胸襟;立格遣调雅者,存乎稽古;然胸襟之雅,亦学问之力也。夫辞调似为文之末事,然文之神气,实寓于此。调俗则神气亦随而薄劣矣。古人之调不必同,同归于雅而已。所谓正者,则专论文体。夫正嘉以前正于隆万以后,江西诸公正于云间诸公。然就其所长论之,亦犹皆可谓之正,以其有学古之功,非从剽窃来也。束书不观,中无所解,剽窃因人,苟且凭臆,怪诞为妖,庸暗为晦,文体若此,亦何由而得正乎?”⑤(清)姚鼐著:《敬敷书院课读四书文》卷首《序目》,清道光十三年陈用光序本。关于清真雅正的阐释,时人体察圣意,应声附和,而又见仁见智,各持己说,但从辞章角度进行解读且如此清晰透彻者,舍姚鼐外,别无他人。
无论怎么说,姚鼐以书院为阵地,以古文为号召,以时文为助益,在敬敷书院讲学期间,确实培养了许鲤跃、姚莹、刘开、鲍桂星等一批英才,扩大了桐城派的声名与影响。更直接的成效还在于,当广大书院生徒将姚鼐传授的古文、时文创作技巧运用到科举考试中,搏取功名,显扬文坛政界时,桐城派的传播也就获得了稳定而快捷的渠道。姚鼐弟子陈用光于清道光五年(1825)校士两江时,“两江人士莫不访求姚先生之佚书轶说,家置户习,以冀有冥冥之合于众。而先生之学,遂愈彰于时。”[8]道光十三年(1833),陈用光督学浙江,立即重刻姚鼐所纂《敬敷书院课读四书文》,希望学子们研习此书,明了经训之旨,进求经史百家之言。陈用光还亲自传授解读该书,他认为先师的四书文选,对于生徒能够起到“为人为学由博返约之功可渐以次第”的作用 。①(清)陈用光著:《太乙舟文集》卷六《重定姚先生四书文选》,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由此亦可知这本书在当时影响之大。
姚鼐与敬敷书院的再次结缘,已是嘉庆六年(1801),其时,年已71岁的姚鼐以年衰体弱,畏涉江涛,由江宁钟山书院改主于此,为时四年,至嘉庆十年(1805)复主钟山。限于史料,姚鼐在敬敷书院的更多事迹,不可详考,但从他此期留下的诗句来看,他的生活相对恬淡,心情也异常平和。如《敬敷书院值雪》:“空庭残雪尚飘萧,时有栖鸦语寂寥。久坐不知身世处,起登高阁见江潮。”[4]又如《不寐闻江声》:“忆昔乘舟遍远征,和风恶浪每殊情。同舟死丧身今老,欹枕江声入皖城。”[4]表达了作者内心沉静而略显落寞的心绪。
与执教钟山书院相比,姚鼐在敬敷书院执教的时间没有那么长,交游没有那么广,生徒也没有那么多,但却是他四十年教育生涯中承先启后的重要阶段,其间,不少青年才俊在他的教诲下成长起来,其中知名者有如下数人。
许鲤跃,字春池。桐城人。姚鼐首次主讲敬敷书院时相从问学,后于乾隆六十年(1795)中进士,任镇江府学教授,著有《春池文钞》十卷。姚鼐称自己“论说学问,必崇古法,盖世人所谓迂谬者;春池时独能信吾说而不疑,余固贤之,知其异矣。”当其五十寿辰时,姚鼐作序为贺,誉其为“笃行君子,而沉思好学。为文华美英辨,而切于理。”[4]298后又以《古文辞类纂》及《春秋左传补注》二书相赠。许鲤跃捧书诵读,“载忻载忭”,激动不已:“盖以先生古文,鲤跃受业敬敷书院时曾读《答鲁挈非书》数篇,继来京江,又从友人处钞读《书制府寿序》数篇,已餍于口而饫于心矣,然恨未读其全也。今裒然大集诸体悉备,得焚香讽诵于明窗净室之内,远之不啻与司马迁、昌黎、欧阳诸公相坐对,近之不啻与震川、正学及同乡望溪、海峰诸先生相追随,听其言论而聆其指授也。幸甚感甚!”至于姚鼐《春秋左传补注》,许鲤跃亦有评价,谓“仰见先生好古之深而著书之勤,然其所补者义理多而考证少,亦望溪说经之意,皆程朱之学,而与徒夸博涉者不同也”。许鲤跃另著有《四书一得》、《五经一得》,重在推阐前人未尽之义理,著作完成后曾请姚鼐批点[9]。
许鲤跃之外,姚鼐此期培养的弟子还有歙县诸生鲍嘉命(字鸾书)。姚鼐曾作诗相赠:“我如山径断行轩,臃肿枝柯大树存。节目何由能待问?青黄久已谢为樽。披榛客自非流俗,歧路谁当见道原?共对小庭芳草积,林风吹晚更无言。”[4]鲍嘉命之父去世,姚鼐为之作墓志铭,其中提到“嘉命及其长子壬子科顺天举人桂星,皆尝问学于鼐。”[4]鲍桂星对此曾有解释:“先大夫曩从问学,桂星尝以诗贽,先生目为海内少年之冠。邮书敦勉,岁时不绝。”②(清)鲍桂星著:《觉生感旧诗钞》卷二《感旧诗》,清嘉庆庚辰刻本。至其面受教诲,当在姚鼐转任歙县紫阳书院时,鲍桂星《觉生诗钞》卷七有《紫阳书院呈姚姬传先生》一诗。其后姚鼐转向钟山书院,他又时来问业,世人视之为姚门嫡传。
姚鼐在敬敷书院的高第弟子还有江西新城鲁仕骥(挈非)和桐城刘开、姚莹等。前者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初见姚鼐,“人观其言动恭饬有礼,而知其学之邃;读其文冲夷和易而有体,亦知其必为君子也”。他开启新城古文一脉,回乡后以姚氏古文传授同乡子弟及外甥陈用光,三年后又将陈用光荐于姚门,使之终成桐城派古文宗师。“新城古文之学日盛,其源自君也。”[4]刘开于辛酉(1801)之夏,“随姬传先生来皖江。”③(清)刘开著:《刘孟涂集·文集》卷七《师荔扉明府诗序》,清道光六年姚氏檗山草堂刻本。姚鼐对他寄予很大希望,常谓人曰“此子他日当以古文名家,望溪、海峰之坠绪,赖以复振,吾乡之幸也”。“孟涂(刘开字孟涂)既游姚公之门,名益著,绝迹千里,笼罩靡前。”①(清)刘开著:《刘孟涂集·前集》卷末陈方海撰《刘孟涂传》,清道光六年姚氏檗山草堂刻本。姚莹为姚范的曾孙,姚范与姚鼐亲如父子,对姚莹自然疼爱有加。姚莹参加府试苦无资费,姚鼐赠金相助。姚莹参加科试住在敬敷书院,姚鼐在生活上予以照顾,更教以学问文章之事。姚莹成进士步入官场后,依然不忘著述,遂成一代名家。姚鼐卒后,桐城学人一度视姚莹为“继宗”。王灼说:“吾乡峣然杰出、继惜抱先生系海内望者,唯足下而已。”②(清)王灼著:《悔生文集》卷二《答姚石甫书》,清刊本。
三、结束语
从刘大櫆算起,桐城派作家在书院中讲学的人数,有案可查的近百人,且各阶段的代表人物都与安徽书院有着或深或浅的渊源。他们在安徽书院的讲学,最主要的贡献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建立了桐城派书院教育的基本范式。桐城派书院教育的特点:一是注重古文义法的传授,也很重视经学讲授与时文写作,时文与古文并重。二是注重教学相长、自由争鸣。三是注重开门办学,所收生徒没有门第出身和地域的限制。四是注重课本的编刊以及生徒之间的相互呼应。在课本编刊上,既有古文选本,也有时文讲艺的选编。生徒之间,相互切磋,谈文论道,交游频繁。
其次,促进了书院所在地文化的发展。即如安庆一府,虽据古皖、桐、舒、黄诸国故地,但长期以来,“文字之奇,艳称千古者,率出其邻郡,而兹地无闻焉。其文士著名史传者,宋李公麟辈数人而已。地僻隘,化导无人,虽有奇士,未由而自振也。”及至清朝别安徽为一省,而以安庆府治为省城,“其后又建立敬敷书院,召诸生肄业其中,延贤士大夫退居林下者为山长以主之。四大吏合山长,月二课,抚部岁一甄别,皆用意,不视为文饰具。由是,安庆文才日迈乎前代。”③(清)管同著:《因寄轩文集补遗·刊刻敬敷书院课艺序》,清道光十三年管氏刻本。可见,敬敷书院对于安庆人文的兴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增进了不同文化区域的相互交流。清代经学以新安及其一系的学者成就最为突出,堪称乾嘉汉学的高峰。其时,桐城人士与新安人士一样尊崇程朱理学,却轻视考证之学,而以古文扬名天下。徽州、桐城,作为清代学术文化的典范区域,如双峰并峙,二水分流,而刘大櫆就是沟通这两个区域的文化使者,方宗诚说:“海峰老为学官于徽,徽之学者经其指授,多以诗文成名。退居于家,则惜抱姚氏既以其所闻于海峰者为一世文章之宗。”④(清)方宗诚著《柏堂集·后编》卷四《江待园诗钞序》,清光绪方氏柏堂遗书本。由此推知,后来姚鼐提出“义理、考证、文章”之说,或与刘大櫆这段徽州讲学经历对他的启示不无关系。至清代中期,姚鼐的门生已逐渐在徽州各书院占据讲席,客观上增进了安徽省内两大区域文化的相互理解与交融。
[1](清)施 璜.紫阳书院志[M].合肥:黄山书社,2010:278.
[2](清)刘大櫆著,吴孟复标点.刘大櫆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3]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4](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5](清)姚鼐著,姚永朴训纂,宋效永校点.惜抱轩诗集训纂[M].合肥:黄山书社,2001.
[6]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M].合肥:黄山书社,1989:139.
[7](清)姚莹.中复堂全集·东溟文集[M]./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1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1-1973.
[8](清)梅曾亮,彭国忠等校点.柏枧山房诗文集[M].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35.
[9]江小角,方宁胜.桐城明清散文选[M].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11:143-144.
[10]铢 庵.人物风俗制度丛谈[M].上海:上海书店,1988:87.